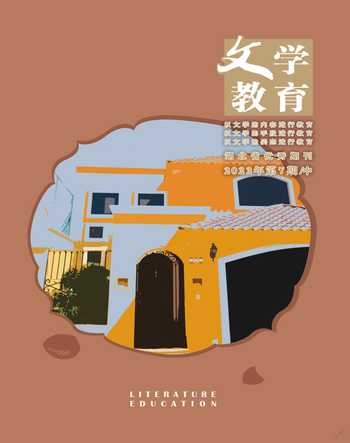巴金笔下民族危难中知识者的众生相
韩婷

内容摘要:纵览巴金建国前的文学创作,他笔下众多形象恰好可以构成旧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编年史。从代剥削阶级家族忏悔,到小资产阶级个体的忏悔,其间充满了痛苦和辛酸,巴金与他的主人公们,带着青春的激情,挣扎奋斗,终于迎来新中国的曙光。
关键词:巴金 知识者 民族 青年
1938年巴金开始了他的第四个三部曲——“抗战三部曲”《火》的创作。当时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日本侵略者的野蛮狂焰,引燃了全中国人民心中的复仇烈火。在这个大时代里,知识者个体的痛苦和哀伤统统被淹没在抗战的洪流中,不同出身、经历的青年们,抛弃了旧的生活,以清新的面目出现在抗战的前线和后方。
一.火一样热情的青年学生
贯穿于这个三部曲的主人公冯文淑就是这千千万万个青年中的一个。这个满脸稚气、一身顽皮的女中学生,中止了学业,不顾商人父亲的反对,毅然去到伤兵医院中当护士,为抗战尽力。她的两个女伴朱素贞和周欣也都勇敢地冲破了心理上和现实中的重重障碍,进入抗战的民族的大家庭中。当时,把个人命运连系在民族的命运上面,成为一代青年的人生准则。当民族的不幸需要每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分担的时候,他们必须首先解决“国”与“家”的矛盾、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矛盾。对于前者,在普遍抗战情绪的感召下,问题似乎不大;如冯文淑,父亲的阻挠完全是因为不明抗战的意义,只担心自己的家产受损的自私的考虑,这怎能敌得过女儿的坚定信念?周欣母女的互相依恋、牵挂,最终也被抗战的大义所战胜。但对于后者,事情要难办得多:刘波、朱素贞这对恋人,为了抗战,必须马上分手。公与私、义务与感情在他们心中起了激斗,当认识到个人在时代中的渺小的时候,他们决心为了民族的利益,牺牲个人的幸福。在这些青年身上,人们既看不到“五四”时代小资产阶级因家族压抑摧残所造成的创伤和痛苦,也看不到二、三十年代,小资产阶级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因屡屡碰壁,而形成的病态的软弱和疯狂,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新的信仰,带着这样的信仰,他们自觉去经受战火的洗礼。但徒有抗战的热情与不知如何抗战的矛盾又苦恼着青年们。和大学生刘波的活动联系着的鸣盛、子成、永言、老九等青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热衷于暗杀活动。这一点与《灭亡》里的杜大心和“爱情三部曲”里的敏极为相像。不同的是,他们开始对这种斗争方式感到恐惧和厌倦,希望“搞较大的公开的活动,有更多更多的人参加,我们正面攻击敌人”,而这又是不切实际的空想。那么,在抗战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发散自己的青春能量呢?巴金以《火》的第二部为他的人物解决了疑惑:走向战场,发挥自己的特长,做宣传鼓动工作。为此,巴金舍弃了“刘波在上海做秘密工作”的线索,权力描写冯文淑们参加战地服务团的活动,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在抗日的烽火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逐步磨炼成长。
《火》的第三部反映的是大西南国统区的生活,描写一个具有虔诚的基督教信仰的知识分子田惠世,为了宣传抗日,殚精竭虑筹办刊物,受到出版当局的种种阻挠,最后含恨而死的感人故事。
田惠世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博爱和殉道是他精神的一个侧面;作为正直的现代知识分子,爱国又构成了他精神的另一个侧面。在抗战的时代,这两个侧面自然融合起来,使他不辞辛苦办《北辰》,默默地为抗战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和非基督徒冯文淑、朱素贞的交往、交流,特别是儿子世清的死,动摇了他的宗教信仰。他不再为了爱生命的缘故才来拥护抗战,认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在抗战方面都是一样的。他们在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两代知识分子殊途同归,虔诚地坚守“祖国永不会灭亡”的信念。
二.知识者个体的忏悔意识
40年代在西南大后方的生活,又为巴金提供了认识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人生和另一部分百姓的世相的机会,他不停地观察着、思索着,把雾一般的压抑感和色彩灰暗的人间景象写进他的“人间三部曲”和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
“人间三部曲”之一《憩园》写于1944年,在此之前,巴金曾在1941年和1942年两次回成都老家,这部中篇小说的创作动机当产生于这两次故乡行之后,面对易主他人的老宅和五叔病死狱中的可悲结局,巴金心中不胜感慨:20多年前,就是在这个家中,许多年轻可爱的生命惨遭礼教的迫害,被剥夺了生命、爱情和自由,一切仿佛历历在目;如今,他又看清了家族的另一种罪恶;用财富把它的子孙培养成爱慕虚荣、墮落、沾染寄生性的败家子、废物。憩园的旧主人杨梦痴和新主人姚园栋的儿子小虎就是这样的例子。巴金借杨、姚两家的不幸,再次代他早已叛离了的旧家族做了忏悔。无论诗酒风流的杨梦痴,还是蛮横刁钻的小虎都是制度的产物。这一点早有人论及,此处不再赘言。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作家通过姚园栋、万昭华和黎德瑞这三个人物形象,所体现出来的知识者个体的忏悔意识。
姚太太万昭华读过书,没到姚家时,下人们都说她是“新派人物”,怕她花样多。可小小的憩园无情地消磨着她的青春,束缚她个性的发展。三年时间,她由新派人物退为旧式女人,掌管家务、服侍丈夫、教育儿子。除了看书消遣,或偶尔去看看电影外,她的活动天地只限于憩园,其寂寞程度可想而知。养尊处优的生活际遇使她“像一只笼子里长大起来的鸟,要飞也飞不起来”。她把残余的一点青春活力转化为美丽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帮助人,把自己的东西拿给人家,让哭的发笑,饿的饱足,冷的温暖。”这个“好心的女人”敏感地意识到丈夫及家庭命运的隐忧,恳请黎先生给予帮助,却不知道自己正是需要拯救的。她的眼泪和叹息告诉人们:她对自己的生活处境无可奈何。
与万昭华的了无生趣的生活不同,姚国栋生活得悠然自得,自我感觉良好。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产,过上了末代地主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历史性的退步。他对太太、儿子和小小憩园的夸耀,对自己写作才能的浮夸自信,无不表现出没落途中的愚蠢和可悲。
作家黎德瑞是一个思想深处怀有很大矛盾的人物。他目睹了杨、姚两家的悲剧,既厌弃又怜悯,同时又深深自责。他早已脱离了剥削阶级家庭,坚信“活着为自己的理想工作是一件美丽的事”。把“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奉为人生理想和创作宗旨。眼前发生的一切使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与失败。黎先生的自省融入了巴金的切身体验,他说:“我写《憩园》的时候,对这些好心女人的命运的确惋惜,我甚至痛苦地想,倘使她们生在另一种社会里,活在另一种制度下,她们的青春可能开放出美丽的花朵,她们的智慧和才能也有机会得到发展和发挥,总之,她们不会像在旧社会里那样做一辈子的寄生虫。”[1]
三.知识者隐忍苟活的心灵弱点
当人们还沉浸在憩园那种窒息、压抑的氛围中的时候,我们的作家已经进入《第四病室》。自然,这里的情景更为阴沉、可怖,但女大夫杨木华的出现,犹如严寒中的一点光亮,给人以慰藉和希望。杨木华这一形象可视为作家理想的化身,她与《憩园》中的万昭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者生活在封建文化的无形巨手之下,生命苍白、贫血;而她从外在到内里都散发出健康的生命气息的青春活力。尽管环境同样压制她的正常发展,但在一定范围内,她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来减轻病人的痛苦,实现要别人“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人有用些”的人道理想。
在战时的国统区,像杨木华大夫这样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凤毛麟角,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注定他们在大时代中很难有所作为:“兼济”固然难以做到,“独善”也鲜能保全,很多人在浊世中浮沉,上演着一幕幕的人生悲剧。《寒夜》中的汪文宣和曾树生就是这样的大多数。《寒夜》笼罩着浓浓的忏悔意识,围绕着汪、曾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巴金对知识者的人格、思想意识等做了较为深刻的忏悔:把当时普遍存在于知识分子中间的隐忍苟活的心灵弱点曝光于世。汪文宣和曾树生曾经是敢于蔑视封建礼教、有追求的青年,自由恋爱,进而同居,共同怀着献身教育的理想。但现实阻断了他们实现理想的路,一个沦为洋行的“花瓶”,一个屈居图书公司校对的职位。战乱、动荡的环境和家庭经济的困窘,迫使他们穷于应对,疲于奔命。尽管如此,家仍然面临着破裂的威胁。在这个四口之家中,三个主要成员互相牵制,构成直接或间接的敌对关系。“知书识礼”的汪母满脑子封建意识,对树生与儿子的“同居”、做“花瓶”耿耿于怀,恶语相加;母慈子孝的传统意识成就了汪氏母子的联盟,对付树生,而且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又使他们不甘心接受让树生养家糊口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树生只好逃离家庭。这一过程表明:封建主义在破坏新式家庭方面的巨大潜力。曾树生离开家庭,继续在个性解放的道路上滑行,她不苟且,珍惜青春,追求幸福,但她一直处在“花瓶”的位置上,会有什么出路呢?
汪文宣是一个处在社会和家庭双重压迫之下,在贫困潦倒、疾病和受歧视的境遇里挣扎,最终走到生活的绝路的小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在生活中处处苟且、敷衍、怯懦、忍让、必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黎明前的寒夜中。
抗战时期,巴金还写了一个反映现实的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不留情面地勾画出苟活、自私、庸俗的渺小的人和渺小的事。大后方苦难人间凡俗生活的林林总总,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之处。如《猪与鸡》中的冯太太因猪和鸡与邻居的龃龉、纷争;《兄与弟》中金钱对亲情的侵害;《夫与妻》中隐含在吵嘴打架中的封建意识的披露等等。作家在描写这些琐碎生活的时候,倾注着对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命运的热烈关怀,有讽刺和批评,也有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但更多的还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式的忧患意识和无力改变芸芸众生不幸处境的忏悔意识。
巴金的“抗战”和“人间”三部曲及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把民族危难中知识者的生活面貌和心理现实凝于笔端,对那些被封建文化窒息了灵魂,被小资产阶级软弱性葬送了生命的知识者,进行了严厉的灵魂拷问;对那些把个人前途和民族命运联系起来,发散青春的激情,充实自己的生命的知识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们像在战火中涅槃的凤凰,让生命和青春在自焚中获得新生。
四.知识者的人格理想
纵览巴金建国前的文学创作,巴金真可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从杜大心到汪文宣,他笔下众多形象的连缀,恰好可以构成旧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编年史。巴金和他心爱的主人公们,像一群命定的殉道者,不屈不挠地奔向自己的目标,热情始终不减。
写作初期,巴金借人物之口骄傲地宣称:“我不怕,我有信仰!”70年代末,巴金仍满怀信心地说:“我还有热情,我能写!”此时,巴金已是年逾七旬的老翁,他有续写现代知识分子编年史的打算。尽管未能如愿,但他的五集《随想录》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遗憾。被誉为“现代忏悔录”和“巴金暮年的伟大完成”的《随想录》塑造了现代知识分子巴金的自我形象,他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叉点上,以人类爱为心灵的底蕴,与民族共忏悔。
以深沉的社会责任感追溯民族灾难的悲剧根源,这是《随想录》的一个基本精神。巴金痛彻地感到,在这场浩劫中,最大的悲剧莫过于人的价值的失落和人格的惨遭践踏。他极为痛惜地谈到了老舍、杨朔、远千里、杨丽坤等作家、艺术家在“文革”中的厄运。他们一夜间就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也谈到了爱人萧珊等普通善良者的不幸。是谁造成了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究竟谁之罪?随着林彪、江青一伙的覆灭,这已是昭然若揭。
巴金把这场民族灾难看成“和全人类有关的大事”,认为“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写下我们的经验,不仅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别人,为了下一代,更重要的是不让这种‘浩劫再一次发生。”作为“以人类之悲为己悲”的作家,巴金在反思这场民族灾难时,还表现出可贵的自省意识,这是《随想录》的又一个基本精神。巴金说,他写《随想录》就是在“挖掘自己的灵魂”。在《随想录》的部分篇章中,他毫不掩饰地列举自己在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他做这些事情,绝非自愿,更不是率先发难,他“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而已。为什么自己会一再地做这些违心的事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己在政治上的幼稚和自私的动机。他说:“我相信别人,同时想保全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待呢?”这种内疚和自责始终纠缠着作家。在《小狗包弟》中,他写道:“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在《怀念老舍同志》中,他又写道:“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巴金对个体人格的忏悔由伦理道德层次深入到社会历史层次,使人们看到:盲从、愚忠和活命哲学决不是发生在个别知识分子身上的个别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已经积淀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习惯和自主意识,这就构成了民族灾难和个人不幸的主要悲剧因素。巴金的自我剖析鞭辟入里,挖出了自己由“奴在身者”到“奴在心者”質变过程的悲剧实质:对强加在自己和其他许多无辜者头上的种种罪名,由怀疑到默默接受,再到主动地“苦行赎罪”,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被扭曲了,悄悄滑向失落的边缘。炼狱的痛苦使巴金从催眠术中警醒过来,从1969年开始,他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逐渐摆脱奴隶哲学,为弄清是非而苦行。这段曲折的心灵历程代表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随想录》蕴含着对人类、民族的使命感和个体的人格理想,表达了反驳时代的荒谬和迷误,重建人的尊严和历史的庄严的企盼。
在巴金的艺术世界里,我们无法保持闲庭信步式的优雅姿态和悠闲心态,很难冷静,也很难客观,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痛苦焦灼和热情执着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征服了我们。这种阅读体验要归因于作家心灵的力量,巴金把自己浓浓的忏悔意识和滚烫的青春激情全部融化在他的艺术世界中,这是他区别于他人的艺术个性,也是我们从不同方位剖析巴金创作的导引。
参考文献
[1]巴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1[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324.
(作者单位:沈阳开放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