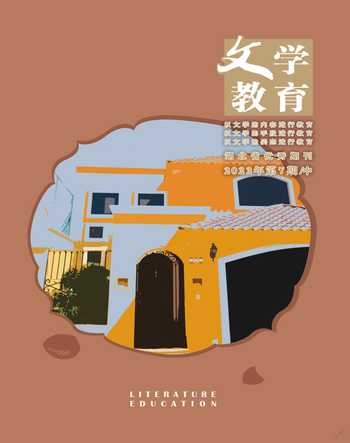论史铁生作品中的残疾主题
周瑶
内容摘要:史铁生作品的残疾主题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逐渐深刻的过程,即从自身的残疾经历出发,在书写人类痛苦不堪的身体残疾的基础上发现与挖掘生活中无所不在且难以消解的精神困境,并立足于“残疾”,以充满哲思的眼光寻找超越深渊的途径,最终在对生命和人格的思考中坦然接受残疾的局限,通过坚守“过程”价值走出了残疾困境。正是史铁生对人类困境与生存意义的苦苦探寻,成就了当代文学史中独一无二的残疾书写。
关键词:史铁生 残疾主题 精神困境 超越困境
关于史铁生作品中的残疾主题,史铁生曾谈道:“一切人都有残疾,这种残疾指的是生命的困境,生命的局限,每個人都有局限,每个人都在这样的局限中试图去超越,这好像是生命最根本的东西,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归到这里。”[1]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史铁生作品中的残疾主题书写尤为深刻并颇具现代性,它跳脱出个体狭隘的生命经历,直逼人类心魂的最深处,指引人们洞悉自身困境的同时,以超然的人生态度坦然面对生命苦难,积极探寻“生之意义”。
一.“残疾”的人:书写肉体的残疾
切身的残疾经历催生了史铁生笔下一个个生动的残疾人物形象,如瘫痪的青年、侏儒症女孩、老瞎子和小瞎子、天生的弱智等等。如史铁生所言,他的作品存在一个转变,“大概是从1985年左右(我说不准,仅仅是感觉)开始转变”[2],在这个“感觉开始转变”之下,作品中对人物肉体残疾书写的关注点呈现出逐渐减弱的转变。
史铁生前期的残疾书写大多与自身经历有关。作品以观照现实为主,书写身体的残疾经历,文风沉重,委婉凄凉,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对命运不公的抱怨和痛苦的情感,对生命的思考多停留在肉体残疾的现实层面上。《午餐半小时》叙述了车间的工人们畅想着被豪华轿车撞伤将得到丰厚的赔偿,甚至一份正式的工作、儿子的婚房都能得到解决。与沉浸在“向往”“欣喜”“如愿以偿”的氛围中格格不入的是沉默的双腿瘫痪的青年。一边是对赔款的热闹畅想,一边是艰难自保的残疾青年冷静地算着微薄的工资,在荒诞的对比中一个身处苦难但敬畏生命的残疾人形象跃然纸上。《足球》讲述的是双腿瘫痪的青年山子和小刚摇着轮椅去看足球比赛的故事。即使只有一张票,即使明白根本上不了体育场的台阶,仍然不顾炎热地一心前往。对生命的热爱追求和不屈夹杂着残疾与爱情的苦涩,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仅显得温情,更有了明亮的色彩。《夏天的玫瑰》中讲述一个下肢瘫痪而忍痛离开爱人到城市独自艰难谋生的老头儿,遇到一对年轻夫妇正在努力医治极有可能成为残废的孩子。老头儿百般纠结之下还是劝慰夫妻放弃孩子,于深受漂泊与偏见之苦的老头儿而言,这是对生命的更高意义上的“人道”。以及《白云》中思念着一个南方姑娘的双腿瘫痪的作家等形象,作为一个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残疾人无法消弭与健康人群之间的芥蒂,无法消弭常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残疾文化的历史。实现史铁生前期残疾主题作品转折的是《山顶上的传说》,小说刻画了一个艰难写作、痛失爱情但坚持探寻“生之意义”的青年形象。一个双腿瘫痪的青年作者在爱情和谋生中深切地体会到“歧视也是战争。不平等是对心灵的屠杀”[3],一度陷入精神的痛楚中。同时,他又不懈地寻找着丢失的鸽子,这象征着一个固执地思考生活与命运、寻找希望的过程。与以往的残疾形象不同,《山顶上的传说》中的青年没有延续因身残导致的凄凉悲愤的心境,而是勇敢地接受了身体的局限,开始从精神的绝境中走出。
史铁生后期的残疾主题作品在总结对残疾经历的现实关照的基础上,呈现出具有超现实意义的形而上的深刻思索。这个时期的作品对肉体的残疾书写有所减弱,而更多关注于在冥冥未知的思考中探究整个人类的精神困境和社会人格的价值,作品深沉而又平和,飘渺而又理性,同时不失机智的幽默。《原罪》中瘫痪卧床的十叔给孩子们讲述神话时总把身体健全、自由自在地游历世界的主人公置换成自己,“您想象一道阳光罩住一张木床,在阳光中飞舞的是他的灵魂,在阳光中死去的是他的肉体”[4]。十叔以神话作为精神的依托寻找活着的理由,表面的自欺欺人实则是一个病骨支离的青年对现实和理性的精神超越,以一己之力为寻找“生之意义”探索一条解释得通的途径。《命若琴弦》刻画了行走在山野间的一老一少瞎眼说书人。老瞎子心怀执念,弹断一千根琴弦,取出师父放在琴槽中的治疗眼病的药方。而当得知追求半生的药方不过一张空空如也的白纸,五十年来以此为生的希望和饱满高昂的精神力量瞬间坍塌。小说的结尾,他同样将这份虚妄的希望告诉小瞎子:弹吧,弹断一千二百根。师徒三代摆脱残疾困境、追求光明生活的形象和心境在对人类命运局限的哲理思考中得到深刻的演绎。《宿命》同样讲述一个被命运捉弄的残疾人。莫非在出国深造前夕发生车祸导致双腿瘫痪,他回溯那天的每一个时间节点,最终发现大好前程不偏不倚毁于一个荒唐的狗屁,小说最终以一个荒诞可笑的理由消解了命运无常的痛苦。《务虚笔记》中徘徊在残疾与爱情之间犹豫不决的残疾人C是作家史铁生的映射。作者在书中跳出现实主义的务实思考而关怀人的精神和形而上的生活本质,注重书写人类生命中真实的印象。在务虚思想的表现之下,残疾人C最终克服身体的残疾,成就了与恋人X的婚姻。以及《我之舞》中的四个分别代表着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残疾阶段的残疾人:我、路、世启和老孟等残疾人形象,与前期作品中的残疾人形象相比,后期的人物形象仍旧囿于肉体的残疾困境,但生命的光芒同时得以显露,“生之意义”在无法改变的肉体残疾中得到探索。
二.人的“残疾”:发现精神的困境
在表现残疾人艰难的生活处境的同时,史铁生思考着人类命运普遍存在的精神困境,实现了从单纯书写残疾的肉体到探索人的精神残疾困境。“我曾经说过人有三大根本困境:第一,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欲望,这意味着痛苦。第三,人生来不想死,而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5]无所不在的孤独、求而不得的欲望和无法摆脱的死亡困境构成了史铁生作品中主要的精神残疾书写。
关于人类普遍的孤独困境,史铁生曾说:“人最初的处境是孤独,因为人都是以个体身份来到群体之中。你只能知道自己的愿望,却不知别人都在想什么,所以恐惧。”[6]在史铁生的作品中,孤独不仅体现在身体的残疾和沟通的芥蒂,更体现在个体之间心灵的隔阂和距离。《我与地坛》中写道:“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7]彼时的主人公自身尚且不能接受突如其来的残疾,更无法面对外界的偏见歧视和刻意的同情,因此地坛成了一个孤独避世的所在。无效的交流导致的孤独也是人类普遍面临的心境。小说《礼拜日》中,即使是两个都渴望坦诚无隔的人也本能地对对方生出防范与猜疑。模糊暧昧的语言和隔靴搔痒一般的交流,使得自身与他人和外界的贴近触摸显得毫无希望。史铁生的作品道出了人性内心的限制引发的孤独困境,即使生活在群体之中也无法实现彼此间彻底的坦诚与理解。由于心灵的隔阂而产生的孤立无援更具杀伤力,史铁生的作品中多次出现“墙”的意象,象征着人心之墙的隔离导致的孤独。《墙下短记》回忆童年时在伙伴的怂恿下,主人公在和最好的朋友L打完架后向他要回了曾送给他的礼物。朋友的失望可想而知,主人公也沮丧而归,“独自贴近墙根我往回走,那墙很长,很长而且荒凉……”[8]此时的“墙”成为一道鸿沟隔断了友谊,酿成了两个朋友之间难以逾越的隔绝。人心高高的围墙使人陷入了普遍的孤独困境,它横亘在人与人、人与外界之间,无形地见证人性最孤独的时光与心境。史铁生曾在《爱情问题》中谈到,善恶观和羞耻感带有原罪的性质,是人类社会的独有记忆,“每个人的心灵都要走进千万种价值的审视、评判、褒贬,乃至误解中去,每个人便都不得不遮挡起肉体和灵魂的羞处,于是走进隔膜与防范,走进了孤独。”[9]可以想见,千万种价值观下的孤独、隔离及其所导致的痛苦和对沟通的渴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永恒的困境,也是无所不在的难以解脱的困境。
人类的精神困境还体现在求而不得的欲望本性。相对于孤独困境而言,欲望更为牢固地存于人心。叔本华认为生命最终的目标在于满足欲望,而理想中的满足又是难以实现的,欲望的无限延伸与人类力量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求而不得的欲望困境。在史铁生的作品中,人的欲望多表现为对爱情和健全的身体的欲望。《原罪》中十叔的生命由不断扩张的想象和欲望支撑,他通过墙上的七面镜子窥看窗外的景象,想象远方白楼里人家的生活,想象每晚走过窗前的人,羡慕探险的科学家,以致不禁忘我地代入其中的角色。无奈上帝在他无穷的欲望和身体的限制之间划下了一道无法弥补的距离,“欲望无边,能力有限,是人类生来的困境。”[10]《命若琴弦》中,能够看一眼这个世界是指引老瞎子卖力活着的唯一欲望。小瞎子的欲望除了光明和“曲折的油狼”,更多源自对女孩兰秀儿的思念。然而师徒两人的欲望皆是求而不得,欲望固然代表了人对生活与自我的热爱与追求,但也必然因欲望落空而陷入失望的困境。欲望之间互相催生,若无法实现便一直心存欲望,现实与欲望之间永远有或远或近的距离,所以欲望的困境永恒存在。《山顶上的传说》中写到:“现代人得到一座别墅的幸福,不见得比原始人得到一块兽皮的幸福大;现代人失去一次晋升机会的痛苦,也不见得比原始人失去一根兽骨的痛苦小。”[11]时代几经更迭,物质条件飞速发展,然而欲望之下生活却像是从未改变,只因人不断有所求而不断地置自身于求之不得的困境之中,因此人类的欲望困境永恒存在。
史铁生对死亡的思考多以普通人,尤其以身患疾病而喪失了平等人格的残疾人的视角出发,思考人类无法摆脱的死亡困境,其中夹杂了作者个人独特的生命思考,呈现出反英雄、审美化的倾向。在史铁生的残疾主题作品中,作者对死亡的思考呈现出一个明显的转变,从最初懵懂的思考和冲动到最后对死亡的理性思考和超越,史铁生从个人的现实体验出发完成了对人类普遍的死亡困境的形而上思考。史铁生在前期作品中对死亡的思索显得朦胧、恐惧,或在突如其来的挫折面前对死亡表现出强烈的渴望。《插队的故事》中主人公主动对死亡进行了初步的探问。那时的“我”尚未经历深恶痛绝的残疾,不知道死亡带给生活的意味和感受,正是在懵懂之下开启了对人生死亡困境和“生之意义”的思考历程。而在《我二十一岁那年》中,主人公在确诊残疾之后对死表现出激烈的情绪,“我终日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心里先是完全的空白,随后由着一个死字去填满”[12]。肉体的痛苦或许尚可忍受,遭遇社会群体的抛弃、习惯性的疏离和同情而产生的孤独自卑和悲观绝望则逼迫残疾人将解脱困境的希望更直接地寄予死神。史铁生后期的作品呈现出对死亡的理性思考和超越。海德格尔认为,“面对死亡人们才可能摆脱世俗功利、个人物欲的局限,摒弃一时一地的恩怨、悲观、离合等世俗的幸福与痛苦,此时人便可以立于一个超越生死的至高境界,升华出对人生的艺术性审视。”[13]人往往在遭遇艰难之中得以深刻地认识自己,一如少年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某个时间节点,残疾人的崭新的生命意识也在绝望痛苦的精神困境中得以形成,并以此超越自身的局限。史铁生对死亡困境的思考和超越即是精神上的改变,他在痛苦不堪的人生节点上追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在陷于死亡困境的苦苦挣扎中顿悟了生与死的认识。如《我与地坛》中写道,“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14]彼时的史铁生以淡然超脱的生死态度思考生命的意义,死亡的困境固然无法摆脱,但却无需摆脱,因为出生和死亡都是自然的事情,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有始有终的生命过程。宽容达观的生死觉悟还将史铁生的人生观从个体的死亡困境升华到宇宙生命的视角。个体的死亡并不影响宇宙文明的绵绵不息,个体的生命同人类的精神文明一样一如既往地得以延续。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无法摆脱的死亡困境恰恰也是人类生命获得延续的根源,“死,不过是一个辉煌的结束,同时是一个灿烂的开始。”[15]
三.走出“残疾”
从被迫承受身体残疾的局限和个人命运的无常,到以更宏观的视角关怀整个人类与生俱来的精神困境,史铁生在他的作品中深刻地表达了对生命的追求和对苦难的反抗。“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16]尤其在史铁生后期的作品中,主人公在超越现实生命与死亡的宗教精神中勇敢地接受了自身的残疾局限,并通过坚守“过程价值”走出了残疾的困境。
人类所面对的身体或精神上难以自救的困境可以使人对生活对生命产生一种新的态度和心境,彼时,上帝的力量便得以显现。史铁生曾在访谈中提到,“宗教精神是清醒时依然保存的坚定信念,是人类知其不可为而绝不放弃的理想,它根本源于对人的本原的向往,对生命价值的深刻感悟。”[17]于经历了特殊的生命体验的史铁生而言,是这份“信念”、“理想”的宗教精神引导其作品中的人物首先突破了坚硬的精神困境,开始接受自身肉体的残疾局限和生活中的苦难遭遇,迈出了内心获得救赎的第一步,并以超越性的眼光看待人类永恒存在的精神困境,“接受天命的限制。接受残缺。接受苦难。接受墙的存在”[18]。但接受难以消解的现状、命运和苦难并不意味着放弃,而是以平和的心态消解残疾导致的苦难与恐惧。史铁生认为,自身的不能行走与优秀的运动员无法突破极限在本质上是两种相同的情况,证明人类的局限普遍存在。因此,接受残疾的宿命和与生俱来的局限,接受人终将死亡的结局,而达到内心精神力量的自我塑造和超越。《原罪》中十叔和父亲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平静超然的心态,他们内心早已消解了对多舛命途的怨恨,冷静地接受了残疾的命运。十叔善于思考、讲述、观察,他在充满想象的神话中超越身体的局限,实现灵魂的飞舞,父亲则一心只为儿子治病而辛苦劳作,他们一起选择理性地接受同时以各自的方式坚持对生活的希望。同样强调接受苦难、接受局限的还有《好运设计》,无苦无忧、全知全能本是人的妄想,一生好运加身只是舒适与平庸,甚至在命运的最后必须承受一笔痛苦不堪的总账。因此,承受不幸才是拥有好运的保证,这是史铁生选择接受困境的逻辑。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假设了一个没有苦难的、无差别社会的存在,然而没有愚钝、丑陋、恶劣和残疾,机智、漂亮、善良和健康便都失去了意义,对立的存在意义本然如此。三代师徒,软骨症女孩,瘫痪的莫非,最终都像宿命论者一般坦然地接受了自身的残疾命运,并领悟到一切苦难都有其合理的因素。直面和接受生活的苦难,这一具有浓重的宗教精神的人生态度,是史铁生虽身陷生命的绝望处却仍旧能够超越深渊的力量,如史铁生所言,这一精神的力量“能使人在知道自己生存的困境与局限之后,也依然不厌弃这个存在,依然不失信心和热情、敬畏与骄傲。”[19]
史铁生在书信《给希洛》中写道:“应该把欲望引向过程,永远对过程感兴趣,而看轻对目的的占有,便是正当的欲望。”[20]史铁生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延伸“过程”而非虚设的“目的”本身,人类自身能够通过努力而把握的仅仅在于一个生命的过程,可见,坚守“过程”价值是史铁生及其笔下的残疾人走出残疾局限的有效途径。《两个故事》中的陌生人在仇恨中生活了几十年,老三早已备下毒药起了自杀之心,自己的复仇反而成了一种无心的帮助。陌生人用苦不堪言的几十年生活换得一个虚无的结局,荒诞而可悲的结果从反面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引向了生命的“过程”。《命若琴弦》中老瞎子最终将药方重新放回琴槽,只为将生命的“过程”哲学再次传授给下一代。作者将生命的“过程”比作琴弦,将人类生命的力量寄托在一个不断拨弄琴弦以求得光明的老瞎子身上,其意义全在不停地行走和弹奏的“过程”中了,药方的存在只為引出一个不断为之奋斗的精彩的生命“过程”。“过程”终止而只剩虚设的“目的”,生命的意义便也随之终止,“得到的只能是过程,理想本身不是为了实现的,他只是用来牵引过程,使过程辉煌,使生命精彩”[21]。如作者在《足球》中所表达的,观看一场足球不在于重视最终的输赢,而在于关注精彩纷呈的球赛过程。坚守过程价值的本质在于真正洞察了“目的”的虚无后全神贯注于生命的“过程”本身,正如史铁生在《好运设计》中提到:“过程!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22]因此,为了避免陷于“目的”的虚无意义之中,人类在生活中需要把专注力从“目的”转向生命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史铁生.史铁生作品全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陶国立.“生之意义”的探寻[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5.
[3]肖婵丹.绝境中的突围[D].重庆:西南大学,2010.
[4]陈亚利.超越深渊的路径[D].保定:河北大学,2020.
[5]王印梅.史铁生小说的“自叙传”性质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21.
注 释
[1][2][5][17][19][21]史铁生.史铁生作品全编·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175,207,176,178,178, 178.
[3][11]史铁生.史铁生作品全编·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71,324.
[4][15]史铁生.史铁生作品全编·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04,189.
[6][18]史铁生.史铁生作品全编·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345,189.
[7][8][9][12][14][16][22]史铁生.史铁生作品全编·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36,248,260,78,36, 15,71.
[10][20]史铁生.史铁生作品全编·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13,180.
[13]肖婵丹.绝境中的突围[D].重庆:西南大学,2010.3.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