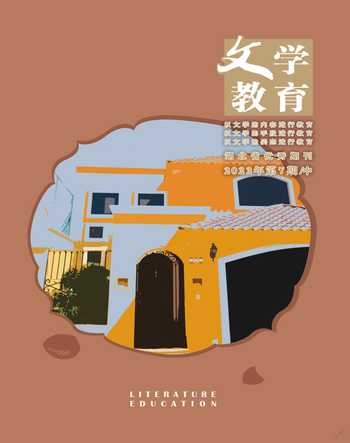吕先觉小说对底层叙事的深度开掘

在小说创作中,湖北作家吕先觉秉持民间叙事立场,直面底层社会真实,贴近底层人物的灵魂,着力表现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纷繁的矛盾和复杂的情感,表现人在那样的生存绝境中所迸发出的顽强的生命力和柔韧精神,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并以独特浓郁富有质感的语言风格,以细腻绵密的细节描写、内敛饱满的叙事语调、灵动曼妙的艺术手法,叙述当下乡村真实发生的人和事,细腻地再现了当下乡村的场景。在展现身处社会底层小人物生存境况与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彰显出一种丰沛沉郁的审美内涵。
发表在《芳草》2009年01期的中篇小说《失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艺术标本,尤其是对作家如何面对眼下的现实,处理当下变革现实中的乡村社会生活及人的命运的转折,并把这一切化为魅力又感人的作品,做出了成功的尝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失地》抓住了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个问题的核心展开叙事。这个小说的深度在于黄磷厂侵占了土地把丁歪歪陷入了困境,千方百计把儿子牯牛争取了进厂当工人,不料儿子被烧伤,险些丧命。丁歪歪迫于生计,在河边一块杂草丛生的乱石岗上“造地”。这是一块无人涉足的荒地,丁歪歪靠一筐筐地背土,建了二分地。按理说这块地的所有权应归丁歪歪,可黄磷厂设法抢占,逼得丁歪歪以死抗争。为了侵占这块土地,工厂和土地局修改了契约,并利用现代法律手段,将丁歪歪告上了法庭,最终,丁歪歪的土地再一次被剥夺。丁歪歪被逼上无路可走的绝境,于是就在这块地头打井,躺在棺材里服下黄磷把自己烧死。丁歪歪死了,这块地黄磷厂也放弃了,丁歪歪以死为残疾的儿子牯牛争取到了这二分地,以死对剥夺了他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权利作最后的挣扎和抗议!这何尝不是最摧人心肺、悲惨凄凉的控诉呢?這最后的抗挣,为他毫无色彩的一生,留下仅有的,也是最后的一抹色彩!可惜,这最后的一抹,却点染了他一生的命运,成了他生命中唯一的底色:凄凉!
发表于《福建文学》2011年第8期,后被《小说选刊》选载的短篇小说《土豆回家》,是吕先觉的代表作。小说内容丰赡扎实,题旨多向,艺术结构圆熟而灵活,笔锋直指人物心理和人物角色充满奥妙的心理嬗变。小说表面上讲述的是乡村草根茂贵执意要为矿难中殉难的儿子土豆奔尸回家,让土豆入土为安,不让其火化时“一阵烟冒了”的故事。其实,在吕先觉的文学自觉里,那是乡村草根最后的一丝自怜,是茂贵内心最隐忍不住最真实的疼痛和呐喊。茂贵把自己的儿子取名“地瓜”和“土豆”,虽认同了自己生命的卑微,但并不认同自己生命的卑贱,这是茂贵要把土豆的尸体奔回家真正的文化意味。可是在奔尸回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痛心地看到他们遭受到的人格践踏,而且还遭遇到补偿金的非法掠夺。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看到了人性的异化、人性的弱点、人的生存困境。更有深意的是,在还来不及舔慰自己失去儿子巨大的悲痛之时,茂贵已决意要去儿子殉难的那个煤矿打工了。这是吕先觉温情的话语中最严厉的冷峻,好似一柄带着倒钩的矛,扎进去见血,拔出来带肉。正如他的同学蒲亨享在《土豆回家》的评论中所言:“《土豆回家》里只不过是一个永远缺席的文化符号,即使奔回尸来,也还会缺席。他们的文化缺席,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永远难以释怀的精神感伤。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让土豆‘一股烟冒了,更像是我们民族精神生活的一场国殇。”
中篇小说《狗眼爱情》发表在《延安文学》2011年06期。这部小说是吕先觉对权力、对人性冷静地观察之后,给人以耳目一新和出其不意的一击。小说以一只充满灵异的狗来作为小说的叙述视觉,构思新颖、奇异、巧妙,这是吕先觉的匠心独运。小说描述手法和语气构建舒缓有致,充满一种诗学意境;小说刻画的两对主人公:人二奎和人蓝眉以及同样名字的狗二奎和狗蓝眉。作为叙述主体的狗二奎以狗眼看世界,这个封闭的乡村世界是哀婉凄清的双线结构:主线与副线,或明线与暗线,通篇是狗二奎的哀叹,但字里行间却表露出人二奎的压抑和痛苦。一些怀想、忧郁、渴望、绝望、期待、等待、委屈、复仇等元素,都围绕着痛苦的神经而颤动。这种痛苦来源于贫穷的现状、来源于心里抑或生理的渴求得不到补偿的压抑、来源于(与村长对比的)人格不平等、来源于对命运的不屈和反抗。最终,他向命运挑战,以一柄利斧,宰割了欺男霸女的村长的阳具以及他的公狗的阳具。当人二奎报仇泄恨之后,他对着远山发出野狼一样的低吼声。这是对被压制人性的控诉,是对自我意识觉醒的呼唤!
吕先觉的小说,写作视角倾向于生活真实,文字质朴,情感细腻,笔下的人物形象也都非常的朴素,贴近生活本色,字里行间透着真情,浸染自然清新的乡土气息。作者是用心在写自己的生活感受和所见所闻所思,创作姿态尤显真诚。
发表于《天津文学》2015年第4期,被《小说选刊》2015年第6期选载的短篇小说《体面的牙齿》,延续了吕先觉朴实厚重的叙事特征,如乡间泥土一样本色自然,却自有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小说中的“父亲”在母亲去世后看似迷上了剪纸,实则心心系念的是教他剪纸的芸老师:上城来不顾儿女的担心直奔书店去寻找关于剪纸的书籍、拿起遥控器急急搜寻有关剪纸的节目、为了“不糊牙齿”忍痛戒掉抽了一辈子的旱烟锅、最后放下长辈的尊严向儿子借钱去安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这一切无不表明年迈的父亲要在所爱的芸老师面前展现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但是,在儿女们面前,他爱得那样小心翼翼、那样谦卑隐忍,丝毫不敢有所流露,更不敢有任何要求。小说中的“我”及父亲的其他子女不可谓不孝,但他们对“孝”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养”的层面,却缺乏对父亲应有的精神关怀,对父亲内心深处的情感渴望仍然是迟钝与隔膜的。直至结尾才谜底式揭晓——原来这一切行动无不关乎父亲想要的“体面的牙齿”,而终极谜底则是为他心中的“芸”。小说在叙述中敞开了“父亲”五味杂陈的情感世界与永远失去父亲之后“我”的深深自责与忏悔。
短篇小说《妇科病》发表在《芒种》2016年第16期。这个小说叙事俏皮,读起来轻松、愉悦,没有负荷感。小说很简单,讲的是农村留守妇女精神上的空虚与寂寞,都以得了妇科病为由求得乡村男医生号脉触摸,获得性的慰藉。写留守妇女性饥渴的小说较多,堪称经典的有晓苏的《花被窝》。同样是写婆媳人性关怀,《妇科病》另辟蹊径,对于“情人”,小说完全省略,而把这个角色集中在一个村医身上。采用大量雷同的场景描写婆媳俩的性幻想,不妨摘录如下:黄麦就那么轻轻一按电钮,她手腕上小闸门就嗡嗡嗡地打开了,紧跟着无数毛毛虫就成群结队涌进来……毕小杏感觉自家身体正被毛毛虫一口口地咬小,一口口咬空,小得空得如一片羽毛,正打药房门口轻轻地飘起,颤颤悠悠地飘起,一直飘到外面场子上空,一直飘到半黄麦田上空。他这么将电钮轻轻一按,麦浪就顺着阮启秀胖手腕上小闸门一缕缕地涌,一股股地涌,一片片地涌……麦浪涌进的时候鸟叫声也跟着一起涌,先是斑鸠叫声,后是布谷叫声,黄莺叫声,再后来是八哥叫声,画眉叫声,鹌鹑叫声,山喳子叫声,软娘子叫声,嗯,差不多石桶村所有鸟叫声都跟着麦浪一起涌进阮启秀身子里去了。
这种写法既突出了人物心境,又增加了小说的幽默感。在生活中,没有两个不同的场景能完全复制。这实际上是夸张的写作手法的巧妙运用。同一场景的重复出现,在吕先觉的小说中并不鲜见。这也是他小说的写作特色之一。
吕先觉的小说有自己独特的让人迷醉的叙事语境,让我们感到扑面而来的浓郁的乡村草根的语言气息,语言颇有当年周立波的流风余韵。他的语言是感性的,抒情的,色香味俱全的,和人物的内心情绪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尤其是带有地域特色的简洁、明朗、多义和质感的方言俚语,会不时地粘住读者的眼睛:“狗日茂贵,你莫骇我”“一股煙冒了”“鼾是鼾屁是屁的”“精壮溜锤的”“脑壳梳得光滴滴的,蚊子落上去都甩跟头。”“久而久之,他办公室顶板都给薰黄了,厚厚一层像是焦锅巴,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砸着人的脑壳。”“太阳早升到一竿子高了,天上云彩白得很,一朵一朵的安安静静,像在坡里吃草的羊群。”“金灿灿的阳光下,地瓜土豆的坟看着像两个安静睡着的孩子。”“一到夜晚,月亮打小院对面的山上升起来,蛙声便应时而起。河水也赶趟儿似的,隐隐约约地响着,像是老太婆对着自家水缸嘀嘀咕咕,又像是牛铃在深山密林里叮叮当当。”
吕先觉大多写的是乡土小说,但一点都不土气。正如刘恪所说,吕先觉对当下乡村生活现象的把握,含有很现代意味的思考。这大体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看,一是现代乡村确实被现代性技术概念所改造,生活方式已经不传统了。二是吕先觉处理乡村材料不拘泥于旧有的元素,而是参照了世界小说的新技术。例如梦幻,荒谬,反讽,元叙述等手段。三是文化语境的变迁。今天是读图的传媒时候,人们自觉地接受了电子信息技术。生活细节的现代性导致了文学表述的新媒体化。吕先觉的写作不传统,反而是传统与现代比较的基础纳入了新的元素。
多年来,吕先觉执着于用自己的作品构筑精神家园,把作品的深刻立意视为小说的命根子。在创作思想境界、生活深度和艺术高度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和风格。他的《土豆回家》《日天峰》《流星划伤夜空》等一批短篇独出机杼,富有创新性、开放性、可能性、探索性、实验性,体现了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创作态度,毫不疑问,这是当代小说的重要收获。他在自树标杆,挑战自我的写作过程,极大地丰富、拓展着小说写作的审美空间。他是身怀绝技、特立独行的侠客,是理智、冷酷的解剖师,在塑造小说人物的同时,他也在塑造一个与众不同的自己。
党世根,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湖北省竹山县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