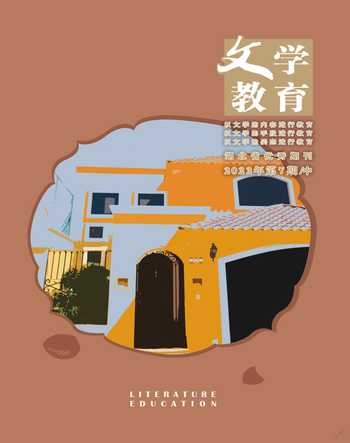外公的院落
杨璐

满满一场院阳光,金灿灿的,一尘不染。阳光裹着细小的草粒,我仿佛都能听到它们轻柔的呼吸。
多少次,在梦中,我站在这场院里。
一栋白墙黑瓦的土屋,屋前,一块夯得平整坚实的黄土大场子。它坐落于一个名叫紫阳的村子,位于穿乡而过的沮河之畔。大门前的沮水,一路集結其它细流至此,宽阔的河面显出浩荡之势。
走进堂屋大门,左手边是两把鄂西北乡村常见的木椅子,椅间一张小方桌。右手边摆放着两张单人沙发,中间是一张小茶几,沙发旁各一把木椅子。你坐他的椅子,是不能随意搬动位置,或坐在那儿摇摇晃晃的。堂屋正中间是一个高条几,几前一张方桌。高条几上,放着几个保温瓶,被排成了一条线,士兵排队似的。物件整齐划一的惯性思维已像一棵大树的根系,永远根植于外公的大脑之中。
那堂屋高条几的右边,一直放着一个“甜薄脆”盒子,里面总是装着一些饼干蛋糕之类的零食。每次去,他都会笑眯眯地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些来,给我和弟弟一人分一些。我们拿着零食边吃边玩,难免洒下一些碎屑。他就挥动着扫把,跟着我们扫。碎屑逶迤前行,他的扫把也跟着逶迤前行,他一声不吭。实在扫烦了,脸往下一拉,大喝一声:“你们都给我站这儿,吃完了再动。”我一看他阴云密布的脸,就不敢动了,吃得小心翼翼。
他最爱打扫,眼里容不得一点尘埃。
大清早,他的两棵高大的香橼树还氤氲着袅袅雾气时,他便开始打扫场子了。黄土场子里无非是些树叶与灰尘,他却睁大眼睛,一处都不放过,手臂用力挥动着一把浅黄色的长把竹扫帚,一扫帚一扫帚地,一块儿挨一块儿地扫着。那力度,那认真劲儿,都让我觉得他不是在扫,而是在刨。
檐下的走廊,屋里的水泥地面,一天中总是被他反复打扫。记忆中,他只要一有点时间,就会拿着扫帚不停地、使劲地扫,或是拿着一个棕黄的鸡毛掸子,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掸着桌椅柜凳上的灰尘,其实很多时候本无灰尘。
闲暇时,他都背着双手在房前屋后地转悠来,转悠去,若有所思。看到哪里的杂物摆放得不顺眼,就马上收拾收拾,如接到如山的军令一样,刻不容缓。连走廊尽头的柴禾都被他码得一丝不苟。
他的打扫每天如是。
那时,我正十二三岁吧,老师常对我们谆谆教导:人要有远大的理想。“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我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保尔·柯察金的这句话正深入青少年的心。精美笔记本粉红粉紫的纸页上,都印着席慕容和汪国真同样粉嫩的诗行。紧张的学习之余,满脑子都是诗歌和远在天边的梦想。
年少的我暗笑他的迂,认为一天之内这样没完没了的打扫,简直是对时光的虚掷。也曾对他这种没完没了的打扫生出一种不屑——人生的价值就体现在一把扫帚和一个鸡毛掸子上,永无休止地与屋里屋外的尘埃较着劲吗?有时,我坐在他那台黑白电视机前正看得入迷,外公突然伸过来的扫把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打扰。
多年以后,当我被城市的喧嚣重重围困,当我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奋力突围时,我开始思念外公的院落。
我开始在周末时一趟一趟行走于故乡。现在的乡下人家,已是一色的白墙红瓦的楼房,家家户户门前都是平坦光滑的水泥场子,场边多有花坛。可是,我走过许多家,哪一家的院子也不如外公的院子那么整洁、美观,我的思绪就像切换电视频道一样,一下子就跳到了外公的院落。
初夏的响亮阳光正一步步撤退,在场子边上拉出一道长长的斜影。外公、外婆、母亲和我正在场子里闲坐,微风捎来阵阵清香,那是场边的两棵桔树开花了,细小雪白的花开得正闹,我仿佛都能听到它们的声声喧哗。不远处,两棵高大的香椽树静静伫立一旁,风吹树叶,沙沙作响。一条独特的小径通向场子边,与屋旁的大路相连,那是外公为了避免雨天的泥泞,用一块块平整的石板搭摆而成的,如同小河里的搭石。
屋旁,一条常年流淌的水渠,渠水活泼,清洌。渠边,两棵葱郁的棕树如同一对姊妹,亭亭如伞。流水声、捣衣声、说笑声,不绝于耳。我曾看到外婆帮人拧床单,她们一人握住一端,往左右相背而拧,床单如麻花一样,水淋漓地就下来了。跨过横卧在水渠上的一块青色的大石板,上几步田埂,眼前,是一望无际、碧浪翻滚的夏日田野。屋后,平整方正的菜园也被外公外婆拾掇得一片葳蕤,一畦一畦的青菜,绿得耀眼。
隔着二十多年的漫漫时光,这一幅幅画面于我,依然清晰如昨。突然想起王安石“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的诗句,我竟感到外公与那位湖阴先生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这时,我才重新去打量他日复一日单曲循环式的琐碎日常,才觉得他的这种拾掇打扫绝不是简单的“讲卫生,爱清洁”所能概括的。
正对着堂屋大门的粉白墙壁上,挂着四轴一组的中堂画。是四幅山水画,画中有繁茂的山林,有曲径、巨石与潺潺溪流,每幅各题有一首五言古诗。算起来,那是我人生中见到的最早的中国山水画了。现在想来,连绵的峰峦,巨大的山石,茂密的树林,构图宏大,意境旷远。一石一叶,一沟一壑,均精笔细描,技法精湛。应是北宋山水画的风格,颇似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外公常背着手在堂屋踱来踱去,左看看,右瞧瞧,欣赏着他的中堂画,有时若有所思,有时满意地点点头。从严、写实的宋画契合了外公严谨的行事风格,旷远的意境满足了他的审美需求。年少的我也从那画中记住了一句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也曾多次想象着自己走进了画中静寂的山林,在墨色的山水间驻足流连。
堂屋右侧的里间卧室里,一张朴素的写字桌上,有个简易的木质两层书架。我曾坐在这里,借着旧式小窗透进的不太明亮的光,看过这些书。有高中语文课本,有《倚天屠龙记》。我跟随张无忌仗剑走天涯,沉迷于广阔的江湖、曲折精彩的故事情节中,欲罢不能。第一次感受到江湖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那大概是我接触的第一套金庸的书,当时并没在意作者是谁,直到后来又多看了一些他的书,渐渐记住“金庸”这一响亮如雷的名字。
他浅黄色的写字桌上,永远摆放着一摞折叠整齐的报纸,一个土黄色老式笔记本,一叠宣纸和一支小号毛笔。他有读报的习惯,直到八十多岁还手拿放大镜读着。他有时也会写写毛笔字,是很娟秀的蝇头小楷。他的识字写字是打小跟随他教私塾的父亲学的,后来去了部队,大多从事文书工作,给长官做秘书,帮战友们写写家书。
写字桌的边上,还放着一本厚厚的老式台历。白纸黑字,或白纸红字,很朴素。他每天翻过一页,这也是他的习惯。记不清是哪个百无聊赖的下午,我發现这台历中还藏着不少的东西——正中间是一个醒目的数字,下面是一段小字,写着那天宜做什么事,忌做什么事。我心想,还有这么多讲究吗?每一页的背面,都讲了一个生活小常识。如,秋燥要多喝雪梨水,常嗑牙健康长寿,等等。每逢一个节气时,都有相关的介绍,我从这儿认识了二十四节气。这小小的台历作用可真不小,难怪外公有时忘了翻页时会哎哟一声,拍拍脑门,疾走进去翻上一页。
他没事时便会背着手在房前屋后散步,这里看看,那里看看,盘算着还差点什么,再来点什么布置。
有一天,他开始在渠边的一小块空地上忙活起来。他用水泥砖垒起,砖洞里插上粗竹竿,做成四根柱子,再在顶上搭上木条。架子搭好了,他便在地上插上葡萄秧。他有事没事就转过去看看秧苗的长势。直到有一天,藤蔓爬满了架,长出了绿油油的叶子。夏日来临,阳光毒辣,他的葡萄架下一片阴凉。每到傍晚,外公就迫不及待地沏上一杯茶,拎着一把木椅子,坐于架下。他手执一把棕叶扇,一边喝茶,一边扇着,享受着自己创造的那片浓阴。
夏末秋初,渠边的蝇子又大又多,用扇子扇也无济于事,他坐上一会儿还是不得不撤到大门前的场子里。可是,他却不时地看一看那片绿色。那时的我,不明白坐在葡萄架下与坐在门前有何分别,撇嘴暗笑,看,坐不住了吧。
如今,当我越来越喜欢在乡间散步,喜欢流连于乡下人家的房前屋后,我终于明白,场院里有了葡萄架,外公的院落才更像院落,才是标准的田园人家。我也终于明白,人坐在葡萄架下,享受夏日里的一片阴凉,的确是件很惬意的事。
又想起我十来岁时,母亲和舅舅劝说外公锁上乡下的房屋,搬到县城居住,可一次次劝说均以失败告终,曾有一次,外公还大发雷霆。大家一致认为:这老头,太犟!
我这才知道,这个上过朝鲜战场的清瘦老兵晚年生活的寄托所在,他仿佛要把年轻时没使完的力气全都用在余生的家园建设中。日复一日的打扫与拾掇,就像是一场场战斗。原来,他那时已有了美化环境的意识。想到这儿时,我不禁对这个不厌其烦打扫庭院的瘦小老头肃然起敬。
如今,美丽乡村建设正如火如荼,乡村一天一天变美。蜿蜒的水泥公路修到各家门前,路边绿树成行。房前屋后,有桃红梨白,有花坛瓜架。门前,是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海,每天早晨,打开大门便可坐拥花海。房子一家比一家漂亮,可没有几家的院子是用心收拾的。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一有闲暇,便喊上三五朋友,喝酒吃肉,聊天吹牛,再打上大半天的麻将。从这家玩到那家,忙坏了女主人。
每当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外公的院落。眼前不断浮现出外公清瘦的身影:打扫场院的外公,读书看报的外公……
(作者单位:湖北省保康县实验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