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张立文先生学习不“照着讲”
林美茂 耿子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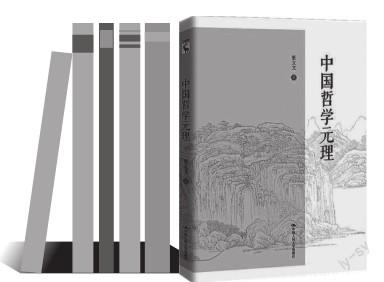
近年来,欧美哲学界出现新的动向,开始反思把“哲学”仅作为西方传统之特有学问的认识历史所存在的偏颇。一些学者认为,“哲学”与“艺术”乃至“宗教”一样,应该是以某种形态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2016年5月11日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由杰依·卡菲尔多和布莱安·梵·诺登联名的文章:《如果哲学不能多样化,那就附上表现其实相之名吧!》(If Philosophy Won,t Diversify Let,s Call It What It Rerlly Is)。这二人都是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前者研究印度哲学、后者是中国哲学的专家。这篇文章主要批判美国的大学对于哲学教育的封闭性,明确提出印度哲学、中国哲学以及其他非西方的哲学传统也应该与西方哲学一样,成为大学的哲学教育中应有的内容,哲学不应该被西方传统的哲学所垄断。于是,他们呼吁在日益多元化的当今世界,大学的哲学教育,应该抛弃西方对于哲学独占之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哲学认识。
正如所知,关于“哲学”在海外学界,基本上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至于“印度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等是否应该作为“哲学”来理解,人们在认识上有所抵触。其实这不仅是西方学界的现象,就是东方学界,比如日本甚至中国等也一样,一般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也不太愿意承认本国的传统学术属于“哲学”,也是有意无意地把“西方哲学”作为“哲学”的唯一标准看待本国的思想传统。对于这种现象,卡尔·雷彼得曾经批判近现代的日本学者否定本国的哲学传统,仅把近代以后研究西方哲学的文献作为“哲学”,而把近代以前的日本传统学术都归入具有降格意味的“思想”中。对此他尖锐指出,这是一种自己参与的西方知性的殖民化。中国学界何曾不是如此?一些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也看不起“中国哲学”,不愿承认中国也有“哲学”。虽然一些人并非真正对中国传统思想有什么研究,但却总是不自觉地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认为中国的传统学术不如西方的“哲学”,以自己对于西方的“哲学”研究作为学术优越感的资本,对于“中国哲学”颇有微词甚至表现出某种不屑。
当然,“中国哲学”研究界的前辈们,并没有因为那些质疑而退却,而是努力探索“中国哲学”以及建构区别于“西方哲学”的“中国哲学史”,留下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关于如何研究“中国哲学”,学界曾经存在着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的探讨,对此,张立文曾明确提出了“自己讲”“讲自己”的主张。他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上下卷)等,就是秉承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自信和“自己讲”“讲自己”理念而诞生的重要论著。最近,他的新著《中国哲学元理》出版发行,也是他践行自己学术理念的又一部大著。在这部论著中,张立文先生为我们展现了如何讲述“中国哲学”的探索精神。
如何看待“中国哲学”
在《中国哲學元理》“前言”中,作者张立文明确表明了对于“哲学”的认识。他说:
如果说philosophy原初的意义可理解为“爱智慧”,那么世界各民族都有爱智慧的哲学,都有“真知之爱”的思想之间无声的对话,构成反思思想的思想。
在此,作者把“爱智慧”作为沟通东西方学术本质共性契合点。当然,我们还需要辨别中国传统的“穷理致知”与西方哲学之“爱智慧”追求的本质不同。作者认为:
中国是中国的哲学,西方是西方的哲学,印度是印度的哲学,各有个性、特点和神韵。这里没有唯一的哲学,也没有哪种哲学能独霸哲学殿堂。
确实,如果从“爱智慧”精神而言,世界各国都拥有求知的传统与探索精神存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谁也不能垄断“爱智慧”的人类精神。也就是说,从“爱智慧”之求知的精神而言,东西方并没有区别,然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在关于如何对待“知”的认识上,东西方确实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所以才有了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的区别。
那么,何谓“中国哲学”?张立文先生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他认为那是“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哲学是‘为道屡迁‘探赜索隐的哲学”,其中有《周易》《道德经》《论语》《孙子兵法》《墨经》《四书章句》《传习录》《正蒙注》等一大批经典名著。
为此,要强调“中国哲学”作为“哲学”不逊于西方,就需要中国学者讲好中国传统思想中拥有怎样的哲学,有哪些具体的内容等。关于这些问题,张立文先生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研究,正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几十年如一日殚精竭虑,笔耕不已。他说是要遵循先哲的求知精神,秉承“循名责实”的信念,追求名实相符之“中国哲学”的确立。《中国哲学元理》,正是通过中国传统学术中所存在的一系列概念以及根据时代不同出现的不同范畴的发展史,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哲学”之“爱智慧”的思想特质、理论体系。
为什么要“自己讲”
然而,“中国哲学”自从诞生以来,就受到所谓“合法性”的质疑,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德里达,东方日本的著名学者津田左右吉等都有相关的言论。
黑格尔认为:“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之外”,因为在东方传统思想中“找不到哲学知识”。他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哲学史讲演录》)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在为《世界文艺大辞典》撰写的“支那哲学”词条中,同样对“中国哲学”提出质疑。他说:
支那哲学的称呼被一般地使用,但实际上这个称呼有问题。一般所说的支那哲学,如儒家、道家、墨家那样,即所谓诸子百家的总称。但那些都是关于道德、政治、处世术的教诲与考说,古代被称为“道”“术”或者“道术”。所谓学问,就是学习那些道,这不过只是实践的手段。这样学问赋予哲学之称并不妥当。
在这里,津田左右吉指出中国传统所重视的知识流于实用,否定对实际生活无用知识的探索,从而造成论证思维之正确与否的逻辑学不发达,这种质疑基本上属于黑格尔等西方观点的沿袭。而在21世纪初,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来中国讲学,同样表达了“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的观点。(王元化《关于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对话》)就这样,“中国哲学”作为“哲学”,一直受到西方乃至东方学界的质疑,其“合法性”问题始终纠缠着“中国哲学”。
正是德里达的这句话,引发了中国学界自2001年开始长达三年的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大讨论,并在2004年3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联合举办、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重写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的学术研讨会,把这场大讨论推向高潮。此次大讨论以及这次研讨会的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彭永捷教授和人民出版社方国根编审,共同收集、编选了4部相关论著(其中3部由彭永捷教授一人主编),于2011年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其实,在这次研讨会的前一年,张立文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论文,阐述了自己关于当时学界热门话题之“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立场。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围着西方文明中心论(包括西方哲学中心论)的指挥棒转。若如此,即使我们写了更多更好的中国哲学史,这些中国哲学史也只是西方哲学的注脚,是西方哲学灵魂在中国的复活或翻版,这将是中国哲学的悲哀!”“中国哲学决不能照猫画虎式地‘照着西方所谓哲学讲,也不能秉承衣钵式地‘接着西方所谓哲学讲,而应该是智能创新式地‘自己讲……中国哲学必须而且只能是‘讲自己。”(《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和学术精神,在其近20年后出版的新著《中国哲学元理》中与我们再次相遇。在该论著的《绪论》中,作者提醒人们:
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记忆和理论思维。其古典哲学思维是以表意语言和象形文字这种特殊的符号为媒体的,“象性”范畴,“实性”范畴和“虚性”范畴两两复合,构成与西方“爱”与“智”二元分裂异趣,具有象外有言、言内有意、爱外有智、智内有爱特性的重重无尽、奥妙无穷的和合精神意境。
所以,他认为不能把中国传统哲学放在源于古希腊的哲学“法庭”上审判其是不是哲学,也不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古希腊哲学“幽灵”一般地制约或支配。这种提醒或指摘,同样是在强调关于“中国哲学”,不能“照着讲”,或“接着讲”,应该我们“自己讲”,“讲自己”,讲述属于中国的“哲学”。
如何“讲自己”
那么,应该如何“讲自己”?讲什么?这是研究“中国哲学”,构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张立文在2003年就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我们应该“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话语本身的重新发现,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时代冲突的艺术化解,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时代危机的义理解决,讲述中国哲学自己对形而上者之谓道的赤诚追求,等等”(《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而在《中国哲学元理》中,他以《周易》之“天”“地”“人”之道為基本架构,并以阴阳论、柔刚论、仁义论对应天、地、人而展开论述,体系性地揭示了“中国哲学”独特而丰富的话语体系。其中对于“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核心概念、范畴,通过生生论、太极论、格致论、健顺论、修身论、诚正论等意蕴的论述进行系统呈现。在此基础上,概括出“中国哲学”之元贞利亨、体用一源、理一分殊、能所相资、不离不杂、内圣外王、融突和合等七大基本元理,并把这些元理放在和生论、道体论、体认论、常变论、中和论、明德论中进行对应性展开与论述,构建出中国哲学的完整理论体系。
张立文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致广大、尽精微的自成系统的哲学理论思维逻辑体系,它已经突破了希腊语词意义的形而上学。他要讲述的中国哲学元理,是中华传统思想中“关于宇宙、社会、人生元始的、最大的道理、原理”。这种元理,是一种建立在融汇、贯通、把握中华民族五千年哲学理论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为此,他把中国哲学定义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寻求阐发超越西方意义之“哲学”的中国哲学。
与西方之哲学始于“惊讶”的认识不同,张立文先生分析了中国哲学区别于西方,呈现着“忧思出哲学”的特点。关于西方哲学之“主客二元”与中国哲学之“天人合一”不同所产生的误解与批判,他分析阐述了中国哲学既有“天人合一”,又有“主客不杂”“明于天人之分”的思考特征,明确指出中国哲学中天与人、客体与主体的关系是精微而独到的,那“是一种具有奥妙而深邃的精神意味的境界,它是建立在主体自由的、普遍的、无限的中国哲学元理之上的”中国哲学之形而上逻辑思维体系。同时,对于中国哲学之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道”的问题,论著中分析了自先秦至近代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其“在先秦为道路、规则、方法;在秦汉为天人、太一之道;在魏晋南北朝为虚无之道;在隋唐为佛道之道;在宋元为理之道;在明清为心之道、气之道;在近代为人道之道”的不同特征,从而“构成了中国哲学元理逻辑体系架构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元始范畴”。正是在这种“道体”的追寻、探索中,形成了中国哲学之“历史与逻辑”“突然与必然”“万象与道理”“问道与道体”的道体思维方式。
作为一部阐述与建构“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原理性论著之《中国哲学元理》,它是张立文先生一直以来所倡导的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的理念践行与学海之钩深探源、穷理致知的“爱智”硕果。论著通过中国传统学术中所存在的一系列概念以及根据时代发展出的不同范畴之发展、演变史,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哲学”之“爱智慧”的思想特质、理论体系。该论著对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如此整体性梳理、分析、把握、阐发与建构,无论在我国学界,还是在世界的中国哲学研究界,都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中国哲学元理》所开创的“中国哲学”作为“哲学”之“讲自己”的“元理”性探索、研究,体系性建构、阐发,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文化软实力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作者简介:林美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耿子洁,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