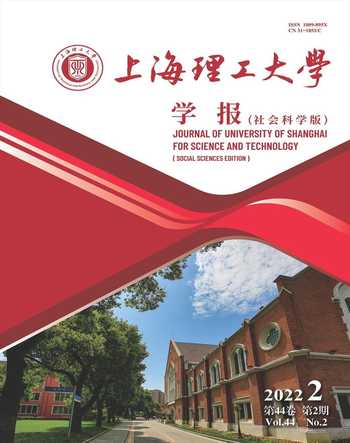接受美学视域下张培基的散文英译
杨晶雨 肖辉
关键词: 《匆匆》;接受美学;张培基;散文翻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 -895X(2022)02 ? 0130 ? 06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22.02.004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特色文化傳统的继承、传播和发扬在中国复兴发展的道路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文学作品承载着中国文化传统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学术界,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有大量学者把精力投入到对戏剧、诗歌和小说的翻译研究中,但是与此同时,对中国散文翻译的研究探讨却相对较少。散文也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类别,自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被人们广泛接受和使用,这为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散文作品中所蕴含的或灵动鲜活、或深刻隽永的思想和精神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和欣赏,因此,散文的翻译值得人们进行深入研究。
散文《匆匆》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散文家朱自清先生(1898?1948)经典的文学作品。本文以张培基先生《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1] 中所收录的散文《匆匆》的英译本Transient Days 为例,试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分析和探讨张培基先生的散文英译的风格特点和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并重点关注“期待视野”“视野融合”以及“未定点”三个接受美学的核心概念在散文翻译中的应用。在散文翻译中,这种以读者为中心的研究理论有效地缩短了中国文化与西方受众之间的距离,有利于西方的读者更好地接受中国散文和中国文学,从而提升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一、接受美学与散文翻译
接受美学理论,又称接受理论,是在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兴起于联邦德国的一种文学理论,主要由联邦德国康兹坦斯大学的一批学者所提出和倡导,这些学者主要包括姚斯(Jauss)和伊泽尔(Iser)。接受美学理论以阐释学和现象学为理论基础,是文学与艺术美学方面一股新兴的思想潮流,起初是文学界用于文学鉴赏与文学分析研究,后来逐渐被应用到翻译研究及许多其他领域。与传统的以作者为中心或者以作品为中心的文学研究不同,接受美学理论最基本和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以读者为中心,将读者看作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一。该理论研究者认为文学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第一位的,读者的审美接受与审美体验是第一位的,“没有读者参与的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是无法想象的”[2]78。
而这对于翻译研究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翻译研究领域,接受美学理论的引入使研究者的研究重点从作者和作品转向读者,翻译学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在翻译过程中译文读者的重要性,译文读者对于译文的审美接受是文学作品及其译文历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样的转变为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启示,开拓了全新的研究方向。此后,国内有众多学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不同类型的翻译文本做了许多研究。伍小君通过对《送元二使安西》四种英译本的评析,探讨了诗歌翻译的接受美学观,认为“诗歌由于具有特殊的文学和美学特征,其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表现得更加突出”[3]。张杰亨借用接受美学理论,对比分析了不同译本《简·爱》中对人物心理描写的翻译,认为译者应该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知识水平和审美经验,使译文符合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域,从而准确再现人物的心理与情感[4]。阮俊斌等学者以接受美学为理论指导探讨了葡萄酒名称的误译及翻译策略,认为翻译要贴近读者,把握读者的阅读习惯,而应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在舶来词的翻译中有很好的传神达意的效果[5]。李贝贝和杨燕分析了接受美学理论对于城市宣传片字幕翻译的启示,以《中国昆明》城市宣传片为例,认为译者在翻译时“要保持合适的审美距离,并达到译文与原文、译文与读者的视野融合”[6]。龙璐对西湖旅游宣传资料的英译做了译者主体性研究,并提出了增添法、删减法、直译法、省略法和意译法等翻译策略[7]。但是,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应用接受美学理论的翻译研究都是以小说、诗歌以及旅游宣传词、商标、广告等实用性文本为研究对象,很少有学者从接受美学理论的角度以散文文本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散文作为文学作品的重要形式之一,以其特有的方式和独有的韵味传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精神境界,展现地方的风土人情、人文风貌,具有极高的文化魅力和美学欣赏价值,因此接受美学理论在散文翻译中有很大的应用价值。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译文受众的审美接受具有重要意义,译者在散文翻译过程中要着重考虑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及审美接受。
二、接受美学视域下对《匆匆》译文的分析
《匆匆》是朱自清先生早期著名的散文作品之一,写于1922 年7 月,文章整体充满诗意,借春天的景色抒发了当时五四运动后读书人忧伤、压抑和苦闷的心情,表达了作者对时光飞逝的无奈和感慨。张培基先生对《匆匆》的英译文收录在其英译散文集《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中,除此之外,该散文集还收录了许多张培基先生其他的英译散文,包括鲁迅、夏丏尊、冰心、郭沫若等著名散文家的作品。通过接受美学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张培基先生的译文很好地保留和传达了原文的审美价值,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译文在目的语读者中的可接受性。
(一)关注期待视野
“期待视野”是姚斯在海德格尔的“先在理解(pre-understanding)”和伽达默尔的“成见(prejudice)”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任何一个读者在阅读某个文学作品之前,都已经具有先前的理解或知识了。如果没有这些先前的理解或知识,任何新的事物都是无法被读者所接受的。”[2]132 由于过往的阅读经验及社会经历的影响,读者在阅读作品前会产生一种先入的理解或思维定式,而这样的一种定向期待决定着读者对作品的审美接受能否有效实现,译文的美学价值能否被有效传达。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文读者的审美经验和期待视野是译者需要重点考虑的一个因素,而张培基先生对散文《匆匆》的翻译就很好地考虑到了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
例1 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1]55。
译文 Like a drop of water falling off a needlepoint into the ocean, my days are quietly dripping intothe stream of time without leaving a trace[1]57.
文中“像针尖上一滴水”译为“like a drop ofwater falling off a needle point”,原文通过喻词“像”,将“日子”明喻为“针尖上一滴水”,而译文中保留了原文明喻的修辞手法,通过直译把原文中的本体、喻体和喻词翻译为“my days”“a drop of water”和“like”,完美地保留了原文意象的审美感受,原文中,作者采用流水的意象来比喻时间,时间流淌如流水飞逝,而译文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时间流逝如流水悄无声息的意境。同样,原文“滴在时间的流里”译为“dripping intothe stream of time”,译者将“时间的流”直译为“the stream of time”,因为“时间如流水”不仅仅符合中国人的认知概念,同样也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接受。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有众多诗人以流水为喻,抒发对时间飞逝的感慨与无奈,如“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外国文学史上同样也有类似的比喻和描写。由此可见,在“时间如流水”这一概念上,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我们是一致的,因此译者在这里采用直译的译法充分考虑了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同时可以更好地保留原文的审美感受。
例2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1]55。
译文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away[1]57.
文中“给了”翻译为“be entitled to”,意思相当于“be given to”,原文中的主动句在译文中变为了被动句,更符合英语使用者的语用习惯,后文“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意译为“my quota ofthem(days)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和原文一样同样表达了“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的意思,表达了惋惜无奈的感情,但是通过“them”这个代词代指前文的“日子”,意为时间,更符合目的语英语使用代词指代前文出现过的重复性词语的表达习惯。同时“wear away”一词使原文“渐渐空虚”这个表述更为具象化,体现出时间逐渐被消磨和耗尽的感觉。这是在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与原文不一致的情况下,采用了意译的方式使译文更好地贴合译文读者的审美接受和期待视野,在文字表达之外更好地跨越了文化界限,引起译文读者的反响和共鸣,使原文的审美效果和审美感受最大可能地在译文读者身上重现。
(二)实现视野融合
伽达默尔认为:“视野是一个范围,包括在某个特定点所看到的一切事物。”[8] 也就是说,随着观察地点的变换和历史时间的推移,视野是会有所变化的,在此基础上,姚斯提出了“视野融合”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文化背景和生活学习环境下,人们会具有不同的视野,而“视野融合”指的就是读者的期待视野与作品的视野相融合的过程。这是接受美学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尤其是对于其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只有当读者的期待视野与作品文本的视野相融合时,才能完美地实现译文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审美接受,才能更好地实现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具体包括译者的期待视野和原文文本视野的融合,以及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和译文文本视野的融合。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尤其需要注意原文作品的知识背景和译文读者的生活经历,采取合适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融合两者的视野,做出适当的调整,同时也需要关注自身的期待视野。在散文《匆匆》的英译中,张培基先生就很好地实现了这样的视野融合。
在词汇层面上,由于英汉语言在词汇层面上的差异,译者在选用词汇时应该根据译文读者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历,使译文读者的视野和作品文本视野相交叠,尽量选择在含义上与作品文本词汇有重叠的中英文词汇。
例3 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去,从我脚边飞去了[1]55。
译文 Aware of its fleeting presence, I reach outfor it only to find it brushing past my outstretchedhands. In the evening, when I lie on my bed, it nimblystrides over my body and flits past my feet [1]57.
文中连用的“从……(手边)过去”“从……(身上)跨过去”“从……(脚边)飞去”三个动词,分别译为“brush past”“stride over”“flit past”三个英语动词短语,选词非常恰当合适,在保留原文拟人修辞手法的同时,更丰富具体地描写出了“时间”偷偷溜走时悄无声息的轻悄情态。译文选用“brush past”暗含时间从手边轻轻掠过时有形似羽毛的轻巧和悄然无息,表现出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匆匆溜去,同樣“flit”意为掠过、轻快地飞,更具象化地表达了原文中“飞去”的意思,表现出时间的飞快流逝。因为在中英文词汇的差异中,相对于中文词汇对于动作的概括性描写,比如“过去”“飞去”等,英文中对动词的描述和分类更为细致具体,比如对应中文“走”一词的英文词汇就有“stroll”“tramp”“plod”“strut”等许多种,所以张培基先生的译文恰当地选择了符合英语读者期待视野的动词词汇,很好地融合了英语读者的视野与作品文本的视野,实现了译文读者对原文意象的审美接受和原文审美效果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再现。
在句式层面上,英汉两种语言在句式结构上也有很大的不同,英语注重形合,多采用关系词、连接词等显性衔接的方式来构造句子,通过句子中词汇屈折变化的形式来表达意义,多使用冠词、介词等功能词。而汉语是一种注重意合的语言,常常通过词汇间的语义连贯来构成句子,句子各成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主要依靠隐性的衔接方式表示。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灵活使用分合句、词序变换等各种翻译策略和技巧,在句式结构上做出适当的调整,使译文的期待视野与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相融合,从而提高译文读者对作品的审美接受和审美体验。
例4 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1]55。
译文 The sun has feet too, edging away softly andsteadily. And, without knowing it, I am already caughtin its revolution [1]57.
文中整体上由分号分隔的两个小分句译为两个独立的句子,由并列连词“and”连接,“and”起到了原文中分号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英语显性衔接的一种方式,点明了原文中暗含的前后文两个句子在结构上的并列关系和在语义上的因果关系。“挪移”翻译为“edging away”,通过“edge”一词的屈折变化,使用其现在分词形式作状语,表示出太阳移动的动作。将原文的两个小句连接为一个完整的长句,同时也表现出了两个小句间隐含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样都以“太阳”作为逻辑主语,更符合英语句子结构紧凑,逻辑关系紧密的句式特点。第二个句子中,“茫茫然”译为介词短语“withoutknowing it”放在句子开头,使用介词“without”衔接前后文,“know”的现在分词形式“knowing”表示伴随,表现出句子内部的逻辑关系,同时也对原文的语序进行了调整,使得译文行文更为流畅,更符合英语重形合的特点,也更符合英语读者的语言使用习惯。因此,张培基先生的译本非常恰当地协调了中英文在句式结构上的差异,很好地实现了译文读者和作品文本的视野融合,实现了译文读者对作品的审美体验。
(三)关注“未定点”
“未定点(Indeterminacy)”是由伊泽尔(Iser)在茵加登(Ingarden)的理论基础上引入接受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概念。伊泽尔认为文学作品中遍布着未定点和空白,文学文本的意义中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主要是因为文学作品的对象和现实世界缺少有意义的连接[9]。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会根据自己的先在理解和先在知识、审美经验和期待视野,对文本中的未定点和空白进行填充,加以自己的解读,这个过程就是将不确定的意义“具体化(concretize)”的过程,也是文学作品意义的最终完成。散文行文神聚形散,表现手法多样,同样存在很多意义的“未定点”。译者作为原文文本的读者,会对原文作品中的未定点提出自己的理解,并且在翻译中将作品文本的意义具体化。与此同时,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想象,译文读者也会对译文文本有自己的理解。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译文读者的审美接受,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决定是保留原文的意义空白还是将原文的意义空白具体化。张培基先生在散文《匆匆》的英译中就充分关注到了对未定点的译法。
例5 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1]55?
译文 But, tell me, you the wise, why should ourdays go by never to return? Perhaps they have beenstolen by someone. But who could it be and wherecould he hide them? Perhaps they have just run awayby themselves. But where could they be at the presentmoment [1]57?
文中作者在开头采用了“为什么?”“是谁?”“何处?”“哪里?”四个疑问句来表现他对时间飞快流逝的疑惑、郁闷、沮丧和感慨的心情,作者在文中没有为这四个疑问句做出回答,这样意义的未定点为读者留下了充分的空白和丰富的思考空间。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和审美经验,所以不同的读者在阅读到此时内心会有不同的回答。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选择保留这四个疑问句中的意义未定点而没有将其具体化,直译为“why”“who”和“where”四个疑问句,充分保留了原文发人深省、引人思考的悠长意境,同时也符合英语读者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接受,与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句“Im nobody! Who are you?”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张培基先生在此处保留原文的空白是非常恰当的翻译方法。但是,同时也有译文需要译者根据自身理解和译文读者的审美接受将未定点具体化。
例6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1]56。
译文 Living in this world with its fleeting daysand teeming millions, what can I do but waver andwander and live a transient life[1]58?
文中“千门万户”译为“teeming millions”是对原文意义“具体化”的体现。“千门万户”一词在原文中意指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千”和“万”是虚指,意在表现世界之大和人数之多,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范围,但译者对这个词有其独到的见解,在翻译过程中添加了自己的解读,在数词前添加形容词“teeming”来表现人数之多、拥挤热闹的景象,同时考虑到英语读者关于数词的使用习惯,将其含义具体化为“teeming millions”,更符合英语读者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接受。后文中“徘徊”翻译为“ waver and wander”,“ 匆匆” 翻译为“ live atransient life”,也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其意义不确定性的具体化。“徘徊”一词在原文中的意义较为抽象,并没有特指某个动作,而是倾向于一种迷茫无所终的状态,每个读者对此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waver”和“wander”两个动词非常形象生动,“waver”是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的意思,而“wander”则是漫无目地漫游、闲逛。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英语读者的审美经验,将“徘徊”的内在含义具体地确定下来。同样,“匆匆”一词模糊地表现了一种时间飞逝,人生匆忙,白驹过隙的感觉,为读者留下了丰富的留白和想象空间。译者在译文中将其含义确定为“live a transient life”,通过“transient”一词表现出生命的短暂,转瞬即逝,同时也呼应了文章的题目“Transient Days”,很好地向译文读者传达了原文意象的审美感受。因此,考虑到译文读者的审美接受,在目标语中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将原文意义未定点具体化,可以更好地提升译文在目标语读者中的审美效果。
三、结论
本文运用接受美学理论,以张培基先生英译朱自清散文《匆匆》(Transient Days)为例,探讨了张培基先生英译朱自清散文《匆匆》散文翻译策略,分析了接受美学理论在散文翻译中的应用,主要包括“期待视野”“视野融合”与“未定点”三个核心概念,同时评析了张培基先生在译文中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和策略。通过研究发现,接受美学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应用到翻译研究中,可以帮助译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文本的美学价值,分析译文读者的审美经验,从而提高译文在译文受众中的审美接受效果。由于散文自由舒畅的写作风格,形式灵活,布局多元,“形散而神不散”,因此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散文的翻译不仅仅是传达原文的意思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更是传递一种审美体验。译者应通过翻译让译文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尽可能得到和原文读者在阅读原文时同样的审美感受。译者需要考虑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采取合适的翻译方法融合譯文读者和作品文本的视野,充分关注原文文本中的意义空白,即未定点。
随着中国在各方面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话题,而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文学作品的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接受美学理论突出以读者为中心,拓展了传统以原文或作者为中心的翻译研究视角,把研究重点转向译文读者,有效地缩短了中国文化与西方受众之间的距离,有利于西方的读者更好地接受中国散文和中国文学,从而提升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实现中国散文的美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外国读者阅读和理解中国散文的过程不仅仅是审美接受的过程,也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碰撞交流的过程,如此更好地促进了中英文读者之间的文化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