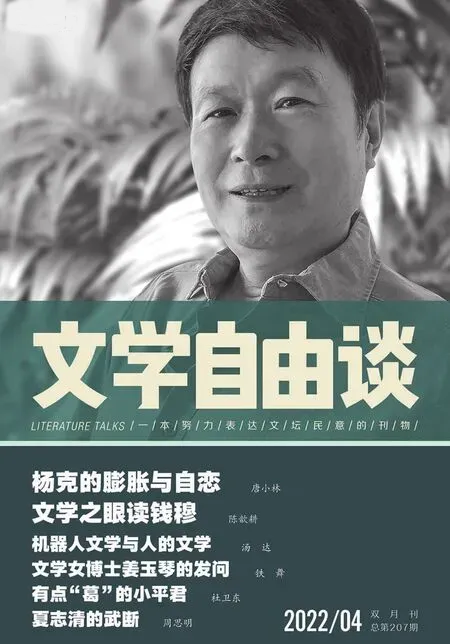《小说月报》第一届百花奖亲历记
□董兆林
打开记忆的相册,钩沉过往的影踪,往事依稀如昨。
那是1985年3月的初春时节。我二十二岁,入职《小说月报》刚刚七个月,便欣逢了刊物首创的第一届百花奖。当时这个奖项的名称叫做“《小说月报》一九八四年优秀中、短篇小说百花奖”。
《小说月报》此时已经创办了四年,盛名如日中天。当时在天津,有两份杂志可谓家喻户晓,一本是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八小时以外》,另一本就是我一脚跨进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小说月报》;说它在全国闻名,似乎也不为过。这一年,一项后来绵延了三十余年的文学活动——《小说月报》百花奖又顺势诞生。作为亲历者,当年的那番盛景很难忘却。这不单单是对一本刊物,以及由其襄举的一项文学盛典的怀念,萦绕心中的还有对那个文学“黄金年代”的留恋。
也可以说,那是一个和文学“热恋”的年代。每一篇在文坛引起轰动的作品横空出世,几乎都会带来万人空巷般的追逐。为了寻找一篇心仪的作品,刊载那篇作品的文学刊物便成了抢手货,传过几轮后,杂志黑黢黢的,仍让人爱不释手。当时很多省市级文学刊物的发行量,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篇有影响的作品致使洛阳纸贵,绝不是天方夜谭。应时而生的《小说月报》,在创刊仅半年,刊物出版到第9期时,发行量已达到一百八十七万份。此时,为了对办刊四年来的成绩有所总结,《小说月报》百花奖的设立,便成为编辑部乃至出版社的一件大事。
后来得知,早在1984年初,《小说月报》百花奖便开始酝酿了。这一年的第3期、第5期、第10期相继刊出了《小说月报》举办百花奖的“评奖启事”。一则仅二百余字的评奖启事,将评选范围、评选篇目、评奖方式以及奖励办法,悉数昭告清楚:首届《小说月报》百花奖从一九八四年起举办,凡这一年本刊选发过的中短篇小说,均为评奖对象;此次将评选出优秀中篇小说两篇,短篇小说八篇,共计十篇。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有些令人意想不到,令编辑部左右为难,最终不得不有所抉择。这是后话;至于评选方式,则完全采用“广大读者投票”的办法进行。这一方式,原为避免由专家评选或许会因某种个人好恶而引起后续的连锁反应,由读者投票,则依据充分,省了麻烦,也是一种鲜见之举;而奖励办法,除了对中选作品的作者颁发获奖证书、纪念品和奖金外,还对获奖作品原发刊物的责任编辑给予适当奖励,对所投选票十篇全中的读者,赠送纪念品一件。这后两项,便逐渐衍变成了后来《小说月报》百花奖的“编辑奖”和“读者奖”。为那些默默奉献,青丝染白霜、“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颁奖,在当代文坛文学评奖活动中尚属首创,可谓独树一帜,一直深得编辑同行们的赞许。设立读者奖,则颇受广大读者的好评。
《小说月报》百花奖的选票,刊登在1984年第12期的最后一页,选票下面附录了五条附言,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投票办法、截止日期、注意事项等。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简单做法竟延续了以后历届百花奖的规制。
查我当年的日记,是这样记录的:“这种活动,以前没搞过,我们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寄发选票,以民意测验的方式评选最佳作品。除刊物随附选票外,(编辑部)又另印了十万张选票。”而寄出这十万张选票,也是颇费周折。为省的上下楼麻烦,就在单位小院传达室的里间,总是一脸笑眯眯的编辑室主任赵克明带着我和编辑部的吴泽林,按照电话簿上的地址,向全国各地一些单位邮寄出了这些选票。填写信封地址,打包,整整忙了三天。
没过多久,刊物上的、单独印刷的那些填好的选票开始陆续回收。那些日子,出版社收发室的邮件属《小说月报》最多,而邮件中又以选票为主。我开始分类汇集,单独的选票,一百张扎成一捆;附带信函的选票,单独存放。果然,随着选票而来的一些读者来信,读着令人感奋,也更加让人觉得,这次“百花奖”的评选活动,多么深入人心。事后统计,当时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地区,都有读者踊跃参加了这次评选活动。有的选票是全家人共同参与,有的是同好集体讨论,才慎重填写寄出;有的地方文学社团还专门为此组织了研讨活动;有的读者为了达到评选准确,甚至再次通读了全年刊物;还有远隔重洋的海外读者,不远万里寄回了选票。因在“评奖启事”中说的清楚,这次评奖完全以读者投票方式进行,故此次评奖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以致被读者称为这是“一次大范围的民意测验及以数码代替文字的文学评奖活动”。所谓数码就是选票只填编号,不写作品名称。想来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才会出现如此痴迷的文学盛景。
面对文件柜里码放着越来越多的选票,怎么统计,也让编辑部有些为难。选票刊登在1984年的最后一期,投票截止时间为转年的1月31日,而颁奖大会计划在三月份举行,时间很是紧迫。为此,在社领导的组织下,编辑部几次开会讨论,大家各抒己见。最初,有人提议通过关系,请驻津某部的官兵给予帮助支持,但沟通无果。又有人提议,想通过天津大学的计算机系解决,那时电子信息技术刚刚开始普及,大家对此也是一知半解,可囿于经费所限,这一方案也不了了之。最终,编辑部决定,还是以最原始的办法,用自己的双手解决这一问题;而整理、统计选票的具体事宜,便由我来组织实施。
经社领导和编辑部同意,选票的统计人员,由出版社的行政人员和部分职工家属子弟组成。最初的工作是分拆选票,给每张选票打上号码,每一百张扎成一捆。这项工作,由人事科的几位同事,花了一周时间完成。我设计了选票统计表格。至于选票的具体统计,只能利用两个周日的时间,在出版社进行。由于前期工作准备得比较充分,选票统计非常顺利。那两个周日,出版社热热闹闹,无论行政人员还是家属子弟,大伙心气很高,兴致勃勃,一大早就来到单位。我简单讲解了一下统计流程、步骤、注意事项后,大家分头有的在办公室,有的在二楼方厅的乒乓球台,就有条不紊地忙活起来。中午,我给大家买来面包、火腿、果仁,权当午餐。经过两个紧张的周日,选票的初选工作结束。为感谢大家的付出,编辑部决定,每统计一百份选票,发给劳务费五元,以作酬劳。
最后选票的汇总,则是在编辑部内部进行的。将各组单独统计的选票汇集在一起,列出每篇小说最终的得票数,并排出顺序。当时编辑部制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不允许向任何人泄露作品的得票数。事实上,确实有一些同事拐弯抹角地前来打探获奖名单。我在事件的中心,知晓其中的一些“内幕”,但遵循领导的要求,在公布获奖结果前,严格保密。那些日子,自己的内心时常如怀揣小兔子般“突突”直跳,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又无可诉说。那种难忍的喜悦,无可名状。
从得票多少排列出的作品篇目来看,公认的入选作品并不意外,但前几篇的得票数过于接近,难分伯仲,实在出人意料;而按照评奖启事的规制数目,又实难取舍,这让编辑部颇有些跋前疐后,难以抉择。经过慎重研究,编辑部报请出版社批准,最终决定破例,增加获奖篇目。中篇由原定的两篇增加到六篇,短篇由原定的八篇增加到十篇。1985年第4期的《小说月报》公布了获奖名单。这十六篇作品是:中篇小说张贤亮的《绿化树》、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刘亚洲的《中国心》、佳峻的《虎门“犬”子》、鲍昌的《祝福你,费尔马!》、冯骥才的《神鞭》,短篇小说姜汤的《新客规今天生效》、陆文夫的《门铃》、梁晓声的《为了收获》、邵振国的《麦客》、何晓鲁的《历史选择了他》、冯骥才的《雪夜来客》、周克芹的《晚霞》、王蒙的《葡萄的精灵》、张洁的《尾灯》、仇学宝的《“我是来当儿子的……”》。
与此同时,颁奖会也在按部就班地有序准备着。获奖证书、纪念品、邀请函、宾馆住宿、会议议程、接送站、车辆安排等等事宜,也在逐步落实。出版社的不少同事,都被动员起来共同参与了这次活动,否则单靠编辑部的几个人,难免捉襟见肘,很难应付这么大的一件事。
1985年3月3日,《小说月报》一九八四年优秀中、短篇小说百花奖,即《小说月报》第一届百花奖颁奖大会在天津宾馆举行。颁奖会的会场布置简朴,但不失为庄重。主席台背面紫色天鹅绒幕布上的红色会标,是美编室的老师们书写后剪纸、用大头针别上的长宋字体,端庄秀丽,“小说月报”几个字,还专门剪成如刊物封面茅盾先生题写刊名那样的“茅体”。会议厅的天幕上,灯光璀璨,偌大的会场,坐满了各路嘉宾,新朋旧友,相谈甚欢。在我的印象里,无论主席台,还是会场一排排的桌子上,隔三五个人就摆放着一个铝质暖瓶,方便人们饮水。那时候可没有什么瓶装矿泉水之类的玩意。获奖的作家和编辑们,在前排就坐。主席台上是中国作协、天津市委宣传部、市人大、市文联、市出版局的各位领导。《文艺报》《人民文学》《十月》《当代》、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单位的负责同志,专程来津赴会。张贤亮、姜汤和《新疆文学》的陈柏中分别代表获奖作家和编辑发言。会上,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的王蒙,对这次评奖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文艺报》副主编吴泰昌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次评奖活动,对于获奖的中篇小说,颁发奖金六百元,责任编辑四百元;短篇小说奖金四百元,责任编辑二百元,除颁发获奖证书外,每位获奖者还获赠一个景泰蓝花瓶作为纪念品。颁奖会由时任天津市出版局副局长、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谢国祥主持。
行文至此,忽念起记忆中谢国祥先生的一个片段。
当时,谢国祥任出版局副局长兼社里的社长、总编辑(后来又荣任市委宣传部部长),但全社上下都叫他“老谢”。老谢公务繁忙,每周来社里一两次,处理完社里的事,一般都要到《小说月报》编辑部来坐坐。在颁奖会筹办最紧张的时刻,老谢来编辑部就更让人期待,因为很多事需要他拍板定夺。有一次,天都快黑了,编辑部还在等他。老谢来了,夹着他的黑色大公文包,一进门,众人便围拢过来,老谢顺势抬腿一屁股靠坐在我的办公桌边上,一一听取汇报,即刻又简明扼要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难题很快柳暗花明,迎刃而解。老谢成为唯一一位坐过我办公桌的领导。世事难料,2001年10月9日,老谢因积劳成疾,猝然离世,令人叹息!
颁奖会结束后,当天晚上,我们在天津干部俱乐部举办了一次联谊舞会。参会嘉宾、获奖作家编辑、出版社的同仁,以及有关方面的来宾,云集这座建于1925年的欧式建筑。夜幕四合,草木葱茏、水榭池塘、曲径通幽的偌大庭院,有着浓郁的英国田园风格。这原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由天津英国赛马会修建的英国乡谊俱乐部。这座外观简洁的两层红砖小楼,内部装饰典雅考究,有游泳池、台球房、保龄球房、西餐厅、舞厅、图书室、茶室等等娱乐设施。这个院落,也曾留下过末代皇帝、民国高官、国内外政要,以及一些达官贵人的足迹,今天则迎来了文坛众多的著名作家和编辑。大家济济一堂,自是开怀畅谈,热闹非凡,舞厅里跳舞的也是人头攒动,摇曳多姿。廓朗的穹顶,霓虹灯、射灯迷离闪烁着炫目的色彩,边侧一排欧式立柱与舞厅相隔,形成动静相宜的两个空间,远处小舞台上的乐队,在演奏着欢快的舞曲。很多人对这个舞厅的弹簧地板饶有兴趣,也别说,踩在上面还真能感觉到地板回弹的力度,跳舞十分惬意。我一直以为,地板下面有弹簧支撑,多年后才知道,这是一种特有的弹簧木,材质特殊,本身就有弹性,而且还是亚洲最大的一块弹簧舞厅地板,如今也算是一种保护文物了。这个颇具民国风情的舞厅,后来还成为不少影视剧拍摄的外景地。
舞厅一隅,张贤亮、鲍昌、佳峻、陆文夫、王蒙等围坐一桌,品茗畅谈。也许是咖啡。自己是刚刚入职的小字辈,也只有围观的份。过去只是读过他们的作品,现在纸上满经纶、笔下展乾坤的这些作家就近在眼前,那种感受确实有些不太真切,感觉在他们身上似乎笼罩着一种神秘的光环,令人仰慕。
在我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佳作频仍,硕果累累,很多作品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扛鼎之作,原因很多。自忖浅见,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因素至为重要。其一,新时期文学发轫的八十年代初,从冲破一元化的极左文学思潮为标志,各种力图回归文学本质的思潮兴盛,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新写实主义、现代派……等等,作家的创作热情得到空前激发,可谓“激情燃烧的岁月”,创作欲勃发,佳作自然此起彼伏,令读者应接不暇。总有新题材突破禁忌,文学的百花园一时间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其二,是作家创作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创作意识得到“激活”。摒弃以往“假大空”的陈旧模式,写属于自我的文学,成为一部分觉醒了的作家的共识,继承传统,借鉴西方思潮,在题材开拓、创作手法、结构方式,甚至语言表达等方面,无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继而形成了令读者耳目一新、又有冲击力的作品。可以说,面前坐着的这些作家,正值年富力强,可谓创作力最为旺盛的时候,便是进行了这样成功的尝试,业已有所突破,博得了读者的认同。可以这样认为,他们的小说在候选的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从而荣膺《小说月报》首届百花奖的殊荣。
第二天,编辑部组织获奖作家和编辑们,到刚刚落成不久的天津食品街参观游览,在咸亨酒店、海味餐厅、峨眉酒家共进午餐。因各路嘉宾众多,只好分拨这三处安顿,好在这几家餐厅都是楼上楼下相邻不远。席间,我陆续约请每位作家写几句“获奖感言”,准备发在下一期的刊物上。大家把酒言欢,为了颁奖会的成功举办,也为了文学的繁荣而开怀畅饮,直至鼓瑟息声,曲尽人散。其情其景,历历在目。想来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活动结束后,我在家歇了两天。已经连续两个周日没有休息,太累了。
从1986年第二届开始,《小说月报》百花奖以后每两年评选一次,到2015年我离开编辑部另谋他职,这一在文坛颇有影响的评奖活动,已连续举办过十六届,获奖作品如恒河沙数,不胜枚举。每一届的获奖作品,如连绵滔滔的江河,浩瀚雄浑,蔚为大观,记录了当代文学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