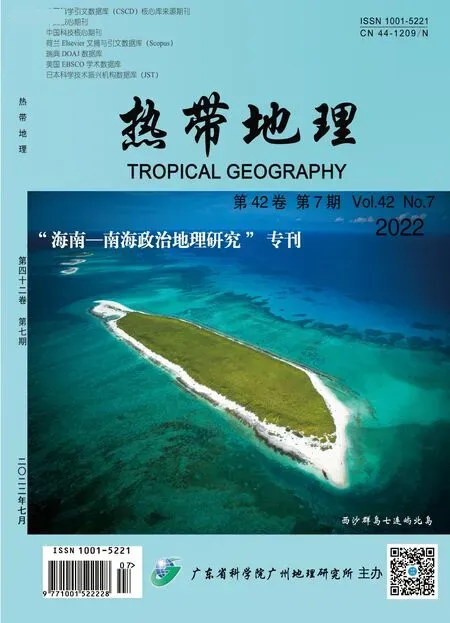流动中的地方记忆:南海渔民的流动性与集体记忆建构
刘玄宇,刘云刚
(1.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亚洲地理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2.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3. 华南师范大学北斗研究院,广东佛山 528225)
“流动性”是当代全球化不可忽视的社会特征之一。早期地理学者关注流动性,侧重从空间和行为动机出发探讨流动现象的机制,探讨流动方式和行为“利益”最大化的可循规律(Cresswell,2010),但往往忽视对流动性过程中深层次“价值负载”(Sheller,2014)的辨识。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流动转向”(Faist, 2013),地理学者开始重视人类流动性实践过程中的利益分配、身份建构、权力关系等社会文化内涵,开始探讨空间流动及其对个体或者社会产生的影响(杨茜好等,2015);自此,流动性研究超越了交通地理和社会学研究的二元视角,成为更多学科领域关注的议题(Hannam et al.,2006)。在此背景下,从多维度、系统地整合流动现象的“新流动性范式”应运而生(Sheller et al.,2006),其不仅主张关注流动现象的发生方式、规律、结果和时空效率,更强调人类流动性实践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利益分配、身份建构、权力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孙九霞等,2016;蔡晓梅等,2020),这也为多重空间尺度的社会文化现象研究提供了新路径。
流动性对于人文地理学基本概念的阐释具有革命性作用,尤其是对地方记忆研究的影响更为显著。记忆根植于特定空间,由一系列地方记忆符号串联而成(汪芳等,2015;周玮等,2015;孔翔等,2017),流动性对地方记忆的建构超越了静态、黏滞的范畴,记忆所依附的物质环境,被赋予立体化与多元化的内涵和外延(Withers,2005)。地理学者以时间和空间作为刻画流动性的标尺,关注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经验、实践的地方差异和多重社会关系(Cresswell, 2010; Faist, 2013; Schapendonk et al., 2020)。从空间角度,流动性不断修正着对地方、边界的认知,通过流动性,人、物、资本、信息的地方性特征得到重新诠释,个体或集体在流动过程中对地方景观及其叙事的感知和记忆,形成了人−地互动的重要纽带(Withers, 2005;汪芳等,2017)。从时间维度看,流动性决定着事物、信息和人的更替速度(Brierley,2010),也影响着地方信息的传递,促使主体形成特定的地方感知,从而建构起特定的地方记忆(Azaryahu,2012)。地方记忆使得民众产生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就像依赖于记忆一样依赖于遗忘,为了保证一个共同建构和维持的地域文化特性,往日被理解为地域发展至今的轨迹。地域的历史遗存、传统仪式和历史遗址等历史景观成为追溯地域往日的重要手段(Jones,2011),进而形成了集体记忆。
受陆地中心主义偏见,已有对流动性的研究较少考虑海洋环境(Benediktsson et al.,2015),这很大程度上与海洋自身的流态特征和不可栖居性密切相关(Steinberg et al.,2015)。不过,现在广袤的海洋已经不是分隔陆地的地理障碍,而更像是一条繁忙的通道,通过它,人与物不停地流动并形成新形态(Lutterbeck, 2021)。在此过程中,人们不断地与海洋景观进行对话,记忆和意义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Straughan,2012)。但相比陆地,海上流动受到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从潮汐流变、季风转换到国际关系,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于流动主体的行为,使得海上流动成为特定时空间的实践。基于此,本文对海上流动主体进行分析,以弥补流动性研究对海洋人类活动及其价值负载关注的不足。在为数不多的海事主体中,渔民是较为常见且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其流动过程被各种可见的或不可见的规则和物质景观所限制,尤其是跨界流动性实践也与地缘关系有关,更能折射其背后复杂的人海关系。故而,本文以海南渔民为对象,探究流动性与地方记忆建构的动态关系,及其对人海关系演变的影响,以此回应新流动性范式对海洋的关注。以期立体呈现南海区域互动网络的历史建构与发展,丰富人文地理视角下的海洋社会研究。
1 数据与方法
数据主要源于3个阶段的田野调查。第一阶段以实地调研为主。笔者于2020年7和8月两次进入文昌文教镇、清澜港和琼海潭门镇,以当地镇政府推荐渔民代表(主要是“更路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核心,滚雪球式扩大样本量和代表性,在开放式访谈中获取清末至建国前(风帆时代)远海渔民的日常生活、捕捞技能、航海经历、跨界贸易、人物故事等,通过对一手数据的编码分析,结合文献阅读,梳理出海南渔民建构的“海南—东南亚跨区域社会体系”海上互动网络。第二阶段,于2020 年11 月,在原有案例地的基础上扩大研究范围,增加文昌市铺前镇、三亚市三亚湾两处案例地;同时提高建国后参与远海捕捞渔民样本量,主要了解建国后远海捕捞的范围、技术、跨国互动的变化,尤其关注地缘政治对渔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并收集地方政府有关渔业管理的工作报告、文件、年鉴、规划和统计数据。第三阶段,于2021年4和5 月回访案例地,扩大访谈对象覆盖面,访谈边防民警2名、大学教授1名、媒体界人士2名,以验证研究内容和结论。总体上,3 次田野调查共计有效访谈渔民20人(表1),访谈对象均具备长期来往于西南沙群岛及跨境流动的经历。访谈时间控制在30~90 min,平均访谈时长为1 h。通过访谈得知,渔民活动的空间范围主要包括海南岛—南海—南洋沿海3个区域,由于渔民代际更替造成的部分“失忆”以及研究资料的限制,本文所指的南洋,主要以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沿海地区为主。

表1 访谈对象(南海渔民)基本情况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Fisherme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2 南海渔民的流动性特征
在新流动性范式中,世界通过流动的节点和流动的空间互相联系,其中流动性强调从流动、停泊、定居3 种不同状态描述世界时空观(张朝枝等,2017)。从流动性视角出发,可以推断渔民的海洋流动性至少由时空范围、物质基础和路径节点3部分构成。
2.1 渔民流动的时空范围
历史上环南海海域并未成为文化与经济交流的阻碍,反而依靠沿海的港口和中国至东南亚的陆地地区连结成有机的网络,形成一个以海洋而非陆地为基础的跨区域共同体。在此过程中,各种物质或非物质的“跨境”“越界”流动频繁(唐雪琼等,2016),其中海南渔民是“跨区域社会网络”的塑造主体之一。从时间维度上南海渔民的海洋流动性有着不同历史阶段,既有早期文明的接触与交流,特殊历史时期的冲突与动荡,也有现代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冲击。
早在秦汉时代,华南一带渔民就已“自日南章塞、徐闻、合浦”经中南半岛、通印度洋远航至非洲沿岸(韩湖初等,2004)。至隋唐,南海近海划归振州管辖,并置水师巡海,在官方上与南洋沿海地区建立了早期的经济、文化沟通。宋元时期,朝廷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带来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司徒尚纪等,2015),在此过程中海南岛迎来了真正意义的开发。海南岛扼守南海要道,是中外商船来往东西方的中继港,明王朝专设琼州府经营南海岛礁及相关海域资源,加上该时期官方多次综合舟师编队规模航海,环南海地区的民间贸易逐渐走向繁荣,在客观上为海南渔民探索远海提供了条件。清承袭明制,继续强化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的行政管辖,尽管清初海禁严重挤压海南渔民的航海自由性和空间范围,但禁海令仅维持8年就已松弛(阎根齐,2017),海南渔民前往南海诸岛捕鱼及到南洋诸国进行渔货贸易的流动性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清末至建国前是海南渔民在环南海地区自由流动的黄金期,同时也是冲突和动荡集中的时期。在殖民主义冲击下中国海防松弛,海南渔民的流动范围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他们凭借不断完善的航海图和丰富的航海智慧,频繁前往东南亚国家开展贸易互动,逐步形成一张覆盖整个环南中国海的跨海贸易网络(王利兵,2018)。尤其到了民国时期,受海防危机所迫,国民政府加大对南海岛礁的开发力度。与此同时,1819年英国在新加坡开埠,欧美国家对马蹄螺壳等海产品的需求激增(王利兵,2018),极大地刺激海南渔民对南海海洋资源的开发。随着前往南洋诸国出售海珍品的海南渔船不断增多,民间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专业从事跨海贸易的群体,他们大多从琼东各口岸出发行至越南会安,然后再沿着近海放帆至新加坡、印尼等地,中间途径柬埔寨、邦戈岛、马来半岛、马六甲、爪哇等国家和地区。此外,为了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和买卖关系,渔民的职业类型也出现分化,许多渔民选择移民定居在东南亚,为海南渔船的跨海贸易提供语言翻译或充当中介,自此开南海地区的民间交流进入黄金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加之东南亚国家海洋权益的争端,跨境流动的管理日趋严苛,海南渔民的“自由流动”成为历史,但渔民依然保有一种可移动能力。尤其是20 世纪80 年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关系缓和后,海南渔民于1983年实现了重返南沙群岛的首航。但近年来,随着南海渔业资源枯竭和国内外政治环境趋紧,渔民传统渔场的范围有所缩减,目前只局限在部分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生产作业。
2.2 渔民流动性的物质基础
流动性在地理学中始终围绕着一个重要的历史和地理要义,即特定方式与风格的移动与鲜明的人或物的主体所在的特定地理位置相关联(Cresswell,2010)。人类具有多样化的流动方式,如行走、跑步、驾驶和飞行,不同的科技工具和物质条件对流动性实践的形式和过程有着重要影响——物质基础决定流动的方式和效率(杨茜好等,2015)。与定栖、稳固的陆地相比,南海“洄沫粘天、奔涛接漠。无复崖埃可寻,村落可志,驿程可计也”(张燮,1981)。因此,渔民与海洋的邂逅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而是通过以船舶为媒介进行的。与陆地交通工具相比,船舶至少存在三方面的差异性:一是船舶被人格化,表现为船舶国籍的规定,船舶要取得航行权,必须经过登记,并悬挂该国国旗。二是渔民处于一个开放的流动空间,并非从完全封闭的独立隐私空间来观察外面的世界,但由于船舶漂泊在海面上,渔民身体和行动也更受制于自然环境的束缚。三是船舶的流动速度相对较慢,慢速流动给渔民更多观察海洋细节的机会,但也容易引发不良的心理问题。因此,在海洋上人与船组合所带来的自主性和流动性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塑造渔民独特的地方认识和空间感。
船舶流动性强化了海洋的主体性。在海洋中,船上渔民的生活与体验超出了陆上的经验和惯习,他们需要在一个沉浸在动感、三维、深度的物质世界中生活。海洋的物质世界不仅与船舶相连,而且成为船员独特空间观的一部分,影响着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在海洋动感环境下,船员对海洋水世界的适应必须面对混乱的生物钟:一方面为了追逐鱼群,船员的精神必须高度集中,连续工作,渔工的生物节律需要根据船舶值班、换班制度进行改变,很容易破坏原有规律而导致身心指标紊乱。另一方面,船舱内空间狭小、密封,船体不断受到海浪的摇动,日夜不停地机械性震动,并产生巨大噪音。渔民在休息时需要用手脚抵在床沿的挡板上以免摔下,甚至会用腰带将自己栓住以固定在床上,这种来自于海洋自然的力量通过动感传达到船上,规训并形塑着渔民的身体体验和习惯。在此情况下,渔民可能对船上工作的重复性和严酷现实感到无可奈何,极易产生身体或心理的疾病问题,如躯体化反应、神经症和精神怠倦等。
船舶流动性改变了渔民与船舶、海洋以及海岸之间的关系(Peters,2014)。在海上,船员在流动过程中不断探寻行进轨迹,持续强化其“在路上”的状态,但与陆地上“流动产生的动态视觉使地方、物、景观相互结合,飞逝和孤立的物体变得特殊”(张朝枝等,2017)。不同的是,海洋是“不包含任何信息的非符号化场域”(Steinberg et al.,2015),减慢了渔民对时间节奏的感知,带有令人压抑的单调和乏味。在海上渔民感受到的是一种超然非现实的世界,船舶被海洋力量塑造成为异端空间。所以,对于很多渔民而言,海洋更多地是承担生计的一种手段,而非海洋所赋予的冒险、刺激和自由感,船舶不断的摇晃强化了他们返回陆地的渴望。然而这种因陆海物质基础对比而产生的流动性体验并非只有负面效应,同样也改变了渔民对海岸生活的看法。例如与内陆居民安土重迁不同,渔民认为定栖往往带有保守与贫困等负面作用,相反他们追求的是通过远航建立与他者、异域的关系,从而满足对财富的追求。正是这种身份认同形成了海南渔民“敢于冒险”的人文精神。
2.3 渔民流动的路径节点
在流动性研究中,流动是人与空间之间的动态联结的通道,但不动性作为流动性的对立面也受到研究者关注,与流动性共同构成“流动/停泊辩证观”。在此关系下,流动的本质才得以显现。在渔民流动过程中,停泊一般是指衔接流动的陆地口岸和海上岛礁。
首先,流动性突显关系性的存在,基础设施本身具有不流动的特质,但其作为流动中的节点,为流动系统提供支撑作用,不同的物质、人员、信息等在此交汇,不同主体对停泊点的实践,使其变为复杂的社会空间(张朝枝等,2017)。在海南沿海分布的港口,就是由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建构起来的有故事的空间。从排列整齐的大型渔船到岸上滨海景观,从繁忙码头到渔产品交易中心,彰显着这些空间始终处于动态中,并被机动和移动的特征所描绘。然而,港口不仅是承载实践活动客观存在的物质景观,同时也被移动的行为所生产。如港口的空间布置和船舶上的神像、渔网、铁锚等物质景观细节,无不阐释着渔民对渔获的希冀、对海难的恐惧以及对家乡的依恋。因此,港口不是简单的物质背景,而是引导或限制着流动性,为渔民的流动实践构建了结构性或基础性语境。
其次,渔民在南海地理空间的流动,是一种追求财富和精神探索的形式,渔民不断受到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影响,又通过他们的行为填充和丰满着空间的内涵。因此,在南海流动过程中,渔民更加注重的是能够获取渔获和休憩的路径节点——海上岛礁。岛礁是海南渔民对南海感知的最小地理单元,渔民根据自己生产、生活经验和岛礁形状、物产状况等,赋予了南海136个岛礁富有地方特色的俗名(刘南威等,2015),从而在南海中串联交织成一幅宏伟的地名景观。南海岛礁土地名具有较强实用性,一方面锚定了航海的方位和航向,满足海南渔民流动过程中导航定位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渔民在南海流动范围的扩大,航线条数和岛礁土地名不断增加,逐渐勾勒出南海的基本轮廓,并最终形成4条由渔民地名组成的作业航线,即东线、东南线、西头线和南头线(图1)。

图1 南海渔民出海作业的东线、东南线、西头线和南头线Fig.1 East,Southeast,West and South lines exploited by fisherme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最后,海上岛礁价值还体现在渔民流动过程中自愿的静止状态,即他们在狭小而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创造出流栖式的海岛经济生活(刘莉,2020)。与近岸渔民和远洋捕捞不同的是,海南渔民在漫长的南海渔猎历史中,逐渐发展出以岛礁为据点的渔业生产模式。从早期以岛礁为临时营地进行机会性捕捞,到后来以岛礁为家长期住岛,在经历漫长历史后,南海渔民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海岛生活和物质文化。现在,在南海各种宜居岛礁上遗存的庙宇、生产生活设施、居住建筑等物质景观,无不累积着渔猎文化传统和族群认同的历史文脉,共同构成渔民流动过程中的记忆符号。
3 渔民流动中的集体记忆建构
集体记忆是渔民在流动过程中进行人海互动与情感建构的重要途径,内核是渔猎文化及跨界网络。在流动性视角下讨论渔民的集体记忆需要明确3 点:一是集体记忆本质上是立足于“现在”并且是对“过去”的一种建构,主体更迭会显著地影响记忆的延续和传承。二是记忆由个人情感和客观环境共同形成。对于渔民而言,集体记忆在特定的地方展开,通过物质的和象征性的记忆景观,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转换。三是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相辅相成,加剧了渔民的差异性,进而导致集体记忆的碎化或断层。基于以上认识,将渔民流动中的集体记忆建构分为3点阐释。
3.1 流动主体更迭凸显出集体记忆的“时间”
集体记忆的产生和形成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枝条上结出的果实(郑宇,2008)。不同主体因“实际和感情”的需要,构成完全不同的叙事框架,导致同一事件在不同时间框架中得出集体记忆形态和性质各异的结果。其最典型表现在渔民流动身份变迁及其对人海关系的影响。对于渔民而言,流动性是渔民主体感知世界、进行空间实践的重要过程,深刻影响着其社会角色分配和扮演。在长期的流动实践及形成的文化意义中,逐步锚定了渔民劳作分工和技术分配,体现个体的主体性建构。
南海捕捞是一项难度高、风险大的作业方式,不仅对渔民的技能和经验要求高,而且需要渔民之间配合默契、合作无间。与现代市场雇佣制不同的是,风帆时代的海洋生产组织模式取决于由血缘、姻缘、业缘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的稳定性。尽管海南渔民在海南岛—南海—南洋构成的多空间尺度中不断地往返流动,与新的地方和空间发生冲突和摩擦,但由于渔民群体结构的相对稳定,船员之间的关系、情感并没有因为空间更替而发生变化,反而在流动过程中增强了集体记忆和族群认同。这种认同和网络不仅是海南渔民勇闯海洋的一种精神象征和支撑,同时也发挥着一种规范和强化渔民与海洋之间关系的作用。然而,到了20 世纪80 年代,技术的改进和市场经济将渔民及其生产逐渐剥离于传统经验和社会文化系统之外,致使渔民的海洋认知能力大大降低,削弱了渔民与海洋之间的连接,风帆时代形成的相对平衡的人−海关系开始出现倾斜(王利兵,2021),主要表现为渔民对海洋的认知趋于客体化,集体记忆也随之发生变化。
记忆的本质在于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半流栖性的生计模式是渔民长期与南海海洋环境打交道并主动选择的结果。由于海洋捕捞以自给性渔业为主,海南渔民对南海岛礁、渔业资源的利用强度较低,人海关系基本处于动态平衡的良性状态。但记忆所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并非仅限于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包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王利兵,2021)。对于渔民而言,其生产与生活均需和变幻莫测的南海打交道,大自然的巨大能量形塑了渔民万物有灵的朴素自然观,这些流动实践所衍生的信仰、规则和惯习等记忆要素贯穿于渔民生命图谱,指导着其与自然海洋的互动。然而,在市场经济和发展逻辑的推动下,渔民的主体诉求也从自给性生计转向商业化捕捞,渔民群体结构来源逐渐复杂化。传统信仰和习俗在记忆主体代际更迭的背景下退化为一种记忆碎片的模糊组合,原有人海关系中海洋的主体地位被削弱,海南渔民与自然南海的关系逐渐从动态平衡走向对立冲突。
3.2 流空间的建构凸显出记忆的“地方”
流动性语境下,地方不再是内生的、僵化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关系化的流空间(孙九霞等,2016)。历史上,渔民频繁前往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生产作业,并远赴南洋国家或地区开展贸易交换和社会互动,从而将其所在渔业村镇置身于跨区域流动的网络中,其结果:一方面,大量的人口流动使得构成村镇的社群与景观呈现多样性的“马赛克化”。另一方面,来自全球的物资、信息、文化等形成流动的网络,以不同的方式交织在村镇空间。这使得原本相对稳定与均质的渔业村镇越来越多地处在与“他者”的身份、文化以及实践不断协商的过程中。从集体记忆角度,特定的社会文化空间环境是形成人的认知方式与途径的基础,环境通过提供线索作用于行为,人们靠着这些线索来判断和解释社会脉络或场合,并相应行事(李凡等,2010),同样渔民的集体记忆离不开环境背景的影响。渔民长期流栖于原住地与南洋诸国之间,带回的异域物质和文化深刻地形塑了渔业村镇的地景,以环境感应为基础的集体记忆因而具备了地域性、连续性、时代性和选择性。
首先,渔业村镇的地域性是指村镇由于所处地域的不同而使集体记忆呈现差异性,文昌和琼海都是南海渔民的主要来源地,但两地渔民由于地理条件和历史传统不同,所形成的集体记忆也不同。如相比于琼海潭门镇以渔猎文化为主的民居景观,在文昌市铺前镇则表现为以海商文化为主的南洋风格。其次,由于渔业村镇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而集体记忆在某一时间跨度上也是连续的,如清澜港、潭门港等都曾是渔民前往南海及南洋的重要出海口,其港镇空间叠加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景观或符号,这些印记折射出海南渔民悠久的渔猎历史或海商文化。再次,即使身处同一空间环境,对于不同时代的人们也有着不同的意义。如调研中不同年龄渔民对待《更路簿》的认知和态度存在差异。老渔民经常能够清晰回忆起《更路簿》及其所蕴含的海洋知识对于风帆时代航海安全的重要性,但年轻渔民对此则反应冷淡,在导航技术和船舶设备现代化的今天,他们能够在科技帮助下轻松实现航行和应对风险,这种时代的差异显著地影响了风帆时代遗存的物质或文化景观在群体中的影响力,使集体记忆产生了选择性。最后,集体记忆建立在渔民环境感应的基础上,即形成什么样的集体记忆与获得什么样的环境线索密切相关。因此在集体记忆形成过程中,人们可以选择那些能强化环境意义的线索。如随着南海局势紧张,渔民集体记忆的选择性愈发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强调渔民群体的历史轨迹(如《更路簿》)、保存营造环境元素(如南海风情小镇)、艺术和手工艺(帆船时代生产工具),以及(南海)博物馆等,以维系这种认同。其中,国家意志起记忆过滤器的作用,对集体记忆的形成产生影响。
3.3 流动性管控凸显出记忆的“权力”
地理流动和社会流动相辅相成。首先,流动性是一种资源,渔民的流动性本身就体现其职业身份价值,过去渔民出海没有太多限制,在海上所获得的流动资源是均等的。因为作为区域的南海是周边国家渔民开展生产生活的传统渔场,来自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的渔民群体拥有着相似捕捞工具和作业模式,共享同一海域及其海洋资源,彼此之间常常发生各种形式和内容的互动交流。其次,流动性是一种获得地理流动的权利,可以促进向上的社会流动(孙九霞等,2016)。从新流动性范式视角,地理流动意味着通向其他区位的资源,可以为群体提供更多的社会和文化资本。因而,尽管南海将海南岛与东南亚隔离,但对生存区域探索的流动本能驱使着渔民突破地理藩篱,远航南洋以获取经济和就业机会,并在异域通过多重社会关系和经贸往来构筑了一个跨尺度的“商贸圈”。这种为了生计而产生的流动使得渔民的劳动力商品价值得到最大化,成为在传统社区中受人敬重的生产者角色。如在潭门社会,渔民家庭的婚姻圈通常局限于渔村范围内,很少与内地农业村落发生联姻关系,其“门当户对”折射出的不仅仅是职业分工,更是对流动资源的垄断和族群记忆的延续。
然而,流动性不仅与移动和自由相关,更与权力存在关联性(Cresswell, 2010)。随着时代的发展,渔业经济体制不断改革,为适应开发中、深海渔业生产需要,国家一方面对海洋捕捞船及船员资格审核标准愈加规范,另一方面划分渔业区规定了不同类型渔船的固定作业区。在此过程中,渔民被赋予差异化的流动机会和能力,不仅渔民无法维持过去通过多重关系所建构的跨区域社会网络,而且也因所持有不同类别的捕捞许可证而被限定在某处作业区,原有生产组织模式及其所附的集体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遗失。然而,有了限制和规则,必定会有抵抗和争论,这种抵抗便是空间流动中的政治−权力的博弈。与陆界不同,海洋边界难以区分和管制,主权国家间的制度化、景观化的屏障无法明确彰显出来,因此渔民发展出一系列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跨界流动策略,如夜间捕鱼、雇佣他国渔民代工捕捞、贿赂他国驻岛士兵以获取捕捞许可等等。但即便如此,不再掌握流动主动权的渔民群体不得不承受权力政治对世代传承记忆的破坏,在国家管控和他国势力威压的夹缝中重构新的航海记忆。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从时空范围、物质基础和路径节点诠释了渔民南海流动性的特征,辨析了流动性对集体记忆的建构作用。研究发现:
渔民跨界流动具有动态盈缩的特点,经历了从民间自觉到官方规范,从渔业生产到商渔复合,从局地到广域再到局地的动态过程。渔民在南中国海的自发流动发轫于对基础生计的热望,早期局限于近海空间范围捕捞,随着海岸线以外的近岸水域和岛屿被渐次纳入王朝政权管辖,中国与海外社会文化交流加速,海南渔民逐渐从船政辅助人员转变为具有主体性的自由流动群体。明清后渔民前往南洋地区或口岸开展贸易互动更加频繁,并分化出两套成熟的商贸模式:一是渔民经由南海岛礁生产作业后前往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和新加坡开展贸易交换,二是民间社会形成了专业从事跨海贸易的海商。无论形式如何,海南渔民经过世代的跨海流动与迁徙,勾勒出一幅覆盖整个环南海的跨海社会关系网络,这一海洋网络不仅建构和塑造了渔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渔民集体记忆的结构性语境,更凸显出渔民群体的海洋主体性地位及其在建构和维系南海区域网络中的重要角色。
与集体记忆沉淀于静态仪式和景观的传统研究略有不同,本文认为渔民集体记忆更多浸染于流动状态和过程中,揭示了海洋族群的行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过程。“流动”是实践性的,船舶是渔民流动性得以发生的物质前提,渔民和船舶的组合带来了自主拓展的能力,塑造了渔民对流栖环境的认识和体验,如渔民为应对陆海差异而调整身体行为和情感波动。当然,渔民的流动性同样存在流动与不流动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渔民流动过程中,陆上口岸和海上岛礁构成不流动的地点,引导或限制着渔民的流动行为,但这些空间本身并不是静止的物质背景,而是始终处于动态中,被各种流动行为所生产,如码头和岛礁上具有流栖色彩的物质和文化景观等。因此,在流动视角下的渔民的集体记忆是一个不断变化和修正的持续过程或未完成式。
流动性对集体记忆具有建构作用,体现在3个维度:时间、地方和权力。时间和空间是流动性的关键维度,流动通过时间和空间实现社会建构,因此在流动性范式下探讨渔民的集体记忆,时间与空间是2个必须考虑的因素。就前者而言,主要表现在记忆主体的变化。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具有一定时空边界群体的支持,风帆时代海南渔民通过跨界流动不仅习得海洋知识和经验,还创造出人海和谐的朴素生态观。进入现代社会后,记忆主体发生变更,集体记忆呈现出动态发展。一方面航海技术进步将渔民及其生产与传统记忆相割裂。另一方面职业代际断层严重削弱了集体记忆的延承性。当然,集体记忆不只是时间的,还是空间的,它根植于地方,通过物质的或文化的景观而被空间化。受历史上流动性的影响,渔业社区被置于跨区域流动的网络中,宏观的人、物体、资本、信息的流动,改变着渔业社区的物质景观以及渔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地方的物质性,意味着记忆并非听任心理过程的反复无常,而是铭记于历史的遗产和资源中,并透过渔民群体的长期堆积和过滤后最终形成集体记忆。此外,本文还发现进入新时代后,海南渔民不得不面对因制度安排和地缘局势等权力因素所造成的流动权利的分配不均。然而,渔民是天然流栖性的族群,即便边界管制束缚其流动的空间弹性,部分渔民依旧发展出各类策略试图重获自由流动的权利。因而如果将流动性作为渔民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来衡量,则具有不同流动能力的渔民意味着掌握不同程度的集体记忆,并且正在被撕裂和遗失,最终在新的流动过程中被重构。
地理空间的记忆是一个涵盖多层、多项社会人文、物质环境指向的复杂巨系统,本文从流动性视角对海南渔民空间记忆做出探讨。流动性与集体记忆的共振、互动,是未来研究海南渔民人−海关系的重要视角,但未来对空间记忆的探讨应建立在庞大渔民数据库的基础上,以空间、地方、情感等人文地理学的基础概念,更加细致地洞悉渔民集体记忆在时空维度的演化机制,在实现记忆理论本土化的同时,不断充实记忆研究的海洋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