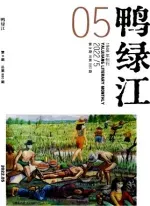阿爸的草原
王樵夫
1
“秋天不垛干草,春天死畜成堆。”
“马伴君子,不伴小人。”
“良马比君子。”
这些话,经常挂在阿爸的嘴边。每当阿爸聊起这些,额吉(蒙古语,妈妈)就忍不住笑,她说阿爸的话没完没了,像太阳落山后回家的马,排着队,一串一串的。
一年年,青草冒芽,大雁南飞,骆驼又下了几个羔子,也看不见孩子们的身影。阿爸落寞地对额吉说:“草原太静了,静得能听见羊在喝水,马莲在开花!”
阿爸在草场上有一处房子。除了他和额吉,在院子里走动的就只有牲畜了。羊群每天回到棚圈里。牛和马在草库伦里溜达,几天回来一次。他们的孩子,曾经每天跟在身后“阿爸、额吉”地叫着,叽叽喳喳的孩子,一个个长大了,都住到城里去了。
定居以后,棚圈附近的草被牲畜踩光了,露出了白晃晃的沙子。半沙化的草场,只有顽强的沙葱和味道浓郁的蒿草冒出头来。
春天,风沙特别大,漫天卷起黄沙,瓦蓝的天空瞬间被搅得混沌不清。沙粒啪啪地抽在脸上,像被无数飞来的针尖,扎得痛。一夜间,毡房外就隆起一溜溜的沙岗子。
退化的草场,让阿爸忧心忡忡。儿子要他们卖了牛羊,搬到城里去。阿爸死活不同意,他闻惯了马粪的味道,喜欢喝新挤下来的牛奶,摸着羊羔子雪白的毛,给它们的嘴巴里灌药。
城里的街道窄窄的,房子像火柴盒垒得老高,整齐的天空被电线分割得七零八碎,看着就堵得慌、闷得慌、热得慌……“街上没有草,遛到哪儿都是汽油味儿。”
他拒绝了儿子,和老伴商量,把牛羊圈起来,先在自家退化的草场上种沙打旺(一种用于改良荒山和固沙的优良牧草)。
为了买种子,阿爸卖了好几只羊。每天天不亮,就和老伴起床去种沙打旺。老牧人哈斯巴根笑他笨,有种沙打旺的工夫,还不如找一片好一点的草场。“再说这鬼天气,热得像下火,种什么能活?”
阿爸也不回话,成天骑着马,在沙地里转悠。
几场雨过后,沙打旺真的活了,几片新蹿出的叶子,嫩绿嫩绿的,把阿爸的心打亮。阿爸似乎又看到了漫山的绿野中点缀着牛羊,他咧开嘴笑了。
棚圈里的羊羔子叫了起来。这几天,阿爸开始准备铁铲子、夹板、小木凳、酒精,要给羊羔子断尾。要断尾的全是改良的绵羊羔,尾巴特长。如果不断尾,遇上跑青拉稀,沾在尾巴上,天长日久就会结成粪疙瘩。如果是母羊,还会把长尾巴尿湿,苍蝇会下蛆。无论公母都要断尾。
断尾和骟蛋一样,牧民都要选择晴朗无风的好天,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迟。太早了会冻,太迟了就有了苍蝇,所以一般在立夏前进行。
阿爸把羊羔子提起来,额吉用夹板夹住羊尾巴,把羊尾固定在木凳上,阿爸拿着烧红的铁铲,刺溜一声一股烟后,大半截尾巴就烫下来了。再用棉花蘸上酒精,涂在断尾上,伤口四五天就痊愈了。
断下的羊尾,用开水烫掉毛,煮熟了,又肥又嫩,但是阿爸从来不吃。
阿爸还要给羊灌驱虫药。阿爸两腿夹住羊,左手将羊嘴扳开,让羊脖仰起,右手飞快地把药灌进去。为了避免漏灌重灌,阿爸一般采用两种办法,一种是灌完一只,打开圈门放出一只;另一种,是把稀牛粪抹在灌过羊的身上,做标记,牧民们称之为“打抹子”。
孩子们小的时候,阿爸最喜欢给他们讲额布格(蒙古语,爷爷)养马的故事。后来,孩子们都长大了,搬走了,没有人再听他讲了。
阿爸一个人的时候,还是常常想起那些事。他想不通,那些发生在草原上的事儿,怎么能说忘就忘了呢?
额布格会相马,好马驽马一眼就能瞅出来。他扳开马嘴,根据马的牙齿,就能知道马多大的口齿(年龄)。有一年春天,额布格的十几匹马被土匪抢走了,家里没有了重要的交通工具,去嘎查买药看病,只能借亲戚家的马。
额布格想念他的马,每天晚上睡不着,就喝酒解闷,还发脾气。额木格(蒙古语,奶奶)不吱声,孩子们都吓得不敢说话,全家人忍着他。
冬天的一个夜晚,蒙古包外突然响起了马的叫声。额布格提着马灯出去一看,原来是抢走的其中一匹灰色的母马,领着几匹别人家的马回来了。母马咴咴地叫着,带着那些马走进了熟悉的棚圈。
马儿们又饥又渴,不知从哪儿回来的,也不知走了多远。
额布格又惊又喜,大喊:“马回来了,马回来了!”
全家人都跑了出来。看着那匹瘦了的灰母马,额木格激动地上前搂住它的脖子,一个劲亲它的额头,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腮上挂满了泪。
这个事情一直让阿爸难忘,马是多么懂感情的动物啊,从此他明白了,他这一生都会和额布格一样,爱马,离不开马。
阿爸给嘎查(蒙古语,村)放马,他亲手调教出来的骑马,都是好马,老实,不咬人,不踢人,人们都说阿爸调教出来的马懂事。
20 世纪80 年代,阿爸曾花了一千元买回三匹马,一匹喜鹊花母马带两个马驹儿。喜鹊花马特别稀少。阿爸高兴地念叨:“有钱难买喜鹊花啊!”
额吉心疼钱。家里的孩子多,要念书,还有老人,用钱的地方多。但是,她对孩子们说:“你阿爸年轻时没养够马,一辈子就爱马,让他养吧。”
过了两年,喜鹊花母马变成了白马,草原上的蒙古马就是这样,过几年就会变成另一种颜色。阿爸逢人就炫耀,开口仍然离不开马:“‘七青八白九长斑’,以后还得长斑呢!”
初冬,阿爸把马群赶到贡格尔河边,河刚结薄冰,阿爸用脚把冰踩破,让马喝水。阿爸踩冰的时候很小心,踩了好几处,冰裂开,才冒出足够多的水,让马喝到。阿爸的鞋常常被水泡湿,一会儿就结了冰,走路一瘸一拐的。
马的警惕性高,不让生人靠近,却非常信任阿爸。它们喝饱了,用湿漉漉的嘴唇去嗅阿爸的手。平时不苟言笑的阿爸咧开嘴,露出半嘴的豁牙。
昏黄的阳光落下来,照着马儿,照着阿爸,河水里的光影就像阿爸的脸一样慈祥。
冬天,贡格尔草原的雪特别大,无论多冷,阿爸半夜总要爬起床,给马多加一些干草,他担心马儿吃不饱。母马若是揣上驹子,阿爸特意给母马加料。他嘴里唠叨:“马不吃夜草不肥,草膘、料劲、水精神,少了哪样儿都不行。”
无论谁骑马外出办事,回来后,阿爸都要亲自饮马。阿爸不放心:“这饮水有说道儿,马吃脏草喝净水,水一定要干净。”饮马的时候,他也特别讲究,不能热饮、暴饮、急饮。他说,马刚骑回来,浑身是汗,这时候不能马上饮马,要拴一会儿,拴得高一点,让马喘匀了气,消了汗。阿爸还说:“要‘一饮三提缰’。”饮马时必须拽几次缰绳,让马抬头,喘喘气儿再喝,这样马才不容易得病。
“我老了,别的想法没有了。我就是想养几匹马,整天放放马,骑骑马,骑在马背上,是最幸福的事情。”阿爸说,“看着一群马在草原上吃草,在天空下跑,我高兴着呢!高兴了我就唱歌,那歌儿从嘴里溜出来,飘出去,就像跟马一起跑呢……”
2
“马就是蒙古人的摇篮。”阿爸自幼长在马背上,现在老了,仍然天天骑马。
“蒙古马是世界上最善解人意的牲畜。别看马的脾气暴,但是对主人忠诚。”他说,“你如果喝醉了,只要能爬上马背,它就能安全地把你驮回家。你信不?”
当年,阿爸当兵复员,本可以在城里分配一份好工作,可是他坚持回草原,当了嘎查的牧马人。“放马是草原上最让男人骄傲的活儿。”那时候,嘎查的马群大,几千匹,加上马的活动范围大,当牧马人非常辛苦,要跟着马跑很远的地方。“只有最能吃苦、最勇敢的人,才有资格干,才会干得好。”
阿爸养着几匹赛马,在那达慕大会多次得过奖。可是,现在的马被汽车、摩托车取代了,马退化成一种旅游娱乐品和蒙古族人的精神寄托,马的经济价值也随之大幅下降。
“骑马的蒙古人越来越少了。”阿爸伤心地说,“蒙古人不骑马,就是忘记了祖宗,背叛了成吉思汗的祖训。”
导致马越来越少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草场承包了,家家都拉起了铁围栏,无法养那么多的马了。
草原上有平地草场、山地草场和戈壁草场。平地草场和山地草场都是典型草原,戈壁草场有点近似于湿地。所谓山地草场,其实就是连绵的高山漫甸草原。不同的草场,生长的草不一样,营养不一样。
以前游牧的时候,牧民夏天把羊群赶到平地上,冬天赶到山地,需要补碱吃的时候赶到戈壁。
阿爸分到的草牧场就是以前的山地草场,是冬草场。冬草场有个特点,没有水源,打井很难出水,也叫无水草场。当年,冬天下雪以后,牧民赶着牲畜过去,牲畜吃积雪解决饮水的问题。春天雪化了,牧民就把牲畜赶到平地草场去了。
草场承包后,长年在冬草场放牧,到了夏天,冬草场的问题一下子严重了——几百只牲畜需要喝水。阿爸为此打过三口井,接近一百米的深井,愣是不见水。打井借了高利贷,到现在还没有还清。阿爸很沮丧地说:“从那时候,我就再也没起来。”
阿爸只好开着拖拉机拉水。春天来了,天气转热,青草要长起来了,牧民都高兴得不行。阿爸却愁得慌,因为天一热,牲畜的需水量增大,他拉的水,供不上牲畜饮用。“除了喝口茶的工夫,一整天的时间全用在拉水上了,没办法,逼着你减少养畜的数量。”
围栏养畜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牲畜吃草太单一,营养不良。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拆掉围栏,实行草场合作社,牧民共同使用草场,恢复四季游牧。可是,牧民的思想很难统一,有的牧民甚至把牧场租出去,什么活儿不干,靠租金度日!
“现在的人,这里有问题了!”阿爸指了指自己的脑袋,长叹一声,“对聪明的人,学问最珍贵;对愚昧的人,金钱最重要。对于我们牧民来说,草原最重要。”
崇尚自然、和谐共生,在蒙古人的心中,早已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愫或民族集体潜意识,它就像吃饭、喝水那样,自然而然地完全熔铸于民族心灵的深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
为了修复草原生态而建设的围栏,在发展过程中,陆续暴露出一系列影响生态的新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已经有人重视了。”阿爸高兴地说。
3
阿爸懂得草原,懂得牲畜,懂得畜群如何管理。他曾经当过嘎查长(蒙古语,村长),负责安排整个嘎查的牲畜转场、牧人搬迁。他认识草,知道什么样的草有营养,什么样的草有毒;什么季节牛羊应该吃什么草,什么季节应该去哪块草场放牧;冬天应该贮多少草料。而且套马、骑生个子、打狼,都是一把好手。他还会做蒙古包、搭蒙古包。阿爸家里保存着好多捆马鬃。“捆蒙古包用的。结实,抗雨,不腐烂。”
草原上,年岁长的牧民经验丰富,他们的养畜知识不比畜牧专家差多少。
蒙古族非常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思想意识甚至变成了一代代蒙古族人的自觉行动和生活习俗,并不断传承和延续。
水是生命之源。在蒙古族人心中,水是纯洁的神灵。阿爸说不能污染水源,不能在河里洗脏衣服;不能把牲畜的尸体和秽物丢进水里;不能往河里撒尿;看见有淹死的老鼠和麻雀,必须捞出来……
对草场和棚圈的环境卫生,阿爸的忌讳很多,他说凡是放牧的草场,不能乱扔牲畜的尸体;牲畜的棚圈要通风向阳,要远离灰堆和厕所,棚圈周围严禁大小便;不许把污秽之物扔进圈里;忌讳陌生人随便出入棚圈;还有冬营盘要背风暖和,夏营盘要高而清爽。
春季接羔的时候,要让小羊羔卧在干燥温暖的地方,喂料、喂奶要使用干净的用具;饲料要新鲜干净,不能有发霉变坏的;春天的弱畜、病畜要喂精饲料,饮干净水。一年四季,都要追逐水清草鲜的草场放牧,转场轮牧。要经常查看牛犊、山绵羊,如果身上起了草鳌、虮虱,要及时清除。
阿爸把刚生下来的马驹子叫“乌纳格”,二岁马驹叫“达阿嘎”,三岁母马叫“古纳格别德斯”,把三岁公马叫“古纳乌热”,把骟龄的四岁公马叫“伊斯格勒乌热”。而汉族人称呼牲畜,大多是几岁后面加上牲畜的通称,比如二岁子马,三岁子牛,四岁子羊……
蒙古族人对马的年龄和毛色有独特的称谓,有三百多种。不论公马还是母马,四岁前都不直接称呼其马的年龄,只要按蒙古族人的习惯称呼,别人即可知道他说的是公马还是母马,并且知道是几岁马。
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一个民族,像蒙古族一样,对牲畜的种种事体有如此丰富的语言。蒙古族人不会堆砌辞藻,他们对牲畜的叫法,给人的感觉直观、形象、简捷,它来自对象的丰富性、牧民观察的细致性和管理上的实用性。
阿爸对牲畜的辨认能力是惊人的。四五百只的羊群,他能一一辨认出来;和邻家混了群的羊,他也能迅速找出来。家里的每头羊、每匹马,什么品种,有无疾病,如何治疗,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阿爸长年生活在草原上,抬头望望天,就能预测出未来三天的天气;根据冬天的气候,就能推断春夏的气候好坏和雨水的多少;瞅一眼草场,就能看出这个地方适合放牧哪种牲畜。连偷杀牲畜的人,都逃不出阿爸的眼睛。
阿爸不仅能从外貌上辨别牲畜,甚至能从蹄印上认出牲畜来,这是他在长期放牧中掌握的一门特殊技术。阿爸认识自家每一匹马的马蹄印,也认识附近牧民家的马蹄印,而且他能根据马蹄印的痕迹,说出它是哪匹公马的后代。如果牧民们认错马,阿爸便根据马蹄印来辨别马是谁家的。
阿爸说,马蹄印里面学问深着呢。马蹄子的形状、叉开的角度、踩地的深浅、运步的方法都不一样。牲畜的蹄子有拢蹄子、散蹄子,形状有圆形、方形、方长形……牲畜走路,有的走起来平直,有的走起来歪斜;有的抬腿拖拉,有的抬腿利索……阿爸就是根据这些特点和长期的实践经验来辨别每一头牲畜,而且准确无误,让人惊叹。
4
“护着负伤的主人,绝不让敌人靠近;望着牺牲的主人,两眼泪雨倾盆。仁慈的蒙古马哟,英雄的蒙古马哟!”阿爸当年是骑兵,他在打仗撤退时,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他的马立即返回他的身边,用嘴拽他,并且卧下让他爬到马背上,他才得以逃生。阿爸说:“如果马不回来救我,我肯定死了。”
还有一次,他们中了埋伏,战友的马中弹了。如果那匹马当即倒地,战友肯定中弹身亡,但是这匹马硬撑着拐了一个弯,倒在一个大土包的后面,正好是敌方的枪无法打到的地方。
战友得救了,那匹马却死了。
阿爸放马的时候,有一年,发生了大雪灾。苏木(蒙古语,乡镇)冻死了好几个人,也冻死了很多马。那天上午十点多,开始刮白毛风,白毛风刮得人什么都看不到,也看不清方向,马群是喜欢顺风跑的,阿爸只好跟着马群一直走。风太大了,仓皇的马群一个劲儿地跑,一下就跑出去了三十多公里。阿爸身上没带吃的东西,走了整整两天两夜。开始,阿爸骑着一匹母马,冬天母马更耐寒。后来母马实在走不动了,阿爸从马群里另外套了一匹马,刚换上,母马就栽倒在雪地里死了。
阿爸现在回忆起来,仍然眼里含泪:“它一直硬撑着,我刚换上马,它就倒下了。雪有一米多深,幸亏我换的这匹马特别好,能在雪里跳着走。这匹马很聪明,不往前面跑,就跟在马群后面。”如果这个时候马不够好,人从马上摔下来,很容易被马群踩死。两天后,苏木发现只有阿爸的马群没回来,就派人出去找。找到的时候,阿爸的腿已经冻僵了。
“这两匹马救了我的命!”阿爸叹息一声,“我后来换上的那匹马也老死了。它死了之后,我一直想着它,它救了我的命啊。我把它的马尾留下来,把它的尸体放在山上了。”
在草原,一般的马都是要剥皮的,但救了主人命的马,还有老母马、种公马,死了以后都不能剥皮,不能宰杀,牧民任其自由死去,然后在马头上系上哈达,放在高高的山上。
马的葬礼,是对马灵魂的召唤,是对生命的礼赞,是对马群的祝福。
阿爸说:“万物有灵,草原上的山川大河,甚至是一草一木,都值得敬畏。”
5
茂密的森林,
装点着曼陀山的沟岔;
在它的树枝上,
喜鹊不断地叫着。
落落大方的巴雅尔,
是哈斯图雅姑娘的依靠,
思念的心情呀,
萦绕在哈斯图雅姑娘的心上。
阿爸从小爱唱歌,不管碰见什么人,只要唱得好,阿爸就跟着唱,直到把歌学会。
阿爸最喜欢听的,是婚礼上长辈们的歌声。后来,阿爸成了贡格尔草原上有名的歌手。现在,阿爸的女儿成了乌兰牧骑的独唱演员;儿子在饭店唱歌,儿媳在城里陪孩子上学。
阿爸放牧的时候,也唱歌,从来不知道累。尤其他喝了酒,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来,那歌声从蒙古包的天窗飞出去,听得牛羊忘记了吃草,百灵鸟忘记了歌唱。
牧民们在草原上碰见他,会说:“来,为我们唱一曲吧!”
蒙古民族自古流传许多关于马的优美的传说故事、英雄史诗、说唱文学,以及歌谣、祝词、谚语、格言,多处会提到马。蒙古族歌曲中,以马为主题的歌曲数量仅次于歌唱母亲和家乡的歌曲。
阿爸唱《立鬃的青马》。深情的音调,一下子在空中飘散开了:
立着鬃毛的青马哟,
是枣骝马的驹儿。
往来徘徊的姑娘哟,
停留停留再走吧。
云雾弥漫的山顶上哟,
扛上步枪去攀登。
和我眷恋的姑娘哟,
谈上几句知心话吧。
年轻人听不够,让他再唱一个。阿爸唱的歌,有赞颂养育之恩的,有思念家乡的,还有歌颂动物歌颂爱情的。阿爸的歌声仿佛是从身体里发出来,嘴唇几乎不动,也张得不大;歌声越高,上嘴唇越往下拉,仿佛阿爸的肚子里装满了歌声。
我在那闵珠尔罕该的北山上哟,
等待你到天蒙亮!
如果知道你失约哟,
我的等待是多么荒唐!
骑上英俊的金黄马儿哟,
不待天黑我就去了!
可我要早知道你在爱着别人哟,
我在这儿熬夜傻等为的是啥?
我那可爱的骏马儿哟,
不分昼夜地都不卸鞍!
如果我知道你爱的是别人哟,
我压根儿就不去将你盼。
岸上的大雁赶不赶哟,
空中的乌鸦射不射?
一想起她已经变了心哟,
想死了我也是白搭!
有时候,他唱着唱着,歌声会变得凄惨忧伤起来,连他骑的黄骠马都听得支棱着耳朵。阿爸抱住马头,说:“我的歌唱给它听,它喜欢我的歌,它不会烦我。”
阿爸唱《孤独的白驼羔》《清秀的膘马》《清凉的杭盖》《金色的空格达山》……随着那悠长、磁性的“诺古拉”(蒙古族长调中特殊的颤音唱法),叹息般地在头、鼻、胸、腹腔深处颤动,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在草原上诉说着别离、思念和重聚。唱着唱着,阿爸把眼睛闭上了,如果不是嘴角微微地动,你不会相信是他在唱。听过蒙古族长调的人都知道,蒙古族人抒情,完全可以在一首民歌中,将心掏出来给你瞧个仔细!
阿爸的歌声中,有柔情似水,有悲悯苍凉,有孤独无奈,有慷慨激昂,有婉转悠扬……蓝天白云,吃草的牛羊,在那起伏的颤音里,跳动着生命的坚韧和顽强,带给人身不由己的悸动。在漫无边际的草原与蓝天之间,有一股原野的风在浮动,在凝聚,草原上的一切,震撼人的灵魂。“唱着唱着,就会管不住自己,要流泪……”
阿爸的歌声里,有牛哞羊咩,有炊烟在袅袅升起;有蚂蚱在草丛中跳跃,有露珠在花叶间化成气霭;有公马的嘶鸣,有母羊在摇动尾巴;有百灵鸟在草窠里孵蛋,有禄马风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有达里诺尔湖的华子鱼在水中抢食,有阿斯哈图的公母鹿在追逐……
虽然,穿蒙古袍子的人少了,骑马的人少了,会唱老歌的人更少了,阿爸却倔强地说:“只要天地还在一起,只要蒙古族人还在马背上,只要我还喘气,那长调就会一直流传下去。”
6
袅袅的炊烟。低矮的毡房。洁白的羊群,云朵儿一样。
草原深处,一群马远远地走过来,领头的是一匹飘着金黄色鬃毛的栗色儿马。
阿爸牵着黄骠马,跟在马群后面,肩上扛着的套马杆打着战儿。
“我的父亲爱唱歌啊,歌声飘荡绿色的草原上;我的父亲是牧马人,歌声伴我童年的时光;我的父亲是牧马人,歌声伴我到远方……父亲的肩膀,父亲的胸膛,父亲的身影雄鹰一样……” 歌词很简单,只是低回深情的调子,让人的心一阵阵温暖,一阵阵哀伤。
“在阿斯哈图山的顶峰,配上了镶银柄的缰绳,额嗬哟——那是我追风的黄骠马。在密林里追捕野兽,总是它跑在前头,额嗬哟——那是我追风的黄骠马。”
黄骠马仰着漂亮的头,安静地看着阿爸,眼睛里润着水一样的温情。它听得懂那歌声,可是它无法诉说,所有的感情,郁积在目光里,只能在暗夜独自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