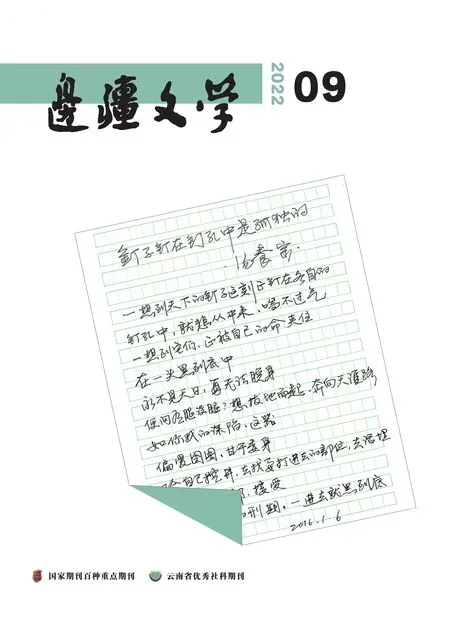带块石头进城
李光彪
从南到北连绵不断的山脉,似刀砍断的树丫分成两半,一半是后山,一半是前山。后山的怀抱里搂着个村庄,坐西向东,前仰一座如龙似虎的石头山。那村庄的名字怪怪的,叫“铁厂”。陌生的人一听,都以为那里机声隆隆,是个铁矿或是熔炼钢铁的地方。而本乡本土的人都知道,那里既不产钢,也不产铁,只是盛产石头。所以,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两句民谣:“铁厂 —— 铁厂,是块石板。”
那个村庄就是我的老家,我就出生在那块“石板”胎衣上,从小在那块巴掌大的山旮旯里长大。
老家由于山高石头多,山上的树木和我一样长不高,大多数都做不了顶梁柱,只是蓬蓬松松,长成一片片“爬地松”之类的小灌木。因为石头多,可开荒种植庄稼的土地也就少,加之坡陡土瘦,气候冷凉,水稻难产。所以,除小河边那几块裤带宽的水稻田外,几乎都是依山梯迭的“雷响田”山坡地,只能种植包谷、黄豆、红薯、洋芋、荞麦之类的旱地作物,使得老家物产稀少,吃食单一,生存艰辛。
老家的人虽然没有多高的文化,但由于生产生活都离不开和石头打交道,就经常用石头喻人说事。比如夸奖人,说坚强能干的男子汉叫“柱脚石”,说乐于助人的人叫“垫脚石”,说忠实诚恳的人叫“铁心石”,形容饱经风霜的老人叫“磨刀石”。骂唱对台戏的人“绊脚石”,骂狡猾的人“鹅卵石”,骂厚颜无耻的人“茅厕石”。就连一些地名也叫“大石崖”“石岗坡”“癞石头”“小石桥”“小石沟”。村庄的名字更直截了当,就叫“大石板”“小石板”“长石板”“石板冲”。夸奖精打细算的人,就说“一个石头打几个鸟”。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就说“穷人需要富人帮,大石头需要小石头镶”等等。给娃娃取名字,也要带个石字,叫“小石头”“小石生”“小石珍”“小石兰”之类的,简单明了,又好听,又好记。
我们小孩子喜欢玩一种“丢石子”的游戏,每个人衣袋里都装着十个蚕豆大的石头,三三两两找一块平整的地方坐下,确定顺序后,依次用一个石子做母本,高高丢起来,迅速抓起地上的两个石子,并接住落下的母本石,放在一旁。然后,再循环往复把母本石高高丢起来,迅速抓起地上的三个石子、四个石子。如果地上的石子没有全部抓起来,或抓到手的石子掉了,或是母本石落下来没有及时接住,就是输家。觉得不过瘾,就把接母本石的“接”改为“啄”。玩的方法不变,只是眨眼间工夫必须抓起地上的石子,老鹅啄食似的“啄”住落下的母本石,很考手脚和眼力。我们男孩子玩“滚珠子”,买不起钢珠、玻璃珠,就找一块坚硬的石头,自己磨一个石珠子,在地上互相滚弹。一块土场子,或是一块院子,就是战场,石珠子追石珠子,石珠子打石珠子,个个都想当神枪手,又刺激,又过瘾,一不小心,就玩过了头,招来父母的责骂声。
石头与老家的人生死相依,修桥铺路、修沟打坝、建房盖屋、修坟刻碑,样样都少不了石头。一直以来,家家户户都喜欢用台阶高来比示生活水平的高低,很多人家都要请石匠打方方正正的“条子石”,把自家门前的台阶一级一级修建得光滑体面,让人既可以走路,又可以当板凳坐。不仅如此,在修建灶时,都要精挑细选上等的石头,做灶膛石、灶台石、灶楣石、灶门石,土石相间,牢固耐用。我家的火塘也是用方方正正的石头入地镶砌的,又耐烧,又保温。每天跨进堂屋门槛,就会感受到火塘里散发出的暖流,感受到家的温暖。
老家的人死了也离不开石头。列祖列宗的坟墓都用石头垒砌,请石匠在石碑上雕刻动物、花草、房屋等图案,中间花岗岩的碑心石上,雕刻着死者的名字以及直系亲属一代代人的名字。雕刻着十几行诗歌一样的文字,简明扼要记录着死者的一生。整座坟镶砌成一间石头房的模样,以显孝心,光宗耀祖。特别是老祖宗的坟山上,还要立一块又高又大醒目的“山神碑”,有了山神碑,山就成了神山,树就成了神树,谁都不敢乱砍树木,自然而然森林就和老祖宗一样得到了保护。
适者生存。有的人家会石匠手艺,叮叮当当,把石头雕琢成石磨、杵臼、猪槽、盐臼、石缸等经久耐用的石器,卖给山前山后的农家使用,找到了一条养家糊口的生财之道。因而,户户人家都离不开石头做的用具,用那些石器舂米、磨面,或是凿石槽喂猪养畜,凿石缸盛水装粮。家家户户门口都有一块磨刀石,专门用来磨砺刀具,切菜、砍柴、割稻谷等等。
生性如磐石般坚硬的母亲,隔三差五都少不了要与那些笨拙的石器打交道。每天黎明,几乎都是被母亲舂米、磨面的声音从睡梦中把我唤醒,催我起床上学;黑夜也常常伴随着母亲舂米、磨面的摇篮曲催眠入梦。天长日久,倾听舂米、磨面的声音,成了我期盼的生活,美好的追求。似乎只要石磨被母亲推转,杵臼被母亲的棒槌舂响,家里就会锅里有煮的,甑子里有蒸的,碗里有吃的,不会断盘缠。
记忆犹新的就是那扇簸箕大的石磨,母亲端来待磨的杂粮,舀几瓢放在磨头上,拴上扁担,抵在脐部,均匀不停地迈开脚步,用力一圈又一圈绕推。原先还是颗粒分明的粮食,经过上下两扇磨的咀嚼,就变成了流洒不断的面粉,白花花吐落磨槽。小时候不懂事的我,像母亲身后的尾巴,遇到母亲磨面时,总是去胡搅蛮缠,不让母亲推磨,母亲只好用绣花裹被把我捆在她身上,背着我推磨。有时,母亲也把我放在磨头上,说是让我“坐飞机”。只见母亲用一只手扶着我,一只手掌握着脐部的磨扁担,加速不停奔跑,石磨由慢到快旋转,嗡嗡作响,周而复始,我一阵眼花缭乱,像是生了两只翅膀飞起来似的,真过瘾。等我有磨头高时,母亲常安排我和她一起学推磨,才知道磨面并不是游戏, 而是一种艰苦费力的繁重劳动。一听说要我去帮母亲磨面,我总是找借口,宁可去拾粪,也不愿意去推磨。
杵臼也是母亲经常都要舂米的石器。一箩稻谷,只要母亲手里的棒槌一举一放,不停地舂捣。一会儿工夫,就脱壳成米了。尤其是舂糍粑、饵块,母亲把蒸熟的米饭倒进杵臼,趁热迅速舂,眨眼间,就粘成团,拿出来放在簸箕里搓揉,就成了糍粑,饵块捏成的小狗、小猪、小鱼、小鸟等各种小动物,让我既可以玩,又可以烧吃,喂养着我,在缺荤少肉的时光里快乐成长。
也常听母亲对我说:“你吃石头都会消化啊。”确实如此,在那个清汤寡水的年月,童年的我,舀饭时,巴不得用脚踩,每顿稀里哗啦两三碗饭菜下肚,蹦蹦跳跳,脚不停,手不住玩耍,不知不觉,就像鬼抹肠子似的,“罗锅肚”变成了腾空粮食的口袋,还没到饭点,就围着母亲叫饿了。
当我有锄头把高时,少不了要参与挖田种地的农活。可是,当我高举锄头狠狠挖下去时,锄头不听我使唤,一接触泥土就打瞌睡。母亲就开始叨念:“一个石头二两油,三堆狗屎瘦田头。”叨念过后,母亲就会叫我放下锄头,专门跟在她屁股后面,捡那些土块中大大小小的石头。慢慢的我才明白,捡去一个石头,就可以多种一棵油菜,多榨二两油,多拾一堆狗屎猪屎,就可以积少成多,培肥一个田头地力,种出好庄稼,多产粮食。可是,田地里的石头就像洋芋红薯花生,生育能力总是那么强,上次耕种时才捡了很多垒田埂地埂,下次耕种时,那些鸟蛋大、鸡蛋大的石头,又不知从哪儿滴里嘟噜冒出来很多,伴随着庄稼生生不息。
“人在路上走,刀在石上磨。”老家的人常常把磨刀具作为衡量男孩子的标尺,如果刀斧磨不锋利,男孩子长大了就不会有出息。磨刀石有多硬,男孩子长大就会有多硬。所以,挑选一块坚硬的石头磨刀斧,是每一个男孩子从小就必须练就的基本功。
常听母亲回忆说,我刚会咿呀学语学爬的时候,为了做家务,经常把我放在杵臼里,让我坐在里面,像个抱窝母鸡,既稳当又安全。而且是舂米的杵臼教会我慢慢站立起来,学会“打灯灯”的。
的确如此,从我记事起,我家堂屋门外的厦子上墙角边,就蹲着一个舂米的石杵臼,屋檐下站着一个圆溜溜大腹挺挺的石缸。长满嫩生生遐想的我不知多少次好奇地问过爷爷奶奶,可谁也说不清石缸的来龙去脉,只知道那个皱纹满面的大石缸比爷爷的爷爷还老。
也常听母亲说,我是那个牛腰粗的大石缸领养大的。那时,顶针高的我还没有断奶,学走路经常摔跤,别出心裁的母亲就在石缸里铺上羊皮褂和棕衣,把我抱进石缸,让我在石缸里摸爬滚打,逐步扶着石缸边缘站立, 一步一步挪动,歪歪斜斜练习走路。年幼无知的我在石缸里玩累了,头一歪,就倒在石缸的怀里睡着了。有时待久了,无意识的我就会随意撒尿、拉屎,然后把尿、屎当作橡皮泥玩。等母亲忙完手里的活计来看我时,见我满身“油画”,又赃又臭。哭笑不得的母亲像抓小鸡似的一边把我拧出石缸,一边用水给我冲洗,一边给我换衣服。可是,母亲手里的活计一忙,又只好无奈地把我丢进大石缸,交给那个不卑不亢的“保姆”,一边做家务,一边照管我。
一天天在石缸里长大的我,看着母亲在厨房里忙前忙后煮饭,经常多脚多手去捣乱。母亲抱我不行,背我不行,哄我也不行,实在拿我没办法,又只好打发我一点零食或几样玩具,把三四岁的我强行放进大石缸,让我独自一人玩耍。慢慢的我才明白,母亲把我交给石缸“保姆”,就像把那些不懂事偷吃庄稼粮食的猪鸡关在栅栏里、笼子里一样,既孤独,又不自由。直到我玩得无趣,哭爹喊娘时,母亲才把吃闲饭的我抱出石缸,“解放”我。从那以后,每次我做错事,母亲就不由分说,把我扔进大石缸,任我发泄。于是,被石缸囚禁的我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如井底之蛙的我,在石缸里东跳西蹿,恨不能立马长高,爬出石缸。可是石缸四周如一道铁铸的屏障,让狗高的我望而兴叹,无计可施。直到我撕心裂肺嚎啕大哭,软嘴软舌向母亲承认错误,立下痛改前非的悔过诺言,母亲才走近石缸,一边教训我,一边把我抱出石缸,一边帮我揩眼泪。可年幼无知的我,常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一次次接受石缸的“再教育”。就这样,石缸成了母亲惩罚我最管用、最安全的刑具。
走过穿开裆裤的年龄,我不知不觉就有石缸高,经常可以翻越石缸,把石缸当马骑。坐在石缸上玩耍的我,仿佛是骑在母亲的背上和母亲玩“蚂蚁驮盐”,无比快乐。那时,老院子是个正房、面房、厢房组成的四合大院,住着六户人家,我们一群孩子无拘无束,经常东家出、西家进,三五成群,叽叽喳喳一起玩“躲猫猫”。小伙伴们不是躲在门后,就是躲在床下,或是墙旮旯里,尽管隐蔽,但很容易被我找到。我躲进大石缸里,像只蝙蝠身子紧贴在石缸边,粗心大意的小伙伴们却很难发现我,都要费很多神,才能找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我。
那个大石缸还盛装过我童年的忧伤。有一次,饥饿的我放学回家,偷嘴吃开水泡饭,慌乱中不小心把热水瓶胆打坏了,闯祸的我正在清扫现场,正巧被下田干活回家的母亲遇见。母亲一边骂我是个“乱脚龙”,一边拿吆鸡棍准备教训我。急中生智的我还不等母亲追上来,就像一只被猎狗追撵的兔子,拔腿插翅般逃出家门,纵身一跃跳进石缸,如骄阳下的一滴露珠,瞬间就蒸发得无影无踪。躲到哥哥姐姐们回家吃饭时,我才爬出石缸,垂头丧气进屋,在全家人的劝阻下,母亲心头的火才慢慢消退,脸上也逐步“阴转晴”。顿时,我高吊的心如石头落地,是那个石缸“保姆”掩护了我,让我幸免了一次皮肉之苦。
那时的乡村没有自来水,每天吃的水都要到村庄脚下的水井里挑。遇到雨季路滑泥泞,家家户户都把水桶、盆摆在屋檐下,接唰啦唰啦流下来的瓦沟水用。我家的那个大石缸就派上用场。每次接满一大石缸雨水,沉淀后用来洗脚、洗脸、洗菜,足够全家人用一两天,让脚不着地奔波忙碌的母亲赢得了更多做针线活的时间,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身上的破衣旧裳,经过母亲的缝补,就会变得有脸有面。雨过天晴,母亲拔掉石缸底的木塞,把石缸刷洗干净,石缸便成了盛装篮筐农具的“百宝箱”,成了我们“躲猫猫”的窝。
有时,母亲叫我磨菜刀、柴刀、镰刀,我就打一碗水,在石缸的口上磨。磨来磨去,石缸的嘴皮磨掉了一层又一层,我也一天天长大,成了一棵松的小伙子。
老家的村庄以一条三四百米长、近千级的石梯为轴,如一只巨人的手,把古老的村庄举在半山腰。凸凹不平的石阶如祖先的脊梁,背负着山村厚重的历史,岁月的沧桑。
村庄躺在山坡上,说大不算大,说小也不小,几百年的繁衍生息至今,也只有稀稀疏疏五十多户人家。常听老人们讲,列祖列宗村庄的人从一个宗族分出三个支系,第一个支系是掌房家,第二个支系是二房家,第三个是三房家,依次派生出一代又一代后裔。依次分布在石梯左右的房屋和院落,就像村庄发达的肌肉。那几个屈指可数居住着各家各户的院子,也称为老院子、新院子、大椿树院子、伙食团院子。村庄里的人并无其他杂姓,除了娶进门的媳妇外,就连入赘的上门女婿,也必须改名换姓,全部姓李,都是同一个祖宗的后生。几乎每个大院的门都面向石梯,全村人出入,上上下下,来来往往,石梯都是必经之路。从早到晚,春夏秋冬,石梯静静地承载着村庄的早晨与黄昏,承载着村庄的快乐与忧伤。
在我枯萎的记忆里,那架从村脚延伸向村头的大石梯,是村庄的主轴,是村里人茶余饭后的乡村文化演展舞台。每天晚饭后,村里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会不约而同来到石梯上,找块合适的石板坐下,三五成群凑在一起,吹牛聊天,谈古论今。天南海北,家长里短,家事村事,好事坏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很多花边新闻,都会在石梯上联播,在石梯上群发。谁买了一套新衣服、一双新胶鞋,谁家娶了新媳妇,谁家添人增口,都会在石梯上一一登台亮相。老弱妇孺,大人小孩,抬头不见低头见,聚在一起,就是一个大家族。人歇手不歇的村里人,有缝针线纳鞋帮的;有吸水烟筒抽烟、咂烟锅吃草烟的;有人就汤下面,端来一盆水,坐在石梯的边沿磨刀子,妇女们就顺便请他戗剪子;有吹竹箫、弹三弦、唱调子对山歌的。不论是谁,不分才艺高低,那些无师自通的民歌手,都会在石梯上层出不穷,比拼展演。父亲是个二胡手,经常在石梯上边拉二胡,边唱放羊调、爬山调、过门调……悠扬的二胡声响彻石梯,萦绕在山村的上空,扎实惹人喜欢。就这样,有说有笑、有苦有乐的乡村人,不怕蚊虫叮咬,再累也常把石梯当作板凳,坐在乡村的大客厅里,久久不愿离去。直到圆月老高,或是镰月西落,或是打雷下雨,才恋恋不舍各自归巢。
石梯是孩子们的乐园。童年的我们,有时玩“讨小狗”,有时玩“弹蚕豆”,有时玩“拍菱角”,有时玩“小猫钓鱼”……一切自娱自乐的玩耍乐趣无穷。最吸引人们目光的是那几块光滑的石板上雕刻出的棋盘,有争先恐后下豆腐棋、牛角棋的,有打扑克、玩游戏的……从早到晚,石梯上都或多或少都坐着几个贪玩的孩子、歇气的老人。因此,孩子、老人从不寂寞,石梯也不缺少伙伴。那架石梯就在我家大门外,吃午饭、晚饭时,我常舀一碗饭,盛上菜,跑到大门外的石梯上,坐着一边吃,一边欣赏石梯上那些特有的乡村风景。
石梯是验证乡村人品德的试金石。谁家丢了一只鸡,几个鸡蛋,瓜菜水果被人偷摘了,就会有人在石梯上拉开嗓门,高音喇叭似的指桑骂槐,骂那些手脚不干净的人。这一招还真管用,骂过之后,知情的人就会悄悄提供线索,做了亏心事的人,也会逐渐醒悟,转个弯悄悄物归原主,慢慢变得干净起来,和和睦睦相处。也有些人家,有时会端着腌菜、葵花瓜子等零食,一一散发给来石梯上玩耍凑热闹的人吃。见者有份,哪怕是一块粑粑,一根甘蔗,只要能进嘴的东西,寄生在石梯上的人,都可以尝到人情味。
石梯是透明开放的。有些哺乳期的妇女,拉起衣服,就敞胸露乳当众给自己的婴儿喂奶。眼睛发炎疼痛的、手脚皴裂的人,就会凑过去,讨几滴白汪汪的乳汁,当眼药水涂眼睛,当香脂涂抹松树皮般的手脚。谁也不觉得是奇耻大辱,谁也不戒备谁。有些婴儿,从小生下地娘就缺奶水,经常抱着嗷嗷待哺的婴儿,向奶水充足的妇女讨几口奶吃。那架石梯如村庄硕大的乳房,大公无私地喂养着村庄的每一个人。
石梯是村庄的主动脉。从早到晚都有人从它的脊梁上走过,听到脚步声、咳嗽声、说话声,远远的石梯也就能猜出是谁来了。出工收工、上山砍柴、下田干活,牛羊出圈、放牧归村,谁早谁迟,谁勤劳、谁懒惰,一切的一切,夜以继日守候着村庄的石梯,都历历在目,铭记在心。
石梯从不嫌贫爱富。在石梯的眼里,没有贫富之分,不管你是穿皮鞋、布鞋、胶鞋、凉鞋,还是赤脚从石梯上走过,石梯总是那样默默无语。来的都是客,不管是谁,你看上石梯的哪一块石头,屁股一坐,就是最好的板凳。石梯从不喜新厌旧,不管你离家多少年,不管你多长时间没来,天长日久迎接着一茬茬降临人间的孩子,娶进门的媳妇,送走一茬茬命归黄泉的老人。
岁月沉浮,一代又一代,村庄的人去的去,来的来,石梯总是依旧躺在那里,毫无怨言地在风雨中、在朝朝暮暮中静静的等着你。
如今的老家早已通了电,有了碾米机、粉碎机、磨面机。舂米、磨面早已被现代化的机械代替,那些回荡在山村的舂米、磨面声,变成了悦耳的蜜蜂酿蜜声,谱写着乡村新生活的乐章。那些曾经像母亲的嘴一样,咀嚼着粮食喂养我们长大的石器,也退居二线,成了没用的东西,搁在了不起眼的地方。一切的一切,都如死去的老人,埋进土地的祖辈,被老去的岁月尘封。
而那些漫山遍野祖祖辈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石头,却变成了稀奇的建筑材料,被源源不断镶砌进了乡村公路通达硬化、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广场地板铺筑等现代文明工程。那些牛高马大的石头,被设计师们布入图纸,一个几万、十万、几十万不等的昂贵价格,变成了稀奇的商品,被搬进了城市,矗立在广场或公园,镌刻上了名人的题字,成为一道“石来运转”的美丽风景。
在城市立足安身之后,磨菜刀成了我唯一的家务事。母亲从乡村来帮我带孩子,年近古稀,全口牙掉光了,咀嚼不便,只好从老家带来一个小石盐臼,让她舂食物吃。我给母亲买了果汁机,母亲不习惯,一直用石盐臼冲捣食物,直至垂暮之年。母亲去世后,我请老家的石匠给母亲打了一座墓碑,全部用石头垒砌而成,了却母亲生前的心愿,也垒起了母亲在我心中坚硬如石的形象。
清明节我回老家上坟,从母亲安息的坟山下来,沿着村庄到处转转,人也越来越少,那架石梯两旁似心肝肺腑的老院子很多已经拆迁,已是残垣断壁。剩下为数不多的几间老房子,房屋门上挂着生锈的铁锁,房顶瓦砾上丛生的杂草已经枯萎。唯有那个磐石如牛、长满青苔,搬不走的大石缸,依然站立在废墟中,如一个背负大地、脸仰苍天的乡村老“保姆”,脉脉含情地收藏着乡村的雨露阳光,珍藏着我闪闪发光的童年。
从老院子出来,我顺着村庄脊梁的大石梯往上走,已经看不到当年谈笑风生的情景,一屁股坐在当年那块下棋的石板上,牛角棋、豆腐棋盘的线纹还清晰可见。我等了很久,想等一个村里人下棋,一直没有人来,只有一条狗伸长脖子向我汪汪狂吠。
起身回城的时候,我从老家带来一块石头,放在门外,专门磨刀具,切割回不去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