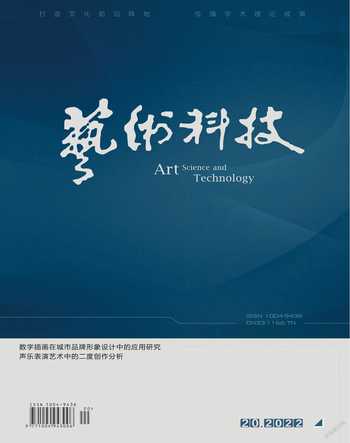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新媒体艺术的可能性探讨

摘要:新媒体艺术的“新”应该体现在与传统艺术相比,其在探索和表现人类精神这一艺术基本主题上有什么独特的贡献。新媒体艺术的虚拟性叙事、多屏幕叙事等叙事方法与表现现代人的生存境遇有双向的默契。文章以《重返桃花源》的创作为例,分析如何运用多叙事的创作方法,以移步换景的方式展示都市人面对现代生活的尴尬与窘迫,以唤起观众对现代性的反思。
关键词:新媒体艺术;现代性;虚拟性;《重返桃花源》;微电影
中图分类号:J904;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20-00-03
当下,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媒体艺术,其一部分成果已经进入商业领域,有一部分艺术团体已经可以不依靠收藏制度来获取利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以沉浸式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作品。伦敦蛇形画廊发行的未来艺术系统手册中调研了日本Teamlab的运营模式,他们提出了艺术堆栈(Art Stark)这一战略,这是一种以出售门票为主要获利方式的新媒体装置艺术展览。在这种展览中,观众更多关注的是,数字技术带来的比架上绘画或雕塑更强烈的感官冲击和全新的身心体验。但是不论这种新的艺术形式披上了多么炫目的数字化外衣,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必然承载着创作者在人类精神探索上的价值追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讨论新媒体艺术“新”在哪里的时候,应该围绕这样一个维度,即相较传统艺术,新媒体艺术在探索和表现人类精神这一基本主题上有什么独特的贡献。比如前文提到的新媒体艺术团队Teamlab,他们擅长打造沉浸式场景,即借助数字技术手段,调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多感官体验,营造虚拟性、沉浸性氛围,能让观众获得传统的艺术形式难以带来的沉浸式深度体验。对此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种沉浸式体验背后是有价值诉求的。当人们敞开身心融入艺术家所创造的仿真世界,会在产生震惊和快感的瞬间建立与他人、万物的关联,进入万物与“我”互联、与“我”合一的审美境界,即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是艺术家打造沉浸式场景背后的价值诉求。再如多视角叙述,新媒体艺术借助媒体技术,可以进行多重投影、多屏幕叙事。彼特·韦伯指出,“由投影于多重屏幕的多重视角所带来的不同步、无线性、无历史逻辑性,看似不合理的、平行的、多重的叙述,是前卫艺术家的目标所在”[1]。多屏幕叙事不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其背后还蕴含艺术家对现代人生存状况的探索,它常常通过时空折叠的方式,把不同阶段的人生(时间折叠)或者各色人生(空间折叠)并列在一起,让观众深刻体会现代人生存的偶然性(无线性)、荒诞性(无历史逻辑性)。
因此,重新质询新媒体艺术对体验背后的价值诉求是有必要的。当艺术家借助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场景,其所要达成的是一种同一性体验,想要使观众与其一同沉入其所营造的诗意浪漫的世界。比如运用多屏幕叙事,在开放给艺术家的众多可能性之中,有一种可能是要达成一种反思性体验,提醒人们关注并反思生存的困境。
本文以笔者和骆煜超、彭浩旻共同创作的《重返桃花源》为例,探究如何运用新媒体艺术表达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该作品曾获亚洲数字艺术展艺术奖、华盛顿华语电影节最佳实验电影等荣誉。我们企图通过三屏影像装置,将都市人面对现代生活的尴尬与窘迫以移步换景的方式呈现出来,以重构《桃花源记》这一具有乌托邦性质的符号作为策略,唤起观众对现代性的反思。
1 创作主题:现代性的悖论
《重返桃花源》所要揭示的是现代性的悖论。现代性是西方社会伴随启蒙运动生成的一个重要概念,启蒙唤醒了人的理性,而随着科学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发展,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也愈发强大。然而,理性主义在推动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不少问题和危机:其一,在经济生产领域,技术的发展以及对生产效率、可计量化的追求,使劳动者成为生产流水线中的一个部件,人被异化为“物”;其二,在社会治理领域,追求管理的可控性、方便性,使科层制成为现代社会最理性的制度选择,但是,在强大的科层体系及格式化管理中,个体的独立与自由发展常常会被压制和忽略。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种现代性的悖论,人们在享受市场经济及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和便利的同时,也感到主体性和个体自由被挤压。尤其是在城市化浪潮中,“北上广”曾经或者现在仍然是大多数年轻人共同的乌托邦幻想,大多数年轻的异乡人都觉得这是一个足以发生奇迹的、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丰功伟业的场所。然而近年来“逃离北上广”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个乌托邦幻想犹如钱钟书的《围城》所描写的生活一样,“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人们开始发现,城市作为一个庞大的机器,也有压抑人性的灰暗面:在分工明确、层级严密的庞大管理体系中,在以追求效率为逻辑的生产与服务链条中,大多数人面对的只是被分类逻辑切分的一个个横截面,或者只是生产或服务流程中的一个零部件,无法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带来的满足感。或许现代社会在追求发展和效率的同时,应当放慢脚步,关注个体的生存困境,不要让有抱负的都市人在城市中迷失,这是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
2 叙事策略:桃花源作为反乌托邦叙事的可能
乌托邦的精神源于危难之际的人们对现实的不满,转而将目光投向不可知之地,重建一个符合内心向往的社会。中国最符合乌托邦精神的文本是《桃花源记》,陶渊明目睹东晋社会动荡腐败,描述了一个理想世界——桃花源,并用与世隔绝的方式来回避现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重返桃花源》的敘事策略则是将桃花源作为反乌托邦的外壳与框架,反乌托邦表达强调一种里外特质错位而引发的矛盾。
而选择桃花源作为作品叙事的起点与框架,就必须对《桃花源记》进行重新解读,找到桃花源与现代性的重合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本是靠语言想象与组织起来的一个避世空间,其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描绘的是一个房屋排列得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的内在空间,以此来传达安定和谐的信号。这一句使笔者联想到自包豪斯运动以来,全世界的城市都争先恐后地修建高度同质化的方方正正的现代建筑,而这种建筑语言本身就指向标准化的、高度理性的、井然有序的制度体系。在作品中,笔者将这本来寓意社会安定和谐的叙事符号转变为寓意高度理性、追求效率和分类的现代性。
姚大钧指出,人们对“赛博朋克”的图景印象和对中国香港九龙城寨及东京黑帮的审美趣味,来自中国外部的“东方主义”审视视角[2],而开发“后东方主义”是中国创作者的使命。将桃花源作为反乌托邦表达叙事就是对“后东方主义”的探索尝试。
3 叙事节点及基本内容
《重返桃花源》的叙事主题是看似美好繁华的现代社会背景下,严密的现代秩序对个体价值的挤压。针对这样的宏大主题,需要一个个不同身份的个体叙事去支撑。接下来本文将介绍作品中的三个叙事节点。
第一个叙事节点的叙事空间是写字楼。聚焦于城市中三个似乎毫不相干的工作人员:外卖软件维护工程师、值班医生、外卖小哥。工程师因为加班维护服务器而住院,从而引发了他与医生、外卖小哥之间连锁反应的隐秘的加班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互为因果的关系将无限循环往复。这个节点试图通过一个荒诞的闭环连锁事件暗示为什么“996”的工作制度无法被打破。
第二个叙事节点的叙事空间是狭小的出租屋,一对情侣为了要不要养猫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男生一直说房子是他租的,他有资格决定是否养猫。男女双方虽然早已貌合神离,但却因为房租昂贵,没有办法离开这间小屋。
第三个叙事节点发生在高速移动的地铁中,两个下班的男人在摇晃的车厢中因为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被挤压,徘徊在快亲上又没亲上的窘迫场景。这种体验指向巨大的生存压力给生活在城市中的个体造成的尴尬与不安。
4 表现语言及手法
4.1 《重返桃花源》的空间构造
《重返桃花源》的空间构造以反乌托邦的表达策略进行设计,即将空间分为表面与内里两层,并在视觉语言上强化其矛盾。在第一层空间,作者将桃花作为美好生活的象征符号放置在由钢筋水泥构成的城市中,呼应原文“忽逢桃花林”。这样做是为了塑造金玉其外的表象,让观者第一眼看到画面误以为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在整体画面的设计中,只有桃花是有颜色的,其他事物皆为没有色彩倾向的黑白灰,突出其非常态。为了缓解桃花林无地扎根的突兀,笔者将云作为桃花的扎根平台,这样做是为了营造一个“仙境”氛围,使画面中的城市和观者固有印象中的城市区别开来,令其逐渐陌生化。同时,为了模糊观者对现实与作品内部空间的看法,使观者的思维不断在作品与现实记忆之间来回跳跃,作者把广州塔作为第一层整个空间的中心位置(见图1)。桃花、现代城市、云层、广州塔组成了一个超现实的异空间图景,给观者留下平和、美好但又有一丝非正常因子的第一印象。
在第二层空间里,笔者构造了一个纵向分布的空间形态:城市中从高处的广州塔、高楼大厦一直到最底端的城中村居民房,强调了空间的纵向分布,削弱了其横向的延展性,这种视觉语言在知觉上强化了从上到下、层级严密的现代社会,观者可以从建筑的外观感受到笔直、有序的视觉语言。
4.2 《重返桃花源》的视觉语言探索
邱志杰在《总体艺术论》中说过,“在你和窗户之间存在着的这根弧线,你视而不见。假如有一只蜜蜂从窗口飞到了你的桌前,这条弧线就被‘实现了”[3]。笔者将其理解为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内容作为已经设定好的事物已经存在于设定里,犹如“窗”“桌前”,而蜜蜂飞过的弧线才是艺术表达的重点,即以一种很少被人使用的表达方式来建立观者与事物的联系。这种表达方式在梵高的笔下是扭曲的点彩,在毕加索的笔下是立体主义的视角,在杜尚的手中是将日常的物品解构并重组,因此探索一个新的表达手法是艺术创作中的重点。
经过探索,首先确定作品的主要表达手法,即水墨动画,因为其黑白灰的视觉语言有别于正常有光谱颜色的观察视角,且足以体现现代性带来的压抑感受。同时,国画的笔触能与笔直的城市外观拉开距离,具备表达多元化且不易被现代性分类的特性。然而,传统的水墨画动画风格过于优美灵动,鉴于此笔者对表达手法的细节进行了调整。笔者首先抛弃了使用水墨进行堆叠的方式,保留其透明的特性,这种视角犹如X光,仿佛可以透视物体看到物体的内部构造,妄图发现被观察物的内部构造,勘破其本质,这种视觉语言创造了一个和现实截然不同的世界。其次,笔者减少画面中的留白空间,在画面空间中尽量填充笔触,表达生活的压抑感。
在制作工艺上,基于逐帧动画的工作流程,思辨性地使用Neural style transfer(NST),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算法,将笔者所描绘的关键帧风格迁移到动画中。在这个制作流程中,机器代替了艺术家完成了大部分的复制性工作,此举意图将机器学习算法的复制性作为媒介,讨论复制性和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
4.3 多屏幕媒介叙事探索
《重返桃花源》使用三个屏幕进行叙事,意在探索多屏幕媒介在展现假想的世界观时起到的作用与叙事语言。在作品中,中间的屏幕发挥展现空间构造的功能,两边的屏幕运用反乌托邦的表达策略而设计,“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冲突本质上是视角不同导致的观测结果不同。因此通过两个屏幕描绘叙事空间里都市小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两者有时充当不同的视角,有时展现假象与真相的对应关系。
高名潞曾经指出,“数码艺术的最有利的叙事方法就是它的虚拟性”“任何再现叙事都具有虚构因素,但虚构不等于虚拟。虚构(fiction)是单线的,是有故事和物象作为参照的‘另一个真实,而虚拟(virtuality)是交叉重叠的时空拼接,不试图创造另一个真实”“数码艺术的叙事可以把不同片段、不同时间和异在空间集合在一起”[4]。多屏幕叙事方式的运用最能体现数码艺术的虚拟性。
5 结语
新媒体艺术通过打造沉浸式场景获得了市场的欢迎,而笔者要进一步表达的是,新媒体艺术是有许多可能性的。新媒体艺术的虚拟叙事在媒介上与现代人的生存境遇有天然的亲近性。对现代人生来说,并不是窥一斑而知全豹,线性的叙事难以表达人生的真相。也许只有通过交叉重叠的时空拼接,把人生的各個侧面以及各色的人生集合在一起,才能表达人生的真相,才能表现现代人生存的偶然性、荒诞性。
参考文献:
[1] 彼特·韦伯.叙述理论:多重投影与多重叙述[M]//高名潞,陈小文.当代数码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8.
[2] 姚大钧.开放的科幻 开放媒体创作方法论[J].新美术,2019(6):82.
[3] 邱志杰.总体艺术论[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21.
[4] 高名潞.此即虚拟:千古一瞬和过眼云烟[M]//高名潞,陈小文.当代数码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1.
作者简介:黄钺(1997—),男,广东普宁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媒体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