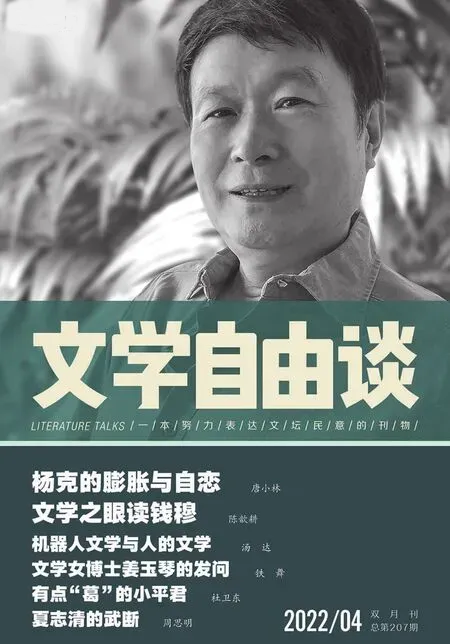《中文桃李》的乏力与缺失
□祁泽宇
《文学自由谈》2022年第3期刊发的《〈人世间〉中“善”的惯力与“真”的缺失》,指出了梁晓声的长篇《人世间》存在真实性缺失的偏弊,相较斩获茅奖、电视剧走红的一片喝彩声,这样的评价是较为冷静的真知灼见。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梁晓声的新作《中文桃李》中。如果说,《人世间》还有其面向现实问题与历史变迁的情怀,而《中文桃李》则令人有些失望。作为梁晓声的压轴之作(梁晓声称《中文桃李》 为其“倒数第二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可能并不成功。
《中文桃李》以“中文”为名,讲中文学子的学业、爱情、家庭、事业……并未偏题跑题,但小说中涉及“中文”的话语并不悦目,过多的语言堆积,让小说被这些庞杂的知识阻塞了气脉。知识言说的代言人是极富人文气质的教授汪先生,零散的插言对读者来说像是在卖弄学识的“秀肌肉”,显得多此一举。例如:
仅几页内就高频率密集地出现了等同于《文学理论》或《作品鉴赏》类的数段文字。全书中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内容几乎涵盖了文学理论、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典文学等全部文学领域。小说的前半部分,明显感受到阅读的不是小说,关注的不是情节,而如同是在上一堂文学课程。这些文本补充的成分在作家的操作下反客为主,后文但凡涉及文学事项的,都使用了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甚至还出现了以散文充填情节的情况。这样的书写不费脑力心力,没有体验和观察,对着课程讲稿做摘录,即便有千言百语,也必然是空泛的。
我们说,在小说中援引其他经典作品构成小说的情节或丰满小说的精神内涵,未尝不可。例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通宵苦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孙少平正直且顽强的人物形象奠定了坚实基础;孙少平借阅《热妮娅·鲁勉采娃》确立了少平与晓霞的恋爱关系,书中男女主人公的结局暗示了少平晓霞两个人的情感命运。这样的借引带给小说相互补充与诠释的功能,打破了作品之间的独立,体现了“互文性”作用。真正的“互文”不是像《中文桃李》这样简单的文字上的并置,而是一种对话关系,是修辞意义上的增值结构。《中文桃李》的引用基本停留在常识层面,成段的理论言说与情节构成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例如“我”和徐冉在家中边看边聊《海上钢琴师》那一段,“我”的存在仿佛只是一个赏析的代言者,除去赏析的成分,只剩下寡淡无味的对话。
梁晓声强调“想给自己的教学生涯留下一点记录”,当他已为我们奉出了《文艺的距离》《梁晓声说:我们的时代与文艺》等作品时,作为一名小说家,他更应该把心力放在小说的规则上,让小说遵循情理的逻辑,让故事写的有温度有细节。但《中文桃李》,远没有达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境界,作者的频频发言恰弄巧成拙,变成了多说无益。
实际上,无论是知识分子小说还是对知识分子个体命运的文学书写,都涉及大量的论说性学科话语。例如《应物兄》以庞杂渊博的儒学为背景,《桃李》以法律专业为背景,《活着之上》讲历史学博士聂致远的经历,《三城记》以文学为主线游走在文学沙龙、文学机构、报社媒体,还有《中文系》《怀雨人》……这些作品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对知识图谱的合理借鉴,体现出一种情怀,学科话语不直接以成段论述的形式置于台前,但在台后的精神场域中绝不缺席。
托尔斯泰在创作《战争与和平》时,也加入了大段不乏远见卓识的议论和评述,但福楼拜、托马斯·曼犀利地指出,这些塞进的议论性文字让故事“突然死亡”。《中文桃李》也是如此,填塞的文字对故事的流畅性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损害,让读者感受到的是理念大于生活,臆想多于事实的模式。当作家企图在思想性上走得更远时,却忽视了小说自身的逻辑,最终钻入自说自话的牛角尖中;相较于对生活图景深度描绘的《人世间》来说,《中文桃李》显得舍本逐末,甚至压制了文学的表达。
回头再看看梁晓声备受好评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知青小说,读起来激情满满,理想主义高扬,却“都把文学看得过分轻易,都表现出文学自身的童稚化和弱智化”。梁晓声自己对此也颇为不满,他说“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问左顾右盼,每顾此失彼,像徘徊于两岸两片草地之间的那一头寓言中的驴”。这样的问题在《中文桃李》中依然存在。作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中文”上,顾此失彼间丧失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与个人内心的体察,人物的设定趋于平面化,不够生活化,小说在真实感上存在难以遮蔽的硬伤,很难具有说服力。例如“我”与母亲的一段争吵:
这段文字被作者称为“建言”,甚至还强调,“在老妈面前,当时我的语言表达天分又获得一次释放的机会”。这种僵硬的书面化语言难称“建言”,根本起不到沟通的作用,纵使一个不谙世事的书呆子在生活中也绝不会用这样毫无头绪的言语来交流,何况“我”还是中文专业的学子。无独有偶,小说中“我”与父母的关系,基本是靠两代人间存在代沟的对话体现的,但无论是“我”与母亲开玩笑时的侃侃而谈,还是与父亲的谈心谈话,都是推心置腹式的有问必答,人物之间的对话过于客套生硬,写得像上下级间的对话,可以说与家人间的闲谈私语毫不搭界。
《中文桃李》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逻辑混乱,这让小说的叙事显得颇为乏力。作家宣称曾经的“中文系”已开始被边缘化,然而徐冉还是凭借一篇文学作品在全校轰动,为了给女主角增加光环,这样的逻辑混乱可以用偶然现象加以解释。但“我”与徐冉的爱情就显得不明所以,小说开头两个人在列车上的遭遇让他们互无好感,后来“我”竟成为徐冉造星神话的主要推手,帮助她在校刊发表文章,态度转变之间几乎没有衔接,工作后二人即使异地分居也依然维系着感情,这让人更摸不清头脑,支持他们走在一起的究竟是什么?
再从主人公“我”与徐冉二人的专业选择上看,徐冉的对外汉语专业,是文科中的理科,徐冉相较主人公更加理性。作为纯粹的文学青年,“我”则代表着“诗和远方”,生活与选择具有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不能否认,《中文桃李》在谋篇布局上突出了“我”与徐冉的差异。梁晓声也很得意,他说“有时也会沾沾自喜,虽然七十多岁了,写年轻人的爱情也还可以信手拈来”。其中的问题却十分明显——二者的相爱、结合、生活异常的平稳,没有经过特别尖锐的矛盾与对立,看不到理性与感性冲突,有的仅是两个人忙碌于工作、服从于生活的情节安排。“我”为了服从徐冉的想法去了北京,又因误会回到老家灵泉,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得到了徐冉的谅解,在小城重新开始生活。就写实的人生而言,这样的书写无可厚非,但作为中文学子,他在爱情中被动且毫无主见,我不禁疑惑那个与家人对话一板一眼,毫不克制“文学腔”和主体意识的主人公哪里去了?
这里作者借用张贤亮的《灵与肉》做了解释,“想那许灵均与秀芝之间,起先连爱都是没有的。后来呢,同命相怜,又做了夫妻,自然便有了肉体之爱。同命相怜无疑也会使肉体之爱如鱼得水。男人大抵如鱼,女人大抵如水。如鱼得水是男人感觉,鱼水之欢才是两情相悦的共同感觉。”一次性的体验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爱,或者说“我”为何爱徐冉,这是否有些太后知后觉了,况且这样的“感受”大有强作解人之嫌,生活的感受降格为对文学的沿袭。读到这里,我的体验是失真、本末倒置。或许,梁晓声对这一年龄段男女情感的状态并不了解,被迫“理念先行”,用一个熟知的爱情模式来套他们的感情发展,这样的书写勉强能够自洽,弊端是无法形成贯通连续的情节与丰富细致的叙事,其结果便是“我”与徐冉之间喜欢来得不知所以,爱情坚定得莫名其妙。
同时,《中文桃李》在精神层面的“中文”意识也不够充沛。主人公在离开自己挚爱的文学后,无论在爱情或是事业上都毫无冲击感。他平淡地面对择业,频繁地变动工作,面对感情的波动不痛不痒,在事业上获取一点点成就或偶遇挫折就当即离开,这种“后现代”式的流浪状态与中文学子的姿态太不相符,与校刊首任主编的身份不相符。另外,文琪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人物设定,在创办《文理》杂志时,她的光芒就压过了“我”,毕业后文琪也力所能及地为“我”提供帮助,可以说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比“我”更强大的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文琪为家道中落而情绪反应强烈时,竟在“我”一句不痛不痒的话中得到安适,这样夸张离奇的情节不禁令人瞠目结舌。在我看来,能够扭转或弥补二者逆差的方式,唯有回到他们的精神血脉中,而两个“中文”人的对话既没有上升到精神层面的抚慰,又没有落到现实中的增益,也就是说“中文”带给“我们”的人生补给是有限的,中文+桃李的价值设定也是虚弱的。
梁晓声所注重、强调的是中文学子走向社会的种种情形,但就我的阅读体验来看,后一部分的书写没有凸显出“中文”这一具有精神性、崇高意味的话语资源,而是刻意地予以淡化、遮掩。即使有所提及,也是像在上半部分中那样故技重施,做一些艺术鉴赏式的摘引,于是后半部分与前半部分的纽带关系就显得很微弱。毫不夸张地说,前一部分换成一个学习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的学子,加上后半部分的故事发展,都可以命名为《地理桃李》《历史桃李》《经济桃李》……
说《中文桃李》的“中文”有缺失,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讨论本世纪之初的文学艺术不应脱离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种无法忽略的文化现象。像汪老师那样抽象地讨论“人文精神”等宏大话语,也非个例,但这样的论说至少要充分考量文学和商业、审美与功利等对立因素。同时,这一时代的中文学子,至少应该接触到包含金庸王朔、畅销读物、网络兴起、娱乐电影、影视剧热、摇滚流行乐等文化元素,《中文桃李》以这一时代为背景,却没有表现出这一时代应有的面貌,更不要说是精英文化同大众文化的“世俗性”之间的冲突。在冲突不够突出的前提下,便难以充分申明文学所捍卫的道德理想,其直接后果是对社会转型中的思想价值的变化书写不到位,作品的精神性实质缺乏,导致后文中的职业选择缺乏必要的支撑。在作者笔下,高校是培育人文精神的净土,以主人公为代表的中文学子们对人生的理解以及审美的体验仍然是保守、传统的,这样一个小圈子里的狂欢极易化为故步自封的虚假与不谙世事的矫情。到最后,作者也发现故事发展必须向文化规律与事实靠拢,便加上了为房地产公司提供文化服务、拍摄纪录片的两段情节,因为前文铺垫不足,展现不出“大众文化”转向中的落差,最终显得平平无奇。最终,《中文桃李》以一个向现实屈服的桥段为结局,徐冉成为殡葬服务单位的干部,“我”在传媒领域干起了纪录片的工作,当年中文系的学子们皆悉数因种种原因远离了文学,他们的理想没有那么坚定,他们的屈服也没有那么曲折。
《中文桃李》是一部读起来绝不顺畅的作品,阅读时的停顿,不是源自审美的品读,而是因为对言语形式上的无奈,以及成段的索引与不合逻辑的表达,这些都表明作家的艺术惰性在生长,靠近生活的真诚在日渐丧失。梁晓声的过度操作无异于一种自我宣判,离开了自己一贯熟知的领域,在作家本人与“80后”群体之间的代沟与隔阂中,书写这一代中文人的生活种种成了难以把握、表达的话题。于是为了完成这部致敬之作,作家只能在书斋里编故事,通篇读起来始终弥漫着“夫子自道”。
老舍曾回忆说:“用长材料写短篇并不吃亏,因为要从够写十几万字的事实中提出一段来,当然是提出那最好的一段。这就是楞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了。”确实,伟大的小说应当具备精益求精的细致与追求。然而,享誉盛名的梁晓声却截然相反,把一个用小篇幅就可写成的小说,却大量地用“材料”填充,辅之拖沓的对话语言、不合乎逻辑的叙事情节强作长篇。小说的创作可能在谋篇布局方面付出若干努力,却在基本方向上与现实主义的小说精神相偏离,其结果便是费力不讨好,自毁“好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