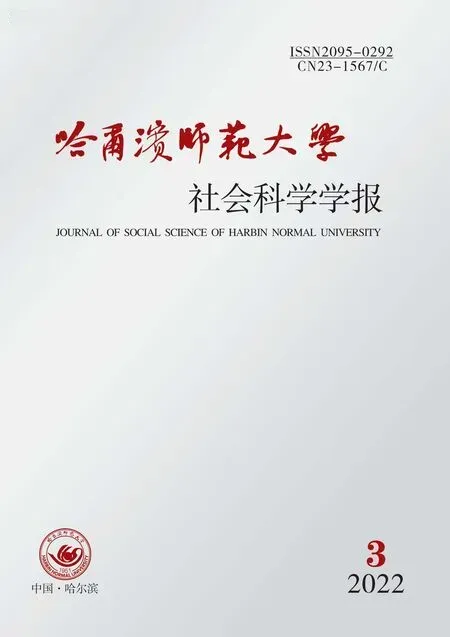大数据杀熟法律规制的误区与克服
吕明瑜,徐梦豪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一、大数据杀熟法律规制的误区
在万物皆可数的年代,大数据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与快捷,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大数据杀熟。大数据杀熟是一种伴随着互联网和数据经济的发展应运而生的一种社会现象,经营者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利用大数据对所收集到的消费者的信息进行分析、归类,依据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支付意愿等信息,对消费者实施差别定价,把“刀”对向熟悉之人,老顾客的价格高于新顾客。[1](P56)大数据杀熟的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屡见不鲜,很多人都经历过被杀熟的行为,同样的商品或者服务,新客户的价格却比老客户要低很多,网购平台、网约车服务等领域更是大数据杀熟的重灾区。经营者的逐利本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目前对大数据杀熟的监管体系不健全以及法律规制的不到位,导致了大数据杀熟的现象在社会中频繁出现。[2](P10-11)
大数据杀熟行为存在违法性,需要用法律对其进行规制。针对大数据杀熟行为,我国没有制定专门的针对性的法律,只是在一些法律中做出了某些规定。面对众多的法律,具体选择哪个法律进行规制,学界意见不一。关于大数据杀熟行为的性质认定,学界有价格欺诈和价格歧视两种观点[3](P236),认为大数据杀熟的本质是价格歧视的学者占多数。有的学者主张将大数据杀熟行为认定为违法的价格歧视,突破反垄断法关于实施主体的禁锢,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也可以实施价格歧视。有的学者主张在现有反垄断法的分析框架下探寻反垄断执法方式,对大数据杀熟行为进行规制。还有些学者认为大数据杀熟的经营者一般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大数据杀熟集中在某些特定的领域,这些领域的经营者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在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大数据杀熟与反垄断法中的价格歧视在行为表现上具有一致性,因此,在对大数据杀熟行为进行规制时,可以优先选择适用《反垄断法》,第十七条是大数据杀熟适用反垄断法的依据。而《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的发布,更是为适用反垄断法规制“大数据杀熟”行为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在大数据杀熟的法律选择中出现这样的一个误区,过于期待作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能够重拳出击,成为遏制大数据杀熟的利器。
二、大数据杀熟法律选择的误区分析
反垄断法通过确立竞争机制、保护竞争秩序从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4](P26)作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适用上应当具有针对性,不能够泛滥化。大数据杀熟行为一般情况下使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满足多种条件时才会涉及到损害市场竞争秩序,才可以由反垄断法介入。考虑大数据杀熟是否适用反垄断法进行规制,需要界定大数据杀熟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反垄断法上的价格歧视,是否使得市场竞争和竞争自由受到实质损害。只有当大数据杀熟行为构成了反垄断法上的价格歧视,实施大数据杀熟行为使竞争秩序受到侵害时,《反垄断法》才是规制大数据杀熟行为的不二之选。《反垄断法》只能规制部分的大数据杀熟行为,不能涵盖所有的情况。因此在面对大数据杀熟行为时,不能将《反垄断法》作为规制的主要法律,要结合大数据杀熟侵害的法益选择适用法律。
(一)《反垄断法》认定价格歧视门槛高
《反垄断法》对价格歧视的认定门槛高,需要满足多重条件。[5](P22)只有当大数据杀熟行为构成反垄断法上的价格歧视,才可以用《反垄断法》进行规制。
第一,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价格歧视的前提条件是要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是由于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并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造成了排除、限制竞争的后果,对公平自由的市场经济竞争秩序产生了损害,从而被法律明确禁止。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对市场的一种控制能力,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通常在相关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对市场价格有较大的影响力,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6](P110)《反垄断法》规制大数据杀熟的前提是实施大数据杀熟的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不是大数据杀熟行为的认定前提,是适用《反垄断法》进行规制的法律前提。
第二,经营者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实行差别待遇。《反垄断法》中的价格歧视是基于对竞争公平和竞争自由的考虑,主要针对的是经营者作为交易相对人的情况。当交易相对人是经营者时,面对相同的经营者和相同的产品或服务,给予差别待遇,进行差异化定价,将会使交易相对人即经营者之间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给予低价的经营者的竞争优势要高于给予高价的经营者,此时市场上的公平竞争秩序受到了损害,需要反垄断法对其进行规制。此外,对交易价格的非同等对待要做广义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商品或者服务反映在标签上的明确规定的价格,如返现、优惠折扣、售后差异、积分赠送等形式也是属于交易价格上的非同等对待,需要保证交易相对人的交易条件与支出的成本是一致的。[7](P22)
第三,产生竞争损害。价格歧视行为只有对公平自由的竞争产生了损害,才会受到《反垄断法》的制裁。经济学中的价格歧视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法学上的价格歧视是不被允许的。经营者实施大数据杀熟行为,只有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对正常的竞争秩序产生了损害,才可能构成价格歧视被反垄断法进行制裁。如果经营者实施大数据杀熟行为,但是对市场的竞争秩序没有产生影响或者影响微乎其微,此时并不需要受到反垄断法的制裁。因此,反垄断法在规制大数据杀熟行为时,要特别注意形式上的差别待遇与实质的损害竞争后果相结合,针对性的打击违背公平竞争秩序的行为。
第四,没有正当理由。在认定价格歧视时,还需要考虑是否具有合理正当的抗辩理由。经营者实施大数据杀熟行为,即使该行为对公平自由的竞争秩序产生了损害,但如果有正当合理的理由,也不受反垄断法的规制和调整。[8](P19-21)《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对经营者适用的正当的抗辩理由进行了列举性规定(1)《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条件相同是指交易相对人之间在交易安全、交易成本、规模和能力、信用状况、所处交易环节、交易持续时间等方面不存在实质性影响交易的差别。”。老顾客对平台的粘性和依赖性较强,新顾客是经营者要拓展的增量用户和潜在目标人群,对新顾客实施价格优惠有利于扩大用户量进而提高市场占有率和核心竞争力。这种对新老顾客的差异化对待是否属于正当的理由还有待考虑,如果直接将其规制在反垄断法中明显具有不合理性。
(二)《反垄断法》规制大数据杀熟行为面临的困境
第一,相关市场界定不明确。明确界定相关市场才能判断经营者在某个市场中是否具有支配地位,进而判断是否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影响竞争的行为。新经济形态具有多元化和复杂性,算法技术比较隐蔽,大数据行为多样且隐蔽、边界模糊。传统的产品替代性分析法与假定垄断者测试法在界定大数据杀熟行为时存在困难。大数据杀熟依托平台经济涉及多个相关市场,且实施手段具有隐蔽性,很难清晰界定产品之间的需求替代。大数据杀熟的特点和平台经济的特性影响SSNIP法的准确适用。[9](P57-60)反垄断法在规制大数据杀熟行为时存在相关市场界定不明确的现象。
第二,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困难。大数据杀熟是商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一种行为手段,通过平台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并利用数据对信息分析,最后对新老消费者给予不同的定价。是由于大数据自身所引起的,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并不是界定大数据杀熟行为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都可以针对新老客户进行不相同的差异化定价实施大数据杀熟行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界定该经营者的市场支配地位是单独由大数据引起的,还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共同导致的,以及大数据在其市场支配地位当中占据了多大的成分,这些在目前的现实生活中还都是比较困难的。[10](P264)
第三,主体的认定。当交易相对人是经营者而非消费者时,才可以用反垄断法规制大数据杀熟行为。现实生活中所提及的大数据杀熟多数情况下是指经营者与消费者的情形[11](P56-57),当交易相对人是消费者时,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此时并不存在同类主体之间的竞争问题,即便实施了差别待遇只是会损害部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经营者在市场中的竞争不会产生影响,对整个社会经济的竞争秩序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直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规制调整即可,无须反垄断法介入。
(三)《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指南》对大数据杀熟的规定有局限性
2021年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制定发布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对大数据杀熟的行为给出了相关回应。《指南》明确指出大数据杀熟行为有可能构成反垄断法中所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的差别待遇行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营者,在没有正当合理的抗辩理由时,对同样的商品或服务给予消费者不同的定价,会构成差别待遇的价格歧视。可以将基于大数据和算法,根据交易相对人支付能力、消费偏好、使用习惯等,实行差异性交易价格或者其他交易条件作为分析是否构成差别待遇的考虑因素(2)《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第十七条规定:“差别待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无正当理由对交易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实施差别待遇,排斥、限制市场竞争。分析是否构成差别待遇,可以考虑以下因素:(一)基于大数据和算法,根据交易相对人支付能力、消费偏好、使用习惯等,实行差异性交易价格或者其他交易条件;(二)实行差异性标准、规则、算法;(三)实行差异性付款调价和交易方式”。。
支付能力、消费偏好、使用习惯等这些所体现的是交易相对人为消费者时的情况,而并没有囊括交易相对人为经营者的情形,而大数据杀熟的对象既可能是消费者也可能是经营者,《指南》应当区分交易对象为经营者和交易对象为消费者的不同情况。当交易相对人为经营者时,被差别待遇后将会导致其竞争地位不公平,与其他的经营者并没有处在相同的公平的竞争秩序中,此时可能会损害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需要反垄断法进行规制。当交易相对人是消费者时,依据消费者的支付能力、消费偏好、使用习惯等区分不同的消费者进行差异化对待,显然会使得部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如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但这与反垄断法所强调的竞争和竞争自由并无太大关系,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更应当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针对性的保护。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是把垄断行为限制在了平台经济领域下,所维护的依然是反垄断法所强调的竞争自由和竞争公平,而支付能力、消费偏好、使用习惯等更多的应当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规制的范畴。《指南》将本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制的内容转嫁到《反垄断法》是否存在错位问题?是否违背了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本应当由《反垄断法》进行规制的,《指南》将其排除在外;却把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对象错位的体现在了《指南》中。因此,《指南》中关于大数据杀熟的规定具有局限性和不恰当性。
三、大数据杀熟法律规制的克服与建议
公平自由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规制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经济行为,应当使市场自由得到尊重,在市场调节能够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公权力不要随意介入。对于大数据杀熟现象,可以通过市场自身来解决一部分。约束平台的行为,提高平台的自治、自律行为。例如,某个平台的经营者多次进行杀熟行为,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对该平台的信任度降低,会使得平台的名誉受损,用户量流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平台为了自身的口碑以及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平台会对经营者利用大数据杀熟的行为进行治理,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管力度,规范平台及平台内经营者的规范定价行为,提高门槛,优化竞争。[12](P26-29)
针对大数据杀熟行为应当审慎执法,尽量交给市场进行管理而非国家盲目监管,当市场的自主调节不能够很好的解决时,再由国家公权力和法律进行管制。在用法律对大数据杀熟的违法行为进行规制时,不能够主观臆断或先入为主的选择适用某个法律,要根据侵害的法益为标准选择具体规制的法律。
(一)首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制大数据杀熟行为
当大数据杀熟行为对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自主选择权等相关合法权益产生了损害时,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直接有效的规制。[13](P106)
首先,大数据杀熟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经营者通过平台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利用消费者与经营者信息不对等的现状,在消费者不知道不清楚的情况下,对消费者实施不一样的价格,熟客的价格一般高于新客,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14](P70)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时,应当明确告知消费者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消费者依据自身条件和能力进行选择。[15](P63)而大数据杀熟行为告知消费者的价格并非是最初的价格,是经营者在通过数据对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分析后的给出的定价,不符合明码标价的本质要求。有些消费者在知道自己作为老顾客却被实施了高价时,会选择拒绝继续交易。其次,大数据杀熟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以知情权为前提,只有对产品或者服务有明确的认知才能够做出不违背自身真实意愿的选择。而当知情权受到侵害时,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就会相应的受到影响。大数据杀熟行为下,消费者由于知情权受到侵害进而做出与自身真实意愿不相符的选择,自主选择权受到侵害。[16](P55-56)最后,大数据杀熟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与经营者相比,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享受服务时,其核心利益应受到保护。经营者应当做到同等条件同等对待,不同条件不同对待。消费者获取相同的商品或服务付出的条件应该是相同的。大数据杀熟行为,在面对同样的商品或服务时,给予消费者不同的价格,使得被杀熟了的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受到侵害。[17](P87-88)公平不仅仅应存在于形式上,还要渗透到实质当中,让消费者在自主交易过程中享受真正的公平。
(二)基于《电子商务法》规制大数据杀熟行为
《电子商务法》允许电商经营者依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个性特征,有针对性的对消费者提供不一样的搜索结果,推送商品和服务,这些个性化的推送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程度上的便利(3)《电子商务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电子商务经营者根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等特征向其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搜索结果的,应当同时向该消费者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尊重和平等保护消费者合法益”。。但是大数据杀熟的平台经营者利用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地位,在对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消费能力、支付意愿分析后,针对不同的消费者实施差异化定价,该差异化定价超越了电子商务法中所允许的信息定向推送的合理范围,违反了电子商务法的规定。[18](P43)电子商务法对于经营者通过大数据对消费者进行精准推送的行为是认可的,但不允许在价格上有歧视。而《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归于简单,更多的是针对经营者对消费则推送的商品或服务,至于如何对大数据杀熟进行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三)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制大数据杀熟行为
数据时代,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可预测,数据本身让经营者有机会有能力对各个消费者进行画像与对号入座,经营者利用平台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依据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和承受能力对用户进行精准划分并实施区别定价。大数据杀熟通过精准的大数据分析,对价格不敏感的熟客或者是对价格接收能力较强的熟客进行间接的高价定价。平台经营者之所以能够利用数据进行杀熟是因为平台掌握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并对个人信息进行不恰当不合理的采集和使用。[19](P67-69)直击痛点,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行为,对个人信息活动进行全面监管,保护用户的信息安全权。
(四)基于《反垄断法》规制大数据杀熟行为
反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而非竞争者,当大数据杀熟侵害的法益不再是消费者个体利益,而是使得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受损,此时大数据杀熟行为可以纳入《反垄断法》进行规制。反垄断法在应对大数据背景下的杀熟行为时,应当秉持审慎的规制原则[20](P226-245)。反垄断法是一把利剑,过于锋利的直指大数据杀熟行为,会矫枉过正,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产生影响。反垄断法是维护竞争自由和竞争公平的法律,直接目的是保护市场上的竞出现的竞争问题,维持公平自由的竞争秩序;在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的基础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反垄断法以竞争机制为核心,良好公平的竞争机制能够保障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反垄断法应当作为必要性法律去介入规制大数据杀熟行为。大数据杀熟行为直接影响损害的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直接进行规制,能够起到最佳效果。能够通过其他的手段或者法律解决的时候,尽量优先其他。当侵害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时,确实需要反垄断法介入,再通过反垄断法进行规制。[21](P89-90)
四、结语
技术无罪,大数据是中立的,大数据杀熟的本质是商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所采取的一种手段,将一些不合理不公平的规制加入在算法之中,由算法影响最后的定价的行为。经营者为了利益最大化,利用算法对消费者进行精准的分析,依据分析结论和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支付能力对不同的消费者给予不同的定价。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等,经营者能够知晓更多的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而消费者对于经营者的信息了解有限,更甚连最基本且最重要的价格有时都不是公开透明的。经营者依托数据与平台使得消费者的议价能力降低,更多的是被动接受经营者的定价。要对大数据杀熟的违法性进行分析,在明确违法的情况下,根据其具体侵害的法益来选择相关的法律进行规制。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规制;违反价格法规定的用《价格法》进行规制;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产生损害的,用《反垄断法》给予制裁;《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也都对大数据杀熟行为有所禁止。健全法律规制,遏制大数据杀熟行为,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公平的市场竞争。针对大数据杀熟行为,还要加强平台的自治和自律,创新监管模式,为平台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22](P10-14)消费者要提高的自我保护意识,学习法律知识,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及时维权,要注重个人信息的保护。使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处于一种较为平衡的关系,营造健康有序、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