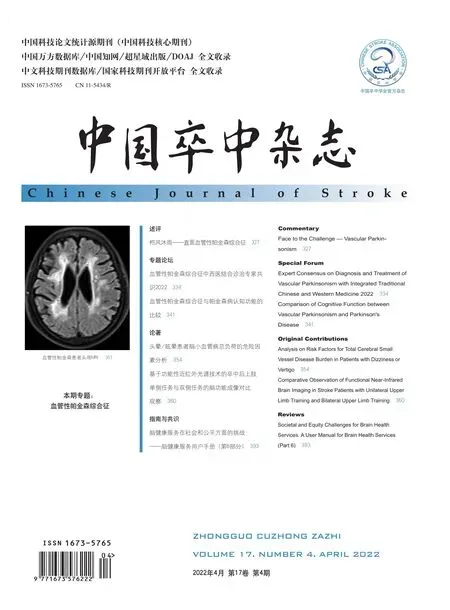TET2突变相关不确定潜能的克隆性造血与卒中发生发展的研究进展
瓮佳旭,仇鑫,2,李子孝,2,3,4
随着年龄的增长,体细胞突变在造血干细胞(hemopoietic stem cells,HSCs)中逐渐积累,导致克隆性造血(clonal hematopoiesis,CH)现象的发生[1]。当克隆性造血发生在没有血液系统肿瘤等异常的个体中时被定义为不确定潜能的克隆性造血(clonal hematopoiesis of indeterminate potential,CHIP)[2]。已有多项研究表明,携带CHIP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及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增加有关。甲基胞嘧啶双加氧酶-2(methylcytosine dioxygenase 2,TET2)基因作为研究最为广泛的CHIP相关基因,其突变可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并增加冠心病、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3-5]。大动脉粥样硬化性卒中是缺血性卒中最常见的类型[6],尽管传统的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如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等已成为卒中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的重点干预对象,且已取得了明显的干预效果,但卒中的发病率和复发率仍不容乐观[7],需要寻找未知的潜在机制并对患者进行更精准的干预,以改善卒中预后。本文总结了与年龄相关的CHIP主要基因TET2参与卒中发生及发展过程的可能机制,为探究卒中防治措施提供新思路。
1 TET2基因及其表达产物的结构功能特点
TET2位于人4号染色体长臂2区4带(4q24)区域,其编码蛋白TET2属于依赖于Fe2+和α-酮戊二酸(α-ketoglutaric acid,α-KG)的TET双加氧酶家族,在DNA主动去甲基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8]。TET2蛋白氨基端的具体结构尚不清楚,其羧基末端由1个半胱氨酸富集区域和1个双链β-螺旋结构组成,是发挥去甲基化作用的核心催化结构。TET2作用于不同修饰形式的胞嘧啶(cytosine,C),可以将5-甲基胞嘧啶(5-methyl cytosine,5mC)依次氧化为5-羟甲基胞嘧啶(5-hydroxymethyl cytosine,5hmC)、5-甲酰基胞嘧啶(5-formyl cytosine,5fC)和5-羧基胞嘧啶(5-carboxyl cytosine,5caC)。5fC和5caC又可被胸腺嘧啶DNA糖基化酶(thymine DNA glycosylase,TDG)特异性识别并切除,进而启动碱基切除修复途径(base excision repair,BER),从而实现主动DNA去甲基化过程[9]。TET2去甲基化作用发生在各种生物环境中,对胚胎发生、细胞分化和神经元功能等多种过程具有关键影响[10]。
2 TET2基因突变相关CHIP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关系
卒中的发生机制复杂,动脉粥样硬化是其中重要病因之一。作为一种内膜炎症性疾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涉及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炎症细胞募集等过程[11]。既往研究表明,TET2基因可能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Jaiswal等[3]将Tet2敲除(knockout,KO)和野生(wildtype,WT)小鼠的骨髓细胞分别移植到低密度脂蛋白受体敲除后易患动脉粥样硬化的小鼠中,通过测量小鼠主动脉根部病变的大小来评估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结果显示,在实验的第5周、9周、13周和17周时,实验组动脉粥样硬化病灶分别是对照组的2.0倍、1.7倍、1.4倍和2.7倍。Fuster等[4]在类似的实验中发现Tet2KO小鼠在第9周时表现出了比WT小鼠扩大60%的粥样硬化斑块,并发现斑块面积与血管内膜中巨噬细胞数量具有相关性。将Tet2KO和WT小鼠骨髓来源的巨噬细胞与低密度脂蛋白(200 mg/mL)共同体外培养,使用mRNA测序分析转录组,结果显示,具有促炎作用的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基因在Tet2KO小鼠的巨噬细胞中转录上调[4],以CXC趋化因子亚家族(CXC chemokine subfamily,Cxcl)1、Cxcl2、Cxcl3、Pf4及细胞因子基因IL-1β和IL-6的转录上调最为显著。Tet2KO小鼠血清中趋化因子的水平是WT小鼠的2~4倍[3]。这说明Tet2基因功能丧失可以加速小鼠的动脉粥样硬化,其机制可能与巨噬细胞中促炎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的转录增加有关。
除此之外,TET2基因还可参与到血管平滑肌细胞(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VSMCs)表型转化、调节内皮细胞功能等过程中,通过去甲基化功能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VSMCs去分化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促进因素之一[12],Liu等[13]的研究揭示了通过选择性去除VSMCs特异性基因组蛋白H3第4位赖氨酸上的二甲基化修饰后,会出现TET2募集受损,VSMCs的分化能力丧失。在氧化低密度脂蛋白处理的内皮细胞中,沉默TET2基因可导致自噬相关基因表达下调,抑制内皮细胞的自噬,加速其功能障碍[14-16]。
3 TET2基因突变相关CHIP与卒中的关系
既往已有研究发现,CHIP与卒中风险增加有关。2014年,Jaiswal等[17]发现包括TET2基因突变在内的160个体细胞突变相关CHIP携带者发生缺血性卒中的风险为非CHIP携带者的2.6倍(HR2.6,95%CI1.3~4.8,P=0.003)。2020年,来自英国的一项研究提示,具有更高变异等位基因频率(variant allele fraction,VAF)>10%的CHIP携带者,发生联合血管事件(心肌梗死、卒中或死亡等)的风险更高(HR1.59,95%CI1.21~2.09,P<0.001),其中TET2基因突变相关风险增高65%(HR1.65,95%CI1.05~2.75,P=0.041)[18]。
2021年,Bhattachary等[19]进一步的研究显示CHIP可作为独立危险因素增加卒中的风险。此项研究共纳入了86 178例参与者,其中6%为CHIP携带者,数据分析显示CHIP携带者的卒中发生风险约为非CHIP携带者的1.14倍(HR1.14,95%CI1.03~1.27,P=0.01),CHIP为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对常见CHIP突变相关基因(DNMT3A、TET2、ASXL1、TP53)分别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只有TET2基因与卒中(缺血性和出血性)风险增加显著相关(HR1.85,95%CI1.19~2.79,P=0.004),且TET2基因突变相关CHIP携带者缺血性卒中发生风险是未携带者的1.93倍(HR1.93,95%CI1.18~3.05,P=0.006)。在缺血性卒中的病因类型分析中,携带CHIP与小血管病型缺血性卒中具有显著相关性(HR1.55,95%CI1.20~2.02,P=0.001),提示CHIP与脑白质病变等脑小血管病可能有潜在相关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4 TET2基因突变相关CHIP与卒中功能预后
卒中后免疫炎性反应是影响患者功能预后的重要因素[20-21]。在卒中急性期,缺血损伤的细胞释放内源性损伤因子——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age-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s)可激活小胶质细胞的固有免疫反应,导致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释放,招募中性粒细胞等髓系细胞进入缺血脑组织[21]。而在CHIP发生后,带有突变的HSCs产生髓系分化偏移,增强固有免疫系统的炎症应答,从而影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22]。
最新一项纳入485例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的前瞻性研究对入组者进行了3年的随访,发现VAF≥2%的TET2基因突变相关CHIP携带者的全因死亡率显著增加(HR2.71,95%CI1.30~5.65,P=0.008),复合不良血管事件(全因死亡、复发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非致死性卒中或心力衰竭住院)的风险也明显增加(HR2.86,95%CI1.57~5.21,P=0.001)。研究进一步比较了VAF≥2%的患者与<2%的患者IL-1β和IL-6因子的血浆浓度,发现VAF≥2%的患者血浆中上述炎症因子的水平显著增高,这可能是导致疾病进展及预后不良的因素之一[23]。目前关于TET2基因突变与卒中预后的临床研究较少,但有研究认为,TET2基因可通过独立于其催化活性的途径增加巨噬细胞IL-1β基因的转录及表达[4,24],而卒中后脑损伤与局部及全身IL-1β水平增高有关。IL-1βKO小鼠中IL-1β蛋白失活可显著减小卒中后的梗死体积[25],这提示靶向调控TET2基因功能,可能会减少相关炎症因子释放,进而改善预后。另有研究显示,TET2基因可以通过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HDAC)介导的组蛋白去乙酰化发挥抑制IL-1β基因转录的作用[26]。使用HDAC抑制剂曲古抑菌素A处理Tet2KO和WT小鼠的巨噬细胞,发现2组IL-1β的转录水平均明显增加。除此之外,TET2还可通过调节Nod样受体蛋白3(Nod-1ike receptor protein 3,NLRP3)炎性小体介导的IL-1β裂解过程影响其分泌[4,24]。因此,卒中后靶向调控TET2基因的表达可能通过NLRP3的抑制减少IL-1β增加,有望减少脑损伤,成为具有前景的治疗靶点。
脑缺血发生24 h内对脑组织样本进行流式细胞学检测,即可发现中性粒细胞数量的增多[27],其激活可受到骨髓调动。有研究发现Tet2KO小鼠接受炎症刺激后,可以出现中性粒细胞反应增强,提示Tet2突变可能改变中性粒细胞在免疫应答中的作用效应,从而影响卒中预后[28]。
5 TET2突变相关CHIP与治疗
逆转TET2基因突变的克隆性造血或靶向干预TET2基因相关炎性通路,可能是未来预防和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思路。Cimmino等[29]利用可逆转的RNA干扰转基因小鼠模型模拟了Tet2基因表达的恢复,可在体内和体外逆转异常的造血干细胞和祖细胞的自我更新。有研究证明,通过阻断炎症小体和IL-1β可抑制Tet2基因突变导致的小鼠动脉粥样硬化加速[30]。MCC950作为NLRP3的特异性阻滞剂,在小鼠模型中可以抑制IL-1β的分泌,从而改善由Tet2基因突变导致的动脉粥样硬化或心力衰竭。除此之外,卡那单抗抗炎血栓结局研究(canakinumab antiinflammatory thrombosis outcomes study,CANTOS)是一项国际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试验,共纳入了10 061例hsCRP≥2 mg/L的心肌梗死患者,结果提示使用150 mg剂量的卡那单抗(人抗IL-1β单克隆抗体)可显著减少CRP水平升高心肌梗死患者的不良心血管结局[31],提示靶向炎症途径在改善血管疾病不良预后中可能具有良好前景。目前卒中领域的相关研究仍然空缺,未来可开展靶向干预TET2基因相关炎症通路的探索研究。
CHIP是人类衰老、炎症和心脑血管疾病间相互影响机制的重要连接途径[30]。作为CHIP中最常见的突变类型之一,TET2基因相关CHIP是近年新发现的独立于传统危险因素的心脑血管疾病潜在危险因素。TET2基因突变可通过激活巨噬细胞、血管平滑肌细胞、内皮细胞加速炎症,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和发展,增加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另外,TET2基因突变可参与并促进多种免疫炎性反应介导的脑损伤,可能与卒中后不良预后相关。逆转克隆性造血或靶向干预TET2等相关基因的治疗可能有助于降低卒中的发生及其不良预后的风险,是潜在的干预卒中发生和发展的新治疗方法。
【点睛】TET2基因突变相关CHIP可能通过炎症通路增加卒中风险,可能成为未来预防和治疗卒中的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