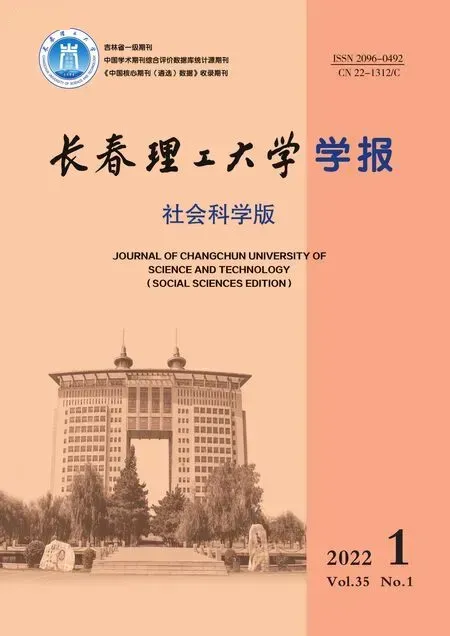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的庙宇叙事探微
付兰梅,刘淑敏
(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2)
庙宇通常意义上是指供奉神佛或者历史名人的地方,“历史上的‘忠’‘义’之士以及各地被称颂的历史人物,受到民众的尊崇而成为偶像,并且被加以神化,造庙祭祀”[1]10。庙宇的建立源于先人对神灵的崇拜,大致包含着两个组成部分,即自然崇拜和英雄崇拜。“《礼记·祭法》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这是自然崇拜;《祭法》又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这是英雄崇拜。”[1]14在现代的乡土中国这两种崇拜依然存在,并发展为一种民间信仰广泛留存于乡土社会中,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思想。
“村村皆有庙,无庙不成村”这句俗语很好地概括了乡土中国庙宇存在的广泛性,在现代乡土小说中,庙宇是一个频繁出现的空间。经整理发现,现代乡土小说家描写到庙宇的乡土小说约有32篇,其中庙宇本身具有叙事功能的小说约有10篇①包括鲁迅(1881-1936)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1921),短篇小说《祝福》(1924)、《长明灯》(1925)、《离婚》(1925);王思玷(1895—1926)的短篇小说《偏枯》(1922);许钦文(1897—1984)的短篇小说《老泪》(1923);彭家煌(1898—1933)的短篇小说《在潮神庙》(1933);王鲁彦(1901—1944)的短篇小说《阿长贼骨头》(1928)、《岔路》(1934)、《河边》(1937)。,均为中短篇小说,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其余小说中的庙宇本身并不具备明显的叙事功能②彭家煌(1898—1933)《美的戏剧》(1929)、蹇先艾(1906—1994)《山城的风波》(1932)、许杰(1901-1993)《的笃戏》(1942)里的庙宇在节日会有戏班子唱戏,给乡民们提供了娱乐休闲的场所;胡也频(1903—1931)《傻子》(1928)、沈从文(1902—1988)《泥涂》(1932)中的庙宇给流浪者们提供了一个遮风挡雨的栖身之地;在一些作品中,庙宇还是孩子们学习生活的地方,台静农(1903—1990)《为彼祈求》(1927)和蹇先艾《盐灾》(1936)中的学校都设在了庙宇中;废名(1901—1967)《半年》《火神庙的和尚》(1923)中的庙宇则是一处少有的、展示温情脉脉的乡村风俗人情的地方。其余作品不再逐一论述。,不在本文考察范围,在此不做赘述。
目前学界对庙宇的研究多集中在非文学层面,如民俗学、社会学等或者是从建筑、旅游等角度对庙宇的设立、功能、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以及当下对庙宇的重修重建等方面进行研究,从文学角度对庙宇的研究相对较少①经检索资料发现,对文学作品中的庙宇进行系统研究的期刊论文仅有两篇,丁燕燕的《庙宇祠堂的空间隐喻与权力——从“庙产兴学”运动谈起》从空间入手,论述了作为权力空间的庙宇祠堂对农民的规训和精神奴役,并刻画了这二者的空间权力在现代教育变革影响下的变迁;苗国梅和徐晓杰的《鲁迅和沈从文小说中的祠堂和庙宇叙事》以鲁迅和沈从文的作品为基础,分别论述了祠堂和庙宇的叙事功能,并指出了二者所具有的叙事价值。,涉及庙宇的研究多为只言片语,偶见于对乡土小说家的个案研究中,且多把庙宇和祠堂做关联表述,但二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祠堂与家族和宗法文化息息相关,而庙宇则不限定于家族内部,它与宗教信仰关系密切,乡土小说家笔下的庙宇更是充斥着迷信与黑暗。因此有必要对乡土小说家笔下的庙宇进行深入研究。
一、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作为“吃人空间”的庙宇
在乡土中国,庙宇是不容忽视的标志性存在,“作为民间信仰的物质载体,庙宇大多情况下捍卫的是整个村落乃至更大区域的利益”[2],人们会根据不同的需求供奉不同的神灵以求庇佑,极具功利色彩,有明确的实用目的。所求于神灵的,无非是避祸求福,希望在生活和生产的一切方面都顺顺利利、万事大吉,庙宇起着慰藉人们心灵、维系民间信仰的功能。除此之外,每年在固定的日子,还会举办庙会,搭建戏台,演出地方大戏,这是乡土社会最盛大的狂欢节,四乡八村的人都赶来庆祝。在一些村庄逢集市的时候,庙宇还会被当作各种专业市场,有卖肉的、卖小吃的,吆喝叫卖声不绝,庙宇仿佛脱去了神圣的外衣,走进了尘世,有了世俗烟火气,又有一定的娱乐功能,极具生活化气息。
随着近代以来科学观念的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了儒家“吃人”的文化传统,它以“科学”和“民主”思想动摇冲击着中国几千年来君主专制的根基,在追求个性解放、破除封建传统的新思潮影响下,一时间对传统文化中非人成分的批判风起云涌,作家们纷纷开始批判文化传统“吃人”的成分对人的愚弄和对社会发展的阻碍,庙宇因承载着太多的因袭传统而来的迷信思想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特别是在乡土小说家笔下,它褪去了昔日光芒,变得平凡丑陋甚至凶残黑暗起来。鲁迅先生把庙宇纳入到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之中,为他所开掘的“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服务,《阿Q正传》中的“土谷祠”(土地庙)看不到连绵不断的香火供奉,成了几乎失去了做人的全部权利的阿Q的栖身之地,是孕育他“精神胜利法”的温床,而正因深受“精神胜利法”的荼毒才导致了阿Q的悲剧;《长明灯》中吉光屯庙里日日燃着一盏“熄不灭”的灯,而“疯子”的悲剧正如飞蛾扑火一般,以一人之力难以熄灭受到村民们悉心“保护”的灯;《祝福》中的祥林嫂深受封建礼教的思想束缚,即使向土地庙捐了门槛也依旧没得到“原谅”,在新年的祝福礼俗中死去,鲁迅笔下的庙宇充斥着“吃人”的恐怖氛围。其后的一些乡土作家,如彭家煌、许杰、许钦文、王鲁彦、王思玷等紧跟鲁迅的步伐,通过对庙宇的筑造和雕琢批判自己最熟悉的土地上存在的种种陋习以及农民的愚昧与落后,王鲁彦的《岔路》中,村民在去关帝庙请关公庇护过程中引发的械斗所带来的灾难远远大过鼠疫;《河边》中明达婆婆身患重病却拒绝去医院看病,拉着儿子去庙里求菩萨,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菩萨身上。王思玷的《偏枯》与《河边》有异曲同工之处,生活在寺庙旁、得了偏枯病的丈夫将儿女卖给了一个假仁假义的和尚,儿女的悲剧结局可想而知。以上种种都是深受封建愚昧思想荼毒而不自知造成的悲剧,而这些悲剧都与“吃人”的庙宇息息相关。
承载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庙宇被新文学先驱者们推上了审判台,现代乡土小说家们试图通过对庙宇的描写刻画来打破深植于村民思想中的封建愚昧幻想,于是多把庙宇塑造成一处黑暗丑陋的“吃人空间”。
二、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庙宇的叙事功能
对作为“吃人”空间的庙宇的关注不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家们的偶然选择,而是他们的精心选择和必然安排,庙宇参与和影响了小说的整体建构。小说家们通过对庙宇的巧妙设计来安排小说情节,小说中的人物也因为和庙宇的牵绊变得更加丰满,它服膺于作家思想的表达和对时代社会的批判,具有丰富的隐喻意义。
(一)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
情节是叙事性作品中主要事件的形式序列,即故事结构中的主干,事件构成小说发展的脉络,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庙宇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事件展开的场所,是情节发展的催化剂。
在《阿Q正传》中,情节的发展并没有按照传统作品的线性模式,而是以阿Q的经历来构建情节,推进叙事进程。其中土谷祠便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土谷祠可以被视为阿Q的家,人们有事来找阿Q的时候便会来土谷祠,土谷祠是小说情节合理发展的必要之处,也是阿Q心理展示和精神呈现之地。当阿Q在土谷祠里完成了他的“畅想”之后,他的梦便有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也便有了后来的“恋爱的悲剧”。土谷祠对小说情节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离婚》中魁星阁的设置也对小说情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没用过多的笔墨进行渲染,但是仍能让人感受到它无声的威严。魁星阁为供奉魁星之所,这也暗示了庞庄乃是由士绅权力主宰的地方,爱姑一踏上庞庄便已注定了她的悲剧结局,在七大人和慰大人的威逼利诱下,爱姑一步步走向妥协。魁星阁的设置不但使故事的发生具有合理性,推动故事情节合理发展,而且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心理暗示和文化象征作用。在《岔路》中,鼠疫横行,吴家村与袁家村的许多村民因此而丧命,人们无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请关公上,然而在请关公出巡的盛典上引发了一场惨烈的械斗。关帝庙以及请关公是小说重要情节开展的推动力,村民本想求庇护却引发了更大的灾难,这种情节反转增加了小说的戏剧性。《河边》中深信菩萨能治病的明达婆婆和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儿子对寺庙的态度截然不同,作者把儿子眼中的寺庙描绘成了充满荒淫腐朽之气的地方,母子关于寺庙的对立态度也使小说情节走向变得扑朔迷离,小说开端盼着儿子回家的母亲却因去寺庙祈福和儿子产生了隔阂,寺庙起到了催化和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二)折射人物命运,塑造人物形象
小说中人物形象除了通过外貌描写、动作行为描写以及心理活动来塑造以外,还可以通过生活环境、时代背景等来侧面烘托、间接塑造,某一特定空间也可以折射人物性格和精神,展现命运沉浮。现代乡土小说中的庙宇就具有折射人物命运、塑造人物形象的叙事功能。
《阿Q正传》中的土谷祠是了解阿Q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小说中约有13次写到了土谷祠。土谷祠是阿Q的避难所,是他的“家”,在这里阿Q可以无所顾忌地幻想,我们可以看到在土谷祠中,常有对阿Q做梦场景的描写,阿Q的各种情绪在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比如躺在土谷祠里想女人、想借革命把秀才娘子的床搬到土谷祠等心理活动被渲染得淋漓尽致。当阿Q在外面受到了委屈和嘲讽时,便回到土谷祠中用“精神胜利法”疗伤,土谷祠是孕育阿Q“精神胜利法”的温床,正是通过对这些想法和美梦的叙述,阿Q的形象被完美地塑造出来。与此同时,作者设定阿Q住在土谷祠也有深意,庇护村民丰衣足食的土谷祠里却住着“田无一垄,房无一间”、靠打短工才能维持生计的阿Q,讽刺性可见一斑,使得阿Q的形象更加丰满。正如许广平所言:“在土谷祠能更亲切地找到阿Q之所在,仿佛此中有熟人,呼之欲出。”[3]《祝福》中通过对祥林嫂去土地庙捐门槛的行为的描写,把这一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得更加入木三分,侧面把封建礼教思想对她的荼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觉得可怜又可悲。《长明灯》中觉醒的“疯子”也是如此,他企图熄灭社庙里的长明灯,遭到了全屯人的反对,他以一己之力难以吹灭吉光屯延续了几千年的“长明灯”,而社庙就如同一个顽固难摧的金刚罩,屹立不倒,“保护”着长明灯,“庇护”着它忠实的信徒,“疯子”在它面前是多么的渺小,这种鲜明对比折射出了“疯子”的悲剧命运,最终“疯子”被关进黑屋,而长明灯则继续“长明”。许钦文的《老泪》中透过庙宇也可以折射出黄老太太的曲折婚姻和悲剧命运。未出嫁前,母亲常常到庙里拜菩萨为她求姻缘,婚后她自己对菩萨也笃信不疑,直到老年她依旧坐在庙堂内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这么一个深受封建思想束缚、愚昧无知的悲剧形象跃然纸上。在王鲁彦的《阿长贼骨头》中,阿长的形象也因庙宇的存在被刻画得更加触动人心,流氓无产者阿长整天干着偷鸡摸狗的勾当,偷了阿瑞婶的绒衣死不认账,被抓到庙里对菩萨发誓。在乡土社会中,菩萨在村民们心里是不可亵渎的尊贵存在,可阿长却敢大言不惭地撒谎,这正鲜明地体现出了阿长的麻木和无赖。
(三)隐喻传统文化思想对人的规训
“中国现代乡土作家们特别是鲁迅喜欢将乡土空间描绘成一处充斥着封建专制和迷信思想的‘万难破毁’的‘铁屋子’。”[4]庙宇作为“吃人”的“铁屋子”的具体表现形式则成为乡土作家笔下经常出现的空间意象。以鲁迅的小说为例,《祝福》中的祥林嫂被禁止参与“祝福”,在听信了柳妈的话之后,她花光所有积蓄向土地庙捐了门槛,以为捐了门槛被千人踩万人踏之后就可以获得救赎,但结果她依旧不被允许参加“祝福”,希望破灭,最终在“祝福”中惨死。祥林嫂被封建礼教所束缚,生活在这种环境中而不自知,她自觉认同了封建礼教对再婚女性的惩罚,企图通过捐门槛赎罪,但正是这种愚昧思想一步步将她推进深渊,作者也以此表达了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荼毒心灵的批判。《长明灯》中,吉光屯社庙里一直燃着一盏灯,村民们深信“那灯一旦熄灭,村庄就要变为海,人们会化为泥鳅”[5]。当想要吹灭这盏灯的“疯子”出现时,村民们千方百计阻止“疯子”靠近社庙,最终以“疯子”的失败而告终。愚昧无知的村民拼命守护的长明灯正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吃人”的文化传统的象征,而村民们的万般守护正说明了封建迷信等传统文化思想已经深深根植于他们的灵魂之中,作为觉醒者的“疯子”以一人之力难以撼动这棵大树,结局只能是失败,这也映射出传统文化思想的顽固性和“改造国民性”的艰难。这些人的愚昧观念和悲剧命运的形成都与庙宇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思想的规训息息相关。
民间的迷信思想在五四时期也成了被抨击的对象,先驱者们认为其严重阻碍了国民思想意识的觉醒,于是五四乡土作家们站在启蒙主义立场上把庙宇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王鲁彦的小说《河边》中,明达婆婆身患重病却不去医院治病,而是坚信菩萨能庇护保佑她平安,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儿子劝说不了母亲,无奈只能陪她去寺庙祈福。在儿子眼中的寺庙“弥漫着香烟的气息,里面还夹杂着肉的气息,鱼的气息”[6],与母亲的虔诚不同,在以儿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眼中,寺庙藏污纳垢、庸俗丑陋,母子俩对寺庙的认知反差造成了彼此亲情上的隔阂,而正是这种反差使作品的意蕴往往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作者通过对寺庙空间的贬斥性描写以及母子对寺庙态度的不同,批判了封建迷信思想规训下民众的愚昧无知。王思玷的《偏枯》也是如此,得了偏枯病的丈夫因无力养家糊口而只能将儿女卖给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坏和尚,而这个和尚是可以把弟子打得皮开肉绽的恶毒之人,由此可见孩子以后的悲惨生活。本是清修之地的佛寺在作者笔下充斥着阴森残酷,据此,作家有力控诉了宗教迷信的愚昧和荒谬。
可见,庙宇不仅为小说情节的发生发展和人物的活动提供了平台,还使得人物形象的塑造变得更加丰满,更是将其空间所特有的隐喻意蕴借由叙事层层铺展开来,是建构小说叙事的重要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三、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庙宇叙事的意义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的庙宇叙事具有独特的意义,一方面出于思想启蒙的需要,作家们通过讽刺更加直观有力地批判承载着传统文化劣根的庙宇,使得庙宇叙事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对故乡的落败和乡民的悲剧命运又感到痛心,在作品中充斥着浓浓的悲剧意味。
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相信只有国民的精神得到解放,国家才有希望,当务之急就是拔掉传统文化的劣根。乡土小说家们需要选择合适的对象来对传统文化中的非人成分进行批判和攻击,庙宇因承载着太多传统文化的劣根而成为众矢之的,这也使得乡土小说家们对庙宇以及其代表的传统文化中的非人成分持有着天然的批判态度,乡土小说中庙宇的叙事带有强烈的讽刺意义。《阿Q正传》的土谷祠中供奉的是土地神,为的是祈求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庇护百姓丰衣足食的土谷祠里住着靠打短工维持生计的阿Q,这种情节设计充满了讽刺与滑稽。《长明灯》中唯一的觉醒者却被全屯的人当做“疯子”,“疯子”拼命地想吹灭这一盏代表着封建迷信的灯,最后却被戏剧性地锁到社庙旁边的黑屋中,加强了小说的讽刺意味。《岔路》中鼠疫横行,却把希望寄托在关帝庙中的关公身上,在请关老爷的途中引发了械斗,械斗的危害远比鼠疫来得惨烈,讽刺性更是可见一斑。《河边》中明达婆婆虔诚地相信菩萨能治病,而在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儿子眼中寺庙充满了世俗欲望,二人思想观念的冲突造成了母子亲情的隔阂,更是通过对寺庙的贬斥性描写讽刺了明达婆婆的冥顽不灵。许钦文的《老泪》中,黄老太太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先问过菩萨,女儿生病不去医院,因为求菩萨得了上上签就无比心安。最终女儿病死了,黄老太太认为这是女儿的命数,还坚定地认为菩萨早已知晓,上上签只是为了宽慰自己,由此可以看出黄老太太不愧为菩萨的“忠实信徒”,讽刺了她的愚昧无知。以上种种都充满了讽刺意味,作家们正是通过讽刺使人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传统文化中的“吃人”成分对人的毒害和扼杀。
五四乡土小说中的庙宇叙事还具有浓浓的悲剧意味,《祝福》中祥林嫂满怀希望地去土地庙捐门槛也没有获得救赎,她的悲剧在于心甘情愿地接受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惩罚和规训;《长明灯》中“疯子”的悲剧在于凭一己之力难以打破扎根已深的封建藩篱;《岔路》《河边》的悲剧则在于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神灵身上。以上作品中主人公的种种遭遇以及他们的悲剧命运令人揪心,善良无助的普通民众遭受的不幸和苦难让人产生痛感和悲悯之情。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这些悲剧人物只是广大民众生存现状的缩影,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民们意识不到自己思想的愚昧和封建,而乡土作家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回望闭塞落后的故乡,激烈批判和否定故乡愚昧野蛮的同时,也隐含着痛心和无奈,在对故乡农村凋敝和人民痛苦的描绘中流露着伤感和乡愁,作家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既深爱自己的故乡、同情农民的不幸,又充满着无力改变的无奈,体现在作品中就流露出了浓浓的悲剧意味。这种悲剧意味并不使人感到绝望,而是作家们对“吃人”的传统文化因素更有力地批判,深刻敲击着国民麻木无知的灵魂,疗救悲而不自知的民众。
综上所述,现代乡土小说家们笔下的庙宇不单是一个物理空间,它还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氤氲着“吃人”的恐怖氛围。从庙宇入手来审视现代乡土小说,不仅可以看出中国乡村固有的顽疾,还能烛照作家在启蒙意识下对国民的关怀与疗救。作家们试图通过对庙宇的描写刻画来打破深植于乡民思想中的愚昧幻想,庙宇是作家们剖析落后乡土社会的一面镜子,揭示的也是乡土社会现实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