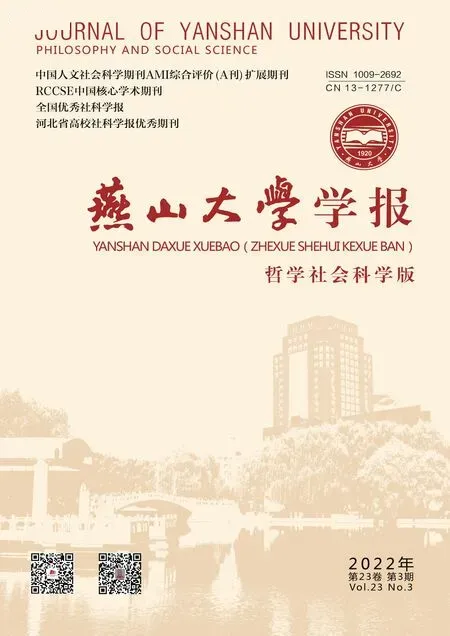跨学科视域下的中国科技典籍对外译介
——访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显斌研究员
王烟朦,孙显斌
(1.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2.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古代史研究室,北京 100190)
一、引言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学史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瓦维洛夫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并称为世界三大科学技术史专门研究机构。[1]孙显斌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研究所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本科、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和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史、古典文献学和典籍数字化。其一直专注于科技典籍整理领域,与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张柏春联合主编的“中国科技典籍选刊”入选“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并被誉为“我国科技古籍整理研究的新成果”[2]。完成《王祯农书》《物理小识》的整理后,撰写了《中国科技典籍整理的回顾与思考》《中国科技基本典籍刍议》等系列论文讨论科技典籍整理的相关问题。
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联合推动,自1995年正式启动的中国文化典籍国家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天工开物》《梦溪笔谈》《黄帝内经》《四元玉鉴》《茶经·续茶经》等15种科技典籍。这些科技典籍的英译本大多为国内外语学者翻译,他们撰文分享翻译过程及实践策略又促使该话题进入学术视野。[3]自2014年《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英译者刘迎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类典籍翻译研究”立项,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的科技典籍外译与传播系统研究逐渐增多。同时,相关学术论文数量稳步增长,发表在外语类核心期刊居多。中国科技典籍对外译介研究未来可期,但也隐藏着制约该领域有序、深入开展的“忧虑”,如概念界定不统一,重复性研究较多。为此,笔者拟围绕科技典籍的海外译介访谈孙显斌研究员,以飨中国科技典籍对外翻译实践和研究的学者,从而更好地在传播中国传统科技文化方面有所作为。
二、科技典籍之“名”与“实”
翻译的本质属性为语言符号的跨语际转换,语言符号又是表示指称对象和表达思想情感的媒介,所以明确科技典籍的基本特征是开展相关对外译介研究的基础。本部分就科技典籍的名称定义和文本特质访谈了孙显斌研究员,具体如下:
问:中国科技典籍的时间界定尚无定论,如“鸦片战争(古代)”[4-5]、“1911年”[6-7]、“五四运动”[8]。请谈一下您的划分选择和依据?
答:“古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讨论古文献学时限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在世界史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才能叫古代,正好相当于我们的明末,也就是说在世界史上,清代就是近现代了。而我们一般把古籍限定在清王朝灭亡的公元1911年,也就是说民国之前的文献称为“古籍”。但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以五四运动划界,这么处理的原因可能暗含了现代白话文之前的文言文阶段的文体界限,但以文体划界有其问题,这是因为白话文文体是连续发展的,宋元明清一直都有白话文体,所以很难这么简单的断限。另外,将民国时的文献称为“古籍”,就其时代而言也不合适。而以鸦片战争为断限的处理可能考虑到中国历史的划分,1840年以后为近代,之前为古代,我们知道清末诞生了大量古典研究的重要文献,这样划分存在更大的麻烦。因此,还是用民国之前这个时限最方便合理。
问:科技典籍具有显著的科学性,其人文性亦有重要价值,如《天工开物》包含符合现代科技概念的知识,也有晚明读书人宋应星呼吁革新科举八股制度和以农为本等社会改良的表达,蕴含了“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具有文学性以及艺术张力。用现代西方概念“科技”命名以《天工开物》为代表的包含科技知识的古代典籍,是否有望文生义之嫌,遮蔽了它们包含的其他文化元素和人文性?
答:无论以什么名称称呼,都是现代的概念,古代人文的概念和现在恐怕也不一致。我国古代知识体系基本上按照《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的四部分类体系展开的,近代以来又增加了丛部、新学类等作为补充,与近代以来我们从西方引进的学术分科体系差别很大。我们今天说的科技就是现代的概念,古代并没有对应的概念,所以我们说的科技典籍往往是按照今天的观念,去寻找科技知识存在于哪些古代典籍中,内容占比较大的就称为科技典籍。虽然如此,我们在解释和理解古代科技知识时,要做同情的理解,就是放在当时的环境包括思想观念的大背景下。如果说称《天工开物》是科技典籍一种遮蔽,那么说《淮南子》是人文典籍同样是一种遮蔽,这个问题似乎没必要纠结。
问:周远方[9]提出,“中国传统博物学”是儒家文化“博物”的产物,包括自然世界的知识,外延囊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农学、动植物学、中药学等,以及社会生活的人文知识,其特征具体包括:(1)“百科全书式”的体系;(2)自成体系的分类方法;(3)描述性判断事物;(4)人文性;(5)实用性。再以《梦溪笔谈》为例,全书涉及人事、乐律、书画、技艺等17类,自然科学条目仅占三分之一。[7]所以用“中国传统博物学典籍”命名科技典籍是否更加符合它们生成的历史语境和内容特征?
答:恐怕那样更不符合,我不太同意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观点,也不认为古希腊就已经存在近代科学。实际上,即使按照今天的观念,中国古代也既有科学,更有技术,只是知识内容有深有浅,理论思维有强有弱罢了。你所说的传统博物学典籍只是古代科技典籍中很小的一个分支。根据《中国古籍总目》,现存1912年以前出版古籍约有20万种,科技典籍主要分布于如下几个类属:史部地理类总志之属(444种)、政书类考工之属(81种)以及水利之属(314种),子部兵家类(约230种)、农家类(467种)、谱录类花木鸟兽之属(339种)、医家类(6684种)、天算类(1656种)、术数类(约140种)、新学类(884种)等,合计约1.2万种以上,占存世古籍总量的6%左右。[10-11]天算类典籍就有1600余种,其知识体系主要为制定天文历法服务,而不是所谓博物学旨趣,就像农学、医学知识体系更是为农业生产、治病救人服务的。传统博物学典籍并不多,即使算上花鸟谱录类和医家类中的本草类,也不会超过天算类,更不用说医家类。想简单用一个现代的词概括是行不通的。
问:原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将《论语》《诗经》《史记》《传习录》《山海经》等文史哲典籍中蕴含科技价值的语篇归为科技典籍。您主张不能因为一部典籍有个别段落记载中国传统科技,就认定其为科技典籍。[12]能否请您界定一下科技典籍的其他特征,怎样更好地将之与文史哲典籍区别开来呢?
答:《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的编撰,是为科技史研究提供最基本的文献资料,所以先秦文献中有科技内容的篇章也被收录进来,是非常合理的。当然我们不能称其整部书为科技典籍,我想这并不矛盾。我的文章中也提到对重要传统科技创新的零星记述,实际上也非常重要,但是不能因为一部典籍有个别段落记载,就认定其为科技典籍,这类文献材料应该进行分类汇编。如果想把科技典籍区别出来,也不难,即其主体部分或者说有相当篇幅是科技内容。即使《梦溪笔谈》,其科技相关内容也不占主体,但是由于科技部分内容成就太高,所以一般也都承认其为科技典籍。
问:我国少数民族有自身悠久的科技史,科技典籍又有汉族科技典籍和少数民族科技典籍之分。[7]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少数民族科技典籍的概况?
答:少数民族科技典籍当然属于中国科技典籍,因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的文明体,但不宜用现代欧洲兴起的民族国家的概念简单类比传统中国。有些少数民族学者撰写的科技典籍是汉语写的,比如元代蒙古族学者忽思慧撰的《饮膳正要》,清代蒙古族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测绘学家明安图撰的《割圆密率捷法》等。不过用民族语言文字编撰的更多,有的还自成体系,比如藏族、彝族、回族的天文历法,各民族的传统医学等就都很突出。从事少数民族科技典籍研究的学者更少,研究非常不充分,需要整理并翻译成现代汉语,方便更多的人阅读和利用。
三、科技典籍对外译介观
问:在明确什么是科技典籍后,下面我想就科技典籍对外翻译与传播这一话题对您进行访谈。首先,请您谈谈我们为什么要推进科技典籍对外译介事业?
答:中华文明古代科技成就举世瞩目,科技典籍文化遗产更是我们凭借认知先人神奇创造的基础资料,同时也是世界认识理解中华民族杰出智慧的重要途径。我们需要对民族优秀科技传统有恰如其分的认识。一方面,我们不能受李约瑟先生误导,认为我们的科技曾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就像认为古希腊就已经存在近代科学一样。实际上,即使按照今天的观念,中国古代也既有科学,也有技术,并且都有悠久的传统。只是知识内容深浅,理论思维强弱罢了。科技传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国内提到传统文化就只会想到文史哲艺术方面,缺乏对科技传统的了解。对外传播更是这样,大家都只知道中国有四大发明而已,其实这仅是中国传统科技很小的一部分。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科技文明,普惠全人类,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的历史使命。
问: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专业性强,而且主要是文言创作,所以译者不仅要掌握娴熟的外语能力,更要具备跨学科知识。请您根据治学科技史和古典文献学的经验,谈一谈作为译者的外语学者该怎样更好地胜任翻译科技典籍的历史使命?
答:我觉得最好方式是与科技典籍研究者合作,因为科技典籍的整理本身就需要古典文献学和科技史双重学术背景,再将其外译,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是很难覆盖的。关于团队协作的翻译方式我认为最好的是唐代译经场的方式,先由兼懂梵汉的翻译师串讲大意,然后众人辩难其中佛教义理,再由主译裁决最终的理解,口授出来,最后由有文采的经师润色成文。这样做,翻译的质量有保障,效率比较低,但是经典的翻译应当用这种方法,一定程度上可以“一劳永逸”。我们所研究员张柏春和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雷恩(Juergen Renn)牵头组成的“马普合作伙伴小组”就在用类似的方法英译王徵的《远西奇器图说》,已经有十多年了,听说他们的成果就要出版了。
问:您整理过元代王祯的《农书》和明代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请您分享一下科技典籍整理和校勘过程?科技典籍翻译人员该如何选择优质的底本呢?
答:科技典籍的整理过程与普通典籍没什么不同,一般是先从各种目录中搜索该书的各种版本,然后获取各种版本,进行初步校勘,理出其版本源流,即版本家族树。然后选择祖本或者最好的本子作为底本,选取其他版本分支的祖本作为参校本进行校勘,在异文更优或者两通的情况下出校勘记,也有所有异文都出校勘记的做法。对于翻译者来说,应该选择有很好整理基础的现代整理本作为底本进行翻译,这样就可以规避版本、校勘等问题。这是因为版本的问题属于古典文献学,其实比较复杂,一般的科技史研究者也未必具有这方面的素养。上面提到的《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在选目上很权威,但具体到每部书所用版本就有不少差强人意,比如我整理的《物理小识》,“通汇”用的光绪甲申宁静堂本,实际上是最差的一个本子。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条件和经费有限,从不少直接采用大多不尽可靠的四库本,就可见一斑。
版本的不同,主要是会有文本的异文,这些异文从理解文意的角度可以区分为一般性异文和实质性异文。一般性异文是指对内容的理解差别不大,所影响的仅是用词习惯等文本风格的不同。而实质性异文则不同,会造成内容理解的巨大差别。举一个实质性异文的例子,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几何原本》中论述平面的时候有一句“绳施于一角,绕面运转,不碍于(於)空。”这里的“不碍于空”,不好理解,查其他版本有异文为“不碍不空”,这就能理解了,就是说在平面的一角处系一根绳,拽住绳的另一端,在平面上划过,既不会受到阻碍(即不碍),也不会有不被划过的地方(即不空)。这里的“于”显然是“不”形近而讹,但是四库本其实错成了“於”,这就让人很难想到原文应该作“不”了。
问:在明确翻译底本之后,需要译者选择具体的翻译策略。为了有效地被科技史研究人士和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认可和接受,您认为什么翻译策略和方法更好?
答:我个人认为翻译科技典籍应该优先考虑学术翻译策略,因为科技典籍比较专业,只是简单翻译很难引起国外一般读者的兴趣,或者说读者也很难真正读懂,理解它的精彩。就像科技典籍翻译成白话文后,国内读者是否有兴趣阅读或者能否看懂,是同样的问题。为国外学者和专业人士提供可靠的翻译之后,在国外的传播就有了基础,国外感兴趣的文化传播者可以据此进行二次创作,可能会达到更理想的传播效果。当然,出于方便异域读者理解考虑,适当的意译也有必要。除非是给通过双语学习语言的读者,可以考虑使用直译。另一方面,术语的对译除了少数完全相同的概念,其他的对译严格来说都需要加注释,这种以注释补充说明翻译词语的方式是严谨的,值得提倡。但是在对译词语的选择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概念相近的词语去翻译,且注释说明两个对译词概念的区别。另一种是直接用汉语拼音,因为既然概念不完全相同,就用新词以免误解,再加注释进行说明,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容易提醒读者两个概念的差别,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是这种方式。但是实际上读起来不够亲切,满篇都是生词。用概念相近词语翻译的优缺点恰好相反。举个例子,中国古代南宋时期出现算盘,珠算继承了筹算的口诀计算方式,成为当时先进的计算工具,并在我国一直使用到现代计算器普及之前。如何翻译“算盘”这个词,西方古罗马时期就有一种“abacus”的计算工具,我们一般翻译成算盘,两个词汇形成对译,都是一种利用珠子的计算工具,但其实差别很大。翻译的时候如果直接用“zhusuan”,西方读者就感觉很陌生,用“abacus”就感觉很亲切,但又容易误解是同一种工具,所以我们用“Chinese abacus”来翻译,即利用相近词汇帮助跨文化理解,又提示实质有区别。
问:多模态文本是指一部作品包含多个符号模态,运用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多种感觉的文字、图像、声音、色彩等手段。[13]《天工开物》是典型的多模态文本,有123幅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黑白插图;央视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以“戏剧+影视化”的手法将这部科技典籍搬上银幕,利用大众媒介对之从视觉和听觉模态的二次呈现,大大提升了它的知名度。科技典籍该从哪些方面进行多模态翻译和创作,使之以更加多元化的方式弘扬中国古代科技文明?
答:科技典籍一般只有配图的情况,如果构建多模态文本,都是整理者或者出版者的行为,翻译者可以和整理者、出版者合作,创作一个多模态的整理版本,比如新配图像、视频以及3D复原模型等,这样的确是方便读者理解。也可以在选定一个整理的版本后,搜集或者让整理者推荐好的多模态的解读版本,将已有的多模态素材融入到翻译版本之中。为提升对外传播和中西交流互鉴的效果,在译介科技典籍的同时,配合译介中国科技史的经典普及读物,包括一些容易理解和趣味性较强的画册和纪录片。如果有机会,在国外策划一些科技文化的巡回展也会锦上添花。
问:您提到古籍数字化分为图像化、全文化和数据库化三个层次,深层次的数据库化相当于将古籍文本信息语义结构化,立体的语义网络有利于深层次的知识挖掘,从而将古籍资源更有效、全面地利用起来。[14]科技典籍译作的数据库化对于开展翻译研究和编撰双语词典亦大有裨益。我们该怎样借助计算机网络技术推进科技典籍翻译的数据库化呢?
答:我觉得最基础的还是构建科技典籍双语对译的语料库,但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为了解决古籍的翻译研究,可以构建一般典籍的双语对译语料库,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多,时代分布也从先秦到清末,内容涉及各个学科。只有在有一定数据规模的情况下,人工智能技术才能展现它的威力,可以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尝试机器自动翻译,利用命名实体标记等技术提取专业术语,辅助编撰双语词典。
问:据您了解,有哪些科技典籍在海外有较好的传播和影响力,国外人士查询和研究科技典籍译作的工具、平台、媒体有哪些?
答:科技典籍在海外有较好的传播和影响力的不多,目前来说《九章算术》《天工开物》《梦溪笔谈》《本草纲目》这些很早就享誉世界的典籍影响力比较大,实际上有较好译本的科技典籍也并不多,这方面翻译者大有可为。毕竟如果自己的译本成为经典译本也是中外翻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且翻译的科技典籍越重要,其影响力和文化贡献也越大。科技典籍的译作作为图书,国外人士一般通过所在地的图书馆、书店等进行查询。比如,亚马逊网店就是一个重要的平台。收藏汉籍的图书馆主要是设在大学内的东亚图书馆,还有不少博物馆、公共图书馆也有收藏。美国亚洲学会(AAS)下面有东亚图书馆委员会(CEAL),北美主要的五十多家东亚图书馆都是其会员。同样,欧洲汉学学会(EACS)下也有欧洲汉学图书馆协会(EASL),会员包括欧洲一百多家收藏汉籍的机构。2015年9月第35届EASL年会在英国牛津大学举办,我有幸参加,还在会上推介了我们整理的“中国科技典籍选刊”,不少与会者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向世界主要汉籍收藏和科技史研究机构赠送了“选刊”第一辑。另外,国际和欧美科技史学会的年会,也是推介科技典籍外译成果的平台,2017年7月巴西里约第25届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上,我们就组织过一个专题Section,讨论中国科技文献。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海外汉学和科技史研究的网站,主动推荐科技典籍译介的书目。
问:最后请您谈一下对外语学者的期许,如何在助力中国科技文化对外传播和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方面“有所为”?
答:我最后再呼吁外语学者和科技史研究者通力合作翻译科技典籍,实际上科技史学界是欢迎外语译介学者和我们合作的。2017年我们研究所创办了英文刊ChineseAnnalsof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以发表中国科技史为主要内容的英文学术期刊,为此我们聘用了两名外语专业的编辑,着力培养。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杨海峥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北美汉学发展与汉籍收藏的关系研究”,也尝试建立“中华文明汉英双语在线词典”,主要想解决汉学研究中各学科专业术语的标准化翻译、参考的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合作。
正如我前面谈到,译介也是一种跨文化沟通,需要具有双方的文化和知识背景,所以翻译科技典籍这类专业典籍对外语学者是很大的挑战,但我还是认为学科术语的标准化双语词典建立是译介工作的关键,希望外语学者与专业研究者合作打造这把跨文化的钥匙,实际上对于外国学者也是很必要的参考。从方法上,充分利用一些英文撰写的中国科技史著作(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词汇表是方便可行的方式。
问:感谢孙老师您的分享。您的这些见解对外语学者更好地翻译科技典籍和开展科技典籍英译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也期待与科技史研究学者的跨学科合作研究早日实现,共同助力我国传统科技文化对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