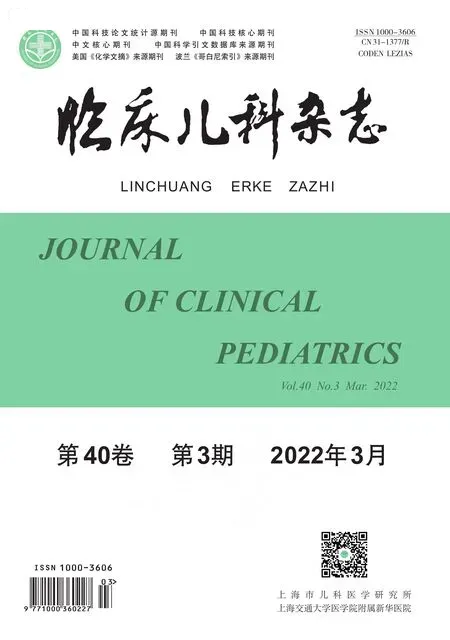精准医学时代中国脊髓性肌萎缩症诊治发展之路
毛姗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内科 国家儿童健康与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浙江杭州 310052)
脊髓性肌萎缩症(spinal muscular atrophy,SMA)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神经肌肉疾病,5qSMA为最常见类型,因位于染色体5q的运动神经元存活基因(survival motor neuron,SMN)1缺失/变异导致SMN 蛋白缺乏致病[1],欧美国家新生儿发病率为1/10000,中国人群变异携带率约1/42[2-3]。根据起病年龄和最大运动里程碑,临床分为0型(常于出生1月内死亡)、1型、2型、3型和4型,其中前四型在儿童期起病,但无论哪一型,患者均表现为进行性肌萎缩与肌无力,并常伴有呼吸、消化、营养、骨骼等多系统器官损害[4],生存质量极低,自然病程下1型患者更常因呼吸并发症于2岁内死亡[5-6]。作为一种严重的致残、致死性疾病,SMA于 2018年被纳入国家《第一批罕见病目录》。
欣喜的是,在经历经验医学、循证医学到如今正式进入精准医学时代,以SMA为代表的诸多罕见病治疗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不再无药可治。受益于国家政策、医学团队、社会公众等对罕见病群体的高度关注,近两年中国SMA诊治更是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里程碑。药物治疗时代,SMA疾病诊治与管理朝着专业化和规范化稳步、快速发展。
1 精准医学的发展给SMA的药物治疗带来前所未有的进展
关于SMA 药物治疗学的发展,可追溯至 1995年SMA 致病基因的发现与定位,法国的研究团队首次报道SMA 致病基因是位于染色体5 q 13 上的SMN 1,致病机制为SMN 1基因发生了致病性突变(包括纯合缺失或复合杂合突变)导致体内SMN 蛋白的水平不足[1,7]。同源基因SMN2是主要异常剪接发生基因,与SMN1仅存在5个碱基差异,但其转录mRNA 中近90%的转录本缺少外显子7,所翻译的SMN蛋白为非全长不稳定蛋白,无法发挥正常生理功能而导致发病[1]。2000年,中国台湾成功建立首个SMA 转基因小鼠模型,为针对SMA 致病原因的治疗药物研发奠定了基础。2016 年全球首个5 q SMA治疗药物诺西那生钠注射液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上市批准,标志着SMA 正式进入了疾病修正治疗(disease modifying therapy,DMT)时代。在这之后的5 年间,针对SMN的靶向治疗药物不断获得突破,先后有针对SMN 2剪接修正以及SMN 1基因替代药物问世,以及其他非SMN靶向药物研发,药物治疗学时代SMA的治疗机遇不断涌现。
截至目前,全球已有3种DMT药物获批用于临床,均为SMN靶向药物[8-9]。
1.1 诺西那生
诺西那生是一种反义寡核苷酸类药物(ASO),通过鞘内注射给药,主要作用靶点为SMN2基因premRNA内含子7中的ISS-N1位点,诺西那生通过与该位点靶向特异性结合促进SMN 2基因mRNA 转录本外显子7 的保留,从而提高全长功能性SMN蛋白生成以治疗5 q SMA。数项关键性临床研究(ENDEAR、CHERISH、NURTURE)证实诺西那生治疗可以显著提高SMA 1 型患者的无事件生存与总生存时间,长期治疗可以实现部分1 型患者达到自然病史中无法达到最大运动能力,同时可以改善或稳定所有临床分型以及广泛年龄段SMA 患者的运动、呼吸等重要功能,而症状前治疗更可以使可能发展为1 型或2 型的SMA 患儿几乎达到与正常儿童相似的运动发育水平[10-11],改变SMA 的疾病自然进程。迄今为止国外关于诺西那生治疗SMA的真实世界研究数据不断增多,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反映了关键临床研究的治疗获益,同时也在积累与回答临床实践遇到的各种问题,以指导更佳的临床应用。2019 年2月,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在国内获批,开启国内 SMA精准治疗的新纪元,截至2021 年11月,全国共有300 余例患者接受治疗,临床结局数据正在不断积累中。DMT 药物在国内的上市促成了中国SMA 发展之路上另一重要里程碑,即2019年4 月中国 SMA 诊治中心联盟成立,来自15 个省份的25家医院成为第一批成员单位。截止2021年,联盟成员单位共计63 家,覆盖全国25 省份。通过联盟平台搭建全国SMA 诊疗协作网,国内已建立多家高水平的SMA 诊治中心,为全国SMA 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2021 年12 月,诺西那生钠注射液正式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使该药的可及性大大提高。
1.2 利司扑兰
利司扑兰是一种口服小分子SMN 2mRNA 剪接修饰剂,2020 年 8 月获美国FDA 上市批准,用于治疗2 个月及以上SMA 患者。利司扑兰主要作用于SMN 2前体mRNA 外显子7 以及内含子7 中的两个结合位点,促进SMN 2基因包含外显子7 的全长mRNA 表达,从而增加全长功能性SMN 蛋白生成。进行中的FISH系列临床研究(RAINBOWFISH、FIREFISH、SUNFISH、JEWELFISH)显示,利司扑兰可显著提高1型SMA患者的生存率,改善或稳定1、2、3 型SMA患者运动功能[12-13],提升生活质量。2021 年6 月,利司扑兰口服溶液用散在中国获批上市,截止12月,全国约90例患者正在接受该药治疗,临床疗效观察有待持续积累。
1.3 Zolgensma
Zolgensma是一种SMN1靶向基因替代疗法,通过静脉注射自身互补腺相关病毒9(scAAV9)将功能性SMN拷贝导入患者细胞以替代缺失或缺陷SMN1基因,从而增加正常SMN 蛋白生成[1,14],该药已于2019年5月后陆续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多处获批上市,但中国尚未获批。相关主要临床研究显示,与自然病史组对比,Zolgensma 治疗可以有效改善SMA患者生存率与相关机体功能[15]。目前该药在美国的适应症为2 岁以内SMA 患者,全球范围内针对2 岁以上SMA患者的相关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
2 多学科团队综合管理是SMA药物治疗的基石
DMT药物的问世给SMA 的精准治疗带来突破性进展,大量临床研究与真实世界报告显示,药物治疗可使患者获得不同程度运动功能与呼吸功能获益。然而,有药可治的今天,SMA始终需要以患者为中心的多学科团队(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综合管理[16]。
众所周知,SMA 是一种由SMN 蛋白水平异常降低引起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患者的起病年龄、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各不相同,临床特点具有高度异质性。除肌肉无力与萎缩进行性加重外,在一系列动物模型和SMA 患者中,还可观察到心血管系统、骨骼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多组织脏器病理性或功能性改变[4]。正因SMA 患者的临床症状与病情进展各有不同,临床诊疗和疾病管理方式也会有所差异。此外,SMA 患者往往合并其他组织脏器的功能障碍,治疗过程中需要涉及不同专科医护团队,如何更好地践行多学科综合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在疾病被首次描述之后的近百年时间,由于缺乏有效的药物以及干预的手段,临床上SMA一直以姑息治疗或症状控制为主。2007年国际首个SMA标准化管理专家共识发布,强调MDT是SMA治疗核心,因疾病的复杂性、渐进性及涉及多器官组织的功能衰退,临床上需要包括神经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临床营养科、重症医学科、康复科等多专业医师共同参与SMA 疾病管理[17]。该共识于2018年更新后再次发布,新增更多临床相关专业团队,如遗传学、心理干预、整形外科、作业治疗等,其核心依然是强调以神经内科为主导的MDT,贯穿疾病诊断、治疗与全程管理[16]。神经内科发起并组建MDT,主导沟通、交流以及协调MDT,明确疾病诊断后与患者家庭充分沟通,使其了解疾病过程、分型、预后及治疗方案,并对患者进行多器官系统评估,制定相应的个体化治疗措施。给予多学科综合管理同时,神经内科更应向家长充分提供药物治疗相关信息,并给予精准的遗传学咨询与指导。
2019年发表的脊髓性肌萎缩症多学科管理专家共识,对SMA的标准化治疗和个体化管理有了新的定义,全文以MDT 为出发点对SMA 疾病诊治与管理进行了深入探讨,强调了全面开展MDT 在SMA临床实践中的应用和价值[18]。MDT 是SMA 临床管理的关键因素,更是SMA药物治疗的基石。基于疾病的个体异质性,MDT 可根据多学科评估结果为SMA患者提供个性化治疗和管理方案,监测多系统进展,改善多系统损害,持续给予前瞻性临床策略,全方位提高SMA 的诊疗质量。2019 年中国SMA 诊治中心联盟成立也带动了国内多家诊治中心成立专业化MDT团队,并开展多学科联合门诊,为患者提供一站式、多层次、个体化的多学科综合管理。因此,无论患者是否接受药物治疗,MDT 对改善SMA 患者结局非常重要。当药物尚不可及的时候,MDT可为药物治疗提供基础支持,维持身体状况,为将来用药奠定基础;当有药可医后,MDT更可协助药物治疗实现最佳疗效。通过多学科合作、融合和不断自我提升,SMA 的MDT 团队建设也将丰富各个医疗角色的跨学科协作经验和知识,提高SMA疾病诊治水平。
3 全生命周期疾病需实现SMA的全病程管理
在疾病发现的历史上,SMA曾被多位专家认定为不同疾病各自命名。1891 年,奥地利神经病学家Guido Werdnig 首次从临床角度描述了两个婴儿兄弟的SMA,从1893 年到1900 年,德国神经病学家Johan Hoffmann描述了另外7例SMA病例,最终临床命名SMA 1型,即Werdnig-Hoffmann病[19]。1956年,SMA 的一种临床较轻表型(患者具有保持站立和行走的能力,并且具有更长存活期)被Wohlfart、Fez和Eliasson正式描述,然后Kugelberg和Welander进行了更详细地描述,由此产生了SMA 3 型,命名为Kugelberg-Welander病[19]。1964年,英国神经学病家Victor Dubowitz描述了12例SMA患者,这些患者几乎没有急剧进展,在婴儿期就开始发病(11 例患者在18月龄之前),并存活到童年和青春期。后来证实,此为SMA 2型,也称为Dubowitz病[19]。经过不断的临床实践与科学研究,最终,这三种疾病被证实为同一种疾病表现的不同临床分型[1,8,19]。SMA 可以在宫内发病,也可以在婴儿期和儿童期起病,甚至还有成人期起病的4 型,但无论哪一型,一旦确诊,疾病将伴随终生。因此,SMA 是一种全生命周期疾病,全生命周期疾病必定需要实现疾病的全病程管理,建立从早期识别、精准诊治到长程管理的全病程诊疗生态环境,以真正提升SMA患者与家庭的生活质量。
首先,SMA的早期识别需依赖于对SMA一系列独特体征和症状的快速识别,如松软儿、运动发育迟缓且智力正常等征象,遗憾的是,国内外SMA 诊断延迟现象均十分普遍,患者确诊往往需要辗转数月甚至数年,经历至少3名专科医师的转诊[20-21]。因此,药物治疗时代更应加强培训基层儿科医师早期识别该疾病。其次,疑似SMA患者应参照脊髓性肌萎缩症遗传学诊断专家共识[22],尽快给予规范精准的遗传学检测以缩短诊断时间窗。在精准诊断的基础上,尽早给予DMT是改变SMA患者疾病进程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高质量的MDT需全程参与。最后,患者主动积极参与的良好依从性将为SMA 全病程管理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多学科团队针对该群体进行全程关怀就显得尤为重要。SMA不止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实现SMA的早诊断、可治疗、有关怀与能负担同样也是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目标所需。2022 年1 月1 日,随着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国家医保政策正式落地,中国SMA诊疗正式宣布进入医保时代。
4 药物治疗时代SMA诊治展望与挑战
经过100 多年的不断探索研究,SMA 的临床管理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从疾病本质的认识,多学科管理观念的确立到当下药物治疗时代来临,SMA疾病研究的百年轨迹充分显示了临床医学、遗传学、转化医学及治疗学的完美衔接与相互促进,成为当代精准医学的典型案例。当然,SMA 诊治相关研究目前只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随着药物使用日趋普及,以及疾病新临床表型的不断发现,SMA研究领域存在未来展望,但也存在许多挑战。
①针对基因型与表型的不一致,在疾病发病发展机制方面,仍需进一步阐明SMA发病的细胞学及相关分子机制,除SMN基因以外,尚有哪些重要的调控基因与分子对疾病产生重要作用,各基因及分子间的时空网络关系如何。②关于SMN蛋白的深入研究,包括蛋白的确切功能,临床可用检测方法,不同器官组织对SMN蛋白的依赖性如何。③在生物标志物探索方面,除SMN2拷贝数、电生理指标、脑脊液磷酸化神经丝蛋白、影像学指标等外,临床仍需开发更精准客观、均一性强、可反映药物疗效以及疾病预后预测的相关生物标志物,并建立多维度、多因素的分析模型,从而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④个体化治疗目标的设定与患者期望值的平衡。DMT药物的不断可及,使得更多SMA 患者有药可治,如何设定个体化治疗目标,并与患者期望值达成最佳平衡,已然成为药物治疗时代的一大挑战,而伴随药物治疗出现的新疾病表型及当前疾病分型定义修正很可能进一步给目前的临床诊治带来新问题。⑤中国本土的大样本真实世界队列研究。目前SMA的流行病学、自然病史、治疗学等相关研究大多来自国外研究成果,随着我国SMA 的MDT 诊治水平提升及DMT药物普及,我们期待更多中国数据与中国声音为国内SMA诊治临床实践提供重要参考依据。⑥多靶点联合治疗探索。虽然现有上市DMT药物均为SMN依赖疗法,但国内外众多非SMN通路的新治疗靶点正在不断涌现,如增强肌肉功能、增强神经肌肉接头功能、针对正性或负性调节因子的治疗、神经保护、神经再生等等,为使患者临床获益最大化,未来SMA 的个体化治疗将有望走向针对不同机制的多靶点联合干预模式。⑦新生儿筛查何时开展。目前普遍观点认为SMA越早治疗临床获益越大,有药可治的今天,普及SMA的症状前筛查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世界上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将SMA疾病筛查纳入到新生儿遗传病检测范围内,相信随着我国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SMA的新生儿筛查将有望早日实现。⑧携带者的孕前产前筛查何时普及。面对1/42的高致病基因携带率,实现SMA的出生缺陷精准防控必定需要孕前产前携带者筛查的全面开展,现有遗传学检测方法是否已完全覆盖所有基因变异。SMA是否已全面实现早期、快速、精准诊断。
诚然,对于SMA,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新的问题也在不断涌现,纵观整个疾病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毋庸置疑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最好的时期,作为医者我们将肩负医治患者及探索科学的双重责任,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中国的SMA诊治之路一定美好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