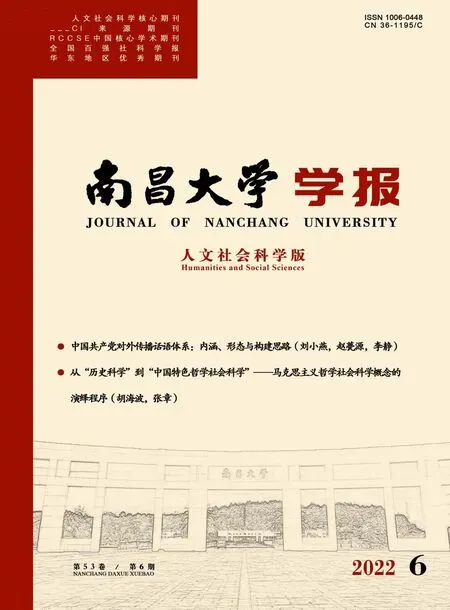中西“同途而殊归”的死亡观念
——以《庄子·至乐》与《别离辞·莫伤悲》为例
孙程程,韦清琦
(东南大学 a.艺术学院;b.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一、引言
著名翻译家朱生豪把《哈姆莱特》中的“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翻译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一翻译引发出很多争议,其中产生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西方存在不同的死亡观念,因此也应该形成完全不可翻译的言说。“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灵肉对立的二元论,似乎不大讲究从毁灭中寻求快感,我们的生命亦无须非得通过痛苦的否定来达到新生和再生。相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使在西方常常是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下的现象世界成了古代中国人至为亲切、物我两忘的生存环境。”[1]33陆扬在详细考察中国思想家的死亡观念以后,指出“庄子是一个例外”。“庄子的死亡哲学是在中国文化中几乎绝无仅有的一种乐死的生死传统,同样是一种少有的可与西方基督教超越精神比较的人文精神。”[1]33《庄子·至乐》细致地描写了庄子面对其妻子死亡“鼓盆而歌”这一非同寻常的行为,表达了他以死亡的超越为至乐的观点。与此极为相似的是,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在《别离辞·莫伤悲》也在与妻子分别时赞颂具有超越意义的死亡。这一诗歌对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到英美新批评的关注。艾略特、退特等新批评理论家都强调,约翰·多恩的《别离辞·莫伤悲》具有明显的超越精神。“所有这一切意义以及其他意义,都归结为一个意义,都蕴藏在这一节诗里:我说‘其它意义’,因为我并未穷尽我有限的能力所能发现的微小的有意义的部分。”[2]132《别离辞·莫伤悲》通过使用比喻等修辞手法,表达出超越自然的玄学观念。
不过,《庄子·至乐》与《别离辞·莫伤悲》在强调死亡的超越性的同时,也体现出中西文化在死亡指向以及文学价值方面存在的具体差异。这两部在中西文学史中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虽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却产生于中西文化的不同语境,除存在比较诗学价值,还证明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提出的间距哲学的重要价值。庄子关于死亡的描写体现出基于主体间关系的美的追求,约翰·多恩的创作则主要体现出西方文化的主客之间的交互关系。“庄子美学中的自然则由于坚持‘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这一‘天人合一’思想而为一种属人的合目的性的自然。故庄子美学中的客体已不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主客关系,而是中国哲学意义上的‘准主体间关系’。或用西方哲学家布伯的话来说,庄子心目中的客体已不是一种借助于认识而把握之的‘它’,而是一种经由移情而相遇之的拟人化的‘你’。”[3]48这一比较主要通过分析中西美学的不同特点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差异,与朱利安运用间距哲学分析中西文化的思路不同。“‘间距’的本性正是让自己不被命名也不受界定,它是如此迅速并在每一个方面和每一种规模里都能起作用,因此破坏了每一个均质化行动。”[4]313朱利安的间距哲学在使中西文化保持适当距离的同时,使两者互为镜像、互为观照,进而努力揭示出庄子与多恩的死亡书写追求的不朽观念,以及被这类不朽观念所遮蔽的中西文化的“未思之处”。
二、庄子与约翰·多恩的死亡观念
向生避死既是人们必须直面的日常生活现象,又是他们试图回避却又都难以回避的人生存在。正是因为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畏惧以及生死所涉及的重要人生意义,对生死问题的哲学探讨一直是中西文学与哲学的永恒话题。不同的思想家要么通过死亡主题审视人生的终极价值,要么借助生死对话或转换分析人生存在的现实意义。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庄子运用汪洋恣肆的文风谈玄说道,以见微知著的笔法宣扬了与天地万物共存的死亡观念。“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绰,其旨玄妙。”[5]1他以深邃的智慧探索天道的规律,将生而为人同天道运化之间联系起来,直面人的生死问题。与庄子相似的是,约翰·多恩也在诗歌中对生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描写,努力从人生哲学的角度审视这一人生难题。“你我的脸庞在彼此的眼中遨游,/真诚坦白的心停歇在脸上;/哪里我们能找到更好的两半球,/没有凛冽的北极、没落的西方?/凡是死亡者,都没有平衡相济;/我们若爱成一体问题,或者,我和你/爱得正相等,谁也不松懈,谁都不会死。”[6]67约翰·多恩在这首《早安》中指出,男女情侣的挚爱可以摆脱寒冷、邪恶,也可以通过使人体的各种元素保持比例平衡而实现对死亡的超越。二人在深入描写人的死亡的同时,也藉此指出死亡的价值与意义。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具有明显的生命关怀意识,强调努力摆脱“外在规定性”,追求个性自由与精神超越。庄子的人生目标是摆脱身心的困境达到逍遥的境界,而要摆脱的困境,既有来自外在社会层面的,又有来自内在精神层面的。正是通过思考如何摆脱这些困境,庄子的人生哲学蕴含了丰富的生死智慧。《庄子·德充符》明确提出:“死生亦大矣。”[7]144活的意义与死的本质之间的关联既体现出人类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也是生命关怀的一个重要命题,还是人生一切意义的依托和前提。庄子通过生与死的对比并将其与天道运行联系起来,指出生死的本质不过是气的聚散而已,生本从无中而来,死又入无中而去,生死交替如同昼夜运行。人在大化运行之中,当随自然的变化而变化,破除对生的执迷与死的忧惧,达到“天人合一”的生命状态,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生死观念,影响中国后世文化思想甚巨。“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7]157生命存亡、事业穷达以及品德好坏都是天道运行的结果,与人力没有任何关系。人们在这类天道面前不能发挥任何作用,既无法窥测其始终,也无法预料其顺逆。人的生死在与道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形成神秘的精神体验,达到最高的精神自由,使庄子哲学的逍遥游的最终归宿得以实现。
与庄子物我两忘的死亡观念不同,西方的死亡观念所追求的超越精神主要体现为对必然的、不死的世界的探索。西方文化中存在乐死恶生与乐生恶死两种关于死亡的基本看法,这也导致了享乐主义与禁欲主义两种不同的面对死亡的人生态度。与古希腊以及中世纪更重视直接探讨死亡问题相比,文艺复兴以后关于生存原则或自我保存原则的探讨逐步成为死亡哲学的主要命题。“在近代哲学家这里,人及其理性则成了死亡问题思考的唯一尺度和准绳。因此,一般说来,近代哲学家的死亡观总是同他们的自然观或宇宙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死亡的终极性也近乎成了自然常识。因而也就出现了‘自然死亡’与‘非自然死亡’(如自杀)这些概念,丰富了死亡哲学的内容。而且,虽然在这个时代,一些哲学家的头脑里还有‘不死的信仰’,但是,这种‘不死的信仰’却同中世纪基督教的迥然有异,因为它所讲的只是一种理性事物的永恒性和不灭性。”[8]153,154具体到英国玄学派诗人,安德鲁·玛弗尔更强调人生苦短与及时行乐的主题,约翰·多恩更重视通过超越世俗欲望而获得永恒。约翰·多恩认为,人应该抛弃一切纵情享乐的感官追求,通过精神长存实现对昙花一现的肉体存在的超度。约翰·多恩的诗歌包含着人本主义的爱的观念,但是这种“爱”“不只是单纯的先后排列或偶然重叠,而是全然的合一,是随着灵魂的历程而逐渐发展、逐渐深化、逐渐完满、达至太一的升华过程,体现着爱的崇高,也体现着生命的神圣”[9]122。与庄子相比,约翰·多恩也通过描写死亡探讨当下与将来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死亡及其艺术传达在展示出中西文化差异的同时,也体现出中西文艺在描写死亡超越性时形成的复杂的美学表征机制与各具特色的人生价值追求。《别离辞·莫伤悲》与《庄子·至乐》都强调死亡的超越性,从具体艺术描写角度来看,都传达出要直面并迎接死亡的观点:相比于世人哀悼死亡,他们都选择了歌颂死亡。这是因为庄子与约翰·多恩都认为人的真正属性不在于会消亡的肉体,而在于精神性的存在,因此肉身的死亡对人的真正属性不会有任何损害,反而具有通达人的精神性存在并回归不朽的重大意义。法国哲学家朱利安指出,中国思想与欧洲思想之间存在可以对其展开深入反思的间距。“我乃在中国思想和欧洲思想之间安排‘面对面’,以至于一方通过间距在对方那里掀开了自己的真实面貌,并且双方都这么做(‘中国思想’,我的意思只是,在中文里思考的思想;‘欧洲思想’,则是在欧洲语言里思考的思想)。”“在中国与欧洲的例子里,随着那些思想所给予的外在性(我还没说‘他者性’),间距的性质能使在间距两边的双方,于相遇之际可以理解自己原先不知道的部分(就是我所称的‘掀开真实面貌’),勘察双方的未思,而由此在思想里找到新的出发点。”[4]305《别离辞·莫伤悲》与《庄子·至乐》的并置并不是传统意义的文学比较,而是借助其关于死亡看法的间距探查中西方死亡美学中的未思之处。
三、“同途”:死亡的超越性
约翰·多恩与庄子之所以礼赞死亡,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死亡是人回归其源头——永恒——的基本途径。这一回归所体现的死亡的本质是“精神性存在”的超越能力,也即“精神性存在”是对由肉身、生命、欲望等组成的人的外在规定性的超越,约翰·多恩认为肉身对灵魂发挥束缚作用,庄子也强调生命限制着元气。约翰·多恩与庄子都主张,文艺是一种精神性存在,具有明显的现实超越能力,这种能力有助于人们实现终极意义的升华,是令人喜悦、值得庆祝的。《别离辞·莫伤悲》是约翰·多恩诗歌的代表作,它的抒情基调比较平和、超脱,但想象突兀,意象奇特。这首诗将生离比作死别,用一系列奇特的比喻将死亡同精神之爱联系到一起,宣扬死亡与精神之爱是同在的关系,明确地表现出死亡所具有的精神超越能力。在《庄子·至乐》中,面对妻子的死去,庄子不但不哭,反而鼓盆而歌。他的怪诞行为对世俗的死亡观念提出了挑战,甚至被认为太过无情。但是,庄子解释道:“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7]450人之生死的本质是天地自然之气的聚散变化,“气的凝聚形成生命,生命终结气消散于自然”[10]55。气是构成生命的质料,人的生命起源于自然的“元气”,元气于人身上体现为一种源于宇宙又内化于人的自然之性。约翰·多恩在《别离辞·莫伤悲》开篇将一对情侣的生离喻作死别,充分表现出世人对死亡所持有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就好像有德人安详离世,
只轻轻对灵魂说一声:走,
悲哀的朋友正纷纷论议,
有的说气断了,有的说没有,
让我们如此融化,不声张,
无叹息风暴,无泪水洪波;
把我们的爱向外人宣讲
就等于亵渎我们的欢乐。[6]136
约翰·多恩通过四句简单的诗句表达出人们对死亡的两种不同态度:有德行的人关注的是灵魂,因此能够平静坦然地接受死亡;世俗的亲友关注的是肉体,以致惶恐忧惧地抗拒死亡。诗人借助这一描写劝慰恋人,希望她对爱人的离别就像有德行的人对待灵魂归天那样“莫伤悲”。约翰·多恩接下来连续使用了三个奇特的比喻:“天体的震动”“黄金的捶打”和“一体二用的圆规”。这些比喻在解释了他所秉持的生死观念的同时,也让读者在震撼之余能体会到奇喻中所蕴含的丰富哲理。
地震带来的伤害和恐慌;
人们猜度其作用和意图,
可是九天穹隆的震荡
虽然大得多,却毫无害处。[6]136
这一对比意在说明,俗人和诗人对死亡本质持有不同的理解。约翰·多恩用“地震”说明俗人对死亡的理解,因为在俗人看来人的意义是以肉体的存在为基础的,死亡是肉体的消亡,代表着自我毁灭以及与亲友爱人永久的分离,显然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诗人则用天体偏移作类比,是为了说明死亡的本质是灵魂与肉体相分离,根本不会危及灵魂的存在。这也体现出约翰·多恩对人的属性的判定:人的根本价值在于不朽的灵魂。死亡只是肉身的消亡,因此“莫伤悲”。
《庄子·至乐》提出死亡像春夏秋冬的四时交替,循环往复而没有终结,所谓“死生为昼夜”[4]452。生死无非是自然的变化,是人力范畴之外的自然规律。人的死亡就像“偃然寝于巨室”,从各种“为人”的外在规定中解脱出来,复归自然之道,因为肉体的生命只是一种限制人的自然之性的外在规定。如果面对死亡,就止不住地嗷嗷大哭,这既有违人死亡的自然规律,又徒然浪费活人的精神,完全是一种“不通乎命”的表现。庄子把死亡视为人类的“自然之性”升华到“天人合一”的基本途径。因此,无论是身生还是身死,人都应该顺应自然规律的安排,这种智慧的人生态度才是人的“自然之性”的具体体现。他乐观地看待妻子死亡的原因是,他将人的“自然之性”看作道的象征。庄子所强调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生死观,这一观念是站在自然的高度以坦然的态度面对生死,方能摆脱世人“悦生恶死”的心理倾向。老庄哲学关于生死的最重要的智慧是,妻子的自然死亡与庄生的乐死观念都借助“自然之性”,实现了对尘世生命的解放以及永恒生命的回归。个体在超越了肉身生命的限制后,将“入于不死不生”,进入“乃入于寥天一”的道的境地。肉体的死亡一旦进入这种境界,也不过是万物之形变而已。
从约翰·多恩与庄子关于死亡的描写来看,他们都认为死亡是对具有束缚作用的肉体的超越,因为死亡既使有形的肉体转化为他物,又使万物的精神归于大道。对个体而言,人的肉体原本是与“贪生失理”“冻馁之患”等“生人之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随着生命的终结能够将自然之性解放出来,这在使人的精神彻底摆脱其外在规定性的同时也复归到自然,成为永恒、自在、无所不在的“无我”。“我们的灵魂是一体浑然,/虽然我人必须走,灵魂却/并不分裂,而只是延展,/像黄金槌打成透明薄叶。”[6]136-137《别离辞·莫伤悲》的这段描写说明,灵魂在恋人分别时并没有分离,就像死亡只能导致肉体的分离,并不会对灵魂带来些许危害,也不会对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的灵魂产生任何负面影响。“即便是一分为二,也如同/僵硬的圆规双脚一般;/你的灵魂,那定脚,不动,/倘若另脚移动,才动弹。”[6]137这一节通过把分离比作“圆规”指明,完美的圆的实现有赖于圆规两脚画圆的过程,这一过程才实现了从起点到终点的同一。与此相似的是,庄子向往的理想人生境界是复归宇宙之间的混沌。人类要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既需要看透生死的本质,也需要放下对死亡的恐惧,最终才摆脱对个体小我生命的拘执,进而体认到与无我生命的宇宙相统一。“精神性存在”在天人合一以后,将超越功利名位与经验性的时空,进入符合天道运行规律的无私无我的逍遥状态。
《别离辞·莫伤悲》与《庄子·至乐》也强调,死亡能够超越生命的限制,进入空无的理想境地。这也是与天道一体的状态,因为死亡“应该是真正的回归,是最真实的存在”[11]21。庄子把人分为元气和形体两个部分。人在死亡以后,元气将回归宇宙秩序(天道),肉体的腐朽也是与之相对应的过程。庄子为庆祝元气终获安宁而歌唱,与凡人对着尸体哭泣的行为相对应。这也说明,庄子对肉体的衰亡视若无睹,但非常重视元气的归宿问题。一般人根本不相信肉眼无法看见的元气,因而将肉体的消亡看作“人”的毁灭。从这些论述来看,庄子与约翰·多恩在两个方面是相通的:首先,庄子对元气与形体的区分与约翰·多恩关于灵魂与肉体的区分相似;其次,庄子关于生死变化的描述与约翰·多恩对灵肉合一则生的看法相同。他们都认为,对人的真实属性而言,死亡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约翰·多恩在诗歌中提出“无叹息风暴,无泪水洪波”,否则就是“亵渎我们的欢乐”。[6]136为什么欢乐呢?约翰·多恩在诗歌的结尾对死亡的定义是:“你的坚定使我的圆正确,使我回到起始处,终了。”[6]137这与庄子提出的“是其始死也”的意思是一致的。死亡被约翰·多恩与庄子看作人的精神性存在回归其本源的基本路径。因此,《别离辞·莫伤悲》中的“回家”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指活着的人在死亡以后回到人间家园,二是指灵魂在结束人生旅程以后返回理念世界。诗人对死亡本质的理解是:死亡是灵魂回归其本源——理念世界。灵魂伴随着至死不渝的爱情,在死亡时迎来了精神境界与人生意义的双重圆满。
四、“殊归”:个性精神的存在与消亡
从中西方文化并置并寻找其未思之处的角度来看,庄子与约翰·多恩虽然都认为死亡是一种超越,精神性存在在脱离肉体以后能够回归本源,但是对夫妻间生离死别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异,对精神性存在在人死以后所登临的境界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简单来说,存在间距的中西方死亡观念在相遇之时,体现出完全不同的终极意义指向。庄子对妻子的死亡表现得非常淡漠,没有一丝柔情与爱意。他所发出“我独无慨然”的感慨,虽然是一句情绪性表达,但并不是针对妻子,而是针对死亡本身,也传递出他对死亡的态度不为世人理解的感叹。从惠子的表述来看,庄子与其妻子几十年相濡以沫,情真意切,但是庄子对妻子的离世没有表达出一丝不舍。与之相反,约翰·多恩虽然也与庄子一样主张人生存在的根本价值取决于精神属性。但是,从对爱情的讴歌以及使用“圆规”的比喻来看,他在与妻子分别时对对方充满了强烈的依恋和不舍。他们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他们强调人在死亡以后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境界,所进入的永恒精神世界存在很大差异。《别离辞·莫伤悲》诞生于风起云涌的文艺复兴时代,其所着力表达的主题是“个体精神”。这一精神是一种与人文主义紧密相连的文化思潮,是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本质的巨大发现,因为“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12]125庄子在死亡的超越中找到是“万物一体”,这种“自然而然”的追求使他打破了人类“私爱”的局限,在对个体形成超越的同时复归到对庄严天地秩序的赞美声中。
《别离辞·莫伤悲》所表现的“个体精神”展示出文艺复兴对人性的自觉与高扬,但又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的宗教色彩,构成涵括理性、感性与信仰的综合体。这种“个体精神”所强调的是个体在尘世中的精神觉醒,力图通过个体的内在精神认识和把握作为“太一”的世界和宇宙,体现出约翰·多恩对个体灵魂拯救的深切关注。“多恩作品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思辨性与实证性的结合,亦即新旧学的糅合,或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合一。”“多恩的新学并非哥白尼的翻版,而更倾向于柏拉图的下界;相应地,约翰·多恩的旧学则更倾向于上界。”“新旧学之间,既有不同的倾向性,又存在互动关系,所以二者的结合,既有助于激发‘诗性的想象’,也有助于从广泛认可的‘存在链’中选取任何相关意象,从而将个人情感体验纳入广袤的宇宙之中。”[9]178《别离辞·莫伤悲》借讴歌人世的相伴与“精神之爱”等形而下的日常经验,书写出明显具有形而上特点的人性之爱。诗人虽然指明爱的来源是神秘的,但是仍然强调两颗自由的心灵在努力经营着“精神之爱”。这份神圣的爱主要以恋人的主体性存在为基础,爱与人是密不可分的。约翰·多恩通过对尘世的恋人之间的爱情的歌颂,实现了人的自身价值的肯定。这份个体性的精神之恋在肉体死亡以后,仍然在超验的世界中存在。更为重要的是,维系爱情的灵魂在死后的世界中,仍然以独立个体的形式存在。这其实也是对生前人格的延续,因为死亡见证了作为个体精神的爱情的存续,也肯定了人的不朽价值。
约翰·多恩认为,以个体精神为基础的爱情可以帮助个体实现对死亡的超越。爱情既是人类固有的情感,也是人类个体价值的体现,还是人通过与更高的形式相结合而实现不朽的具体途径。约翰·多恩的诗歌一贯坚持对爱的推崇和对精神家园的追求,明显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普罗提诺等新柏拉图主义者在柏拉图学说的基础之上,融合哲学与宗教,提倡太一、理智与灵魂的三本体说[13]210-211。普罗提诺明确强调世界的终极存在是“最完满的理式”——“太一”。太一可以通过流溢达到自我显现,流溢的过程从高到低依次为宇宙心灵、宇宙灵魂、自然世界和物质世界。约翰·多恩将“宇宙灵魂”诠释成“个体精神”,使个体精神与太一形成同源关系。这既是个体精神备受约翰·多恩推崇的原因之一,也使其作品“饱含着人类个体精神所独有的创造力”[14]13。约翰·多恩的毕生追求是发展一段毕生之爱,他从一开始就对肉体之爱和精神之爱作了明确区分,不遗余力地赞美后者:“而我们被爱情炼得精纯。”[3]136“提炼”在中世纪的欧洲特指炼金术士将贱金属转化为贵金属,特别是黄金的过程。约翰·多恩借用这一术语指明,他努力调动自己的一切情感与智慧,与更高形式结合并达到完满的精神境界。在他看来,世人应该始终提醒自己的灵魂不要忘却本性,必须不断向上求索,以达到与“太一”合为一体。只有这样,人的“个体精神”才能最终超越自身的局限性而达到完满的境地。从表面看来,这与老庄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颇为相似,但是其中蕴含着积极能动的“个体精神”。
庄子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死亡观,蕴含着道法自然、顺其自然等彼此关联的精神追求。在庄子看来,这个世界产生于“道”,道是万物的根源,无所不在,超越时空,世界上的每个生命都与生生不息的宇宙大道紧密相连。个体必须顺应天道,才能长盛不衰。庄子的生死观认为,人的生死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万物的生死都是无生无死的大道的形变,属于自然造化的必然环节。“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7]77人既然无法抗拒死亡的到来,就应该达观地直面死亡,努力达到天人合一的道的境界。人们对待生死的基本态度应该是“效法自然”,只有在超越“人类自我局限”的基础上看待生死,才能抛弃“悦生恶死”的世俗心态,成就“生死一如”的坦然心境。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要做到“吾丧我”才能真正与道合一,获得一种超验的、至乐的超越状态。不过,自然死亡才是进入这种超越状态的基本途径。与之相反,各种非正常死亡因为违背了自然天道,完全属于对生命的漠视和戕害。人只能通过自然死亡,才能重回生命的循环和自然(道)的怀抱。这也是顺其自然的死亡观的基本意义。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庄子面对妻子受命运支配的自然死亡,没有表现出任何眷恋,而是用“道法自然”的立场审视夫妻关系。人世间的一切关系包括夫妻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人生价值,都存在于“有形”的世界,属于人的“形而下”的部分,与作为人的精神性存在的“元气”无关,只能属于人在死亡之前的生的存在。
庄子的死亡观与约翰·多恩完全不同,庄子主要强调死亡除了使人回归自然之道,还在效法自然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个体精神的消解。在庄子看来,人生价值只能存在于死亡以前的生命历程之中,在面对死亡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回归时都无足轻重。与人生价值相比,死亡的回归才是人生存在。因此,死亡是值得庆祝的,这种欢庆之所以不包括爱情,是因为死后只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失去了任何“个体性”意义,也泯灭了一切活着时的人生价值。个体精神重归于无,只能安然顺应自然之道。庄子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是因为“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7]559。他的这种高歌一曲、了无牵挂的态度,既超越了个体的情感羁绊,也把死亡视为对个体精神的超越。《庄子·至乐》对死亡的态度体现出庄子把死亡视为一种通向“大道”的哲学,是一种使情感处于自然本真状态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人通过死亡,进入道的境界,超越了人生固有各种价值、意义与观念,抛弃了悲伤与欢乐,摒弃了仇恨与友爱。然而,处于世俗中的人由于受到个体意识的限制,将自身的存在等同于形而下的肉体与肉体所处的人间世,使作为自然之性的人的真实属性受到淡忘。虽然世俗之人因畏惧丧失肉体生命而抗拒回归大道的生生不息,但是有形的生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死亡的真正意义在于人与道合一、回归永恒,真正实现不朽的自然之性。
五、未思之处:“不朽”的殊途
庄子与约翰·多恩的死亡观念体现出明显的“同途而殊归”的特点,在强调死亡过程的相似性同时又认为死亡具有完全不同的指向。他们之所以得到并置,除了他们的死亡观念具有相似性,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文艺的不朽性。庄子与约翰·多恩都认为,死亡是一个明显具有超越性的行为,人的精神在实现与肉体成功分离的同时,将升华到永恒的理想境界。但是,他们对死亡之后的最终目的地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庄子认为,“终其天年”的自然死亡是实现道的基本途径。人的死亡既使元气散佚,也是消解个体精神并使顺应自然之道的过程。约翰·多恩等玄学派诗人将死亡的归宿指向“理想国”的完美世界。人在活着时只有发展出一段区别于肉欲之爱的精神之爱,才能使人在死亡以后顺利地回归灵魂世界。正像朱利安所提出的,把中西方思想并置在一起的目的是发现这些思想的未思之处。这也意味着,通过《庄子·至乐》与《别离辞·莫伤悲》的并置,庄子与约翰·多恩关于文艺不朽论的未思之处得以显豁,成为管窥并体察人生不朽的有效途径。弗朗西斯·培根在《学术的进展》中指出:“总结我们关于知识和学问的尊贵和优越的讨论,我们认为,知识和学问的价值在于人们最渴望得到的不朽和延续,正是人们渴望不朽的愿望促使人们繁殖后代,修建房屋,养育子女;不朽的渴求还造就了许多房屋、建筑、纪念碑;不朽的期望还铸就了回忆、名声、颂扬;实际上人类其他的各种愿望也正是来源于对不朽的追求。”[15]52
培根关于不朽的论述主要肯定了活着时的各种努力对死后的声誉的决定意义,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现世化的特点。但是,他也指出不朽的追求既是有形的生命的延续,也是现世人生存在的动力,在对活着的肉体不断形成超越的同时,也使活着时的精神性存在在肉体死亡以后得以延续。弗朗西斯·培根的这一论述,有利于进一步审视庄子与约翰·多恩的生死观以及由此引出的不朽论,也体现出中西文化关于不朽的不同看法。庄子提出的死亡超越是全方位的,彻底摆脱经验世界、个体与人生的存在性限制的,回归宇宙初始的道的混沌状态。“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邪?果不乐邪?吾观夫俗之所乐,举群趣者,硁硁然如将不得已,而皆曰乐者,吾未之乐也,亦未之不乐也。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7]446这种无乐、无誉的超越意识源自对人和世界的本质——“道”的理解,与西方认为人的灵魂来源于理想国的理解完全不同。“老子所贵道,虚无”,“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16]2156人要通向终极自由的世界,成为无桎梏、无羁绊的存在,不受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者”的遮蔽,实现人生的“澄明之境”与“诗意的栖居”,必须泯息“一切相对分别”的成心,与“万物浑然一体”的大道相和合。因此,死亡既能够突破并超越现实人生价值,又进入“与道合一”的自然而然的境界。死亡,在庄子看来已经不是途径和手段,而是道、永恒与不朽的具体体现。
约翰·多恩在《别离辞·莫伤悲》中关于死亡以及爱情延续的描写,仍然处于“个体精神”视域中,在以这一精神为依托的基础上强调死亡是对有形生命的超越,是由“个体精神”转化为超验永恒价值的具体生成,也是实现人生不朽的基本路径。《别离辞·莫伤悲》通过描写爱人的坚贞、对陪伴的期许以及最终所表达的感激之情,指明爱对尚处尘世的肉体中的灵魂具有提炼能力。这首诗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爱情对人生的根本意义在于,它能够贯穿人的一生并超越死亡,使人在结束尘世的生命时顺利回归“自我”的本源。“自我”与爱情都在死后的世界中继续存在,不断延续。约翰·多恩通过描写爱情并强调其对死亡的超越,既赞美了精神之爱的重要价值,也对个体精神进行了讴歌。个体精神是爱情得以存在的基础,也以爱情这一人生表象超越死亡,把世俗的活人世界与死后的理念世界联系在一起。“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是“个体精神”的具体体现,能够自由地表达其爱意与情感。个体精神既通过“超越死亡的爱情”证明人生存在的永恒价值,也被约翰·多恩运用丰富的想象与隽永的艺术语言描写出来,融意于象,构筑出奇思妙喻的精妙世界。诗歌通过“圆规”等一系列隐喻的使用,使读者在对回环往复的意象的体会中认识到个体精神对死亡的超越所具有的复杂美学意义,以及由死亡所反衬出的个体精神的深刻、复杂与奇异。因此,与庄子把自然死亡等同于不朽的思路不同,约翰·多恩笔下的死亡是展望不朽并使不朽得以凸显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