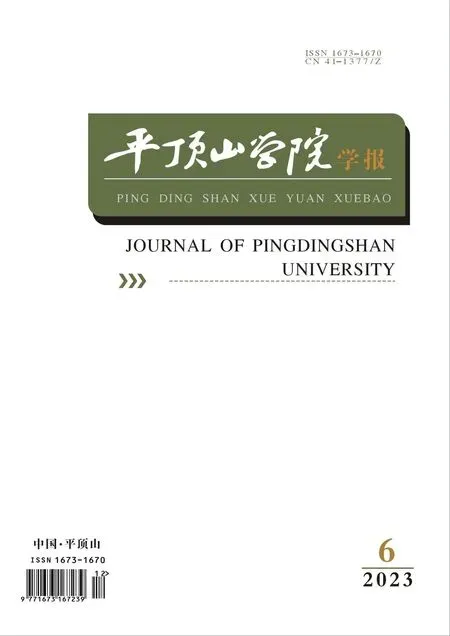原始儒家伦理观中的自助精神研究
徐佰义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原始儒家是指中国古代尚未被政治化的儒家,以先秦时期的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人物。作为轴心时代的华夏文明及华夏文明的根基部分,原始儒家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魅力的原发思想。原始儒家哲学立足于道德,以仁、礼为核心思想,而自助本身就是一个伦理或道德范畴的概念(1)道德主要体现为自律,以唤醒人们内心的良知而自觉履行道德义务为最终目的,由此观之,自助精神与道德的自律性是完全契合的。,其精神也必然且自然地彰显于原始儒家的伦理观中。本文抛砖引玉,探析原始儒家自助精神体现在哪些层面及其何以体现在这些层面。
一、原始儒家自助精神的历史奠基
自助精神是指一种凭借自身力量完成事情,在逆境中克服困难,不过度依赖外部条件的意识。自助既是个体的道德品质,也是民族的精神力量。回望中国古代历史,时代的发展总能激荡出新的思想观念。原始文明时代中国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夏商周三代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明,殷周巨变则是从他助走向自助的一次重大精神突破。
(一)殷周之际天命观的道德转向
夏商周三代都将自己的统治依据归属于天命,只是在朝代变更中,人们对天命是否恒常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
1.夏商的天命有常观
在夏商时期,上天也叫“上帝”,是被当作最高的神来看待的。《礼记·表记》篇有这样的记载: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憃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1]1056-1057
上述记载是孔子对于三代政治制度的综合性评价,不难发现,三代对于鬼神都持敬的态度,尤其是殷商,孔子谓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为何三代都尊神?这是因为天作为至上的最高神,给予了最高统治者统治权。在认知水平还比较低下的时候,人们把自身的统治依据建立在天神之上,称作天命。在那时,统治者往往通过祭祀、占卜以及天象来判断事物的变化并引导人们的生活,三者实际上都是他助性质的活动力量,这也充分说明人们尚未认识到自身的巨大力量,主观能动、道德自律等专属于人的特性也尚未被认识到。此时人当然还没有真正的自我觉醒意识,统治者也只能把其政治统治的依据归于上天,认为自身是上天的代言人,从而造就了天命有常观。
殷商时天命有常观体现得极为明显。在《诗经》中,《商颂》不同于《周颂》,后者多以德为中心,前者则完全以天命为中心。在殷商社会中,人们所做的努力就是祭祀百神,而天神作为最高神,给予了商族人统治的权利,自然是他们至高无上的信仰。在那时,人们是没有自助意识的,唯将一切寄予天命,因此,殷商的统治者通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2]888的神话故事宣称自己是上天的代言人,并由此合法拥有统治权。
灭夏之后,商族人更加强调自身肩负的天命。在《汤誓》中,商汤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3]82“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3]82商汤宣称,夏桀有罪,天要处罚他,自己只是代表天灭夏。殷商强调夏有罪,并没有像西周那样把“德”的因素阐释出来,可以说,殷商取代夏朝时强调的是反面,即有罪当罚,而西周取代殷商时强调的是正面,即有德当保。
2.西周的天命靡常观
吸取夏、商的经验教训,西周统治者对于天命的思考逐渐深入,开始从天命有常的政治观念转向天命靡常。总的来看,周人依然保持对天的至上信仰,但是他们认为只有重视道德,才可永保天命,开始把政治统治的依据转移到人的身上,逐渐扩大人事在国家统治过程中的力量,形成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3]262的统治观念。
《诗经·大雅·文王》篇不仅歌颂周文王的高尚品德,还多次提及天命的概念,体现了殷周之际统治者对于天命的重新认知。这首诗开篇就点名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2]643的主旨,暗含着西周统治者对天命认知的深化。接下来,《文王》篇还明确指出“侯服于周,天命靡常”[2]645,就是说商人臣服于周是天命变化无常的结果。该认知一改殷商的天命有常观,随之周人又进一步思考天命为何会变化:“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2]645他们认为只有努力修养德行,才能永远地配合上天的旨意,争取到更多的福祉。在西周统治者对于天命的认知中,“德”的地位凸显了出来,这正是《尚书·蔡仲之命》所说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3]262尽管西周统治者意识到人的德行在国家统治中的重要性,但面对大量的殷商遗民,周人并未完全抛弃对天命的信仰,而是将德与天命结合起来,更加注重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人们认识上的这一重大突破无疑为原始儒家自助精神奠定了初步的历史根基。
(二)周公制礼作乐
为强化“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政治理念,西周采取了一系列敬德保民的政治举措,并以周公制礼作乐最为突出。礼和乐的目的皆为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此时的“德”立足于统治者的角度,听说者大多是当时的贵族阶级,这种自助精神的萌发也相应体现在部分人民的整体性认知观和实践观上。
1.制礼作乐的方式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文治精神
周公制礼作乐是人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标志,在这时,人事的凸显无疑是自助精神的彰显。《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4]《礼记·明堂位》篇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1]604时值姬发死后,其子成王姬诵年幼,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多次平定叛乱,周朝得以稳步发展。游唤民等指出:“周公摄政六年的前前后后,诸侯已封建,洛邑已成,东都已定,为了进一步使有周一代政治达于高尚优雅之境,致太平之盛,从而以典章制度肯定和完善已经或将要建立起来的新的统治秩序便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才有周公的制礼作乐。”[5]另,所谓“偃武修文”就是社会稳定之后需要以文治谋求精神和谐,因此,制礼作乐体现了文治精神。
2.制礼作乐的目的主要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礼乐制度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其目的是一致的。在礼的方面,包括了典章制度、礼节仪式等。典章制度上,西周推行井田制,建立了宗法制和嫡长子继承制。周公还推行国野或乡遂制度,改革了祭祀制度。礼节仪式上,周礼包含了天子登基大典的仪式、诸侯朝见天子之礼,以及吉、凶、宾、嘉、军五种礼仪。在乐的方面,周朝的音乐大体可分为雅乐和俗乐。宫廷音乐为雅乐,民间音乐为俗乐。目前可考证的由周公所作的乐有歌颂武王击败殷商的战功、宣示开国盛况的《大武》之乐,宣扬德政的《周颂·时迈》之乐,起着周朝国歌作用的《大雅·文王》之乐,以及歌颂文王实行德政的《周颂·清庙》之乐。乐与礼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统一。
3.礼乐的道德教化机制完善
《礼记·曲礼》篇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1]6这说的就是中国古代文明中的礼教思想,礼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以教导人们为目的。《礼记·礼运》篇又说:“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故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1]438“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1]438“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1]438这些论述强调礼义的重要性,“以治人情”还阐明了礼义的教化机制。实际上,礼是通过约束人自然的性情和欲望来实现社会的有序状态。荀子在这一点上说得更清楚,他指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6]42,任由人本来的性情发展就会导致争夺进而产生混乱[6]46-47,因此需要用礼约束人的行为。此外,这里还指出了制礼的原则:以义制礼。何谓义也?《礼记·礼运》篇说:“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1]438义是区分事理的标准、衡量仁爱的尺度,在儒家话语体系中通常是合宜和适度的意思,因此,礼根据义制定就能达到万物和谐的共生状态。
礼教还包含了乐教的成分。乐与礼发挥作用的机制不同,但它们相辅相成,都以道德教化为目的。其机制的不同具体体现在“乐者为同,礼者为异”[1]720、“乐由中出,礼自外作”[1]721、“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1]721、“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1]722、“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1]723、“乐由天作,礼以地制”[1]723等方面。礼与乐虽然教化机制不同,但是两者起到的精神作用是相同的,即通过道德教化实现社会和谐。
综上所述,不同于殷商之时仅仅求助于上天的神秘力量、却忽视了人本身在历史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周公制礼作乐体现了文治的精神理念,凸显了人事本身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出的重要作用,彰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制礼作乐是基于对当时社会发展的道德化认知——把道德融入意识形态之中,同时,制礼作乐更是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正是兼具了人主动地认知世界和在认知基础上再改造世界的综合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讲,西周的礼乐文明无疑成了原始儒家自助精神的重要历史奠基者。
二、原始儒家自助精神体现在天人合一的致思维度中
如上所述,周公援德入礼奠定了原始儒家自助精神的历史根基,孔子则将德的内容落实在仁德之上,建构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要旨,并逐步将重心从统治阶级的道德教化转向个体的道德修养。然而,仁究竟是如何被创立出来并运用到人的实践活动中的?对于这一问题的探寻需要追本溯源,回到原始儒家伦理观天人合一的致思维度之中。
(一)《周易》中对于天道与人道的伦理认知
天人合一中的“一”是指道德,天人合一也可以被称为天人合德,以天道论人道就是以天德论人德。那么,古人对于天道的伦理认知或道德认知是怎样的?天道被建构在何种德性上?在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中,《易经》清晰地展现了古人对于天的伦理认知,《易传》(2)在欧阳修否定十翼与孔子的关系之前,汉代以后的学者大都相信司马迁、班固孔子为《易经》作十翼之说。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十翼不是孔子所作,但是也有认可班、马的说法者。详参高亨、董治安:《孔子与〈周易〉》,见《文史哲》,1962年第6期,第5页。又将这种伦理认知不断深化。
作为六十四卦的首卦,《乾》卦就阐述了对天道的伦理认知。这种伦理认知不是凭借人的想象或者形而上的理论论证,而是基于作者对自然之天的直观观察。《乾》的卦形是六个阳爻组成的,展现的是纯阳的性质。《乾》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7]1《乾》卦象征天,作者认为天体现着元始、亨通、和谐有利、贞正坚固这四种德性。作者之所以赋予天这样四种德性,在于对天之“健”的理解。据《说卦传》,“乾,健也”[7]435,也就是说天象征着强健。古往今来,苍天在上,静默不语,健行周流,昼夜不懈,永不衰竭,因此,天的核心德性当为“健”,就是不依赖外物,且永远运行不息。“元,亨,利,贞”是“健”之德的扩充,具有“健”之德方能创生万物,亨通有利。这种德性对应在人的身上就是自强不息的自助精神,因此,《象》传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7]5的呼吁。这是由天道走向人道、由天德走向人德的致思路径,指代君子当效法“天行健”之象,立身行事当不断进取、奋发图强。
《周易》中除了建构自强不息的天道观和人道观,还呈现了事物是在两种对立的性质的辩证统一中发展起来的规律。这一天道规律同样告诫人们要奋斗不止,且居安思危。这在《周易》的六十四卦中是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例如《乾》卦和《坤》卦,《泰》卦和《否》卦,《损》卦和《益》卦,《既济》卦和《未济》卦。《周易》的原理是以具备阴和阳两种性质事物的互相转化来体现物极必反、辩证统一的哲学思想,如《乾》卦和《坤》卦是阳和阴的互相转化,《泰》卦和《否》卦是通泰和闭塞的互相转化,《损》卦和《益》卦是减损和增益的互相转化,《既济》卦和《未济》卦是事成和事未成的相互转化。需要强调的是,《既济》卦和《未济》卦是六十四卦的最后两卦,意义深远。《既济》卦代表事已成,却并不是六十四卦的完结;作者用《未济》卦作为最后一卦,在次序上虽居于末,但在意义上却是开始性的,提倡人在逆境中进取。《未济》卦的卦形是下坎上离,从取象上来看,就是下水上火、水火不交,乃事未成之象,并且六爻皆不得位,因此,朱熹曰:“未济,事未成之时也,水火不交,不相为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为未济。”[8]87可是,《未济》卦中也并非全是不利因素,仍然有可行之处,那就是六爻上下能够刚柔相济,循着这一有利因素,便可完成从未济到既济的转化。在这里,《周易》强调人们要在逆境中寻找希望,不断地努力和进取,最终化逆境为顺境。基于此,《未济》卦象征人要积极努力,开始新的征程,而不是指事情以未济消极而终。这也体现了“生生之谓易”[7]381的重要思想,且在逆境之中寻找希望并砥砺奋进仍然彰显了人的自助精神。
(二)孔子之仁的致思维度与实践路径
仁是原始儒家的伦理要旨,亦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孔子在仁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除了在《周易》中阐述仁的致思维度,他还在《论语》中建构了以道德内求为仁之实践路径的理论思想,让原始儒家的自助精神在仁的伦理要旨中体现得更为清晰明了。
1.仁为“众善之长”
《周易》中建构了天人合德的形上逻辑: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7]7
《文言》的这段论述将天德推向人德,简而言之,即天的四种德性元、亨、利、贞对应着人的四种德性仁、礼、义、智。这种对应关系之间是有一定的逻辑支撑的。朱熹在《周易本义》中给出了他的理解:
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知,而为众事之干。干,木之身,枝叶所依以立者也。[8]146
朱熹将德性融入四时之中,以一定的逻辑关系将天德落实到人德,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致思维度。在这里,仁、礼、义、智是四种对等的道德德性,就犹如四季一般。在这四种德性之中,仁是居于首位的,也是最核心的。仁是由天之元德对应而来,于时则为春。“元”有开元、元始、开始之义,意味着事物的开端,自然对应着四季之春,那么为何对应到人则为仁呢?人们通常用果仁来指代水果的种子,既然果仁是指生命的开始,仁也就被赋予了与元同样的开创之义。这里还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为何《周易》的作者将元与仁归为“众善之长”。元是天德,仁是人德,于时皆为春,象征万物复苏,两者都意蕴着生命的开始。如果这世界上有千百万种善行,有哪一种善行能大得过给予生命的孕育和开始?《周易》将其理解为“众善之长”是符合逻辑和情理的。
2.内求的实践路径
《论语》中“仁”字出现了一百多次,孔子在《周易》的基础上继续发扬了仁的思想,确立了仁的理论向度。在《论语·颜渊》篇,孔子首先给出仁的定义,进而将爱人视为仁的根本定义,并建构了众多仁的理论向度。在这众多的理论向度中,为仁的主体性和道德内求路径又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这两个层面的仁爱思想都建构在个体的道德修养观之上,充分体现了原始儒家伦理观的自助精神。
《论语·颜渊》篇记载了孔子和弟子颜渊关于仁的对话。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9]125在这里,孔子除了指明仁与礼的关系,更以反问的形式强调了为仁的主体性。《论语·述而》篇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9]96孔子在这里再次以反问的形式强化为仁的道德主体性。为仁之主体性是指道德个体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进行道德实践活动的特性,既彰显了道德主体的自助精神,同时也彰显了人的自由意志。朱熹对《述而》篇中孔子的论述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为远者;反而求之,则即此而在矣,夫岂远哉?”[9]96朱熹认为作为心之德行的仁不在外面,放失而不寻求就会觉得仁离自身很远,但若回头去寻求,它就在心里,哪有什么远呢?朱熹的理解进一步指明了为仁当以内求为实践路径,而非外求,且与《论语》中表述的仁的实践路径完全契合。在《论语·卫灵公》篇,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9]154孔子还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9]155在《论语·学而》篇,孔门弟子曾子更是留下了著名的修身之道:“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9]50《论语》中这些论述都指出了为仁当以道德内求为其实践路径,充分彰显了儒家的自助精神,并对后世学者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让自助精神在儒家思想的发展中不断得以强化。
三、原始儒家自助精神体现在“思”的德性实践活动中
就先秦而言,孟子最为充分地继承了孔子仁德的内求路径,并且建构了更为体系化的、以“思”为核心的道德修养理论,强化了原始儒家的自助精神。“思”作为孟子的道德修养工夫,是在人性观的理论基础之上和可欲之谓善的逻辑主线中建构起来的,是孟子伦理思想的终极目的。自助精神则是“思”的精神内核,意义深远。
(一)基于情感的性善论
孟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探讨人性善恶的思想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9]164,孔子对于人性的考察就只有这一句话,他并未对人性的道德属性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然而,孟子却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观。
孟子人性善的观点是在和告子的辩论中提出的。他们关于人性的争论主要有三个回合。其一,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10]304告子持人性无善恶的观点,这里他以杞柳和杯棬作比喻是说明表现出仁义的道德性行为改变了人的本性。孟子质疑告子是顺应杞柳的本性来制作杯盘还是残害杞柳的本性来制作杯盘,如果是后者,孟子指责告子的言论是带领天下的人来损害仁义[10]304。其二,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10]304告子再次重申了人性无善恶的观点,他以水流为喻,认为后天的引导决定了人的发展方向。孟子利用水的另一特性再次驳斥了告子:“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0]305孟子预设了人的本性为善,认为人性善犹如水自然而然就是往下流一样。其三,告子曰“生之谓性”[10]305,孟子则认为,如果生之谓性,则无法区分人与动物的本性[10]305。由此,孟子在对告子的辩驳中,提出了人性善的观点。
再来看孟子对于人性善的论证方式。如果不能有一定的理论支撑,人性善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无法解释人性中恶的行为。那么孟子是如何论证人性善的呢?在《孟子》中,他基于人的情感视域,以心善论性善。孟子说: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10]220-221
孟子认为人见到小孩子将要掉落井中,都会产生救助的冲动,都会有恻隐之心。他基于经验论的观点,从人的情感视域出发,认为人的本心都是善的,从而进一步论证人性善的观点。孟子显然是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混淆而谈,这也是其性善道德论证中的失败之处。然而,孟子性善观的提出及论证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为孔子仁爱思想的实践性弥补了理论基础,即由于人性本善,所以仁具有实践性,而且为其自身以“思”为核心的道德修养观做了理论上的铺垫。
(二)“可欲之谓善”的逻辑主线
“可欲之谓善”[10]346是孟子提出的一大重要观点,出自《孟子·尽心下》篇。在孟子看来,值得追求的事物就是善的,这是这句话的正推逻辑,然而,这句话还隐含了一个反推的逻辑。如果首先界定了“可欲之谓善”,那么,反之,善者必可欲,也就是说如果一些事物已经被界定为善的,那么这些事物就一定是值得追求的。孟子以心善论性善,在他这里,人的本心与本性都已经被赋予了善的道德属性,那么自然是值得欲求的。这也正是孟子所说的要不断扩充自己的善心和善性:“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10]221在“可欲之谓善”的逻辑指引下,人要不断去扩充本于内在的善心和善性,把人性中良好的有利因素全部开发出来,最终抵达至善的圣人境界。
(三)“思”的道德修养方法
孟子除了赋予人心善的道德属性,还意识到心作为“君主之官”[11]的重要功能——“思”。孟子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10]313-314孟子认为心和其他的器官不同,人的眼睛、耳朵等器官是不会思考的,容易被外物所蒙蔽。这种不会思考的器官只是器物罢了,与外物接触的时候就会受到诱惑。然而,心却是理性的,人充分发挥其“思”的功能就能够克服客观器物带来的蒙蔽和迷惑,因此,人要首先把心作为“君主之官”的地位奠定起来,这样就能够通过“思”而充分发扬心之善性,进而不会被次要的器官夺走人心中的善性。孟子多次强调“思”的功能,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10]307、“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10]314,足见他对“思”的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自助精神在孟子的思想体系中是十分突出的。很多学者将“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10]260作为孟子道德修养观的一贯之道,因为在孟子这里,他已经预设了人的本心和本性为善的道德属性。也就是说,人的内在具有可求助的有利因素。孟子所有的思想最后落在一个“思”字上,“反求诸己”是道德修养的内求路径,思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方法论。“思”依靠其自身的作用与价值成为人禽之别的关键点,也有力彰显了人的内在价值[12]。因此,思作为一种道德主体的理性实践活动,是孟子沿袭孔子之仁的内求路径而得来的思想成果,彰显并进一步强化了自助精神在个体生命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如上所论,原始儒家伦理观中的自助精神关注人的内在价值,寻求依赖自身而非外物的理念。与自助相对的概念是他助,人总是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他助自然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依靠他人的帮助收效甚微。他助只在某些时刻和境遇下出现,自助则是个体能动性的体现。“自助精神是个人所有成长的真正根基,散布于众的自助精神,是民族活力迸发的真正源泉。”[13]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应以培养自助能力为主,这包含了自主、自立、自强、自信、自律等涉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诸多品质。尤其是面对当前社会中以拜金主义为代表的物化思想及以青年躺平现象为代表的消极人生观,自助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改善人们过度依赖外物和不作为的思想观念,因此,自助精神的研究对于当代个体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回到中国文化的元典时期,从自助精神的源头——原始儒家哲学中汲取有益成分,不仅更加重要,而且不可或缺。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