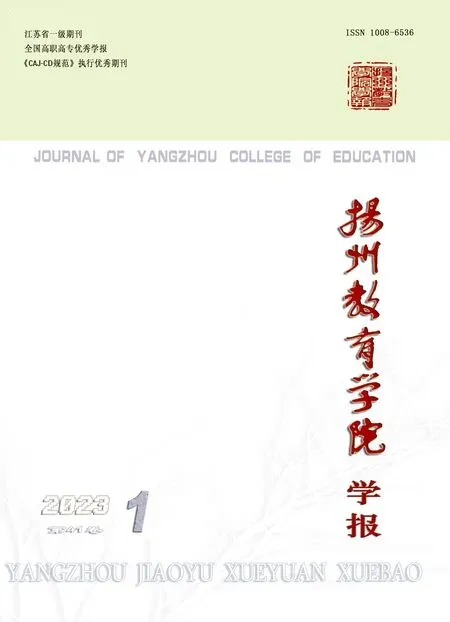为了忘却的写作:双雪涛、班宇、郑执创作论
公 言 海
(浙江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58)
近年来,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的创作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三位80后年轻作家的作品同时引发了大众文化领域和纯文学领域的重点关注和集中讨论,他们也由此被冠以“铁西三剑客”“东北文艺复兴三杰”“80后东北作家群”和“新东北作家群”之名。
作为年轻的文学新人,三人的出场近乎默契,在2016—2020年间,三位作家共出版6部小说集,完成了一次集中的创作“爆发”,在短时间内收获众多读者与奖项的同时,也使许多评论家感到欣喜与鼓舞:“我们的作家在现实主义的追求上实现了一次重要的突破。”[1]“一座已经崛起的小说城将注定不会再沉没。”[2]“‘新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将不仅仅是‘东北文学’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的变化。”[3]
评论家们的欣喜之声言犹在耳,但是曾经身负重望、蓄势待发的三位黑马作家,却在短暂的“爆发”之后,集体步入了某种程度的“沉寂”:三人再未出版新的作品,发表小说的数量也断崖式下降。默契的“爆发”引人关注,但是集体的“沉寂”更值得思考,本文所追问的便是:这种迅速“沉寂”的创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书写?集体“沉寂”的原因又是什么?
一、伤痕,谁的伤痕
东北下岗潮是双雪涛、班宇、郑执作品的主要背景。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为适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大量国有企业进行改制,大批工人下岗,而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在全国下岗的3000多万职工中,东北便有800多万,占全国下岗职工总数的25%。几百万人失去生计、生活困苦,下岗成为那个年代东北人心中一道隐隐作痛的伤痕。
这一时代伤痕在三位作家的小说中得到了生动书写:父亲失业后家徒四壁,冬天没有钱买煤,以醉酒入睡避寒;下岗后以卖烤串谋生的父亲,在元旦前夜仍只身站在冬天夜晚的冷风中忙碌……伤痕的疼痛以其强烈与深刻触动人心,双雪涛、班宇、郑执的小说因而获得了一种可贵的真挚与动人。但是时代并未为伤痕命名,时代的伤痕降落在每个人身上时各不相同,所以面对东北下岗潮这一巨大的时代伤痕,人们不禁要问,三位作家所书写的到底是谁的伤痕?
双雪涛、班宇、郑执分别出生于1983年、1986年、1987年,下岗潮到来时,三位作家正处少年,尚在父母保护之下的他们只能算作时代变动的旁观者,而他们的父辈——李守廉、孙旭庭、王战团们,才是真正的亲历者,小说所描写的在下岗潮中艰难挣扎的也是他们,或许三位作家所书写的正是父辈的伤痕?但是这样的推论无疑过于顺畅,过于粗疏,令人生疑。小说中,第一人称“我”是三位作家最常用的叙述视角,但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我”都是作为子辈的“我”,没有任何一篇小说是以父辈的第一视角展开叙述。当然,这是三位作家在回忆自己少年记忆时自然采取的叙述位置,但又何尝不是叙述立场的一种无意识体现?父辈始终在子辈“我”的注视或回忆中说话、行动,虽然故事得到了完整叙述,但父辈实际上只是被观察、被诉说、被征用的故事主人公,始终失语的父辈的内心感受与真实心理从未得到展示。于是,父辈众多疼痛的瞬间、难熬的时刻都被轻轻抹去,只剩下流畅的概括与光阴易逝的感慨:“后来,他又做过很多不同种类的工作,学着去做一些事情,很快他就变老了,这一点也出乎意料,我是说,那些年过得都很快。”[4](班宇《肃杀》)而父辈的生命中得到重点诉说的时刻,则只是子辈的“我”感兴趣、有感触、印象深刻的时刻,当然,诉说仍然以子辈“我”的视角和声音进行。正如班宇所说:“那个年代对我来说,更近乎于一种诉说的介质、一种镜像,而非实际存在,或者说,我是在假托于此,进行一种更为自我的表述。”[5]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父辈与子辈对于下岗潮的书写会如此迥异。早在20世纪90年代,谈歌、何申、刘醒龙等作家就已对当时正在发生的经济转轨、国企改制进行了敏锐反映,谈歌的《年底》《大厂》《车间》等作品就直接触及国企改制、工人下岗的问题。这批作家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正是双雪涛、班宇、郑执的父辈,也是90年代阵痛的亲历者。对于他们而言,正在发生的经济转轨、国企改制是放置在每一个具体的人面前,需要每个人去面对、承受、解决的“艰难”。时代其实首先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疼痛的伤痕,就像《大厂》中的贺桂梅、《年前年后》中的李德林、《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每个人都在时代变动中忍受着难言的疼痛,但是他们无暇沉湎于对于疼痛的自伤,而是集中全部精力解决眼前的难题——挽救“大厂”或为县乡百姓造福,以图渡过难关。领导如此,普通百姓同样如此,敏锐的班宇也早对父辈亲历者的这一态度有所感知:“所有的人都一样,每一代人都在遭遇。需要消化,但是来不及消化。我们家亲戚里很多人下岗,但是从不觉得他们会把自己的痛苦互相倾诉,他们知道抱怨是无效的,所以也就不去怨天尤人。”[6]
不过,无论是一心挽救危机的领导者,还是不去怨天尤人的普通人,他们搁置疼痛向前看的姿态实则都包含着亲历者无计可施、别无出路的无奈,但是作为旁观者的子辈从这种被逼无奈中看到的,却是鼓舞人心的顽强与乐观。这是一种微妙的转变,因为无奈与顽强在很多情况下紧密相连,但是无奈和顽强却又决不能混淆,这一微妙的转变实则表明了子辈与父辈之间的遥远距离。双雪涛、班宇、郑执根本无力也无意从宏观上理解下岗潮以及思考如何应对下岗潮,他们不愿认同也不能接受宏观上的应对之法。双雪涛说,“上一辈和这一辈,苦难的方式不同”[7]203,身处父母保护之下的少年们旁观着下岗潮,他们无法真正理解下岗潮的由来,更不用去思考如何解决,他们所拥有的只是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于是,父辈面对下岗潮时的辗转踌躇、酸甜苦辣,在少年的心中都统统简化为一种朦胧的疼痛感,子辈作家创作的动机也正出于此,或许可以说,谈歌、何申、刘醒龙等父辈作家和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位子辈作家所书写的都是只属于自己的下岗潮。
班宇说:“所有人都在灰尘之雾里,看不清未来的方向,但必须往前走,我小说讲的不是怀旧,而是你必须走入尘埃之中的感觉,你没有办法不向前走。”[8]双雪涛、班宇、郑执所书写的正是旁观父辈“必须走入尘埃”时,少年心中的“感觉”,是这一时代变动中独属于子辈的伤痕。这种书写是子辈这一代人对于东北下岗潮所作出的独特反应。
二、少年贫穷,何以成为伤痕
下岗潮最直接、最强烈、最疼痛的后果便是经济的贫穷,无数家庭失去经济来源,“那时抢五块钱就把人弄死了,这些人找不到地方挣钱,出了很大问题”[9],双雪涛、班宇、郑执正是在自己的少年时期遭遇了这一切。少年是最为敏感的年纪,贫穷无疑会对少年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但不得不问的是,少年时期的贫穷并不罕见,可它为何偏偏在双雪涛、班宇、郑执心中,成为了如此刻骨铭心的伤痕?
首先,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三位作家的伤痕并非来自单纯的贫穷。双雪涛、班宇、郑执对于东北下岗潮的书写,并非旨在简单表现人们下岗后的生活贫穷,比如双雪涛的《大师》中,父亲下岗后生活极其潦倒,没有生活来源,依靠老街坊的帮衬才勉强维持,“我”也是依靠老师垫钱才得以继续读书,这是何其凄怆的生活。可是,双雪涛对于这对父子的凄怆生活只是一笔带过,将写作重心置于父亲的精神。再如班宇的《肃杀》中,失业后靠骑摩托“拉脚儿”为生的父亲,在冬天的早晨跺着冻僵的双脚等客人,这的确令人心酸,而父亲丢车后的茫然、焦急更使人动容,但是小说对此的描写仅点到为止,其后篇幅的着力点则在于肖树斌乐观的生活态度。双雪涛、班宇、郑执的其他创作皆是如此,贫穷的生活只是作品的虚幻背景,三位作家的作品绝非揭露下岗工人生活贫穷的“问题小说”。
不同于苏童从物质贫乏的少年时代看到了“少年血”的美感,在双雪清、班宇、郑执的笔下,被贫穷笼罩的少年生活只有暗淡一种色彩。少年的“我”的目光始终注视着下岗后生活困窘的失败者,少年的“我”的声音始终伤感地诉说着他们卑微、艰难的生活。固然,时代变动带来的贫穷会让敏感的少年感受到痛楚,但是少年的生活绝非只有暗淡,还有着遇到“温柔有力的手”[10]的感念,有着“战栗、激动,杀气重重”[11],也有着完成“唯一一件能令我爸提起兴致骄傲的事”[12]的高光时刻,但是这些亮色在三位作家的笔下都被统统排除,只余下统一的暗淡,因为双雪涛、班宇、郑执从少年的贫穷中收获的是一道道疼痛的伤痕。但是,贫穷为何令三位作家如此疼痛?其实这一问题的答案早已藏在了三位作家自白的文字中:
家境的差别让我(双雪涛——引者注)从那时起就产生了一种自卑感……这种自卑一直困扰着我,我经常想,到现在我还因此是个比较懦弱的人。[13]
那时内心有一点忧虑……虽然家里极力营造一种平和的氛围,但我(班宇——引者注)仍能感受到一种不可控,如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头上,久久挥之不去,只能去自寻出口。[14]
每隔几年,一个饭桌上的叔叔就少几个人,死的、失踪的、进去的。他们内心一定有自己的苦痛……我(郑执——引者注)就是在这些人包围下长大的。[15]
下岗潮到来之前,东北作为全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拥有着规模最大、设施最健全的国营工厂,工厂为工人们提供了从衣食住行到空闲娱乐的一切生活所需,彼时“工人老大哥”的生活稳定、富足。但是随着下岗潮的到来,国企破产重组,工人纷纷下岗失业,无数家庭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为继,人们经历了从衣食无忧到朝不保夕的坠落。
这正是双雪涛和班宇所经历的贫穷——从富足坠落而抵达的贫穷。出生于“工人老大哥”家庭的双雪涛、班宇、郑执,度过了富足的童年,但在最敏感的少年时期却突然坠落进不可逃脱的贫穷,这种落差对少年来说何其疼痛,正如少年时“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鲁迅,直到四十一岁时还仍然深深铭记着自己当时从“一倍高的柜台”上看到的“侮蔑”。由此三位敏感的少年感受到持久的“自卑”、阴影般的“忧虑”以及藏于内心的“苦痛”,这正是他们作品中疼痛感的来源。正如郑执所说:“文学有一定的延迟性,二十年后,当我们成人,有了表达能力,童年时期在我脑子里种下的这粒种子发芽了,这粒种子,正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经历的残酷现实。”[16]
东北下岗潮令无数人由富足坠入贫穷,其中所含的对比与落差令少年敏感于心、郁结于胸、以致成伤,贫穷由此成为三位作家心中始终隐隐作痛并经久不愈的伤痕。
三、如何疗治,以及有何“副作用”
班宇说:“见证了父母从企业的辉煌到‘双下岗’,耳闻目睹了那段历史,这些事情在我的头脑里一直是一个小小的负担,我要通过写作把它给卸掉,或是刻写在更深处。”[14]当少年长大成人,并因不同的原因而拿起创作之笔,他们终于发现了疗愈伤痕的方式——文学,于是三位作家默契地通过写作,展开了隐秘的自我疗治。
首先,直面伤痕,重新整理过去。三位作家都重新梳理了下岗潮后的艰难生活,一方面,从父辈的故事中截取触动自己的“某个模糊短暂的时刻”[17],或一种“说不清的感情”[18]进行重新讲述,通过对众多生活困窘的失败者及其暗淡故事的书写,捕捉并表达这些模糊的时刻与感情,自己的来路由此变得清晰。另一方面,回顾自己的中学校园记忆,这是双雪涛和郑执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双雪涛看来,初中的经历对自己来说“就像是中了玄冥神掌”[19],而要“治愈自己,把中过的玄冥神掌的余毒吐出来”,“只有把初中的磨难写出来”[7]203;对郑执而言,高中的压抑和迷茫令他感到强烈的精神困苦,在小说《我们是不是很无聊》(又名《浮》)和《生吞》中,他分别对校园生活进行了不自觉的回望和有意识的重新整理。重新体会并表达伤痛,这是疗伤的基础。
其次,书写父辈的人生,从中获得力量与信念。三位作家从下岗潮后的父辈故事中发掘出父辈的力量、坚强与尊严,作为自己疗治伤痕的精神资源。以被双雪涛视作重要作品的《大师》为例,小说中的父亲穷困潦倒,堪称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但他却有着一种动人的纯粹和洞达的智慧,《大师》的故事不仅是双雪涛对于父亲一生意义的肯定,更是对于当时身处困境、失去写作信心的自己的巨大鼓舞,可以说,是小说中“失败”的父亲赋予了当时双雪涛坚持写作的信念。正如双雪涛所说,父辈那代人是有力量、有生命力、更笃定的,关于父辈的记忆对于双雪涛来说“有着非凡的,决定性,信仰一样的意义”。[20]班宇则致力于从直面“艰难”的父辈身上发现鼓舞人心的顽强,他曾直言:“其实我想表现的是,东北是经历过大变迁的,人们的生活也确实经历了变故,却并没有穷途末路,每个人都活得特别顽强。”[21]孙旭庭、肖树斌、张久生、董四凤、许福明……每一个人都在沉重的生活中散发出顽强、乐观、坚韧的光芒。郑执也是如此,《仙症》中的精神病人王战团善良、要强、纯粹、有原则,那句“你爬啊!爬过去就是人尖儿”正是对于作者最好的鼓舞。在父辈的鼓舞下,郑执认真地说:“从今往后,我只想努力不再被万事万物卡住。”[22]三位作家从上一代人身上找到了从伤痕处新生的力量与信念。
第三,植入个人的真善美理念。三位作家通过虚构设计,将自己关于人生和社会的真善美理念植入到小说中,用理想的光明和温暖平衡现实的艰难与冰冷。对于双雪涛而言,他认为“小说里应该有一些‘温柔的奇迹’”[23],这既体现为小说中坚守善良、宽容、正义的“光明的尾巴”,如《平原上的摩西》中庄树最终掏出烟盒、《冷枪》中棍儿出于义愤的偷袭等;也体现为小说中象征超越世俗的奇幻情节和宗教因素,如《飞行家》中二姑夫李明奇坐热气球去南美洲,以及小说中屡次出现的“摩西”、十字架、教堂等。至于班宇,他常常为作品设置一个意义复杂的结尾,并于其中隐含一种善良真挚的立场,如《梯形夕阳》结尾处“我”望着河流而产生的深沉遐想,表现出班宇对于困境中个体的慈悲与责任感。郑执的小说,则在众多关键情节处屡屡体现着真善美,如《凯旋门》结尾处时建龙卧推受伤但阳痿却不治而愈,阳光仿佛驱散了这个庸碌而倒霉的小人物头顶的阴霾。郑执说:“我觉得人最有意思的,就是在作为这么脆弱的个体的时候,总会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冒出一个命运设计以外的东西,就像你刚好抬头就看到一颗流星划过。”[24]这颗命运设计之外的流星,正是三位作家插入小说中的真善美,它以温柔的光热疗愈着现实刻在少年内心的伤痕。
但是,这种自我疗治式的写作在疗愈少年伤痕的同时,也具有着严重的“副作用”,即三位作家在强烈的疗伤动机下所持有的疗伤立场,大大限制了作家对于少年记忆的观察与感受,造成了写作的单一、片面。具体而言,其一,双雪涛和郑执的青春校园题材小说(《聋哑时代》《我们是不是很无聊》《生吞》)均专注于诉说少年回忆和缅怀少年真情,对于少年与自我、少年与成长、少年与社会等问题的深层思考有所欠缺。其二,屡屡从父辈身上发掘出顽强与尊严,虽然给人信心与力量,但只显示了父辈人生的一种面向,削弱了父辈命运的丰富性与广阔度。其三,三位作家在小说中插入的真善美理念,虽然能够“平衡”现实生活的黑暗,但却牺牲了人生与世界的可能性与深度,拒绝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更加复杂的存在。此种单一、片面使三位作家的创作面临着重复的危机,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三位作家很快放弃相关创作,正如班宇所说:“在小说里面只能写自己的话,问题是说和写自己的话,现在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困境,就是如何生产出新的话。这样的作品,我也可以再写一年两年,别的期刊还能发一发,对吧?但是我不想这么干。”[18]
事实上,所有疗伤式的写作最终都会走向“沉寂”,这是此种写作的必然命运。因为疗伤式写作的动机在于内心的伤痕,当作家通过写作逐步疗愈内心伤痕,也便渐渐消解了写作的动机,所以伤痕的痊愈即意味着此种写作的终结。
四、结语
可以说,双雪涛、班宇、郑执关于东北下岗潮的创作是一种“为了忘却的写作”,用写作疗愈伤痕,以求忘却疼痛,从而卸下过去的重负。在此之后,三位作家纷纷尝试创作转型,不过从现有的转型作品来看,转型并不算成功。但是,这是他们必须经历的路途,因为只有忘记钻心的疼痛,才能自由地感知,真正拥有身外广阔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