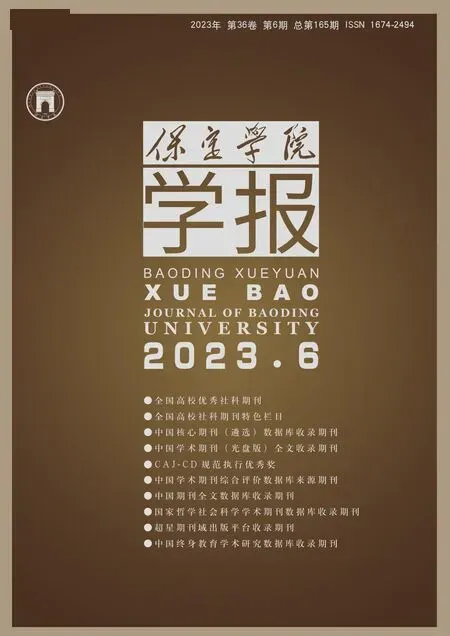叶嘉莹中西文学理论互鉴中的词学探索
李 云
(天津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天津 300222)
叶嘉莹先生(1924—),号迦陵,在词学方面多有建树,论著丰富,其中具有开拓性的是将中西文学理论相融合,对张惠言比兴寄托、王国维感发联想的说词方式,以及小词具有丰富潜能的原由、作用,进行了精密、细致、深邃的阐释和分析,为中国现代词学的发展开拓了新境界①本文经叶嘉莹先生亲自审订,获得首肯,同意发表。。
一、对王国维、顾随词学的承继
叶嘉莹的词学承继王国维、顾随而来,他们一脉相承之处有两个大的方面:其一是以真诚的生命体悟为中心,以感发联想为主要说词方式,予人以人生和心灵的启迪,传递诗词中生生不已的感发力量;其二是具有鲜明的开拓创新精神,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观照之下构建中国词学,努力为词学开辟新的道路。与西方文论偏于科学推理的思辨分析不同,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虽然有很多词话,但词学并没有发展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晚清西学东渐的大潮中,王国维是第一位尝试为中国词学批评开拓新途径的人物,他尝试“把西方富于思辨的理论概念融入到中国传统之中”[1],《人间词话》被词学界公认为“为中国词学打开新的一页”[2]。但是,《人间词话》在思维方式上还是以抽象的主观感悟为主,对究竟何为“境界”表述得并不清晰。如杨义所指出的:“《人间词话》对‘境界’这个中心词的内涵……过多地依赖吉光片羽的感悟,缺乏缜密严整的思辨,因而未能从根本上超越传统诗话词话的体例,形成现代学术的精严结构和深邃层次”[3]107,所以只能遗憾地称它为“未完成的伟大”,或者“伟大的未完成”[3]107,留待后人去完善。
顾随被吴宓称为王国维之后的“后起之秀”词人,他是最早在大学课堂讲解《人间词话》与《人间词》的学者之一,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评点《人间词话》,对其进行疏义、解说。顾随自幼即有着扎实的古典文学修养,曾经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北大校长认为他文学水平已经很高,遂建议他进入英语系学习。顾随对西方文学有着相当深厚的造诣,在讲解诗词时善于进行中西对比,可惜当时西方文学理论还没有迎来繁盛阶段,不如后来六七十年代丰富,客观条件限制了他对词学进行中西理论相结合的系统建构。顾随曾借用禅宗的“因缘”思想来解释“境界”,很有独到见解,但这种方法颇为抽象,需要具有较强的领悟能力才能理解。顾随深谙中国词学理论建设的出路在于与西方文论相结合,遂将希望寄托在其学生叶嘉莹身上。他在1946年给叶嘉莹的信中曾说:
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然而“欲达到此目的”,则除取径于蟹行文字外,无他途也。[4]
顾随的“法”主要是指他讲解诗词、治学乃至做人的方法、准则。他讲解诗词注重感发,以自身真诚的生命体悟为中心进行创作、评赏,同时参以章法、句法、字法,以及文字的“音”“形”“义”等各种不同的作用,以此为衡量体系,颇有心得,这些对叶嘉莹影响很大。顾随向来是一位追求创新的学者,他希望叶嘉莹能够有所开拓,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是只继承老师做“孔门之曾参”,并指明“取径于蟹行文字”的道路,既给予了她精神上的鼓励,又指出了努力的方向。
叶嘉莹早年有一些英文基础,但因中学时生活在沦陷的北平,没有机会好好学习英文。南下之后,生活十分艰辛,无力再进行学术上的探索,顾随老师的殷切期冀成为隐藏在她内心深处一个未完成的使命。直至1966年叶嘉莹到密歇根州立大学任教,才开始重学英文。凭着超强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她在赴美任教的英文选拔考试中取得了98分的优秀成绩。她先到密歇根州立大学任客座教授一年,再到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一年。后因未能再申请到美国的签证,1969年转至加拿大的UBC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她被生活所迫,曾经白天上课,晚上艰难地查着字典读英文书籍备课。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叶嘉莹抽空旁听了UBC大学的英文诗课程、英文文学理论课程,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理论著作。
叶嘉莹学习西方文学理论首先是因海外教学的需求,也有完成内心使命的因素存在。她在海外给学生讲中国诗词时,常常被学生问为什么,她尝试对中国诗词进行种种关于“为什么”的解答。她曾在《红蕖留梦》中说:“这些尝试不仅为我在中国词学理论的研究中找到了理论的依据,而且在课堂教学上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多年来在海外教学,使我感到中国传统的妙悟心通式的评说诗词的方法,很难使西方的学生接受和理解。而运用这些西方文学理论来解释,能够帮助那些西方文化背景的洋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美感特质。”[5]她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观照下反思中国词学,每每发现二者的相通暗合之处,由此借用西方文学理论来阐释,使西方的学生能够在思维上理解和欣赏中国诗词。
二、对西方文学理论的翻译、介绍和辨析
叶嘉莹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运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解释中国词学,当时很多新出现的西方文学理论著作,并没有中文译本。叶嘉莹不仅是把西方最新的文学理论引入到中国词学的探索者,也是西方文学理论的翻译者和介绍者。
(一)对《文学与传记》的评译
1966年,叶嘉莹开始与哈佛大学海陶玮教授合作。海陶玮认为需要把一些西方研究方法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才能使西方读者心服口服地接受中国文学。叶嘉莹在他的建议下读了勒内·韦勒克(Rene Wellek)与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该书 20世纪 40年代在美国出版,直到1984年才正式有了刘象愚、刘培明翻译的中译本。在80年代之前,只有朱光潜、钱锺书等少数学人对《文学理论》英文原著有过一些关注。叶嘉莹不仅关注此书,还翻译了其中的一章《文学与传记》(Literature and Biography),1968年在台湾大学学生刊物《新潮》发表。此篇翻译不仅是单纯的翻译,同时夹有叶嘉莹的述评,夹译夹评,颇为独特。从中可以看到叶嘉莹接受西方文学理论时的思辨过程,她始终站在中西互鉴的角度来接受西方文论。她在每一小段翻译之后,对其主旨有所总结;在翻译完一大部分之后,还进一步归纳其观点,在中西互鉴中辨析其观点的合理或不合理之处,表现出独特的见解。比如对于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韦勒克认为时代较早的作者其作品与其生平之关系较少,他举了莎士比亚为例证。叶嘉莹认为这一点在中国文学中不适用,因为莎氏约生活于1564年至1616年,中国最早的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则大约生活于公元前340年至公元前278年之间,屈原要比莎士比亚早了18个世纪,可是屈原《离骚》中所表现的个人色彩却极为浓厚。韦氏只对西方文学有所关注,对中国文学没有了解,得出来的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由此,叶嘉莹认为韦氏的这一观点并不周密,她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讨论,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作品与作者生平之间的关系,主要并不在于时代之先后,而在于其作品之体式的不同及作者性格之不同。”[6]16相较于韦氏文学视野的局限性而形成的片面化观点,叶嘉莹的观点无疑是更为合理的。经过她对《文学与传记》周密思辨的阐发,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变得非常清晰,如她所说:“因为中国文学传统一向过于强调作者主观的‘言志’的作用,经常喜欢以作者之生平及人格来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准,这对于文学之艺术的成就而言,乃是并不正确的一种尺寸,韦氏的文章恰巧可以唤起我们对这一方面的省察和觉悟。”[6]16这为人们恰当运用韦氏的观点和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观点提供了理性的参考。
真正平等的亲子关系是父母既能满足幼儿的合理需求,也能让宝宝了解父母的愿望,是充分表达对幼儿的爱也要求幼儿对父母付出应有的关心和体贴,从而使幼儿真正意识到自己和成人一样,是一个平等的独立的“人”。家长不能因为宝宝小、需要成人照顾而把他看作是成人的附属品,要受成人的支配。宝宝也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个体,应该允许他有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空间,要接受宝宝对成人的合理建议等。
20世纪70年代,身居海外的叶嘉莹对西方新出现的各种文学理论多有留意,她认为:“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出现,其所提示的新的观念,都可以对旧有的各种学术研究投射出一种新的观照,使之可以获致一种新的发现,并作出一种新的探讨。”[7]69而且,她恰好遇上西方文学理论繁盛发展的时代,有机会直接接触到很多新理论,如她所说:“很多新的理论,而且是非常好的、精华的、扼要的理论都是那个时候出现的……我赶上了那个时代,也看了很多西方的理论的书,同时因为我要用英文教书,‘境界’跟‘兴趣’说不明白的,我就尝试用了西方的理论来解说。”[8]188她从新的文学理论中获得灵感,不断反思和完善对中国词学的阐释,如《对常州词派张惠言与周济二家词学的现代反思》《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等文,都是叶嘉莹在西方新文学理论的启发下对相关问题的再度思考和认识。
(二)对西方文学理论的介绍
自20世纪70年代末,叶嘉莹即开始利用暑假时间回国教书。从她80年代的《唐宋词十七讲》《迦陵随笔》等著述中可以看到她对西方文学理论多有介绍。《迦陵随笔》是叶嘉莹1986年至1987年为《光明日报》撰写的学术随笔,她怀着“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中西本自同”的主旨,以较为系统的西方文学理论来说明中西诗学的相通暗合之处。对于所用到的西方文学理论,她往往先简单地追溯其源,然后将重点放在近年来的发展上,再介绍对中国词学有启发的相关论著与观点,除发挥阐释诗词的作用之外,还有着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学理论思潮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祝晓风就曾经说:“谈《人间词话》,却引用佛语,还有现象学、接受美学的理论。真的是让人眼界大开。我就是读‘迦陵随笔’才知道什么现象学、符号学这些新词的。”[9]叶嘉莹在《迦陵随笔》中对西方文学理论的介绍和运用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她较为详细地解释了西方的诠释学,还梳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诠释学的新进展和理论观点,特别介绍了李查·庞马(Richard Palmer)《诠释学》(Hermeneutics)中的“原义”,赫芝(E.D.Hirsch)《诠释的正确性》(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中的“衍义”,以及赫芝20世纪70年代的新著《诠释的目的》(The Aims of Interpretation)中“创造者才是意义的创造者”等观点[7]4,以此说明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传统“诗无达诂”的暗合之处。
其二,因诠释学受到了现象学的影响,她又简要地介绍了现象学,重点介绍了美国詹姆士·艾迪(James Edie)《什么是现象学》中“意识向客体投射的意向性活动之说”[7]7,并与中国传统诗论中的“心”与“物”交相感应的关系相对比,以说明中西文论相通之处。
其三,她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的接受美学,重点谈及的有捷克结构主义评论家莫卡洛夫斯基(Jan Mukarovsky)20世纪 70年代的《结构、符号与功能》(Structure,Sign and Function)中“艺术成品”与“美学客体”之说,“未经读者的阅读和想象而加以重新创造,那么这部作品就只不过是一种艺术成品而已,惟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想象之重新创造者,这部作品方能提升成为一种美学客体”[7]15,以此来说明王国维、张惠言等对词的两种不同的创造性解读。她还谈及伊塞尔的《阅读过程:一个现象学的探讨》(The Reading Process: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中作者与读者的“两极”说,以及弗兰哥·墨尔加利(Franco Meregalli)的《论文学接受》(La Reception Literaire)中对读者的三种分类,由此说明王国维的“三种境界”说是带有创造性之背离原意的一种解读法。
其四,她创新性地运用了西方的符号学,尤其是运用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符号具”“符号义”“语序轴”“联想轴”之说,同时参以俄国符号学家洛特曼(Lotman)的“信息交流论”,说明无论是语序轴或联想轴所可能传达的信息,还是知性符号或感性符号都可视为诗篇的一个环节,以此分析张惠言认为“照花前后镜”有“离骚初服”之意依据的是联想轴上所提供之信息;又引用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语言符码”观点,说明张惠言读温庭筠词所依据的是词中具有文化意义的语码。
其五,她简略介绍并运用了新批评学派的理论观点,一方面不赞成艾略特(T.S.Eliot)、卫姆塞特(W.K.Wimsatt Jr.)的“泯除作者个性”,另一方面又对他们重视文字的形象、结构及肌理等质素的细读方式颇为认同,在解说诗词时经常加以运用。
以上西方文学理论虽然同时出现在叶嘉莹的文章中,但它们并非西方同一时代的产物。对这些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情况,笔者查阅了陈厚诚、王宁主编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其中新批评、现象学等引入较早(20世纪20年代),但较少有人将其系统地运用到词学中;至于诠释学①关于诠释学,笔者查阅了李清良、张洪志所著的《中国诠释学研究40年》(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19年第4期,第68~82页),文中指出“我国首次集中刊发西方诠释学译文始于1986年第3期《哲学译丛》”,之后才逐渐走向译介、研究和反思。、接受美学②关于接受美学,笔者查阅了文浩的博士论文《接受美学在中国文艺学中的“旅行”:整体行程与两大问题》(湖南师范大学,2011年),文中指出接受美学在西方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兴盛于70年代—80年代,80年代引入中国。、符号学③关于符号学,笔者查阅了黄文虎《20世纪80年代以来符号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载于《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57~64页),文中指出虽然早在1926年赵元任曾关注过西方符号学,但在“此后近40年间,符号学在中国并未引发实质性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其重要意义才得到中国学界的普遍认可”,进入起步阶段。等,则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引入。叶嘉莹很早就接触到了西方文学理论,掌握并运用得十分熟练,无论是讲课还是著述都能娓娓道来。从其接受西方文学理论时间之早、了解西方文学理论程度之深、运用西方文学理论技巧之熟等各方面来看,叶嘉莹不仅是中国词学的大力开拓者,也是较早将西方新的文学理论进行传播运用的学者。
(三)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持续关注和运用
可贵的是,叶嘉莹一直站在世界文学的前沿,与时俱进地运用西方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照中国词学,不断受到启发而产生灵感,同时也介绍给读者和学生。如她1990年写作的长篇论文《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就是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启发下产生的硕果。该文长达4万字,对西方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梳理,从1949年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第二性》(译名:The Second Sex,原名:Le deuxièmesexe),一直到 80 年代的重要理论著作及思想,都作了概括性的介绍。其中很多理论著作是叶嘉莹独具慧眼发现并运用的,比如玛丽·安·佛格森(Mary Anne Ferguson)的《文学中之女性形象》(Images of Women in Literature),该书出版于 1980年,书中对女性进行详细分类的思路对叶嘉莹很有启发性。欧丽娟还将此理论从叶嘉莹的文中引用到她自己的《唐诗公开课》中,也取得了很好的分析效果。再比如美国学者劳伦斯·利普金(Lawrence Lipking)的《弃妇与诗歌传统》(Abandoned Women and Poetic Tradition),该书出版于1988年(至今没有中译本),1990年叶嘉莹就引用了其理论。可见,叶嘉莹在西方文学理论方面下的功夫很深,在中西互鉴中创造性地运用西方文论,对中国词学不断地进行新的观照,修订完善自己早年的观点,解决了词学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笔者有幸得见叶嘉莹先生曾经读过的一本西方文学理论著作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此书印刷于1994年,当时她已70岁,还一直保持着对西方文学理论的研读和关注。这本英文书近700页,留有叶嘉莹先生阅读、思考的痕迹,随处可见她用彩笔标注的重点、夹存的备忘纸条。“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对西方文学理论的研读、理解、翻译并运用,是叶嘉莹对中国词学开拓创新的一个源头。
三、对词之美感特质根源的探索
(一)对词之美感特质进行探索的原因
叶嘉莹词学的核心之一是对词之美感特质的探索。她在《西方文论与中国词学》①《西方文论与中国词学》收录在《我的老师顾随先生》一书中,作为她在学业方面取得的成绩向老师“汇报”,其实质是叶嘉莹晚年对自己在词学探索方面的总结。中曾说:“我一生之中真正努力完成的,是要把词的美感特质,它的原由、作用、理论解说出来,这真正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的对于词的特质的一个根本的诠释和说明。我以为这在词学领域是很重要的开拓,解决了词学的一大问题。”[8]199虽然她对词学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但她只看重这一点。这一问题为何值得她探索多年,因为词最早产生于歌筵酒席之间,其中所写的伤春怨别男女之情,不合于传统诗文中言志与载道的标准,导致文人士大夫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知如何衡量艳歌小词,以及是否应该写作此类小词,所以,中国词学是在困惑与争议中发展出来的。
张惠言运用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比兴寄托”来说词,影响既广且久。王国维反对比兴寄托说,运用感发联想的方式来说词,并尝试将西方思想融入中国词学以建立理论体系。叶嘉莹在髫龄时就曾读过《人间词话》,产生一种直觉的感动,但王国维所说的“境界”究竟是什么,成为萦绕在她心中挥之不去的困惑。这个困惑不仅是她个人的,也是中国词学发展千年以来的困惑——即词之美感特质根源是什么。张惠言、王国维、顾随等都是尝试回答这一问题的学人。叶嘉莹在多年的研读中,总是感觉到:“小词里面有一个可以引起读者非常丰富的,而没有一定专指的种种的联想的作用。那么这个东西应该叫什么,而且这种作用是从何而来的?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回答、没有解决,从来没有人真正解说明白的一个问题。”[8]188所以,她一直想要解答这个难题。
(二)发现小词具有丰富潜能
如何借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解决词学中张惠言与王国维的争议问题,循着《西方文论与中国词学》,我们可追寻叶嘉莹的思路与方法。她用一种思辨的思维,发现虽然诗词并称,但词的传统与诗歌的传统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诗歌的“言志”传统,属于显意识的言语,而词却是一种新兴的音乐文学,不能用“言志”传统产生的诗学理论来衡量。《花间集》本是给歌儿酒女演唱的歌词集,这些表面上写美女和爱情的小词却引发了读者丰富的联想,而且还产生了不休的争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段公案就是关于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这首词所写是一个女子梳妆打扮,但张惠言却以比兴寄托论词,认为是作者“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王国维反对张惠言,认为:“兴到之作,有何命意?”批评张惠言“深文罗织”。王国维提出新的评词标准,“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可是他没说明白境界是什么,也令后人产生种种歧义。叶嘉莹认为“是比兴寄托,太狭窄了;是境界,太广泛了,张惠言、王国维他们都没有把词的真正的好处和作用说出来”[8]188,所以,她要努力把词令人产生争议的根源解释清楚,解决词学中引发争议的根本问题。
叶嘉莹受到波伏娃《第二性》中“女性是第二性,是男性眼中的‘他者’,是‘被男性所观看的’对象”,以及佛格森《文学中之女性形象》将女性形象分为五种类型等理论与方法的启示,将《花间集》中的女性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和分类:第一种是被男性作为观赏对象的女性,如欧阳炯的《南乡子》(二八花钿);第二种是爱的对象,如欧阳炯的《浣溪沙》(相见休言有泪珠);第三种是独处之女性的相思期待,如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前两种是用男性的口吻来写的,后一种是以女性口吻所写的思妇、怨妇。第三种小词中的思妇和怨妇为何引起张惠言和王国维丰富的联想和争议,叶嘉莹又借用“双性人格”来说明,在男性作者的显意识中小词所写的是弃妇、怨妇,可是在他们的潜意识之中却流露了自己失意的感情。“所以小词里边所写的弃妇就很可能有男子的托喻,所以张惠言说温庭筠的‘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是‘感士不遇也’”[8]192。而王国维却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批评张惠言“深文罗织”。
叶嘉莹发现小词中产生这么多的联想,“是因为小词里边有一种potential effect”,她把它翻译成“潜能”。她认为:“词的特色不要说那是比兴寄托,这是牵强附会;也不能说那是境界,这太浮泛了,都是不可靠的。我说好的词包含了丰富的潜能(potential effect)……”[8]196,优秀的小词本身具有丰富的潜能,这是小词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并产生争议的根源之所在,对《花间集》词的争议是因为评论者不懂得这一道理,只运用自己惯用的一种思维和方法进行批评,只看到了一方面,所以产生了争议。通过叶嘉莹的阐释,这些争议自然就有了一个了断,无论是张惠言还是王国维,他们的词说在西方文学理论的阐释中都有着一定的思维模式和道理。
(三)建立评赏词的依据与方法
如何诠释具有丰富潜能的词,叶嘉莹运用诠释学中“诠释的循环”理论来说明,每一种诠释都来自诠释者自身的主体意识,不同的读者能够从词中读出不同的意思。是否所有批评者的意见都准确,评赏词究竟有没有对错之分,有没有法度可依,这些也是叶嘉莹解决的重要的词学问题。她运用了西方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解析张惠言比兴寄托、王国维感发联想的说词方式的思维轨迹和理论依据,为两种说词方式找到与西方文论的暗合之处,并为如何正确运用这两种说词方式建立了有“法”可依的理论依据。
她将词的发展过程分为歌辞之词、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大致而言,王国维的说词方式适用于第一类以自然感发取胜的歌辞之词的评说;张惠言的说词方式适用于第三类有心以思索安排取胜的赋化之词的评说;第二类诗化之词,已经有了与诗相近的倾向,其所叙写的情志也属于作者显意识中的概念,不容许读者以一己之联想对其作任意的比附和发挥,但它们也具有词的曲折含蕴之美质。所以,在评赏词时需要具体分析与精确辨析,再选用适当的评赏方法,不能无所区分地一概而论,也不能采取牵强附会的态度。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解说温庭筠的《菩萨蛮》即是犯了此种错误。
(四)提倡创造性的背离
中西方传统文论都重视作者和文本,叶嘉莹受到接受美学的启发,转向同时重视读者的作用:“当这个作品被读者读到的时候它才成为一个美学客体,才有了美学作用,真正把这个作品的价值完成的是读者”[8]195。她赞同对词进行创造性的阅读,发挥读者对作品诠释的作用,读者在文学的阅读接受过程中可以有“创造性的背离”,即违背诗词的原意,把自己创造的情思放进去,这样能够更好地传达出诗词中生生不已的生命感发。由此,她认为王国维从小词中读出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重境界,是最为成功的一种说词方式,充分地发挥了小词中的丰富潜能。
叶嘉莹运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解释中国词学,立足于她的感发性思维和独立的思辨精神。她在《迦陵论诗丛稿·后叙》中说:“(评赏诗词)一向原是以自己真诚之感受为主的,无论中西新旧的理论,我都仅只是择其所需而取之,然后再将之加以我个人之融会结合的运用。”[10]叶嘉莹在《论纳兰性德词》中也曾说:“我文非古亦非今,言不求工但写心。恰似涌泉无择地,东坡妙语一沉吟。”[11]叶嘉莹还曾表示非常欣赏解释符号学家朱丽亚·克利斯特娃,认为她是一位非常有思想有个性的杰出新女性,并借用她的话“我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无论那是什么理论”来说明自己的主张[12]。叶嘉莹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态度和方法,对于后学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四、中西文学理论互鉴的意义
叶嘉莹的词学颇为丰富,在探索词之美感特质的过程中她还提出“兴发感动”“弱德之美”等,都是具有创新性的值得深入探究的理论。缪钺先生称赞她:“不但精熟中国传统的诗论,而且能采撷西方哲思、文评之要旨,故新意焕发,不主故常,能发扬静安未竟之绪。”[13]286因她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精熟的掌握,又恰好赶上西方文学理论的繁荣时期,见到了王国维、顾随没有见到的西方文学理论,所以能够在中西文学理论的互鉴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完成王国维、顾随几代学人的心愿。当然,也在于她敏锐而富有探索精神的天性契合了词的微妙性,如她所说:“词是很微妙的,从作者到作品,到接受,到诠释,甚至于你接受和诠释的时候可以不是作者的原意,这是小词的微妙作用。”[8]199叶嘉莹向来对晦涩难解的诗最感兴趣,词的深微幽隐使她势必要对其一探究竟才肯罢休,正因如此,她对中国词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叶嘉莹不仅运用西方文论解释了词之美学特质的根源,还对词之评赏进行了理论建构,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推动词学理论的发展,还在于为中国词学理论在世界文化中找到坐标,让世界理解中国词学的同时,也让国人明白自身文化的优势之所在。她的努力在海内外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加拿大学者施吉瑞曾说:“许多中国读者认为她只是一个中国学者。其实,叶老师在加拿大工作多年,培养了许多中国古典诗歌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并成为加拿大中国文学领域唯一的加拿大皇家学会勋章获得者。叶老师如同一个‘现代加拿大骑士’,她的贡献在于一直努力地、执着地把丰富的中国文学遗产传授到加拿大和西方其他国家。”[13]128①加拿大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Canada)是加拿大的最高科研学术机构,院士为加拿大学术界的最高荣誉,其提名和评选都要经过严格的评估和审查程序,只有学科领域最为优秀的领军人物才能入选。正是因为叶嘉莹先生在学术中取得的卓越成就,在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词学互鉴中的大力开拓创新,使她1990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她像一座桥梁沟通了中西诗学,在中西文学理论的互鉴共赏中开拓出新境界。
叶嘉莹向来以谦逊为美德,对自己在词学方面的建树较少谈起,晚年出于向老师顾随“汇报”的心理,才对自己的成绩进行简单的回顾、总结。她曾在《我与顾随先生七十五年的情谊》中说:“我最近就在想我的学生们,他们所感兴趣的就是看一看我的《唐宋词十七讲》,看一看我的词说、词论,觉得挺有意思。可是很多时候,你做学问不是只能够肤浅地欣赏一下就算了,你真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把它表里澄澈,能够发掘,能够表述,能够说明出来。”[6]312所以,学习叶嘉莹不能仅停留在表层,还要深入探索其在诗词学术中的开拓,学习其创新精神、思维与方法,才不辜负她“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的殷切期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