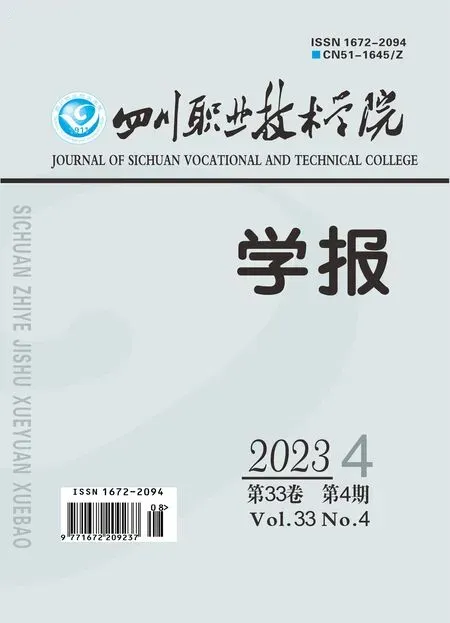论《虬髯客传》中的“空间”
胡奥琳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0)
《虬髯客传》全文现载于《太平广记》卷一九三“豪侠”类,写太原三侠:虬髯客、李靖、红拂女。与唐人其它传奇相比,《虬髯客传》的“空间创制”格外成功,但却一直未能引起评论家的重视。本文试从空间角度切入,剖析传奇如何通过空间转换来完成情节叙事、挖掘空间创制背后的深刻隐喻及其所映射出的地域文化并考察空间与人物塑造的深层关系。需要注意的是,通常对文学作品进行空间维度的研究时,会将空间大致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小说文本空间、作者创作空间与读者接受空间。由于《虬髯客传》的作者尚未在学界形成定论①,具体创作时间也难以确证,又囿于篇幅,所以本文只聚焦于传奇所呈现的文本空间。
一、空间与叙事
众所周知,任何叙事作品都必然是在某段时间和某个(或几个)空间内展开的,叙事是具体时空中的现象。自莱辛在《拉奥孔》中将“诗”与“画”分别划归为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以来,从时间角度研究小说叙事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具备极其深厚的学术基础和传统,但若打破“故事就是对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小说面面观》)这一传统观点,就会发现空间在叙事中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叙事作品内既有时间顺序更有空间流动。从空间叙事的角度来考察《虬髯客传》,可以发现其中共出现了七个空间,整个故事情节正是在这七个空间的流动中展开。现将空间流动线索概括如下:
长安杨素府—长安旅馆—灵石旅舍—汾阳桥—太原刘文静宅—长安马行东酒楼—汾阳桥—太原刘文静宅—长安虬髯客宅
故事开篇,李靖前往长安向司空杨素献策。本欲投其麾下的李靖不想得杨素府妓红拂女的青睐而与之结好,两人为避事端,离开长安前往太原,又在灵石旅舍中结识了报仇而归且善相面的虬髯客。虬髯客听闻李靖言太原有“真人”,便欲与其同见。三人于太原汾阳桥相会后,在李靖好友刘文静宅中见到了李世民。虬髯客见李世民真乃天子,“见之心死”却又不死心,还要找道兄来确证,便又与李靖夫妇约在长安马行东酒楼会见道兄。待李靖二人到后,暂留下红拂,虬髯客与道兄、李靖三人复归刘文静宅中。道士一见李世民便言虬髯客“此局全输”,让其另寻霸业。李靖帮助虬髯客见到李世民后便回到长安接回红拂,期间二人又应虬髯客之邀,拜访了其在长安的住所。哪知得见真天子的虬髯客知道自己功业无望后便将全部家财赠与李靖夫妇来辅佐真主李世民,自己则带着妻子前往东南异邦。故事结尾,李世民一匡天下,虬髯客入扶余国另成国君。
通过上述故事梗概,可以发现《虬髯客传》中的空间与情节有着极强的因果关联,可概言之为“正是有了某个情节才使人物来到某个空间,而在此空间的人物行为又导致了人物前往下一空间,从而发生下一情节。”这种借由空间转换来推动情节发展的叙事技巧看似简单但却需要作者具备极强的逻辑性和空间调度能力。一般而言,叙事空间的转换,通常有两种模式:直接转换和间接转换。②《虬髯客传》中的空间转换是依靠人物行动而非叙事焦点的直接转移,是为间接转换模式,其所依靠的核心中介无疑是李靖。全文基本都是根据李靖的行动路线而设定不同的空间来承担文本叙事的需要,此间多种空间成并列关系,互不干扰。这又可以概括为“人物在场—人物离开—遇见新的人物—前往新的地点”如此循环的经典行动模式。
有时候,在由人物运动串联不同的叙事空间时,往往会加入此叙事场景之外的人物或事物作为空间转换与衔接的推动因素,促进这个叙事场景向下一个叙事场景过渡,如本文中的虬髯客。一开始,李靖与红拂二人对投奔太原是信心不足的,正是虬髯客的出现,要求他共同前往:“李郎能致吾一见乎?”[1]1447才坚定了李靖夫妇前往太原的决心:“公与张氏且惊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无畏。’促鞭而行。”[1]1447同样,在虬髯客与道兄面见李世民后,也是因虬髯客的邀约,李靖夫妇才得以进入虬宅的空间并继承了虬髯客的资产。这一功能,在后世小说中就逐渐演化出了“报信人”这种推动空间转换与衔接的典型人物。
空间转换模式有直接和间接之分,其转换速度也有快慢之别。《虬髯客传》中的空间转换十分干脆利落,上文提到某一空间,下文紧接着就转到这个空间内。这种摈弃枝节,直接切入,快速转换的技法,后世总结为“顶真法”。但此法的缺点是过于生硬,如果两个空间的情节关联性不强,硬用“顶针法”就会显得十分突兀。在《虬髯客传》中,作者还采用了另一种空间转换技法来补其不足。如前所述,虬髯客最后将自己数十年来积累的家当资产都赠与了李靖夫妇来帮助李世民。那么问题出现了,虬髯客的住宅在长安,面见李世民之地是在太原,如果虬髯客在太原见过李世民后就已认命,那么李靖二人与虬髯客的缘分也就止步于此了,如何让李靖二人与其同回长安来接受其家产呢?作者虽增补了虬髯客要回长安邀请道兄同见李世民的情节,但相见地点仍在太原,如何才能让李靖再返回长安呢?此时若强行让李靖夫妇同虬髯客回到长安,读者必会疑惑,明明李靖二人是要前往太原避祸的为何又要去长安?正是出于太原与长安两处空间衔接的考虑,所以在长安马行东酒楼,虬髯客才要让红拂留下,由此成为此后李靖不得不返回长安的理由。如此,太原和长安这两处空间才能顺利连接,情节才能合理推进下去。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去一来间,情节有了起伏摇曳,艺术性和趣味性大大增强。虬髯客让红拂留下的情节,在《虬髯客传》中虽只有一句交代:“楼下柜中有钱十万,择一深隐处驻一妹。”[1]1447但这种为了使几处空间之间合理衔接而巧妙增设情节的方法却成为后世创作小说的经典手法之一,金圣叹总结为“鸾胶续弦法”。以往论者多从情节结构的角度来研究此法,却忽略了该法背后明显的空间转换与衔接问题。
二、空间隐喻性
比起巧妙运用空间转换推动情节的跌宕起伏,《虬髯客传》作者对空间选择的匠心独具似乎更能佐证鲁迅先生“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论断。历来论者多对《虬髯客传》的故事隐喻性进行考证论说,而对空间的隐喻性有所忽视。事实上,在这七个空间中,汾阳桥与灵石旅舍的选择十分具有深意。从上面的空间流动线索中,可以发现汾阳桥这个空间出现了两次。如果说第一次提及汾阳桥,是虬髯客为了能在太原与李靖夫妇相会而随口一提的地点,那在众人于刘文静宅中见到李世民之后,二进太原时,虬髯客为何还要与李靖相约汾阳桥呢?虬髯客二进太原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道兄确证李世民是否为真龙天子,他们一行人二见李世民的地点也还是在刘文静宅中,而非汾阳桥,所以虬髯客完全可以与李靖约在刘文静宅中,不必非得“复会我于汾阳桥”[1]1447。汾阳桥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能在并不承担主要情节的前提下被作者反复提及呢?查《元和郡县志》,唐时,太原府下共辖十三个县,在这十三个县中,并无汾阳桥的记载,但在晋阳县下有“汾桥”一条,记:“汾桥,架汾水,在县东一里,即豫让欲刺赵襄子,伏于桥下,襄子解衣之处。桥长七十五步,广六丈四尺。”[2]366那这座汾桥是否就是汾阳桥呢?《元和郡县志》中又记载“太原有三城,府及晋阳县在西城,太原县在东城,汾水贯中城南流。”[2]362由此可知,当时的行政中心太原府和晋阳县是在一处,那么作为州将之子的李世民和晋阳县令刘文静,其二人的住宅理应在西城,而汾桥在晋阳县东,正是进入西城的必经之所。此外,《元和郡县志》成书于元和八年(813),属于唐中期,裴铏则出生于晚唐。在这几十年间,汾水之上不可能只有一座桥梁,那么属于晋阳县的汾桥,确实有可能出于某种标明特征的目的,在民间口头流传中变为汾阳桥。如果《元和郡县志》中所记载的“汾桥”正是《虬髯客传》中的“汾阳桥”,那么作者两次提及汾阳桥就确实“别有用心”。
《元和郡县志》中的“汾桥”并非一座普通桥梁,它还是一场历史事件的见证者。“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今见于《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作为战国四大刺客之一的晋人豫让,在其主公智伯为赵襄子所灭后,为了替智伯报仇曾假扮刑人,入赵襄子宫中涂厕以伺机行刺。后来事情败露,赵襄子感其忠心义气放了他。不想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完成了全身易容和变声后,埋伏在汾桥下等待赵襄子。哪知赵襄子的马在过桥时感知到了危险而有所惊动,一众护卫又抓获了豫让。豫让深知赵襄子此次必定不会再放过自己,便请求刺穿赵襄子的外衣,以全报仇之意。赵襄子命人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豫让在智伯之前,还曾为范氏与中行氏效力,但他二人并不看重豫让,只有智伯真正赏识他,所以豫让终其一生也要为智伯报仇。豫让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典范,其自杀之所“汾桥”背后所承载的,是豪侠义士间的惺惺相惜,更是臣子对主公的忠心不二。这一内涵又与《虬髯客传》的主旨两相契合。小说结尾写道:“乃知真人之兴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1]1448正是因为裴铏所生活的晚唐,藩镇已成推翻朝廷之势,唐王朝的政治形势空前紧张,所以作者才要警诫各思乱之人臣,并特意安排了汾阳桥这一空间来暗示忠君之理想。巧妙利用空间隐喻性来进行主题表达,是《虬髯客传》的又一精妙构思处。
此外,在长安与太原之间安插灵石旅舍同样也具有特殊意义。据《唐代交通图考》一书,灵石正位于长安—太原驿道上,且是由河中府进入太原府的第一站。表面上看将虬髯客与李靖夫妇的相遇点安在此处正符合客观实际,但灵石一地还有更重要的暗示性,且与李唐王朝的开创史密不可分。同样据《元和郡县志》中对灵石县的记载,在县南三十五里有贾胡堡一地,这正是唐初著名的霍邑之战的发生地。隋大业十三年(617)六月,李渊屯兵贾胡堡,与隋将宋老生的霍邑驻军相持,战事激烈,久攻不下。又逢久雨而粮尽,李渊便欲北还太原,以图后举。李世民谏止无效,于帐外号泣,痛陈利弊,力谏迎战,李渊方改变计划。《旧唐书》记:“高祖乃悟而止。八月己卯,雨霁,高祖引师趣霍邑。太宗自南原率二骑驰下峻坂,冲断其军,引兵奋击,贼众大败,各舍仗而走。”[3]16除此之外,在灵石县东南还有险隘异常的雀鼠谷。武德三年(620)初,李世民由河东北上,与刘武周的得意将领宋金刚对峙于柏壁(今绛州),后因宋金刚粮尽而逃,李世民便乘胜追击,正是在雀鼠谷与其展开激战。
后世学者曾如此评价这两场关键战争:“贾胡堡一战,一举打通了李唐西图关中的道路,是隋唐兴替的关键之战;雀鼠谷一役,终结了初唐刘武周的割据与突厥的干涉,巩固住了新生的唐王朝。”小说中的灵石旅舍,作为“风尘三侠”的相遇地是整出故事的开端,而在现实空间中,李氏父子在灵石的两次重大胜利,则成为了唐王朝的开端。作者并非生活在不受任何文化影响的“真空”,其所在地的地域文化与历史记忆会对其创作产生巨大影响。《虬髯客传》的作者裴铏作为河东裴氏家族的一员必然对河东一带的历史典故和军事地理了如指掌,所以在创作中自然就选入了那些富含现实隐喻义的空间。
并且《虬髯客传》作为中国侠义小说之祖,其本身就是河东侠文化的最佳注脚。隋末唐初,河东一带豪侠之风盛行。在小说中,虬髯客一出场便带着“亡命天涯”的游侠气质。他在与李靖夫妇并不相识的情况下,贸然闯入他人房中并以轻薄的姿态躺着看红拂梳头,其行为挑衅意味十足。此后因与李靖夫妇相谈甚欢,便又从袋子中取出仇人的人头与心肝,与二人切而共食。这种全凭意气、仗行天下的豪侠风范与当时中原大乱、群雄并起,以武勇夺天下的时局十分契合。且考唐史可知,李氏父子的霸业功成,与豪侠之助也密不可分。《旧唐书·太宗纪上》云,“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3]22。并且在唐朝的开国功臣中,诸如柴绍、唐宪、段志玄、刘弘基等,尽为当时太原一带的亡命豪侠。李氏父子延揽豪侠之士以为己助的历史事实和当时河东地域的豪风侠气,在小说中正是借由灵石这一空间得以渲染。
三、空间与人物
通常说来,叙事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通过人物行动刻画人物性格特征;第二种是借助人物的外貌描写;第三种则是“专名的暗示与粘结”③。在这三种主要方式中,“空间”被忽视了。实际上,正如我们无法想象出一个不存在于空间中的人,任何叙事作品中的人物都需要一个“生成场所”,也就是“空间”。有了这个空间,人物才能展开行动,才能表现性格。并且在不同的空间中,人的行为往往不同,这些行为差异又与人的性格直接相关。正是这种空间与人物性格及其所导致的行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使得创作者们利用“空间”来刻画人物成为可能。这便是龙迪勇在《空间叙事学》中所总结的,叙事作品塑造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形象的第四种方法——空间表征法[4]。
人物性格的空间表征法虽然是在近二十年间才为学者所重视并形成相关理论,但早在唐末的《虬髯客传》中,作者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空间”来刻画人物。在传奇中,虬髯客与李靖夫妇的相遇地点是灵石旅舍,更确切说是在李靖夫妇的私人空间内。文中写道:“张氏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公方刷马。”[1]1446女子晨起梳妆处,必不是任谁可见的公共空间。在这十分私密的空间内,任何外来者的闯入都带有极强的冒犯性。虬髯客正是在不该闯入时,不能闯入处,突然出现。“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梳头。”[1]1446贸然闯入的虬髯客,不仅未向李靖夫妇说明来由,反而顺手投下革囊,随意取过枕头,又无所顾忌地歪躺在张氏面前。这一连串动作,无一不显现出虬髯客的轻浮与狂傲,而这层性格特质又借由空间的私密性得以放大。试想下,若此时的空间是烟柳之地,那虬髯客的系列动作恰恰是合乎常理的,但正因为此处的空间是私人的,所以才具备激怒李靖的条件。这一私密空间的设置,不仅放大了虬髯客的性格,同时也刻画出了李靖和红拂的个人性格。面对虬髯客的挑衅,李靖和红拂二人的反应都十分值得深析。如果说虬髯客前面的闯入还只是激发了李靖在空间上的领地意识,那么之后其毫无顾忌地欣赏红拂梳头,则无异于对李靖直接宣战。李靖当然愤怒,但他不会“冲冠一怒为红颜”。他犹豫不决,最后选择一边刷马一边静观其变:“公怒甚,未决,犹刷马。”[1]1446)李靖与虬髯客不同,他十分谨慎小心,在不清楚来人底细的情况下,面对挑衅,他选择了忍让和等待。红拂同样选择了不激化与虬髯客的矛盾,但她与李靖又不同,她还兼有智谋,懂得以退为进。她一面沉着地安抚李靖情绪:“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公,令勿怒。”[1]1446)一面极力表现出对虬髯客的尊敬以缓和局面:“急急梳头毕,敛衽前问其姓。”[1]1446)当得知虬髯客与自己同姓时,她更是借机拜其为兄来拉近彼此距离,又不忘让李靖前来同拜以消解二人可能发生的冲突。正是在红拂的周旋下,虬髯客才坦怀相待,与他二人结交,所以虬髯客说“非一妹不能识李郎”[1]1448。红拂遇事之沉着冷静与为人之八面玲珑,在灵石旅舍的空间内得到了充分表现和对比突出。莫怪虬髯客最后盛赞红拂是“以天人之姿,蕴不世之艺”[1]1448。
在《虬髯客传》中除了有同一空间内不同人物的行为对比,还有同一人物在不同空间内的行为对比。灵石旅舍中侠肝义胆、一身江湖气的虬髯客在太原刘文静宅中见到神气异乎常人的李世民后,俨然像只泄气皮球,只能“默居末坐”,又“饮数杯,招靖曰:‘真天子也!’”[1]1447,而当回到自家宅邸后又是纱帽裼裘,“亦有龙虎之状”。俗语言“识时务者为俊杰”,虬髯客在李世民面前一反常态,一方面从侧面表现出李世民的天人之姿,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空间的社会性对人物行为的限制,在他人宅邸理当有所收敛。在这放敛之间,虬髯客的性格更为丰满。除了直接在空间中展开人物行为,刻画人物性格,《虬髯客传》的作者还巧妙借由空间的暗示性来刻画人物。如前在谈到灵石空间的隐喻意时所言,奠定唐帝国根基的两场战争——贾胡堡和雀鼠谷——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李世民个人的胜利。《虬髯客传》中,对李世民的直接描写只有两处,一处言其 “不衫不履,褐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1]1447,另一处言“俄而文皇到来,精采惊人,长揖而坐,神气清朗,满坐风生,顾盼炜如也”[1]1447。这两处描写都集中在李世民的天子面相与气度,而对李世民的天子才干与勇谋,作者则借用灵石这一空间的暗示性作为对李世民的“不写之写”。人的生存状貌往往要借助空间来呈现,从空间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人物行为,也许能给小说人物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启示和发现。
四、结语
《虬髯客传》中的空间创制,无论是在叙事层面上将空间转换与情节因果糅合,还是在主题表达上借由空间来隐喻,抑或是在空间中塑造人物都体现了此为作者精心结撰的结果。通过对传奇空间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把握《虬髯客传》的深刻内涵,并对揭示唐人究竟是如何“始有意为小说”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注释:
①《虬髯客传》的作者和创作年代,学界迄今未有定论。关于其作者,主要有张说、裴铏和杜光庭三说。由于本文主要是从“空间维度”对《虬髯客传》进行研究,所以并不涉及作者考证。又因为最早由鲁迅、汪辟疆提出的杜光庭说已被众多研究推翻,目前学界争论的焦点主要在张说和裴铏之间,所以本文暂取裴铏为《虬髯客传》的作者。且《虬髯客传》中所折射出的河东道地域文化,也可为裴铏说提供一点佐证。
②直接转换是指两个叙事空间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不需要人物运动等等中介力量作为牵引线索,而是依靠作者叙事焦点的转移而发生直接跳转;间接转换是指两个叙事空间之间通过人物或事物等较为明显的中介力量作为牵引线索而发生转变。两个叙事空间中的叙事场景往往是按中介人物或事物运动的时间次序先后发生的。详见韩晓.中国古代小说空间论[D].复旦大学,2006.
③由傅修延在《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一书中提出。专名即指在作品中,作者给特定人物所取的专用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