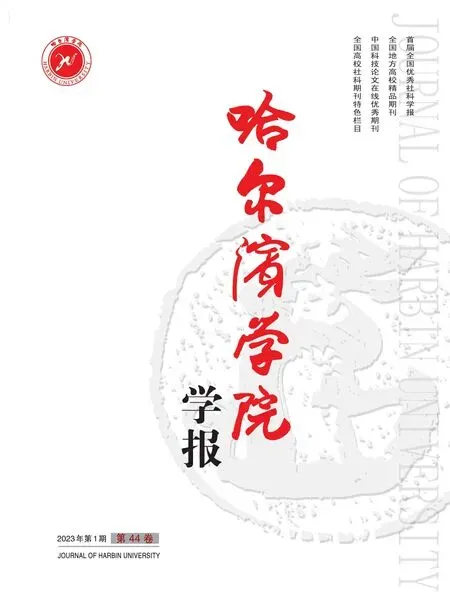真实的白日梦
——伊恩·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景观社会
杜小梅
(1.淮南联合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2.曲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一、引言
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是当代英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作品不仅继承了英国文学的传统,而且密切关注当今英国社会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影响。麦克尤恩风格各异的作品正如人性试验场,当小说中的主人公遭遇或大或小的考验时,其心理判断和行为方式无一不是现代社会人们的缩影。国内研究者在对麦克尤恩的作品进行解读时,主要集中于心理分析、女性主义、伦理批评和叙事分析等。研究文本更多聚焦于《赎罪》《水泥花园》《黑犬》《时间中的孩子》等,对出版于2005年的作品《星期六》(Saturday)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学者从微观的角度探究作为景观的建筑、商品、媒介是如何在景观社会中影响现代人们的生活的。[1]本文将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景观社会是如何形塑现代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旨在进一步丰富和扩充《星期六》的研究视角。
法国情境主义哲学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观察到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向现代化社会高速发展且大众的日常生活逐渐以视觉为先导,由此“德波创造性地把当代社会定义为‘景观社会’”。[2]德波在其著作《景观社会》(TheSocietyoftheSpectacle)中凸显了一个社会批判理论的关键词——“景观”。“从‘景观’的词源入手,其对应的英文单词是spectacle,据相关研究考证,与其相应的拉丁语有spectaculum、spectae、specere,意为与人的视觉相关的‘观察’‘看着’‘重复地看’;且古法语和古英语中都有‘spectacle’;‘景观’一词外延的延展性极强且融合了诸多辞义。”[3]景观“原意为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色、景象,也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做秀。德波藉其概括他眼中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质,具体来说即当代社会存在的主导性本质主要体现为一种被展现的图景性”。[4]
德波通过其著作《景观社会》宣告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所身处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已转变为一个视觉表象符号作为社会主体的景观社会。德波所提出的景观社会理论反映了西方现代经济生产、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符号化与景观化的新趋势,这种现象仍然延续下来,景观在《星期六》所展现出的景观社会中仍占据着掌控和主导地位。麦克尤恩在《星期六》的叙述中,以伦敦为舞台背景来形塑主人公贝罗安的主体心理,同时以伦敦来影射后工业时代景观社会的意指空间,反映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社会表征。通过描写景观支配下的社会现象和小说主人公沦为景观奴隶的困境,麦克尤恩深入剖析并批判了后现代景观社会。
二、景观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生活模式
科技作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大幅提高,现如今人们不再仅是追求满足自己衣食住行的需要,而是追求一种让人沉迷其中、无法自拔的虚幻景观,这导致了人们的生活追求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人们把自己的幻想投射在景观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中,比如观看新闻、参加艺术展览、度假等。正如德波所说:景观“不是现实世界的替补物”,他进一步解释说,“即这个世界额外的装饰。它是现实社会的非现实主义心脏。在其种种独特的形式下,如新闻或宣传,广告或消遣的直接消费,景观构成了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生活的现有模式。”[5](P4)
仰海峰更具体地说:“随着电子媒介的普遍化,影像自身构成了一个体系,社会生活本身首先表现为影像的世界,正是影像的普遍化才能建构出一个景观社会。”[6]麦克尤恩凭借“都市景观碎片的透视”,在《星期六》中使用第一人称视角和全知视角讲述了主人公贝罗安在星期六这一天中无意中看到飞机失事、开车在游行中遭遇刮擦事故、与朋友打壁球、看望母亲、全家人团聚以及遭遇暴力威胁的故事,穿插其中的还有贝罗安大量涌现的意识流。[7]所有的这些故事情节均是在电视、收音机、报纸和商品等景观大量积聚的景观社会中徐徐展开的。《星期六》中的主人公贝罗安卷入了景观的漩涡之中,作为电子时代的公民,贝罗安习惯性地借助景观媒介了解生活中的新闻,并且景观媒介自带一种权威,举个例子,仿佛只有出现在电视新闻上的事件才真正发生过,而没有经电视新闻播报的事情似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真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沦为漂浮的、虚幻的符号,而只有当事物变身为景观时,在人们的眼中才是真实的存在。在电视、收音机、报纸等各种媒介所组成的媒介景观的影响下,一切存在的价值就是——被人看到,人们的亲身经历似乎只有经过新闻媒体的报道才是客观存在的。麦克尤恩在《星期六》中描述了一架着火的客机如流星般坠向希思罗机场的事件。贝罗安在夜晚亲眼目睹了这起事故,且不停地幻想着意外发生时的景象,并因那看不见的情景而恐惧。当这一切结束后,贝罗安向儿子讲述这件事,紧接着父子俩的反应都是打开电视观看关于这起事故的报道,通过电视报道来确认这件突发性飞机起火事故的真实性。但当时电视新闻还没有一丝一毫对此事故的报道,贝罗安急切地需要新闻媒体的报道来证明他亲眼所见的事故是真实发生了的。如果没有新闻媒体的播报,这件飞机起火事故便“停留在一个不足为信的主观印象阶段”。[8](P33)在景观社会中,真实与虚假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对一件事情是否真实的评价标准不在于这个事件本身的真实性,而在于这件事是否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如果一个事件不经新闻媒体的播报,它似乎就是不真实的、从未发生过的。“真实世界沦为影像,影像却升格成看似真实的存在。”[4]
德波认为“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5](P3)这种景观的积聚在《星期六》中有着鲜明的表现,麦克尤恩在《星期六》中有意识地罗列了大量的意象,如飞机、汽车、收音机、电视、报纸、电话以及各式各样的商店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意象正是后工业化时代甚至是信息时代的典型产物,体现了景观社会中庞杂的景观堆积。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说道:“我们总是看重工具,将手段本身当成了目的,而不会高瞻远瞩,看到工具手段只因服务于长远目标,才有了价值。”[9](P39)人们在景观社会中正是如此看重景观,将追求景观本身当成人生的目的,以至于景观成为了人们的主宰,使得人们为景观服务。景观本应该是帮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的工具,可惜人们本末倒置,误将景观的价值无限放大,在致力于追求景观的过程中不过是自欺欺人、自我麻痹、自我放逐而已。
三、景观作为隐性的意识形态
景观作为隐性的意识形态占据了人们的时间和空间,牢牢将人们束缚在社会层层叠叠的景观中,让人们身处其中却无法脱身。景观作为隐性的意识形态,体现在景观对人们非劳动时间的占有,使得人们的闲暇时间变为景观时间,即“可消费的伪循环时间”。[5](P99)人们自以为在劳动时间之外,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外出游玩,殊不知,不管人们身在何处,总无法逃避作为景观的商品对人们的俘获。服务业和休闲行业也是作为景观的商品,悄无声息地占据了人们的闲暇时间。在《星期六》中,不管是商店里售卖的形形色色的商品、舒适惬意的居住环境,还是去不同的地方度假以及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等,这些作为景观的商品占据着贝罗安及其家人的闲暇时间。
作为景观的另一具体表现形式——新闻媒体,固定地占有着贝罗安的闲暇时间。“每日关注新闻动态,并且在每周日下午躺在沙发上浏览更多空穴来风的评论专栏,更时常研读长篇累牍的时事追踪,聆听他人对事态的预测,众说纷纭以至于预言还没来得及实现或者落空就被忘在了脑后。”[8](P214)贝罗安不仅把每日的闲暇时间拿出一大部分来浏览新闻,还时时地追踪新闻的动态发展,将其当做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景观作为隐性的意识形态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空间上也大肆拓展。景观对人们在空间上的统治具体体现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两个方面。电视、收音机、报纸作为景观的具体代言,不仅占据着贝罗安的私人空间,也充斥着城市的公共空间,其中电视的出现频次最多,也最为典型。最具代表性的私人空间是一个人的家,贝罗安在家时总会感受到来自电视新闻无尽的吸引力。“他感到那即将开始的电视新闻,像地球引力一般牢牢地吸引着他。”[8](P209)电视新闻对贝罗安的吸引力正如地球引力般不可抗拒、无可抵挡、无法挣脱。与此同时,在小说的叙事技巧上,麦克尤恩先以贝罗安凌晨目睹的飞机起火事故为导入,接下来的叙事就以电视新闻对这起事故的播报为线索,推动小说情节不断向前发展,这在看似随意的贝罗安的意识洪流中,实则是一条稳步向前的叙事线。在公共空间的层面,不管贝罗安身处何地,比如他所工作医院的病房、与朋友施特劳斯打壁球的壁球室、贝罗安母亲住的养老院,甚至是开车行驶的街道,无一例外,电视机就如同鬼魅一般充满在城市的公共空间里,让贝罗安无处可躲、无处可逃。
电视作为景观的具体表现形式,以一种光明正大的方式将隐性的意识形态强加给看电视节目的人们。“景观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实证性,既无可争辩又难以企及。”[5](P23)电视机所播放的新闻即是一种无可争辩的独白,观众作为观看者,无法与其进行辩驳,即使观众对新闻的真实性有所怀疑,观众不能也不会与荧屏中的人物就针对某个问题的观点展开辩论,只能被动地听着电视新闻传达的观点。贝罗安开车行驶在路上遇到一家电视商店时,不由得被五花八门的电视所吸引。此时商店里所有的电视都播放着相同的内容,即首相的电视专访,贝罗安注视着电视当中首相的面孔,对他所言持怀疑态度。“这个政治家说的是真话吗?但问题是谁能分辨真假呢?诚实的人该是什么模样?”[8](P168)尽管贝罗安对荧屏上首相的神情细致入微地察言观色,也无法找到一些强有力的证据来辨明首相所言究竟是真是假,只得听其滔滔不绝的演讲。景观以一种看似非强制性的手段,实则是不动声色地将隐性的意识形态灌输给电视机前的观众,使得观众毫无还手之力。在景观社会中,真实已经离人们远去,人们行走在城市当中,忙忙碌碌,却找不到生活的锚点,只得在景观社会中四处游荡,找不到生活的真正意义和脚踏实地的安全感。景观社会正如同真实的白日梦一般虚无缥缈,让人们身在其中,却无法触摸到真实,找不到生活的归途。
四、景观社会的主体性消解
“随着资本在全球的扩张,景观模式也随之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和复制,商品的影像充斥在全球大量的电子传媒中、弥散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中,大量人群沉溺在商品影像中,在迷入性的观看中泯灭了主体意识和创造活动,在追求‘伪’消费欲望的道路上感受无尽的厌倦感、焦灼感和束缚感。”[10]在世界这幅宏大的景观中,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活动一旦被抹杀,也就意味着人的主体性在景观中就此被消解,彻底沦落为景观支配的附庸。《星期六》中的贝罗安沉溺于对商品的迷恋,无可救药。贝罗安买了一辆价格不菲的银色奔驰,对这部车的喜爱让贝罗安沉浸在心醉神迷的幸福感中。贝罗安开车去旅行时,他对自己的爱车是这样评价的,“人有可能也有权利去爱恋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那时那刻正是这种喜爱的巅峰。”[8](P90)贝罗安对奔驰车的爱恋展现出他心甘情愿地沉醉在景观为人们所营造出的华丽欲望中。“贝罗安更喜欢坐在车里欣赏这座城市,呼吸着经过过滤的洁净空气,聆听着高保真的车内音响将音乐的震撼诠释得淋漓尽致——《舒伯特三重奏》使得他正在穿越的这条狭窄的街道也显得高贵起来。”[8](P91)高保真音响里播放的音乐展示着贝罗安身为中产阶级的高级趣味,然而他享有高贵生活的感受正是由于他拥有的高档商品带给他的优越感。“景观制造的欲望不是我们必需的,而是本能无节制的虚假满足。”[11]在贝罗安看来,“购物比祈祷更能带来满足。”[8](P149)在景观营造的欲望的迷惑下,贝罗安偏离了自己本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享受着商品带给他的满足和安慰,仿佛找到了生活的充实。
不仅是贝罗安已经获得的商品,还有陈列在柜台上可满足人们各种生活需要的商品以及供人们消遣的服务业和休闲行业也对贝罗安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贝罗安“喜欢这里,各种便利服务和高档享受齐聚在这里,令整条街道看起来既鲜活又亮丽:在这里你不但可以买到镜子、鲜花、肥皂、报纸、插座和涂料等物品,甚至还可以配到钥匙,各式小店中间还城市化地夹杂着高级餐馆、葡萄酒专营店、墨西哥小馆子和旅馆”。[8](P145)贝罗安如痴如醉地欣赏着作为景观的商品,心满意足。“心灵的伟大创造力不断为拜物的力量所消解,因而主体的精神文化日益让位于客观的物质文化。”[12](P43)贝罗安受到景观的迷惑,沉陷在对商品的愉悦和满足中弱化了思考的能力,逐渐失去了主体的批判性,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变成了易受支配的客体。“在商品符号的无限包围下,贝罗安逐渐丧失了作为消费主体的理性判断力,受制于商品的符码控制,陷入‘消费主体异化’”。[13]贝罗安在资本主义操控下的生活深受景观的催眠,将商品等同于承担着精神意义和美学价值的符号。在景观的迷幻作用下,贝罗安无意识地放大了商品的作用,借此来逃避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并在作为景观的商品中寄托着他对美好生活的幻想。贝罗安对商品的迷恋促成了其主体性的失落,并让自己遗忘了内心真正的需求。
新闻媒体本应该帮助人们开拓视野,可作为景观的媒介却蒙蔽人们的眼目,让人们对真相视而不见。真实的世界被淹没在新闻媒介所虚拟的世界中,人们自以为自己看到的都是真相,但实际上人们看到的新闻都是被媒体凸显出来的部分事实,那些不想被人们看到的部分则被故意遮蔽起来。当贝罗安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来自前线的报道时,从这些电视画面中体会到的是“伪装的欢欣和虚假的味道”。[8](P213)媒体制造视角的部分真实性还会被政治加以利用,民众原本想借助关注新闻的方式来参与政治生活,但却无可奈何地又陷入了一种被人设计的、盲从的境地。当人们自以为在独立地观察世界时,众多媒体及宣传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取代了人们的思考。媒体资讯的发达虽然空前地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媒体在播报新闻时早已暗中设好了让人们来接受这些新闻的视角,要摆脱媒体的影响去独立地思考变得愈加困难。贝罗安在自我反思时也曾对自己思想观点的独立性有所怀疑。“他怀疑自己变成了一个易受欺骗的傻瓜,自愿而又盲目地追随着当局施舍给公众的任何一点点新闻素材、观点和推论。”[8](P214)在新闻媒介无处不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在媒体观点的裹挟之下,贝罗安意识到身处庞杂的景观社会中,真实的观察和独立的思考变成了一种奢求。“他已经丧失了不轻易相信的习惯,对其他的观点反应迟钝,他不能清晰地思考,更糟糕的是,他感到自己已经不会独立思考问题了。”[8](P215)
五、结语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文艺的真实性是指文学艺术将社会生活原原本本地再现出来,以文字的形式将生活及人物真实地刻画出来。”[14](P67)麦克尤恩在《星期六》中所描述的一系列人物与事件,正是现代社会中的人和事的真实再现。《星期六》中的贝罗安是一名出色的神经外科医生,他拿着手术刀为病人清除病灶。麦克尤恩所塑造的这个人物正是他本身的写照:麦克尤恩正如一名医者,站在整个现代社会前,以笔作手术刀,鞭辟入里地解剖着整个社会,将这个社会的隐疾清楚明了地展露在人们面前。在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借助权力与资本渗入城市,建造了庞大的景观帝国。景观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生活模式以及作为隐性的意识形态,无一不以表象遮蔽抑或取代了社会本真的存在,从而导致了个体的主体性失落。麦克尤恩在《星期六》中透过揭露景观堆聚下人们的精神困境,让人们在后现代社会中进行自我反思且帮助人们去重新认识景观支配下面临信息超载、陷入精神困境的自我。贝罗安生活在景观社会中,并非全然麻木,他对自己沦为景观附庸的状态是有所感知的,但却无法摆脱这种现状,因而陷入了精神上的焦虑状态。贝罗安在本该可以好好休息放松的安息日——星期六,无来由地失眠,挥之不去地还有时常萦绕的疲惫感,这种焦虑是生活在景观社会中大多数现代人精神状态的呈现。如何在景观社会中对抗焦虑,是麦克尤恩留给人们的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