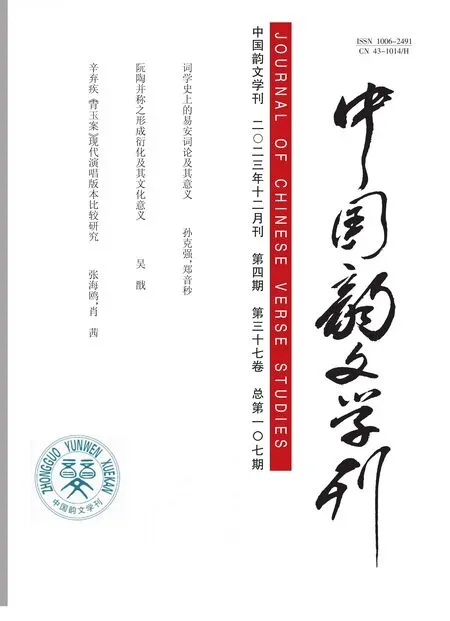源流与影响:赋与白话小说的两重关系
陶明玉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21)
赋与白话小说皆为中国古代文学体系中的重要文类,二者虽然文体有别,且在文学史上各行其道,但是在白话小说的起源与发展历史上,赋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者进行过一定的探索,但缺乏系统性的总结。(1)专门论述小说产生与赋的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于少数论文,主要有:程毅中《叙事赋与中国小说的发展》(《中国文化》2007年第1期);张鸿勋《探寻俗赋的流变遗踪——简论敦煌俗赋与后世文学》[《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廖群《汉代俗赋与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理论学刊》2009年第5期);王猛《赋与古代小说的关系探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白晓帆《俗赋与小说的关系——由刘勰的〈文心雕龙·谐隐〉谈起》[《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8年第8期];王焕然《试论汉赋的小说意味》(《南都学坛》2003年第5期);莫山洪《骈文与中国古典小说》[《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傅修延《赋与中国叙事的演进》(《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王齐洲、李平《曹植诵俳优小说发覆》(《学术研究》2013年第5期);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版)专列一节论述辞赋与小说之关系。本文以白话小说史为中心,梳理出赋与白话小说潜在的两重关系:第一是纵向的源流关系,即赋特别是俗赋曾作为中国早期说唱文学的代表形式而成为白话小说的重要源头;第二是横向的影响关系,白话小说在发展演变历程中,其文体和叙述受到来自异质文类赋(包括文人赋与俗赋)的影响。下文将分别论述。
一 源流关系:赋与白话小说起源
长久以来,关于古代白话小说的起源,研究界普遍以宋元话本小说为可依据的起点。随着敦煌文学研究的深入,将唐宋说话(话本)和俗讲(变文)作为古代白话小说的起源成为研究界的主流观点。但事实上,宋元话本小说以及唐代变文、话本也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们的产生也自有其来处。赋在作书面文学之前,就已以口头文学的形式长期存在。而在赋被确立为文人化的书面文学之后,赋的口头形式即俗赋仍然在民间流传。俗赋,作为中国古代说唱文学的一种形式,自然可视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重要源头之一(另一源头为史传叙事)。
一般认为,赋是诗之变体。班固“赋者,古诗之流”[1](P1)是历代论者频繁引述的话语,但此说模糊不清,后世解人多从“诗六义”之流变入手来论说。事实上,“赋”最初是作为周代大师传述诗的方式,即所谓“六诗”之一。《周礼·春官·宗伯下》曰:“(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2](P880-881)西周时期的“六诗”与汉代《毛诗序》所说的诗“六义”不同。据王小盾的说法,“六诗”是指大师教授瞽蒙的六种传述诗的方式,“风”是指用直述即方音诵的方式传述地方诗歌,而赋则是用雅言诵(王都之音)的方式传述地方诗歌。[3](P222-229)但是春秋以后,这套以“六诗”等为重要内容的乐教制度就已没落。当春秋时期孔子删诗,《诗经》成为经典文本之后,在儒家德教思想的影响下,“六诗”逐渐演变为“六义”。《汉书·艺文志》说:“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4](P1383)“聘问歌咏”是从周代乐教制度延伸出来的政治行为,但随着周道衰落,学诗之士下移至民间,其用诵诗的方式创作了新的文体即赋。[5](P19-26)这就是“赋者,古诗之流也”的真实义。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进而可对俗赋做出一个大致的界定。俗赋虽然是现代人提出的用以区别文人雅赋的概念,但是其所指仍然言之有物。在战国文士(人)赋出现以前,就已存在未经雅言整理的地方土风诗赋,例如在《左传》中就存在着许多“国人诵”“舆人诵”“乡人歌”,这些地方土风诗赋可视为俗赋的源头;这些地方土风歌是用地方语言和语调表述,经过下层文士以赋诵的形式传述或书写最终成为书写文本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正是我们今天能够看(读)到的俗赋文本。文士传述土风歌赋的功能大致与西周时期瞽蒙用雅言诵诗来整理民间歌赋的行为相似。但是二者又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瞽蒙诵诗是一种官方行为,是采诗制度的重要一环,其对风俗诗歌的取舍具有严格的礼乐标准。而文士传述诗的行为则是个人行为,更加自由,形式多样,并且文士传述、书写民间歌赋经历了一个延续不绝的历史进程。从先秦到唐代的传世和出土文献中,我们都能看到络绎不绝的各类形态的俗赋文本(详见下文例子),这些俗赋文本更偏向于原始的民间俗赋形态还是偏向于文人化的俗赋本就存在可变化的弹性。因此可以说,俗赋是民间赋与下层文士传写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区别于文士赋的赋类,俗赋更多的是一个文类的概念,而非文体的概念。因此对其内涵的界定关键在“俗”而非“赋”,俗赋之俗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文本内容的通俗,即多表现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俚俗内容,或讲诵故事,或言语调笑;第二是表述方式的通俗,即俗赋一般可用于韵诵、讲诵,语言通俗,是一种说唱文学,具有表演性,与文士的书面文学不同,但文人受民间俗赋影响而拟作的虽不用于表演的类俗赋也可归入俗赋之中。俗赋的这一文类属性即已表明其作为白话小说远源的可能性。
关于白话小说源出于赋的猜想,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开始。1925年,刘复(半农)在出版《敦煌掇琐》前发表的《敦煌掇琐叙目》将敦煌俗赋《韩朋赋》《燕子赋》《晏子赋》等列入“小说”,开了以赋入小说的先河。[6](P1)1927年,郭绍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提道:“……小说与诗歌之间本有赋这一种东西,一方面为古诗之流,而另一方面其述客主以首引,又本于庄、列寓言,实为小说之滥觞。”[7](P87)(原载于《小说月报》1927年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胡适于1928年出版《白话文学史》也意识到赋具备发展为叙事文学的可能性,认为“赋体本可以用作铺叙故事的长诗”,但“北迁之后”(指汉朝建立)的“庙堂化”切断了这种可能性。[8](P172)钱锺书读杜笃《首阳山赋》而有“玩索斯篇,可想象汉人小说之仿佛焉”的判断。[9](1573)前人诸说都看到了赋中的小说因素,但是限于条件,并未展开赋与小说之关系的研究。
随着敦煌文献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敦煌俗赋(包括《燕子赋》《晏子赋》《韩朋赋》等)与敦煌变文、话本同属于中国传统说唱文学体系,且都具备了“小说”的性质,为早期白话小说即宋元话本小说找到了“直接渊源”[李骞《变文简说》(1957)、《唐“话本”初探》(1959)两篇文章是最早对变文、话本为宋元白话小说来源作详细论证的文章],[10](P1-48)并推测在唐代变文流行之前,汉魏六朝就已流传着讲唱故事的韵文赋体(1935年,容肇祖发表的《敦煌本〈韩朋赋〉考》首倡此说)。[11](P649-681)而1993年出土的西汉俗赋《神乌傅(赋)》,因与敦煌俗赋在体制、内容上一致,将俗赋的历史提前到了汉代。值此契机,先秦以降的俗赋流变脉络逐渐浮出历史的水面。正是由于俗赋文献的陆续发现,及其与唐宋讲唱文学的亲缘关系,俗赋作为宋代以后白话小说的重要源头逐渐为学界确认。
就目前已发现的俗赋文献来看,早在西汉末期,以故事讲诵为主、篇幅可观的俗赋就已出现,出土汉简《神乌赋》与《妄稽》是可信可征的文献例证(在传世文献中出现的俗赋片段(2)如《庄子》中“儒以诗礼发冢”“说剑”的寓言故事性强且有叶韵的特点,可能都是取材于故事俗赋;如《史记·龟策列传》中记载了一段宋元王与神龟的故事,其中大段叶韵,俗赋韵诵特点明显。暗示俗赋早在先秦就已广泛流传)。《神乌赋》讲述一对神乌新建的鸟巢被盗鸟破坏,雌乌护巢战斗而死,雄乌悲愤离开的故事。该赋六百余字,以四言为主,全篇皆能叶韵,口诵特征明显。故事主要以对话的形式展开,多用通俗、质朴的白话。它应当是俳优小说的脚本或记录。(3)俳优演禽鸟是古代俳优戏的一种。《国语·晋语》载优施在宴会上起舞作歌:“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见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76页)俳优自比于鸟,应当就是其节目或受其平时节目影响。张衡《西京赋》曰:“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注曰:“洪涯,三皇时伎人。倡家托作之,衣毛羽之衣。”(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可见汉代倡俳演禽鸟是一种常见的伎艺。《妄稽》主要叙述了荥阳名族男子周春因包办婚姻娶得丑妻妄稽,心中不悦因而再买一美妾虞士,其妾却遭到妄稽的妒恨和迫害,但周春善待虞士而冷落妄稽,妄稽因妒成疾而亡。该赋三千言,语言通俗,基本全篇押韵。这两篇汉代俗赋已接近于后世的“小说”。笔者对西汉竹简《妄稽》的故事情节与明人冯梦龙所编话本小说《两县令竞义婚孤女》进行对比,发现二者情节、主题高度相合,推断《两县令竞义婚孤女》的主体故事是通过民间说唱文学的形式传承于汉代俗赋《妄稽》。(4)《妄稽》原文见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9—76页。《妄稽》与后世话本小说《两县令竞义婚孤女》的亲缘关系为“白话小说源出于俗赋”这一文学史命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
汉代故事俗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继续发展。收录在《全晋文》中的刘谧之(其人不可考)的《庞郎赋》(《全晋文》中一作“宠郎赋”)就是一篇典型的故事俗赋,该赋全用五言诗体,词句皆是通俗白话。虽然残缺不全,但是能够反映出魏晋时期故事俗赋的面貌:
坐上诸君子,各各明君耳。
听我作文章,说此河南事。
(《初学记》十九引刘谥之《庞郎赋》)
宠(庞)郎居山中,稀行岀朝市。
暂来到豫章,因便造人士。
东西二城门,赫奕正相似,
向风径东征,直去不转耳。
(《御览》四百九十)
头戴鹿心帽,足着狗皮靴。
面傅黄灰泽,髻插芜菁花。
男女四五人,皆如烧虾蟆。[12](P1546)
(《御览》六百八十七)
现存的部分内容尚不足以勾勒出全貌,但基本可以判定其以故事演诵为主。且篇中已出现了类似唐宋说话艺人的声口,从开篇四句不难想象出在宴会上进行俗赋韵诵的情境。此外,受民间俗赋启发创作的文人俗赋如王褒《僮约》,也暗示着民间俗赋应该存在着冰山之下的广阔世界可以推测,发源于先秦时期的俳优俗赋,到汉魏六朝时期已发展出以叙事为主、篇幅可观的故事类俗赋,成为汉魏六朝说唱文学的主要形式。
敦煌俗赋《韩朋赋》《晏子赋》《燕子赋》《牙齿可新妇文》等故事俗赋的集中出现,表明了唐代俗赋已经非常发达、成熟,且其在体制、内容上与变文、话本的相似性,又说明俗赋已向唐五代转变和说话发展。相关研究已较为充分,兹不赘述。笔者曾在《曹植“诵俳优小说”与白话小说的起源》一文中指出:
故事俗赋曾长期作为中国古代尤其是汉魏六朝时期叙事类说唱文学的代表形式,而汉魏六朝故事俗赋又向唐宋讲唱文学发展,并最终以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的形式向元明书面文学延伸,促成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最终生成。要言之,汉魏六朝俗赋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所能追溯到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源头。[13](P138)
俗赋作为中国古代早期说唱文学的一种代表形式,是中国唐宋讲唱文学的重要源头,也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远源。俗赋向白话小说的演变,并不是空洞无物的名词变换,这一历时性的演变过程伴随着文体层面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细微具体的嬗变,这有待于更加具体尤其是微观层面的研究。(5)例如白话小说说话人叙述的程式用语“但见”“且说”等多能从俗赋中找到渊源。毕庶春《俗赋嬗变刍论(上、下)——从“但见”、“怎见得”说起》[《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2期]一文已有研究。
二 影响关系:赋与白话小说的发展
赋与白话小说不仅存在纵向的源流关系,还存在着横向的影响关系。到唐代以后白话小说脱离俗赋产生,赋与白话小说开始并行发展。但赋对白话小说还保留着横向的影响关系,促进着白话小说的持续发展。赋对白话小说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体和叙述两个方面。
在文体上,赋对白话小说的影响表现在白话小说及其母体对文人赋和俗赋的直接取用。早在唐代讲唱文学(变文、话本)中,较为浅俗的文人赋体就大量存在,这些文人赋体尤其以唐代盛行的骈赋对唐代变文、话本影响最大。例如《伍子胥变文》中写江景:“又见长洲浩汗,漠浦波涛,雾起冥昏,云阴叆叇;树摧老岸,月照孤山。龙振鳖惊,江豚作浪。若有失乡之客,登岫岭以思家;乘查之宾,指参辰而为正。岷山一住(柱),似虎狼盘旋。”[14](P7)这段赋体描写虽然不及正统文人赋那般高雅,但是与民间的俗赋区别明显。这种浅白的骈赋正是在文人赋的文体主导下形成的。笔者推测这种文人赋风格的形成具体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转变人在讲唱中有意贴近文人辞赋,以使得其表演更加雅致有韵,第二是变文抄写过程中,抄写者将活态的转变伎艺进行了部分改写和书面化,使得变场上的通俗叙述更加文雅,即从韵诵之俗赋转变为读诵之文人赋。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我们今天所见变文中赋具有文人赋的色彩。在宋元时期,白话小说以口头的说话和书面的话本两种形式流传。此时说话人、书会才人在表演或编创小说时,都有意识地吸纳或创作文人赋,以达到更佳的叙述效果。罗烨《醉翁谈录》曾提到说话人“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15](P3-4)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赋,但是赋与诗词同属韵文,自然也会顺及牵入,且就宋元话本所用韵文来看,赋也是其中一大宗。只不过这些赋并非文人成篇,而是对文人成句多方化用。在白话小说脱离宋元说话而成为案头之作的时候,对文人赋的直接吸取和作文人风格之赋以叙述成为白话小说文体的普遍现象。这种倾向自晚明小说文人化之后更加突出。而宋代以后的白话小说同样与俗赋保持了亲密的关系。俗赋在唐代以后并未消失,而是仍然流行于民间,它们在嘲调、隐语、致语、词咏、杂说等口头伎艺中继续存在,其中部分内容不可避免地被白话小说吸收。在元明话本小说和明代章回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赋的体式在文人赋中根本就不存在或者难以找到源头,它们只能是民间流行的俗赋体式。(6)例如明代章回小说《西游记》中的赋赞就多用一种特别开头体式,如第一回:“势镇汪洋,威宁瑶海。势镇汪洋,潮涌银山鱼入穴;威宁瑶海,波翻雪浪蜃离渊……”“金丸珠弹,红绽黄肥。金丸珠弹腊樱桃,色真甘美;红绽黄肥熟梅子,味果香酸……”(见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8页)而据有些学者的研究,在元明白话小说中大量以“但见”“怎见得”等为引领的赋其实都是俗赋。[16](P1-10)总之,在白话小说产生以后,俗赋仍然对白话小说产生着持续性的影响。
白话小说不仅在文体层面受赋之影响,还在叙述层面受赋之影响。第一,在叙述言语上,白话小说曾大量袭用赋的叙述语言。相较历史悠久的诗赋而言,白话小说的产生时间较晚,是中国文学文类体系中的新生力量。在白话小说产生的早期(宋元时期),白话小说在写景状物描人等方面缺少叙写经验,因此曾大量使用韵文作为其叙述话语,而赋无疑是白话小说用于叙述话语的主要来源。在明代前中期的章回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等中,赋体叙述大量存在,且这些赋体叙述虽一般不用于情节推进,但大多与故事情节相关,参与了叙事文本的建构。至晚明以后,伴随着白话小说的发展成熟,白话小说确立了一种以白话散文为主的叙述语言,白话小说的叙述语言也完全脱离诗赋而走向独立和成熟。但是,用赋体骈文以叙事的小说现象却始终存在,直到晚清都不绝。第二,在修辞方式上,白话小说的敷演叙述与赋的“敷演”修辞相通,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其影响。赋的修辞特点如刘勰所说为“铺采摛文”,即是用富有文采的语言来铺陈文章,“赋者,铺也”[17](P134)。敷演与铺陈意思相近,所以魏晋人也用“敷演”来形容赋。如刘勰言“敷写似赋”[17](P158),表明赋的特点是敷写(7)裘锡圭先生释《神乌傅》之“傅”为“赋”,认为“赋”的本字为“尃”,“尃”训作“布”,“傅”是“尃”的引申字,取“铺陈”之义。无论是作为诗六义之一的赋还是作为文类的赋,本字都是“尃”,“所取的都应是‘陈述’、‘铺陈’一类意义”。参见裘锡圭《〈神乌赋〉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皇甫谧《三都赋序》曰:“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1](P2038)成公绥《天地赋》云:“赋者,贵能分赋物理,敷演无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18](P1)。赋,是一种通过“敷演”来表现和体验天地万物的文体。而白话小说在宋元说话阶段就是以“敷演”为主要的叙述方式,敷演既有时间线上的情节排列,也有空间面上的物象铺陈,后者尤其多受赋的影响。白话小说中存在着大量以“但见”“只见”“怎见得”领起的人物描写、景色描写和场景描述,且多用赋体,正好说明了白话小说的“敷演”是源自赋的“铺陈”“敷演”。郭绍虞先生指出赋“由其‘铺采摛文’方面而言,则近于小说”[7](P35-36),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第三,在叙述结构上,白话小说的结构模式也多少受赋之影响。对话体是赋之重要一脉。自楚辞《卜居》《渔父》肇其源,到宋玉《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继其踵,对话体成为赋的一种基本体式。这类赋作因人物和对白的存在而具备了如小说般鲜明的叙事性,在故事俗赋中尤其普遍。程毅中先生即认为赋用对话以叙事,“是古代小说的一体”。[19](P30)如果将赋的对话扩展开来,加入故事和情节要素,就变成了小说体。正由于此,先秦两汉赋中的客主问答赋就已显露出小说的端倪。但是,对话体的赋与小说的共通性乃在更深的层面,即结构方式上。唐代刘知几《史通》曰:“自战国已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20](P480)赋的“伪立客主,假相酬答”与白话小说的叙事模式存在共通之处。赋的对话代表了一种结构,在对话的框架之中赋的铺陈藻绘文字得以展开,“客主问答”是引出赋的主体内容的方式。这种虚拟性、结构性的叙述模式与白话小说的说话人叙事模式本质上是相通的,它不仅是白话小说叙述结构的重要源头,也曾影响元明清白话小说的叙述结构。例如,《红楼梦》主体叙事是以冷子兴向贾雨村演说荣国府为开端,虽然表面上不是说话人对话体,但实际上也是承担说话人的叙事功能。这不能说与赋“遂客主以首引”的结构方式无关,尤其是“假语村”体现的幻设法,与司马相如赋的“子虚”“乌有”先生显示出相似的意趣。
三 总结
赋与白话小说的关系错综复杂,其间的复杂演变过程并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本文的总结难免挂一漏万。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纵向上的源流关系和横向上的影响关系是赋与白话小说关系史的主轴。在白话小说起源之际(唐代以前),赋特别是俗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白话小说的重要源头。在白话小说成型以后(唐宋以后),赋仍然对白话小说发挥着持续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白话小说的文体和叙述。
从总体上来看,赋与白话小说的关系以赋对白话小说的作用为主,但还需要关注的是,白话小说也对赋产生过反向的作用,如白话小说的文体和叙述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过赋的创作。但是这种影响是极为有限的,且多局限于少数俗赋,或者更多的是在思维和结构等隐形的层面,较少体现在文体和形式方面,这主要缘于中国古代文学存在较为明显的文类等级差异。赋在文人化以后,一直处于中国文类体系的上层,而白话小说则主要作为通俗文类,处于中国文类体系的下层;受制于中国文体互参中的以高行卑的规律,[21](P149-167)赋与白话小说的互动一般以体位较高的赋对体位低下的白话小说的影响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