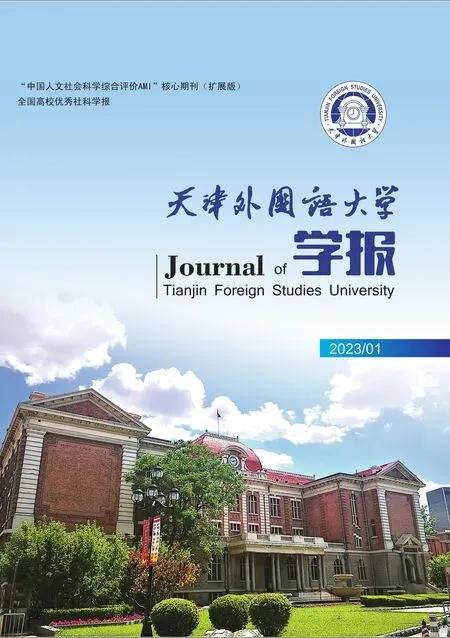动词概念隐喻多义衍生的隐性错置
彭玉海,王 叶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
1 引言
动词多义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它的义位语义衍生往往与语言主体对动作事件的认知体验、概念经验和主观认知思维紧密相关。动词本原动作同新创动作之间依据一定认知相似原则相结合,与一定认知意象的映射相照应,进而建立起不同动作概念域事件的认知语义关联。而这些又都与施喻者对不同事件域一定的关系认同有关,或者以其对这一概念语义关系的心理认同为基础,形成动词意义衍化中极为独特的概念隐喻认知运作思维和语义认知机制。相关方面的内容即是本文要谈的动词多义语义衍生中的隐性语义错置问题。“人类语言处于常规与偏离、变异与不变的张力之间”(赵彦春,2014:1),动词概念隐喻多义衍生中的语义错置(semantic violation)即是这一张力效应之下的特殊语义运作的方式及产物。动词多义中的隐性语义错置在很大程度上是动词事件关系和情境参与者在概念逻辑和语义事象思维中意念化的直观反映。它一方面赋予原本单一、静态的动词内容单位以突出的认知语义性质和动态识解功能,另一方面使动词事件语义和题元名词之间形成特殊的相互解释、相互构建的关系。从自然语言的现实语义表现和功能关系上讲,动词多义衍生中的语义特征、语义条件并不局限于词典释义,而多出来的这一部分往往同人的经验认识、朴素感受(源于动作认知背景中的对象知识系统)和情态框架等意义因素密切相关,正是这些因素连同丰富多样的动作现实表现的客观需要促成了动词概念隐喻多义衍生中的隐性语义错置。因此,许多时候动词多义衍生所伴随的语义错置往往是词汇认知语义变异在人的动作经验想象和语义意识中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式。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主要从动作事件关系视角出发,对动词概念隐喻多义衍生中的隐性语义错置内涵特质和运作机理进行考察。相关研究是在认知语义层面上对动词概念隐喻能力的挖掘,有益于厘清动词多义语义衍生的概念隐喻深层机制,同时对深入理解动词多义语义变化的来龙去脉和义位结构关系的实质大有裨益。
2 语义错置的内涵特质
语义错置是指通过不同层面、不同关系中的语义项(内容单位)之间的意义矛盾、冲突的张力来实现动词多义语义衍生的特殊方式和机制。类属其中的动词多义的隐性语义错置表现为动词事件的命题结构涉及成员内部存在的范畴逻辑错置,它不同于动词构式表层组配中以“违反‘语义选择限制’,造成逻辑矛盾性”(孙毅、张俊龙,2017:31)为表征的显性错置①,属于隐藏于逻辑判断范畴和概念范畴背后的语义作用关系形式。作为动词多义衍生的基础和核心操作手段,词位所包含的语义错置不以表层显在的方式来体现,而是以隐性的形式展开,并且从概念、意识的方式层面看,它几乎内化为动词概念隐喻语义衍生过程中人的一种语义直觉或施喻者自觉的概念意识转化行为,在动词多义语义衍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需要弄清在隐性语义错置中到底是什么层面、什么概念条件在进行错置和概念交换,以及如何错置和交换。这些问题不仅同隐性错置本身的识解有关,同时也直接关系到动词多义语义衍生的运作形态。
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探讨相对有限,已有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隐性错置的逻辑、认知基础,即对内容单位意义变化过程中的范畴误置、逻辑错合及其语义构建性(隐性语义冲突)、认知转化性进行分析,同时对语义衍生中的事件要素功能联结与认知关联性、认知错接性、认知冲突性乃至体认性进行考察;二是隐性错置的概念隐喻实质,即在认知隐喻的概念关系基础上对语义衍生过程中涉及的现象类别信息、物的蕴涵、格式塔认知理论、认知次逻辑与事象等进行分析,并由此探解隐性错置特殊认知的无意识性和自我消解性;三是隐性错置的概念系统性,即对语义衍生同认知主体的概念系统运作以及事件本体和喻体的概念关系内容进行分析,试图通过心理完形、心理联觉、心理图式、概念整合和概念化意识处理等实现对隐性错置运作体系的深层机制和网络层次化构建。
2.1 隐性错置的内涵
动词多义衍生的隐性语义错置是指在出现语义组配矛盾的动词概念隐喻构式中,以意识化方式潜隐式地进行动词事件与所涉项(动作事件中的动词、题元概念结构要素)内部的概念范畴交叉、错合,从而各自达成事件及其要素的概念意识跨接、交换和意识化等同,以语义调适的方式重新建立事件与成素之间的意义顺应,消解动词表层构式中的语义矛盾和冲突。简言之,就是通过隐藏于动词表层结构下的语义冲突体现动词隐喻内部的语义错置关系。作为动词多义衍生语义操作的意识性基础和概念经验交织、互动环节,隐性错置包含语言主体对动词构式语义矛盾进行处理的意识化自我暗示、自我求证过程。当发现动词构式语义矛盾时,在认同动词构式语义动机并配合其得以实现的前提下,认知主体会敏锐地感受到来自动词语义错置的张力感(tension sense)②,会自觉搜寻释放这一张力和消除语义冲突的方法与路径,意识方法上的认知调动和语义能动作用也随之产生。该能动处理和调动在范畴认知的隐性层面展开,其间涉及人在认知概念意识和语义意识方面的积极跟进及二者之间的双向作用、配合。从概念意识方面看,隐性语义错置是在心理意象和认知心理框架中将制约着动词衍生义位(正确解读)的概念交叉形式和关联内容查找出来,这主要依靠语言主体的动作、事物对象百科知识系统③和语言认知、识解能力。而从语义意识方面看,隐性语义错置是在语义觉知和语义分析判断中对动词非规约性语义搭配进行的联想性比对和意识转化,并借此确定动词述体的情景核心语义变异走向,筛查语义组配项背后所隐藏的现象类别信息和语义关系项,从而在“语义熟觉”(semantic conscientiousness)④、语义意识的引领下还原并确立动词构式的常规语义关系,同时建构面向新的语义关系的认知心理空间。在这一过程中,语言主体的语义联觉能力及其对现实语义事况和语义系统知识、语义分析手段的驾驭和把握显得尤为重要。
2.2 隐喻错置的特质
隐性错置是语言主体面对动词构式语义冲突的一种语义选择和语义操作行为,是在概念意识层面实现的有关动作及事体内部的“超常组配和隐喻错置关系”(彭玉海,2020:256)。它所蕴含的命题事件跨接和概念关系错合同语义意识、认知布局和概念意识分布及调配等多方面因素都有深刻的联系,相较于一般的常规语义运作方式和形态,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质。首先,隐性错置是范畴概念意识的交叉错置,动词构式内外的动作、事体(事物名项)各自的语义交织和意识连接及并置,分别通过概念-事理关系内容的错合式对应关联和呼应得以实现,这同时也是隐性语义错置的一个基本且典型的运作方式。其次,隐性错置是深层的、意识化的概念意义关系特征操作,带有相应的认知无意识性(cognitive unconscious)特质(Lakoff &Johnson,1999:73)。该无意识性构成隐性语义错置的显著特点,一方面,这一般是人被动完成的,并非人主动、有意识地进行概念范畴错置;另一方面,这是由语义矛盾的张力感给语句理解带来的压力,即语义压制所造成的(李勇忠,2004:433)。意义理解的基本诉求会引导人下意识地进行语义意识的隐性交错、联动,动词构式相关词项语义及事件、事体的错置借由概念意识的非常规式相融得以完成。这也是词汇语义动态模式积极理论原则(Падучева,2004:147-176;蔡晖,2010:63-64)和意义相互作用原则在动词概念隐喻语义关系中的体现(Апресян,2005:19-20)。再次,隐性语义错置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语义思维的离境操作,动词概念事件和题元名词的理解都需要联系动词本原义之下典型环境的意义联想信息,以特定方法、策略在潜意识当中抽离于动词表层的词围和语境,以审视和应对构式语义矛盾。从离境操作关系的认知处理程序上讲,虽然动词多义构式的隐性错置中,题元名词是语言主体对语义失配关系的直观感知点或语义直觉的捕捉点,人们最初是由它觉察到了构式语义关系的矛盾和张力,但从命题事件背后的认知完形心理和认知就近原则出发,由于在整个动词事件框架中动词述体是认知上更为核心、凸显的部分,因而在具体操作时,语义关系意识首先处理的往往是动词述体描写性语义特征的转移,而后才是题元事物的语义投射和迁移。后者受前者的语义驱动参与动词事件义征变异的相应语义联动变化,形成离境操作中的联动隐性语义错置。
3 动词多义隐性错置运作
动词多义隐性语义错置的运作既同概念意识有关,又同语义组配方式相连,是一个关联着语义转化、衍变和认知范畴逻辑等方面的多维运行系统。对动词多义衍生的隐性错置来讲,重要的是动作本体同喻体之间是如何关联的,不同事件、事体(情境参与者)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建立和运作的。这涉及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动作层的对象关联和转化,二是题元、事体层的对象关联与转化。隐性错置的具体展开分别是在概念事件层和题元关系层内部进行的,这两个不同层级分别包含不同范畴(不同的情景事件范畴)、物类(不同属性的题元参项)的认知对象以及相应的语义交叉组构与概念认知操作。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对动词多义衍生中动作事件层面的隐性错置运作机理展开分析和讨论。
动作事件中的隐性语义错置是指在动词多义衍生过程中,认知主体通过概念逻辑范畴错置的方式进行本体动作同喻体动作之间的交叉、搭接,形成两个动作事件之间在产生形式上的语义逻辑错置和误配,造成动词句子表层组合背后语义动作事实的矛盾和悖谬,从而借此建立本体和喻体动作之间的概念意义交换和认知意识化等同。动词多义的语义关系中,动作本体同喻体之间存在认知距离和落差。从表象上看,“两个指称对象在类属上处于‘隔’的状态,彼此不能有直接的类属上的关联”(施春宏,2003:21),而动作事件的隐性错置就是为了弥合这一隔绝状态而出现的。它通过意识化、概念化处理,引导看似无关、彼此隔离的动作产生意义交集和跨域等同,从语义意识中消弭动作概念关系错置,进而在语义空间的张力之中拉近动作本体同喻体之间的认知心理距离。
动词多义的动作事件隐性错置运作机理主要包括认知相似性、意象转移、名与实的语义关联与照应、同质重合选择四个方面。根据概念意识基础和认知心理基础发现的相似性,在此基础上进行认知意象转移,进而建立动作表层和深层上的名实相成的语义关联与照应,最后在动作本体和喻体之间进行同质重合选择,将二者统合为意识上并行不悖的事件语义结构体。经过上述操作最终消解动词多义衍生中的事件关系语义冲突,实现对动作对象的新认识,从动作事件的语义要求为动词概念隐喻的多义语义衍生理顺了范畴逻辑关系。
3.1 基于动作概念认知的心理相似
心理相似是动词多义衍生中动作事件隐性错置的基础和先决条件,有了相似性,才会有动词事件的概念意识等同所带来的语义错置,或者说这一概念关系操作的认知语义基础即是相似性。“相似性存在于相对于特定概念系统的经验之中并得以体验”(Lakoff & Johnson,2003:155),这里动作事件的相似性表现为认知经验、概念经验上的相似,而非客观实在上的物理相似,属于认知心理中形成的动作主观体验性相似。借助这种心理感知相似,喻体动作事件可以通过与本体事件的并置、互动,将新的动作认知特点和内容加置于本体动作,使其获得经验事实上的映射性添加,达成彼此之间的语义沟通和交流,即语义融通性。
动词多义衍生的隐性语义错置中,基于动作概念认知的心理相似指语言主体在本无概念关联和相似关系可言的动作事件之间先进行主观性认同,进而由人的语义意识确立概念特征心理相似,凭借对本体动作和喻体动作的动觉体验、心理感知与意识关联,形成关于二者之间带有特殊矛盾性的相似关系的认识。由于它是发生在动词主命题隐喻构式之下的次层隐喻联类关系,相当于动词事件之间的二性隐喻(secondary metaphor),往往也基于概念化、定势化的认知想象经验,以概念隐喻方式得以反映和体现,可将该冲突性相似记为X动作本体=Y动作喻体⑤。从认知逻辑和范畴语义上看,这一冲突性相似内容实际是人立足于对动作事件的动态语义认知思考和认知统觉想象,借助类比逻辑对本体、喻体动作进行概念信息方面的融汇、糅合性提炼和相应的认知解析与推理,得出关于两个动作情景的特殊语义比照关系,并由此折射出心理投影,其间往往还会伴随喻体动作的概念意义内涵向本体动作一定程度的倾斜和延伸。这种相似性的显著特点是必须有一个游离于表层并置关系的心理认知定位点,该定位点是动词多义衍生的心理坐标,即人对动词语义衍生关系的整体心理把握,它维系着动词基义事件与喻义命题事件的跨范畴(错位)组构和应接性、衍推性,否则这一相似关系将会失去语义逻辑依据而无法成立。因此,隐性错置中的事件相似性具体围绕动作本体与喻体之间的认知共性心理基点来展开,通过语言主体的认知心理联想可以将动词构式的本体行为同其基义下的喻体行为进行联类、比照,发现它同喻体动作在行为方式、结构、结果、功能、性质或主观感知、体验、评价等方面的一致性、类同性,从而在主观心理认同上进一步落实和具化两个动作事件之间的相似性感知,并相应确立起动作本体与喻体之间的概念认知逻辑。以动词смести(扫除)为例,смести мусор(扫除垃圾),смести паль(扫除尘土),смести грязь(扫除污垢)的隐喻多义义位清除、消除、铲除衍生过程中的隐性错置运作伴有动作认知心理相似性的积极参与,如смести остатки сил,смести рутину,смести феодальное сознание,смести неграмотность,смест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едуги,смести языковые барьеры,смести ленивое настроение,смести дурное поветрие(扫除残余势力,扫除陈规陋习,扫除封建意识,扫除文盲,扫除社会弊端,扫除语言障碍,扫除懒惰情绪,扫除不良风气)。试对比смести мусор - смести остатки сил,смести пыль - смести рутину,смести грязь - смести феодальное сознание(扫除垃圾——扫除残余势力,扫除灰尘——扫除陈规陋习,扫除污垢——扫除封建意识),这里本体动作同喻体动作在动作结构形态、动作结果以及人的主观对待或价值意识评价等方面存在心理上的相似,抽象的社会、精神活动的扫除类同于物性动作(物质动作方式)的扫除,即面对上述语义错置的动词语句,在语言主体内心和脑海里会自觉形成一种把不合时宜的精神物质清除干净与把脏污物清扫干净之间的相似性联想、心理联觉和意识成像,并借助两个动作信息中相应形成的共性特征意义内容和概念结构关系来帮助化解动词多义隐喻构式中的语义矛盾——“(动词)命题关系中的语义错置可以通过‘喻底’,即本体与喻体之间的某种‘相似性’而得以消解”(Kittay,1987:36)。
3.2 认知意象转移
心理、认知意象在动词多义衍生所关涉的本体和喻体事件的语义关联与跨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认知领悟和概念化层面讲,许多时候“语义又体现为意象”(徐盛桓,2017:17),或“语义是由意象呈现的”(何爱晶,2013:40)。在自然语言意义活动中,认知意象本身是极具意义潜势及意义创生性的语义因子,这在动词多义的隐性语义错置中得到了验证。这里的认知意象“是人类在对现实世界反复、多次的体验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孙毅、杨一姝,2012:45),是动作对象在人的头脑中反复校正和自觉涌现的一种动作经历、动作体验心智模式,具有心理经验的自涌性(spontaneous surge)。用Rowlandz(2010:169)的话来讲,就是特定动作对象“面向主体所涌现出来的形貌、样态”,是人在想象、体悟和识解动作对象事件时激发出来的一种动觉心智形象或动作经验结构图式。在动词多义衍生的隐性错置中,根据本体动作同喻体动作概念结构特征某方面的相似,认知主体将表层动作事件的物理行为意象和概念结构移用到深层抽象事件所代表的其他动作概念域,帮助动作意识完成“透过空间对抽象世界的认知”(王敬媛、陈万会,2017:73)。这意味着通过包含于喻体动作的意象性典型特征的映射来认识和表现主体心目中的本体动作形象,喻体动作往往含有鲜明、独特的意象内容和特征,该特征也是认知主体选用此动词而非彼动词来表征特定目标动作的缘由和依据。
“隐喻的基础过程本质上是投射过程。”(林书武,1995:71)从认知表现的角度看,由于认知语域的概念意象转移一般是以经验性强、熟悉度高的动作来表现动作目标语义对象,喻体动作易将来自身体感知和心理经验的意象内容投射到本体动作上,一方面消除语义错置中本体动作同喻体动作之间的某种距离感和差异感,另一方面也以节约、形象的意象化方式使抽象的本体动作事件获得生动、鲜明的具象化呈现,从而凸显本体动作的核心语义和动作特点,使其拥有包含动作喻体意象功能特性的认知新意和张力,这包括基于心理图式、心理意象进行的动作概念映射与动作认知域转移。语言主体经过语义解析和动作情景想象、思考,将喻体动作意象图式的核心经验内容转用、搭接于本体动作之中,二者在动作认知意象上形成契合与互动,由此帮助认识、刻画目标动作对象,凸显目标动作的语义核心和价值性特征,实现动作语义形象和概念意象的认知转化。例如,сплести великие планы,сплести надежду,сплести мечту,сплести будущее,сплести счастье,сплести стихи,сплести сказки,сплести жизнь,сплести верования(编织宏图,编织希望,编织梦想,编织未来,编织幸福,编织诗篇,编织童话,编织人生,编织信念)相较于动词原有语义,即сплести венок/свитер/соломенную шляпу/рыболовную сеть(编织花环/毛衣/草帽/渔网),此时的编织这一本体动作充分摄取了喻体动作中使物件相互交错、钩连的复杂组构特点和语言主体细心而为、用心之至乃至热切期盼的动作意象和心理特征,并借助概念域的转移将这一复杂、用心、专一的动作认知意象投射于本体动作的概念结构中,简练、清晰、形象地传达出目标动作的语义特点,同时也从认知意象图式上勾勒出语言主体对这一动作表现出的心理体悟和感知,反映出动词概念隐喻多义衍生中动作概念事象错置关系的特殊认知语义张力。因此,通过认知意象转移,喻体动作特征的典型意象最终会融入本体动作的语义思维,并进入本体动作语义所凸显的新创价值部分。
3.3 名实相成的语义关联与照应
在动词多义衍生的认知意象转移过程中,语言主体的语义意识中存在一个名实相成的语义关联与照应过程。名指表层(显在)的语义单位构造、动作基本语义和情景事件,即喻体动作;实指深层(隐在)的语义信息内容和情景事件,即实际传达的本体动作。此时有一个透过表层找深层、透过显在找隐在的认知运作环节。表层、显在的喻体动作事件对深层、隐在的情景事件具有概念意识上的成就性、构建性,或者说深层、隐在的本体动作事件需要表层、显在动作的基本情景语义的概念意识支撑和协助,才能得到理解、接受。因此,深层与表层、隐在与显在之间的语义联系和结合点的确立意味着达成了动词构式所示情景语义的本体-喻体概念化联系,建立起名与实的特殊语义比照与呼应关系,实质就是基于对动作进行物质感知和心理认知所得的概念经验、想象经验,借助喻体动作的语义结构和概念内容的特点来认识、把握和凸显本体动作事件的语义特征和表义价值点。例如,прививать мнение о ценности,прививать убеждения,прививать знания,прививать идеи,прививать идеологию,прививать щедрость и доброжелательность,прививать любовь к жизни,прививать ненависть,прививать чувство новаторства(灌输价值观,灌输信仰,灌输知识,灌输思想理念,灌输意识形态,灌输宽厚仁爱,灌输对生命的热爱,灌输仇恨,灌输创新意识)表层、显在的喻体动作嫁接、植入(灌入、注入)经由透过表层找深层、透过显在找隐在的语义意识引导,同本体动作之间建立起错合性的概念语义对位联系,亦即物性动作“把事物引导、传送到需要的地方”同输送、领会/接受这一抽象心智动作之间形成了动作意义上的意识衔接、联类、比照以及实在而真切的概念化心理表征,物理表象上深层的动作概念思维嫁接、植入同隐在的抽象动作输送、领会/接受(思想、知识、观念、情感等)之间产生名实相成的语义关联与照应,为动词多义义位的语义生发创建了动作意识相互映合和对接的意义接口。
3.4 同质重合选择
隐性错置运作过程中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原则和语言心智特点,那就是动词多义衍生相伴的语义意识中的概念化同质重合选择。从语义错置运行机制的整体过程看,这同时也是在认知相似、意象转移和名实相成的语义关联与照应基础之上进行本体与喻体动作的同质重合选择,通过动作概念域的覆盖、置换,使喻体动作向本体动作事件的语义延伸成为可能。
“隐性语义错置通过不同动作、事物的概念的并置间接地表现出来”(彭玉海、王洪明,2015:102),在动词多义语义错置的概念关系确定、对比中,语义特征的同质性来源于人对动词构式、条件的语义动态分析与语义判断。所谓同质重合选择,是指动词隐喻隐性错置的语义关联体通过概念等同和认知相似性找出类同或同质的语义特征联系内容,并以此为代换项,对关联体中发生错置的对象进行替换,从而在二者之间实现概念性等同。具体来说,在人的语言意识中,这里的本体、喻体动作代表的两个事件域基于心理相似和动作意象的关联、映射,在喻体动作中提取出典型的语义特征X,并且通过心理感知、领悟以及语义意识的平行式或交叉式层级推进、融合与对应切换等认知发掘,在本体动作中也同样发现了类似于X 特征的语义信息,然后建立起一个以X 特征为语义内涵核心的新类动作Y,该新类动作拥有自己的外延和内涵,即动作的结构特点⑥,进而Y 成为动作本体和喻体的共性语义特征和内容,即语义共相。据此可以在心理上对二者进行语义同化的对等转换,使Y 这一语义共相在动作本体、喻体之中得到转化、传承,即本体、喻体动作均可等同于Y,并替换为Y,从而实现彼此之间的同质重合选择。这为动词多义衍生的喻义生成创造了坚实的概念语义交换和意识等同语义条件。例如,разоравть линию обороны,разоравть контракт,разоравть план,разоравть заговор врага,разоравть несбыточную мечту,разоравть психический страх,разоравть слухи,разоравть уродство,разоравть устаревшие идеи,разоравть хороши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разорвать старый мир(撕碎防线,撕碎合约,撕碎计划,撕碎敌人阴谋,撕碎黄粱美梦,撕碎内心恐惧,撕碎传闻,撕碎丑恶,撕碎陈旧观念,撕碎美好记忆,撕碎旧世界)的物理本原动作撕碎(如разорвать газету/билет/письмо/документ,撕碎报纸/车票/来信/文件)有一个典型的语义特征X——撕扯、弄破,X 被提取出来并在本体动作中找到了特殊对应信息(成素),进而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以X 为语义核心的新的动作类属和含动作共性内容的抽象概念(集合)Y——“使物类因失去结构整体性而无法继续存在”。后者以共性语义代换项的身份对本体和喻体动作进行语义渗透和意识替换,这就在两个动作之间建立起意义交换等式,即撕碎=消除/废除,形成该语义共相对本原动作和目标动作的意识化等同,即同质重合选择,为动词构式语义矛盾的消解和动词义位的衍生创造了充分条件,促成动词喻义的产出和转移。
通过由心理相似的契合到意象转移的事象映合,再到名与实的语义照应和情景语义的同质重合选择,形成动词事件隐喻错置的运作机制,动词多义的语义衍生实现了情景事件和命题结构方面的语义矛盾消解。从动词事件语义错置动态运作的整体连续性方面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动词概念隐喻多义衍生过程实际是语言主体语义认知状态的推进和延续以及其语义意识的不断跟进与深化的过程,通过它可以对动词多义义位衍生背后的事件互动联系方式和作用机制作出细致、明晰的剖析和审视,从而窥探出动词语义演化的深层内在机理和实质。
4 结语
综上所述,从概念隐喻角度看,意义是在认知主体与环境现实的有机互动之下形成的关于事物、动作和关系、性质等概念意象和概念结构的转移,其中包含人赋予它们的丰富、复杂的认知想象经验和概念化内容。动词多义衍生的隐性错置所反映的事件范畴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认知与人的意义世界的关系问题,其运作特点和机理都同人的语义意识、概念方式和关系意识息息相关,一定程度上也包含行为、动作日常经验语义化的认识表现过程和机制。本文从隐性错置的内涵特质切入,从动作事件层对动词多义的语义错置问题进行探讨,着重对事件层次语义错置的内涵、特性和运作机理进行分析和阐释。在动作事件的隐性错置运作中,认知主体根据概念意识定位和认知心理基础确定动作的相似性,在此基础上进行认知意象转移,进而建立动作表层和深层名实相成的语义关联与照应,最后在动作本体和喻体之间进行同质重合选择,从而确立起本体、喻体动作事象上的并置和动作概念意识的语义互动、融合,为动词语义衍生创造相应条件,促成动词隐喻意义的产生。动作事件层次隐性错置从情景关系和相应概念语义特征切换的角度为动词多义衍生创造了命题事件整体转移的认知处理和语义逻辑条件。动词多义语义错置的动作事件以潜化、隐在的语义渗透行为为动词隐喻义变提供积极有效的认知跨域(意识)运行方式,消解了动词构式的语义冲突,成就了动词多义的语义衍生。认知心理、语义意识、意象转移、同质重合选择以及动作事象的显隐交织与功能互动等在隐性错置的运作中各自发挥了积极作用。相关研究可以加深对动词多义衍生的语义基础和衍变过程、衍变机制的认识和理解,正是借助概念隐喻隐性错置这一独特的语言认知机理,多义动词的事件语义完成了由身体行为、身体义到非身体行为、非身体义的具体-抽象的描写性转化,动词多义的义位得以由物性动作向非物性动作的多向位发散、迁移,完成了动词语义的创生和动词义位新的语义逻辑关系的构建。
注释:
① 这样的显性错置表现为动词述体与其相关语义关系项的范畴错置,“指在语义组合中违反选择条件或常理的现象”(孙毅、张俊龙,2017:32)。
② 动词构式组配成分或动作本体与喻体事件之间存在着一个(行为)概念意义联想与意义理解的想象性空间,也就是彼此之间的语义张力空间,这就是动词多义衍生中的意义张力和张力感,“张力的消解即语义错置中冲突的消除、毁灭,并由此重生新的动词语义”(彭玉海,2012:39)。
③ 单从动词多义义位的语义内容本身来看,也离不开语言主体有关动作现实事况的百科知识,“动词语义是丰富的百科知识(encyclopedic knowledge),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概念语义,它们反映人类活动的经验或世界知识”(程倩雯、程琪龙,2018:34)。
④ 指由内在经验、外在经验(彭宣维,2013:6)等身体经验积淀、升华而来的认知记忆和心理经验内容在语义层面的投射和记载(彭玉海,2018:254;Сергеевна,2007:5)。
⑤ 这一动作概念的相似性心理等同实际与动词基义中语义特征的转移和衍射有关,此时的动作延扩式心理联想可视为是由动词语义内涵扩展了其所示动作范围所致,“每个动词除自身必有的词汇和句法信息外……还有内涵可以扩展外延的词汇语义特征”(常玲玲,2013:26)。
⑥ 该新类动作Y 不仅指向外延,而且构建并纳入新的动作内涵认识,“其所指也不单纯是一种外延意义,而派生出一定的内涵意义”(彭文钊,19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