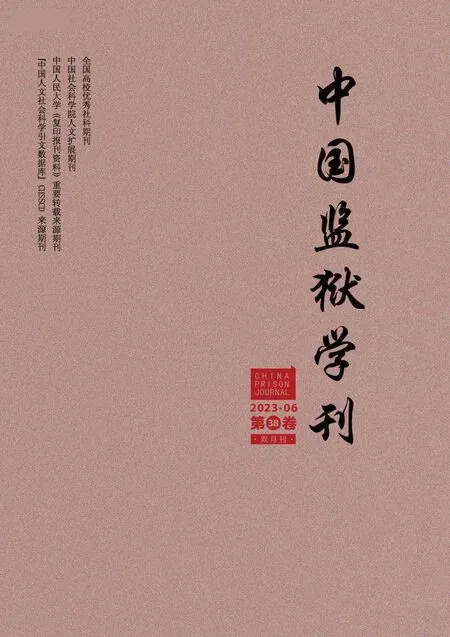清代监狱中的债务问题研究*
张 波 赵玉敏
(泰山学院历史学院 山东泰安市 271000)
通常认为,人犯在监狱之中无法进行正常的商业交易活动,不会产生债务关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清代狱内债务大量存在,并且,往往是导致许多人犯再犯罪的重要原因。了解清代狱内债务的产生原因、具体情形和影响,以及相关人员的参与程度、反应态度,对于加深对清代监狱有关问题的了解,包括人犯的生活状态、狱卒的实际待遇、监狱的财政状况和日常管理情形等,都有重要意义。
一、清代狱内债务问题的产生
依据债务主体的身份差异,清代狱内债务问题可分为如下几种:
(一)人犯与人犯之间的债务关系
1.入狱之前的人犯双方即存在债务关系
地方府县监狱中的人犯,多为本地籍贯,故而不免有在狱外时即相互熟识,并存在债务关系者。随着双方均被羁押入狱,原有的债务关系也不可避免地转入狱中,成为狱内债务的一种。
例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江西南康县人犯吴菖桂在狱外时,便曾向郭三孜借用钱一千文,未还,迟至道光三十年(1850),两人均因故入狱,郭三孜遂继续向吴菖桂讨要。据记载:“道光二十九年(1849)五月十六日,郭三孜与吴菖桂同在食饭,郭三孜闻知吴菖桂已经减流,即须解配,复向索讨前欠。吴菖桂无钱,央俟随后寄还。郭三孜不依,致相争闹。”〔1〕
不过,像这种债务双方后来均锒铛入狱成为“难兄难弟”,并将债务关系带入狱中的情况并不多见。狱内债务更多的是入狱后产生的。
2.人犯之间的相互借债
清代监狱虽然为人犯提供囚粮、囚衣等,但是,盐菜银的数额极少,通常为每人每天给钱五文,或折银五厘〔2〕。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物价的上涨,这点钱逐渐不能满足人犯的实际需要。因此,一些家境稍好的人犯,便会让家属送钱进来,然后买菜食用;一些家境稍差或者暂时没钱的人犯,也时常会向其他人犯借钱使用,由此,产生债务关系。
例如,道光八年(1828),四川大邑县人犯任起兰曾陆续向同监人犯安荣借用钱一千四百七十文。后来安荣“因没钱买菜,就向任起兰讨要欠钱”〔3〕。道光十六年(1836),贵州荔波县监犯胡老六曾陆续向同监人犯潘阿平借过盐菜钱共二百文〔4〕。
3.人犯之间物品交易引发的债务关系
狱中的生活待遇较差,为补贴生活,有时一些人犯会将私人物品,例如衣服、食物等转卖给其他人犯,或相互交换,由此,产生债务关系。
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山东临朐县人犯王小三与同监人犯张荃得交换衣物,并找补差价。据王小三供称:“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初六日,伊用棉袄换得张荃得大褂坎肩各一件,应许找给制钱六百文,屡索未偿。”〔5〕
4.因为赴省秋审盘缠不够而产生的债务关系
每年秋审时,一些人犯奉命提省审理,虽然有户部拨给的秋审经费供给,但是,沿途亦需要一定的额外开支。如果碰巧手中无钱,这些人犯往往会向同监其他人犯借钱使用,由此,产生债务关系。
例如,嘉庆二十一年(1816),陕西宁陕厅人犯杨剃头在解省秋审时,便曾向同监人犯龙可班借钱三百文使用,约定审后回监即还,后来龙可班屡次讨要,但杨剃头始终未还〔6〕。道光六年(1826),四川德阳县人犯张沇富在解省秋审时,曾向同监人犯张富生子借钱六百文使用,亦说好回到县里就归还,但后来屡讨未还〔7〕。
以上不难发现,狱内债务关系一般发生在同牢房的两个人犯之间。人犯虽然大多是本地籍贯,但在入狱前未必彼此认识,入狱后,同牢房者朝夕相处,甚至共享一张床位,所以,能够很快熟识,进而发生债务关系。此种情形亦为将来引发纠纷甚至命案埋下了祸根。据笔者查阅资料所见,许多命案恰恰是发生在同牢房的人犯之间。
(二)人犯与禁卒、典史等人之间的债务关系
1.人犯与吏目、典史等人之间的债务关系
例如,光绪五年(1879),陕西阶州吏目段成章“因闻监犯李应庚家道殷实,辄以代为周旋免罪等词,诈骗得钱五百八十六串”,后来,因李应庚多次向其催促,段成章害怕东窗事发,遂以事未办成,退还其钱二百串,余钱折银三百八十六两,俟有银时陆续归还,转化为债务关系〔8〕。
2.人犯与禁卒之间的债务关系
(1)个别禁卒因向人犯借债形成的债务关系。例如,嘉庆二十一年(1816)山东巡抚陈预即奏称,山东博平县“拟绞监候之犯桑广宗家颇饶裕,时向家中取钱进监应用。同监人犯以及禁卒每向桑广宗告贷”〔9〕。
(2)一些人犯将私人物品卖给禁卒形成的债务关系。例如,嘉庆二十一年(1816),河南监犯易良员“因在监将饭食卖与解役康发祥,食毕,起意乘机讹诈钱文,康发祥不允,该犯用拳殴伤康发祥额头等处”〔10〕。
(三)人犯与狱外人员之间的债务关系
此种债务关系一般形成于人犯入狱之前,但因讨要时是在狱中,并经由典史、禁卒等人之手,与寻常的讨债事务不同,因此,本文亦将其归入狱内债务进行分析。此种债务包括两种:一种是典史、禁卒等代人犯向狱外人员讨债,一种是典史、禁卒代人向狱内人犯讨债。
例如,道光六年(1826),山东商河县“吴曰忠曾借用监犯王克杰故父王纪京钱四十三千七百文,先还过王克杰京钱五千,余欠未偿。嗣王克杰乘典史章谨赴监收封,求追吴曰忠欠项。该典史差传吴曰忠讯断,令其缴还王克杰钱二十千清结”〔11〕。
二、 狱中债务的影响
监狱中的债务问题虽然具体产生原因不一,但是,影响却都比较恶劣,具体如下:
1.人犯与人犯之间的债务影响
因为彼此都在狱中,依靠家人送钱使用,所以,一旦形成债务关系,债务人往往无法按时归还,进而产生纠纷甚至命案。
例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江西会昌县人犯何老金仔将同监人犯何芳连砍死一案中,据禁卒曾茂禀称:“监犯何老金仔因向同监犯人何芳连借用铜钱六十文,屡索无偿。本日上午伊在厨房煮饭,何老金仔令伊(曾茂)买得猪肉在监门外桌上切肉代煮。伊忘记收回菜刀。何芳连见何老金仔食肉,亦欲买肉吃食,向何老金仔催索前欠。何老金仔央缓,何芳连不允,互骂争闹。何老金仔扭断手铐,取刀划伤何芳连右手心,戳伤肚腹倒地。”〔12〕
2.人犯与监狱管理人员之间的债务影响
通常是吏目、禁卒等向人犯借债,或占用人犯物品而产生,虽然通常不会发生直接纠纷,但因存在债务关系,所以,一旦作为债权人的人犯与其他人犯发生冲突,作为债务人的吏目、禁卒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偏袒债权人一方,导致冲突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为命案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例如,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山东博平县监犯王复薪砍毙同监人犯桑广宗案件中,禁卒张法顺曾向人犯桑广宗借债,所以,在桑广宗与王复薪的冲突中,多次偏袒桑广宗,而叱责王复薪,最终导致王复薪怀恨在心,借机将两人杀害〔13〕。
3.人犯与狱外人员之间的债务影响
人犯与狱外人员之间的债务虽然一般不会给监狱方面带来什么直接的麻烦,但是,因为经由了监狱管理人员之手,所以,往往产生一些令人始料未及的后果,甚至是命案。
例如,上述道光六年(1826)山东商河县吴曰忠一案,因为典史章谨插手了吴曰忠与人犯王克杰的债务问题,“该典史差传吴曰忠讯断,令其缴还王克杰钱二十千清结”。吴曰忠被迫凑集钱文,进城缴纳至典史衙门,却不料被典史衙门门丁沈幅、张奎、张怀智等起意勒诈,结果,“吴曰忠被诈情急,乘间用刀自戕殒命”〔14〕。
三、官方对狱内债务的反应与处理
对于狱内债务,有关官员通常是依照债务双方的关系,而有不同的反应与处理。
1.对于人犯之间的债务关系
有关官员对狱内人犯之间债务关系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但基本上是采取了不予过问的态度。例如,道光八年(1828),四川大邑县人犯安荣因为讨债而将同监人犯任起兰杀死。禁卒余伸、李俸便供称:“监犯安荣与死的任起兰平日和好,任起兰陆续借用安荣钱一千四百七十文,小的们听得他们说起过的。”〔15〕
又,咸丰八年(1858),吉林长春厅人犯弓照青因被讨债而杀死同监人犯赵连振一案,禁卒杨发供称:“咸丰六年(1856)十二月十五日,监犯弓照青借使同监人犯赵连振市钱五百文,没还,我是知道的。”〔16〕
显然,禁卒余伸、李俸、杨发等对于人犯之间的债务关系明显是事先知道的,但是,都没有进行干预。不仅如此,即使是借债双方因为债务问题而发生冲突甚至命案时,有关官员在向上奏报的公文中对于债务关系也毫不避讳隐瞒,作为其上级的官员甚至是朝廷亦未有何反应,足以表明当时狱中债务的普遍性和人们的司空见惯。而且,在相关命案的最后处理中,有关官员通常亦会判决人亡债消。例如,上述道光八年(1828)安荣致死任起兰一案,最后判决便是“任起兰所欠钱文,身死勿徵”〔17〕。
2.对于与吏目、典史等管理监狱官员有关的债务关系
因为吏目、典史等人的身份比较特殊,有关官员可能担心存在勒索欺诈人犯等现象,所以,通常比较重视。
例如,在上述道光六年(1826)吴曰忠与王克杰一案中,插手双方债务关系的典史章谨便受到追究。“至典史章谨于监犯求追还欠项,并不详县,辄自行传追,已属专擅,并恐尚有授意需索,希图染指分肥各情。原审亦尚恐未实,亦应一并根究,以昭核实。”〔18〕又,光绪五年(1879)阶州吏目段成章诈骗监犯李应庚一案中,段成章亦被追究问责。“照依用计诈欺官私取财律,计赃准窃盗论,犯该徒罪以上,合依指称衙门打点使用明色诈骗财物计,赃犯该徒罪以上者,发近边充军例,发近边充军。系官员犯赃,应从重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照例免其刺字……段成章未退钱文,应饬如数追缴入官。”〔19〕
四、乾隆帝对于狱中债务的注意和处理
乾隆五十六年(1791),陕西巡抚秦承恩奏报的白河县人犯陈应照杀死同监人犯李得发一案,引起了乾隆帝的注意,原因就在于双方的起衅缘由。据监狱方面禀称,系“陈应照因与李得发争吃肉块,互相嚷骂”。对此,乾隆帝表示了强烈的怀疑,认为:“此语殊不可信。各处监禁人犯皆系穷民,安得带有钱文私买肉食?否则即系该县监狱平日漫无管束,一任监犯等家属来往,私给钱文买肉共食,禁子系中取利,致有彼此争殴毙命之案。该抚系此事问擬罪名虽无错误,但所取供词殊非实情。秦承恩何以轻信属员详报之词,漫不加察,率行入奏?著传旨申饬,并著将指出情节查明据实覆奏。”〔20〕
在此段谕旨中,乾隆帝表示了至少三点疑问:第一,人犯为何能够有钱买肉食用?第二,监狱平时管理是否松懈不堪,允许人犯家属随意往来狱中?第三,禁卒或者说监狱有关官员是否从人犯的日常购买物品中渔利?
乾隆帝的怀疑引起了陕西方面的高度警惕,对此,秦承恩巧妙地予以应对。
首先,秦承恩将人犯买肉所需的钱财说成是人犯个人日常的积攒。“臣遵即飞提提牢、禁卒人等到案,率同按察使姚学瑛亲加研讯。据提牢刘斯民、禁卒罗文辅、王万盈等供称,监犯每日于所得口粮外,例给盐菜油薪钱五文。已死绞犯李得发陆续积存钱二十四文。九月初四日,央禁卒罗文辅转交买办代买熟羊肉一碗,午间放饭时,罗文辅将肉给食。”〔21〕
随后,秦承恩话锋一转,立即对乾隆帝所怀疑的人犯家属可以随意出入监狱的问题进行了否认,并声明禁卒人等并无克扣人犯或帮助人犯代购牟利。其奏称:“已死李得发进监后从无亲属来往私给钱文。禁卒等实无从中克扣以致彼此争殴情事。反覆严究,矢口不移。臣随检查定例,监犯每名日给口粮米八合三勺,盐菜油薪钱五文。并核阅李得发犯罪原招,据供山西曲沃县人,并没父母兄弟妻子等语。是所称李得发积存钱文令禁卒代买羊肉及提牢禁卒等并无纵容该犯亲属来往之处,似属可信。”〔22〕
最后,或许是照顾皇帝的面子起见,秦承恩仅仅承认了一点过错:“惟是此案监犯因何有钱买肉之处,干涉囹圄弊端,自应彻底推究,以昭切实。乃臣于此等紧要口供并未详晰研求,实属率忽。”〔23〕但是,很显然,秦承恩前面已经提到人犯买肉的钱财乃是其平时每日五文盐菜钱的积攒,只要乾隆帝不是眼盲,他一定会看到此点提示,那么,疑问自然消失,而对于秦承恩的覆奏亦无可奈何,只有顺水推舟,将此案件不了了之。
五、对狱中债务的几点认识
狱中债务问题,从根源上讲,都与“钱”字密不可分,从中可以看出:
1.清代人犯的生活待遇较差
清王朝虽然为人犯提供了月粮银、囚粮和盐菜银等,但这些钱文仅足以让人犯维持生存,远未达到温饱。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如监狱方面的挪用月粮银、禁卒等人侵吞克扣囚粮、物价上涨问题等,都导致人犯的生活更加窘迫。
嘉道时期的名将罗思举(1765—1840)年少时曾因故入狱,其记载乾隆五十年(1785)时的四川太平县监狱称:“余拘禁两载,日夜在卡受苦,一进寒狱,衣食俱乏,忽生一方,见新来之人带有镣肘枷杻,不能小解,我即代为周旋,每次酬钱八十,因无现钱,遇发粥时,独余一碗与余,算钱五文,以作利息。又见有新来之人无有坐次,余即将所枕之草一束与之代椅,每日认赁钱四十文,余因此获延残喘。”〔24〕
乾隆五十年已是如此,及至晚清,更是可想而知。光绪三十二年(1906),无名氏曾记载广东某县监狱情形称:“查狱囚人犯每名每日给米一斤、钱十二文。此十二个钱,除买柴九文外,只剩三文,持此三文买油盐。且发之米均粗糙不堪,除拣清谷稗米碎外,仅得十三、四两之间。在押人犯多半粗壮之人,日食十三、四两粗米,何能胞腹?若果有家属料理者。尚可由家顾送,以为弥补;若无家属者,则日饿日瘦,以致气衰生病,死于狱中。”〔25〕
在此种情形下,人犯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借务问题。例如,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陕西安化县人犯李生智之弟李生玉便曾入狱为其送口食制钱五百文。李生智因为暂时用不着,便借给了同监人犯张银。十一月初七日,张银之妻为其送来制钱二百文。李生智看到后,便向张银讨债,但张银支吾未还。次日早晨,李生智再次讨债,张银因为其妻送钱不多,不敷用度,恳求暂缓〔26〕。
2.禁卒的收入待遇较差
清代各地禁卒每年的工食银数量不等,但通常都是六至八两白银。例如,安徽凤台县〔27〕、太平县皆为六两〔28〕,福建永春州为六两二钱〔29〕,安徽铜陵县〔30〕、直隶昌平州为七两二钱〔31〕,山西广灵县为八两〔32〕。
而清代物价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上涨,徐珂曾记称:“至康熙时,则斗米值银二钱,雍正时,市平银一两,可易大制钱八九百文,米色虽有高下,每斗米市价以百文上下为率。乾隆庚寅(乾隆三十五年,1770),斗米值钱三百五十钱,武昌县志已列为灾异。道光以来,米价极限贱时,一斗必在二百文外,昂时或千余钱、银一两,从无千钱以内者,始知往日物轻钱重。”〔33〕
显然,每年这么点工食银根本就无法养活禁卒及其家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因故被关入广东某县监狱的无名氏在出狱后,便曾向官方建议“足养廉”,认为“丁役勒索,由于工食太少……如果仍前工食之少,难免枵腹从公”〔34〕。
在此种情形下,禁卒不得不另外寻找收入,除克扣囚衣囚粮、敲诈勒索人犯外,还会通过帮助人犯从狱外代买物品获利。例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浙江巡抚臣三宝陈奏湖州府属孝丰县监犯陈永加等越狱脱逃一案时,便提道:“陈永加因越境买盐拒捕,殴伤陈文荣身死,拟斩监候,自知罪重,时买酒肉与禁卒王永、许武并同监人犯丁松牙等饮食,又借给王永、许武银两代做衣服。王永、许武利其银衣口食,随相交好。”〔35〕陈文荣既然被判斩监候,自然无法出狱购买酒肉,只能是委托禁卒王永、许武等代劳。而王永、许武帮其购买酒肉,自然亦不会白白帮忙,或者是共同享用,或者是少买多报。
3.地方监狱的经费始终比较紧张
清代监狱经费始终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以浙江平湖县为例,其每年的存留银为三千二十一两二钱二分八毫五丝四忽八微五尘,遇闰加正银一百四十四两二钱三分三厘参毫三丝。其开支情形如下:(1)各衙门办公经费,包括乍浦理事同知,本府通判,本县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儒学、乍浦白沙湾巡检二员,办公经费总计约银一千八百六十六两。(2)各衙门官员俸禄,包括本府通判,本县知县、县丞、主簿、典史、教谕、乍浦白沙湾巡检二员,所有俸银总计约三百零四两。(3)各衙门机构的差役胥吏的工资,总计约一百六十三两。(4)各种祭祀费用,总计一百四十九两。(5)各种慈善救济费用,例如赈济孤贫银三百三十六两〔36〕。
其中,平湖县监狱有关开支情形如下:(1)囚粮方面,平湖县境内共有监狱两处,一是乍浦理事同知衙门所属人犯,一是平湖县监狱所属重囚人犯,两处额设囚粮均是银三十六两,合计七十二两。但是,监狱的实际开支远超规定数额。仅宣统元年(1909)上半年,平湖县监狱就有囚犯三十三名,囚粮加盐菜银开支为八十三两七钱七分四厘五毫,加上草席、葵扇等,合计银八十八两一钱二分四厘五毫〔37〕。下半年有囚犯三十四名,囚粮加盐菜银开支为九十一两八钱三分一厘,加上草席、棉衣、棉裤、草荐、葵扇等,合计银一百二十八两一钱八分一厘〔38〕。全年合计二百一十六两三钱五厘五毫。
此外,人犯的医药、监狱常规性公共防疫药物,监狱维修,置办刑具、灯油,押解人犯路费,人犯瘐毙后的验尸、棺椁、埋葬费用等,尚未包含在内。
可以说,清代监狱中需要用钱之处,而地方经费有限,不可能任由监狱无限制地开支,所以,根本无法为禁卒等提高收入待遇,遑论进一步改善人犯的生活水平。既然如此,地方官府和监狱方面对于狱内债务问题的存在只能是坐视不理,对于禁卒等人盘剥人犯的行径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总之,清代监狱债务中问题的表现不一,但无论是人犯与人犯之间,还是人犯与监狱管理人员之间,各种债务的产生,实质上都反映了监狱体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就人犯而言,是监狱囚粮、囚衣等供给不足问题;就监狱管理人员而言,则是禁卒等人收入待遇过低等问题。两者又互相影响,让监狱问题更加严重,并引发其他问题。对于监狱中的债务问题,清代官方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其既然无力提高监狱有关经费,就注定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亦只能是不予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