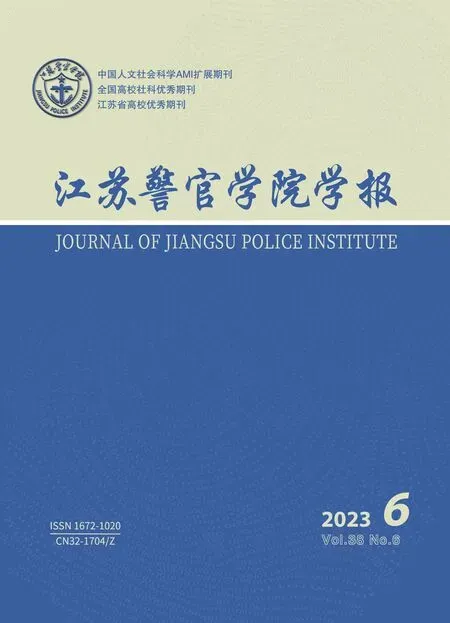检视与省思:补充侦查的“程序倒流”样态
苏志远
一、问题的提出
诉讼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对于完善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通常情况下,刑事诉讼程序是从前一阶段流向后一阶段。但是,实践中经常存在“程序倒流”现象,即案件从后一阶段向前一阶段返回并需开展相应的诉讼行为。①陈瑞华:《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85 页。虽然加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有助于全面收集证据,避免出现“带病起诉”,但正是因为补充侦查制度在线性结构上具有程序逆向运作的特点,其在理论研究和司法适用中面临许多批评。比如,补充侦查制度使诉讼程序多次回溯,有违诉讼的经济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借助补充侦查制度变相延长诉讼程序“时限”,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与程序正义的理念相悖;补充侦查制度过度强化国家追诉力量,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弱势地位,不利于控辩平等的实现,等等。这些批评观点不免令人产生疑问:补充侦查制度中的“程序倒流”现象是否具有合理性?曾有理论认为,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的程序倒流可以分为程序性补救程序倒流、实体性补救程序倒流和规避错误的程序倒流等类型。其中,补充侦查制度发挥的是实体性补充功能。②汪海燕:《论刑事程序倒流》,《法学研究》2008 年第5 期。有学者认为,“查明事实真相应当进行反复调查”③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288 页。。在实体性补救方面,补充侦查制度能在客观上对侦查工作的缺陷进行补救、纠正,继而完善证据体系、提升侦查质量,保障案件定罪量刑工作顺利进行。同时,在程序性补救方面,该制度可以规范侦查活动,纠正前期程序错误。在规避错误方面,该制度可以纠正前一阶段错误的处理决定。可见,即使面对诸多批评,补充侦查制度仍具有其合理性,理论研究应着力思考如何对补充侦查的“程序倒流”现象进行公正、客观评价,并有效保障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功能发挥。
2020 年4 月,《关于加强和规范补充侦查工作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指导意见》)发布后,补充侦查制度的适用条件和运行路径更加明确。按照《指导意见》第2 条规定,补充侦查是依照法定程序,在原有侦查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查清事实,补充完善证据的诉讼活动。“查清事实”的最终目的是“补充完善证据”,由此,补充侦查制度可以完善前一阶段侦查工作在证据收集数量与质量上的不足,并弥补证据收集程序上的缺陷。不过,这是否仅仅是用来完善指控体系,保证有罪判决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5 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证明信息是案件发生所遗留于外部世界的一种痕迹,证据正是通过其所包含的证明信息发挥作用。①封利强:《司法证明过程论——以系统科学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12 年版,第153~155 页。在刑事诉讼中,除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关的证据外,还有涉及程序公正情况的证据。按照具有包容性的证据法理念,证据的完整性要求侦查工作尽量全面收集证据。从这个视角切入,补充侦查制度的运作应围绕完善证据体系而进行。在新的时空场域下,补充侦查制度的适用效果如何?究竟应发挥何种功能?其有无制约因素?对补充侦查制度的理论预期有待司法实践的反馈结果。因此,应深入实践过程,寻找问题症结所在。否则,如果尚未明晰补充侦查制度运作的实践样态,尚未反思“程序倒流”表象背后的深层逻辑,那么对于上述批评的回应将是“无本之木”,难以具有生命力。在本文中,笔者将借助证据完整性这一理论,首先考察补充侦查制度的整体运行状况,探讨该制度在证据选择方面的功能;继而围绕“程序倒流”现象,逐步厘清和回应实践困惑,探讨解决措施,以期规范、引导补充侦查制度的适用。
二、“程序倒流”现象的实践考察
(一)实证研究的基本范围
在对补充侦查制度实施效果加以观察、分析之前,首先应当界定补充侦查的外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补充侦查制度的外延主要包括审查逮捕阶段的补充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的自行补充侦查、退回补充侦查,以及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对于刑事诉讼法第175 条分别列举出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可以要求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这两种补充(正)证据的活动而言,其是否也属于补充侦查制度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从刑事诉讼法第175 条表述可以看出,这两种活动与补充侦查之间并非绝对的包含或被包含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并列的地位。由于《指导意见》第2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提出补充侦查意见……要求公安机关提供证据材料,要求公安机关对证据的合法性作出说明等情形,适用本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容易使人混淆这些行为之间的关系,将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提供证据材料、说明证据的合法性等行为都作为补充侦查加以适用。事实上,补充侦查活动应当依据法定程序进行,不宜将上述两种活动纳入补充侦查制度而加以扩大适用。虽然在补充侦查工作中可能涉及这些活动,但是这些伴随性的行为并不属于调查工作,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虽然平息理论上的争议尚需时日,但是在本文的讨论中补充侦查制度不包括这些证据补充活动。
(二)理论基础、数据来源和样本筛选
目前,针对补充侦查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阐述、价值评断等方面,缺乏以实证调查结果为基础的讨论。因此,在强调“完善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政策导向下,应依据证据完整性理论,开展补充侦查制度的实践考察。笔者认为,补充侦查制度对证据完整性的影响在于证据范围的变化,包括实体事实层面上的有罪、罪重证据的变化,无罪、罪轻证据的变化,以及程序正义层面上证明侦查行为合法的证据变化。刑事裁判文书应对包括不同证据的数量增减、质量变化以及性质判断在内的各方面情况作出描述和评价。在这一理论认识的基础上,笔者通过检索“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以寻求案例样本。考虑到审结日期与补充侦查的发生日期并不同一,因而以2021 年3 月1 日至2023年5 月1 日(即《指导意见》发布一年后至今)为时间段,以“补充侦查”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获得2069 份刑事裁判文书。经过人工筛选,去除形式上符合检索条件但实质上并无研究价值的案例后,剩余132 份刑事裁判文书。其中,涉及审查逮捕阶段补充侦查的裁判文书为2 份;涉及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的裁判文书为96 份,自行补充侦查的裁判文书为6 份;涉及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裁判文书为28 份。在占比最多的两类文书中,审查起诉阶段的退回补充侦查是典型的程序倒流现象。另外,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工作也在退回后经由检察机关实施,同样属于一种程序倒流现象。这两类样本正与本文所研究的补充侦查制度中的“程序倒流”现象相契合。因此,下文即以这124 份刑事裁判文书为依据展开研究。
(三)补充侦查制度的实践样态
1.收集证明有罪、罪重的证据。补充侦查工作的作用之一,在于收集证明有罪、罪重的证据。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通过补充侦查工作收集、调取相关证据,可以弥补案件可能的存疑之处,强化犯罪事实中的相关细节。此外,通过补充侦查工作还可达到以下效果:其一,加重犯罪情节。如有的案件经过补充侦查,被告人“非法猎捕的野生动物数量”出现了增加。①参见(2019)湘1227 刑初145 号刑事判决书。其二,排除虚假言词证据与其他证据的矛盾。如通过补充侦查,可以反驳被告人的辩解,或是纠正被害人的虚假陈述。其三,发现新的罪行、新的罪犯。如在有的案件中,通过补充侦查,可以发现被告人串通提供虚假供述,相互包庇的犯罪事实,继而发现之前被告人身份认定中出现的错误。②参见(2021)鲁1481 刑初91 号刑事判决书。其四,经过补充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存在犯罪前科。总的来说,补充侦查活动不仅可以加固指控体系中证据链条的薄弱环节,而且可以拓展原有指控体系,有效打击犯罪。
2.收集证明无罪、罪轻的证据。在侦查取证中,侦查人员可能受到主客观方面的影响,没有收集某些证明无罪、罪轻的证据。通过补充侦查可以获取这方面的证据,继而将其收入卷宗,从而发挥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作用。在无罪证据收集方面,若补充侦查中发现犯罪嫌疑人可能无罪,有的司法机关会以“证据不足”为由,撤回起诉;③参见(2021)新2222 刑初86 号刑事裁定书。有的则可能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要求公安机关撤销案件,从而终止刑事程序。④参见(2021)云0828 刑初51 号刑事判决书。
在罪轻证据收集方面,补充侦查工作主要发挥了以下作用:其一,发现矛盾证据,使原先对关键事实的指控无法实现。比如,在张某飞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放火罪⑤参见(2021)云0624 刑初5 号刑事判决书。一案中,经过补充侦查,法官认为“是否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生命、健康及重大财产安全造成危害,和当时的环境及其他诸多客观原因有关,不能预见”,因此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又如,在李某卓、蒙某齐等开设赌场罪⑥参见(2021)浙1082 刑初90 号刑事判决书。一案中,就被告人李某卓持有的具体股份数额及是否取得6.5 万元分红的事实,经过补充侦查后,相关证人证言发生改变,从而使“现有证据尚不能排除其他合理怀疑”,最终案件的关键事实不能认定。
其二,发现犯罪嫌疑人构成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以及具有获得被害人谅解、积极退赔损失等其他量刑情节。具体来说,这包括以下工作: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自首情节的材料;收集证明立功的相关材料;查证立功线索;获得被告人检举他人犯罪的相关事实;查证不存在逃逸情节;证实犯罪嫌疑人精神方面存在问题等等。在共同犯罪中,还有认定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补充获得被害人谅解的材料、补充退还部分犯罪所得的材料等等。
其三,减少犯罪数额的认定。在实践中,这方面的表现具体有:核减司法鉴定中有关体内乙醇含量数据;更正因为笔误造成的多增的毒品数据;核减现场初步清点时确定的假币数量;核减转账资金中不属于赌资的部分;纠正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中指控销售数额的错误;降低非法采矿的数量,扣除部分指控数额;将“双方约定的财务费用”视为公司同意,从而减少职务侵占犯罪的数额认定;去除经过补充侦查无法查实的情节,核减合同诈骗犯罪数额等等。
3.补正、排除存在程序问题的证据。《指导意见》第2 条规定,“要求公安机关对证据的合法性作出说明等情形”同样“适用本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第14 条强调“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可能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书面说明或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必要时,可以自行调查核实。”根据上述条文来看,虽然这种行为并不在补充侦查制度中,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可以通过补充侦查程序进行证据收集的补正工作。具体而言,一方面是补正瑕疵证据,由侦查人员再次提交证据或者作出进一步说明,比如询问、讯问笔录内容雷同,需要做出证据转换;对于讯问过程是否存在打骂行为作出情况说明;对于搜查、扣押过程中存在重大程序问题作出说明等等。另一方面,是排除非法证据。比如,讯问笔录采集程序违法时,则应当排除使用。又如,被告人“在被抓获后受到侦查人员的殴打及疲劳审讯、诱供导致的虚假供述”,经过补充侦查“不足以证明取证的合法性”,应对“供述予以排除”。
三、“程序倒流”现象的合理性分析
其实,因“程序倒流”现象而饱受理论争议的补充侦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却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补充侦查制度的适用前提在于原有的侦查活动目标没有彻底完成。造成这一前提事实的原因是多样的:原有侦查活动所确定的犯罪嫌疑人,既可能是尚未获得足够证据证明其所犯罪行的有罪之人,也可能是并不构成犯罪、无法以充足证据证明罪行的无罪之人;或是在侦查活动中,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补充侦查制度具有查证实体性内容和程序性内容等两个方面的作用。在实体性内容上,该制度能够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以及无罪、罪轻的证据,实现强化指控、发现错案的实体功能;在程序性内容上,该制度也能保障证据收集过程的合法性,发挥侦查监督的程序功能。
(一)强化指控功能
补充侦查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实现“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的任务。这从补充侦查的主要适用条件——将尚未查清的犯罪事实和遗漏的罪行调查清楚,将尚未收集的证据收集完毕,将漏诉的犯罪嫌疑人依法追诉——可以看出。检察机关的补充侦查权并不依附于侦查权,而是公诉权所派生出来的应有权力。①陈卫东:《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程序若干问题研究》,《政治与法律》2018 年第1 期。“警察以被告可能有罪为根据,认为某个人违反了法律而实行拘留,检察官则必须提出具有更高质量的证据以便在审判室内将同一个人定罪。”②[美]琼·雅各比:《美国检察官研究》,周叶谦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1990 年版,第134 页。借助补充侦查制度,可以保障检察机关更有力地追诉、指控刑事犯罪。对于不批准逮捕后的补充侦查,因仍处于侦查阶段,并未出现程序倒流现象,可以看作原先侦查工作的延续,故在此不做讨论。根据相关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如果案卷中证据不足或者证据存疑,导致相应的犯罪事实难以证明,检察人员为了强化指控,可以通过启动退回补充侦查程序,引导侦查人员收集、完善证据。在审判阶段,如果“发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等情形且需要补充侦查的,检察机关可以建议法庭延期审理,然后开展补充侦查。此外,如果出现被告人提出新的立功线索情形的,审判机关可以建议检察机关补充侦查。由此可见,检察机关通过启动补充侦查,能够完成案件事实“碎片”的最终整合,使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确保案件达到起诉标准。司法实践中,大多数补充侦查工作的目的都在于强化刑事指控、有效追诉犯罪。
(二)发现错案功能
补充侦查制度也具有发现错案的功能,进而防止错捕、错诉和错判的发生。补充侦查并非只具有惩罚犯罪的效果,其还具有确认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作用。案件之所以变得“疑难”,一是因为案件发生时留存的证据往往较少,容易造成证据稀缺;二是因某些案件的自身特点所导致,比如“一对一”案件、现场遭到严重破坏的案件以及犯罪手段较为隐蔽的案件等等;三是因案件侦办过程出现错误而导致。在侦查活动中,很难保证不会出现任何失误。这些错误一旦发生,将最终影响证据的完整性,并形成刑事错案。例如,侦查人员没有依法收集证据、在证据保管过程中出现差错、对于证据的理解出现偏差,甚至有的侦查人员故意隐匿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等等。这些情况都会影响证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当案件出现关键证据缺失或者证据相互矛盾等情形,“需要补充侦查或者补充提供证据”时,便会隐藏着这样一种可能:由于案件侦办过程出现的错误,使得原本无罪、罪轻的犯罪嫌疑人面临更为严重的刑事处理结果。通过补充侦查可以再度检视案件侦查过程,继续收集、核实证据,排除存在刑事错案的可能。而且,如果先前的侦查活动违反法定程序,经过补充侦查,发现不能证明原来提交证据的取证合法性,从而对被追诉者予以从宽处罚,实质上是将程序问题转化成了实体问题。所以说,这种特殊处理方式也为被追诉者提供了补充性的司法救济。①吴宏耀、赵常成:《程序性违法的量刑补偿机制研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 年第3 期。由此,当案件因为事实、证据等方面原因需要补充侦查时,除了可以强化指控外,还有可能帮助司法机关发现错案。从该角度讲,补充侦查亦是一种纠错机制,具有吸收、消化无罪案件,保障有罪案件罚当其罪的作用,可以防止公民受到错误的、不当的刑事追诉。如果公安机关明知证据不足还要移交审查起诉,或者检察机关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不做撤诉处理而是直接“带病”起诉,都将使程序回流的意义无法得到实现。
(三)法律监督功能
有学者指出,补充侦查活动具有法律监督属性②卞建林:《检察机关侦查权的部分保留及其规范运行——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现代法学》2020 年第4 期。,可以作为监督侦查活动的一种措施③荣晓红:《论侦查监督检察政策》,《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22 年第6 期。,发现和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基本特点是:由承担侦查、公诉职能的检察机关对侦查实施监督。④刘计划:《侦查监督制度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中国法学》2014 年第1 期。侦查活动具有典型的侦查权属性,而补充侦查活动则不仅具有侦查权属性,还带有一定程度的法律监督权属性。补充侦查制度是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体现。此处讨论的法律监督,并非对补充侦查过程的监督,而是补充侦查过程对于先前侦查活动的监督。由此,检察机关的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在补充侦查中出现交叉。监督的最终目的和意义在于使侦查机关提高侦查工作质量,既有效打击犯罪,又切实保障人权。⑤孙谦:《刑事侦查与法律监督》,《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 年第4 期。从实践来看,“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的检察理念,赋予补充侦查制度的法律监督功能以新的场域和途径。为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付诸实践,不仅需要关注案件结果,还需重视办案过程。执法办案既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基本手段,也是彰显法律监督实效的重要途径。①谢鹏程:《坚持“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的检察理念》,《检察日报》2021 年1 月22 日。“必须把监督寓于办案,把办案作为监督履责的过程和基本手段。”②郑赫南、闫晶晶、姜洪:《首席大检察官释放哪些创新发展新信号》,《检察日报》2018 年7 月26 日。通过补充侦查制度,扩大监督场域。首先,检察人员若在审查案件时发现侦查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可以命令办案人员重新组织实施。例如,先前的辨认活动违法时,可以让公安机关重新安排相关人员进行辨认。其次,对于侦查取证过程中各种的缺陷,可以向公安机关发放检察建议或者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其予以纠正。最后,对于补充侦查后仍无法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应按照法律规定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罪起诉的依据,进而防止和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四、“程序倒流”面临的困扰
补充侦查制度是刑事诉讼纵向流程中的“程序倒流”现象。由于其在适用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实践效果不佳,合理性面临质疑。
(一)程序规定尚需细化
实践中,补充侦查制度的启动和适用范围没有严格限制,容易出现大量非必要的程序倒流,造成程序空转。虽然在法律规定和理论认识上,在必要条件下适用补充侦查制度已得到确认,但是该制度的具体适用仍呈现出空泛、无序的状态。一方面,关于启动和决定补充侦查程序的法律规定较为粗陋。根据相关法律条文,只有出现符合“法定程序”的相关情形,才可启动补充侦查制度。那么,究竟什么是“法定程序”?虽然《指导意见》对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自行补充侦查的适用情形作出了规定,但是该文件效力并未达到“法定程序”的规范程度。这使得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少借助补充侦查制度进行程序上的技术处理的问题,如饱受诟病的“借期限”等虚假补充侦查活动,从而影响了刑事诉讼程序的运行效果,使立法目的无法实现。另一方面,补充侦查制度的范畴过多,实践中难以把握具体的适用尺度。补充侦查本质上是一种发挥辅助作用的补救程序,补充侦查的内容必须是非采用侦查手段不可的问题。③徐益初:《论补充侦查》,《中国刑事法杂志》1995 年第1 期。可以用一般调查方法解决的问题,不能采用补充侦查。也就是说,如果过度适用补救程序,甚至以补救程序替代正式程序,将导致该制度的功能异化甚至错位,从而在结构上产生失衡风险,影响法律程序的稳定状态。对于刑事诉讼法第175 条规定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可以要求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而言,虽然这些“补而不侦”的诉讼行为也对原侦查工作具有完善效果,但只能看作刑事程序的自治功能,而非补救功能。如果以此为名,将一种预设的补救程序变为常规程序,将会忽视补充侦查的非常态性,造成程序滥用,最终使其“变质”并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
(二)实践机制有待加强
从司法实践来看,补充侦查制度的配合程度有待加强。补充侦查制度的适用造成“程序倒流”,使得案件不同阶段的诉讼主体都可能重新参与进来,因而对诉讼过程的协同配合提出了较高要求。但在实践中,公安、检察机关往往缺乏有效配合,很多时候仅是交流意见,而未明确具体的协作分工,难以真正完善案件证据体系。④曾军、杨毅伟:《浅析刑事诉讼程序回转——以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权为视角》,《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 年第4 期。以审查起诉阶段的退回补充侦查来说,公安、检察机关已形成固定思维习惯:一方重视批捕、破案的成功率,一方追求起诉的成功率。由于目标上存在偏差,工作的配合程度容易受到影响。这可能产生两种消极倾向:一种情形是部分检察人员仅停留在浏览卷宗层面,没有亲历性地接触侦查活动,制定的补充侦查提纲的可行性、说理性和有效性不足。当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后,侦查人员可能已将批准逮捕决定作为案件侦查终结的标志,对于补侦工作容易产生反感或者事不关己的极端态度①徐航:《退回补充侦查制度的实证分析——以审查起诉环节为视角的观察》,《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 年第3 期。,不愿再对案件进行深入侦查。对于补充侦查的要求,往往以“情况说明”报告敷衍了事,代替实质侦查。如果检察人员发现补侦工作不够理想,只能将案件再次退回补充侦查,导致出现一补再补的局面,甚至陷入无法补救的窘境。在唐某犯贩卖毒品罪一案②参见(2021)湘02 刑终150 号刑事裁定书。中,毒品取样过程存在程序瑕疵,但是“经过补充侦查后,已无重新鉴定可能”,最终审理法院对其他未鉴定的毒品不予认定。可见,补充侦查的不当操作不仅带来办案效率的低下和司法资源的浪费,还有可能影响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另一种情形是当公安、检察机关的平时联系较为紧密时,检察人员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卷宗材料存在瑕疵后,会通过非正式途径与办案人员取得联系,指导公安机关予以完善。虽然这种做法有效减少了程序倒流,但绕过法定程序的做法有违程序正当理念。总的来看,当前补充侦查工作尚不存在常态化的协作机制,如果这一问题没有解决,制度的预期价值将难以发挥。
(三)案件评价体系亟需转变
目前,补充侦查制度在运行中还受到案件评价指标的直接影响:一是由批捕率、起诉率、结案率和无罪判决率等指标所产生的结果导向评价;二是在检察机关建立的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存在着“案-件比”这一核心指标的过程导向评价。
就结果导向的评价指标而言,其使补充侦查工作往往突破必要性的限制。具体来说,批捕率、起诉率、结案率和无罪判决率等指标涉及公检法之间的程序协作,使刑事诉讼活动中后一环节的处理结果直接影响前面环节中办案机关的业绩考评。这就造成一些司法人员将追求某种有利的考评结果作为诉讼活动的目标,而根本不考虑法律程序的整体实施效果,甚至这种有利结果的取得本身就是通过架空和规避法律程序实现的。③陈瑞华:《刑事程序失灵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国法学》2007 年第6 期。目前,虽然上级部门一再强调不能以刑事拘留数、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指标作为业务考评的根据,但是这些指标仍在发挥作用。④印波:《绩效考核指标对刑事程序法治的冲击与反制》,《法学论坛》2021 年第2 期。例如,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退回补充侦查中,检察机关为了规避作出不起诉决定,希望将未达起诉标准的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由其作出撤案处理。但是,公安机关的绩效考核中还包括撤案率这一指标,因而使其同样面临阻力。为此,检察机关可能在明知将案件退补也无法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仍然决定退补,等到两次退补后案件仍不符合起诉标准时,促使公安机关作出撤案决定;或者检察机关在两次退补后,模糊处理案件中的存疑之处,将“带病”案件强行诉到法院。在案件无法继续或者没有必要补充侦查的情况下,这种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规避考核结果的做法,导致补充侦查的补救功能被滥用,有违制度设计初衷。
就“案-件比”指标而言,其注重减少案件程序环节次数,提高办案质效,以期获得更好的社会评价。该指标在规范检察工作的同时,也对侦查工作产生一定影响。目前,补充侦查制度中的“程序倒流”成为影响“案-件比”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减少补充侦查适用次数,检察机关常以自行补充侦查等方法进行代替。⑤池通、赵卿:《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权适用研究》,《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22 年第4 期。《2023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与2018 年相比,2022 年退回补充侦查下降80%,自行补充侦查上升264.6 倍。由此,“案-件比”指标对于减少程序空转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在短时间内引起的数据巨大变动,究竟是司法规律的正常变化,还是考核机制的直接影响呢?显然,在减少诉讼环节的考核机制影响下,补充侦查制度的功能难以正常发挥。一方面,为了避免受到“案-件比”的负面评价,检察人员开始注重案件的全流程引导,在审查起诉阶段要求公安机关同步补充侦查或者自行补充侦查,甚至在侦查阶段根据公安机关的商请提前介入引导侦查。这在提高办案效率,避免程序虚置的同时,可能导致公安司法机关“抓大放小”,即保证案件的定性、量刑建议没有重大错误,但案件细节或部分情节可能存在疏漏,从而出现对新证据收集不全面、固定不到位、审查不准确等问题,使得部分案件补侦效果不甚理想。有的检察人员仅为降低“案-件比”,在没有充足准备的情况下,放弃其他补侦措施,不仅影响案件质量,还可能侵害当事人的救济权利。另一方面,部分检察人员一味追求办案进度,在发挥审查起诉职能的同时,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有所忽视,使得监督职能弱化。可见,统一的、格式化的办案要求和评价标准,往往会使一些疑难复杂案件的办理受到影响。
五、“程序倒流”的困境破解
面对“程序倒流”导致的多重困扰,有关部门可以通过规范补充侦查工作机制、构建补充侦查协同模式和调整办案评价标准等措施,确保这项制度得到规范化、协同化、科学化适用。
(一)规范补充侦查工作机制
一方面,不能将“调取证据材料”“说明取证行为的合法性”等情形,以及提前引导侦查、捕后继续侦查等手段纳入补充侦查制度,以避免该制度出现适用泛化和功能异化。正如有学者认为,对于一些并非关键证据或者补充移送难度不大、花费时间不多的证据,检察机关可以要求公安机关直接补充移送,而不得适用补充侦查制度,以此提高办案效率,促进司法公平正义。①卞建林、李艳玲:《论我国补充侦查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法治现代化研究》2021 年第1 期。由此,可以将补充侦查制度与其他有助于侦查取证的诉讼行为区分开来。
另一方面,应当建立补充侦查制度的“繁简分流”机制。在审查逮捕阶段,补充侦查虽然不会造成程序倒流,但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时候,只有存在进一步查明存疑事实的必要,且仅限于因证据不足情形时才可继续补充侦查。对于不构成犯罪、无社会危险性、不适宜羁押等情形作出的不批准逮捕决定,则不应适用补充侦查。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建立严格的“过滤”机制,慎重启动“第一次退回补充侦查”。如果经过审查,认为在客观上无法补充起诉所需的证据,应当依法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同时,要限制启动“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如果案件中相关证据无法获得,部分定罪量刑事实仍未查清,检察机关应依法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不再退回补充侦查。如果认为案件存在无罪、罪轻的可能性,或者存在程序性违法行为,则可以启动“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重新查清相关事实。在审判阶段,如果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可以判决无罪;如果在事实认定以及法律程序方面可能出现重大错误,可以由检察机关申请补充侦查,且只能将其限定在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新证据这一范围内。总的来说,应当综合考察不同诉讼阶段的具体情况,逐步引导、规范补充侦查制度的适用。
(二)构建补充侦查协同模式
在补充侦查工作中,应明确职责边界,以检察机关为主体,立足建构“以检察为主体”的补充侦查协同模式,将临时性协商变为常态化机制,真正发挥“补充”效果。检警“协同”目标模式的设计,并非要构建单纯的“惩罚犯罪”利益共同体,而是要在兼顾诉讼效率、司法公正与法律监督理念的基础上,查明案件事实,正确定罪量刑,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在需要开展补充侦查的案件中,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应共同弥补案件的证据瑕疵,其共同任务并非为起诉、审判做准备,而是查证犯罪行为的有无,进而适用不同程序。②桂梦美、苏志远:《补充侦查制度协同模式及其实践描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2 期。
在补充侦查协同模式中,应以个案为重心进行功能整合。《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是首份系统规定、明确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监督、制约和配合关系的指导文件,其中涉及配合关系的内容多集中于加强办案衔接、健全对口衔接等过程性事项,以及建立业务研判通报、完善联席会议和提升业务能力等建设性事项,对于具体案件的关注仅限于重大疑难案件。因此,在具体案件中,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应积极建立“补充侦查工作小组”,加强个案中的沟通联络,协调处理相关事宜,既发挥检察机关的庭前主导作用,又促进了公安机关的具体配合,从而在保证侦查机关侦查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将检察机关的补充侦查权作为一种补充性权力加以运用。①谢佑平、万毅:《刑事侦查制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181 页。检察人员应摆脱“卷宗依赖”,发挥亲历优势,听取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等多方主体的意见,还可查明办案人员是否存在侵犯人权、非法取证等违法行为,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公安机关应当坚持侦查主体地位,在开展工作时不仅围绕证据数量,还应关注证据质量,及时对应当收集而未收集的证据以及违法收集的非法证据、瑕疵证据进行处理。
(三)调整办案评价标准
从总体上看,应当建立一套规范补充侦查适用的评价体系。补充侦查制度适用应当遵循基本的诉讼原理和司法规律:对于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以证据完善程度为指标,启用补充侦查制度;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以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为指标,慎用补充侦查制度。补充侦查制度具有多种预设效果,不能因为追求“案-件比”的考核指标而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忽视办案质效。相反,应给予补充侦查这种“非必要”诉讼行为以一定的制度空间。
从具体程序上看,应发挥检察机关的审前主导作用,调整相关评价标准。首先,要将司法业务考评核心指标从计分式考评方法中抽离出来,探索“案-件比”与不起诉率、无罪判决率等其他评价指标的组合运用,充分发挥指标间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功能,有效反映办案活动的数量、质量和效率等情况②林喜芬、周晨:《论检察机关的“案-件比”改革》,《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1 年第3 期。,使补充侦查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要重视个案具体情况。仅凭量化指标的数值不能确定个案程序是否正确,③熊秋红:《“案-件比”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学理观察》,《人民检察》2020 年第9 期。应根据不同案件的特点、规律和难度,灵活设置办案质量评价范围,将是否符合实体情况、程序规范、过程标准等作为考核重点,突出对办案质量的考评,实现惩罚犯罪、控制犯罪与维护司法公正并重。最后,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引入案件质量评查机制,通过对个案中补充侦查制度实际效果的分析,校正部分指标,确保评价指标体系客观、有效地运作,为评价补充侦查过程是否规范、结果是否客观、评价是否科学提供有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