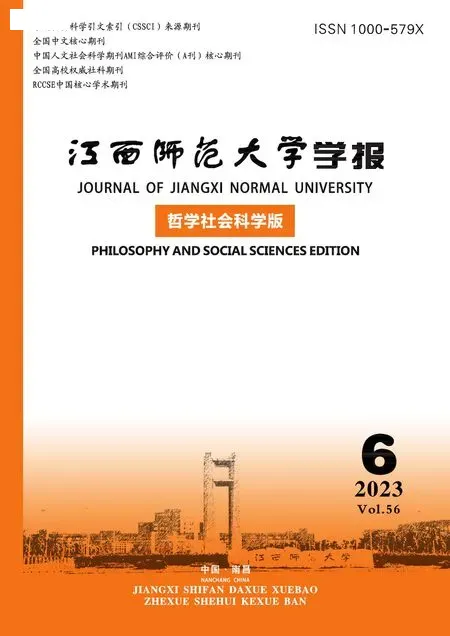近代农村复兴视域下的农村人才培养及其镜鉴
杨树明, 郭晓霞
(1.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2.江西省民政学校,江西 南昌 330043)
中国传统教育的显著特征为“舍士无学”[1]206,严复指出这样的“士”只“治人”,却“养于人”,是劳其心而不劳其力[1]206-207。也就是说在传统教育下的“士”缺乏实践,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人民。晚清以降,随着西方学科分类体系引进与五四运动中民主观念的传播,平民教育运动逐渐兴起。近代农村的衰败又促使知识分子关注农村人才的质量、培养等问题(1)参见:傅葆琛《乡村人才质量的研究与乡村教育的责任》(《师大月刊》1933年第4期)、张宗麟《乡村运动与乡村教育的人才问题》(《中华教育界》1934年第4期)、瞿仲捷《农村建设与农村人才的培养》(《民间》1935年第8期)。。经过努力,20世纪初乡村教育逐渐走向以公学(学堂)为主体、私塾为辅助的新兴教育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村振兴”的提出又让学者反思近代乡村建设的得失,思考如何有效地培养乡村建设人才(2)代表性论文有许怀林等《试论江西近代人才状况的变化及其启示》(《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缪进鸿等主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宣朝庆《地方人才培养与社会重建——民国乡村建设研究中长期轻忽的一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任金帅《“归农运动”与乡村建设人才思想的转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代表性论著有王先明《乡路漫漫:20世纪之中国乡村(1901—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笔者认为从近代农村人才培养体系、农村人才培养制度及农村人才培养实践等方面进行反思,以近代江西为考察中心探讨近代农村人才培养问题,可以为当下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镜鉴。
一、教育是农村复兴之路的基础
20世纪初,列强侵华,政权更迭频繁,社会杌陧动荡,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农村濒临破产,甚至无产可破,农民“即非荒年,以树皮树叶、糠粞、野菜,乃至观音土果腹的,实不在少数”[2]541。有识之士呼吁全国民众行动起来,“救活农村”,“复兴农村”,建设农村。“农村复兴运动”就是在此背景下兴起。晏阳初在定县,高践四在无锡,梁漱溟在邹平,彭禹廷在镇平,沈玄应在东乡,陶行知在晓庄,以“复兴农村”为目标,积极探索乡村建设新路径(3)乡村建设运动、平民或民众教育运动、农村自卫运动、农村合作运动、农业推广运动等,名称虽殊,其目的都在改造农村、复兴农村,故本文统一命名为“农村复兴运动”。。民间的呼吁和初见成效的实践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蔓延,形势风云变幻。为了振兴经济,美国于1933年制定了农业整理法、实业复兴法(4)美国劳工部部长潘金丝的《美国复兴运动的意义》由曹云祥翻译,刊载于1934年《工商管理月刊》第1期与第4期,主要介绍罗斯福“新政”的内容。。为了应对大萧条,日本实行救济农村的政策,以经济振兴为主。与美国、日本相比,日本的入侵让大萧条下的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军事等情况更严峻更恶劣。国破家亡,人民陷入困顿,食不果腹,即使有稳定收入的教育界也“饥啼号寒”(5)各学校经费拮据,时常欠薪。参见磊:《饥啼号寒之教育界》,《时代与教育》1931年第1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如何复兴经济的问题引起国内热烈讨论,政府开始关注乡村建设,并将其提升为国家战略层面。1933年设立全国性经济领导组织——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指导全国的农村复兴工作。同年该委员会着手搜集日本政府各关系机关所发布救济农村的法规,对苏、浙、陕、豫四省的乡村调查全面铺开,1934年对广西、云南一带农村情况调查摸底,同时邀请专家编撰经济复兴方面的著作。1934—1935年,推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丛书”(6)1934年刊发了《江苏省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陕西省农村调查》《河南省农村调查》《中国农业之改进》《日本救济农村法规汇编》等调查报告与相关资料。1935年刊发的有《广西省农村调查》《云南省农村调查》、胡浩川与吴觉农合著的《中国茶叶复兴计划》、徐渊若《日本之农业金融》《农业仓库论》、吴敬敷与徐渊若合著的《农业金融制度论》、中央大学经济资料室编的《田赋附加税调查》。,统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主要的借镜对象是邻国日本,因其“颇见成效,且其国情较与我国相近,非如欧美之相差悬远,故其方法颇足资吾国之借镜”[3]序。然而,日本的农村救济运动仅是“昙花一现”[4],是无法给予面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中国更多经验。中国需要走自己的复兴之路。
20世纪20—30年代,社会活动家和学者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全国进行调查研究,共同探讨如何复兴中国、复兴农村。概括而言主要有四派:以陈翰笙、薛暮桥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农村派,主张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赶走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主张重建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提高农民教育水平;以薛仙舟、伍玉璋、寿勉成等为代表的农村合作派,主张建立现代农业金融体系,促进农业生产运销;以卜凯、戴乐仁为首的农业生产技术改革派,主张改善农业经营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复兴农村”涉及文化、教育、农业、经济、自卫等各方面的工作[5]565,甚至可以说波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建设,方式多样,主要有如下几方面:识字运动、电力灌溉、合作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统制经济、手工业建设、造林运动、教育改造、废除苛捐杂税、农村金融、棉业改进、荒地清理、土地政策、农村自治、租佃问题、交通建设、农村副业、农具改良、发展林业、农村水利等。1932年,《申报月刊》第4期刊发了叶恭绰、王志莘、俞庆棠等人关于“中国农村衰落的原因和救济方法”的讨论文章,其中叶恭绰、俞庆棠、周宪文等人认为提高农民的知识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此前,有人认为只有人通过知识自救,达到经济自救,最后才有能力救中国,如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派”、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派”、以陶行知为代表的“教育改进派”等。当时,教育并非首要问题。如共产党人孙冶方认为:“很多人以为中国农业经济的衰退原因是技术落后、资本缺乏、农民知识缺乏等。其实这都是农业经济衰退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残余的束缚。”[6]9又如杨东莼认为农村衰败的原因有七点:帝国主义的侵略、高额地租、苛捐杂税、高利贷、鸦片、战争与匪患、天灾。据此,他认为复兴的方法有下面几点:解除帝国主义的束缚;平均地权;减轻地租、整理田赋与废除苛杂;流通农村金融;发展合作事业;农业改良;普及农村教育[2]541-544。总而言之,教育虽然不是20世纪30年代的首要问题,但它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因为无论哪种学派以何种方式建设农村,都会面临着农民知识缺乏这一实际问题。马克思曾说:“创造这一切、拥有着一切并为这一切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7]118要建设乡村复兴乡村,提高农民的民主知识、科学知识,扫除文盲,就离不开根植于乡村的农村人才。
近代农村人才短缺,亟须培养大量能够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又能实践的农村人才。自同文馆开启了西方学科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后,新式教育在中国得到蓬勃发展,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具有科学知识的人才。但是它注重城市人才的培养,与乡村社会需求存在严重脱节,产生不良影响,正如梁漱溟所言:“三十年间新式教育的结果,就是一批一批地将农村人家子弟诱之驱之于都市而不返。……故新式教育于乡村曾无所开益,而转促其枯落破坏。”[8]678据陶行知统计,20世纪初叶,中国城乡教育分化明显,乡村学校仅占全国学校总数的10%[9]167。不仅如此,城乡人才也出现明显分流,乡村人才大量流向城市成为一种趋势,造成了乡村“悬空”[10]60的现状。江西尤为严重。据1936年《江西农村社会调查》可知,江西农民离村占总人口数的4.49%,其中19岁至45岁的青壮年离村人数占离村总人数的65.29%[11]67-68。近代文盲率高,农民文化水平低。如1934年江西省莲花县 “全县师范毕业生仅余三名”[12]。1935年南丰县尧村服务区“完全小学毕业者,亦只三四人”[13]。向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宣传工业化改革,让他们较快掌握现代化机械生产和改良的农业技术的任务,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
江西的农村复兴是近代中国农村复兴运动重要目标之一,孙科曾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上说:“救济农村,为物力人材关系,多数意见将由江西入手,江西急待复兴。”[14]其原因一是江西的贫困现状,二是来自“竞争”的压力。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推行农村革命,传播文化知识,培养农村人才,鼓励农民主动参与农村建设:1.中国共产党重视教育的先导功能,切实举办农村补习学校,对农民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提升农民的文化水平。扫盲组织以方便群众学习为前提,采取夜校、半日学校、识字班、识字组、识字所等诸多形式传播知识。到1932年,苏区共成立识字委员会2744个,识字俱乐部712个,识字小组19812个,有87916人达到了当时脱盲毕业标准[15]。脱盲率的提高,又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的销量。如《红色中华》发行量达40000份(最初是3000份),《青年实话》发行28000份,《斗争》杂志发行27000份,《红星》发行17300份[16]336。这些党报党刊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苏维埃政权、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发挥了巨大作用。2.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使其掌握一技之能。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开办农事试验场,开办中央农业学校,培养农业干部及农业技术人才[16]300。3.推广列宁小学。凡年满6岁至15岁的贫苦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以上措施为苏区农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人力基础,促进了农业生产。
而江西省府则采取“政教合一、服务农村”人才培养模式相抗衡:借助媒体宣传造势,补助农村人才培养经费;建立全国最大农业科研机构,蓄积农村科技人才;开展乡村师范实施区及农村服务区建设,培养农村实用性人才。然而,江西省政府对农村人才培养多停留在“口号”层面,突出“政治”宣传属性,致使人才培养的实际效果较差,引起社会不满。有识之士,如全国经济委员会驻江西办事处张福良与江西农村改进社王枕心、苏邨圃等,在农村实践中突破“口号”限制,深入农村,在江西农村服务区、乡村实验区及农业院开展农村人才的培训与训练,为江西培养了不少农村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农村人才大多留在江西,继续从事农村建设。其中王枕心尤为突出,他担任农业部宣传处专员等职,主动为新中国的农村建设贡献力量。
二、多层次的农村人才培养体系在近代已具雏形
农村人才是指在农村劳动与生活,能为农民文化传播、农民技能提升、农村社会管理提供服务的人才。从理论到实践,江西在培养农村人才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已具雏形。主要以义务教育方式培养在校生培养农村建设基础性人才,以实用技能培训方式培养农村手工业人才造就农村建设的骨干型人才,以行政改革与组训方式培训地方干部培养农村领袖型人才,以短期集训方式培养农村妇女拓展农村建设人才范围,以延揽人才方式吸收为服务农村的高端科研管理人才。需要明确的是,这种体系的形成并非由政府有计划的设计,而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
(一)以义务教育的方式培养农村建设人才
农村建设基础性力量主要来自接受了小学、初中教育的农村人才。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当时只有“省的教育”而无“县以下的教育”[17]1,不能满足农村建设。如1931年,江西初等教育学校只有6000余所,学生不到25万人[17]3。
普及义务教育是加大基础性人才培养的有效举措。受到中央苏区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的影响,1934年江西创立保学制度,就近按保设学,运用保甲组织的力量来实施国民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全省普设“保学教育”,分为10大保教区,以行政区为单位,联络进行,严格订定各区教育经费,推广“平教”,提倡“健身”“卫生”等普遍中心工作[18]。加强保学教育后,学校上升到8641所,学生达到375045人[17]3。1935年采取“管教养卫”连锁方式培养学生[19],全省推行保立小学。
普及义务教育,需要大量的经费和师资。以当时教育界普遍欠薪的情况来看,当局是没有经济能力办义务教育。那么教育经费从何而来?从文献来看,主要靠公产和族产。如江西保学人才培养的试办点丰城县就是采用公产解决问题。丰城县采取合理调整食盐公卖、整理公产的方式,共得13万元,解决了全县803个保学的经费[20]。江西第12行政区计划拨付各县祠堂庙宇等公产为教育专款[21]。江西第8行政区以族产办学[22]1-7。至于师资则通过开办保学教师训练班方式培养。1935—1936年江西在南昌设立各县县立小学教师训练班,共4期,主要对象是各县立小学现任教师,训练时间为3个月。这些教师充任各县保立小学教学示范干部人员。为了扩充教师队伍,自1937年起,各县中心小学教师改调训为招考,受训期为6个月。
此外,为了保证保学开设和推广,各种社会组织也被调动起来。如江西第五行政区规定:耆老会指导全保超过45周岁民众的教育;户主会指导全保各户户主的教育;妇女会指导全保各户主妇及壮年妇女的教育;壮丁会指导20—45岁壮丁的教育;青年会指导15—19岁青年的教育;儿童会指导6—15岁儿童教育(7)《江西省第五行政区普设保学暂行办法》,九江市档案馆藏,卷宗号1007-001-026-008,1935年7月3日。。为了尽快提高覆盖面积,保学学级编制以年龄区分:儿童班采复式编制,6—10岁者4年毕业,10—15岁者2年毕业,尽先容纳2年毕业者;成人班分团编制,6个月毕业并得另设妇女班。
在保学政策的推动下,近代江西农村在校生人才培养数量得到发展。以江西新干县保学为例,到1935年3月已成立保学60所,其中第四区第二保联设立保学师范区1所、三湖实验区开办实验小学1所[23]。1936年,江西保学实施就地筹款设学,每保都有保学,分设儿童班及成人班。一年来已设12000余保学,接收儿童29万,成人10余万[24]。
保学教育的开展有利于减少农村的文盲率,促进地方教育发展。
(二)开展实用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建设骨干型人才成长
“抑文向实”是教育理念在近代的转向,人才培养趋向适应现实需求。如安义县万家埠设立农村实用学校,其教学采用“教学用”三者合一办法,达到实用实学为原则[25]81,培养改进农村的基层干部和农村技能型人才。同时,为促进江西农村传统手工业等特色产业的“复兴”,江西开始有意识地开展百业教育。
百业教育是从事农工商各种职业人员的补习教育,是以增进职业技能、改善生活为目标的教育。1936年江西正式实施百业教育,由省建设厅、省立职业学校、省立工厂等组织百业教育委员会,从事调查设计指导推行工作。实施原则是“使有业者精业,使已受职业训练的失业青年归业”,参加教育者可以得到精神或物质上的补助[26]。百业教育首先在南昌市试办,由教育委员会具体实施。1937年5月举办过15个补习班,每个补习班时间3—6个月不等,涉及理发业、藤器业、木器业等14个行业,接受补习人数为1751人[27]。百业教育实施3年后共举办省会百业补习班27班,各县百业补习班14班,各班受教人数2508人,各地函授人数20人等[28]。5年后,因抗战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受教人数减少,各县举办事业补习班42所,涉及8个行业,受教者只1681人[29]。
百业教育对农村手工业者提高技艺、提高出品精良度等有所帮助。江西省试行的百业教育,取得较好社会声誉,影响较大,后由国民政府采纳,通行各省仿效[30]。然而,江西农村手工业人才培养仍遇到不少困难,如技能型师资严重不足,受教人员参与积极性不高,政府财力供给严重不足等,终以人才、经济及其他方面之关系,尚未能发挥百业教育之实效[31]15。
(三)以行政改革与培训方式培养农村领袖型人才
农村建设中农村领袖的作用不可忽视。这时期的农村领袖主要是农村保甲长和地方管理人员。前者是连接政府与农民的桥梁。然而近代“绅士名流阶层发生裂变并与农村疏离”[32]57,他们逐渐隐退。此时,农村领袖出现劣化趋势,乡村失序时有发生。不少保甲长贪征苛索、鱼肉乡民,与农民关系紧张。为缓和两者间的矛盾冲突,地方政府整理保甲,设立保甲长训练班,并对保甲长的行为进行一定约束。以江西农村复兴试验基地万家埠实验区为例,其保甲长训练班的培训内容有合作训练、村容整理、民众组训等。培训书目有《国际情报史》《警察权之研究》《胡林翼军政语录》《新生活运动纲要》《公务人员工作纲领》等。江西农村服务区开办后多次举办乡村建设讲习会,一年之内受训保甲长达1500余人[33]。从传授情报、政务等培训内容可以看出,提升其管理农村的能力、让其掌握农村情报,实现对农村社会的管控训练的主要目标。
除保甲长之外,地方管理人员也承担着农村领袖的职责。
因县政人才缺乏、机关组织构成简单,寥寥几人难以应付日益复杂的现代工作强度。如1934年一个县政府每天起码要接受20—30个高级机关命令,而区的组织不过5—6人,政府人员往往忙得头昏眼花。为了解决县政人才的不足,江西主要采取短期训练的方法快速储备县政人才。至1934年共举办6期县政研讨会,参与研究者344人,每期研究期限1—3个月,是为江西省人才训练工作之滥觞[34]2。此外,江西省府开始整饬县政,培植干部。江西省就原有县政研究会人员,分别班期训练,设立全省性县政人员训练机构——县政人员训练所(以下简称县训所)。县训所设主任与副主任各1人,由省主席与民政厅长分别兼任。下设教育长1人,办理全所一切教育行政事宜,设教务员2人,分掌军事、政治、教育设计及考绩事宜。另设队长、队附与区长训练班,训练项目包括精神训话、县政研究、问题讨论与军事训练4种。县训所首期学员原定300人,分县长、县佐、区长等四队,实际247人[35]。1935年计办3期,受训人数中,官长类共28人,学员类财务班共75人,教建班共148人,区政班共426人[36]68。1935—1937年间共开设6期,训练人才1375人,其中县长149人、县佐153人、教建人员209人、区政人员共864人,内计区长274人、区员590人[34]3。
这段时期正是国民政府县政改革时期。地方行政人才的训练,有助于提升江西县政人员的管理理论水平,客观上为江西农村复兴运动工作输送了一批农村管理人才。
(四)解放妇女,鼓励农村妇女在农村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经过五四新文化的鼓荡,中国妇女的自立精神得到提升。而技能教育和文化教育又让中国妇女获得生存能力和知识文化,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有一席之地。可以说妇女解放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其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保障。这一时期,江西妇女教育表现优秀。至1932年,江西省兴办4所省立完全女子中学、2所教会女子中学、1所省立助产学校、1所省立女子职业学校,江西中等学校女子人数约5000人[37]。她们经过训练后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或一技之长,成为江西建设尤其是农村建设的人才。中央苏区非常重视妇女知识和技能教育,明确提出“各级的文化部都应设立妇女半日学校、组织妇女识字班、可办家庭临时训练班、田间流动识字班,教员由政府及各地学校教员及群众团体的干部来担任”[38]244的具体措施。新生活运动兴起后,宋美龄也认识到妇女的作用,她认为时代新女性应是“有知识、有魄力、有志气、有才干、有目标”[39]405的女性。在宋美龄的推动下,作为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江西成立了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从《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组织大纲》可以知道,对农村妇女提供指导与培训的项目集中在家政类、生计类工作,目的是使之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农村女性。江西省农业院积极响应,开设农村妇女学校及农村合作工厂,在农事、家事、副业、社会、卫生各方面对妇女进行教育,帮助妇女提高经济地位[40]。而在江西省农村服务区,则开展家政训练并组建妇女组织,并对农村妇女传授缝纫、刺绣工艺技巧。这些女性手工业人才的培养与储备,为全面抗战时期吉安、赣县义民工厂的建立提供了人才储备[41]120。此外,江西省妇指处对县高级妇工干部开展训练,并举办工艺训练班。各县指处也对妇女进行训练,主要培养乡镇、保、甲三级妇女干部,受训干部为64987人[42]111。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其经济地位和社会政治地位的提升。
(五)延揽高端人才,做好服务农村的智库
江西积极利用各种人际网延揽人才。1931年底熊式辉主政江西后,积极利用自身人际网,延揽人才,标榜要集中江西各方面力量来建设“新江西”,实现“赣人治赣”的主张。他以新政学系代表自居,对江西新旧各派在政治上较知名且有代表性的上层人物进行延揽。如1933年邀请王枕心等人贡献建设“新江西”的意见。经过熊式辉的举荐与争取,当时江西引进了一批国内知名的高级人才。尤其是1933年熊式辉确定从经济着手从事农村复兴工作后,聘请许多经济专门人才,设置江西省经济委员会作为经济复兴领导组织。他多次邀请萧纯锦担纲经济委员会主任;聘请程时煃为江西省教育厅长;聘请音乐家程懋筠担任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聘请董时进为江西省农业院院长,从事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邀请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雷洁琼来赣开办家政学校[43]185;聘请熊芷来南昌参与主持江西省城乡妇女工作等。以上人才为赣效力,服务地方建设多年,为江西经济社会复兴提供一定的人才保障。
经过努力,江西人才引进取得了一定成绩。如,1934年,江西省农业院创建之初,全院引进科技人员59人,其中归国留学人员21人,技术力量之雄厚,规模之大,堪称全国第一[44]22。截至1936年10月,教育部统计全国学术机关共45家,其中江西4家,全国排名第三。研究人员集中在地质、陶业、农业领域。具体而言,江西地质矿业调查所有13人,江西陶业管理局有11人,江西省立农业院有120人[45]。这些人才为近代江西钨矿、稀土、陶瓷、水稻技术等科技进步做出了努力,如邹如圭成功研制出低压电瓷,结束了中国低压电瓷靠进口的历史[46]352。人才的引进也带动了江西科技人才持续发展。
经过本土培训与人才引进,江西农村复兴运动所需各类人才数量得到一定的满足,人才缺口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尽管近代农村人才培养仍有诸多不足,但其体系化的初步形成昭示近代中国农村人才出现职业化的倾向。其中,农业技术推广员、家畜经纪人、家畜防疫员、农村合作人员、卫生技术员、农产检验员、农村土地调查员、土地航空测绘员等专业性人才在近代涌现表明中国农村人才走向职业化与专门化,推动农村技能人才培养制度的深化。
三、重实际的农村技能人才培养制度的设计与推行
农村教育是培养农村人才的必然选择,教育培训与政策扶持是农村技能人才建设的常规手段。时人认为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人才自然会成长起来。人才培养遵循“三比”(快比慢好、多比少好、有比无好)[47]24政策。也就是先求数量再求质量,这个政策在人才洼地的时代是可行和必要的。
为了实现普及教育的目标,江西省教育厅对农村人才培养制度进行了设计。
1.改变传统的科举应试的人才教育观念,制定面向农村的人才培养方针。近代农村衰败的现实,促使江西改变人才培养模式,欲达成“在最短时间内,发展农村教育,使适应农业环境,提倡生产劳动,实现教育职业化”[48]的目标。1933年2月江西省颁布《江西教育行政方针十条》,明确提出特别注重科学教育、生产教育及乡村教育。6月江西省务会议制定《二十二年度改进教育实施方案》,确定教育应以培养民族精神为首要,教育应社会化、科学化与生产化,特重身体锻炼与人格修养三原则,强调教养互动,教育应为生产服务。8月,为推动“教”“养”融合,教育厅通过《江西推行生产教育方案》,强调培养农村技能实用型人才,加快农村经济复兴。
2.农村人才培养内容向实用性、针对性倾斜。1931年底江西推出“教养卫”策略。“教”即人才培养工作是优先着手点,“教”的内容应“注重实用”。比如,针对性、实用性较强的农村社会调查、农村手工业技能、农村合作等课程就是应时代之需而设立的。
在上述人才培养理念的引领下,江西近代农村人才培养由知识理论型向实际技能型转向。在建设乡村中,急需农村合作人员、土地测量人员、农业建设人员等农村技能人才,这时短平快的培训方式无疑成为一时之选。如1931年江西省农村合作指导员训练所成立,其目的是以短期训练方式培养农村合作指导人员。同年,政府开办豫鄂皖赣四省农村合作指导员训练所,共收学员339人,其中录取江西籍学员124名。1934年后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多次分层次举办这类培训,如1934年举办为时2个月的助理员讲习会,招收中学毕业生,结业78人。1936年办理为时3个月的合作指导员短期训练班,培养98人。1937年,受训期为3个月,甲级结业58人,任用为指导人员;乙级结业81人,任用为助理员[34]4。又如土地整理工作需要航空测量专门人员。1934年起江西开始办理土地测量人员训练班,计3期共150人,均分发航空测量队分队工作[34]5。江西省农业院为了推动科学建设农村,主持办理农业建设人员训练班,从1936年起,分3期开始训练家畜防疫员,每期时长3个月,82人结业后均派充农业院任家畜员[34]4。
重实际的农村技能人才培养制度的制定,是回应江西农村人才匮乏的现实需求。此项制度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村建设的急需人才。但培训农村各类人才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一是人才数量仍存在较大的缺口。如,到1936年,江西全省接受中等教育的仅为14402人[50],与江西全省人口约1500万相比,比例仍旧很低;二是乡村人才培养教育虽然倾向实用性,但是更多的仍是理论上的说教,“不少农村教师完全没有农民魂和农业技术知识”[51]8,造成与乡村社会实际存在较大脱节;三是采用短平快方式培训的人才的质量远远达不到乡村需要。这些不足表明近代江西乡村建设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四、近代农村人才培养的历史镜鉴
近代以来,实现农村复兴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中国共产党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模式,大力开展根据地建设,为苏区乡村经济复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开展经济制度的变革,如开展土地革命、力行合作社经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苏区农村经济进步;面对苏区人才不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及时培养苏区农村人才,运用识字扫盲、技能培训、习性培养、信念教育等形式,提升农民素养。苏区农村人才数量的增加为近代农村复兴提供人才保障。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在江西推行农村复兴运动。面对列宁主义学说深得民心,青年儿童“只知有苏维埃,不知有中华民国”[51]239的现实,政府官员竭力主张:消除共产主义学说在江西农村的影响力,强化三民主义学说的权威地位。随后,政府倡导“新生活运动”,为江西各地制定特殊文化政策,重建文化控制体系,以期争取民心。一场以争取民心为实质的改良运动——农村复兴运动在江西出现。
民心的争取离不开人才培养这一重要环节。江西省府推行农村保学教育,为农村提供众多基础性人才;实施技能型人才教育推动农村经济的救济与复苏;实施管理型人才教育有助于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对农村妇女进行知识教育、技能教育,推动妇女解放。延揽社会高端人才到江西农村服务区、乡村师范实验区、农村改进实验区工作,部分补充了农村紧缺人才、高端人才。多层次农村人才的现代培养模式已具雏形,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农村人才基数,提升了农村建设者与管理者的技能,以适应近代农业生产、农村管理的需要,客观上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性发展。
回顾近代农村复兴视域下的农村人才培养历史,农村人才的重要性在当时的学界已成为共识。近代农村人才培养实际效果不佳,农村复兴的任务无法实现的重要原因,是近代中国最迫切要解决的现实难题是驱赶外国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近代的农村复兴运动必然呈现“复而不兴”的结局。
今天,中国人民正在朝乡村振兴的目标奋勇前行。总结近代农村人才培养历史,或许可以为当下乡村振兴运动的人才建设提供些微历史镜鉴:一、农村人才建设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政策扶持、资金投入、技术支持等协同配合。为此,农村人才建设不能就人才谈人才,应将之纳入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之中。二是重视农村领袖的作用,应注重培养热心农村建设的人士,加强其情感教育和信念教育,让其乐意且有信心建设好管理好农村。三是要进一步重视妇女教育,尤其是对农村妇女进行技能教育使其获得职业技能,从而能独立生存或者为家庭增加一份经济来源。她们是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52]。四是重视农村人才技能培训,可通过系统的职业技能训练,提高其适应时代需要的工作技能,鼓励他们“归业”或再就业。五是应尊重农村人才的自由流动。与此同时,要在保障农村人才政治地位的基础上,强化各级人才支撑,努力优化人才培养和引进的措施[53],实施激励政策,让扎根农村、服务农村的人才成为村落文化共同体,产生“生斯长斯,爱斯护斯”的归属感与责任感。
总之,实现乡村振兴离不开强有力的人才支撑,离不开农村人才队伍的发展和壮大,注重和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势在必行。这也是学者普遍认为的,培养农村内生性人才作为农村复兴的主体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