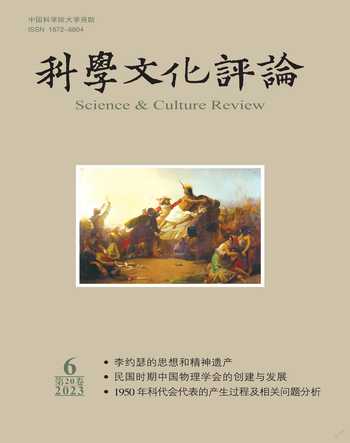1950年科代会代表的产生过程及相关问题分析



摘 要 1949—1950年间,科代筹委会在推选科代会代表的过程中,抛开原有的学会组织,试图在开展自然科学工作者大规模登记的基础上进行普选。但限于诸多客观条件,大多数地区进展并不理想,最终科代筹委会不得不求助于各地党政机关,才完成任务。通过考察科代会代表产生的过程,分析这一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重新评价原有学会的作用和经验。
关键词 科代会 科代筹委会 推选代表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23-11-10
作者简介:王传超,1981年生,山东菏泽人,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Email: ccw32@163.com。
作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开篇,1950年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以下简称“科代会”)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它通过为期一年多的筹备工作,将全国科学工作者组织起来为国家建设服务。关于它的发起、筹备、召开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对新中国科学发展方针的确立、对科技团体组织形式的设计等问题,此前学者已有系统回顾[1],本文不再赘述。目前尚有一些细节问题值得讨论,如科代会代表产生的过程,代表的地域、学科、性别、年龄等方面的情况,与之前“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科代筹委会”)委员产生过程相比有何不同,这些情况对我们今天又有哪些启示,等等。剖析这些问题,可以深化我们对当时中国科学发展状况的认识,探讨当时对科学发展方针所做探索的得失。
一 科代会代表推选的准备工作
1949年5月,为团结教育科技工作者,有组织有领导地发展科技事业,并邀请科技界派代表參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贡献,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等四个科学团体正式发起筹备全国科学会议,随后推选筹备委员会委员,并将“决定出席会议之人数及分配原则”[2]列为筹委会任务。
在酝酿过程中,尹赞勋等五位筹备委员曾就筹备期间需要讨论的问题开列了一份清单,其中关于科代会代表产生的方式列出了以下几种供讨论:(1)由政府的全国性的科学中心机构聘请;(2)由全国科学工作者的新的总组织系统选举;(3)由全国综合性的科学社团推选;(4)由全国各专门科学学会推选;(5)由全国各科学机关及有关部门推选;(6)由以上两种或两种以上方式产生[3]。7月13日,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京召开,科代筹委会正式定名,并成立了常务委员会(按照当时习惯,以下简称“总会”)。在以学科分组的讨论当中,理、工、农、医各组普遍支持以普选方式产生代表[4]。
其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关于代表名额总数,相关讨论以800为基础展开,除工组想要增加人数以外(可能由于工组从业人员数量大),其他三组无意见;第二,各组普遍支持普选,反对或主张限制由旧有专门学会推举代表;第三,强调在登记、选举工作中重视青年、妇女等群体。
科代筹委会“代表产生原则”工作组于7月16日开会讨论了《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产生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7月18日筹委会大会正式通过)。《条例》对代表及选举人的资格做出了规定:“凡符合下列各项条件并愿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者,均得参加选举及被选举为出席大会代表。甲、在自然科学的任一部门内有学理的素养者。乙、现在从事自然科学的工作者,或过去曾从事自然科学工作5年以上者。”[5]但这一规定过于笼统,给之后的工作带来大量问题,主要是对“有学理的素养”缺少明确、可操作的说明,导致各地自行其是,将标准放得比较宽。8月17日,科代筹委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产生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对条例中涉及的术语做出了解释,其中“学理素养”是指“对任一专门科学的基本学理有超出普通经验水平以上的了解,并能负责应用或继续研究”。这一说法其实仍然很笼统,不过《细则》中还举例说明了哪些人算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其中包括“普通中等学校或中等职业学校的自然科学教员”和医院中的“护士、助产士”[6]。
关于代表名额,《条例》暂定为700名,其中各地区代表500名,解放军代表100名,团体代表20名(由青联、妇联、总工会、农会分别推举5名,须符合基本资格条件),其他代表80名(由总会协商推举或聘请)。关于具体产生办法,除解放军代表及团体代表各由其单位自定外,《条例》对各地区代表的产生程序规划为:(1)总会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地区,分别组织分会;(2)分会根据总会相关规定,于1949年10月底前完成对本地区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调查、登记、审核;(3)分会根据登记结果,结合当地情况,拟订本区代表选举办法及名额分配比例,与登记结果一并汇报总会;(4)总会根据上述汇报,加以复核,决定各地区的代表名额及分配比例;(5)分会按照总会规定的代表名额及分配比例,进行选举,产生大会代表,并报总会;(6)如因当地特殊情形,选举进行困难,经总会核准,分会可以协商提名方式产生部分或全部代表[5]。
科代筹委会全体会议闭幕后,各项工作随即开展起来。总会组织部做了分区规划,准备在全国(包括未解放区)设立23个分会,但由于各地情况的差异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实际成立的分会并没有那么多。到1949年11月以前,有上海、杭州、东北、武汉、济南、山西、石家庄、天津、西北、郑州、长沙总会在北平、南京也指定了召集人组建分会,但前者由于筹备阶段在组织及工作方向上存在疑难而未能成立,后者因召集人工作变动,在1949年11月底前限于停顿,直到总会另行指定召集人后才启动相关工作。成立的各分会命名方式不统一,大多以城市命名,但负责地域则不限于本市,如石家庄分会负责“冀中、冀南及平原省”,天津分会负责“天津、唐山、冀东地区”等等。成立了分会。大多将自然科学工作者登记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到1949年底,大多数分会在初步完成登记工作后,一边开展补充登记,一边进行审核工作。但是因为登记标准中“学理素养”方面的要求不够清晰、难以量化,而总会对于下一步科学组织的定位及目标任务缺乏共识,导致审核工作陷入停顿。
1950年4月,吴玉章在总会第10次会议上作报告时,明确了日后科学团体的主要任务在于配合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工作,其主要组织形式将是与政府有关部门密切结合的专门性学术研究团体,而不是以个体成员为主的工会性组织。这就要求下一步的工作要更强调学术性:在自然科学工作者登记表的审核中,明确要求“专科以上(指大学程度)学校毕业,或相当于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程度”;在代表人数方面,也由原定的700降到450(暂定) [7]。
1950年5月,各分会陆续将审核后的登记名单报送总会复审。同时,总会组织部也对代表名额的分配和产生的方式进行了研究,制订了《条例》的实施细则补充部分,其中对各地代表的产生办法进行了详细说明(表1)。
6月11日,总会召开第12次会议,吴玉章在报告中请各地分会加速登记工作并汇报总会审核,同时强调:“有好些地方没有分会,没有举办登记,所以代表产生不能全部用选举方式,但要照顾到各方面如青年的科学家与妇女等。”[8]事实上,按照总会的指示,登记工作不再与推选科代会代表挂钩,大多数地区(即便是已设分会并举办登记的地区)不再以普选方式推举代表,而是求助于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在其指导或帮助下推举代表;有些地区甚至直接由当地军政委员会代办代表产生事宜。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体现了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和科技事业要为政府的工作服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多数地区的科代筹备工作很不完善,缺乏举行普选的基础条件,只能求助于党政机关。6月11日的会上还修正通过了各地区代表名额分配办法(表2)。
这一分配计划是总会常委们讨论后确定的。此时各地登记人数尚未完全报送总会,因此名额分配并未与登记情况挂钩。但事后来看,各地得到的指标与各自科工人数在全国的占比情况相差较多,如上海通过复审的科工人数占全国登记总数的近三成,而代表名额只是全部登记地区所占指标(261)的17.24%;与之相反,东北上报的科工登记人数不到上海的六成,获得的名额却比上海要多15人。这可能是东北作为老解放区的政治地位和作为工业基地的经济地位决定的。
除东北外,尽管从登记科工人数的对比上来看,其他各地区获得的名额数也毫无规律可言,但如果考察各地区的高端研究人才,会发现各地所获名额与其科学地位基本相称。按照科代筹委会的统计[9],参与登记的“研究院毕业”人才共有747人,各地排名及人数依次为上海(225)、北京(146)、天津(86)、武汉(60)、中央科学领导机关(54)、南京(47)、东北(35)、杭州(31)、济南(28)、长沙(22)、西北(7)、山西(6)、郑州(0),除少数例外除长沙分会所获名额偏少外,东北、西北名额偏多。东北有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而西北则因为上报的登记人数只包括西安、银川两地,甘肃、青海、新疆以及陕西部分地区未包括在内。,各地代表数额基本与此相称。这说明常委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对于国内科研力量的分布有比较全面的估计。
除各地区这335个名额外,总会组织部在7月9日第13次常委会议上报告:中央直属机构代表名额为35人,其中文委会7人(内中卫生部2人,文化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出版总署、新闻总署各1人)、财委会28人,其代表产生办法由各该会人事处自行处理;军委会代表名额共计70人,包括各野战军及军委直属机构[8]。代表名额总计为440人。
总结科代筹委会为推选代表所做的准备,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其一、在旧科技社团遭到批判、亟需整改的背景下,科代筹委会抛弃了通过旧有社团推举科代会代表的途径,而是探索先进行科学工作者登记,然后在登记基础上进行普选的新方式。
其二、由于对科学工作者的定义过于宽泛,各地登记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难以把握的问题,导致工作进展缓慢,加上对即将成立的科技社团的定位存在分歧,因此代表推选工作被搁置了一段时间。上述问题解决后,因时间仓促,大多数地区来不及组织普选,且已经确定了科技界要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方针,总会指示代表推选工作要更多地依靠地方党政机关。
其三、尽管科代会以科技界为主,但代表的推选也受到当时国家大政方针的影响,不能只考虑候选人在科技界的影响。比如,考虑到男女平等和培养后备人才的需求,总会方面要求各地推选代表时要照顾青年和女性。
二 科代会代表的产生
代表名额分配办法出台后,各地迅速行动,制订代表推選方案。各地在选举代表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即总会常委是否具有直接参会资格、是否占用地方名额。在收到南京分会的请示后,总会组织部于1950年7月11日通知各分会:“总会顷决定全体总会常务委员为出席大会当然代表,各地方产生代表时可不必再选总会常委。”[10]
负责地域比较广的分会还存在名额二次分配的问题,比如济南分会的10个名额,经各方面的考虑协商,最终定下来的分配方案是:济南4名、青岛4名、徐州1名、淄博和潍坊共享1名。对这一方案,青岛支会在写给总会的报告中说:“在科工的人数比例上,青岛的代表名额是少了些,但是为了照顾全省,我们青岛支会同意这样的分配。”[11]
各地推选代表的方式不尽相同,甚至有些地方本身就采用了多种方式,但大多是在当地党政机关指导下进行的。以青岛为例,4名代表中,有1名由军管会直接选派,剩下3名则由选举产生,具体选举方法是:以普选方式推选142名代表,和青岛支会的45位筹备委员一起,召开青岛市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于会上选出3位代表[11]。
杭州分会采取了以下方式:先由筹委会常委与浙江省文教厅等进行协商、研究,确定10个代表名额的分配(结果为理组3、工组3、农组2、医组2);次由筹委会各组提出候选人名单,邀请筹委以外一倍半的人士召开扩大会议,协商产生代表;然后再由常委与省领导机构共同研究,定下初步名单意见,并采取了照顾妇女代表的措施;最后再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代表名单[11]。
长沙分会先召集全市与科学工作相关的53家单位,举行联络会议,协商代表产生办法及名额分配比例,让各单位照比例普选出170位代表,召开长沙区域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选出出席科代会的5名代表。7月15日,分会得到省文教厅转来的通知,代表名额增至8名,遂研讨再产生3名代表的方法[11]。
北京情况特殊,由于分会迟迟未能建立,该地区的登记及代表选举都是由总会组织部代办的。6月11日,总会第12次常委会议通过了由20人组成的北京区代表候选人提名委员会(理、工、农、医每组5人,提名委员为当然候选人),在开展登记的同时发放选票,以普选方式选举代表。共计发出选票2933张,收回73%的选票,产生代表20人(表3)[8]。
据上表所示,北京选出的代表绝大多数为资历较深的正副教授或研究员,且全部为男性,在选举过程中主要关注候选人在科学界的影响。
同样采用普选方式,上海的工作虽然细致周到,但结果却与北京大不一样。6月初,上海分会就开始筹备代表产生工作,举行了数次全体筹委会、常委会和候选人提名小组会议,反复商讨代表名额问题、代表产生方式问题、候选人数目和具体人选问题,以及如何遵照总会指示适当照顾青年、妇女,并兼顾理工农医各组间的相对均衡分布。相关讨论结果随时报送总会核示。总会确定上海名额为45人时,也同意上海方面采取普选方式,由登记合格之选举人(即参加前期登记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科代会代表。
上海分会候选人提名小组经反复磋商研讨,提出了180人的候选人名单,报分会常委会修正通过,复经全体筹委会讨论修正,期间还向政府文教等有关部门征询意见,最终形成了包含180名候选人的选举票,发放给选举人(但选举人可在候选人外另选自己认为合适的代表)。180名候选人的分布情况见表4。上海分会通过总会复审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登记人数为10049人,其中理组1223人、工组5583人、农组575人、医组2668人(各组女性依次为252人、77人、65人、946人),各组候选人数及其中的女性人数是参照登记总人数,并在学科、性别方面加以平衡调整的结果。
合计180人,女性13人60岁以上16人,30岁以下9人有留学经历者120人;有博士学位者53人医组的博士学位有两种,一种是医学博士(相当于后来的八年制医学本科),另一种是哲学博士(或医学科学博士)。本表对此未作区分。
为遵照总会指示,适当照顾青年、妇女及各学科间的平衡分布,分会在“选举注意事项”中规定:“选举人于下列180名候选人中圈选45人……理工农医各组每组必须至少圈选6人。被选人总数多于45名者,作为废票;但少于45名者,仍属有效。选举时应适当照顾青年、妇女。”普选工作始于7月11日,7月20日截止,共发出选票9000余张,收回4000张[8]。录取规则为开票后先依理、工、农、医四组最高票数每组录取6名,其余21位按票数多少、不按学科而依次录取。实际上,7月21日开票后,因种种原因对结果进行了一些微调据投票结果,理组的彭慧云(女,1466票)、庄长恭(785票),工组的钱正英(女,1017票),农组的何康(1493票)、钱崇澍(1228票)、周宗璜(1099票),医组的崔义田(1342票)均得高票而未入代表之列。其原因不一而足,有的可能是因為工作调动离开上海(如钱崇澍),有些可能是因工作原因难以分身(如崔义田)。,最终选出代表的情况见表5。
共16人,其中女性6人60岁以上3人, 30岁以下0人有留学经历者10人;有博士学位者6人
合计共45人,其中女性10人60岁以上7人, 30岁以下5人有留学经历者32人;有博士学位者17人
女性候选人当选比例为76.92%,30岁以下候选人当选比例为55.56%,远高于平均当选率25%,体现出广大选举人在投票时的确遵照了分会关于“适当照顾青年、妇女”的政策选举人中包括不少中等学校教师,以及助产、护理人员,他们并不熟悉科学界的状况,在选举时只能按照形式上的要求照本宣科。“妇女”这条标准是最好掌握的,因此女性候选人的得票往往很高。。但女性候选人及当选代表过度集中于医组,实际体现出在此之前妇女就业受到极大限制。与北京的情况相比,上海方面的选举结果更多地凸显出候选人的行政职务、性别角色及年龄特征。
1950年7月中下旬,各地按照分配的名额陆续完成了代表选举工作,并将代表姓名、简历报送给总会。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地方出现了超额问题。杭州超额一名,发函给总会表示“欲以代表团秘书资格列席大会”。山东、兰州、专门学会等方面也纷纷来函要求增加代表。总会允许山东方面增加5位代表,兰州方面增加4位少数民族代表。台湾方面要求增加代表3名,总会也予以通过。
对学会方面提出的需求,总会决定让其以特邀代表身份与会,并由组织部拟订了一份特邀代表名单,为每个学会提供两个名额,其中至少一名分配到京外。一些未能当选代表的知名科学家便通过这一渠道得以与会,其中有孙云铸、王鸿祯、尹赞勋、赵九章、高士其,等等。此外,为满足各界旁听大会的需求,组织方印发了470张旁听证,对于各地超额代表想要列席会议的,也按照旁听处理[8]。
虽然总会事先对代表额数及分配做了规定,但随着形势发展,总有增减微调。据总会统计,科代会最终的代表总额数为529名据1950年8月编印、作为资料发放给与会代表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名录》,代表总数为530人,各类别代表数字也稍有出入。但这可能是由于编印这本名录的时候,代表情况尚未尘埃落定。本文以会后的统计数字为准。,其中包括:(1)总会常委46名;(2)中央直属有关科学工作机构代表40名;(3)解放军及军委直属机关代表57名;(4)各地区代表327名;(5)特邀代表59名。各地区代表具体分布见表6[13]。
对于科代会代表产生的过程,有以下认识:
其一、在总会安排下,大多数地区的代表是在当地党政机关指导或参与下产生的,采取普选方式的只有北京、上海两地。
其二、即便同样采取普选方式,但由于选举程序上的不同,北京和上海的选举结果也出现了较大差异。上海方面按照总会要求,在选举中明确要选举人投票时适当照顾青年、妇女,这一点忠实地反映在投票结果中。这可能与上海方面的选举人中有比例较大的基层知识分子不无关系根据《全国各地区登记核准自然科学工作者统计表》,北京核准自然科学工作者人数为3069人,其中大学专科以上毕业者为2862人,占比93.26%;上海核准人数为10049人,其中大学专科以上毕业者为7846人,占比78.08%。北京选票回收率73%,上海则不足50%。上海方面各学历层次的选举人的选举参与度及投票差异情况,尚待进一步的资料来揭示。。这些人主要集中在中学教师及护士、助产士群体,对科学界的情况并不熟悉,在投票时可能更加倾向于按照官方明确的标准来执行。
其三、此次代表推选总体上比较仓促,无论是以选举形式,还是政府指导下的推举形式,都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在后期科代筹委会又采取了不少补救措施,主要有:针对名额明显不足的地区或少数民族等特殊群体,追加名额;对学会方面做出妥协,以特邀代表的形式给予照顾;发放大量旁听证给社会各界,等等。
三 科代会代表情况分析
科代会召开期间,实际向大会报到的代表为469名,其中总会常委40名、中央直属有关科学工作机构代表37名、解放军及军委直属机关代表50名、各地区代表291名、特邀代表51名。按学科分类,实际报到的代表中有理组119名、工组173名、农组78名、医组99名。其中农组代表数量最少,以至于出席会议的农学家丁颖说:“农组工作者原占多数,而代表特少。经于主席团会议时,由各代表提请于将来代表机构成立时,予以增加。”[14]事实上,据总会复审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登记结果,总登记人数为37797,其中理、工、农、医四组人数分别为6158、18428、4028、9183尽管因华南、西南未开展登记工作,且其他地区也多有遗漏,导致这组数字并不完善,但从人员占比方面来说,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农组的人数实际上是最少的。各组代表数量之间的差异,并不像登记人数之间的差异那样大。
在科代会的代表中,女性只有20名[12]。在女性代表中,属于医组的占了绝大多数,而上海一地就有10位女性,当中有4位非医组代表,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和工作的机会较多,另一方面还因为上海分会在选举代表时对于“照顾妇女”落实得比较好。
将所在单位划分为政府机关、高校(含高等职业学校)、科研院所、厂矿企业、社会服务机构(包括医疗卫生、科学普及等)几个类型,对各地出席科代会的代表加以分析,能够对此次会议的代表构成及其代表性形成更加明确的认知。依照《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名录》,排除少量信息不明的条目,能够明确服务机关的代表一共有309位,其中来自政府机关的有74位,来自高校等教育机构的有142位,来自科研院所的有19位,来自厂矿企业的有41位有些厂矿企业性质比较特殊,如张家口机电厂,全称“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张家口机电厂”,其厂长(此次会议代表)在工作中的身份更多地是行政管理人员,而非技术人员。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来自社会服务机构的有33位医组代表有其特殊性,兼有高校教师和医疗从业人员的特点,本表统计时依照《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名录》登记的服务机关,登记为高校的就计入“高校等教育机构”栏,登记为医院的就计入“社会服务机构”栏。。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来自政府机关的代表占了较大比重(如沈阳的16位代表中有8位身担要职[12]),如果加上厂矿企业的代表,就占到了代表总数的近四成,这从侧面体现出此后科学界要在党的领导下与政府有关部门密切结合,积极配合国家的建设工作;二是来自科研院所的代表明显偏少,若非总会设置了特邀代表这一选项,很多知名科学家就会被排除在科代会之外,比较典型的如冯德培、贝时璋、赵九章、尹赞勋,等等。即便如此,还是有一大批深刻影响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开拓者没有出现在科代会上。与一年前的科代筹委会全体会议相比,科代会少了很多为人熟知的名字,如:饶毓泰、罗宗洛、戴松恩、钱崇澍、蔡翘、裴文中、章鸿钊、林巧稚、伍献文……[15, 16]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两次会议代表推选方式不同造成的。1949年,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其他社团,在科技界经过广泛宣传、协商,邀请国内理、工、农、医各界及各地区和各团体代表共同组织筹备,最终形成了科代筹委会。由于各团体充分发挥了在本学科领域的资源和影响力,因此科代筹委会尽量涵盖了科技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科代会代表的选举则大为不同。当时对旧有学会整体持批判态度,认为其有着“人力财力分散、分宗划派、争名夺利等弊端”[17],是“腐败的”[4],因此在讨论代表推选方式时,首先就排除了通过旧有学会来推选的渠道。当时主流意见是实行普选,但工作进展并不顺利,有些地方尤其是新解放区不具备开展选举人登记的条件,开展登记工作的地區在工作中也颇费周折。到1950年4月,总会才确定了今后的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随后根据新的要求调整了代表额数,制订了分配方案。但此时,大部分地区并不具备开展普选的条件,因此往往是在当地党政机关指导下,召开筹委会扩大会议,以选定科代会代表,只有上海等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以普选形式选举了代表。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有大量此前一直从事基层工作的小知识分子参与到代表推选中来此次自然科学工作者登记,科代筹委会明确将“普通中等学校或中等职业学校的自然科学教员”和“医院中的……护士、助产士”纳入登记范围。前者多在理组当中,比如杭州分会自审通过的理组登记人员为786人,其中476人从事中等教育;后者多在医组当中,医组人员里女性数量较多的原因就在于大量助产、护理人员的存在。。他们对科学研究的方法、历史和现状都不够了解,参与选举只能是随波逐流、草草了事。加之总会又提出了“适当照顾青年、妇女”的要求,使得推选更加偏离了“科学”这个主题。这些共同造成了科代会代表情况中的种种不如人意之处。
四 结语
1950年的科代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发展史上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回顾历史,科代会的历史使命和重要工作,大多在一年多的筹备过程中就已经完成或是做好铺垫了,包括推选科学界的政协代表,将延安和解放区的科技工作经验引入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实践当中,为筹备中国科学院出谋划策,设计新科学团体的组织架构和工作方针,等等。因此,被推选出来于8月份来京参加科代会的代表们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工作任务(提案审议工作非常仓促,“潦草塞责”[18]),更多地是来为一年多的筹备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并见证人民科学工作翻开新的一页。
尽管如此,代表产生的过程却颇有值得注意之处。此前一年,科代筹委会筹备过程中,委员的推选是由科技界通过原有的社团来组织商讨、酝酿的;此后不久,原有的社团组织就受到“不团结”“宗派主义”“名利场”等等批评,而科代会代表的产生方式遂另起炉灶,试图在开展自然科学工作者大规模登记的基础上进行普选。但大多数地区进展并不理想,最终不得不求助于各地党政机关,才得以完成任务。
对比两种方式下产生的结果:科代筹委会的成员不仅有大量有声望的科学家,还有不少来自解放区的科技工作者,群贤荟萃、团结一致;而科代会代表数量近两倍于科代筹委会,却在容纳知名科学家方面颇多遗珠之憾,即便以“特邀代表”的方式打过补丁,也只是聊胜于无。出现这种问题,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无论是求助于党政机关,还是通过普选来选出科代会代表,其中都要关涉到诸多对科学事业、科学界不那么了解的基层科学工作者。他们缺少深入了解科学家的机会,在需要做出关键选择(审核或投票)的时候,只能借用临阵磨枪或道听途说得来的信息。而科代筹委会的形成则仍主要是科技界自发行动,互相之间都很熟悉,所以做起事来事半功倍。其二、按照总会要求,科代会代表的推选中要考虑各学科间的平衡分布,并适当照顾青年、妇女。在这方面做得最到位的是上海,但这种偏离了科学主题的要求,再遇上本就对科学了解不够深入的选举人团体,就使得很多并不那么合适的候选人被选中了。
综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对旧有学会的批判和改造在政治上确有其“不得不发”的态势,但对学会已有的工作經验未能认真总结并发扬,未免有兰艾同焚之叹。其实,在追求科学精神、探索科学思想、组织学术活动等多个方面,原有学会做过大量工作,积累了很多经验,值得好好借鉴、发挥。然而,在科代会代表选举过程中,科代筹委会抛弃了旧有的工作方式,却限于诸多客观条件,没能把新的工作机制建立起来,最终又求助于行政干预,导致代表产生当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其中的经验和教训,至今仍值得我们反思。
参考文献
[1] 王扬宗. 1949—1950年的科代会: 共和国科学事业的开篇[J]. 科学文化评论, 2008, 5(2): 8—36.
[2] 全国科学会议促进会. 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简章草案[J]. 科学通讯, 1949, (1).
[3] 尹赞勋等. 试拟关于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的基本任务可以提出的问题[J]. 科学通讯, 1949, (1).
[4] 马大猷等. 筹委会学科小组讨论摘要[J]. 科学通讯, 1949, (2).
[5] 科代筹委会大会. 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产生条例[J]. 科学通讯, 1949, (2).
[6] 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签寄筹备委员会简章、代表产生办法、选举人登记办法等通知及同德医学院为报送自然科学工作者名单、登记表的函件[B]. 1950. 上海:上海档案馆, Q249-1-58.
[7] 严济慈等. 本会常委会一年来总结报告[J]. 科学通讯, 1950, (10).
[8] 佚名. 本会常委会会议记录摘要[J]. 科学通讯, 1950, (10).
[9] 科代筹委会. 全国各地区登记核准自然科学工作者统计表[M]. 北京: 科代筹委会, 1950.
[10] 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上海分会选举人登记办法、选举办法结果及全国科代会( 筹 )有关问题的函件[B]. 1950. 上海:上海档案馆, C42-1-3.
[11] 佚名. 各地分会筹备状况[J]. 科学通讯, 1950, (10).
[12] 科代筹委会.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名录[M]. 北京: 科代筹委会, 1950.
[13]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纪念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1.
[14]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经过报告[B]. 1950. 北京: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馆藏基地, 丁颖SG-001-145.
[15] 樊洪业. “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留影[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3, (1).
[16] 王天骏. 文明梦: 记第一批庚款留美生[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106—107.
[17] 王淦昌等. 关于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的基本任务的意见[J]. 科学通讯, 1949, (1).
[18] 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第12卷[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23. 163.
Analysis of the Selection Process and Related Issues of Representatives for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as Natural Science Workers in 1950
WANG Chuanchao
Abstract: From 1949 to 1950, in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representatives for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as Natural Science Workers,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abandoned the original academic organization and attempted to conduct universal suffrage on the basis of large-scale registration of natural science workers. However, due to many objective conditions, the progress in most regions was not ideal, and ultimately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had to seek help from local party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task. This article reviews various issues in this process and re-evaluates the role and experience of the original society.
Keywords: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as Natural Science Workers,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as Natural Science Workers, the Se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