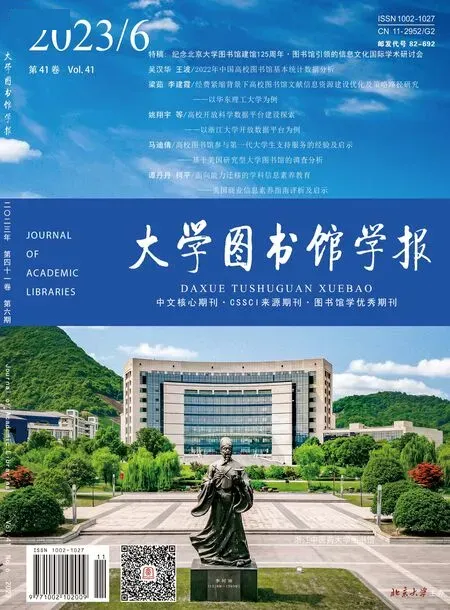构建人间天堂:中国文化中的藏书传统
□程章灿
曾经担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达十八年之久的著名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曾经说过:“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昏昏然缓缓将空幽勘察,凭借着那迟疑无定的手杖[1]。”这句话在中国图书馆界广为流传,早已脍炙人口。博尔赫斯博学多闻,爱书如命,这句话表达了他对图书馆的深厚感情,而藏书对于美好人生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也暗寓其中。鉴于博尔赫斯的身份及其成长背景,人们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往往只联想到西方宗教文化中的天堂想象,而忽略了其中隐含的中国文化元素。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涉猎很多,他在小说名著《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塑造了一个人物,那就是“精通天文、占星、经典诠诂、棋艺,又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的云南总督彭最。彭总督致仕之后闭门谢客,一心一意要完成两大工程:第一个是写一部比《红楼梦》还要人物繁多的巨著,第二个是建造一座谁都走不出来的迷宫,有无数小径分岔的花园[2]。可见,博尔赫斯对中国小说叙事、中国传统文化是颇有了解的(1)参看:付艳云. 从《小径分岔的花园》看博尔赫斯的中国情结[J].花溪,2022(12).,他对中国小说中的天堂叙事以及藏书叙事,也饶有兴趣,换句话说,塑造博尔赫斯的天堂图书馆想象的,可能是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藏书传统。
一 在人间想象天堂:中国人的藏书理想
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凝聚为绮丽的文学想象,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悠久的传统。在中国传统小说叙事中,对美好生活的描写与想象,总是离不开丰富而神奇的藏书,离不开高贵而神秘的藏书楼和图书馆,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下面就以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为序,各举一段小说叙事,管中窥豹,以见一斑。
先说东部。在浙江东部的绍兴,有一座文化名山,叫做会稽山。历史上,这座山与儒、道、释三教都有深厚的渊源,有大禹陵、道家洞天、阳明洞等名胜,富有神圣意味。据南朝作家孔灵符在《会稽山记》中的描述[3],会稽山中有一座宛委山,“宛委”的意思,是说此山隐藏在幽深曲折之处,不易寻找。山上有一个巨大的石匮,据说当年大禹治水,功成名就之后,曾登临此山,并将写有自己治水经验的“金简玉字”典藏在石匮之中。因此,宛委山又名为“石匮山”。谁能打开石匮,谁就能看到这些秘籍,谁就掌握了山河体势,就能治理百川,以保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这是多么神奇的秘籍!可惜,石匮山位于悬崖峭壁之上,高耸入云,是属于神仙的境界,凡夫俗子可望而不可即。后来,人们就把珍贵而稀罕的典籍称为“宛委别藏”,面对这些神圣、神奇的秘籍,世人只能感叹:“此书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看?”
再说西部。中国古代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叫《穆天子传》,说的是在遥远的西部,有一座巍峨的昆仑山。昆仑山盛产玉石,被称为“玉山”,也叫做“群玉之山”。在中国文学想象中,昆仑山很早就被塑造成一座圣洁的、神秘的、高冷却引人向往的仙山。山上不仅住着神秘的西王母,而且储藏着历代先王积累下来的典籍,这个藏书之地因此也被称为“册府”,或者“玉山册府”。对于这座“玉山册府”,人间从来不缺乏热忱的仰望者,大名鼎鼎的周穆王就是其中之一。他不远千里来到这里,不仅实现了瞻仰西王母的愿望,也成为玉山册府的最早的访客。他东归之时,西王母依依惜别,吟唱了一首送别之歌:“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4]。”遗憾的是,周穆王回去之后并没有再来,更为遗憾的是,除了周穆王之外,似乎再没有人到过玉山册府。遥远的昆仑山,神秘的玉山册府,却一直被人间仰望,寄托人类的理想。
再说南方。《嫏嬛记》讲了一段南方的故事,故事发生地在福建,主角是西晋著名学者张华。在当时的学者中,张华以“博学强记”著称。有一次,他在福建某地山中遇见一个奇人,被这个人带到一处“别是天地,宫室嵯峨”的所在。这座洞天既不属于大禹,也不属于西王母,主人是谁没有交代,但它的布局摆设却完全是图书馆的模样。陈列书籍,分门别类,有历代史藏书室,有万国志藏书室,还有很多间其他藏书室,“各有奇书”。有一间屋宇特别高大,封锁得特别严,门口有两只龙守护,里面藏的是“玉京紫微、金真七暎、丹书紫字诸秘籍”。张华参观了各个藏书室,发现里面都是“三坟、九丘、梼杌、春秋”之类的古代秘籍,讲的都是“汉以前事”,都是他闻所未闻的。号称无书不读的张华被震撼了,也被彻底迷住了,他要求在这里借住一段时间,好让他能读一读这些书。那个奇人微笑着拒绝了。张华只好满怀遗憾地离开了,临走前,他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嫏嬛福地”,难怪不能借住[5]。 “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嫏嬛福地,也就是洞天福地,显然与道教的天堂想象有关。
最后说到北方。与西晋的张华一样,西汉的刘向也是一位“书痴”。张、刘二人对书籍异乎寻常的博闻强记,使人们怀疑他们或者天赋异禀,或者有超越现实的奇遇。在东晋王嘉(王子年)《拾遗记》中,刘向的奇遇与张华的奇遇相映成趣。身为图书馆馆长的刘向在西汉皇家图书馆天禄阁校书的时候,遇上一位拄着青藜拐杖的老者,这老者不是别人,正是主管”天地图谶”的神仙太乙之精。他不仅为刘向点火照明,而且与刘向讨论“三代以前帝王兴亡之事”以及“阴阳运数起灭之状”,指导刘向学习了“五行洪范之文”。临走前,他还送给刘向很多写在竹简之上的“天文地图之书”[6]。这段故事出现的太乙之精,可以说是天堂图书馆馆长首次亮相,也可以说是天堂图书馆与人间图书馆的第一次学术交流。刘向校书天禄阁的奇遇表明,异书难得,博学难成,没有异书,也就无法成就一个大学者。直到今天,读书人还期盼有刘向那样的奇遇,凭借新材料,才有可能做出新学问。
“藏之名山”,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对于藏书的想象、对于美好世界的想象,都离不开名山。它是那么高远、高冷,那么神奇、神秘,那么与世隔绝,可望而不可即,又那么被世人仰望,为万众瞩目。它具有天堂所有的一切特征。中国小说中对珍藏各种奇书的天堂的生动叙事,体现了中国人的藏书理想,寄托了中国人对于美好世界的想象。
二 在人间营造天堂:中国人的理想藏书
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凝聚为美好的文学想象,进而转化为创造美好生活的动力。将文学的虚构或想象在人间世界落实,让理想“变现”,有名与实两个方向。名就是采用文学想象中的地名与典故,实就是模仿小说中的描写建筑藏书楼。名和实,就是现实世界对于想象世界的双重模仿。现实世界对想象世界的模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名称相同容易,实际相同很难。最初,只有皇家图书馆、皇帝或内府藏书、某些贵族以及少数富裕士人的私人藏书楼,具有这一方面的条件,庶几得其形貌。
汉朝人把皇家图书馆称为天禄阁,天禄是天赐的福禄的意思。汉代只有像刘向、刘歆、扬雄之类的一流学者,才有福分在天禄阁里读书,这很符合天禄阁这个名称的本义。清代乾隆皇帝将自己的藏书楼(图书馆)命名为天禄琳琅阁,就是延用汉朝的旧名,以维持它的高贵品格。天禄琳琅阁位于故宫乾清宫东侧的昭仁殿。乾隆在位之日,万机待理,无暇较多过问天禄琳琅阁的藏书,导致藏书中的一些珍贵图书被调包,乃至失踪。详情可参阅刘啬教授的专著《天禄琳琅书目研究》[7]。乾隆退位以后,才将精力专注于天禄琳琅阁的藏书。不幸的是,嘉庆二年(1797)冬,此阁失火,一批珍贵的图书被毁。即便遭遇了这些变故,天禄琳琅阁藏书的质量还是极高的,是一般读书人无法企及的。对于乾隆皇帝来说,天禄琳琅阁中的图书就是他理想的藏书;而对于天下士子来说,天禄琳琅阁只是他们的藏书的理想,犹如“美人如花隔云端”。
历代王朝都很重视其皇家图书馆的命名,不但要名正而言顺,还要正大而高尚。宋代人把皇家图书馆称为册府,很显然,这个精致典雅的称呼来自《穆天子传》,显示了宋代皇室对西王母的“玉山册府”的模仿。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皇帝命学士王钦若、杨亿等人修撰《历代君臣事迹》。这部历经八年、成书千卷的皇皇巨著,最后定名为《册府元龟》。顾名思义,就是从皇家图书馆藏书中精选的有关治国理政的参考文献集成[8]。文士们一边编书,一边唱和作诗,在人间的“玉山册府”中大享清福,他们的唱和诗作《西昆酬唱集》,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派“西昆派”的标杆。“西昆”也是对西王母所在的昆仑山的模仿与纪念。《西昆酬唱集》的产生,是文士们分享皇室藏书的结果[9]。皇室的理想藏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部分文士们的理想藏书。
元代国家图书馆的命名,也与宋代一脉相承。据《元史·文宗纪》记载,元代先改司籍郎为群玉署,又升群玉署为群玉内司,负责掌管奎章阁的图书宝玩等[10]。将图书与宝玩放在一起,既是对图书的看重,也恰好切合“群玉署”和“群玉内司”字面上的那个“玉”字。不用说,“群玉署”或“群玉内司”中的“群玉”是有典故的,典出《穆天子传》中的“群玉之山”,也就是“玉山”。这是一个典雅的名号。《穆天子传》中即将沉睡的历史记忆,在元代再次被唤醒,被刮垢磨光。
十九世纪前半叶,北京有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名叫完颜麟庆(1791-1846)。他是满州镶黄旗人,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官至江南河道总督。他将清初著名戏剧家和造园家李渔设计的著名的园林——半亩园买了下来,作为自己的住处。这个地方位于北京东城弓弦胡同(今属黄米胡同)。麟庆在半亩园中为自己建了一座私人藏书楼或者私人图书馆,叫做“嫏嬛妙境”,并将家族先人数代收藏的善本上千部(其中包括宋元本十余种)都贮藏其中。他从宋代诗人黄庭坚和唐代诗人元稹的诗集中集了两句诗,凑成一副对联,“万卷藏书宜子弟(黄山谷),一家终日在楼台(元微之)”,并将其刻在“嫏嬛妙境”的楹柱之上[11]。他在诗中说:“嫏嬛古福地,梦到惟张华。藏书千万卷,便是神仙家[12]。”他身居嫏嬛福地,住在天堂,成为神仙,实现了张华当年的梦想。但他毕竟不是皇帝,也不是神仙,他的私人图书馆居然起了这么一个高大上的名字,可见他的自鸣得意。“嫏嬛妙境”作为麟庆个人理想的藏书楼,只向他的少数亲朋好友开放与分享。
麟庆也知道,“嫏嬛妙境”这个名字起得太高调了一些,奢侈以致露富,得意近乎僭越,非但挑战了古人,恐怕也刺激了不少同时代人。与他同时代而稍早的福建学者兼藏书家陈寿祺,就比较低调。陈寿祺将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小嫏嬛馆”,虽然“嫏嬛”二字仍然透露出一丝得意,但冠以一个“小”字,就显得谦抑多了。据说,陈寿祺的藏书“藏在深闺人不识”,外人难得一窥[13](1234-1240)。这样看来,这小嫏嬛馆也只是陈寿祺个人的理想藏书而已。
三 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为实现中国的理想
清代常熟藏书家张金吾说过:“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14]。”藏书是读书的前提,也是学问的基础。然而,在古代中国,很多人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就像那句俗话说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无论如何,现实的藏书与想象的藏书总是有距离的,理想的藏书与藏书的理想也有很大的距离。明初文学家宋濂从小家境贫寒,买不起书,更谈不上藏书。他只能向藏书之家借阅,拿回家抄录,哪怕数九寒天,“手指不可屈伸”,也不敢懈怠,总是赶着把书抄完,送回去还给人家。他就靠这样借书抄书,得以“遍观群书”[15]。凡是读过宋濂那篇著名的《送东阳马生序》的人,对这幕情景都会有深刻的印象。难怪拥有吴氏测海楼的清代扬州藏书家吴引孙,曾以“有福读书堂”命名自己的书堂[13](690-698)。藏书不易,读书有福,有书可读的地方便是天堂。
相对来说,明清时代的江南可能是拥有最好的藏书条件的地区。藏书的风气弥漫于江南士林,催生了许多藏书家和藏书楼,也就是私家图书馆。杭州丁丙兄弟八千卷楼、苏州顾氏过云楼、常熟赵氏脉望馆、瞿氏铁琴铜剑楼等,便是其中的翘楚。某些藏书家开始将自己的藏书与人分享、出借于人,但其开放度仍是相当有限的。藏书风气由士林而推广到社会各界,由僧人、士绅、官员各方以“众筹”方式建立的镇江“焦山书藏”,是最早的面向社会共享的山林图书馆[16]。但与近现代以来的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相比,其面向社会、旨在开放共享的尺度,也是小巫见大巫。而且,不幸的是,焦山书藏如昙花一现,便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了。
2020年4月到2021年7月,南京大学图书馆微信公号推出“上书房行走”,40位南大人现身说法,以图文配合的方式,展示自己的书房,讲述自己藏书与读书的故事。2022年6月,这组系列推文以《书房记》为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7]。从40位书房主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大多数以教书育人为业,但文章展示的毕竟是个人的书房,主要表达的是“独善其身”的思想姿态。作为南大人共享的大书房,南京大学图书馆策划这组系列推文的目的,在于宣传藏书文化、推广全民阅读,实寓有“兼济天下”的胸怀。2022年8月29日,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开办“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展览,从书房史的角度,展示“中国人的理想书房”。为了呼应这次展览,《三联生活周刊》特别筹划了一期以“中国人的理想书房”为主题的专刊,于2022年第40期适时推出。这引起了人们对“中国人的理想书房”的讨论,并由此扩展到对“中国人的书房理想”以及“中国人的阅读理想”的思考。
中国人的书房理想与阅读理想是什么样子的呢?据古书《仙经》上说,有一种蠧鱼(书虫)喜欢吃书中的“神仙”字样,吃了多次之后,它就变成一团圆卷的头发样子的东西,名叫脉望。手持脉望,即可以唤来神仙,求得仙丹,立即羽化升仙。常熟赵氏脉望馆藏书楼就是以此意命名的[13](472-480)。先师程千帆先生喜欢书写这样一副集句对联:“蠧鱼三食神仙字,海燕双栖玳瑁梁[18]。”上句出自唐代笔记《酉阳杂俎》[19],下句出自唐人沈佺期《古意呈乔补阙知之》[20]。这一副对联概括了传统士人的理想生活境界的两个元素:神奇的书籍与美满的眷属,便是人生最美好的陪伴。
图书馆是古代藏书楼的现代化,在开放性和共享性方面,它是传统藏书楼的“升级换代版”,也是对天堂图书馆的想象的落实。它使图书馆成为真正的、读书人在人间的天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各种公立图书馆(尤其各级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藏书的规模高速扩张,软硬件面貌焕然一新,服务水平今非昔比。24小时图书馆、24小时城市书房,一处又一处美丽的读书天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人间,给读书人带来天堂般的温暖。众多大学图书馆争先恐后地推出各类促进阅读、服务读者的措施,北京大学图书馆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44年前,一位16岁的少年第一次走进这座天堂一样的楼宇,在此后的四年时间里,他怡然享受这里的书香薰陶,眼界大开,心胸拓展。这无疑是他平生所拥有的最富丽的一座藏书天堂。饮水思源,今天,他回到这里,就是为了表达对这个读书与藏书天堂的深深感激之情。值此母校北京大学图书馆125周年馆庆之际,谨以此文衷心祝愿北京大学图书馆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为更多读者送去天堂的书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