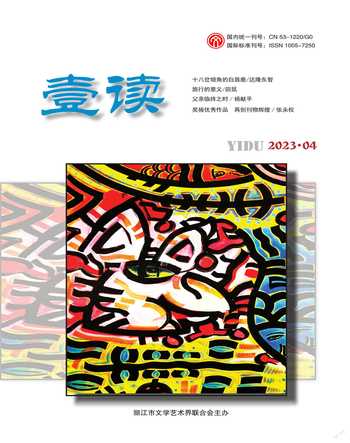金兰村的“神曲”
赵晓梅
我在《永胜县志》中看到:程海沿岸,烟户稠密,村村绿竹粉墙,楼阁高崎,处处曲溪环绕,柳暗花明。
在程海西岸,抵达一个叫“金兰村”的彝族村寨,这是程海湖岸唯一的一个民族村落,古旧的瓦房错落有致地安放在白云山的臂弯里。门前水田任白云和稻田鱼游荡,房后古树凭清风和鸟群欢唱。那村后山体密林翠绿,泉水潺潺从村旁流过。层层梯田铺满了绿茵茵的秧苗,棵棵大树挂满了鸟语花香。站在田野,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背靠青山,面朝大海,碧蓝的海水就在眼前荡漾。于是,金兰村人世世代代过着依山傍水,渔樵耕读的安宁日子。
这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那些几百年的红椿树林在村庄的左右两边,沿着峡谷向白云山攀爬。深入山林,到处布满寂静。自然之音是寂静的一部分,我的视野是寂静的一部分,寂静的流水声从幽暗的谷底向着寂静的高处扩散;寂静的藤蔓向着高大古朴的清香树寂静地缠缠绵绵;寂静的岩石捧着榕树根系寂静的千丝万缕,厚厚的苔藓覆盖寂静的潮湿;在寂静的下午,我听到山泉哗哗流淌的声音在寂静森林里凝固成山水交响的乐音。原始森林中,密布着水冬瓜、黄梨木、红椿树、清香树、青皮树、青香藤等保水树木,那粗大的藤蔓,宛若一条条麻黄的蟒蛇,绕着一块巨大的石头盘旋,远远看去,惊吓出一身冷汗。“藤包树”“石包树”“树包石”的雨林奇观,构造出一幅大自然的绝美图像。
山腰间,我看见崖洞敞开,一股白花花的泉水从大山的肚脐里喷涌而出,形成了一道银白色的瀑布,阳光穿透水雾,映出一弯彩虹,神奇地撞击着我的思维,撞击着岩石的喜悦,撞击着大山的喜悦。
我借一片绿叶,舀一叶神泉水,一口喝下去,清冽、甘甜,萦绕舌尖,激活我己枯萎的味蕾。坐下来吧,喝一口这里的山泉水,那清凉的甜,润养着森林和白云,也润养着我的乡愁和眷恋;坐下来吧,坐在藤蔓的缠绕中,把焦虑、忧伤、悲凉和无奈,撒落在山野,我会在一片绿叶上摘下一滴露珠,摘下昨夜与你一起住舍水岸的梦;坐下来吧,坐在裸露的树根上,一起看见石头包裹着生长的清香树枝,向着天空祈祷的样子,我会在高高的枝头,把写给你的诗,折叠成一片树叶的形状,悄悄藏在这里。如果,今夜你为我打开梦的门窗,明天,你一定会在白云山的树上,找到那首诗歌,找到人间真爱。
啊!这被自然之神宠爱的金兰村。神性在雨水停留的森林中,神性在岩石的石缝里,神性在花草的露珠上,神性在秋天的稻谷间,神性在野兽奔跑的深山幽谷处,神性在每一滴泉水中,神性在辽阔的海域上,神性在每一棵绿树里,树根扎进祖先的骨头里,树眼在树干的中间睁开,每一片叶子都是一页族谱。自然世界的神性,在金兰村人的心里无处不在。村后的青皮树林间,一棵高大笔直的古树,枝叶十分繁茂,而在树干上长出了一只“眼睛”,村里人把这棵树叫“神树”,把那只灵动的“眼睛”称为“树神眼”,神灵在树上睁开一只充满真、善、美符号的眼睛,天天看着金兰村,守望着这块神性的土地,走的再远的人都离不开他的护佑,头顶有神灵,足下就有禁忌,任何人都不敢在这里撒野。
村民对大自然心存敬畏,坚守着人性善良真诚的品德,他们深信,再黑的心,也能被程海水洗白。
是的,这是一个被众神宠爱的地方。
天子庙就在古树密林间,庙内竖有各种神像,不仅供奉着天子,还供奉着本土状元和36位土主,具有明显的祖先崇拜特征。70岁的女东巴杨翠兰,在神庙中一一指点一尊尊神像,这是女神像:老老慈祖、九天圣母、九天金木、金花娘娘、伞花太婆、赏花娘娘。这是男神像:赵王天子、惠康皇帝、赵福皇帝,天生状元、红鼻太公、杨四将军、引神太公、哼哈二将、土地公公娘等。金兰村人对这些神灵的称谓是这么亲切,不是慈祖、圣母,就是太婆、娘娘,不是太公、公公,就是大姐、二姐,像叫着每天相遇的亲人一样。
茶余饭后,村里的老人每天都会相约着来到天子庙,敬香拜神,这种生活的仪式感已成为老人们平常日子里的重要部分。
在天子庙,我看到村中清代《行知批录》碑文称金兰村为均早郎,民国《永垂千古》碑文称金早郎,当地民间俗称格早兰(郎),1951年正式定名为金兰村。“金兰”原指牢固而融洽的交情,源自《易经》“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成语“义结金兰”,指像兄弟姐妹一样的情谊。
金兰村有杨、罗、李姓人家世代居住,三姓祖宗香位均署湖广长沙府湘乡县,族别自称“阿乌浦”,当地人称“湘潭人”。明代以来,金兰村的少数民族“阿乌浦”,因与澜沧卫边屯军民交往密切,其语言、服饰、住房、婚恋、丧葬等习俗,均与当地汉族大致相同。然而,金兰村又有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流传至今,那就是“刀杆节”。
坐在天子庙的古柏树下,40岁的东巴李龙讲述金兰村刀杆节的来历:在唐代南诏国和宋代大理国时期,南诏通海节度使段思平,遭大义宁国杨干贞追杀,时善巨郡郡守高方与段思平交往甚好,遂派心腹至通海将段思平接到永胜共商大计,高方助段思平灭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段思平当了皇帝,高氏即为大理国重臣,云南八府四郡成为高氏世袭领地,段思平来到善巨郡时恰逢春节,便居住在风光秀美的程海金兰村。人们后来不仅修建了天子庙供奉,还在每年正月初三举行“太平盛会刀杆节”以示纪念,真可谓“义结金兰”之举。还有一种说法:相传明末清初,金兰村有一个杨姓读书人,虽然家境贫寒,但他勤奋读书,得到村民赞助,赴京参加科举考试,高中状元。不料,“状元郎”在中秋节返家途中,却被奸臣谋害而死。为了纪念这位杨状元,祭祀本土祖先,村民每年农历八月十五要在天子庙举行“科升科中刀杆节”。
程海湖里有多少朵浪花就有多少个奇幻动人的民间传说,程海湖里有多少个旋涡就有多少頁土著秘史,程海湖里有多少道波涛就有多少首哀婉的民谣,程海湖岸有多少个燃烧不熄的火塘,就有多少个坚贞不屈的爱情故事,程海湖岸有多少种声音的秘语,就有多少种文化的传奇。
“上刀山,下火海”这是一项古老而神奇的祭祀活动,也是无畏者大显身手的空中舞台。
中秋节这天,我亲眼见识了金兰村“上刀山下火海”的场景。
这天,村里充满着喜庆的气氛。男女老少身穿着艳丽的民族服装。小伙们背上三弦和佩刀,姑娘们戴上自己精心制作的绣花筒帕,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刀杆节活动场所天子庙。寺院中间竖起将近30米高的刀杆,由36把砍柴刀排列扎成。这木杆是在活动前15天由祭司择日亲自带人上山选取两棵鲜活笔直的松木,烧香祷告敬树神,边伐树边齐声大吼:“唔咋唔,唔咋喂……”树木倒地,用斧削去半边,火烧去皮,烘烤半干才抬到寺里。
节日头一天,村中的东巴们要举行“封刀”仪式。仪式上祭司跳起祭神舞,左右有专人递上磨得锋利的刀子,祭司接过刀子在自己的舌头上横竖各划一刀,见血则留,若不见血则抛到身后,如此反复,一共选取36把。做好刀梯,选择吉时将其笔直竖立,四边用扎满小彩旗的绳子拉紧,固定在寺院的古树上,顶端插上两面旗帜,刀刃朝上,把36把锋利的刀子牢固地安装在刀梯上,作为36台梯级。当晚寺里燃起篝火,祭司们分别跳神“过堂”,整夜守护刀梯。
八月十五(中秋节)上午十时,锣鼓齐鸣,鞭炮喧天,在笛子的伴奏下“上刀山下火海”的祭祀活动开始。东巴们头戴五幅冠,幅冠上画着图腾,身穿红马褂,腰系红腰带。先跳一段东巴舞旋即进入正殿敬香请神,诵经念咒,喝下大碗白酒,舞着东巴剑术来到大殿外的刀梯前。剑在东巴手上“呼呼”作响,击在青石上火星四溅,锋利的刀刃在阳光下寒光闪闪。
东巴箭步冲向刀杆,迎着锋利的刀口,赤脚踩在刀刃上,一级级往上爬,一直爬到插满小红旗的刀杆顶上,摘一朵半空中的白云,做个优美的动作。让我看的胆颤心惊。接着又一级级地下到地上,脚底不但没有一丝血迹,而且没有一点点划破的痕迹。之后,赤着双脚,从燃烧的红彤彤的火炭上走过,一个一个东巴毫不畏惧地纵身跳进通红的“火海”,让我倒吸一口冷气。
舞剑、上刀杆、过红犁下火海,全套仪式一气呵成,东巴们一个接着一个,冲向刀山和火海,整個过程,扣人心弦、惊心动魄,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勇敢精神和精妙技艺。
按常理,我会认为“上刀山,下火海”这样的绝活男人才能做得到。可是,让我惊讶的是,在金兰村女人也毫不示弱,有十六七岁的年轻姑娘,也有70多岁的老妇,在上刀山,下火海时,她们身手敏捷,动作轻柔,更能搏得观众的掌声和村民的敬重。
李龙说,金兰村信仰东巴教,现有男女东巴26人,男东巴有15人,女东巴有11人。
东巴们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本领和技艺,而是有神相助,所以,每次上刀山下火海,东巴们都要在供奉神灵的大殿里敬香跪拜,念经祈祷。李龙说,这是在请神附身。几百年来,金兰村的东巴们就这样在俗世和神灵间,打通了一条神秘而神奇的通道,悄然演绎着一方传奇。
赤脚爬上的刀山,闪耀着升向天空,裸足踩过的火海,滚烫着铺盖在必经的路上,铧犁烧红了,你敢舔一舔吗?一些民间的事物,与神灵有关,与神奇有关,与秘诀有关,与心愿有关,与沧桑有关,与你和我,永远无关。
金兰村东巴不分男女,只要对东巴仪式感兴趣,在天子庙进行拜师礼,过关者可在师傅口传身教的带领下学习东巴咒语和经文。
上刀山,下火海活动后,村民们在天子庙的古树上荡秋千,高高的秋千向着程海湖荡去,又高又远,在绿树林间穿梭,在白云间回荡。笛子、芦笙吹响了,三弦琴弹响了,“龙摆舞”跳起来了,男女老少,携手挽臂,领舞者唱完一句民谣,所有打跳的人都合唱下一句。欢喜的笑脸,整齐的舞步跳得山响,跳得人心振奋;悠扬的民歌调子,叙述着金兰村人劳动、恋爱、婚姻的生活场景,表达着金兰村人对生活的热爱和饱满的激情,尽情地展示金兰村人古老而纯朴的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内涵。
白云山,一年四季用绿色的臂弯把金兰村揽入怀中。这片终年云雾缭绕,森林郁葱的群山,曾有一座白云寺,这座白云寺如今还清淅地记在清朝乾隆时期黄恩锡的诗句里:白云山寺白云封,海色遥看寺外峰。几处楼台深树里,隔林敲落一声钟。
这样的诗句在我的耳畔一字一句地反复吟咏,让我的心在开满鲜花的幽径里,不断地听到一阵阵诵经的声音,从云雾里飘渺而来。清晨的天空碧蓝高远,阳光带着水的光泽像波浪一样无声地穿行在清幽的松树林中。山花依着藤蔓,坠着一滴滴水晶般的夜露,安静地凝着一缕缕幽香飘散。
站在山腰,回望程海,湖畔田畦雾霭流岚,点点房舍绿树烟村,一砚湖泊水雾蒸发,烟波浩渺。
“山门无锁白云封,雾霭含情翠鸟鸣;一砚程湖润瀚墨,幽山半壁证禅心。”我把这首诗默默地书写在我的心壁上。
行走在茂密的林荫之中,叮叮当当的马铃声从远方传来,一队马帮驮着山货匆匆远去,我的思绪却追随着马蹄声相逢在那遥远的时光里。当我慢慢靠近一段过去的时空时,隔着450多年的时光,我能看到什么?腐蚀、毁坏、抢劫、偷盗、贪婪……对于时间的河,三秒是一瞬,几百年也是一瞬,对于历史的河,谁能把握?谁又能触摸?
白云寺让美丽的白云山染上了神圣的佛教色彩,人们常说,头顶三尺有神灵。459年,一个寺院从诞生到灭亡,从鼎盛到没落,有着美丽的神话传说,也有金戈铁马的冰冷无情,有着苦心孤诣的经营,更有愚蠢贪婪的毁灭。如今,这一切早已烟消云散,战乱的厮杀归于沉寂,净土的争执归于沉寂,佛主的神灵归于沉寂,祈求的诵经归于沉寂。一个香火旺盛了四百多年的寺院,只能在那美丽的神话传说中,在民间,在史书里存活。清《乾隆永北府志》载:“白云山在程海西,上有龙潭,俗传有龙马出其中,因建刹焉。”《永北府志》二十三卷“仙释”条载:“海悟,道号印舟,原藉楚岫,衲云游北胜,至白云山,架木为小庵,栖止十余年,爱其山水清幽,不复他往。适与土司高斗光结方外交,同建梵刹,枕山临海,为永郡胜地。有大司马王宏祚碑记,现存。”
高斗光是永胜历代土司中唯一有文字墨迹遗留后世的土司。他在六德他留山梅云洞题写“谁能超世界,共坐白云间”的诗句,至今尚存。另外,还有现存于灵源篝观音阁的草书匾额“相好光明”、“千古如在”。可见,高斗光在汉文化、儒学和道释研究上的造诣。史载,白云寺为土司高斗光与海悟和尚于公元1661年至1664年所建。白云寺建有大雄宝殿、天王殿、观音殿、尼姑庵等殿宇十余院,还建有高达七丈的海慧宝塔,又名望海塔。寺内有两口重达500余斤的铜钟。民国初期,军阀混战,盗寇横行,白云寺被土匪纵火烧毁,一口铜钟被匪徒滚入程海,另一口由村民抬回,作为河口小学上课的敲钟,后被化铜损毁,还有一对雕刻精美的石狮,现存于昆明金马寺。
到达白云寺遗址前时,一池清澈见底的湖水呈现在眼前,四周绿树倒映水中,清亮亮的潭水纳白云游动,收水花芳香,当地人称草海,又名莲花潭,这就是传说中“有龙马出其中”的地方。
我在寻找,我在钻不通的森林中寻找,我在葳蕤的荒草丛中寻找,寻找一种美丽信仰的存在,寻找远古的美丽传说。在白云寺的遗址上徜徉,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一片片破碎的瓦砾上,从一堆堆残遗的墙垣中,从一块块沉寂着厚厚苔藓的石阶上。白雾柔情,丝丝缕缕,缠绕着寻找的脚步,白云温情,一朵一朵,依恋着寻找的目光。在一个寺院的碎片里,我不知道我会遇见什么,更不知道会错过什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不是一座废墟,这是一段历史的记忆,也是一段历史的诉说。
我只有倾听。在寻找中倾听。
在寺院背后高高的后山顶的松林坡上,有一片僧侣的墓葬群被贼人挖掘得残破不堪。我在想,盗墓贼盗得的是不是青铜、玉饰、陶器、金钵……不,这一切都没有,有的只是守候神灵的灵魂,在幽暗的角落里,或呻吟、或呐喊、或叹息,幽幽地、悠悠地诉说。很遥远,但不陌生。在一处一处的寻找中,边屯文化學者简良开、陈洪金等人,从一堆乱石里找到了一块完整的石碑,石碑上明显地刻着“清圆寂……”等字样,分明是一位和尚的墓碑。我站在石碑前,思考着这些文字,感觉这字活动起来了,每一个字都是那时的阳光、月色、云雾、花草、清香,是翩翩飞舞的蝴蝶,是带着佛祖意念的盘香香气,是潺潺流动的山泉水,那么鲜活,灵动,有声音和色彩,有温度和香味。在星星点点的历史碎片里,我好像进入了一个强大的磁场,能与过去的阳光、风雨、白云、花香、水色奇异地糅合在一起,与白云寺的僧侣们虔诚地侍奉着头顶的神灵。
雾来了,浓厚的雾将我们裹进一种神秘之中,风雨来了,风夹着淅淅沥沥的雨水在空空的山野飘落一地的诉说,白云来了,带着一束耀眼的阳光从稠密的树林里射向墓群,石碑被雨水洗涤后,阳光照着,闪动着岁月滑动后的光亮,一对精美的石狮在挖空的坟墓前忠实地守候着。
只有源头的清冽与高洁,才会有这样的清淡和幽远的美,隔着459年的时光,生命已走远了,昼夜不灭的香火熄了,敲动铜钟的双手僵冻了,海悟和尚圆寂后的灵魂游走在这幽香的圣地,诵经的小僧却在佛的面前倒下了……那青铜的绿锈,那碧玉的沉光,那陶瓷的泥土本色,那永不更改的景仰,却还在,还在人们的心里好好存放着。
于是,朗诵诗句的声音常常从程海湖畔的泥院里传来:“白云深处隐蓬莱,乘兴游观践碧苔;云挂松根飞不尽,鸟闻客履始惊开。参差楼阁随山现,出没峰峦积翠来;野径幽香谁领略,尘氛不到任徘徊。”谁都知道,这是儒学廪生杨崃的《白云山》诗句。
而乾隆二十六年贡生郭鸿畿的诗却又是一番意景:“览胜寻幽处,苍苔印屐痕;崖虚云欲坠,岸仄水争喧。老树多穿屋,山花不碍门;悠然无限趣,翘首望烟村。”
这是一个真实的神话,也是一个真实的消亡。只有沉默,只能沉默。如这白云山上的白云,静静地栖息在山水林间,让美丽沉寂在白云山的美丽里,沉寂在程海湖的清丽中。
还在行走,行走在白云山的美丽中。还在寻找,寻找那些被人们遗忘的自然景色,云南松、罗汉松、潺潺流淌的山泉水,梅子篝里的幽谷兰馨,滴水崖上直泻而下的银白瀑布,老龙洞的喀斯特地貌溶洞……这一切都让每一个寻找的人心花怒放。
写到这,我想到了何晓坤先生的几句诗:雾霭,是大地的袈裟/岚黛,是峰峦的袈裟/云朵,是天空的袈裟/疼痛,是死亡的袈裟。此时,我想说,程海湖,是永胜的袈裟,白云寺,是历史的袈裟。只要我们的眼里还饱含着泪水,那良知的袈裟就会披在众生的身上。
责任编辑:尹晓燕 包成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