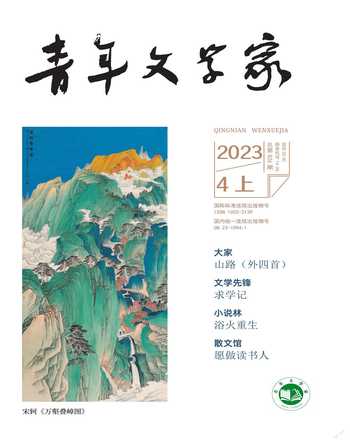论苏轼寓惠时期纪游诗的艺术特质
陈金林
寓惠时期是苏轼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之一,史载,苏轼于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郭超《四库全书精华·史部》)。作为苏轼自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生阶段,居惠近三载,苏轼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等名句。综观学界当前对苏轼寓惠时期诗作的研究,多集中在阐释苏轼诗作中的山水审美特性和个人乐观心态,即“對黄州诗、岭南诗及海外诗的探讨,则多与其思想、心态及岭外风物等相联系”(朱付利《新世纪以来苏轼诗研究综述》),而对苏轼纪游诗这一诗作类型的探讨则较为缺乏。本文意在从纪游诗这一具体诗歌类型入手,探讨苏轼寓居惠州时期纪游诗的艺术特质。
一、纪游诗的界定
纪游诗,顾名思义,是记叙诗人游行经历的诗歌,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诗歌类型,又可称为记游诗、记行诗。但纪游诗与纪行诗又不完全相同,严格来说,二者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广义的纪游诗可以看作为一切记录诗人出行、游途中所见所感的诗歌,近似于诗歌体裁的游记小品,从这个角度上而言,纪游诗与纪行诗的功能和特性基本重合。而狭义的纪游诗则指那些专门记叙诗人出游经历的诗作,这类诗作的诗题多带有“游”字,如苏轼的《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关于狭义的纪游诗的观念,元人杨维桢在《云间纪游诗序》中指出:“诗者,为纪行而作者乎……幸而出乎太平无事之时,则为登山临水、寻奇拾胜之诗。不幸而出于四方多事、豺虎纵横之时,则为伤今思古、险阻艰难之作……”杨维桢认为,纪行诗的风格和思想情感是感伤的,内容侧重于记载乱世之行役。而纪游诗则与之迥异,是“出乎太平无事之时”,是将山水风物记之于诗。这种观念虽然有一定的偏颇(纪游诗也有伤情悲世之作),却准确地指出了狭义的纪游诗与纪行诗的差异。
此外,研究苏轼的纪游诗,无法脱离苏轼个人的生平,苏轼一生遭受多次贬谪,奔走四方,对个人出行经历的记载,实际上贯穿苏轼大半生的诗作。因此,如果从广义的纪游诗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将面临苏轼的纪游诗与其山水诗、咏物诗等其他诗歌类型难以界定边界的问题。而狭义的纪游诗概念因其界定范围的明确和严格,更强调纪游的特质,具有更高的研究价值。
二、苏轼寓惠时期的纪游诗及其艺术特质
(一)苏轼寓惠时期的纪游诗
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贬谪至惠州,直至绍圣四年(1097)才由惠州经梧州入海南,在惠州久居两年零七个月。这一时期,苏轼的诗风较黄州时期已有较大变化,诗作类型涵盖赠答、悼亡、咏物等,其中可以算得上纪游诗的诗作却只有七首,分别是:《白水山佛迹岩》《咏汤泉》《正月二十四日与儿子过赖仙芝王原秀才僧昙颖》《游博罗香积寺》《同正辅表兄游白水山》《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与正辅游香积寺》。从内容上看,苏轼寓惠时期所作的这七首纪游诗,不仅描绘出苏轼谪居生活的样貌,也多层次地展示出苏轼纪游诗的独特艺术特质,表露出苏轼复杂的思想心态。
(二)寓惠时期纪游诗的艺术特质
综合而言,苏轼这一时期的纪游诗主要含有以下艺术特质:
1.情景交融的对称结构
山水风光是纪游诗创作的基本素材之一,但苏轼寓惠时期所作的纪游诗中对山水风光的描写别具一格,这种特殊性显著地表现在其诗歌的结构中。如其《白水山佛迹岩》一诗:
何人守蓬莱,夜半失左股。浮山若鹏蹲,忽展垂天羽。根株互连络,崖峤争吞吐。神工自炉鞲,融液相缀补。至今余隙罅,流出千斛乳。方其欲合时,天匠麾月斧。帝觞分余沥,山骨醉后土。峰峦尚开阖,涧谷犹呼舞。海风吹未凝,古佛来布武。当时汪罔氏,投足不尽拇。青莲虽不见,千古落花雨。双溪汇九折,万马腾一鼓。奔雷溅玉雪,潭洞开水府。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我来方醉后,濯足聊戏侮。回风卷飞雹,掠面过强弩。山灵莫恶剧,微命安足赌。此山吾欲老,慎勿厌求取。溪流变春酒,与我相宾主。当连青竹竿,下灌黄精圃。
此诗共四十句,从结构上看,自首句“何人守蓬莱”起至“掉尾取渴虎”句,苏轼用二十八句的篇幅描绘白水山及周边的风光。首先,介绍了罗浮山的传说源来及其气势的恢宏;其次,描绘了白水山泉水的浩大声势;最后,谈及佛迹岩守山之神的传说。而在讲述佛迹岩神话传说的过程中,苏轼无疑又渗透了个人的豪迈情怀,如其“万马腾一鼓”“奔雷溅玉雪”数句,既是在渲染白水山溪水落潭之气势,也有个人豪放情怀的寄托,可见苏轼《答陈季常书》云,“游白水佛迹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辊电散,未易名状,大略如项羽破章邯时也”。从“我来方醉后,濯足聊戏侮”起,至结尾的十二句内容,言及苏轼个人对此次出游的感受,并以“此山吾欲老,慎勿厌求取”两句直言对白水山的赞赏态度,这种对山水风光的赞赏之情,既是对诗歌前半部分写景内容的承接,同时,也使全诗形成了一种情景交融的匀称结构。这种结构在苏轼另一首《咏汤泉》诗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积水焚大槐,蓄油灾武库。惊然丞相井,疑浣将军布。自怜耳目隘,未测阴阳故。郁攸火山烈,觱沸汤泉注。岂惟渴兽骇,坐使痴儿怖。安能长鱼鳖,仅可燖狐兔。山中惟木客,户外时芒屦。虽无倾城浴,幸免亡国污。
此诗共十六句,首句“积水焚大槐”起至“疑浣将军布”这四句,是苏轼在描摹汤泉之景象,苏轼首先引用庄子、晋武帝、诸葛亮、梁冀等人的史实,极言汤泉水之沸腾。“自怜耳目隘,未测阴阳故”二句,是苏轼个人面临汤泉奇景的感慨:可惜自己耳目闭塞,即便面临如此奇景,却不知这世间的阴阳造化。从“郁攸火山烈”起至结尾,则是苏轼又从个人感慨回归写景,并于写景之中阐发此次出游的感悟:“虽无倾城浴,幸免亡国污。”此处的倾城意为“绝色女子”,“倾城浴”则无疑是用杨贵妃华清池沐浴的典故,可见《苏轼全集校注》:“虽无二句,由白水汤泉而及骊山华清宫温泉。”由此可知,苏轼认为汤泉虽偏僻,不得贵人临幸此地,却正因为不地处高贵之境,免遭亡国之辱,得以保全高洁。换言之,苏轼于北宋文坛也如汤泉一般,名震天下,却因不懂委曲求全,于是被贬谪至僻远之境,虽身居下位,却也由此得以远离庙堂,保全自身的高洁独立。综合而言,此诗每写景数句,其后便有抒发个人情志之句,周而复始,情景交融,结构匀称。
2.写景中心系民生的情怀
纪游诗本为诗人记载出游见闻之作,故多以描摹山水景物为主,苏轼的纪游诗之中却时常蕴含着爱民情怀。如其《游博罗香积寺》:
二年流落蛙鱼乡,朝来喜见麦吐芒。东风摇波舞净绿,初日泫露酣娇黄。汪汪春泥已没膝,剡剡秋谷初分秧。谁言万里出无友,见此二美喜欲狂。三山屏擁僧舍小,一溪雷转松阴凉。要令水力供臼磨,与相地脉增堤防。霏霏落雪看收面,隐隐叠鼓闻舂糠。散流一啜云子白,炊裂十字琼肌香。岂惟牢丸荐古味,要使真一流天浆。诗成捧腹便绝倒,书生说食真膏肓。
全诗共二十句,首句“二年流落蛙鱼乡”起至“见此二美喜欲狂”数句,叙述苏轼于游途中所见的景物:“吐芒”的麦与“分秧”的禾苗。在这部分篇幅中,苏轼用了十分精细的笔触,刻画了嫩黄色的麦苗和插好的秧苗的茁壮长势,并直言自己内心的欣喜之情。从“三山屏拥僧舍小”至“与相地脉增堤防”四句,则是提及苏轼对农田设施提出的建议:发展水力和建筑堤坝。“霏霏落雪看收面”起至结尾,是苏轼幻想碓磨建成后的丰收景象,其中尤为难得的是,在幻想中苏轼与民其乐:“诗成捧腹便绝倒,书生说食真膏肓。”此诗诗题为《游博罗香积寺》,然而纵观全诗,诗歌中并未细致描绘“香积寺”的风光山色,只以“三山屏拥僧舍小,一溪雷转松阴凉”二句略微提及。与之相对应的是,诗作中随处可见苏轼对民生的关怀:从开篇对庄稼的关注,到其后对农作设施的建议,再到最后对农民丰收后的憧憬。可以说,在这首纪游诗中,苏轼突破了传统纪游诗专注于诗人个体情志抒发的格局,开辟出在纪游诗中关怀民生的新方向。如苏轼《同正辅游香积寺》一诗:
越山少松竹,常苦野火厄。此峰独苍然,感荷佛祖力。茯苓无人采,千岁化琥珀。幽光发中夜,见者惟木客。我岂无长镵,真赝苦难识。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把玩竟不食,弃置长太息。山僧类有道,辛苦常谷汲。我惭作机舂,凿破混沌穴。幽寻恐不继,书板记岁月。
此诗共二十句,是苏轼游香积寺后又与程正辅同游香积寺时所作。本诗与《游博罗香积寺》不同,苏轼自“此峰独苍然,感荷佛祖力”二句起便重在阐述个人的禅学思想:世间事物本微末之差,但差之毫厘却失之千里。其后“山僧类有道”至“凿破混沌穴”四句,交代苏轼禅学思想中的自然观点,即认为万事万物应遵循原有的规律进行,山寺的僧人遵循自然之道,因而常辛苦去谷中汲水,相比之下,苏轼制作碓磨的建议便是违背了自然之道。然而细读本诗结尾二句,却又不见苏轼反思自己的“过失”,寻求弥补之道,苏轼只是感慨幽静之地恐将不再,并决意将制作水磨的日期记录下来。由此可知,制作碓磨一事于苏轼心中具有重要意义,以至于这种“过失”违背了苏轼禅学思想中的自然之道,却依旧令苏轼不愿更改自己的行为。换言之,制作碓磨造福百姓、心系民生,在苏轼心中超过了个人禅修的自然之道。
3.纪游中的复杂思想心态
关于苏轼寓惠时期诗文的思想倾向历来有争议,正如王启鹏先生所说:“有的人说苏轼晚年是儒家思想为主,有的说是以佛道思想为主;有的说苏轼贬寓惠州是积极乐观的,有的说是消极低沉的。”(《苏轼寓惠研究综述》)而苏轼寓惠时期所作的纪游诗,其思想内容也十分复杂,这种复杂性尤其表现在俗情与隐退的矛盾中,如苏轼《同正辅表兄游白水山》一诗:
伟哉造物真豪纵,攫土抟沙为此弄。劈开翠峡走云雷,截破奔流作潭洞。因随化人履巨迹,得与仙兄蹑飞鞚。曳杖不知岩谷深,穿云但觉衣裘重。坐看惊鸟投霜叶,知有老蛟蟠石瓮。金沙玉砾粲可数,古镜宝奁寒不动。念兄独立与世疏,绝境难到惟我共。永辞角上两蛮触,一洗胸中九云梦。浮来山高回望失,武陵路绝无人送。筠篮撷翠爪甲香,素绠分碧银瓶冻。归路霏霏汤谷暗,野堂活活神泉涌。解衣浴此无垢人,身轻可试云间凤。
此诗写于绍圣二年十月,共二十四句。从除本诗首句“伟哉造物真豪纵”起至“古镜宝奁寒不动”十二句皆在写白水山之风光外,从“念兄独立与世疏”一句起至结尾,皆是苏轼在表明个人心志。“念兄独立与世疏,绝境难到惟我共”二句,既指程正辅独立于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实则也言明苏轼自己内心的高洁。“永辞角上两蛮触,一洗胸中九云梦”二句,则是苏轼自言已割弃世间纷争,回归内心的清明。然而,其后“浮来山高回望失,武陵路绝无人送”二句,却又与苏轼适才言明的隐退之心相冲突:浮来山高耸,回望后无处寻觅,而可以归隐的桃花源也无迹可求。综合全诗可知,苏轼既感自己因自身高洁而独立于世,沦落绝境,想由此远离世间纷争,却又自觉无处归隐,无法脱离世俗,从而陷入隐与仕的矛盾之中。
总而言之,苏轼寓惠时期创作的纪游诗存在自身独特的艺术特质,通过对苏轼纪游诗艺术特质的研究,我们可以对苏轼诗歌拥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同时也为研究苏轼寓惠时期的诗歌创作提供一个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