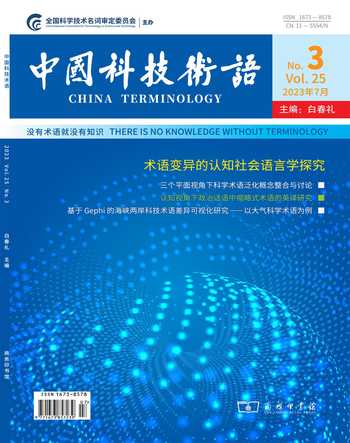国际语境下中医术语翻译的标准化与多样性



摘 要:为更加清楚地认识中医术语翻译标准化和多样化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本研究从社会背景、情境语境两个方面分析国际语境对中医术语翻译的影响和制约作用。通过对中医术语翻译标准的主导性、复杂性和差异性分析,指出“多样性”概念是对“标准化”这一核心概念的补偿,有助于提升中医术语翻译的合理性和规范化。通过选取中医典籍、论著和教材三种文本,结合中医教学实践,对不同交际语境下术语翻译标准的差异性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中医术语翻译;术语标准化;翻译多样性;国际语境
中图分类号:R22;H315.9文献标识码:ADOI:10.12339/j.issn.1673-8578.2023.03.007
Abstract: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tendency of standard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TCM term translation more clearl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and restraints of international context on TCM term translation from two aspects of social background and situational contex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ominance, complexity and difference of TCM term translation standards, we think that the concept of “diversity” is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core concept of “standardization”, which helps to improve the rationality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CM term translation. Based on three types of texts (TCM classics, works and textbooks) and TCM teaching practice, we also explored the varying degree of difference in the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standard under these communication contexts.
Keywords: Translation of TCM terms;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Diversity of Translation; International Context
收稿日期:2022-12-07修回日期:2023-02-20
基金項目: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挖掘、整理及翻译标准化研究”(19ZDA301);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2021年度科研项目“中医药应用文本术语翻译规范和研究”(YB2021021)
0 引言
中医术语是中医理论和文化的凝练,中医术语翻译是中医翻译的核心问题。21世纪以来,中医术语英译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成为研究热点[1]。要推动中医的国际交流,中医界普遍认为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和规范化必不可少。国内主要中医药翻译标准化词典有近20种,但始终存在标准不一、译名不统一的问题[2]。由于学术争鸣的持续存在,一些学者对中医术语标准化本身提出了异议[3]。当前,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中医文本翻译中是否应该规定一套标准化术语仍存在重大分歧[4]。支持或反对的原因也各不同,并且广泛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中医典籍英译、英文教材编写、英语教学及临床实践中,严重制约了中医在国际上的传播和使用。而当前中国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向外表达自己的新时代,为更好服务于中医文化的海外传播和提升中医药话语权,非常有必要从国际语境的宏阔视角来探究中医术语的标准化和多样性问题。本文基于术语翻译的跨学科研究特点,构建中医术语翻译的国际语境分析框架,试图使研究人员和译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国际语境对中医术语翻译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从而有助于解决中医术语翻译的标准化和多样化方面的具体相关问题。
1 中医术语翻译的国际语境分析框架
1.1 国际语境分析框架的构建
中医术语翻译本质上是中医术语相关概念跨语言和跨文化传播后的二次命名过程,既表征中医药专业领域知识,建构中医药知识体系,同时满足语言交际需要,进行话语构建。术语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码过程中,一方面受语言内在本质属性和术语翻译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深受社会文化外部因素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外译术语的产生、存在与发展是英汉内在的语言特点和社会文化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5]。以往国内中医术语翻译的标准化研究主要关注标准中具体术语的对比研究和英译标准化本体,虽也有对政府主导权、话语权、历史多元性、文化背景等社会文化因素的研究[6-8],但较为零散,且缺乏行之有效的理论研究来理解影响术语翻译的语言外因素[9]。
本项研究在语言学、翻译学、术语学、人类学等不同领域相关理论的综合指导下,构建中医术语翻译的国际语境分析框架(如图1)。该框架分内外两层,外层指与中医术语翻译有关的宏观语言外因素,即“语言外诸要素相互结合、相互制约而形成的广阔的社会背景”[10],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环境、译者的态度、目标语读者的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和语言态度[5]。现代术语学认为目的语的语言文化特性是再次定名的理据,是影响术语翻译的最为重要的参数,在准确把握术语所表征的专业内涵的前提下,源语与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对比非常重要[11]。近年来,翻译研究不断扩展其研究视野,注重对宏阔社会文化系统结构中的文化解读,以及对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政治因素和权力关系的研究。外层因素对译文构建的影响较为隐秘,抽象度较高。
分析框架的内层借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情景语境”(即语域)概念,通过分析语场(即语言发生的环境,通常也指交际目的)、语旨(即交际参与者的角色及其关系)和语式(即语言表达的风格、方式)三个要素,显化社会背景对译文构建的影响,增强该分析模式的可操作性。可以说,情境语境决定术语翻译策略[12],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术语的语场、语旨和语式的认识和把握,决定了翻译策略的选择和操作。在中医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把文本置于新语境中,基于语场、语旨和语式对等原则,根据目的语的不同交际目的、译者心目中不同的读者群以及不同的交际方法进行术语翻译,产生出“其所希望的、与新语境相联系的新话语,提供读者偏好的话语解读方式”[13]。
人类学家Sonya E. Pritzker(索尼娅·普里茨克)将中医翻译视为“活翻译”(living translation):“通过书写、互动、体验和实践,将中医翻译转化为多种口头和书面形式,挑战权力和差异的二元概念”[4],是“一种涉及多个文本、作者、教师——解释者的持续对话”[4],其独特视角将中医翻译置身于“权利”和“差异”的社会背景下,交际语境不仅涉及学术互动,还包括实践体验,参与者包括作者、教师、学生等,交际方式有书面和口头两种。
1.2 中医术语翻译的社会背景
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医传播实际上是持有不同利益、立场和价值观主体之间的跨文化沟通和对话[14]。国际社会就谁主导中医英译文化权的问题上一直争议不休,力图通过术语翻译取得话语权。中西方译者视中医为具有独特理论框架和实践体系的独立科学,是否套用西医理论来理解中医,决定了译文的价值取向[15]。
一方面,在当下中国大国崛起、谋求世界范围影响力的背景下,国内译界学者多认为中医术语的翻译应注意保留中医文化因子,更多采用“以我为准”的异化策略,完整地表达中医术语中负载的医学、文化和哲学信息,建立明确的中医话语体系。同时,西方国家试图通过中医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因而出现了Nigel Wiseman(魏遒杰)、Paul U. Unschuld(文树德)等一批致力于挖掘中医经典、探索源语言翻译方式的西方学者。另一方面,为促成中医西传,国内学者认为中医与西医的相似点更为重要,因而试图通过目标语导向的术语翻译,尤其是生物词汇提高西方的接受度,而忽略中医术语的文化因素。也有西方学者在民族优越感和殖民主义思想的驱使下,在翻译中医文本时多采用目标语导向的归化翻译,如Felix Mann(费列满)专研针灸,却运用西医神经系统理论对经络穴位进行解释。
目标语读者的民族心理和语言态度等也是导致译文价值取向的重要原因。在西方观念里,中医被视为一种“替代疗法”,认为它相比生物医学本身更加注重自然性、整体性和以人为本,是一种可以通过实践习得的直觉性和整体性医学,因此没必要注重语言的准确性。如中医典籍中杀灭、防御和攻击等军事语言的比喻用法并未出现在西方宣传的翻译版本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方流行将“营气”“卫气”译为“nutrient qi”“protective qi”,该译法否定了中医的“攻击”作用,限制了中医的疗效范围。因此,文树德提出为体现原文中“营盘”和“卫兵”的原意,应译为“camp Qi”“guard Qi”。这种偏见实际上是将中国作者排除在西方市场之外:所有的英译中医畅销书中,无一本是中国作者翻译的[16]。
1.3 中医术语翻译的语境
根据术语的交际语境观,术语只有被用在某种语境中才能认为是术语。术语通常可以用于以下交際语境中:专家―专家间的交际(用高度专门化的行话谈论其学科),专家―初学者间的交际(专家与初学者交际时也会使用术语,但会做解释),师生间的交际(学生需要掌握术语以达到教学目的),以及专家―大众(外行)间的交际。前三种语境中出现的术语需要以精确的方式翻译。因此可以说,包含这三种语境的文本中出现的术语是术语翻译的对象[11],而第四种交际以知识普及为目的,专家只需传达出术语的大意即可。
中医文本类型根据文本的主要功能分为表情型(如中医药典籍文献、歌赋等)、信息型(如教科书、学术论文与报告等)和感染型(如中医药说明书、企事业宣传资料等)。中医表情型文本的参与者主要是专家―专家,信息型文本的参与者主要包括专家―专家、专家―初学者或师生,感染型文本的目标受众是大众,因此中医表情型和信息型文本中出现的术语更符合中医术语的界定,而中医感染型文本中的术语不太符合,不在本次术语研究范围内。对于以实践为交际目的中医翻译而言,中医课堂教学实践的参与者是师生,同样符合对中医术语的界定,而中医临床实践发生在中医师和病人之间,术语使用并不严格,也不纳入本次研究范围。
2 国际语境下的中医术语标准化和多样性
在国际语境的制约和影响下,中医术语的翻译出现了赞成和反对标准化两种声音。因此,对中医术语翻译标准的主导性、复杂性和差异性的思考有助于加深对标准化问题的认识,也能对多样性的必然性有更加清楚的了解。
2.1 中医术语翻译标准的主导性
为推动中医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2000年之后,国内外先后出版了《中医药学名词》《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英译》《中医基础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西太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等关于中医术语标准化的权威著作,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见表1)。鉴于这一阶段Nigel Wiseman的《实用英文中医词典》的翻译思想广为西方人士接受[3],在此也一并纳入探讨。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中医药联合会颁布的两份文件都推荐若干标准译文,且“翻译思路与方法目前已基本趋同”[17],但因学界对某些译文分歧巨大,或与国外从业人员常用译法存在出入,故未被广泛采用[15],中医翻译中缺乏主导翻译标准的核心权威。经过多年努力,世界首部且由我国主导的“中医术语类国际标准”(ISO 18662-1: 2017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VocabularyPart 1: Chinese Materia Media)于2017年7月18日作为ISO 正式标准,由ISO总部发布,这对中医术语标准化具有重要意义[18]。另一方面,标准化的反对者认为标准化翻译追求的是结构的一体性,并营造社会稳定平衡的形象,但体现的是一种支配地位和对语言多样性的漠视,中医术语翻译标准也是如此。还有反对者提出标准化不符合西方崇尚自由的文化,并且不适用于复杂、中立而又不断演进的医学界[4]。
2.2 中医术语翻译标准的复杂性
中医术语兼具科学性与文化性术语的本质特征[18],科学性特征要求中医术语以其科学性和标准化为努力目标,其概念的符号化要求标准一致。另一方面,中医术语应该更多考虑其文化属性,以合理性和规范化作为翻译标准,不排斥术语翻译再命名过程中有限的合理差异性。中医术语的双重本质特征、不同的译者价值取向,以及中医理论的多样性和术语的多义性都增加了中医术语标准化的复杂性。
赞成中医术语标准化的国内外学者和医师持两种态度:持源语导向标准化的一派认为只有掌握源语言的人才能领会中医真理,标准化是实现忠实度的关键,只有采用标准化翻译才能使读者相信中医来源的可靠性,进而能以中国中医师的方式进行思考、诊断和治疗。Nigel Wiseman是将源语导向翻译融入文化背景的集大成者,他将中医语言归类为“特殊用途语言”(LSP)[19],从而让正式标准化的术语更具合理性。目标语导向的术语翻译标准的支持者重视中医翻译在中医实践中的作用,认为基于生物医学的目标语导向翻译标准能让中医更有效地迎合当下的时代,有助于中医融入当下国际医疗体系。中醫术语标准化的反对者坚持翻译的多样性,认为术语标准化会限制中文术语的多层含义,主张采用更通俗且简明的语言,代替源语导向术语翻译标准使用的晦涩翻译[4]。
2.3 中医术语翻译标准的差异性
情境语境分析能够更加直观地体现中医术语翻译标准中存在的差异性。基于前文对中医术语的界定,选取中医典籍、论著和教材三种文本为代表的中医表情型和信息型文本,以及中医教学实践的部分文本,分析这些语境下术语翻译标准的差异性(如图2)。
中医典籍既是表情型文本,也是信息型文本。作为表情型文本,中医典籍的英译重形式,译者需忠实原作,以源语为导向,运用音译、直译等翻译方法表达原作的情感与态度,其参与者是专家―专家,运用高度专门化的中医术语进行交际,因此,术语翻译的标准化程度最高,差异性最小。如作为信息型文本,中医典籍中术语翻译可以有一定的合理差异性,以满足目标受众的信息需求。中医论著是信息型文本,主要为中医初学者提供信息,宜采用直译、意译等简洁明了的翻译方法表现事物与事实,术语翻译可具有一定的合理差异性。中医教材的目标受众是西方中医初学者,为帮助学生明白中医术语内涵,可以在中医术语翻译标准的基础上,采用编译以及译释并用等多样化翻译策略,契合目标语学习者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和阅读习惯,为他们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促进受众的理解和认知。Giovanni Maciocia(马万里)以此为翻译标准而编写的《中医基础学》就是对外传播的成功案例。该教材重印超过18次,是亚马逊中医畅销书北美排行榜中为数不多的中医基础理论类书籍[14]。
由于语言学者所做的翻译专业学术研究无法满足中医师和中医教育者的需要[20],标准化语言的强制性要求会严重限制教师阐释中医基本理论和概念的能力,而多样化有益于学生深层次理解丰富的中医含义[4],因此,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学生对标准术语的理解取决于基于自身体验取得的对中医的认知,在交际实践中学生的个人经验比语言更加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教学实践语境中的术语翻译的差异性最明显。
3 结语
中医术语的科学性与文化性特征,译者的理解角度、采取的译则译法等因素,都会造成中医术语的英译不一致,而很多时候不能简单地判定孰是孰非。因此,有必要引入“多样性”的概念对“标准化”这一核心概念进行补偿,从而确保中医术语翻译在“概念界定层面的准确性,语符表征层面的一致性的前提下,使之更加合理规范”[21]。
在当代国际语境下,如何制定由我国政府掌握话语权的中医术语国际标准且此类标准乐于和易于为西方读者所接受,仍是中医翻译人员面临的现实挑战。中医术语翻译选择国际化还是民族化的翻译策略,绝非简单的翻译方法方面的选择,而是对传统中医及其所蕴含的丰富文化的输出或对外传播的不同态度,是文化软实力的一种体现。为此,一方面我们坚持“以我为准”的术语翻译标准,加大对基于源语文化术语翻译的研究力度,要有“中国选择”和“中国阐释” 的译作走出去;另一方面,也需要借鉴“外国选择”和“外国阐释”[22],通过对Nigel Wiseman、Paul U. Unschuld、Giovanni Maciocia等一批外国中医著名译者的作品研究,希冀从“他者”的角度审视“自我”,更好把握国外目标读者的中医背景和信息需求,体现术语翻译标准的合理差异化,实现中医翻译更加多元化立体化的发展,进而推动中西方文化和医学体系的融合。在具体层面上,我们可以依据学术交流和中医实践的不同交际目的,以及文本类型等对术语翻译标准进行适当标注,以体现一定的合理差异性,或开发中医术语英译查询软件并收录不同版本的标准[23],从而能够根据交际语境对译文选择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本研究聚焦中医术语翻译的非语言因素,今后,如何将中医术语的内本质属性和翻译规律纳入研究框架,探究语言和非语言因素相互作用下的中医术语标准化和多元化现象,有待下一步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 董俭,王天芳,都立澜,等. 1991年—2015年国内中医术语英译研究现状的计量学与可视化分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7, 32(9): 4277-4281.
[2] 李孝英,邝旖雯. 从中医典籍外译乱象看中国传统文化翻译的策略重建:以《黄帝内经》书名翻译为例[J]. 外语电化教学, 2021(5): 26-33, 4.
[3] 李静,胡建鹏. 中医基本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的研究综述[J]. 科技信息, 2012(15): 24-25.
[4] PRITZKER S. Living Translation: Language and the Search for Resonance in U.S. Chinese Medicine[M]. New York: Berghahn Book, 2014: 9,56,78-86,146.
[5] 张沉香. 影响术语翻译的因素及其分析[J].上海翻译, 2006(3): 63-66.
[6] HUI K K, PRITZKER S.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The Perspective from UCLA Center for East West Medicine(I)[J]. 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2007, 13(1): 64-66.
[7] SOLOS I, HONG M, DING J, et al. Thoughts on the importance of government regulated Chinese medicine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2017: 1-5.
[8] 蒋继彪.国家形象视域下中医术语英译策略研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21, 27(11): 1802-1805.
[9] 唐韧,中医跨文化传播:中医术语翻译的修辞和语言挑战[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5:120-122.
[10] 方梦之,中国译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11] 魏向清, 赵连振.术语翻译研究导引[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9,164.
[12] 黎晓伟. 语域视野下的翻译策略[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S2): 174-176.
[13] BLOMMAERT J. Discours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Cambridge: CUP, 2005: 47.
[14] 钱敏娟,张宗明. 基于“他者”的叙事策略探求中医对外传播有效路径[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6, 31(8): 2946-2950.
[15] 陈斯歆. 文化视阈下中医术语英译的原则与策略[J]. 上海翻译, 2017(3): 51-56, 94.
[16] UNSCHULD P U. The Sprea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World: An Attempt at an Explanation of a Surprising Phenomenon[J].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2003, 22(3): 215-222.
[17] 李照国.中医基本名词术语英译国际标准化研究:理论研究、实践总结、方法探索[M].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50.
[18] 朱文晓,童林,韩佳悦. 中国中医药翻译研究40年(1978—2018)[J]. 上海翻译, 2020(1): 55-61, 95.
[19] WISEMAN N. Translation for Chinese Medical Terminology: A Sourceoriented Approach[D]. Department of Complementary Health Studies, Exeter University. 2000:53.
[20] BUCK C. On Terminology and Translation[J].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00, 63: 38-42.
[21] 魏向清, 杨平. 中国特色话语对外传播与术语翻译标准化[J].中国翻译, 2019, 40(1): 91-97.
[22] 許多, 许钧. 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 关于《大中华文库》的评价与思考[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5(3): 13-17, 94.
[23] 蒋继彪, 祁兴华. 中医药术语汉英在线查询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 中国科技术语, 2022, 24(2): 92-96.
作者简介:高芸(1971—),女,硕士,上海中医药大学外语教学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医外宣翻译和术语翻译。主持和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一般项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项目等20余项。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1部。通信方式:gybook200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