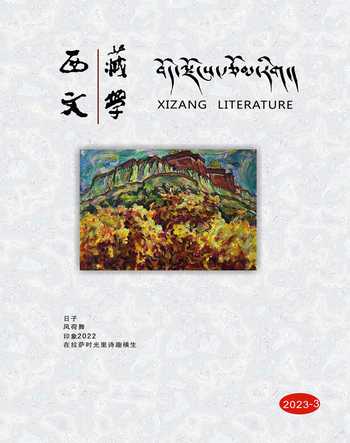走进故乡
其米卓嘎
寻得这般难得的机会,又一次走回了老家,从嘎拉山隧道出来就算是踏上了山南的土地。我莫名有些激动,或许是许久封闭的思乡情结在作乱,或许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旅途刺激了。
绿色的震撼
汽车奔跑在高速公路上,只见路的一边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它们像一团团绿色的棉花糖,顶着丰厚的树冠,一次次热情地迎接着慕山南之名而来的行人,年复一年默默坚守在这条满载情思的公路边。那是一片看不到树根的林海,像一片绿色的大海,在淅淅沥沥的雨水中依旧守望着陌生人的梦想。我们赞叹着又感慨着,时光似乎从来没有等待过谁,但是转瞬的变化并没有输给谁。
片片树林就这样在短短的光阴中长成浩瀚的林海,依偎在雅鲁藏布大江的怀抱里,它从未辜负过大江不求回报的滋养,就这样呈现了生命不卑不亢而顽强的美丽,把山南的一片沙漠地牢牢地换作了绿洲,日日夜夜温润着雅砻文化。
雨还在下,车窗外透明的雨水仿佛是心中的哽咽,模糊了干涩的双眼。多久没有踏上这条路了,连梦里都不敢走近。原来一个人可以悲哀到连回家的勇气都没有。那些触摸不得的往事,那些无法释怀的事情,仿佛因为日常的忙碌而变得销声匿迹。但是,当你踏上回家的这条路的那一刻,一切都变得无比清晰,仿佛从未遗 忘过。
梦幻的泽当
“那不是泽当吗?”孩子爸突然问,只见越过林海,在视线所到之处除了绿色的山脉,便是那一簇依稀可见的高楼大厦。它仿佛是远处耸立的白塔,倚靠着山脉被林海深深地托举在头顶,显得格外地庄严肃穆。“我们不去泽当吗?可不可以去一高(山南一高)玩玩……”孩子急切的恳求充盈在耳边。我们理解她的心情,毕竟在一高,她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从幼儿园回来后在一高的草坪上跟着一群小朋友玩耍,有时被她的“妈妈格央”带去家里吃吃喝喝,周末会被妈妈带去游乐场……生活里没有写不完的作业,没有清晨就起床的痛苦,更没有考试的紧张和学习的种种压力。六岁之前的生活似乎是她生活中最甜蜜的回忆,让她时时怀念那时候的无忧无虑。
我也跟着感伤起来,心疼孩子的辛苦,她跟我一样是个认真的人,所以在很多时候即便是一件小小的事情,也会把她折腾得心烦意乱。“今天不去一高,下次去好不好?”我带着几分抱歉的语气说。“哼……”显然,我的回答让她十分不悦。其实,我何尝不想去一高?何尝不想去看看现在的一高?想去看看那片见证很多孩子成长的草地是否依旧那样柔软,想去看看教学楼前的草坪上蒲公英的笑容是否仍然那样灿烂,想去看看阿酷平措瘦小的背影是否依旧那样亲切可爱……
“往哪边走?”思绪猛地被拽了回来。“直走这条路便是,不用过桥。”仓促地回答。
惊奇的画面
甩开傍山的小路,汽车驶进了乡间公路,与其说是乡间公路,不如说是未来的城市马路。宽阔平坦的水泥路如一条条迎接我们的哈达,舒展在这古老的旷野中;欢快闪烁的红绿灯仿佛是鸟儿的清脆鸣叫,陶醉着习惯于劳累奔波的心灵;各种拔地而起的工厂恰似如梦初醒的游子,在追逐富裕的道路上奋不顾身……我茫然地寻找着从前坑坑洼洼的纤细的马路,搜索着被碎石子覆盖的荒凉的原野和沉浸在麦田间的矮小的房屋。
那破败的乡村呢?
我差点哭出来了!
“这里变化真大,将来要变成大城市啦!”孩子惊奇地东张西望着随口惊叫着。“先去送东西,要过杂玛桥。”姐姐说。对,前面靠山的那座小桥就叫“杂玛桥”,要是姐姐不说,我都忘了这名字。
小时候有一次,二姐的儿子在夜里哭得厉害,我就陪着二姐夫到杂玛桥寻一小块桥梁的木头(听长辈说孩子夜里哭闹不止可以用桥梁的一小块木头放枕头下,有助于安神)的时候,在明亮的月光下我看到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走近一看,结果是个锋利的镰刀。
我把捡到镰刀的事跟孩子讲,她突然说:“夜里出来,你不害怕吗?你爸爸妈妈允许吗?”我们几个都笑了。
小路上的惊喜
车子一过杂玛桥,就踏入了一片绿葱葱的小路,道旁高大、茂密的树叶在头顶交织成一把大自然的雨伞,渲染着来客雀跃的心情。透过树枝能看见一旁齐整的青稞麦穗,她们在雨水的呢喃中羞涩地低下了头,像是一位青春懵懂的少女。突然,眼前出现了小摊——拖着嫩绿尾巴的水灵灵的水萝卜,面颊上涂着泥土的憨厚的土豆,还有裹着彩色头巾的亲切阿佳。我们把车停在路边的杂草和小石子上,迈向摊位。“水萝卜甜不,阿佳?”我问到。“我也不知道啊哈哈,周末才挖出来卖……”阿佳爽朗的笑声和淳朴的语言瞬间拨动着我的某个神经,犹如叮叮咚咚滑动的泉水,让人仿佛偷听到大自然的窃窃私语。听过太多谎言和大话的我们早已习惯了微笑点头,却从来没有把谁的话经过自己的神经。于是,突然觉得有些激动,觉得我们是多么渴望真心,渴望尘世如自己设计的乌托邦,人人都是真理的秉持者。借助这样的情绪,我买了水萝卜,它真的很甜,是那种久违的甜蜜。
“她们怎么不去泽当卖?”孩子爸问。“还得来回,不如这样划算。现在大家都变聪明了。”姐姐解释道。果然,一路都有这样简单的摊位——一个木架子,上面放着一袋装满土豆的尼龙袋,旁边的盆子里摆放着刚刚挖出来的白白嫩嫩的水萝卜,有的摊位上多一个电饭锅,那热腾腾的新鲜煮土豆绝对能满足游客尝鲜的美好愿望,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车子停留在路边?欢快的笑声怎么会一阵阵划过沉睡的油麦菜?
“那是你的小学学校吧?”孩子爸突然冒出来一句,我猛地往前望,“结巴乡完小”的蓝色牌子映入眼帘。我让孩子爸开慢点,从破旧的围墙边回忆着我的小学生活——贫乏的物质、奋斗的少年、严厉的老师……似乎是生活的某种恩赐,在我们贫穷而发奋的岁月里变得格外珍贵。
那时候,老师们是那样的负责认真,每天清晨一个厉声打断着我们的夢,在一阵慌乱的穿衣和叠被的匆促声音之后,大家都点上蜡烛走出校门,往田野的怀抱中去背书。手中的蜡烛在破旧书本和瘦弱的胸襟中不断地晃动着它微弱的脑袋,却一直坚持着发光发亮,从未熄灭过。在这样年复一年的发奋图强中,我们终于走出了大山,开始了缤纷多彩的内地西藏班的生涯。
在放假回家的时间里,我每每都会去看望小学老师们,要不是他们当初的坚守和付出,我们又怎么会有机会去见识外面的世界?后来,听说数学老师病故了,至此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经常会梦见他,梦里依旧能看见他夹着数学书走进教室……忽地醒来,除了深深的难过和怀念,只剩下自己……直至今日,一旦想起数学老师,我都会有一种酸楚,他的父母、两个女儿,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我无从知晓。只是,太多的遗憾在心底残留着,像漩涡一样打乱着我的神经。
那时候的食堂伙食,面疙瘩几粒、米饭几粒、大白菜几片里兑水,但是,没有一个孩子因为那样贫穷的条件而放弃学业,村里每年上内地西藏班的孩子如雨后春笋。“坐飞机去内地上学”是每个孩子藏在心底的梦想,孩子们也会为这样隐秘的梦想而早起晚睡地学习。在那雨后的早上,当我戴上哈达在父老乡亲们羡慕的目光中离开家的那一刻,我望见父母脸上不仅挂着依依不舍的泪水,也显露着几分掩盖不住的骄傲。
只是,从那以后,我和故乡画上了难以相逢的逗号。完成了内地求学任务的我在泽当工作了十一年。虽然家在河的对面,但是由于父母的离去,我失去了回家的念头和勇气。现如今,我在异地谋生,“故乡”成了永远最熟悉的陌生地,我们之间隔的不仅仅是一条河,更是无法描述的无形的距离。我在那里的记忆也许一辈子都会那样清晰美丽,但是没有父母的老家永远都是游子身上无法结痂的伤口。
农家小院的恬淡
我们到家时已经是中午两点了,妹妹准备好的食物在我们的狼吞虎咽中逐渐减少。我不停地喝着酥油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觉得这里的酥油茶,有着说不出的醇厚和甘甜。就好像在云朵里躺着,安静、甜蜜,阳光温柔地抚摸着,睁开惺忪睡眼,翻了身,只见周围都是软绵绵的热乎乎的云朵。那种静谧和舒适,今生只有故乡的酥油茶给过。
之后,我走进佛堂里,昏暗的光线里,一盏黄色的酥油灯在眨眼,我借着酥油灯微弱的光靠近佛龛,佛龛里的神像依旧慈眉善目,好像从未怪罪过我的迟迟不归。双手合十,在心里呼唤着双亲,告诉她们我终于回家了,终于踏上了故土,请她们放心。猛然有一些心酸,人到中年深感父母的辛苦,欲报父母的恩情。可惜,一切都迟了,我们已经阴阳相隔,今生再无缘分可续了。只能轻轻地挑亮酥油灯,感激它陪伴着我走过了那些恍惚的岁月。
妹妹家在装修,大院子的四周盖起了房子,院子被玻璃包起来,似乎有些城里独家独院的味道。原来院子里的桃树被移到了外面,可惜枯萎了。我有些心疼,呆呆地望着那突出来的小坑。仿佛那枝干上曾缀满香甜的桃子在阳光下甜甜地欢笑。
我问外甥女要是考上了内地大学有啥打算。妹妹说:“要上啊,还要搞个欢送聚会……”我有些羡慕,我的女儿那么小,妹妹的孩子却都高中毕业了。做父母的一辈子都在为孩子拼搏,等孩子成家立业了是不是也可以卸一卸肩上的重担呢?
闲暇之余,我望见了缭绕在半山腰的云雾,孩子想把它装在瓶子里,轻柔动人;一头刚出生不久的牛犊子,在午后的牛棚里午睡,它发亮的毛发在杂草间跳跃;一滩黄褐色的浑水有牛粪和泥土的气息,它让我想起从前母亲挤牛奶时候的情景:母亲一手提着牛奶桶,一手挽起藏袍,在混着雨水和牛粪的黄褐色泥泞中小心翼翼地靠近母牛,母亲卖力地拉开牛犊子,差点绊倒在泥泞里。
这个时候我都会不顾一切去帮忙,母亲瘦弱的身躯在我眼里变得更加弱不禁风。母亲总是说:“你不要来,担心弄脏了鞋子……”可是母亲并不知道,她的坚强和默默的疼爱时时刻刻刺痛着我幼小的心灵。我抓着牛犊子的脖子,它在我顽固的束缚中吃力地扭动着滑溜的脖子,把一嘴的牛奶泡沫涂抹在我胸前,圆溜溜的眼睛無可奈何地到处瞄着……
一切都是那样恬静如初,唯独我暗自出 神……
责任编辑:索朗卓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