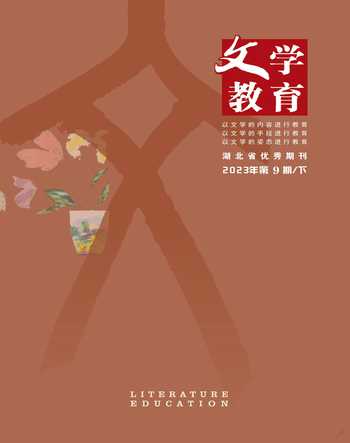心理分析视阈下《守望灯塔》中银儿的自我蜕变
曾冬梅
内容摘要:《守望灯塔》中的主人公银儿是个身世悲惨的孤儿。在其成长过程中,原生家庭的创伤以及现代文明催生的离殇使她几近丢失自我、陷入迷惘状态。普尤的收养与陪伴让银儿有了安全的归宿,爱的启蒙由此开始。然而现代科技的到来使得这个安全之家被冲散,银儿被迫踏上自我追寻的旅途并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故事是她成长的见证,亦是指引她自我觉醒的航标。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美好记忆浮现,银儿逐渐与创伤和解,并带着创伤事件积累的认知开启了新的生活之旅。以朱迪斯·赫尔曼的创伤复原三阶段理论解读《守望灯塔》中银儿的心理成长变化,可透视温特森笔下女性成长的历程,引发女性对自我生存和自我意识的反思。
关键词:创伤心理 爱与归属 女性生存 《守望灯塔》
《守望灯塔》是英国当代女作家詹尼特·温特森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孤儿---银儿,和灯塔看守人---普尤的故事。生来就不知道父亲是谁的银儿在十岁的时候又失去了母亲,飘无定所,后被瞎子普尤收养。银儿一边给普尤当助手,一边听他讲灯塔的历史及各种传奇故事。这些故事与银儿自己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是其穿越黑暗、疗愈内心创伤并最终找到归属的航向标。银儿的孤儿身份“从一开始就意味着爱的缺失和对爱的渴求”。[1]8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使得银儿深陷黑暗之中,爱与安全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普尤的收养与陪伴让银儿慢慢走出内心黑暗、并初步接受爱的启蒙。然而现代文明冲击下,这种幸福生活转瞬即逝。灯塔接受现代化改造的现实迫使他们离开这片土地,踏上各自的旅途。在寻找普尤的途中,银儿饱尝离殇之苦,创伤再现。爱的失落与归属感的缺失使得银儿迷失了自己,甚至被心理医生诊断为心理变态。与林中伴侣的相遇、相爱让银儿领悟到爱的真意,自我觉醒开始。自我意识觉醒促成美好记忆浮现,银儿逐渐与内心创伤和解,创伤自我也得以疗愈。
以往学者主要从叙事、意象、主题及存在主义等角度研究该小说。本文力图从文本出发,分析银儿在时空交错、故事交织中的心路历程,并结合朱迪思·赫尔曼的创伤心理学理论阐释银儿在复原三阶段中逐步走出创伤、实现自我蜕变的过程。
一.创伤及其复原
“创伤”(Trauma)一词在早期主要见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与工业事故创伤相关的临床医学,常用于泛指外力作用下身体所遭受的伤口或疼痛。随着社会文化以及学术研究的纵深发展,“创伤”一词渐渐被应用到精神分析或心理学领域。在心理学上,“创伤”指的是一个人对痛苦经历的情感反应。它是一种停留在记忆中的痛苦体验,其带来的伤痛不亚于身体上所受的损伤。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指出:“如果在一个很短的时期里某种经验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导致其不能以正常的方法求得适应,因而使心灵的有效功能的分配被永远地扰乱,我们把这种经验称作‘创伤性的”。[2]430这句话中所强调的刺激是指当事人亲身经历的与死亡、重大伤害或威胁有关的事件。与普通的苦难不同,这些创伤性事件往往是突然的、不可预测的,它们常常被压抑在潜意识层面,有时会通过梦境的形式呈现出来,有时也会因外界触碰到心理因素,片段式地出现在意识层,给当事人造成心灵伤害。然而,创伤事件能否对个体心理造成创伤要满足的条件有两个:“一是事件本身的性质(包括现实的或害怕的死亡,以及严重的身体或情绪的损害);二是事件对于受害者的意义。”[3]94从这两个条件来看,《守望灯塔》中银儿在童年失去父母双亲的经历、在灯塔接受现代改造时与普尤的离别以及之后在追寻途中所经受的自我分裂都可以归为创伤性事件。因为对银儿来说,父母以及普尤都是重要的亲人。他们的离去对银儿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损害甚至让银儿陷入了迷惘,找不到自我存在的意义。
在種种创伤事件的侵扰下,银儿的成长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其克服内心黑暗与孤独、找到爱与归属的成长蜕变之旅可以用朱迪思·赫尔曼的创伤复原理论阐释。赫尔曼在《创伤与复原》一书中指出创伤复原有三个阶段:一是“建立安全感,还原创伤事件真相,修复幸存者与其社群之间的关联性”。[4]13接着,患者以相对缓和的态度再次面对创伤性事件,痛苦的记忆以碎片化的形式出现在患者脑海里,给受创者造成心理伤害,甚至影响其正常生活。此时,受创者尝试用美好的记忆替代创伤记忆来淡化、化解痛苦。步入第三阶段后,创伤患者需要与自己和解,尝试着接纳不完美,并带着创伤事件积累的认知开创新生活。在本小说中,银儿所经历的“遭受创伤---寻求化解创伤之法---与创伤自我和解”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其经历“迷失自我---追寻自我---找回自我”的蜕变过程。
二.银儿成长过程中所经受的创伤
(一)与生俱来的家庭创伤
家是每个人自出生起所接触的最小的生活单位。根据词源学上对“family”一词的解释,一个完整的家庭必须包括父母双亲、孩子等成员。然而《守望灯塔》中的银儿却降落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里。她从出生开始就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十岁那年,母亲又不幸坠崖身亡。正如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所强调的那样,童年所处的环境会影响个人对生活意义的判断[5]32。父爱与母爱的缺失使得银儿把“意外”当作自己的父亲,认为自己的出生是种“不幸”、是种“过错”,认为那座倾斜的房子把母亲和自己扔出去是因为她们从来就不该出现在那。双亲的离去使得银儿无处安放的内心失去了一部分光,并且从此过上了一种带着倾斜角度的生活。这种原生家庭的不幸给银儿带来的影响极深,甚至影响了她此后的成长之路。从小说中呈现的理据来看,无论是银儿从普尤口中听到的故事还是离开灯塔后银儿自己所讲述的故事,这些都与爱的主题有关。缺乏爱与安全感的银儿这一路上都在寻找一个温暖幸福的、充满爱的家,以此来弥补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
(二)现代文明冲击下的离殇
除了家庭,患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患者个人的情感也都会给人带来创伤。离家之后的银儿被普尤收养,成为灯塔守护者的助手。刚到灯塔时,黑暗成了银儿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如影随形。虽然人可以自主选择性地遗忘曾经的伤痛,但创伤记忆仍会在不经意间以碎片化的形式出现。例如,银儿有时候会看见母亲幽暗无声地朝自己飘落下来。幸运的是,在普尤讲述的一串串故事中银儿渐渐学会了面对内心的黑暗并尝试走出黑暗。普尤父亲般的陪伴与教导让银儿渐渐体会到爱与温暖。然而,平静美好的生活被一纸命令打破。现代文明的推进促使北方灯塔管委会要对灯塔做自动改造。收到这一命令之后,普尤悄悄离开了灯塔。银儿再次孤零一人。两次被抛出去---先是从母亲身边,然后是从普尤身边。银儿想寻找一个安全可靠的着陆地的梦想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破碎了。刚体验到的爱与温暖被现实冲散,银儿内心再次受创,面临自我生存的抉择。
(三)追寻自我中的迷途
经历两次失去亲人的银儿内心受到极大创伤,她模糊了爱的含义甚至丢失了自我。当北方灯塔管委会要对灯塔进行自动化改造,品契小姐问银儿的未来有何打算时,银儿的回答是“我的未来就是这灯塔,没有灯塔,我就得从新开始—-重新”。[6]95因此,离开灯塔之后,银儿便踏上了寻找普尤也即寻找自我的旅程。在途中,加入图书馆遇到的麻烦以及借书过程中的波折让她明白“在一个要么买要么放下的世界里,爱是没有意义的”。[6]124孤独无依的感觉再次向她袭来,她感觉不到生活的意义,感觉自己的精神在崩溃。她希望“以一种混乱的、令人发疯的方式继续忘掉自己而同时也找到自己”。[6]137因此,她偷书、偷鸟,甚至日夜颠倒地工作。在被心理医生诊断为心理变态时,她向医生解释这样做是为了寻找生活的意义。两次遭受创伤,自身心理与外部环境断裂,银儿迷失了自己。她希望书籍、鸟儿能慰藉自己空落的心。然而,在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理论框架下,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途中经历的一切让银儿明白爱具有双面性的特质,自我意识开始慢慢觉醒。
三.创伤愈合与自我蜕变
既然创伤与生俱来,无可避免,那如何治愈创伤、复原重生则显得至关重要。朱迪思·赫尔曼在《创伤与复原》一书中认为创伤复原有三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即建立安全的环境、回顾与哀悼创伤和重建联系感。小说中,银儿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后便离开了那座倾斜的房子,迈出了创伤治愈过程中的一小步---离开带来创伤的原生家庭。然而暂住在品契小姐家中的银儿在吃饭、睡觉等方面被差别对待,安全与温暖的需要并没有得到满足。后来,银儿跟着普尤来到灯塔,成为灯塔守护者的助手。初到灯塔,黑暗如影随形,银儿仍然没有完全感受到爱与安全。例如,睡觉时她会“蜷起身子,膝盖顶着下巴,两手搂着脚趾,好让自己暖和一些”[6]29,她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子宫里,回到了各种问题出来之前的安全空间里”。[6]29从这里可以看出银儿对温暖与安全的渴求。同时也可以知晓初到灯塔的银儿之前似乎一直处于“依仰母怀”的婴儿状态,一直把母体作为安全和温暖的源头。母亲在坠崖时剪断扣在母女之间的安全带暗示着连接在母亲与婴儿之间的脐带被剪断,也即银儿真正脱离了母体。可是,离开母体后的银儿孤独无依,找不到自我存在的意义。而在与普尤日渐一日父亲般的陪伴中,她感受到了一个安全之“家”带来的爱与温暖。某种意义上,家是安全与归属感的象征。银儿在普尤父亲般的陪伴下体会到家的感觉意味着她从“依赖母怀”的“镜像阶段”[7]步入了“象征秩序”[7]的阶段。普尤与灯塔是安全之家建立的见证,复原的第一阶段在此基本实现。
然而,在复原第一阶段建立了安全环境并不意味着创伤不再侵扰患者。面对创伤记忆的侵扰,患者发挥自我主观能动性至关重要。银儿刚体验到的美好生活被现代社會带来的科技打破。灯塔接受自动化改造意味着普尤的失业,也意味着两人不得不面对离别。对于本身缺乏爱与归属感的银儿来说,这种离别或许不是甜蜜的悲伤,而是沉重的创伤。离开灯塔以后,银儿踏上了寻找普尤的旅途。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更喜欢被水围绕的感觉”[6]134,在途中她去的每一处地方都有岛屿、海水---与在灯塔生活时的环境相似。从这可以看出灯塔已经烙印在银儿的深层记忆,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她的选择。正如灯塔照亮了航行的水手那般,灯塔发出的故事之光也照亮了银儿的内心。实际上,银儿寻找普尤的过程也是她寻找并讲述自己故事的过程。故事是治愈银儿心灵创伤的一剂良药。“讲故事是给混沌的生活赋予一个形态,一个生存经验得到自我观照、获得自主性的形态”。[1]7在寻找普尤的旅程中,银儿讲述了自己偷书、偷鸟的经历,以及一些与爱的主题相关的故事,如: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之间的故事。正如马斯洛所主张的那样,“当爱的需求未得到满足时,个体会产生强烈的孤独感、异化感和疏离感”。[8]55为了借书籍慰藉自己空虚的内心世界,她像机器般日夜颠倒地为假日酒店工作。又因为鸟儿有呼唤名字、提醒自己是谁的功用,她偷了那只鸟。银儿偷书、偷鸟的行为其实是在外界极度压抑下渴求爱的表现。在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故事中,银儿渐渐明白虽然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变化,但爱不是自然选择的部分。就算世界消失得不留痕迹,但爱还在。怀着这种信念,她开始按自己的理解、重新讲述达克的故事,回忆并重新面对以前的伤痛记忆。在回忆过程中,美好记忆渐渐浮现,她发现“生活中真实的东西,我记得的东西,我手里摆弄的东西,不是房子,不是银行存款,也不是奖金或升职。我所记得的是爱---全都是爱……”。[6]173从银儿自主回顾伤痛记忆并以美好记忆取代创伤记忆可以看出,复原的第二阶段到此也基本完成。
回顾与哀悼创伤记忆之后,患者会与创伤和解,重建联系感。小说中痊愈之后的银儿,找到了一个最像灯塔的地方---林中小屋。在小屋中,她遇见了自己的伴侣,找到了爱与归属。破碎的自我和完好的自我和解,外界的联系得到重新建立,银儿带着创伤事件积累的认知开启了新生活。
家在每个人的成长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幸福的家庭可以成为治愈创伤的疗养地,而不幸的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可能伴随一生。生于单亲家庭加上经历幼年丧母之痛的银儿这一路上的成长经历终归是在逃离创伤之家、追寻安全温暖之家。这个家既是现实中能为人遮风挡雨的港湾,如灯塔,又是抽象意义上能让人感受到安全与爱的归宿。从小说结尾可以看出,银儿显然找到了这样一个家,她遭受的创伤也得到了治愈。虽然小说中讲到白银发出的光百分之九十五来自它自身的反射,但银儿在别人的故事里慢慢走出黑暗、自我意识觉醒,蜕变成长,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光。
实际上,从白银是我们可以微量服食的贵金属这一事实上看,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银元素,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银儿的影子。因此小说中银儿治愈创伤的过程可以给我们或者遭受创伤的人一些启示。现代社会是个压抑、快节奏的社会,创伤无处不在。原生家庭的伤害,现代社会飞速发展下带来的各种欲望、诱惑使人成为一种抑郁的劳作动物,身体与心理断裂,直至走上自杀的极端。银儿的蜕变之路告诉我们经受创伤的人仍然有多种选择,仍然可以好好地过着自己的一生。创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遭受创伤后自暴自弃、轻易地放弃自身寻找治愈通道的努力。
参考文献
[1]侯毅凌.珍奈特·温特森:灯塔守望者之歌[J].外国文学,2006(1):3-10.
[2]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周丽,译.武汉:武汉出版社,2014.
[3]赵冬梅.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6):93-97.
[4]朱迪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M].施宏达、陈文琪,译.北京:机械出版社,2015.
[5]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自卑与超越》[M].徐姗,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
[6]詹妮特·温特森.《守望灯塔》[M]. 侯毅凌,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M]. 成明,编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