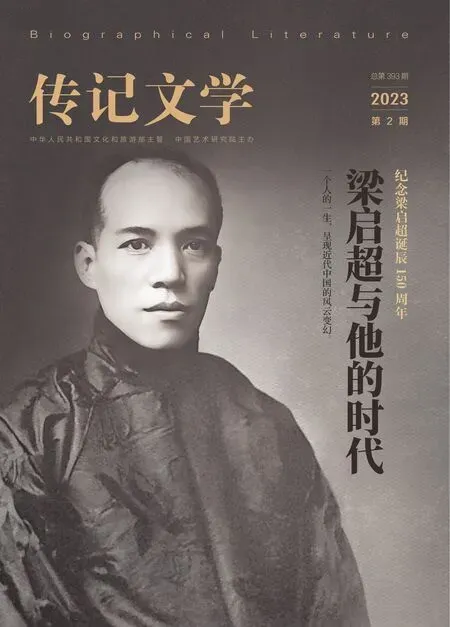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以来鲁迅传记写作与知识分子精神建构
朱 旭 李斯琪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事鲁迅传记写作的知识分子,对于前人经验有重新审视的意识,更直面当代社会转型和文学逐步边缘化的现状,在传记写作中呈现出各自的学术选择。具体到鲁迅传记的书写,知识分子面对变化着的社会现实,透过个体精神的变迁,达成群体性传记书写的某种共识,建构起鲁迅传记写作的新时代。本文将从鲁迅传记写作与知识分子精神建构的关系着手,试图为理解新世纪传记与传记家的关系提供有效参考。
80年代以来的鲁迅传记呈现出蓬勃发展、异彩纷呈的整体态势。一方面,30年代至70年代,自增田涉、斯诺、王士菁,至曹聚仁、路焕华、石一歌等学者,都为后续鲁迅传记写作奠定了应有的基础;另一方面,80年代以来,文坛涌现出一批极为优秀的从事鲁迅传记写作的知识分子:林辰、林志浩、唐弢、朱正、曹庆瑞、吴中杰、彭定安、陈漱渝、林非、刘再复、林贤治、曾智中、吴俊、王晓明、钮岱峰、孙郁、房向东、张梦阳、项义华、乔丽华、李伶伶、黄乔生、薛林荣、赵瑜等学者,在鲁迅传记写作上成绩斐然。表层的传记书写指向传主鲁迅一人,而传记家却能够在其深处刻下属于知识分子独特的个性烙印和时代轨迹。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个体精神的变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个性意识的再度勃发、社会变迁的现实响应以及民族意识的现代化解读。而每一方面的变迁,都融合了相应时代的异动,折射出80年代至今中国思想文化的脉搏,与传记写作形成了一种互有叠合、相互指涉的关系。
个性意识的再度勃发
20世纪80年代以来,鲁迅传记写作经历了三个繁盛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80年代中期至世纪末以及新世纪以降。而这三个阶段知识分子对于鲁迅形象的解构、重构以及新旨的挖掘,都有其不同的书写原则。知识分子的个性意识继“五四”后迎来了再度勃发,映现于传记书写中,即呈现出被迫务实、多处突围、最后与“民间性”结合的变迁过程。
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值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前后,是鲁迅传记写作的第一个繁盛期。随着社会语境和文化格局逐步摆脱一体化,传记家的话语空间也有所松动,于是提出重现“人之鲁迅”的主张,并在传记中开始解构“神之鲁迅”。但在应和“回到五四”口号的同时,知识分子的个性意识呈现出“摆脱纯粹的理想主义,拥抱务实的人生态度”的特点,这与“五四”时期的个性追求是截然不同的,且这一个性意识带有被迫务实的嫌疑。
在此之前的鲁迅传记,包括王士菁的《鲁迅传》、曹聚仁的《鲁迅评传》、朱正的《鲁迅传略》等一系列作品,除去缺乏对鲁迅日常生活的叙述、对学术问题的分析略显简单、看人看事过近而少有宏大的历史观以外,最大的问题就是传记家们统一先入为主地把鲁迅当作“伟人”去写。这一点在此阶段的代表著作——吴中杰的《鲁迅传略》、林志浩的《鲁迅传》以及林非、刘再复的《鲁迅传》中,得到相应的改善。例如在林本中,作者不避讳鲁迅曾为国民党左派机关报《国民新报》主编,并且肯定该刊物中张荣福译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对鲁迅一段时期的战斗生活与思想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与影响。以真实的史料对鲁迅“神”的形象的解构,不仅可以从他作为普通文艺工作者开始,亦可以从一个渴望获得亲密关系的普通男性入手。林非、刘再复第一次在传记中将鲁迅、许广平、高长虹三人之间的关系交代详尽,其中包括高长虹为何受尽鲁迅恩惠后选择背叛以及“月亮”之争,等等。总而言之,这一时期传记家们开始以各种角度和形式重现“人之鲁迅”,这不禁使人联想起“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人本思想,但是其本质是大不相同的。“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大多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具有纯粹的理想主义激情,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体的关系往往是自上而下的,且知识分子秉承着一种崇高的姿态。但是80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虽也在极力表达个性,但是却没有摆脱理想曾被掩埋的悲哀情绪,所以此阶段的知识分子更加渴望回归朴素务实的生活。体现在传记中就是追溯鲁迅的童年——不仅怀念父母祖辈,还有保姆长妈妈,另外介绍鲁迅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交往全过程,并不一味记录鲁迅的写作生涯和革命斗争,而是多角度记录鲁迅的生活,比如与夫人许广平同游杭州、为女佣王阿花代付赎身费等事,等等。知识分子将自己的生活常态融入传记的写作目标之中,“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去写作一时蔚然成风。
在经历短暂的“解冻”后,学术界关于“新启蒙精神”“新人文主义”有了更为明显的界定和鼓励,知识分子于80年代中期开始大刀阔斧地对鲁迅传记进行重构:加深“向内转”的写作模式、革新创作形式与艺术手法等,力图实现时代性的突围。这场直至世纪末的突围是知识分子的个性意识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之下主动作出的努力,彰显了知识分子开拓创新的精神特质。
“方法论年”过后,文学界各体裁的创作与研究,都从“向外转”至“向内转”的趋势发展,鲁迅传记写作也不例外。以当时的几部传记为例,林贤治的《人间鲁迅》系列丛书(《探索者》《爱与复仇》《横站的士兵》)在写法上延续之前刻画“有血有肉的鲁迅形象”的创作宗旨,作者在突出文学性的同时把握鲁迅哲学的独立性,“特别是对专制与奴性的揭批(‘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对‘立人’思想的倡导(‘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个性张,沙聚之邦,转为人国’),以及对‘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的表达”[1]。这是对鲁迅精神世界的返真。曾智中于90年代初期出版的《三人行:鲁迅与许广平、朱安》作为国内首部鲁迅婚恋传记,专门从婚恋角度探寻鲁迅作为一个普通男性的心灵世界,不仅表达鲁迅对婚姻的无感和爱情的自卑,还有朱安“蜗牛”般一成不变、缓慢麻木的生活常态以及许广平对所经历之事的心底所想,都被作者以复调式结构同时呈现在一本传记之中,少有大篇幅地交代时代背景,皆是从不同视角去表达个体对他者的态度和外部世界的反应。从中仍然可以看到80年代初期“萨特热”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存在主义理论运用于“向内转”的写作方式,彰显出此阶段知识分子开拓创新的精神特质。此外,这二十年间鲁迅传记的创作形式与艺术手法也在不断革新,传记家们力图完成一场直至世纪末的全方位的精神突围。
一方面,比较体鲁迅传在文体范式上初露头角:朱文华《鲁迅、胡适、郭沫若连环比较评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开创了大陆首例传记新文体——连环比较体,但由于这部传记仍受到外部因素束缚,且作者拘泥于细部未观于整体,以致其在传记史上影响极为有限,却为新世纪的比较体鲁迅传开辟了新风;另一方面,不应忽视“向内转”在世纪末之前的鲁迅传记中已成“铁律”的事实。此阶段有多部传记聚焦于鲁迅个体的内心世界,如彭定安的《走向鲁迅世界》、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还有吴俊所著的非正式传记《鲁迅个性心理研究》等书,都立足于刻画鲁迅个人的生命本能:少年时期的凄哀、期待和忧郁,青年时期的呐喊和彷徨,中年时期的悲观、虚无和绝望,步入晚年又坚持“独站”的姿态。从个性心理的角度评述鲁迅的心灵历程,其间作者虽各有创新,但针对鲁迅心理结构和精神状态的写作角度基本是一致的。此阶段的知识分子不再有80年代初期的沉重顾虑,而是大力重构鲁迅“人之子”的形象,以一种突围的姿态面对市场经济导向下消费时代的大潮,那种“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精英姿态故态复萌,这种情况直至新世纪以降才稍有好转。
新世纪的前二十年间,鲁迅传记真正实现了以“新视角、新模式”的书写原则去挖掘鲁迅的新旨。例如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周晔《伯父的最后岁月》(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运用亲友视角作传,图传、画传式传记横空出世,以及企图透过鲁迅构建民国文学史、文化史的学术构想层出不穷,等等。这些新的书写原则都源于传记家不再囿于知识分子和研究学者的身份,转向“大”鲁迅传和“小”鲁迅传并行,“向外转”和“二度内转”分流的新形势,知识分子才得以以平民立场完成个性与民间性相结合的精神建构。
新世纪以降,随着史料的不断丰富,知识分子愈发关注鲁迅的社会关系,力图建构起一张以鲁迅为中心的人际地图,用以重新阐发民国时期的文学史、文化史。这样的作品虽不多,但贵在立意新颖,学术原创性强——例如鲍川的《鲁迅与义乌人》、朱正的《鲁迅的人际关系:从文化界教育界到政界军界》、李伶伶的《周家后院:鲁迅三兄弟家事》《鲁迅地图》,等等。建立人际地图的学术构想看似庞大,实际出发点却是书写鲁迅作为一个普通人是怎样在时代里发现并守护自我个性的,这与经历20世纪末摇摆的知识分子关于新世纪的现代化设想不谋而合。并且为保证原有传记顺利实现现代性转变而不失内质,传记家以图传、画传为载体进行鲁迅传记写作,其代表作品有黄乔生的《鲁迅图传》、吴中杰的《荒野中的呼喊者:鲁迅图传》、上海鲁迅纪念馆所编著的《鲁迅图传》等。可以说,画传、图传式传记的横空出世,是传记家打破传统传记写作模式,与美术品为载体所形成的新世纪的嫁接模式,是对鲁迅新旨挖掘、克服时代局限的成功示范。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在这一阶段的精神建构中,个性意识显示出返璞归真的意义。知识分子在结合了历史经验后,在传记书写中显示出多元与融合的态势,在精神建构中又以平民立场完成个性与民间性的结合。新世纪鲁迅传记书写最明显的趋势就是,“大”鲁迅传和“小”鲁迅传并行,“向外转”和“二度内转”的分流形势凸显。这里所说的“大”鲁迅传,指的是传记具有史诗性追求,即在传记中包含恢宏的结构、深厚的历史内涵、巨幅的篇章以及诗化的审美书写。这一模式在鲁迅传记书写中并不罕见,早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林贤治《人间鲁迅》三部曲、陈平199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鲁迅》皆是这种“大”鲁迅传的模式,新世纪以张梦阳的《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影响最甚。此书以全新的鲁迅观与独特的文体形式来呈现鲁迅的现实人生与精神世界,绘制出一幅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复杂世相,展现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独特的心灵史与精神史[2]。全书116 万字,以《会稽耻》《野草梦》《怀霜夜》三部分组成,最大的特点就是史与诗的交相辉映。仍然保留鲁迅作为“人”本身的日常生活、行为事迹、人际交往等内容,吸取此前传记求真、典型等原则,将审美的诗化手法纳入干瘪的时代背景介绍与鲁迅短暂又伟大的人生书写的缝隙中去,形成史与诗融合并存、相辅相成的局面。而这种局面正好契合当今学术界倡导的文学的“向外转”主张:着意在重新调整文学之内与外的关系、个体与人类的关系、审美与思想的关系、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叙事与道德的关系,等等。而其中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就是重新建立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血肉联系与紧密的契合度,锐意突进外部世界与国人文化心理,创造直逼当下和人心的自由叙事伦理,从而建构起属于新世纪的审美空间与精神生活[3]。“小”鲁迅传指的是新世纪的很多年轻学者选择从事与鲁迅有关的外部研究,例如薛林荣的《鲁迅的饭局》《鲁迅的门牌号》《鲁迅草木谱》,施晓燕的《鲁迅在上海的居住与饮食》,赵瑜的《恋爱中的鲁迅》《花边鲁迅》《鲁迅:照片背后的故事》等。这些作品可充当传记的一部分史料,或者说它们与传记之间的界限相对模糊,相比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向内转”,大有一种“二度内转”的趋势。此阶段的“二度内转”与之前“向内转”的不同在于,80年代中期西方存在主义理论对知识分子个性意识的影响,几乎是单向的且极为高调的;而新世纪的知识分子早已掌握与西方“和平共处”的方式:一方面,对西方自由主义精神表示理解,却并不认同其中个体与他者近乎敌对的关系;另一方面,与中国民间的世俗情怀紧密相连,并早已抛弃那高高在上的圣人姿态,将自身的个性与一切民间性的捕捉相结合。这些造就了传记家对新世纪鲁迅传记书写的新旨的挖掘。新一代的传记家们,在收获了几十年的前人经验与世纪之交的磨砺后,以平民立场彻底远离了对鲁迅理想人格的设计,而认同鲁迅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丰富多彩、人生历程的不拘一格,在消解崇高中完成对自身精神的洗礼与净化,充分将个性与民间性相结合。
社会变迁的现实响应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鲁迅传记写作并非一蹴而就的。几代知识分子几十年间对社会现实的持续关注,他们的社会关怀和忧患意识,直接映现于“在起伏中寻求稳定,在稳定中力图发展”这一写作趋势上来。
由于历史的惯性使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传记写作仍受“左”倾影响,具体表现在传主形象“高大全”、传记立意政治赋形、阶级性强细节失真等方面,知识分子面对这一情况依然坚持对社会现实的政治关怀,在起伏中寻求稳定,对个体精神建构进行自我纠偏与重塑。在张梦阳的《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三)》中,曾对林志浩的《鲁迅传》发表过以下评述:“鲁迅在留日时期就以‘革命党之骁将’的姿态,参加过实际斗争,却举不出实例,显然属于依臆想而拔高。”[4]而张梦阳将林著中所带有的“‘左’的印痕”仅仅归因于其写于“文革”后不久,这是略显片面的。根据鲁迅本人自述以及许广平、许寿裳等人的回忆录,这段史实是传记作者受“左”的政治羁绊过深而导致对鲁迅革命家人格“过度地拔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作者刚刚经历高度统一的特殊时期,一时无法将头脑中的想法转移至笔尖;另一方面是学者们仍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研究,短期内无法实现学力与思想同样深刻。林志浩在《鲁迅传》“后记”中也写道:“在前后期的比重中,更侧重于后期,上海十年写了十四章,比起前期四十多年的十三章来,篇幅还要多一些。从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六年每年都写了两章,一共写了十章,为的是忠实于鲁迅丰富的战斗生活,可以较为充分地展示他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格。”[5]传记作者将全本的主旨指向“一个革命者深厚的人情和崇高的人格”[6],说明传记作者仍倾向于将鲁迅革命家、思想家的身份提前,文学家的身份置后。
上述情况在90年代至今的鲁迅传记中得以改善,这一阶段的传记书写不仅仅停留在鲁迅形象的塑造上,同时也在加强学术性和审美性,扩大传记在传播领域的学术效应和社会效应。早在80年代吴俊就在《鲁迅评传》的结语中表示,他设想在《鲁迅评传》的基础上,完成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现代学术史或学术思想史论的编著。“这其中有两个问题或困难是必须首先解决和克服的,一是如何真正全面地把握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思想实质与精神面貌;二是如何用现代的科学眼光来审视和分析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7]传记作者并不局限于某一部传记的写作,而是为所有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全新的、可实现的研究路径,从而建构起一种健康的、互动互涉的作家传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术史的关系。四十年后的今天,知识分子仍在为这一设想贡献自己的努力。2021年11月9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举办第7 期传记论坛,主题为“互源与互构:重审作家传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关系”。陈子善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作为一部好的传记,必须要“跟文学史的研究产生好的互动。一本传记出来对象是谁?作者、研究者是谁?读者又是谁”[8]?传记在中国从一个非独立学科发展成为具有专业建设可能性的研究类别,书写主体传记家必须要建立起历史主体(传记家写作对象,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人物)、文本主体(传主,传记家创作出的人物)和阅读主体(读者)之间互源互构的关系,这样对于传记在创作领域的学术性和审美性提供了相应的保障,更是扩大了传记在传播领域的学术效应和社会效应。这不仅关乎于鲁迅传记写作的具体问题,而且对于当代传记文学本身的现代化发展也是极为有利的。
另外,此阶段老一代传记家在传记中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突显了鲁迅传记书写中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已逾高龄的陈漱渝在《民族魂·鲁迅传》的再版跋语中强调,当今社会有关鲁迅的博文微信中,充斥着大量对鲁迅的不公评价,虽然某些发言力图满足当今人们不良的阅读习惯,看似是情有可原,但这种社会现象是值得所有知识分子警觉的[9]。老一辈研究学者仿佛对现存事物始终保持居安思危的敏感意识,这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变相对鲁迅传记历史经典化的召唤,当代知识分子正是在前人行稳致远中感受鲁迅传记核心对其立德立身的影响。
民族意识的现代化解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记文学在与寻根文学、新写实写作、私人写作、底层写作共同发展的进程中,对“民族”“民魂”等关键词表现出更为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在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的今天,知识分子一边坚守“爱国思想为写作核心、力图回归民族传统”等书写原则,一边对这些原则进行现代化的思考和解读。
80年代的大部分鲁迅传记,仍没有放弃对鲁迅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形象的塑造,纵使其他方面有所革新,但爱国思想的核心没有改动。但随着90年代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世俗化浪潮的高涨,当代传记家对“民族”“民魂”有了新的认识,并且逐步在躲避崇高、消解崇高。自王士菁出版第一部完整的《鲁迅传》(上海新知书店1948年版),到八九十年代,传记家们始终没有放弃对鲁迅“民族魂”的书写,80年代传记中关于鲁迅“民族魂”的刻画,属林志浩的《鲁迅传》最具代表性:“鲁迅的崇高人格和精神,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五点:第一,鲁迅的骨头最硬,最能进行持久的韧性的战斗,这是他身上最可宝贵的精神。……第二,勇于改革的精神,也是贯穿鲁迅革命一生的一个重要特点。……第三,积极参加现实斗争,在斗争中严于解剖自己,这也是鲁迅精神的十分宝贵的特点。……第四,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最可宝贵的革命学风,这也是鲁迅身上突出的特点。……第五,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在文艺创作上的实践和主张,是深入生活,面对现实,勇于吸收,善于创造,这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财富。”[10]但是从中也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在强调鲁迅“民族魂”以及爱国豪情时,80年代知识分子主要围绕鲁迅思想家、革命家身份大谈特谈,忽视了作为文学大家的爱国情怀,传记家主观上区分传记文学与文本分析所作出的选择,变相使“民族”“民魂”的概念狭隘化。伴随着80年代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爱国主义被知识分子始终置于此阶段鲁迅传记的写作核心。知识分子一方面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牵引;另一方面陷入集体记忆的苦痛纠缠,所以他们在80年代对“民族”“民魂”的界定是自上而下的。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80年代中后期,文学界“重新认识民族魂”的民族主义思潮又一次影响传记家书写,90年代传记中关于“民族魂”的爱国核心思想,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如果说80年代鲁迅传记的“民族魂”充斥着崇高的社会性的集体意识,那么90年代的“民族魂”就带有一种个体的生命本能,还原了鲁迅生活和生命的无限生动和无尽复杂。吴俊的《鲁迅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主要呈现鲁迅的学术生平、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和学术影响,对于不同时期的文化心态、研究个性与思维方法进行评述,尤其是鲁迅在学术工作中严谨的治学品质和理性光芒,都表示他是一位贯彻始终的爱国主义者。吴俊也在评传中谈道:“我觉得与其说鲁迅的国学研究动机纯粹是出于学术、学理的探求,勿宁承认,感情的成份及其表现或许更为明显,更为强烈。”[11]传记作者一直在强调情感与理性是构成鲁迅治学心态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份情感来自于鲁迅心中绝望的孤独和极大的痛苦,又怎么能不与国家和人民相关呢?此外,当代传记家也在努力冲破启蒙话语的弊端,力图回到鲁迅本身,从个体生存的心理结构和思想困境的角度去重新解读“民族魂”。
反观新世纪前二十年间的鲁迅传记书写,是力图以个人历史与民族历史相结合,构建一幅以鲁迅为中心展开的别样的文化地图。知识分子用此方式丰富历史书写,回归民族传统,重拾民族自信心。其中,比较体鲁迅传更是显示出别样的特征:无论是孙郁的《鲁迅与胡适》,还是李继凯的《鲁迅与茅盾》、黄乔生的《鲁迅与胡风》以及董大中的《鲁迅与林语堂》,都指向传主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影响,以个人衡量历史价值,以历史评判个人得失,比较个体作为微观视角实际上是为历史宏观所考虑的,反过来从重构历史的宏观角度对个体微观的某些行为和所造成的影响就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孙郁的《鲁迅与胡适:影响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两位智者》,从性情、互往(二者之间的交往)、新梦(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倡导者与捍卫者)等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作者提到,20世纪中国是“被现代”的历史,“鲁迅与胡适在现代化之旅中的两种思考、两种选择,代表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精神路向。二者对现代性拥有既相近又充满对立的文化思路”[12]。事实上,20世纪的现代化,实际上是新型知识分子在面对国家存亡之际,被迫但主动对外国文化、制度等加以吸收和借鉴,并短暂摒除传统文化理念的不彻底、有弊端的改造运动。当代知识分子借传记书写对20世纪现代化加以回顾与反思,有几个目的:一是通过鲁迅、胡适等可以代表20世纪的文化智者为节点,还原历史细节,使现当代历史链条不再有缺憾;二是借此历史经验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提供参照。当今文学界是一个缺少大师与经典的时代,“何以大师、何以经典、何以未来”,这样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鲁迅与胡适的身上寻求答案;三是针对鲁迅传记而言,比较体传记更易突出传主的性格特点,尤其是两个在各方面差异很大的主体,例如鲁迅与胡适,我们很容易得出二者在政治思想(如平民化)、学术思想等方面的巨大不同。另外,80年代末90年代初,鲁迅研究界兴起了扩大研究范围的热潮,具体说就是开始了鲁迅同时代人的研究,研究同时代人,也是为了研究鲁迅。发展至新世纪传记,知识分子充分将鲁迅个人历史与民族历史相结合,用以构建鲁迅为中心的人际地图、文化地图。这也符合“在遵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前提下,继承传统,走向开放,拥抱‘现代性’”的“任何一种地域文化和文学所理应践行的发展方向”[13]。
此外,如何将传记书写落入民族传统书写之中,也是知识分子们在写作中直面的重要问题。换言之,如何在传记中实现历史参照与审美价值并存?张梦阳的《苦魂三部曲》可以代表当代知识分子给出一份答案:《会稽耻》《野草梦》《怀霜夜》分别对应的是鲁迅少年、中年、晚年时期在绍兴、北京、上海的生活经历,三地作为地域空间与鲁迅的人生历程经纬交织,不仅承载着鲁迅所有的行为活动,亦表现出不同地域20世纪初的时代风貌,为读者营造出一幅以鲁迅等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文化地图。“在构建绍兴、北京与上海这三个地域场所时,作者擅长抓取并精心刻画最具象征意味的典型物件来营造地域氛围,譬如写到绍兴时聚焦的乌毡帽、乌篷船、会稽山,写到北京时着眼的鸽子、琉璃厂、白塔寺庙会,写到上海时则选取了亭子间、老弄堂、外滩等等。此外,作品还对各地市井生态、民俗生态与民众生态亦进行了有声有色的描绘。”[14]张梦阳以文学性的审美书写运用于传记写作之中,用风俗画的方式对鲁迅生活的地域进行历史性的勾勒,是新世纪鲁迅传记写作的一大创新,也是对民族传统回归给予了知识分子最深的致意。
结语
本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鲁迅传记的书写着手,对知识分子精神结构的变迁进行了一系列梳理:近四十年间知识分子在个体精神建构方面的特质,主要体现在个性意识的再度勃发、社会变迁的现实响应以及民族意识的现代化解读。而这些方面与传记叠合呈现出时代性的变化,但也有着趋同的态势。当今,文学界对鲁迅传记研究亦百花齐放。近日,南京大学教授吴俊的新书《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成为传记作者将疫情期间自己的生命体验与鲁迅个人文学史相结合的范例。传记作者借这次书写尝试用朴素的方法回归文学,回归鲁迅,也回归自己的人间生活。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鲁迅与传记家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呢?笔者认为二者是一种同构兼重构的关系。一方面,传记家选择鲁迅,除去热点性、消费性等外部因素不论,能够在鲁迅身上找到“自己”(人格、治学经验等),二者之间形成同构关系;另一方面,传记家在力图重构传记时,利用当代社会、现代人格为参照,以此补足鲁迅生活时代的文化细节的空缺,这样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重构性。当然,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期待在未来关于鲁迅传记书写的研究中能够得到更为详尽的答案。
注释:
[1]张元珂:《寻根、对话、识见与大文体实践——论夏立君〈时间的压力〉的精神品格与当代意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4 期。
[2]董卉川、吕周聚:《以文学形式塑造形神兼备的鲁迅形象——评〈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9 期。
[3]张光芒:《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文艺争鸣》2012年第2 期。
[4]张梦阳:《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三)》,《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5 期。
[5][6][10]林志浩:《鲁迅传》,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431 页,第509—510 页,第497—506 页。
[7][11]吴俊:《鲁迅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 页,第138 页。
[8]陈子善、辜也平、房伟、易彬、张元珂:《互源与互构:重审作家传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关系》,《传记文学》2022年第1 期。
[9]陈漱渝:《民族魂·鲁迅传》,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98—201 页。
[12]孙郁:《鲁迅与胡适:影响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两位智者》,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8 页。
[13]张元珂:《绽放在沂蒙大地上的民族之花——沂蒙精神与沂蒙文学互源互构发展史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1 期。
[14]黎丹丽:《传记学视域下〈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研究》,绍兴文理学院2020年硕士论文,第3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