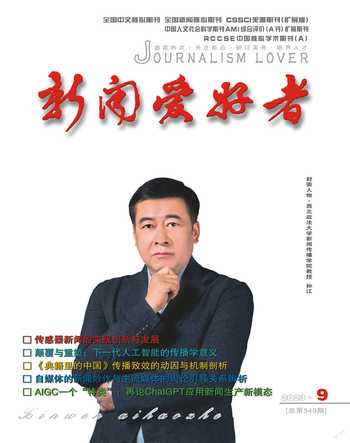“刷礼物”:网络直播中的符码操纵与拜物迷思
钟知伦 周祉含
【摘要】以B站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借助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理论视角,重新思考了网络直播中的“刷礼物”现象。梳理“礼物”概念变迁与其引发的交互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发现支撑莫斯式互惠交换的礼物之“灵”在数字时代成了鲍德里亚批判的消费之“因”,即平台消费规则集置下的符码操控,但参与其中的观看者并非全然无意识的消费者,他们在策略性使用中展现出了抵抗符号拜物迷思的能动性。
【关键词】礼物;刷礼物;符号拜物教;鲍德里亚
无论何种社会形态,都有“礼物”存在——它推动社会关系建构,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长久以来,“礼物”都承载着文化意涵。进入数字时代,“礼物”的所指变得更加宽泛,尤其在“直播”这一新兴行业兴起后,更以“刷礼物”的全新样貌面向大众。然而,需要追问的是:从传统社会到数字社会“礼物”的内涵是否依旧如初?若“礼物”内涵发生变化,那么从“送礼物”再到“刷礼物”的行为变化中,社会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最为重要的是,如何以反思的视角看待这一变迁?这些是本文试图讨论的主题。
一、理论回顾与研究方法
(一)重看“礼物”:数字时代“礼物”的另一种讨论可能
最经典的“礼物”研究无疑是法国学者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1925年发表于《社会学年鉴》上的《礼物》。莫斯通过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扎实的资料和文献分析,对“礼物”交换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礼物”的“总体呈献体系”。该体系将“礼物”的交换分解为三个环节,即送礼、收礼和回礼,经过三个环节的相继发生,“礼物”得以在整个体系中循环往复,进而完成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比较有趣的是,莫斯发现了收礼和回礼发生的强制性机制,即“礼物之灵”的存在。如果不及时将“礼物”送出将会为自己招致灾祸;如果不接受“礼物”将会面对赠予者的猛烈攻击。“礼物之灵”在萨摩亚人和毛利族那里分别被叫作“曼纳”(mana)和“豪”(hau)。[1]可见,尽管礼物运作的动力具有某种神秘主义色彩,但其归根到底是切己的,并以它为基点展开交往和互动。“礼物”交换通过莫斯的分析揭示了传统社会中最朴实的交往观念。
在中国语境下,杨美惠通过“礼物”的流转揭示了在一个特殊时期中国特定关系学的发展形态。杨美惠在研究中发现官方意识形态所排斥的关系运作与民间中的常见实践能在一个人身上并行不悖地实现。通过“礼物”的馈赠,个人完成了区别于国家型的主体性建构。[2]阎云翔受杨美惠启发,以下岬村为个案,以“礼物”为具体研究对象,探讨农村那种有序却兼具“非制度化”的结构特点。[3]值得注意的是,二者都发现了“礼物”流动中的人情和面子。在这里,莫斯眼中的“礼物之灵”褪去了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切实地落在了社会心理层面,其制造的效果是所谓的“势”,这是一种更为阴柔的支配性权力和效力。总体看来,围绕“礼物”的经典研究,都揭示了礼物的交换性、物质性、道德性以及商品性等诸多特点,这些相对集中的特征也在数字时代的“数字礼物”(Digital Gift)上有所延续。
随着直播行业的蓬勃发展,“礼物”最终以“刷礼物”这一数字的形态出现在了直播这一全新产业。也因此,“刷礼物”和直播常绑定在一起进入研究视野。对直播和“刷礼物”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有学者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切入点,揭示对主播生存空间挤压和剥削[4];也有学者从粉丝视角出发,研究多集中于情感劳动,并以此为情感冲动带动“刷礼物”的热潮,从而实现情感变现。[5]总体来看,刷礼物的现有成果多是从“情感劳动”等范畴出发,就其根本,仍是属于马克思式的“生产”领域。然而,在充值、购买并送出“礼物”的行为中其实蕴含着生产的另一个面向:“消费”。“刷礼物”这个活动的最直观含义就是消耗和给予,因此,如果从“消费”领域回看“刷礼物”或许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二)符号拜物教视角的初步搭建
作为消费理论的代表学者,让·鲍德里亚难以绕过。以《物体系》《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三本著作为代表,青年鲍德里亚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其中,最具创新性的是基于马克思“拜物教”概念发展出了“符号拜物教”批判理论。
在马克思看来,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奴役一切并获得多数人认同的机制。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一个思想前提就是要打破拜物教意识形态。然而,鲍德里亚认为,现代拜物教已经延伸到了一切生活领域,且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将整个社会体系中的特权和差异作为符号价值,变成自己的崇拜对象。鲍德里亚用符号学重解了“消费社会”拜物教的内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鲍德里亚想强调,基于生产主义的真伪区分已经没有价值,重要的是符码的编码过程。因此,现代意义上的拜物教,是一种符號的编码结果,拜物教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符号的操控过程。拜物教不再是对特定物体或特定价值的神秘化,而是体系的神秘化——物体只有将自己置于体系中,通过差异与编码才能获得自己的位置。[6]鲍德里亚的符号学拜物教批判在今天的数字时代极具启发性。它为解答“刷礼物”行为的含义以及“礼物”数字化的后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三)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根据研究选题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来说:研究者首先通过有偿招募的形式召集受访者,在核对访谈对象充值和刷礼物的相关截图证明后,开始正式访谈。本次研究中的访谈环节全部以腾讯会议的形式在线上进行并全程录音,访谈时长均在50分钟左右;后期就关键名称和个人信息与受访者反复校对,以保证准确性。此外,研究者还加入受访者推荐的UP主粉丝群以开展参与式观察,从6月确定选题后一直在群众中观察互动情况,并继续对群内的活跃粉丝进行有偿访谈,确保观察和访谈的一致性。因从第八人开始,关于主播和观众关系界定等问题已经出现重复和饱和情况,在补访两人后,便停止材料收集,共计访谈对象10人。
二、从“送礼物”到“刷礼物”:“礼物”及其关系结构变迁
根据研究发现,在“送礼物”到“刷礼物”的演变过程中,“礼物”按鲍德里亚的分析,本身从物的物质性走向物的符号性,符号结构的差异逻辑恰好赋予各类“礼物”不同阶序的意义,同时物的结构差异也对社会关系进行了编码和建构,使互惠循环的文化关系成了隐蔽且多样的经济关系。
(一)“礼物之谜”:对“礼物”类型的再思考
要对“刷礼物”及其关系问题进行探讨,必须先对“礼物”类型及其性质进行再思考。本研究将“礼物”初步分成线上和线下两种样态。研究发现,受访者对线上“刷礼物”意义的理解总体一致。例如,受访者eww认为刷礼物为主播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撑,因为“如果观众不给他打赏,主播就没有办法直播下去了”。受访者773则认为“刷礼物”的意义在于情感反馈:“我很喜欢听我自己名字被念叨的那一刻,我非常喜欢听那个声音。对,我甚至会把主播念我名字id时的音频录下来。”总体看来,对线上“刷礼物”的意义的理解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为主播带去收益和认可,二是为自己带来满足和反馈。
在询问到线下礼物的意义时,每位受访者都更加健谈,很乐于分享自己最近的送礼经历。受访者Triptych回忆说:“我朋友他们搬新家了,因为他是画画的,我就想在他阳台上布置一个工作间,我觉得那里光秃秃的,看到他可能要坐在地上,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个地毯。”我要减肥说:“发了工资在‘618’给女朋友买了iPad,因为她在复习考研嘛;然后我给爸爸买了一台按摩椅。”当追问每位受访者线下礼物的意义时,每个人都先停顿了小一会儿才开始分享自己的理解。受访者Jhesxltrso认为:“在线下送礼物可能会想得更多,包括礼物的金额、质量,然后或者数量之类的,而且我觉得还需要有一些噱头,比如说某个节日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可能想要为送礼物找的借口,或者是看礼物合不合适,要给它找的原因相对来说是牵绊比较多的。”将以上所有礼物形式并置,再探讨其中意义的差异后发现,每个人都会按照亲疏远近的关系形成自己的“差序格局”,从中心向周边展开的过程中“礼物”的样态逐渐转至线上且随意。
鲍德里亚曾在《物体系》中将物分成功能性物品体系、非功能性的物品体系、过度功能化的技术体系以及作为消费意识形态的文化体系。[7]其中,物品逐渐从功能性过渡到非功能再到符号性的价值之中。“礼物”从实体走向虚拟,正是不断抽象和数字化的过程。正如不同符号之间以差异性获得意义,“数字礼物”同样是在系列符号的并列与差异中获得其意义和符号价值,它们的价值并不来自物质性的使用价值,而是符号差异带来的阶序落差,以及由此互相衬托出的价值意义。如鲍德里亚所说:“它们是在相互暗示着更多意义的高档物品,从而使得消费者滋生出一系列五味杂陈的动机。”当“礼物”本身被抽象符号性所主导,就进入“人的关系和人际关系系统”[8],因此,“刷礼物”不再是具体的物品消耗,而是对关系本身的消费。对“数字礼物”的虚拟性、经济性与消费本质再发掘后,接下来将转入对于“礼物”关系的再定义。
(二)锚定“数字夸富宴”中的相对优势地位:对“礼物”关系的再定义
如前所述,莫斯笔下的“礼物日常交换体系”是秉持互惠交往的原则,其道德性胜于功利性,但在直播间里,随着“数字礼物”和“刷礼物”行为的中介,直播间内的关系将会被重解为不同关系类型。
围绕礼物交换形成的关系结构涉及两种类型:一是前述以礼物为核心所形成的非功利交往结构,二是基于这一交往结构形成的等级关系。前者是莫斯在《礼物》一书中开宗明义的研究对象,即理论上是自愿的,实际上却是义务性的送礼与还礼的交换结构。[9]促成这一体系持续运转的是所谓礼物之“灵”的力量。原始社会的各个部落也在“总体呈献体系”的循环过程中形成暂时稳定的等级关系。[10]实际上,这场象征互动行为有一种政治考量,即为了“在不同群体及其首领之间建立等级关系,赠送、摧毁财富最多的人就是最强者”。[11]在荣誉上压过对手的冲动,也制造主奴关系的冲动。
在数字时代,随礼物形态变迁赠受双方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平台的匿名性、观看的单向性与聚集的临时性趋近于莫斯笔下的不稳定等级社会,通过“刷礼物”的符号狂欢,观看者与主播、观看者与观看者在符号互动间都在锚定自己的位置——确立相对优势关系的冲动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例如,观看者常以“打赏”的心态定义自己与主播的关系。在受访者773眼中,网络直播与“虚拟风俗业”无二:“我觉得流量、时间和金钱一样,都是属于你们付出的一个成本,他们应该以服务来回报。”也有观看者以“交易”的态度平等看待双方关系,比如受访者TY觉得刷礼物“是消费和服务这一类,无论是知识消费还是说其他什么消费”;受访者eww将主播视作“内容输出者”。但是这种关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会出现转移和变化的情况,受访者Jhesxltrso指出:“它最开始肯定就是消费者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这么一種关系,然后如果你看主播看的时间长,然后对他本人的一种个人魅力或者直播风格有了喜欢的感觉的话,可能慢慢就会转化为粉丝和爱豆之间的关系。”观看者最初的平等甚至俯视的态度,会在长期互动中变成仰视,这也体现出了参与者在以符号狂欢为手段的“数字夸富宴”中的地位变化。
尽管礼物形态与赠受关系发生了变化,但促动整个关系结构运作的礼物之“灵”仍兼具荣誉与惩罚的“双重属性”[12]——对通过符号互动积累文化与经济资本的渴望,以及对失去持久礼物来源的恐惧共同促成了直播间符号狂欢的景观。这印证了鲍德里亚的论断,消费成了一种主动模式,也体现着关系。深陷其中的大众成了无意识的消费者,在大众媒体引诱下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盲目活动。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本次访谈中,研究者发现了无意识消费论断之外的特例,即有意识的策略行动。
(三)有意识策略行动:作为“代币”的礼物
在网络直播语境下被平台结构了的观看,其实并非是全然无意识的冲动消费,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策略行动,除空洞的符号游戏外,还有将礼物作为代币的考量。被冠以符号拜物教下无意识行动者名号的用户显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能动性。
平台时代“刷礼物”还要面对另一个问题:抽成。在被问及是否了解抽成情况时,一半受访者表示并不知情,另一半受访者表示清楚了解。而当前者了解抽成比例后,表示不能接受:“对我来说,其实我会很在乎。说实话,我觉得他们的劳动付出得这么多,而且可能作息还不规律,甚至要直播到凌晨那种,究竟能不能和他们的收获成正比,其实我会挺关心这个的。”
本研究发现了的第一个“例外”现象就是源自上述情况:礼物作为一种“代币”用以支付给主播。在面对平台剥削时,主播和理性的“消费者”结成了一个新的“联合体”。烟水微茫表示:“我如果要打赏的话,数额比较大的那种,我就直接从微信或者支付宝转账就好了。”主播这边也会选择迂回提醒的方式,降低“消费者”不必要的投入。虽然直接支付能避免B站在礼物收益中的抽成,但对于主播自己未来职业发展来说是不利的,像受访者Jhesxltrso被问到跨平台转账时,她解释:“如果是你私下给他转礼物的话,在平台上是没有这些扶持的。所以等于B站抽的那一部分,它一方面是给了你一个在相关分区里一个位置的资源位的提供,然后另一方面它会定期给你做一个流量包,或者是官方的一些分区活动之类的东西,等于把这些钱给B站那边相关分区管理的一些工资。”于是,作为“代币”的偿付机制成了主播的折中选择。受访者TY谈到自己用“刷礼物”作为“代币”的经历:“具体描述的话,就是游戏中有一个任务我过不了,然后他因为技术好,所以我就让他帮我过,你可以理解为花了130多元钱,让他帮我把这个事情搞定了。”由此可见,强大的平台结构压力导致这个“联合体”在抵抗的同时又不得不依赖它。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每个消费者并不像鲍德里亚说的那种受符号操纵而深陷拜物教的迷狂状态,但他们又陷入了新的矛盾状态。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Bilibili平台直播间“刷礼物”这一逐渐自然化的社会现象进行重新思考,发现所谓“礼物”的概念在数字时代存在断裂与延续,即在礼物形态与关系上的断裂以及在话语修辞上的延续。具体来说,礼物在数字时代的多平台经济模式下,已然出现意指关系断裂的倾向,并在“刷礼物”这一完全虚拟化的互动场域中达到最终形态。直播间内可选择的“礼物”只是代码组合在界面层呈现的能指素材,其所指内容不再与实物相关,并在直播间的礼物规则下转向了能指间的拼贴组合游戏。在这个过程中,礼物的价值来自它们在自己构成的能指链上的位置,意义也来自于相互咬合的链条关系。例如,“玫瑰”和“辣条”的意义不在于指代具体的植物或食品,而是在直播间中送出的符号资本,并且,礼物形态的变化也导致礼物关系的变化。莫斯笔下的“送礼—收礼—还礼”的三元“总体呈献体系”在平台默认收取的“充值—消费”逻辑下,简化成“送礼—还礼”。这一新的礼物关系加速了整个类交换关系在数字时代的节奏,送礼者获得了来自他者的承认,还礼者含蓄地表达了深化关系的期望,以期能在主播群体中积累自己的社会、经济资本与职业名望。
另外,莫斯的礼物之“灵”在直播间“刷礼物”的新语境中也有了新解释:它不再是因带有经手人痕迹的实物而带上的宗教性力量,而是在平台架构的消费规则中策略性组合符号资源以提升和维持自己社会地位的经济动因。在后者的符号组合活动中,“刷礼物”的双方既受制于平台规则,同时也以默认的态度再生产和强化了这个结构,从而为平台积累数据资本。因此,本质上,礼物交换动力是从莫斯式的宗教之“灵”变成了鲍德里亚式的消费之“因”,即外在于主体的结构以创造规则与操纵符码组合可能的方式,将主体纳入了“刷礼物”的活动中来。
最后,本文还想作出的理论修正是,主体在其中并不如鲍德里亚所说完全无意识的参与。他们或以礼物为代币的形式转译平台规则,或以跨平台转账的方式绕过平台抽成。无论哪种方式,都体现出了符码操纵下的另一种主体自觉,即有意识地与平台与结构进行抵抗,寻求两全之策。然而,尽管如此,平台对主播与看客之间在经济抽成和数据积累的双重剥削下,仍是不可完全忽视的现实,这是要參与平台游戏时无法绕过的无奈。现在能做的,或许是不断识破平台布下的一个又一个符号拜物教迷思,从而保持主体的清醒与自觉。
参考文献:
[1]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2]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M].张旭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3]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张一璇.劳动空间在延伸:女性网络主播的身份、情感与劳动过程[J].社会学评论,2021,9(5):236-256.
[5]涂永前,熊赟.情感制造:泛娱乐直播中女主播的劳动过程研究[J].青年研究,2019(4):1-12+94.
[6]仰海峰.符号之镜: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75-190.
[7]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17.
[8]孔明安.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研究[J].哲学研究,2002(11):68-74+80.
[9]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6.
[10]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87-190.
[11]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6.
[12]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98-203.
作者简介:钟知伦,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北京 100081);周祉含,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博士(北京 100088)。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