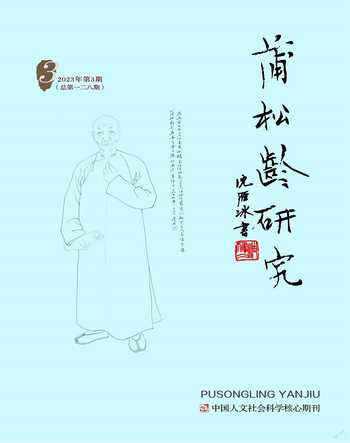新世纪聊斋电影的改编脉象和原因探析
赵庆超 夏菲凡
摘要:受到大众文化、网络语境和新媒体技术的催生,新世纪以来的聊斋题材影片出现了宗教元素泛滥、情感戏份膨胀、闹剧精神蔓延的改编脉象。制作者对虐恋、同性恋、无厘头、“二次元”、御宅以及萌文化等多种外来亚文化元素的借用与整合,为聊斋电影改编提供了多种机遇,也孕育着重重的危机。因此,立足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思考基点,勘探改编过程中出现的艺术盲点,防范因为改编不当而可能带来的话语风险,进一步为新时代文艺添砖加瓦,将显得迫切而重要。
关键词:新世纪;《聊斋志异》;电影改编:宗教;闹剧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志码:A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大众文化的勃兴,人民群众审美消费的多样态症候也日益凸显出来。由于全球化思潮的强力拉动,这种消费症候诉求在新世纪渣滓泛涌的复杂语境里更加趋于“合理化”和“必然性”,进而从需求关系上加速了审美文化生产与输出的多元化步伐。因此,受到现代性、后现代性、民族化、全球化之间多边互渗的“犬牙交错”关系的影响,聊斋小说的影像改编和审美“再生”必然交叠着多重话语的梳理痕迹。原著作品的古典意蕴在新世纪的文化语境下遭遇到大众审美消费话语赋魅与祛魅的反复涂抹,传统文化内涵一方面在影像生成中得以感性转换,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被浅思维接受风潮遮蔽、放逐而弱化散逸的时代风险,其影像改编的价值路径也呈现出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陈晓明针对“后革命”年代消费主义、游戏主义和享乐主义兴起的语境氛围,认为“革命变成一个庞大的洞穴,所有的求生者和逃离者都变成寄生者”,因此“寄生的法则就是‘后革命的辩证法则” [1]。由此类推聊斋电影的新世纪再生产状况,不难发现同样也存在着类似“寄生”的法则,只不过拥挤在“聊斋”名号下面的更多是文化审美的“求生者”,它们更愿意借着聊斋文化的“老字号”招牌悄悄夹带和兜售个人的“私货”,通过制造卖点和噱头来换取更大的商业利润。这种浅思维消费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中小成本制作的众多网络电影中更加趋于流行的态势,当然不同的文本所涉及的问题也不尽相同,需要结合具体文本加以辩证分析。所以,这类作品的改编脉象及其背后的生成原因就成为笔者探究的重点。
一、宗教元素符码泛滥
聊斋电影在新世纪的创编繁盛显然与“后革命”年代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泛革命氛围的进一步退场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为包括聊斋小说在内的古典传统资源的审美再接受提供了“合理性”的语境条件。但由此带来的影像改编叙事更容易剥离其深邃理性的思想内蕴,从而披挂上大众消费的感性化外衣。因此聊斋小说里镶嵌在因果叙事链中与其主题预设相互关联的审美化、知识性的宗教符号,在改编电影里容易被变换走形,甚至蜕化为干瘪零散的形象符码。
在《聊斋志异》中,直接与道教有关联因果报应的小说都约占三分之一,有近40篇写到僧侣生活或涉及僧侣的有关活动,涉及鬼狐、神仙和精怪的共有331篇,约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而在异类形象的塑造上,鬼有144个,狐83个,神68位,仙47位,共382个,其中有姓名、身份之类明确称谓的为288个 [2]。因此从传统宗教元素的呈现角度来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描绘了诸多的生命个体在仙界、妖界、幽冥界与人界之间的生死轮回故事,并蕴含着复杂的因果报应的天命观和宿命论。在其中,和尚与道士身怀绝技,离开寺庙、道观后进入荒村宅院捉鬼打妖,惩凶缉恶,既承担了民间侠客与官差捕快的部分功能,又暗含着作家一以贯之的社会性想象和宗教式情感,因此存留着历史文化传统漫长积淀的民族思维习慣,但由此把这些仙妖鬼神的审美元素完全定位到作家的本体论观念层面上也不尽准确。
其实,蒲松龄对于鬼神世界的认识态度是比较复杂的,他往往在抽象的层面上相信冥冥之中有神灵,但在具体层面上又把它们当作心造的幻影和心灵的寄托来完成精神上的自我慰藉。有学者认为:“蒲松龄从客观、主观两方面都不可能摆脱有神观而成为真正的唯物者,反过来,他的个别的、片断的反神言论和观点也不足以改变他的有神的总方向。” [3]明季清初改朝换代之际的社会苦难和科举屡屡不中的个人遭遇,在不断加深他现实认知的绝望情绪的同时,也容易把他推向主观唯心主义精神世界之中,在皈依宗教世界的审美寄托中得到镇痛和麻醉,借幻想中的鬼神威力来惩处制造苦难的异己力量,从而为现实和个人的不幸造梦。但儒家文化实用主义观念的长期影响,使得聊斋小说中的宗教寄托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不了作家别有所指的工具论色彩。
因此,与干宝创作《搜神记》时生发的“发明神道之不诬” [4]原序1的观念预设不同,“蒲松龄并不相信他自己的虚拟的故事、虚构的狐鬼花妖,是真实的和现实世界中可能有过的,他也无意让读者真正信以为真” [5]前言10,他主要是通过“假神道以设教,证因果于鬼狐” [6]的审美虚构方式来实现自己儒家教化和现实劝诫的良苦用心,所以其小说中这些形象符码的设定具有更多的功能论层面的呈现价值。潜意识里积淀承传的原始崇拜的泛神思想、佛家散布的果报观念和道教的神仙学说在蒲松龄的精神世界里相互融合,与儒家的天命观、善恶说一起成为建构小说主题意蕴的重要内容,这种审美层面的宗教赋魅更多地成为他现实奖惩的隐喻书写方式,其神秘主义的知识性凸显并没有与三教融合的文化传统语境相脱节,反而在似信非信的鬼神仙妖叙事中绽放出诡异而迷人的绮丽风采。因此,“蒲松龄在接受宗教文化影响的同时,又主动自觉地利用宗教文化观念、形式来进行小说创作,达到救世和自救的目的” [7]228,他在向这一现实目的努力的同时,进一步自觉地打开了浸润着宗教情结的人与异类浪漫共存的传奇化视窗。
在科学理性昌明的当下时代,不仅鬼神的“在场”变得虚无缥缈,宗教的信仰救赎也因为唯物主义话语的丰盈而显得遥不可及。因此,聊斋电影的宗教祛魅便更加趋于顺理成章,聊斋小说所彰显的作家冥冥之中认为有神而实际上又对之半信半疑的混沌性认知,在新世纪的“无神”语境里被淡化稀释,归结为万神“退位”的清晰化判断。但由此建构的影像世界中的宗教符号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在艺术层面上被赋魅化处理,常常横亘在改编电影上天入地、打鬼捉妖的叙事链条中,化为了丰富主题内涵、增加审美亮色的影像风景线。在这些影片中,宗教元素的本体论“退场”与审美呈现的工具性赋魅成为吊诡式的存在,诸多宗教元素的泛滥其实暗含着大众消费娱乐化风潮的风生水起。
首先,这些元素背后更多流露出后现代式的戏拟化生成技巧。在电影《白秋练》(2006)及其同名小说中,虽然由洞庭湖真君转生的道士都对慕蟾宫与白秋练的跨界恋情进行了助推,但影片中的道士增加了迂腐滑稽的新貌,他一方面法力无边,宅心仁厚,另一方面又不断被戏弄,出丑搞怪,极尽世俗娱乐之能事,避开了蒲松龄对宗教神秘力量的敬畏之心,而沾染上癫狂表演的大众娱乐气息。这种改编倾向在《儿女仙踪》(2005)、《聊斋新传之奇女子》(2019)、《大梦聊斋》(2020)、《奇花记》(2021)、《聊斋新编之渡情》(2022)、《聊斋新传之画皮人》(2022)、《猎妖记》(2022)等诸多影片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改编者于原著基础上增添的捉妖队伍更加趋于多样化,和尚、道士们离开自身居住的道观寺庙与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在极具传奇性的场景打斗中放大了僧侣生活的底蕴,却放逐了原著小说借用佛道元素的严肃立场。同样,改编者也远离了港台早期聊斋电影的僧道形象处理方式,不但像鲍方的《画皮》(1966)里那样鹤发童颜、除鬼扶弱而大义凛然的道士不见了,而且如胡金铨的《侠女》(1971)中那样氤氲着神圣佛光的方丈大师也尽行消失,这类人物形象在大众娱乐中的“出场”隐藏着改编者消解宗教情怀的戏拟性态度,去神圣化的工具性调用决定了宗教元素在被知识性萎缩的同时,也经受着功能论意义上的衰减。
其次,这些元素粘连着更多虚构世界的游戏主义倾向。相对于聊斋原著而言,新世纪的许多改编影片纷纷消除了改编取材上的文化顾忌,借聊斋名目在情节建构上另起炉灶,通过夹杂着宗教符码的正面力量与邪恶异类势力之间的激烈对抗,来完成升级打怪的游戏虚构。在万神退位、魔鬼狰狞的后现代语境下,这些聊斋影片所使用的宗教符号大多蜕化为游戏符码,失去了聊斋小说里充盈多义的意文化深层所指,而风化为猎奇耍宝的干瘪意符,从而沦落为大众娱乐生产线上的滑稽变体。在取材于《婴宁》的《大梦聊斋》(2020)中,改编者镶嵌了婚礼僵尸、丑怪修罗、冥间妖娃、天煞戮神、铁甲伏魔卫等异类形象群,并与絮絮叨叨的驱魔道长、上天入地的降魔师、美丽动人的青丘狐女、法术拙劣的炼妖师相互勾连,上演了附体为魂、借体转世的跨界轮回故事和善恶相生、邪不压正的叙述套路。这些来自冥界的异类他者与奔走于阳间的捉妖道士之间产生了许多啼笑皆非、逸趣横生的离奇故事,成为蔓延在《侠女复仇记》(2005)、《聊斋新编之画皮新娘》(2016)、《玄夜狐影》(2021)、《阴阳画皮》(2022)等诸多聊斋电影里的叙述模式,“由生死轮回强调个体生存的绝对性” [8],从而挣脱了古典文化的传统羁绊,改变了聊斋原著小说的道德惩戒和宗教赋能意味,而滑入了大众文化的游戏消费预设之中。
最后,这些元素不断呈现出更加鲜明的现实指涉意味。纵观新世纪聊斋电影的改编历程,不难发现的是后来涌现的网络电影中的宗教元素更加泛滥,几乎让这一阶段的院线电影望尘莫及,但其蕴含的宗教意味却越发稀薄,在价值依托上更加靠向了当下的现实。不像《画皮》(2008)、《倩女幽魂》(2010)、《画壁》(2011)、《神探蒲松龄》(2018)这样的院线大片在宗教元素的运用上还比较慎重,《聊斋之极道天师》(2020)、《倩女仙缘》(2020)、《妖手摧花》(2020)、《倩女幽魂:人间情》(2020)、《新画皮》(2022)之类的网络电影因为制作成本的限制,在审美输出上容易不自觉地淡化了精品意识,主要来满足网络受众的情感宣泄和消费欲望。对宗教元素的使用则更显随意性和空洞化,召之即来的捉妖道士、落入俗窠的因果报应、可望而不可求的人仙遇合、众妖离席后的胜利大团圆不是在回应聊斋文化的改编传播,而是为满足现实日常生活的庸常寡淡与精神匮乏。这种浅层次的意蕴建构和花里胡哨的影像拼贴收拢了聊斋小说的叙事格局,化高冷的宗教隐喻为喧嚣的世俗异托邦,在瞄向现实的话语降格中抽空了原著小说的深意寄托。所以,网络电影关于宗教话语的流布,更像是一把双刃剑,它们一方面推动了僧侣道士、冥界仙域等宗教符号的大众传播,另一方面又斩去了这些审美符号的传统指代,变为了轻飘飘的消费义符浮现在现实指涉的上空,这种愈演愈烈的网络电影改编倾向值得警惕。
二、情感戲份不断膨胀
《聊斋志异》建构了庞大的书生群体与异类形象之间的情缘故事,这些穷困潦倒的书生虽然带有作家个人自叙传的想象成分,不免有些千人一面,但他们艳遇对象的异彩纷呈(人、仙、鬼、妖等)推进了跨界叙事的浪漫化和传奇性,这种传奇加浪漫的言情内容恰恰成为聊斋小说的重要审美徽章,也成为后来电影作品改编演绎的先在基础。新世纪的聊斋电影一方面稀释了原著小说的宗教内涵之外,另一方面却着意增补拉长了角色形象之间的情感故事,在人与人、异类与人、同性与异性、同性与同性之间的多边恋情中凸显自身的戏份卖点。情感戏份的不断膨胀既延伸了聊斋小说谈狐写妖、书生遇艳、人鬼不分的言说传统,也迎合了当下人们面向传统寻求精神新变的潜在消费需求,这种改编倾向较之前的大陆同类影片而言变得更加鲜明,进一步对应着后革命年代日常情爱话语强势“在场”的语境症候。
首先,营构不同形象之间的多角恋情故事成为新世纪聊斋电影改编的一个重要热点。在蒲松龄生活的明季清初,传统社会里的乡村生活仍然相对封闭,青年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主要建构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类似于前喻文化 ① 的长辈设计中,他们婚前婚后的异性组合方式相对单一,虽然《聊斋志异》在跨界叙事中通过奇幻的想象铺开了鬼狐等幻化的异性女子主动接近书生们形成相对复杂的情缘遇合,但很难对位小说诞生时乡土中国的现实语境。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小说的这种情缘虚构在时过境迁的当下影片中不断凸显,被改编拉长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多角恋情,在异性或同性之间的张力与合力中撕扯纠缠,成为新世纪此类电影改编的重要审美亮点。
在电影《画皮》(2008)中,原著中的厉鬼变为狐女小唯,被蜥蜴精小易追求,王生成为了武将,情感迷失在小唯与妻子佩蓉之间,而捉妖师庞勇对佩蓉念念不忘。这部影片以王生、佩蓉、小唯之间的三角恋情为演绎重心,描绘了小三上位与失位的复杂历程,又勾连起其它的情缘关系,形成了多个三角关系串在一起的复杂网络,呈现出对当前婚恋现实的内在隐喻。在《倩女幽魂》(2010)中,小倩同样由原著中的鬼女变为妩媚可爱的狐女,先与猎妖师燕赤霞产生了一段美丽的前缘故事,又在宁采臣出现后二男一女之间形成了曲折的三角恋情,这种横亘在猎妖者与狐妖、柔弱书生与深情女子、男性情敌与共同对手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扩充了原著小说的叙事格局,也在通俗的意义上放大了人物情感世界的内在矛盾和多元化诉求。电影《翠狐戏夫》(2020)增加了狐女小翠上一代之间的恩怨故事,小翠之母虞姬深爱同门师兄袁生,却遭到师妹紫玉的嫉妒和陷害而被师兄误解,恋人被紫玉抢走后,自己忍辱负重抚养女儿,最终云开雾散,赢回了袁生的回心转意。改编自聊斋散文体小说《绛妃》的影片《妖手摧花》(2020)同样在男女主人公宋逸尘与绛妃之间的情爱故事基础上增加了上辈人的悲情“前史”,绛妃的姑姑与同门师妹紫玉都深爱着师兄江郎,后来紫玉为增加功力偷吸活人精血被逐出师门,心生怨念刺伤江郎,化身猎妖族族长雷宁儿报复绛妃的姑姑,在人界和仙界掀起了惊天动地的血雨腥风。改编者在诸如此类的多角恋爱框架中融入了情爱或情殇的故事内核,通过人物之间多对一、多对多的复杂感情的艰难分合深化和升华了原著小说的主题意蕴,就容易把受众带入与现实世界多方对位的情感话语场之中。
其次,人与异类之间虐恋 ① 的生发成为新世纪聊斋电影改编的另一个重要热点。循依着聊斋小说人鬼(妖)殊途、好事多磨的逻辑生发路径,新世纪的改编电影更愿意铺叙书生、捉妖师等现实世界的人们与来自异界的鬼狐妖仙之间缠绵悱恻的虐恋故事。来自传统道德、伦理的观念束缚和男女主人公背后的家庭、师门的集体控制加重了虐心展现的深广度,也成为影片展的新重点,而虐恋亚文化里一方对另一方的身心折磨则滑落到影像世界的边缘。一方面,影片会全方位凸显恋爱主角自身的善良与纯洁,不管是《狐仙》(2011)里的王子服与婴宁,还是《非狐外传》(2013)里的王生和仙儿,甚或还有《人鱼缚》(2020)里的白秋练和柳梦白,《龙无目》(2020)里的海兰珠与陆海笙,《海大鱼》(2020)里的阿狸与海大鱼,《神龟岛》(2021)里的芸芷和王勉,都拥有着青春靓丽的容貌和忠贞不渝的痴情,成为聊斋影像美学修饰展现的亮点;另一方面,男女双方的遇合往往起自于浪漫的开端,在抵达结局的过程中总是充满曲折,来自对方的情感试探或者考验与接踵而至的外界磨难和压力,总让他们一次次困难重重,又常常死里逃生,种种难以预知的外在冲突带来了激烈多变的情感畸变,又引发了幽微细腻的情爱心理矛盾,从而形成了撕心裂肺的虐戀过程。像《妖手摧花》(2020)、《龙无目》(2020)、《海大鱼》(2020)等改编影片还会在异类差异或者巧合误会中展现有情人难成眷属的落寞或者悔恨,通过“此事古难全”的悲剧大结局做足虐恋戏份的后劲和余响。
由于传统文化的漫长惯性,“中国虐恋中的打和骂止于调笑戏谑,若有责打程度也轻” [9]。因此,聊斋小说里的“书生遇艳”叙事常常展现狡黠的异类(狐女、鬼女、花精等)对呆头呆脑却淳朴可爱的书生们的善意戏弄,不受传统道德约束的她们在对书生的近身试探和打情骂俏中逐渐建立了情感的信任,直至心生爱意,这种近乎游戏性的情节书写往往充满了两性相悦的温馨,也成为新世纪聊斋电影取材改编的故事起点。他们起始阶段的小打小闹也为后来共同抵御外力破坏、接受爱恨离别的考验大戏做出了精心的铺垫,此时邂逅而来的小幸福与后来余劫尚存的苦情等待形成了叙事节奏上的波动,所以《画皮》(2008)、《倩女幽魂》(2010)、《狐仙》(2011)、《聊斋媚狐传》(2018)等诸多影片中书生与异类女性间度尽余波情尚在的虐心之恋、猎妖师与猎物间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情劫收官,与前面的情节铺垫之间形成了较为连贯完整的叙事链条,进一步强化了情爱主体痛彻心扉的刺激性体验和花好月圆的美好祈愿。其中需要警惕的是因为虐恋戏份的夸大而出现的巧合环节的刻意营造与坎坷波折的任意设置倾向,这种化“必然律”为偶然性的剧情媚俗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情爱叙事的起承转合,应该予以避免。
最后是由同性恋亚文化所引发的男色呈现也成为新世纪部分聊斋电影情感叙事的一个新症候。其实《聊斋志异》中也存在着对同性之爱的书写篇目,比如《黄九郎》描写了男人迷恋狐男的故事,《念秧》中有旅客为男色所诱惑的情节,《封三娘》记叙了女人与狐女的亲密情感。但蒲松龄对男性与女性内部的同性爱恋持有不同的态度,小说中痴迷于同性之爱的男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落得个精枯体衰、遽然身死的悲剧,“断袖分桃,难免掩鼻之丑” [10]455,他们的做法违反了夫妇之伦、阴阳之理,因此遭到了批判式书写;而女同性恋者则可以借着传统家庭的庇护营建了自己温暖的爱巢,她们之间的隐秘情感仍然需要依附于封建男权社会造就的社会空间,因此危害性较低,而容易被作家宽容对待。
蒲松龄这种基于传统礼法下的性别之爱的情感暗示,特别是对于男风之弊的揭示和批判,在新世纪的聊斋电影改编中重新得到了艺术取舍。一方面,创编者由聊斋小说里的男同书写得出启示,并据此放大演绎成亚文化语境下的“男狐聊斋”系列影片,改变了作家对男风的鞭挞抨击态度,而迎合为小众隐秘世界的男色消费;另一方面,为了避开大众文化的话语禁忌,他们又对男狐们的同性习好做出了淡化处理,不会在西方“酷儿”理论的指引下率意进行类似于“第六代”同性恋电影的快感“犯禁”,而是通过拟古典的影像修辞对之遮遮掩掩,欲说还休,在相对中庸的骑墙式书写里获取性别隐私空间接受的利润最大化效应。在这三部“男狐聊斋”系列影片中,改编自《阿绣》的《男狐聊斋》(2016)在男同书写上最为鲜明。小说里的狐女阿绣被改换为男狐秀郎,时而以帅男秀郎的形象成为刘子固的知己,时而以与民女阿绣一样的外表和刘子固春风一度;《男狐聊斋2兰若寺》(2018)里的男同味道较前者有所弱化,相对于原著小说《聂小倩》而言,已变为狐女的聂小倩增加了一个哥哥倩郎,为使妹妹少受伤害,他经常以妹妹的形象去诱惑男人,却被好色男人欺凌得伤痕累累;《男狐聊斋3》(2022)保存着狐报恩的故事轮廓,依稀带有《小翠》等聊斋小说的影子,但故事内核已经另起炉灶,狐女小翠被改换为青丘少主白辰,王子服被改换为云府里身患怪疾却智力正常的少爷云月。白辰为报云家之恩在姑姑指点之下来到云月身边做了侍卫,两位武功高强的花季美少男最终消除了人与狐之间的重重误解,为战胜妖道、摆脱天劫咒而共同拼争,他们之间惺惺相惜的知己关系被凸显出来,而欲说还休的同志关系则明显被弱化处理。因此,聊斋原著的男风书写不仅成为新世纪影像改编的重要灵感,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满足大众窥视欲望的卖点和噱头。这种情感戏改编往往打着亚文化小众趣味呈现的擦边球,借刷人眼睑的同性话题博取猎奇窥私者的观赏注意力,小心翼翼地游走于大众“犯禁”与“投诚”的灰色地带,匆匆留下了浅尝辄止的娱乐碎片,在充分摆脱传统男权意识形态和封建礼法禁锢的同时,又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消费意识形态的话语牢笼,它的改编潜力和不良倾向都应得到区别对待。
三、闹剧精神蔓延生长
在当前这样一个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浅、轻、低的无深度诉求似乎成了追求娱乐的审美风尚,“如释重负”的喜剧精神自然而然地在艺术传播中迅速播撒开来,催生出一串接一串的五彩缤纷的话语泡沫。来势汹涌的后现代语境所拉动的重感性、轻理性的体验方式也对聊斋电影改编再生产带来了“意味深长”的影响,闹剧精神 ① 的蔓延生长就是这其中一个重要的话语症候。
与聊斋小说起底于传统乡村世界的道德伦理、倾向于在相对封闭的故事空间里隐喻式地展现人与异类之间的隐秘交往不同,当下更多的聊斋电影对准了需要满足审美消费和娱乐刺激的社会受众,在空间呈现上扩充到西部的沙漠异域和东面的神秘海岛,再加上虚拟化的阴森冥界和缥缈空灵的华丽仙苑,种种具象化的场景搭建扩充了聊斋故事的展现视域,应景而生的形象群体穿梭活跃于形态多变的故事空间里,从而演绎出许多异彩纷呈的传奇情节。从《画皮》(2008)开头沙匪大寨的攻坚打斗,到《狐仙》(2011)结尾人狐历劫后的再次相逢,西域黄沙背景下的跨界情缘次第展开;从《海大鱼》(2020)中的水妖作怪和大鱼显灵,到《神龟岛》(2021)里的船中奇遇和岛上迷案,辽阔海域里的奇特故事扣人心弦;从《席方平》(2000)里阴森可怖的冥界地狱,到《妖手摧花》(2020)中如诗如画的三重天外的花仙阁,神秘幻境里的冷暖叙事诡异曲折。除了与跨界恋情相互对应的唯美浪漫的“文戏”之外,二元对立、喧嚣鼓噪的“武戏”也不甘示弱,在新世纪聊斋电影里铺排开来,但由于国家话语对影片制作中恐怖、怪异、暴力表现元素的政策性限制 ② ,喜剧元素特别是偏向闹剧的极端化喜剧元素迎合着语境消费的审美需求,成为与“武戏”并行不悖的重要风格诉求。
新世纪聊斋电影里的许多武打动作戏往往稀释了恐怖、血腥和暴力色彩,在点到为止的阴郁色调降格中增加了导向日常氛围的喜剧性元素。不但一些和尚、道士等带有宗教色彩的人物形象趋于世俗性还原,“贼和尚”“臭道士”的被呼来喝去下坠到日常生活中,进行了身份祛魅,而且貌似强大的邪派形象也不是完全的面目可憎,些许增加的“再人情化”观照也让他们的形象“可爱”了许多,改编者还经常在他们的失败和消失过程中做卡通化处理,从而丰富了影片表现的喜剧性和个体内涵的复杂性。严嘉导演的《神探蒲松龄》(2018)承袭了成龙电影一以贯之的动作喜剧风格,以神探兼捉妖师身份出现的“蒲松龄”(由成龙饰演)带领着一伙随从破案除凶、捉妖拿奸,与聂小倩、宁采臣、燕赤霞等聊斋小说中出现过的人物形象发生互文性关联,在喜剧性十足的火爆打斗中大呼小叫,动感极强,富有滑稽色彩的人物主角不断引发着情节前行的爆发点,穿越了不同的世间场面和天上幻境,带动了整部影片的喜感格调和闹剧风味。其它的一些影片,如《大梦聊斋》(2020)、《聊斋之极道天师》(2020)、《罗刹劫》(2020)、《奇花记》(2021)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靠向世俗的闹剧精神,离奇古怪的形象造型、絮絮叨叨的人物台词、丑态百出的打斗动作、绕来绕去的故事情节都极尽夸张搞笑之能事,已与原著小说“刺贪刺虐”的喜剧讽刺意味相去甚远,更多迎合了去中心化、轻深度化、再猎奇化的时代风尚。
在《倩女失魂之天师捉妖》(2004)、《聊斋变异》(2016)、《伏狐记》(2018)中,由于港味无厘头喜剧色彩的进一步被强化,其影像处理上的去古典化意味也愈加鲜明。快节奏的情节行进方式和喜剧打斗中的不规则构图、不平衡镜头的频繁运用,以及混乱、冗杂、热闹的背景音乐的反复设置,都显示出改编者颠覆古典美学传统、填充当下时代感觉的审美趣味,不像刘镇伟、周星驰他们的《大话西游》(1995)与原著小说《西游记》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喜剧转喻。这些聊斋电影的改编更多脱离了原著小说借鬼神以说教、语言简约而意旨深远的表意策略,在另起故事炉灶中夹带了自己的“私货”,通过为古典卸妆的方式释放和转移了蓄积在大众心底的焦虑意识。“无厘头文化在主人公、叙事、语言上都达到一种出位和狂欢化的效果,从而具有了后现代文体夸张、反讽、戏仿、碎片化等特征” [11],诸多聊斋影片中的无厘头症候明显具有了跨语境、跨文化移植的话语痕迹,神、鬼、仙、妖多方互动的假面狂欢挣脱了传统美学的语境羁绊,以神性祛魅的现实隐喻方式直达自由个体寻求快感释放的审美娱乐满足。从古典式的话语意蕴到后现代的修辞处理,新世纪聊斋电影在改编步伐上做出了巨大的跨越,这其中的文化对接、话语转换和审美新变都似乎显得顺理成章,合乎“必然”,但由此带来的聊斋文化的散逸是触目惊心的,应该对之加以必要的艺术反省。
这些影片里的闹剧形态与类似于“正月十五闹元宵”里的那种传统节庆的“热闹”还不尽相同。聊斋小说里的喜感之“闹”更多对应着“正月十五闹元宵”里那种类似于传统节庆的“热闹”,书生个体(如《小谢》中的陶望三、《鲁公女》中的张于旦、《青凤》中的耿去病)不惧邪恶权贵、狐妖异类的狷狂表现与元宵节里夜景观赏者的游走徜徉一样,背后都拖曳着长长的古典文化暗影,他们往往很难摆脱传统等级制度的内在制约,无法达到西方狂欢节里的癫狂状态和自由境界,反而得到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自我安慰与自我蒙骗,清初天下方定建立起来的教化秩序仍然从深层上制约着蒲松龄和他的小说创作;而聊斋改编电影里诸多形象之间叽叽歪歪的夸张搞笑蕴含了神圣脱冕后的民间诙谐,《神探蒲松龄》(2018)里被誉为神探的“蒲松龄”看似成为官方主流文化的延伸力量,但实际上他和潘长江饰演的县令都显得滑稽可笑,围绕在他身旁的身份庞杂的探案队伍同样充满了民间自由世界的蓬勃元气,稽查活动中可以上下颠倒、尊卑移位的团队成员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西方狂欢节节庆仪式泛乌托邦化的外在律令。这种聊斋改编影片自觉建构的“热闹”带给人们的“无疑是一种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的怪诞感、滑稽感、喜剧感” [12],是等级关系暂时遁形、自由平等获得“归位”的高光时刻,更多契合了当下大众传媒和网络文化传播的碎片化、快捷性、虚拟式症候。
相对于香港电影先在性的无厘头呈现方式,它们所展现的具有相似性的艺术处理方式在原创性上是应该被质疑的,“后知后觉”式的借鉴模仿和中小成本的资金注入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些充满闹剧精神的聊斋电影成为艺术精品的可能性。如果说院线电影《神探蒲松龄》(2018)在艺术上还做得差强人意的话,那么《倩女失魂之天师捉妖》(2004)、《聊斋变异》(2016)、《伏狐记》(2018)、《大梦聊斋》(2020)等网络电影的制作则显得较为粗糙简单,其中材料拷贝、艺术粘贴的手法几乎都可以有迹可循,加冕与脱冕的狂欢节仪式仍然在竞相表演,但巴赫金式的自我的确证变为了后现代式的自我的消解,这种后置的时代狂欢“遗留下来的是文化平面上的意义的消费和支离破碎的话语游戏” [13],所蕴含的闹剧精神不但与聊斋小说的喜剧内涵相去甚远,而且容易滑向能指单薄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改编者所依托的聊斋文化在这里更多是一种名号或者噱头,真正的精神真髓已被釜底抽薪,留下来的只有一张张面目模糊却动感十足、轻盈无比的“画皮”,看似魅性招摇,却早已失“魂”落“魄”,沦落为大众文化生产流水线上的次品货和边角料,这种改编所带来的教训也是十分沉重的。
聊斋电影的改编需要艺术上的借鉴和创新,應该在更为广阔开放的文化视野中选取、借鉴和扬弃各种外来元素,但这种立足于传统经典基础上影像改编还应该坚持文化传承上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不能置聊斋小说所依托的时代语境和文化传统于不顾,过分密集地移植域外的审美元素和话语风格,忽略语境使用之间的文化差异,否则就容易使得聊斋电影的改编显得不及物。种种看似时髦的后现代式的无厘头元素在新世纪聊斋电影里的广泛植入,大面积指向了浅表性文化消费的闹剧精神,虽然加快了拟古的影像叙事与现实观照密切接轨的改编步伐,但容易偏离原著小说的审美意蕴,阻碍了聊斋小说影像改编的“在地”生成与“及物性”传播。其实,偏向癫狂呈现的闹剧元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元素所勾连的无厘头文化与聊斋元典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内在关联,却常常被改编者“镶嵌”在聊斋影片中,因此需要对这种热闹的“镶嵌”叙事加以审美考辨。改编者仍然需要在拟古典化的跨界故事与面向当下的现实观照之间做出平衡,过分脱离原著和忠实拘泥于原著都是不可取的,在影像叙事中变聊斋小说中的“文戏”为打鬼捉妖的热闹“武戏”,对于大众接受而言未尝不是一个化“旧”为“新”的改编策略,但无厘头闹剧式的化“简”为“繁”已与聊斋文化相去甚远,它的外来移借已使改编重心向“后”倾斜,弱化甚至忽视了文化传统的前设影响,是背向聊斋元典进行的“聊斋”叙事改编,因此应该引发改编学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反省。
综上所述,受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影响,新世纪聊斋电影出现了对虐恋亚文化、同性恋亚文化、无厘头亚文化、“二次元”文化、御宅文化、萌文化等多种外来文化元素的借用与整合,以及宗教元素的泛滥和传统内涵的弱化等现象,这些改编脉象的产生往往与大众文化消费的多元语境密切相关。网络文化的兴盛和新媒体技术的更新为聊斋电影改编提供了多种机遇,同时也孕育着重重的危机,如果改编者在泥沙俱下的改编市场中做到了激浊扬清、取长补短,那么对于传统优秀文化的复兴将会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不但如此,聊斋小说的电影改编也事关中国的文化自信问题。王朱杰认为文化自信既是一种“敞开”面向的自信,也是一种“在地性”的自信 [14]。因此,小到具体个人,大到民族国家,都需要以包容性的视野去直面日新月异的时代语境,不能故步自封、盲目自大,也不应该脱离自身所依托的文化传统,不回避自己的生长链条,在内外兼修中做大做强,从而立身于多元共存的当代世界。改编者在聊斋元典基础上所进行的艺术创新,对于扩充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播影响力功不可没,对于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意义深远,对于加强大国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输出同样值得重视。所以,立足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思考基点,勘探改编过程中出现的艺术盲点,防范因为改编不当可能带来的话语风险,警惕和规范受网络文化和大众消费左右而产生的改编乱象,寻绎聊斋电影承前启后、蓬勃发展的改编新契机,为新时代文艺添砖加瓦,仍然是一个迫切而又必须深入探究的话题。
参考文献:
[1]陈晓明.“后革命”阐释:理论与现实[J].美苑,2005,(5).
[2]吴九成.《聊斋志异》与宗教(三题)[J].蒲松龄研究,2000,(3).
[3]安国梁.论《聊斋志异》的宗教体系[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5).
[4][东晋]干宝.搜神记[M].邹憬,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5][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但明伦评点本)[M].济南:齐鲁书社,1994.
[6]冀运鲁.论《聊斋志异》的因果观念二重性及其对叙事模式的影响[J].齐鲁学刊,2012,(3).
[7]黄洽.《聊斋志异》与宗教文化[M].济南:齐鲁书社,2005.
[8]秦建鸿.文化守恒及其审美:以鬼怪文学现象为例[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11).
[9]王福湘.中国人的虐恋心理和文学中的虐恋描写[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8,(1).
[10][清]蒲松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修订本)[M].任笃行,辑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11]包兆会.无厘头文化中喜剧的笑与中国式后现代[J].文艺争鸣,2006,(2).
[12]修倜.“狂欢化”理论与喜剧意识——巴赫金的启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
[13]贺志刚.对话·狂欢后现代——关于巴赫金的随想[J].艺术广角,1996,(6).
[14]王朱杰.中国文化的两种传统和在地性[J].东方论坛,2018,(1).
Analysis of the Adaptation Pulse and Reasons of the New CenturyLiaozhai Movies
ZHAO Qing-chao XIA Fei-fan
(School of Humanism,Jinggangshan University,Ji'an 343009,China)
Abstract: Driven by popular culture,online context,and new media technology,Liaozhai themed films in the new century have seen a flood of religious element codes,a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emotional scenes,and the growth of farce spirit in adaptation. Producers' borrowing and integration of various foreign cultural elements,such as sadistic subculture,homosexual subculture,Wulitou subculture,“anime” culture,yuzhai culture,and meng culture,have provided multiple opportunities for Liaozhai film adaptation,and also bred numerous crises. Therefore,based on the thinking basi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exploring the artistic blind spots that arise during the adaptation process,preventing the potential discourse risks caused by improper adaptation,and adding bricks and tiles to the prosperit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new era,will be urgent and important.
Key Words: New century;Liaozhai Zhiyi;Movie adaptation;Religion;Fa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