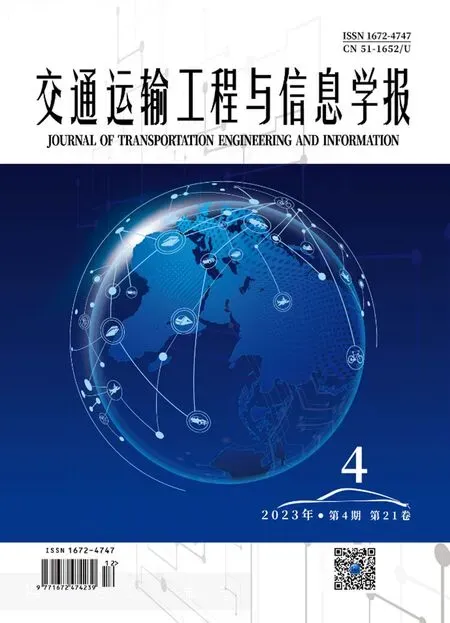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研究综述
葛姝欣,陈国俊,刘好德,周 正,万志伟①
(1.武汉理工大学,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武汉 430063;2.武汉理工大学襄阳示范区,襄阳 441106;3.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通与轨道交通研究中心,北京 100029;4.重庆市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 400020)
0 引言
城市公共汽电车(下文统称“公交”)是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出行的社会公益性事业,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公共交通安全作为城市公交运营的第一要素,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近年来有关城市公交的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尤其是2018 年重庆万州“10.28”城市公交车坠江事故和2020 年贵州安顺“7.7”公交车坠湖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产生了极大社会影响。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大约94%的事故是驾驶员人为因素造成的[1],而心理因素已被证实是危险驾驶行为和交通事故的重要致因[2],因此公交驾驶员不良心理状态会增加交通违法行为和安全事故的风险,需要加以重视。
受职业特征影响,公交驾驶员需要在复杂的道路环境下进行长时间的驾驶任务,精神高度集中,极易产生焦虑、紧张等负面情绪[3]。周虹等[4]使用一般健康问卷(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GHQ-12)进行心理健康调查发现,成都市995 名公交驾驶员中有266 人(26.73%)属于心理障碍的高危人群,显著高于其他职业人群的心理障碍检出率[5]。公交驾驶员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突出,已经呈现出职业特性,必须加以关注。科学的评估工具和方法可以对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进行客观评估与监测,而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则需要依据影响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的各种因素。本文采用文献综述方法,首先分析公交驾驶员的职业心理问题现状,包括职业心理问题类型、危害性和严重情况,然后通过分析影响职业心理问题的因素,并整合现行职业心理问题干预措施,为后续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研究提供参考。为全面了解和掌握公交驾驶员面临的职业心理问题困境,本文选取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万方知识服务平台,以中文关键词公交驾驶员、公交、心理健康、心理、职业心理等为条件进行检索,选取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以英文关键词bus drivers,bus,mental health,psychology,occupational psychological problems 等为条件进行检索,选取article 和review 类型文献。通过剔除无关文献和重复文献,并补充相关法律法规及新闻,最终将85 篇文献纳入综述分析。
1 职业心理问题现状
心理问题又称心理失衡,是指个体在社会适应中产生其能意识到或未意识到的主观困惑状态[6]。本文中研究的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是指由于个人生活或驾驶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现实性因素诱发,以不良情绪或伴随不良行为为具体表现,并呈现出一定职业特性的不良心理状态。为更好地掌握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的研究热点,本文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为来源,采用上文提到的检索方式,利用VOSviewer 构建关键词网络视图。在选择分析方式中,选择Co-occurrence、ALL keywords,设置关键词出现最小频次为2,生成的初始网络视图较为杂乱,进一步对关键词进行处理,删除联系较少或与主题无关的关键词,将含义相同或近似的关键词整合,重复上述步骤,导出网络视图,如图1所示。

图1 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研究文献关键词网络视图Fig.1 Network view of literature keywords in researches on bus drivers’occupational psychological problems
图中节点代表关键词,连线代表关键词共线,颜色代表同属一个聚类。关键词网络视图大致可分为6 个聚类,聚类1 主要为抑郁相关研究,包括抑郁的危害、诱因等,以depression 关键词为主;聚类2主要为心理状态与生理健康之间的研究,包含stress、well-being、symptoms、low-back-pain 等关键词;聚类3 主要为工作满意度有关研究,包含job satisfaction、health 等关键词;聚类4 主要为后果与影响因素研究,包含accidents、driving behavior、personality等关键词;聚类5主要为焦虑相关,包含焦虑的后果、诱因,以anxiety 关键词为主;聚类6主要为疲劳相关,包含疲劳的诱因、后果,包含fatigue、sleep、peformance 等关键词。从心理健康问题角度对上述关键词进行提取,总结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的研究热点问题,包括抑郁、焦虑、职业倦怠和躯体化症状。此外,本文梳理其他关键词后加入了其他职业心理问题包括驾驶愤怒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作为补充。
1.1 抑郁
抑郁是描述情绪低落的一种状态,在精神科特指抑郁发作。抑郁的外在表现包括情绪极度低落、消沉、愉悦感下降或丧失、对工作生活兴趣下降甚至失去兴趣等等。多数抑郁状态属于轻度症状,可自行缓解,少数会转为慢性或重度抑郁,形成抑郁症。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是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思维迟缓、认知功能损害、意志活动减退等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类心境障碍[7]。抑郁状态的公交驾驶员可能会持续性的情绪低落、焦躁,甚至会产生自杀念头。抑郁状态也会对公交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和决策能力产生消极影响,导致驾驶员可能出现疏忽或者错误驾驶行为,增加交通事故风险[8]。若长期处于抑郁状态还会对驾驶员的生理健康造成风险,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抑郁是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抑郁症发病率会使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增加2倍[9-10]。由于抑郁症易隐瞒、危害大,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抑郁症视为世界第四大病患,仅次于冠心病等生理疾病。
公交驾驶员的心理状态呈现出明显的职业群体性抑郁倾向[11],合肥市380 名被调查公交驾驶员中有269 名驾驶员有抑郁倾向,比例超过了70%,成为患病率最高的职业疾病[12];重庆市299 名被调查公交驾驶员中有107 人为抑郁状态,占比35.79%[13];宁波市城区131名公交驾驶员的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 List 90,SCL-90)结果显示其抑郁因子得分(1.65±0.36)高于常模(1.50±0.59),差异显著(p<0.01)[14],唐山市公交驾驶员[15]、长沙市公交驾驶员[16]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对比其他职业人群,公交驾驶员的抑郁症状人数更多,李剑等[17]运用抑郁自评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对浙江省307名公交驾驶员进行调查,抑郁症状阳性驾驶员206 名,占总人数的67.10%,显著高于公务员(41.56%)、高校教师(36.49%)、医生(44.7%)等其他职业人群的抑郁症阳性率。
目前公交驾驶员抑郁的检测手段以量表调查法为主,调查量表包括SCL-90 量表、PHQ-9 量表、CES-D 量表等等,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量表为SCL-90量表。为进一步确认公交驾驶员的抑郁现状,本文采用连续变量Meta 分析的手段进行定量分析。文献筛选条件:①研究对象为公交驾驶员;②研究手段为定量分析,包括样本量Ν、抑郁因子得分均值M和抑郁因子得分标准差SD。考虑到SCL-90 量表使用广泛,本文选择金华等[18]的研究结果作为常模,共选出7 篇文献进行Meta 分析(见表1)。由于研究结论存在异质性,因此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纳入文献采用相同研究量表,不需要考虑变量和单位,因此选用加权均数差WMD模型计算效应量。Meta分析的森林图(见图2)显示公交驾驶员抑郁有关文献的合并效应量为0.24,介于0.2~0.7 之间,说明公交驾驶员抑郁情况差于常模,且差异显著。

表1 公交驾驶员抑郁相关研究文献及常模数据Tab.1 Bus drivers’depression data in related literature and constant norm

图2 公交驾驶员抑郁问题相关文献Meta分析结果Fig.2 Meta-analysis results of literature related to depression among bus drivers
1.2 焦虑
焦虑是人类基本情绪之一,是人面对问题或挑战形成的适应性情绪反映。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产生焦虑情绪是正常现象,大多数情况下可自行缓解,若焦虑情绪无原因的持续或加重则会构成病理性焦虑障碍。焦虑障碍又称焦虑性神经症,是以无事实根据或无明确对象的焦虑情绪为主要特征的疾病。长期处在焦虑状态下可能导致公交驾驶员不明缘由的恐惧和提心吊胆,对现实生活的适应能力严重受损[24]。焦虑状态通过危害公交驾驶员的注意力,增加公交驾驶员的错误或失误型驾驶行为,进而增加事故风险[25]。与抑郁类似,焦虑同样会引起不良生理反应,焦虑引发的情绪反应可能会干扰中枢神经系统对血压调节的控制,是高血压病症很容易被忽略的重要诱因之一[26-27]。
纪春磊等[28]研究发现公交驾驶员的焦虑水平显著高于常模,且没有出现过交通事故的驾驶员在焦虑水平上显著高于出现过交通事故的驾驶员,原因为公交驾驶员为保证公交安全秩序运行,需要在工作中长期维持一定的焦虑水平,但这也导致公交驾驶员较非职业驾驶员更容易将工作中的焦虑情绪带到生活中。若公交驾驶员的焦虑情绪在下班后没有得到缓解,或不断加重,则会增加其患有焦虑症的风险[29]。广东省12 793名公交驾驶员中1 808人存在焦虑症状,占14.3%[30],重庆市299名公交驾驶员中有87人为焦虑状态,占29.10%[13]。宁波市131名公交驾驶员(1.45±0.32)[14]、唐山市100名公交驾驶员(1.48±0.63)[15]、长沙市220 名公交驾驶员(1.46±0.48)[16]在SCL-90量表中焦虑因子的得分均高于常模(1.39±0.43)[18]。其他国家公交驾驶员也存在焦虑问题,208 名伊朗公交驾驶员在接受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pielberger’s State and Trait Anxiety Inventory,STAI)调查后,有127 人(61%)的状态焦虑超过正常人群的最高焦虑水平,183 人(88%)的特质焦虑超过正常人群的最高焦虑水平[31]。
目前公交驾驶员焦虑状况的检测手段同样以量表调查法为主,调查量表包括SCL-90 量表、GAD-7量表、STAI量表等等,我国应用较为广泛的量表为SCL-90 量表和STAI 量表。本文同样采用连续变量Meta 分析的手段进行定量分析,基于前文提出的文献筛选方法共得到8篇文献,并提取样本量Ν、焦虑因子得分均值M和焦虑因子得分标准差SD等参数(见表2)。鉴于SCL-90 量表使用广泛,7 篇与上文研究抑郁的文献相同,因此同样采用金华等[18]的研究结果作为常模;剩余的1 篇使用STAI 量表,以该文章中提到的私家车驾驶员结果为常模。由于研究结论同样存在异质性,因此亦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纳入分析的文献采用不同研究量表,需要考虑变量和单位,因此选用标准化均数差SMD 模型计算效应量。Meta 分析的森林图(见图3)显示公交驾驶员焦虑的合并效应量为0.32,介于0.2~0.7 之间,说明公交驾驶员焦虑情况差于常模,且差异显著。

图3 公交驾驶员焦虑问题相关文献Meta分析结果Fig.3 Meta-analysis results of literature related to anxiety among bus drivers
1.3 躯体化症状
躯体化症状又称躯体症状障碍,最早由Steckel 提出,原指躯体障碍的一种深层神经症,现在泛指将心理问题以躯体反应或躯体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32]。躯体化症状引起的腰痛等身体不适会引起公交驾驶员驾驶行为异常,影响到驾驶安全。Wang等[21]发现躯体化症状使公交驾驶员采取违法驾驶行为的风险增加了11倍。同时由于躯体化症状繁多且常缺乏明确的病理病因,所以确诊这类临床病例较为困难,在公交驾驶员自身缺乏注意的情况下,存在较大隐匿性。
公交驾驶员躯体化症状显著高于一般人群,并表现出一定职业特征。钟媛等[19]使用SCL-90对重庆210名公交驾驶员进行调查后发现,公交驾驶员躯体化症状因子得分(1.71±0.70)高于常模(1.37±0.48),差异显著(p<0.001)。刘堂龙等[14]对宁波市城区131 名公交驾驶员,Wang 等[21]对广西的596 名公交驾驶员采用SCL-90 调查均得到了相似结论。在公交驾驶员躯体化症状中最常见的外在表征是腰痛。Issever 等[31]发现61%(127 名)公交驾驶员患有下腰痛,其中88%的驾驶员对工作不满并认为该症状由工作条件引起。我国公交驾驶员腰痛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彭中全[33]分析了重庆市457名公交驾驶员的健康状况,64%的公交驾驶员患有腰椎疾病。
目前公交驾驶员躯体化症状的检测手段以SCL-90量表为主,参照抑郁问题的文献筛选条件,本文筛选出7 篇文献,并提取样本量Ν、躯体化症状因子得分均值M和躯体化症状因子得分标准差SD等参数(见表3),采用连续变量Meta 分析手段进行定量分析,以金华等[18]的研究结果作为常模。由于研究结论存在异质性,因此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纳入分析的文献采用相同研究量表,不需要考虑变量和单位,因此选用加权均数差WMD模型计算效应量。Meta分析的森林图(见图4)显示公交驾驶员躯体化的合并效应量为0.61,介于0.2~0.7 之间,说明公交驾驶员躯体化症状情况差于常模,且差异显著。

表3 公交驾驶员躯体化症状相关研究文献及常模数据Tab.3 Bus drivers’somatization data in related literature and constant modulus

图4 公交驾驶员躯体化症状相关文献Meta分结果Fig.4 Meta-analysis results of literature related to somatization among bus drivers
1.4 职业倦怠
职业倦怠指个体在工作重压下产生的身心疲劳与耗竭的状态。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临床心理学家Freudenberger[34]提出,用于指代个体对工作极度疲惫的一种心理状态。职业倦怠根据主要表现可分为情绪衰竭、去个性化和成就感缺失三个维度。职业倦怠症患者会逐渐丧失工作热情,否定自己的工作价值,甚至对社会和他人冷漠、麻木[35]。职业倦怠会增加公交驾驶员患有抑郁等其他职业心理问题的风险,谭阳等[36]研究发现职业倦怠对抑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p<0.01)。其次,职业倦怠的外在表现如去个性化会增加驾驶员攻击性驾驶行为(如超车、言语攻击他人等)的概率[37],进而导致公交驾驶员危险驾驶行为增加,影响公交运行安全。职业倦怠影响途径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职业倦怠可直接正向预测不良驾驶行为[38],亦可通过影响驾驶员心理健康间接作用于攻击性驾驶行为[39]。以往职业倦怠的研究对象主要为教师、医护人群等,公交驾驶员的职业倦怠问题也逐渐引起研究重视。
公交驾驶员作为职业驾驶人员需要面对考核压力(如在道路拥挤时需要准点运行)、保持固定驾驶姿势、完成长时间驾驶任务等,很容易产生不满、倦怠情绪,属于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40]。王偲怡等[41]使用职业倦怠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vey,MBI-GS)调查成都市995 名公交驾驶员发现601名(60.4%)驾驶员为轻度职业倦怠,212名(21.3%)驾驶员为重度职业倦怠,仅有182 名(18.3%)驾驶员无职业倦怠问题。马雪铭等[38]使用中国版修订MBI-GS量表调查上海市844名公交驾驶员发现大约1/3 的驾驶员存在职业倦怠,其中23.3%的驾驶员为中度的职业倦怠,6%的驾驶员存在重度及以上的职业倦怠。职业倦怠可分为三个维度,李孜佳等[42]认为职业倦怠程度不能用总分衡量而需要分维度测算,其研究发现太原市100 名公交驾驶员中68 名驾驶员在情感衰竭维度处于高分水平;74 名驾驶员在去个性化维度处于高分水平;66 名驾驶员在成就感缺失处于高分水平。Innstrand等[43]发现,从事公交驾驶的人群在情绪衰竭和去人性化两个维度评分均高于从事其他职业人群,公交驾驶员是职业倦怠感严重和辞职意向最强的职业之一。
目前职业倦怠采用的调查方式以量表调查法为主,其中MBI-GS 量表使用较为广泛。MBI-GS量表存在许多版本,本文采用李超平等[44]编制的中国版MBI-GS 作为常模,参照抑郁问题的文献筛选条件,选取了4 篇文献。由于研究结论存在异质性,因此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纳入文献采用相同研究量表,不需要考虑变量和单位,因此选用加权均数差WMD 模型计算公交驾驶员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的分别合并效应量。Meta分析结果发现公交驾驶员三个维度均与常模无显著差异,原因可能为文献纳入量少,数据代表性不足。
1.5 其他心理问题
除上述职业心理问题外,本文综合文献分析发现在公交驾驶员群体中驾驶愤怒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问题也值得关注。
驾驶愤怒又称路怒,是驾驶员以愤怒心情驾驶汽车的一种心理问题。驾驶愤怒的具体表现为机动车驾驶员在受到外界刺激后产生难以控制的愤怒情绪,伴有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等生理反应,并采取过激或攻击性驾驶行为[45]。公交驾驶员是以驾驶为任务的职业人群,在面对相同的突发道路情况时,公交驾驶员更容易产生愤怒情绪,路怒症的发生率显著高于非职业驾驶员[46],Yan 等[47]研究发现普通机动车驾驶员中有5%到7%患有路怒症,但在职业驾驶员中这一比例超过30%。李瑞瑞等[48]对上海市的844 名公交驾驶员进行驾驶愤怒量表(Driving Anger Scale,DAS)调查发现公交驾驶员驾驶愤怒现象严重,40.2%的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有中度以上的驾驶愤怒情绪。驾驶愤怒的危害不容小觑,雷虎[49]研究发现公交驾驶员中23.4%的驾驶员在愤怒情况下更容易冲动开车,明显高于普通私家车驾驶员(17.5%)和其他三类职业驾驶员(长途客车、出租车、货车)所占比例(14.3%、13.8%、21.2%)。任高晓等[50]对比公交驾驶员事故数据佐证了雷虎的观点。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目前国内关注较少的一类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突发性、威胁性或灾难性创伤等应激事件导致的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的精神心理障碍,主要表现为反复的创伤性体验、警觉性增高、情感麻木和回避行为[51]。公交驾驶员长期在复杂交通条件下驾驶,较其他职业人群更容易在工作中遭受身体或心理创伤,例如遭遇交通事故或者面对有攻击性行为的乘客等,这种创伤会增加公交驾驶员患有应激障碍的可能性[52]。Zhou 等[53]对109 名公交驾驶员进行急性应激调查后发现超过一半的公交驾驶员患有急性应激,其中大多数(84.3%)驾驶员应激障碍的症状持续了一个月以上,更严重的是几乎一半的驾驶员在一年后仍存在中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问题。
2 职业心理问题影响因素分析
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成因复杂,受多种因素制约。本文依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①研究对象为公交驾驶员;②研究内容包括上述职业心理问题及其影响因素;③研究方法为定量分析,文献内研究的影响因素存在p值,共得到符合标准的文献25 篇。25 篇文献共涉及41 种影响因素,其中具有统计意义(p<0.05)的因素28 种。本文将具有统计意义的28 种影响因素归纳为2 种一级因素和7 种二级因素。一级因素分别为个人属性因素和职业特征因素,其中个人属性因素[54]包括3 种二级因素,分别为人口统计学特征因素、人格特质因素和生活习惯因素;职业特征因素中包括4 种二级因素分别为工作压力因素、工作时长因素、工作环境因素和工作待遇因素,如表4 所示。由于文献研究的研究样本、分析方法及结论异质性较大,因此采用定性方式对影响因素进行归纳分析。

表4 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影响因素归纳Tab.4 Influence factors on occupational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bus drivers
2.1 个人属性因素
(1)人口统计学特征
人口统计学因素共计报告90 次,其中报告频次最高的因素为性别因素(17次),其次为年龄因素(15次),学历因素(14次)、生活习惯因素(14次)和家庭状况(12 次)的报告频次也较多。对比统计意义显著的文献量,工龄(60.00%)和驾龄(55.56%)统计意义显著的文献占比最高,其次为学历(42.86%)和年龄(40.00%),性别(35.29%)和家庭状况(25.00%)统计意义显著的文献占比较小。
性别是报告文献量最多的因素,但统计意义显著的文献却占比较小,说明目前针对性别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异质性较强,原因可能是目前公交驾驶员群体性别占比较为悬殊,男性比例明显高于女性,导致纳入研究的女性驾驶员样本较少。男性公交驾驶员比女性公交驾驶员更容易路怒[49],有研究认为这与男女性格差异有关,男性掌控欲更强,遇事更易冲动,而女性则相对更加保守、有耐心[55],但另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男女处理愤怒的方式不同,男性偏向于直接的身体攻击表达,而女性更倾向于语言表达[56]。女性公交驾驶员更容易抑郁,在李剑等[17]的调查结果中,女性公交驾驶员抑郁症状阳性检出率(79.22%)显著高于男性公交驾驶员阳性检出率(63.60%),原因可能为女性的情绪更加细腻内敛,更易受到他人或外在事物的影响[57]。但在职业倦怠方面,性别的影响存在争议,王偲怡等[41]认为男性驾驶员较女性会更易产生职业倦怠,这与TU等[58]的研究结论相反。
公交驾驶员的生理年龄和驾龄越小越容易产生心理波动。青年驾驶员因为驾驶经验不足,在日常执行驾驶任务中会格外谨慎小心,承受的压力较大,因此更容易焦虑[29]。同时青年驾驶员的好胜心也相对较强,容易产生角逐意识,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更容易愤怒。Wickens 等[59]研究显示34 岁以下的青年驾驶员路怒的可能性为51%,超过35~54 岁的中年驾驶员(37%)和55 岁及以上的老年驾驶员(18%)。但在职业倦怠和躯体化症状方面,驾龄在3年以上的公交驾驶员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且驾龄越长职业倦怠[60]和躯体化症状[15]发生频率越高。
公交驾驶员的受教育年限正向影响抑郁、焦虑、躯体化症状等职业心理问题,即学历越高,职业心理问题越突出[61,19]。公交驾驶员的工作较为单调重复,很难满足高学历驾驶员对职业发展的心理预期,因而心理健康水平下降,患有职业心理问题的风险增加。学历对职业倦怠的影响存在较大异质性,李琼等[62]认为公交驾驶员学历越高,其职业倦怠等问题越突出,而张名芳等[63]的数据呈现相反的结论,可能原因为二者使用的调查问卷不同。家庭状况因素的正负向研究结论也不一致,刘志怀等[64]对赣州公交驾驶员调查后发现已婚驾驶员相比于未婚或离异驾驶员在心理健康方面表现更好,这可能因为驾驶员处在未婚或离异的家庭环境下,遇到困扰和难题很难得到理解和合理疏导,长期压抑自己的消极情绪,容易变得冷漠、麻木、失去工作热情;然而,李孜佳等[42]研究结果显示已婚公交驾驶员在职业倦怠中去个性化维度的表现显著差于未婚驾驶员,其解释为已婚公交驾驶员家庭、工作事务繁多,压力大,所以对待工作会更加消极。
(2)人格特质
人格特质是心理学界普遍认同的影响心理问题的因素之一。某些人格特质有助于维持心理健康状态,减少患心理问题的风险,例如张名芳等[63]以人格冷怒对公交驾驶员进行调查发现冷静型驾驶员不易患有职业倦怠;Lin 等[65]研究发现利他人格特质是公交驾驶员路怒的重要预测因素,利他特质倾向强的驾驶员会更关注他人需求,在驾驶中会更加克制愤怒情绪。而某些人格特质会增加患有职业心理问题的概率[66],蒲明慧等[22]研究发现冲动性强的公交驾驶员抑郁、焦虑、躯体化等问题的评分较高,差异显著(p<0.01)。神经质[67]也属于风险较高的人格特质,谭阳等[36]和李梦倩等[20]均发现神经质评分越高的驾驶员其职业心理问题评分越高。
(3)生活习惯
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助于保持心理健康,预防职业心理问题。李剑等[17]研究表明有球类运动的公交驾驶员抑郁症状阳性率是无球类驾驶员的0.23 倍;周虹等[4]也发现每周锻炼1~2 次或≥3 次的公交驾驶员相较于从不或偶尔锻炼的公交驾驶员,其心理状况更加健康。不良生活习惯会逐步恶化公交驾驶员的身心健康,增加患有职业心理问题的风险。酗酒、吸烟等不良生活习惯会增加驾驶员患有高血压等生理疾病的风险,而高血压等生理疾病会使得驾驶员过于关注身体状况,引发焦虑进而影响心理健康和工作状态[68]。睡眠不足会使驾驶员情绪消极,焦虑水平上升,合肥市公交驾驶员中每日睡眠时长小于5 h 的驾驶员较每日睡眠时长5 h 及以上的驾驶员更易出现焦虑情绪,差异显著(p<0.001)[12];广州公交驾驶员中睡眠时间不足5 h的驾驶员中患有中度焦虑者为33.2%,而睡眠时间超过8 小时的驾驶员中患有中度焦虑者仅为9.2%[69]。
2.2 职业特征因素
(1)工作压力
公交驾驶员的驾驶技术难度高,驾驶环境复杂,需要在保证乘客和驾驶安全的情况下准时准点完成驾驶任务,这给驾驶员带来了很大的工作压力。哥伦比亚3 665 名被调查公交驾驶员中大约三分之一的驾驶员承受着高工作压力,且与其心理健康、交通事故表现出一定相关性[70]。Tu等[58]对上海公交驾驶员进行压力、职业倦怠对心理健康影响的调查后发现,公交驾驶员承受的压力越大,他们的职业倦怠程度就越高。心理学上亦证明高工作压力与抑郁、焦虑的患病率有关,工作要求高和工作压力大的男性服用抗抑郁药物的风险较高[71],公交驾驶员的职业特性符合上述风险人群特点。
(2)工作时长
高强度、长时间工作负荷对公交驾驶员的情绪存在显著负面影响[72],工作时长会增加公交驾驶员患有职业心理问题的风险。合肥市公交驾驶员群体中,每日工作时长为8 h 的驾驶员焦虑、抑郁的发生率是每日工作时长为6 h 的驾驶员的4.08倍[12];上海市公交驾驶员群体中,工作时间越长、平均每日驾驶里程越长的驾驶员,职业倦怠程度越高[38]。目前甚至还存在部分公交驾驶员的工作时间从早上4 点至5 点开始进行发车准备到晚上22点左右收车休息[73],期间正常的休息和三餐时间都无法保证,其罹患职业心理问题的风险极高。
(3)工作环境
公交驾驶员的工作环境特殊,经常会受到交通噪声和其他车辆驾驶员不规范驾驶行为的干扰,无法顺利完成工作任务,并且大部分公交驾驶员独立工作,缺少交流,这高度影响公交驾驶员的情绪状态[74]。更加特殊的是,公交驾驶员面对的工作环境除了驾驶环境还有社会环境。公交驾驶员身处服务岗位,在工作中常会受到车上乘客的影响,经常面对乘客的不同要求、投诉甚至是暴力,属于职业倦怠高发人群[75-76]。澳大利亚多数公交驾驶员表示在一年中经历过来自乘客的身体暴力行为、反社会行为等不文明行为[25]。我国针对公交驾驶员的不文明行为也时有发生,Zhang 等[77]对长沙732 名公交驾驶员进行冲突调查后发现,635 名驾驶员表示在过去一个月内至少与乘客发生过一次冲突,占到了总人数的86.7%。
(4)工作待遇
工作待遇对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健康的保持起重要作用,对于收入较低的公交驾驶员来说,他们可能面临着生活压力大、家庭负担重的问题,这些因素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导致焦虑[69]、抑郁[36]等不良情绪,加重职业倦怠问题[62]。公交驾驶员的工作时间长、任务繁重,当付出感大于获得感时,严重影响公交驾驶员的职业心理健康。在李剑等[17]的调查结果中,192 名(62.40%)公交驾驶员在工作中感觉不平衡,感觉不平衡的驾驶员抑郁症状的阳性率是平衡者的5.978倍。
本文系统总结了12类因素对公交驾驶员不同职业心理问题的影响程度,并以“++”、“+”分别对应下面两种情况:对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影响非常显著(p<0.01)、对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影响显著(0.01≤p<0.05)。若关于某一因素的结论为影响非常显著的文献数等于结论为显著的文献数则综合结果认为显著,其他情况则以数量多的文献结论为准。以抑郁情况为例(见表5),1 篇文献认为工作环境影响非常显著(++),另1篇认为影响显著(+),那么工作环境综合影响为显著(+);2 篇文献认为家庭情况影响非常显著(++),1篇文献认为影响显著(+),那么家庭状况综合影响为非常显著(++)。按照以上规则对研究上述6 种职业心理问题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整理,结果见表6。

表5 公交驾驶员抑郁问题影响因素汇总Tab.5 Summary of influence factors on depression of bus drivers

表6 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影响因素汇总Tab.6 Summary of influence factors on occupational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bus drivers
本文发现在个人属性因素中,年龄对躯体化症状影响非常显著;学历对抑郁、焦虑和职业倦怠影响非常显著;家庭状况对抑郁、焦虑和躯体化症状影响非常显著;生活习惯对抑郁和职业倦怠影响非常显著;人格特质对以上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影响均非常显著。在职业特征因素中,工作压力对抑郁、焦虑影响非常显著;工作时长对驾驶愤怒影响非常显著;工作环境对躯体化症状和PTSD 影响非常显著;工作待遇对抑郁和职业倦怠影响非常显著。
2.3 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分析
目前探索职业心理问题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应用较多的方法为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等等,其中回归分析应用最为广泛。例如姜志文等[12]使用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多种高危因素对职业心理问题的影响,发现工作时长、休息时间等因素显著影响公交驾驶员的焦虑、抑郁情绪。利用该种分析方法,可在众多纳入模型的因素中获得对某一职业心理问题影响最显著的因素,并确定正负向路径。但职业心理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机制复杂,常存在多种因素在复杂的心理过程中共同作用的情况。而简单的回归分析模型仅能获得一个或多个独立影响因素对单一心理问题的影响路径,无法解释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和交互作用,这与现实情况相差较大。为解决这一问题,有研究人员在影响因素机制分析中采用了结构方程模型,得到职业心理问题致因的同时探索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例如Wang等[21]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公交驾驶员人口统计学特征、人格特质和职业心理问题之间的关系,发现除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人格特质直接影响职业心理健康外,人口统计学特征对人格特质存在影响路径。Shin 等[78]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驾驶员工作环境、工作-家庭冲突和抑郁之间的关系,发现除二者均会直接加剧抑郁症状外,不良工作环境和工作家庭冲突之间存在相互影响机制,即不良工作环境会加剧驾驶员的工作-家庭冲突,而驾驶员工作-家庭的不和谐又导致工作环境更差。
3 职业心理问题干预措施
3.1 开展心理检测和评估
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健康测评是目前应用最多的干预手段。多个国家,例如日本和波兰等,均高度重视公交驾驶员心理测评,并已建立相对健全的测评体系[79]。我国在法律层面,《劳动法》中提出用人单位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在行业层面,多个公交企业针对驾驶员不同岗位阶段的职业心理健康建立了检测环节。在招聘公交驾驶员环节,青岛公交集团对应聘驾驶员的人格、心理成熟度、深度知觉等多方面指标进行检测,考察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反应能力等[80];佛山市佛广集团要求驾驶入职前进行第三方心理健康测评,测评结果为高风险的驾驶员不予录用[81]。在周期性测评方面,江宁公交集团制定了《江宁公交集团公交驾驶员心理健康监测管理制度》,确保心理健康管理工作得以常态化、规范化推进;此外,还制定了《职工体检管理规定》,实行了驾驶员年度体检机制,定期对心理健康等指标进行检查[3]。佛广集团每年对全体驾驶员进行的心理健康测评,并对筛查出存有心理问题的人员重点跟踪监控,有效掌握驾驶员心理状态[81]。
3.2 开展心理培训
开展心理健康相关培训也是目前较多的一类针对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的干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定期开展心理知识讲座、团体解压心理治疗等。孙翠柏等[82]对南充公交驾驶员进行了为期3 个月的心理讲座和咨询,发现其SCL-90 筛选阳性率明显下降,公交驾驶员心理健康状态改善明显,与之前差异显著(p<0.05)。Feng等[83]将认知干预和宽恕干预应用于公交驾驶员的驾驶愤怒干预,发现这两种手段均能有效减少驾驶员的愤怒情绪,且认知干预效果更好。
3.3 提高福利待遇
绍兴公交集团通过建立家访制度,了解驾驶员需求,并为驾驶员协调廉租房名额、优化工作时间等,提高了驾驶员的职业归属感[84]。佛广集团通过改善工作环境、建立奖励机制、帮扶困难员工等多种手段解决公交驾驶员的后顾之忧[81]。其他的一些小型或相对简单的福利待遇提升方法也能取得一定的效果,例如上海市公交企业在驾驶员午餐基础上额外多增加一份水果,即可提高公交驾驶员的积极性和幸福感,降低抑郁水平[85]。
现行的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干预机制可总结为企业首先通过入职测试,在招聘阶段筛除不适宜入职的驾驶员;然后对符合入职条件的驾驶员进行出岗检测和周期评估,筛选出存在职业心理问题或倾向的驾驶员,暂缓或取消其驾驶任务,通过开展心理培训等手段对问题驾驶员进行心理疏导,使其重新满足上岗要求(见图5)。此外,在驾驶员任职周期中,企业常通过提高福利待遇等手段降低职业特征因素对驾驶员心理的消极影响,整体改善公交驾驶员的心理状态。

图5 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现行干预措施流程图Fig.5 Current interventions for occupational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bus drivers
综合全文分析,本文对公交驾驶员的职业心理问题现状、危害、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梳理,如图6所示。其中↑代表正向相关,↓代表负向相关,以生活习惯类因素为例,公交驾驶员熬夜与职业心理问题的风险正向相关(↑),即熬夜越多其患有职业心理问题的风险越高;公交驾驶员锻炼频率与职业心理问题的风险负向相关(↓),即锻炼频率越高,患有职业心理问题的风险越低(↓);没有箭头的因素代表目前研究结论虽证实其对职业心理问题存在影响,但是正负向存在争议或同种因素对不同职业心理问题的正负向存在差异。个人属性因素和职业特征因素均为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致因。严重的职业心理问题会对公交驾驶员的身心健康造成威胁,并增加不良驾驶行为和事故发生率,同时,公交驾驶员的身心健康恶化也会导致事故率升高。因此,为了减少职业心理问题的发生率,企业需要通过对公交驾驶员进行心理健康评估,监控其风险因素。此外,还可以通过开展心理培训和提高福利待遇来降低职业特征因素对公交驾驶员的影响。

图6 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要素交互作用机制Fig.6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elements of occupational bus drivers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对公交驾驶员的职业心理问题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干预措施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分析,研究结论、不足之处与未来展望总结如下:
(1)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严重,危害较大,亟须重点关注
公交驾驶员的整体心理健康较差。对比Meta分析合并效应量,公交驾驶员群体中检出率最高的职业心理问题为躯体化症状(0.61)、焦虑(0.32)、抑郁(0.24),均显著差于常模。心理健康问题在公交驾驶员群体中分布更广,对公交驾驶员的影响程度更深,逐渐成为公交驾驶员的新型“职业病”。职业心理问题影响公交驾驶员的身心健康,干扰驾驶行为,危害公交运营安全。抑郁和焦虑容易导致情绪低落、自我伤害和自杀倾向,同时还增加了患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躯体化症状会增加公交驾驶员患腰椎疼痛等生理疾病的风险;职业倦怠会降低公交驾驶员的工作热情,并增加他们离职的意愿。
当前研究的不足在于:①相比于其他职业群体而言,对公交驾驶员职业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关注度较低;②目前研究多集中在单一职业心理问题,对职业心理问题可能存在共病或相互影响的情况关注较少;③现阶段的主要研究手段为量表调查法,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局限。针对上述不足,希望未来研究:①重视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增加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的定量研究;②关注公交驾驶职业心理问题的共病情况及其相互影响造成的危害;③引入生理测量法,采集公交驾驶员真实的、瞬时的生理信号,与量表调查自陈的、长期的调查结果互为补充,完整地还原公交驾驶员真实的心理状态。
(2)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成因复杂,涉及个人属性因素和职业特征因素
公交驾驶员的个人属性因素和职业特征因素均会影响职业心理问题。从个人属性角度总结,学历较高、年龄大或驾龄长、偏向风险人格特质或有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等的公交驾驶员患有职业心理问题的风险更高;从职业特征角度总结,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或工作待遇差的公交驾驶员患有职业心理问题的风险更高。
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①影响因素的正负向、影响程度在不同研究中的结果存在异质性,例如性别、家庭状况等;②部分研究已关注到影响因素存在交互作用关系,但探究的样本量不够大、影响因素不够全面,交互作用机制的研究结论没得到充分证实;③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传统机理分析方法在影响因素繁杂且变量增加的情况下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针对以上不足,希望未来研究:①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数量,减少地域特征、组群效应带来的影响;②结合实际,对不同研究结果进行整合分析,系统性探究不同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机理,进一步细化职业心理问题致因研究;③加深机理分析模型的细化,基于数据驱动去辨识影响因素之间的复杂、动态交互作用关系。
(3)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干预以开展心理检测和评估为主
目前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的干预措施应用最多的为开展公交驾驶员心理筛查、监测和评估,包含入职测评、周期性测评、执行营运任务前测评三个阶段;其次为开展心理讲座,提高福利待遇。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存在不足之处:①企业对驾驶员各个阶段的测评内容及评定标准、评定周期多为自行设定,业内目前并没有一套得到公认的公交驾驶员心理健康评价体系、标准或方法;②企业在对公交驾驶员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干预时,培训方案的制定缺乏可参考的科学依据支撑;③暂缓驾驶员的驾驶任务或调离驾驶岗位属于企业内部规定,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支持,容易引发劳务纠纷。针对以上不足,希望未来研究:①开发符合我国公交驾驶员实际情况及其职业特征的心理健康评价工具,并不断实证完善,使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的干预事出有因、查有实据;②总结已达到共识的职业心理问题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并对不同地域、年龄、性别的驾驶员进行差异化研究,基于研究结论指导公交企业科学化制定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干预措施;③出台涉及公交驾驶员职业心理问题的有关法律法规,指导企业实施规范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