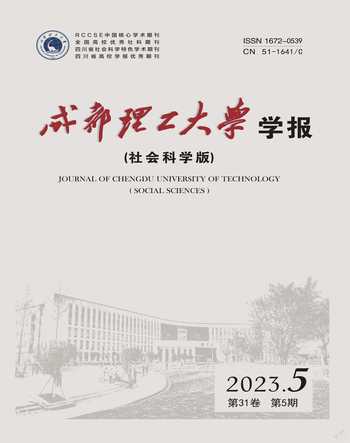紧急救治权的适用困境与纾解进路研究
李荣 李佳瑞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0条首次明确了紧急救治权的触发条件,为司法审查患者知情同意权保护条件下医方救治侵权责任提供了制度支撑,但仍存在紧急救治权的主体存有争议、紧急情况界定模糊、不能取得患者或者近亲属意见界定不明、紧急救治权的责任规则未明确等适用困境,导致紧急救治权的立法目的难以实现。比例原则的引入可以为紧急救治权的适用开辟一条新的路径,将“三阶说”作为审查工具,按照“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的顺序对医方紧急救治行为进行审查,以此判定医方救治行为是否具备正当性、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关键词:紧急救治权;知情同意;比例原则;民事责任
中图分类号: D922.16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3)05-0077-12
一、问题的引出
2017年,在陕西榆林市第一医院妇产科,孕妇马某某因无法忍受分娩前的痛苦,在向院方和家人要求实施剖宫产手术不得成功后,选择了跳楼以终结自己的生命(1)。2007年,四十一周岁的孕妇李丽云在朝阳医院京西分院就医,经检查发现孕妇及其体内胎儿的情况危急,面临严重生命危险,医生建议实施剖宫产手术,但其丈夫肖志军坚持顺产,拒绝手术,最终导致一尸两命的悲惨结局,这亦是引发各界广泛关注的肖志军案(2)。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2008年,产妇周某某在医院生产后大出血致昏迷,医生立即建议切除子宫以保性命,因无法取得周某某的知情同意,医生询问其丈夫胡某意见,但胡某始终拒绝手术,紧急情况下,经两名主治医生联合签名,对孕妇周某某实施了切宫手术才得以挽回其性命(3)。
前述案例中,患者没有自主选择手术方式的情况下,因医方的处置不同带来不同后果:榆林马某某跳楼、李丽云及其胎儿双双殒命的悲剧结果,周某某却因医方实施紧急救治权从而生命及健康权益得以保障。随着此类案例的讨论推进,“紧急救治权”的引入与规则供给显得尤为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220条第一款顺应这一要求,对紧急救治权的行使条件做了具体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这一规定为患者知情同意权开辟了例外空间,为出现前述类似情形时医方不经同意权人同意而采取紧急救治行为提供了免责的法律依据。然而在实务中,医方援引这款规定主张免除自身责任或者法官判断医方的救治行为是否属于紧急救治权范畴仍会遇到诸多问题,如紧急救治权的主体归属于患者还是医方?若归属于医方,是归属于医院还是医生?除了条文列举的生命垂危外,还有哪些情形属于紧急情况,其判定标准是什么?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中“意见”是积极意见还是消极意见,像上述案例中,丈夫拒绝手术对孕妇不利的意见是否应该包含其中?患者与近亲属的意见发生分歧时,应采纳谁的意见?紧急救治权的性质属于权利还是义务?权利主体不行使或者不当行使紧急救治权应承担何种责任?这些问题尚有待探讨。
二、紧急救治权的适用困境
(一)紧急救治权的主体存有争议
1.患者权利抑或医方权利
学界对紧急救治权的主体存在患者紧急救治权和医方紧急救治权两种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患者紧急救治权是“公民在患病急危时,有受到紧急抢救、治疗的权利”[1-3],该说从患者的角度出发,认为紧急救治权是患者的一项权利。也有学者认为,医方紧急救治权是特殊情况时“赋予医生行使限制患者自主决定权的特殊权利”[4]或者“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未经患方知情同意即可行使医疗救治的权利”[5],“医方……可以依据诊疗规范立即采取医疗措施,而无须再等待患方做出意思表示”[6]。
司法实务中也同样存有这一争点。在何某甲与重庆市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中(4),法院判决认为紧急救治权属于患者一方的权利。何某甲的妻子曹某入院待產时,经产检具备了明显的剖宫产手术指征,但医院无正当理由拖延了四小时,给孕妇及胎儿带来了巨大伤害。法院经审判认为该医院未及时履行紧急救治手术的义务,具有医疗过错的明显性、危害性及其后果的严重性,应对患者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也有裁判认为,紧急救治权是医方的权利。在朱静与赤峰松山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中(5),原告朱静到松山区医院就诊洗胃,由于医护人员操作不当,将原告朱静牙齿撬掉三颗,但最终保护了患者的生命。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赤峰松山医院医务人员对原告实施的紧急救治权是对原告的生命健康权的保障,衡量人的生命健康权与医疗机构的紧急救治行为,即使对原告造成了不良后果,只要被告赤峰松山医院在实施该权利时遵循基本的医疗紧急救治规范,就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医生权利抑或医院权利
即便紧急救治权归属于医方,也存在其归属于医院还是医生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紧急救治权应当归属于医生[7]。这是因为,医生是实施紧急救治行为的主体,特定科室的医生因其具有丰富的经验以及专业知识,对患者的病情最为了解,也是最能提出有效治疗方案的主体。在当下医疗分工日益细化的背景下,医疗机构负责人未必是熟悉该医疗领域的专家,或因其无法到场致判断有失,待其“批准”或“签字”无疑增加延误治疗或者错误判断的风险。
不过,这一观点在现行制度设计中容易受到质疑,紧急救治权也许归属于医院更为恰当。一方面,《民法典》第1220条既然规定紧急情况下,未能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意见的,需要经过医疗机构负责人批准才可以采取救治措施,即有其合理之处。“批准”这一程序要件既是法律增加的紧急救治权行使的内部控制机制,在扩大医方紧急救治权的同时也一定程度限缩救治权,试图在医方救济权、患者知情同意权之间寻求一个新的平衡,还反映出立法将紧急救治权赋予医院的意图,毕竟,经过医院内部批准的紧急救治行为,其自然代表医院的意志,紧急救治权当然归属于医院,法律后果也当然由医院承担。另一方面,医生隶属于医疗机构,根据《民法典》第1218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生基于职务行为应当竭尽全力采取具体的诊疗和紧急救治措施,不遗余力地挽救患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因此,根据权责一致原则,医生紧急救治所致后果应当由其所在的医疗机构承担,医疗机构作为最终的责任方,紧急救治权亦应归属于医疗机构。
(二)紧急情况界定模糊
1.紧急情况的扩张或限缩存有争议
患者病情的严重性和紧急性,决定了医务人员需在较短的时间内对病情做出判断,并及时采取合理的救治措施,若延迟治疗,患者的生命健康将面临巨大的风险或嗣后消除该风险会付出更大的代价[8]。医学发展到今天,医疗手段还不完善,绝大多数医疗行为都带有正负双重作用[9]。紧急情况下患者身体大多处于危险边缘,诊疗行为危险系数较高,对患者身体具有较强的侵袭性,相较于一般诊疗行为,紧急救治下通常会伴随更严重的损害或者后遗症等危害结果发生,因此对患者采取医疗措施的方式应比一般的诊疗行为更加细微谨慎。鉴于此,法律应当对“紧急情况”进行明确规定。目前对于“紧急情况”的界定,《民法典》仅仅列举了“生命垂危”这一情形,并未对紧急情况的内涵进行界定,故对其内涵需要通过解释论的方式予以解决。
从立法界的角度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将“紧急情况”界定为“患者因疾病发作、突然外伤受害及异物侵入体内,身体处于危险状态或非常痛苦的状态”[10]。这一界定中列举了疾病发作、突然外伤受害、异物侵入体内三种情形,但仅仅符合这三种情形尚不足以构成紧急情况,其还有关键的结果判断标准:身体处于危险状态或非常痛苦的状态。换言之,列举的三种情形是原因,核心在于结果这一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患者的生命权、身体健康权才具有受到严重损害的迫切性,才能满足紧急性的内在要求。故沿着这一逻辑,可推导出实务中只要造成了患者“身體处于危险状态或非常痛苦的状态”,无论是列举的三种情形造成的,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都应当符合紧急情况,而非仅仅局限于列举的三种情形。
理论界对“紧急情况”的界定也存在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法律将“紧急情况”限定在“生命垂危”这一前提下,因此应当将生命垂危解释为患者的生命存在丧失风险或身体持续遭受损害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如不及时采取诊疗措施,将无法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对患者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11],这是对生命垂危的扩大解释。也有学者对“生命垂危”做出了限缩解释,认为应当仅限于涉及生命利益这一种情形而不能包括病情恶化情形[12]。前述法工委的观点采用扩大解释,将患者的身体状态纳入了“紧急情况”的判断标准。
司法实务中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持限缩解释观点方认为,判断是否构成紧急情况,应当考虑患者正在发生的病况是否对其生命造成现实的、急迫的威胁,不立即采取紧急救治措施必然导致患者死亡的后果。如在张传花、张传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6),受害人入院时虽然处于昏迷状态,但是体征平稳,由于缺少普通病房,医院建议入住ICU病房,此建议遭到了肇事者的严厉拒绝,且未获得患者家属的同意。随后,肇事者将患者转入大医二院后患者因抢救不及时而身亡。法院经审理认为患者离开大医一院时生命体征稳定,没有生命危险,医方因未获得知情同意没实施紧急救治手术,不承担法律责任。
持扩张解释观点方认为,“紧急情况”应扩大解释至患者存在重大身体健康风险需要紧急救治的情形。在蒋成立诉浙江中控西子科技有限公司一案中(7),出警信息中载明,民警在到达现场后,发现蒋成立摔入三米深的电梯井,但并无生命危险,后“120”到达现场并将其送往医院实施了紧急救治。在此情况下,虽然患者没有生命危险,但因其从高处坠落,也给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既包括外伤,也包括需要经医学检测后才能得知的内患,为了患者身体健康考虑,医方在第一时间实施了紧急救治措施,法院经审理对紧急救治行为持赞成态度,认为因紧急救治所需费用应当由被告承担。很明显,本案法官秉持的是扩张解释观点,认为紧急情况的界定不只限于抢救生命垂危患者的情况,还可以扩张解释为虽然患者生命没有严重危险,但如果不采取紧急救治行为,患者健康利益将严重受损的情况。
2.紧急情况采用主观标准抑或客观标准
在医学实践中,紧急情况纷繁复杂,医务人员的水平各不相同,医院的设备设施差异较大,面对同一案件情形常常会做出不同的判断,此时采用何种标准判断“紧急情况”成为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紧急情况的判断应当采用客观标准,即根据患者的客观、确定、真实的身体状态进行判断。如高空坠落陷入昏迷的工人需马上进行截肢手术,一旦延误治疗就很有可能危及生命,此种情形即应当被认定为具有医疗紧迫性[13]。而如何界定患者的病情是否紧迫很难判断,故实务根据医学研究和临床经验,将其外化为诸多临床症状特征,只有患者具备了临时症状特征,才能判断为患者达到了紧急情况的状态。如2013年11月原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印发的《需要紧急救治的急危重伤病标准及诊疗规范》规定,急诊救治范围主要为濒危和危重病人,包括无呼吸无脉搏病人、急性意识障碍病人或可能严重致残者,在临床上表现为脑挫伤、意识消失、大出血、心绞痛、急性严重中毒、呼吸困难、各种原因所致的休克等。患者一旦发生上述状况,要求院前急救人员必须及时、有效地对符合标准的危急重伤病患者实施急救,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推诿或拖延救治。对于违反规定的医疗机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依法依规追究医疗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14]。
另一种观点认为,紧急情况的判断无法采用客观标准,只能采用主观标准,也就是授权医生在当时的技术水平、设备条件下,基于医学专业知识作出紧急情况的判断即可。目前法律明确列举了生命垂危这一种紧急状态,但生命垂危的外在表现不一而足,而且生命垂危仅仅只是紧急情况的一种情形。患者是否处于紧急状态,对其判断最有发言权的显然是临床一线各科室的医师,因此应该给予医师一定的自由裁量权[7]。目前,很多地区的医院对急诊科室进行了分级,医生根据患者的症状和体征,区分病情的轻重缓急及隶属专科,如此可以更好地应对突发的罕见病症,更有利于保护患者的生命健康权。
(三)不能取得患者或者近亲属意见界定不明
1.“患者或近亲属”顺位不明
紧急救治权的实施前提之一是不能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的意见,紧急救治权是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补充,对抗患者的知情同意权[15]。而患者或近亲属的顺位不明将难以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在医疗实践中,由于行使医疗紧急救治权会使医疗机构承担更大的风险,所以医方对紧急救治权的行使一般持保守态度,医疗机构会尝试各种方法与患者近亲属取得联系并履行说明告知义务,在征得患方意见后再决定后续的治疗方案。
通过北大法宝搜索第一组关键词:“危机情况或者紧急救治”“知情同意”“家属签署”获得了27篇案例,该27篇案例中,医方均表示在紧急情况下,对患者实施紧急措施获得了家属的知情同意。搜索第二组关键词:“危机情况或者紧急救治”“知情同意”“患者签署”获得了7篇案例,该7篇案例中则是患者对医方即将实施的手术方针表示知情同意。梳理34篇案例可以发现,临床实践中,以患者的病情轻重以及是否具备自主决定意识和能力为依据,可以区分出6种不同的告知同意处理情形(见表1),该6种处理情形反映出医方对“患者或近亲属”的顺位问题存在不同理解,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情形1和情形4符合现行制度的立法意蕴,是正确的行为方式。在该两种情形下,患者均具备自主意识和自主能力,医方的告知方式合理保障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其次,情形2和情形5未合理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在患者具备自主决定意识和自主能力的情况下,医方仅告知了其家属,获取了家属的意见,而患者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及处置办法并没有自主决定权。
最后,情形3和情形6中,醫方虽履行了告知患者知情同意的行为义务,但是否合理保障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有待商榷。如“榆林马某某”案符合情形6的模型,在患者具有自主决定意识时,医疗机构除了取得患者本人的意见,还会要求其通知家属,在家属的同意及陪伴下实施诊疗行为。此情形下,医方大多将家属的知情同意权放在了首位,原因是此类诊疗行为风险系数较高,除了患者本人需要承担身体上的不利后果,其近亲属仍然需要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因此,实践中常常出现医方采取紧急救治措施后患者或其家属以不知情为由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的情况。显然医疗机构此种做法将“患者或者近亲属”理解成并列的关系,即“患者和近亲属”,两者缺一不可。很明显,这一理解失之偏颇,否则,在“榆林马某某”案中,医院就不会过分执着于家属的知情同意而拒绝手术,也就不会造成孕妇因难以忍受痛苦跳楼的悲惨结局。同理,在情形3中,医方虽告知了患者和家属,但应该以患者的意见为主才属于正确的做法。
2.“近亲属意见”界定不明
第一,未规定近亲属内部冲突的解决机制。医疗机构在征得患者近亲属知情同意权时可能会面临着不同主体之间复杂的利益冲突和利益选择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决策,应当以谁的利益作为优先考虑是法律亟须解决的问题。我国法律所调整的亲属关系包括三代以内的直系和旁系亲属,当近亲属众多,意见不一时,医方应该采取谁的意见?虽然司法解释规定了当近亲属内部达不成一致意见时可以认定属于不能取得患者近亲属意见的行为,但实践中,医疗机构为了规避己方的责任通常会要求近亲属内部商议,给出一个最终答案,否则将不轻易实施紧急救治措施。假如近亲属无法做出一致决策,是否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的近亲属顺位来决定采取哪一种决策?法律条文的修改总是顺应社会发展的,法律对于近亲属顺位的规定有其合理性,医疗机构要做的就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在近亲属作出的不同决策中进行选择,但遗憾的是当前的紧急救治制度并没有妥善解决此问题。
第二,患者近亲属的意见是积极意见还是消极意见?抑或同时包括?当近亲属做出不利于患者的决定时,医方是否可以拒绝采纳近亲属的意见?如肖志军案中,医院采纳了肖志军对于患者李丽云的不利意见;“榆林马某某”案中,医方采纳了患者家属不利于患者的意见,由此给患者及家属造成了惨重的代价。这些个案体现出来的不仅是医生的医德问题,更是法律规范的伦理问题。此后,随着立法的不断完善,多数观点认为,这种消极的、不利于患者的意见表示并不属于《民法典》第1220条中所述之“意见”。立法之所以赋予近亲属知情同意权,其目的在于更好地维护患者利益,而不是提供近亲属合法伤害患者工具。因此,法律规定取得患者家属的意见应当属于积极意见,而非消极意见。故当近亲属作出的意见严重违背患者最佳利益原则时,医疗机构可以不采纳该意见,以保护患者生命健康权为目的进行紧急救治[16]。
(四)紧急救治权的责任规则未明确
1.紧急救治权的性质不明
医方紧急救治权这一观点虽然较患者紧急救治权更为合理,但是没有指明医方进行紧急救治是权利还是义务的问题。通过梳理关于紧急救治权的法律法规及历史沿革发现(见图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在设立紧急救治权的相关规定时,使用了“应当”一词,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开始,各法律条文对紧急救治权性质的规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涉及紧急救治权使用的词语是“可以”。
“应当”和“可以”的意义在法律规范上区别很大,“应当”是义务性规范,具有命令性与强制性,用在紧急救治制度中,即要求当患者出现紧急情况时,医方必须对其进行紧急救治。根据权利义务的对应性原则,在一定的法律关系中一方的义务即为相对方的权利[17],因此,在执业医师与患者所形成的医事法律关系中,患者享有受到紧急救治的法定权利[3]。此时紧急救治权作为医方的义务,当出现紧急情况时,医务人员没有选择余地,必须履行救治义务,救治行为本身可能不会给医务人员带来较大的负担,但救治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如损害承担、医疗费用承担、医闹等问题将给医务人员带来沉重的压力。义务性规范给医方施加了过重的责任,不利于医患关系的健康发展。如在刘某诉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中(8),医疗机构违背患者意愿实施了医疗手术,虽然该行为挽救了患者的生命,但由于未获得患者的知情同意,患者要求医方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而“可以”是授权性规范,赋予医方具有选择的权利,当患者出现紧急情况时,医方是否立即实施诊疗措施由其自主决定。鉴于权利的可处分性,医务人员有权选择行使或者不行使,从理性人趋利避害的选择来看,医务人员大多不会选择冒险行使此项权利,毕竟该“权利”的行使不能为医方带来利益,甚至可能因为操作不当惹祸上身,徒增紧急救治权正当行使的证明責任。
2.紧急救治权不当行使的责任主体有待厘清
《民法典》第1220条规定,在突发紧急情况下,难以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的意见时,需要经过医疗机构负责人审批同意才能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实践中,医疗机构的负责人大多为医院的法人代表——院长,院长极有可能是单纯的行政管理人员,不具备医学知识,即使具备医学知识,也难以涵盖所有的医学领域,其未必能够对患者的病情及主治医生的诊疗方案进行准确把控。因此,是否需要进行紧急救治,应该由主治医生提出申请及救治意见,院长再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合理判断。如果医生经过审慎判断提出紧急救治的诊疗措施,而医疗机构不予批准,鉴于医生的职务行为,其已尽到合理提示义务,因未实施紧急救治给患者带来的损害自应由医院承担。反之,医生认为不应该实施紧急救治,或者实施紧急救治的风险极大,但医疗机构认为应该实施紧急救治的,医生因实施紧急救治手术给患者带来的直接损害亦应归属于医疗机构,因为医生是在医疗机构的批准或授权下进行的。如果医生对于紧急救治的诊疗判断有误,院长又因缺乏该专业知识进行了批准,由此错上加错的行为给患者带来的损害应该由谁承担呢?《民法典》第1220条并没有规定紧急救治的责任承担问题,只是简要说明了紧急救治权的行使条件,以至于在实践中,医务人员常常陷于救死扶伤与遵守法律规定的旋涡之中,一边抢救患者,一边取得家属的知情同意。因此明确责任承担的范围有利于一线医务人员全力以赴抢救患者,而不会因害怕侵权不敢为,或者被患者及其家属当做“潜在的侵权人”,如此不仅有利于医方作为,更有利于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得到保护。
三、紧急救治权困境的纾解新思路:比例原则的引入比例原则通常应用于行政法领域,也被称为“最小侵害原则”“禁止过度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而进行”[18],其主要作用是对行政权力进行审查和限制。关于比例原则,一个亟待说明的现象是它日益明显的普遍化趋势[19]。按照法学一般理论,法律体系内部有公、私法二元划分,近些年来,伴随公、私法的互动与交融,公法领域的比例原则开始渗入私法领域。德国法学家拉伦茨认为民事裁判的法益衡量“尚须适用比例原则、最轻微侵害手段或尽可能微小限制的原则”[20]。我国学者也提出类似看法,例如,郑晓剑从公民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联系角度详细论证了比例原则在民法上适用的可行性[21];纪海龙认为比例原则是利益衡量的基本方法,是对各种理性的社会行为全面的概括,其适用领域应该包括民法等私法领域[22]。但需注意,比例原则向民法领域渗透虽然没有法理和制度障碍,但也不能盲目地将其适用于民法的全部领域。一言以蔽之,判断比例原则是否可以解决某一民事领域问题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李海平认为比例原则在民法中只能有限适用,而其适用的条件即“私主体之间实力相差悬殊”,体现在一方私主体对其他私主体具有单方的支配力,此种支配力可称作“社会权力”,而根据权力来源的差异,可以将比例原则在民法中的适用分为“法定社会权力情形下的适用”和“事实性社会权力情形下的适用”[23]。那么,在医疗紧急救治权制度中,比例原则是否具有提供规制路径的可能?其适用于民法紧急救治权的正当性以及责任认定是否具有可行性?
(一)法定社会权力情形下的适用可行性
法定社会权力情形下比例原则的民法适用,是指依据法律规定某私主体具有相对于其他私主体的强势地位,从而对比例原则加以适用的情形[23]。一般情况下,民事法律关系中各私主体地位平等,但特殊情况下,法律赋予了部分私主体强势的地位,造成民事主体之间地位失衡,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相邻关系。以正当防卫为例,面对不法侵害,享有正当防卫权的主体可以积极反抗,由此造成的侵害可以不承担责任。正当防卫权具有较强的支配性,很容易出现滥用权利的情况,因此法律还规定所实施的侵害必须是限度内的侵害,超过必要限度仍然要承担民事责任。对侵害限度的要求则体现了比例原则的影子,赋予了弱势一方特殊权利以抗衡强势一方,有利于对强势方权利加以限制,使权利行使保持在必要的限度以内,以免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医方紧急救治权与正当防卫有异曲同工之处,紧急救治权赋予医方在未经过患者或其近亲属的知情同意下对患者进行诊疗救治,无论结果好坏均可免责的权利。但部分医方却借此机会滥用职权,为赚取更多医疗费,对患者使用超出其健康需求的手术方案或治疗方案,或是采用复杂手段解决简易问题,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严重阻碍了紧急救治权设立目的的实现。鉴于此,比例原则在法定社会权力情形下可以适用于医方紧急救治权中。法律为保护患者权益赋予医方紧急救治权,法律授予了医方敢于行权的信心与底气,但也要抑制医方滥用权利的不良行为。通过适当引入比例原则,让医方在行使紧急救治权时需要接受比例原则的检验,确保其没有超过限度和滥用权利,以此保护和平衡医患双方的权益,达到立法目的。
(二)事实性社会权力情形下的适用可行性
事实性社会权力是指私主体凭借相对于其他私主体在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等资源占有上的明显优势,对其他私主体实际具有间接的、隐性的支配力[23]。民法所体现的平等原则是形式平等,而非实质平等。形式平等不管实际境况,把所有人当作无差别个体对待,而实质平等则关注具体情况,对不同个体区别对待。由于每个人的生存环境和人生经历不同,造就人和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性,这些差异使得社会个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资源的分配占有上相差悬殊,这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实质的不平等性,此种不平等本是社会常态,也符合一般的正义原则,是为大众所普遍接受的。但当部分私主体可以凭借个人资源优势支配其他私主体的时候,私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配置就需要受到相应的干预,此时引入比例原则有利于矫正资源配置在私主体中严重失衡的态势。
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受过专业系统的学习,拥有专业的医学知识,而绝大多数病人都不具备专业的医学知识,甚至普通的医学常识都不懂。患者因对疾病的无知、恐惧、忧虑,愿意把生命交给一个“陌生人”来操控,可见其对医生的充分信任和对诊治结果的满怀期待。在医疗过程中,无论是诊断、检查,还是用药、手术,医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虽然病人有知情同意权,但始终是以医生的意见为主导,大部分患者难以对医生的专业性提出质疑,通常对医生的诊疗方案言听计从,故医方事实上处于强势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医生的权利之大,其对患者身体健康具有较强的操控权和支配权,患者难以提出反对意见,医生的意见直接决定了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具有强制性色彩,已无法将其当作是私法现象放任其自行依私法加以规范,因此比例原则对其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四、紧急救治权具体适用之展开:“三阶说”
“三阶说”是比例原则为学界所公认的三个子原则,三个原则之间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为审查对象提供了一套逻辑严密、操作方便的适用规范。将比例原则“三阶说”的分析框架充分运用到医方紧急救治权行使过程中(见图2),以此评判在患者知情同意缺失下紧急救治权作为“手段”是否满足保护患者生命健康权的“目的”,反思制度的取舍,不仅有利于凝练出具体适用的规则,还能对实施紧急救治给患者造成的损害找到归责方,进而令紧急救治权制度有效运作,发挥其制度设立之目的。
(一)适当性:保障患者生命健康权为目的
比例原则的第一个审查步骤是“适当性”,适当性的主要功能是合目的性判断,考察机关、单位和组织所采取的手段是否有助于目的达成,审查者须反复论证“手段”为“目的”之所需,即达到了“适当性”的基准;反之,则违背了比例原则的适当性,将承担法律责任[24]。根据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生命健康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是一切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石。确定“紧急情况”的界限应以维护患者生命健康权为目的,满足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
1.明确救治权的权利主体为医院
紧急救治权作为手段,其目的在于保护患者的生命健康权,但法律将该“手段”的实施前提规定为患者处于紧急情况之下,此背景下将医方作为紧急救治权的主体更有利于保护患者的生命健康权,体现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一旦将紧急救治权的主体界定为患者,突发紧急状况时,患者通常难以自主表达意思,其家属一般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难以对病情做出合理判断,最终使得该权利的存在有名无实,难以发挥紧急救治制度设立之目的。
2.合理确定紧急情况的界定标准
考察现有立法安排,紧急救治权作为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例外予以定位,双方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张力,需要在紧急救治权与患者知情同意权之间进行平衡,无疑“紧急情况”即为有效缓冲。不过,考虑到患者知情同意权保护的是知情权和同意权,紧急救治权保护的是生命权、健康权。根据权利位阶理论,生命权作为第一代基本人权,如果生命权得不到尊重,所有权利就失去意义[25]。因此,当二者发生冲突时,生命健康权应优于知情同意权。故任何威胁患者生命健康的“紧急情况”发生时,医方应当始终以保证患者的生命健康权为原则,积极实施紧急救治措施,对“紧急情况”的界定不必过于严厉,否则不利于患者生命健康权的保护。基于此,可将“紧急情况”扩张性解释界定为:患者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且不容耽搁的威胁,如不及时救治将会导致超过治疗潜在风险的损害后果[26]。
(二)必要性:维护患者最佳利益原则为标准
必要性原则要求手段在合目的的前提下,通过比较不同手段导致损害的大小,挑选出一个造成损害最小的手段[27]。紧急救治权是为了保护患者的生命健康而设定的,因此即使在未取得患者、近亲属知情同意的条件下,医方也可以实施。其中,未取得患者、近亲属的知情同意也包括了患者、近亲属作出的不利于患者的决定。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不具有医学专业知识,且伴随医疗技术的进步与医学人才的培养,对很多疾病都有了新的诊疗方案,但患者、近亲属因医学知识空白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同时患者近亲属可能出于个人利益或者迫害患者的目的,借用该权利损害患者的权益,相比之下,医生与患者之间一般不存在利益牵扯,其会基于职业道德和专业素养作出更利于患者的判断[28]。因此,面对紧急情况时,当存在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前提条件,医方应该告知患者及其家属并征求其意见,对于近亲属所做的医疗决定,医方应该以维护患者最佳利益原则为标准进行必要的判断。即便在不能取得患者、近亲属的知情同意情况下,医方也可以基于维护患者最佳利益原则,自主決定是否实施紧急救治权。
1.确定患者本人意见为第一顺位
法律规定在紧急情况下,需要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的知情同意意见。从一般的社会情理出发,近亲属通常会做出有利于患者的决定,但也存在个别情况下,近亲属和患者的关系并不十分友好与纯粹,近亲属与患者关系的亲疏远近会影响近亲属作出判断。尤其是当有财产利益纠纷时,患者近亲属的考量通常不会从保护患者生命健康权的角度出发。因此,在实践中,对于“患者或者其近亲属”的理解应该进行适当排序,即将患者本人的知情同意意见作为首选,在无法取得患者本人的知情同意意见时,才采纳近亲属的知情同意意见。换言之,当患者本人意识清醒,有自主表达意识和能力时,其作出的知情同意意思表示可以排除患者亲属的知情同意意见。《民法典》第1219条对知情同意权行使顺序的规定是较为合理的且可以类推适用于医方紧急救治权之中。在紧急情况下,患者近亲属行使知情同意权是特殊情形、是例外、是变态,而患者本人行使才是一般情形、是原则、是常态[29],医疗机构应首先征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在患者不具有自主表达意识和能力时,才能轮到征求近亲属的意见,而非混乱地采用患者与近亲属并行或者患者与近亲属二选一的模式,如此才能真正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2.近亲属内部冲突解决机制
第一,当不同的亲属之间的决策产生冲突时,可以患者的近亲属作出决策为主,以患者最佳利益原则为辅。对于近亲属意见的采纳,一般可以先采纳监护人的意见,如果患者已婚,可以考虑患者的配偶和父母的意见。如果患者近亲属人数众多,且共同生活在一起,可以采取多数表决的方式。如果无法做出一致决定,也无法做出多数表决的决定时,由医疗机构根据患者最佳利益原则从近亲属的多种决策中做出选择。这样规制的意义在于既充分尊重了近亲属作为患者最亲密的人代理行使知情同意权,又可以保障患者的权益不受损害。
第二,根据维护患者最佳利益原则,医疗机构可以在代理作出决策的亲属出现以下情况时适当作出干预:一是亲属作出的决策将对患者造成不可预防的重大伤害;二是大多数的理性人认为,亲属作出的决策不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三是亲属对患者的真实意图做出了不合理的推断;四是近亲属的替代判断虽然并非不合理,但很可能对患者造成严重伤害。
(三)均衡性:紧急救治效果利大于弊为考量
均衡性原则指行为人付出的成本与取得的收益间应成比例[30]。简言之,如果行为人所损害的利益小于或者远远小于救助的利益时,行为人不需要承担损害责任。在判断医方行使紧急救治权是否超过合理限度时即可通过紧急救治效果进行考量,如果紧急救治结果较实施紧急救治前给患者带来了积极的作用,则符合均衡性原则。
1.紧急救治权属于医方的义务性权利
在医患关系紧张的今天,医方在行使紧急救治权时难免有所顾虑,这不仅与紧急救治权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而且让医方在本就错综复杂的医患关系中更加寸步难行。根据最高法的相关司法解释(9),满足一定条件下,如无法及时联系近亲属,在经过医疗机构负责人批准后,即便医方实施医疗措施给患者带来了难以避免的损害,也不予赔偿,而怠于采取相应措施给患者带来损害的则应当赔偿。因此,紧急情况下的救治应当兼具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为医方的义务性权利。在保证医务人员能够切实履行治病救人使命的同时,减轻医务人员对实施紧急救治后风险承担的忧虑。对于特定条件的满足,不必拘泥于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此时可以将比例原则的均衡性工具引入,判断医方是否应当实施紧急救治权,只需考量立即实施紧急救治措施是否有利于保护患者的生命健康权益,是否给患者带来了减缓痛苦或者稳定生命体征等良好效果,如果满足这一条件,医方都应当不遗余力地作为。义务性权利警示医方紧急救治权虽为医方的一项权利,但不可随意放弃。此权利具有义务性,医方应当规范、理性且合法地行使该权利,不能为避免责任承担而不作为或乱作为,由此给患者造成难以弥补的身体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
2.紧急救治利大于弊时医院免责
医方实施紧急救治权未尽到合理义务给患者带来损害的应当由医院或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医生实施紧急救治权前提是获得了医院的批准,属于职务行为给患者带来的损害,应当由医院承担责任。但是,如果医生在行使手术时未尽到合理义务或者存在重大过失致使患者身体受到本可避免的损害的,医院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医生进行合理追偿。
值得注意的是,紧急情况下患者的身体状况十分虚弱,且大部分医生会施行侵入性手术给患者的身体完整度等方面带来不可避免的损害,也存在后遗症、并发症等危险的副作用。如果将紧急救治后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都归于医方的诊疗过失之中,以后再面临紧急救治患者时,大部分医生都不会在第一时间实施紧急救治权或者因实施治疗方案过分小心求稳而达不到治疗效果,造成紧急情况下的救治效果远不及一般情况下的救治效果,从而使得医方的紧急救治权形同虚设。故将紧急救治权的性质界定为医方的义务性权利的价值得以彰显,有利于促使医方更加合理规范地行使该权利,更有利于比例原则的均衡性在紧急救治中得以体现。
实践中,对于是否符合“均衡性”只需按照一般社会人的认知标准进行评判,考量患者治疗后相较于治疗前存在的症状是否得到短暂的缓解,患者的身体状况是否好转,是否缓解了诊疗前患者的身体痛苦即可,由此认定医方实施紧急救治权是否尽到合理诊疗义务,进而作出损害责任的承担判断。而对患者后续引发的其他损害,应当由患者及其家属承担风险后果。
五、结论
在医患纠纷愈演愈烈的今天,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患者的权利,减少了医患纠纷的发生,但在实践中,却与医疗机构的救治行为产生冲突。为此,立法者设立了医疗机构紧急救治权,目的是在患者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第一时间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权。然而,由于紧急救治权规定模糊不清,其运行并未达到立法者所预想的效果,这使其在实践中常常被闲置。文章通过引入比例原则为紧急救治权的适用及归责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在比例原则视角下,紧急救治权作为“手段”应当满足保障患者生命健康权的“目的”;在适当性规则下,应当确定医院为紧急救治权的主体,且“紧急情况”的界定不必过于严苛,任何具有紧急性、突发性、痛苦性、威胁性性质的病症都可归结为紧急情况;在必要性规则下,“患者或近亲属”意见效力辨析应当以维护患者最佳利益原则为标准,首先将患者的意见作为第一顺位进行采纳,在多个近亲属内部意见冲突时,医方为维护患者最佳利益可以在必要时进行干预;在均衡性规则下,将紧急救治权作为医方的义务性权利有利于医方合理规范地实施救治,而紧急救治责任承担需根据紧急救治效果的利弊进行考量,只要存在患者在治疗后相较于治疗前身体症状得到短暂的缓解,或具有好转等为一般社会人所认知和接受的诊疗效果,便可认定医方实施紧急救治权已尽到合理诊疗义务,从而免除医方责任。
注释:
(1)详情见央视网2017年11月26日报道“独家采访!‘陕西榆林产妇坠楼事件还原!在场人员一一回应”,http://news.cctv.com/2017/11/25/ARTIMW7mMKVdXabz8JM-0GkIi171125.shtml。
(2)李小娥等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2010)二中民终字05230号。
(3)详情见浙江日报2008年1月28日第10版报道“医生联合签名救了产妇”。
(4)何某甲与重庆市某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上诉案,(2015)渝五中法少民终字第03764号。
(5)朱静与赤峰松山医院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赤峰中心支公司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6)内0404民初4692号。
(6)张传花、张传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2018)辽0203民再14号。
(7)蒋成立诉浙江中控西子科技有限公司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2016)浙0111民初5204号。
(8)刘某诉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84辑(2013.2),(2010)西民初字第1461号。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且不能取得患者意见时,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条规定的不能取得患者近亲属意见:(一)近亲属不明的;(二)不能及时联系到近亲属的;(三)近亲属拒绝发表意见的;(四)近亲属达不成一致意见的;(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前款情形,医务人员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立即实施相应医疗措施,患者因此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不予支持;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怠于实施相应医疗措施造成损害,患者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予支持。
参考文献:
[1]任丽明,刘俊荣.试论患者紧急救治权与知情同意权的冲突与化解[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21(5):58.
[2]肖鹏,任丽明.论患者紧急救治权与知情同意权的冲突及对策——对北京朝阳医院孕妇胎儿双亡事件的法律思考[J].医学与哲学,2008,29(10):35.
[3]戴剑波.公民医疗权若干问题研究[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6):456-466.
[4]郇春松.试论医生的特殊干涉权[J].医学与法学,2015,7(2):26.
[5]姜贤飞,廖志林,朱方,等.医疗机构“紧急救治权”存在的问题及思考[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10,10(6):658.
[6]田侃,虞凯.试论“紧急情况”下医方告知义务的履行与豁免[J].医学与哲学,2018,39(8):8.
[7]谈在祥.论紧急情况下医师知情同意义务之豁免——兼论《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六条之完善[J].中国卫生法制,2016,25(5):20.
[8]崔玉明.紧急情况下医疗行为的正当性研究[J].河北法学,2013,31(3):150.
[9]梅春英,王晓波.患者知情同意权保护中的权利冲突与协调[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7,34(5):364.
[10]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45.
[11]王利明.试论患者知情同意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557.
[12]王竹.解释论视野下的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侵权责任[J].法学,2011,(11):99.
[13]宣思宇,田侃,臧运森,等.论自我决定权与紧急救治权的适用——关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探讨[J].医学与哲学,2019,40(8):74.
[14]国家卫生计生委.不得拒绝需紧急救治但无力缴费的患者[J].中国卫生法制,2014,22(5):35.
[15]张恒福.民事维权法律手册[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98.
[16]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75.
[17][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米健,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6.
[18]黄学贤.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研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1,19(1):76.
[19]陈景辉.比例原则的普遍化与基本权利的性质[J].中国法学,2017,(5):279.
[20][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85.
[21]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J].中国法学,2016,(2):148-151.
[22]纪海龙.比例原则在私法中的普适性及其例证[J].政法论坛,2016,34(3):95.
[23]李海平.比例原则在民法中的适用的条件和路径——以民事审判实践为中心 [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24(5):171-172.
[24]梅扬.比例原则的立法适用与展开[J].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2,(4):11.
[25]许娟.关于生命权位阶的确定性[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5(2):51-52.
[26]陈歆.论医疗特殊干预权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限制——以《侵权责任法》第55、56条的法律适用为视角[C]//最高人民法院.探索社会主义司法规律与完善民商事法律制度研究——全国法院第23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下).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1064.
[27]刘权.行政判决中比例原则的适用[J].中国法学,2019,(3):95.
[28]何鞠师.紧急救治规则研究[J].醫学与哲学,2018,39(8):4.
[29]杨会.知情同意权行使主体的异化及其匡正[J].南京社会科学,2020,(4):88.
[30]姜昕.比例原则释义学结构构建及反思[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8,26(5):47.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Dilemmas and Resolutions
of the Right to Emergency Treatment
LI Ronga,LI Jiaruib
(a. Academy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Area Studies;
b. Law School,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610068,China)
Abstract:Article 1220 of the “Civil Code” for the first time clarifies the triggering conditions for the right to emergency treatment, providing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the judicial review of the patients right to informed consent under the protection conditions of medical treatment liability.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 application dilemmas like disputes over the subject of the right to emergency treatment, vague definitions of emergency situations, unclear definitions when the opinions of patients or close relatives cannot be obtained, and the responsibility rules for the right to emergency treatment are not specified, making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the right to emergency treatmen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can open a new path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ight to emergency treatment. Using the “three-stage theory” as a review tool, and following the order of “appropriateness-necessity-balance” to review the emergency treatment actions of the medical party, it can be determined whether the treatment actions are justified and whether civil liability needs to be assumed.
Key words: Right to Emergency Treatment, Informed Consent,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Civil Liability
編辑:李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