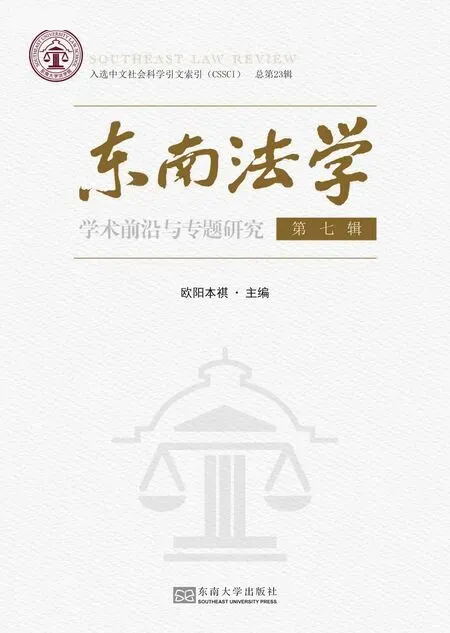论承继的共犯*
——以因果共犯论为视角
[日]松原芳博 王昭武* 译
一、前言
最高裁判所平成二十四年(2012 年)11 月6 日决定①参见最决平成二十四年11月6日刑集第66卷11号,第1281页。,是最高裁判所第一次针对承继的共犯做出的判断。
该案大致案情如下:A 与B 经过共谋,在第一犯罪现场、第二犯罪现场对C、D 实施暴力造成伤害结果。其后,到达第二犯罪现场的被告人X 经过与A 等人的共谋参与进来,用金属梯子、方木材殴打D 的背部、脚部,殴打C 的头部、肩部、背部与脚部,并脚踢D 的头部,实施了强度更大的暴力,相当程度上加重了C 等人已遭受的伤害结果。对此,原判决(二审)②参见高松高判平成二十三年11月15日刑集第66卷11号,第1324页。判定,“就X 而言,其对A、B 的行为以及由此引起的结果存在认识、放任,并且在将这种行为及其结果作为出于制裁目的的暴力这种实现自己的犯罪的手段而积极地利用的意思之下,共谋、参与处于一罪关系的伤害,将上述行为等作为这种制裁的手段实际加以了利用,因此,X 对于包括其参与之前由A 与B 造成的伤害在内的整体,作为承继的共同正犯承担责任”,这就支持了同样旨趣的一审判决③参见松山地判平成二十三年3月24日刑集第66卷11号,第1299页。。对此,被告人一方以让X 就共谋、参与之前的行为承担责任有违责任主义为由,向最高裁判所提出了上告。
最高裁判所虽认为上告旨趣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405 条之上告理由,仍依职权做出了以下判决:“对于共谋、参与之前A 等人已经造成的伤害结果,由于被告人的共谋以及基于该共谋的行为与该伤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此,被告人不承担作为伤害罪之共同正犯的责任,仅仅对由共谋、参与之后足以引起伤害的暴力对C 等人的伤害结果的发生所做出的贡献,承担作为伤害罪之共同正犯的责任,这样理解是相当的。原判决的……认定被理解为,其旨趣在于就被告人而言,利用C 等人因A 等人的暴力行为而受伤、处于难以逃走或者抵抗的状态,进一步实施了暴力。但即便存在这种事实,那也不过是被告人共谋、参与之后进一步实施暴力行为的动机或者契机,不能说,那是得以就共谋参与之前的伤害结果追究刑事责任的理由,是能够左右有关伤害罪之共同正犯成立范围的上述判断的情况。这样的话,就不得不说,包括被告人共谋、参与之前A 等人已经造成的伤害结果在内,认定被告人成立伤害罪之共同正犯的原判决,存在错误解释、适用有关伤害罪之共同正犯的成立范围的《刑法》第60 条、第204 条之法令违反。”不过,最高裁判所认为,原判决的以上法令违反不会对罪数、处断刑造成影响,而且共谋参与之后的X 的暴力行为相当程度上加重了C 等人的伤害结果,本案量刑不能说是不当,因此不能认定属于应适用《刑事诉讼法》第411 条的情况,最终驳回了上告。另外,本决定还附加了千叶胜美裁判官有关共谋参与之后的伤害的认定方法与本决定的射程的补充意见①针对本决定的评析,参见豊田兼彦:《判批》,《法学セミナー》697号(2013年),第133页;早渕宏毅:《判批》,《研修》777号(2013年),第25页以下;丸山嘉代:《判批》,《警察学論集》第66卷2号(2013年),第151页;坂田正史:《判批》,《警察公論》第68卷5号(2013年),第83页以下;前田雅英:《承継的共同正犯》,《警察学論集》第66卷1号(2013年),第139页以下;久冨木大輔:《判批》,《捜査研究》第62卷11号(2013年),第21页以下;松尾誠紀:《判批》,《法学教室》401号(別冊付録《判例セレクト2013》)(2014年),第28页;高橋則夫:《判批》,《刑事法ジャーナル》39号(2014年),第85页以下;森住信夫:《判批》,《専修法学論集》119号(2013年),第89页以下;照沼亮介:《判批》,《平成二十五年度重要判例解説》(2014年),第164页以下;水落伸介:《判批》,《法学新報》第122卷3、4号(2014年),第327页以下;設楽裕文、淵脇千寿保:《判批》,《日本法学》第79卷4号(2014年),第165页以下;今井康介:《判批》,《早稲田法学》第89卷2号(2014年),第101页以下;淵脇千寿保:《判批》,沼野輝彦、設楽裕文编:《現代の判例と刑法理論の展開》,八千代2014年版,第167页以下;小林憲太郎:《判批》,山口厚、佐伯仁志编:《刑法判例百選Ⅱ各論》,有斐閣2014年第7版,第166页以下;十河太朗:《判批》,大谷實编:《判例講義刑法1総論》,悠悠社2014年第2版,第142页以下。以本判决为契机,学者迄今发表了以下论文:松尾誠紀:《事後的な関与と傷害結果の帰責》,《法と政治》第64卷1号(2013年),第1页以下;松宮孝明:《承継的共犯について:最決平成二十四年11月26日刑集66卷11号1282页を素材に》,《立命館法学》325号(2013年),第355页以下;小林憲太郎:《いわゆる承継的共犯をめぐって》,《研修》791号(2014年),第3页以下;阿部力也:《承継的共同正犯:部分的肯定説の再検討》,《川端博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成文堂2014年版,第557页以下;高橋則夫:《“承継的共同正犯”について》,《川端博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成文堂2014年版,第557页以下;橋本正博:《“承継的共同正犯”について》,《川端博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成文堂2014年版,第579页以下;小島秀夫:《いわゆる承継的共犯の規範論的考察》,《大東法学》第24卷1号(2014年),第7页以下。。
针对从近年的下级裁判所的主流观点即限定肯定说(利用说)的角度肯定对共谋、参与之前的伤害的承继的原判决,本决定从因果共犯论的角度否定了对由共谋、参与之前的暴力引起的伤害结果的承继。在这一点上,与有关共犯关系脱离的最高裁判所平成元年(1989年)6 月26 日决定②最决平成元年6月26日刑集第43卷6号,第567页。一并作为因果共犯论对判例的渗透③参见朝山芳史:《実務における共同正犯論の現状》,《刑法雑誌》第53卷2号(2014年),第311页。,受到普遍关注。并且,以往的下级裁判所判例(裁判例)的倾向是,对于在一系列暴力行为的中途参与的后行为人,往往以伤害结果的整体性、不可分性为理由,让其就包括由参与之前的暴力引起的伤害在内的伤害结果整体承担责任。对此,本判决肯定伤害结果的可分性,否定将由参与之前的暴行所引起的结果归责于后行为人。在这一点上,又与针对在游戏厅里用非法手段窃取的弹子与通过合法游戏手段取得的弹子混在一起的案件的最高裁判所平成二十一年(2009 年)6 月29 日决定①最决平成二十一年6月29日刑集第63卷5号,第461页。②该案大致案情为:共犯X通过作弊行为窃取“弹子店”(游戏厅)的弹子,被告人在邻桌以正常方式打游戏,但其目的完全在于扮演从店内的监控器以及店员的监视之下掩护X的作弊行为的“配合作弊者”的角色。在案发当时,在X的台子的(接弹子的)容器内有72枚弹子,放在被告人大腿上的“弹子篮”内有414枚弹子。对于该案,原判决(二审)以被告人打游戏的行为也能被评价为本案犯罪行为的一部分,受害“弹子店”显然不会允许被告人以这种方式获取弹子为理由,认定被告人获取的弹子也属于本案的受害财物,判定就(接弹子的)容器与“弹子篮”内的总计486枚弹子成立盗窃罪。相反,最高裁判所平成二十一年(2009年)6月29日决定则认为,“尽管可以说,X对自己通过作弊行为所取得的弹子成立盗窃罪,被告人也属于X的共同正犯,但对被告人自己取得的弹子而言,由于是通过受害店铺允许的正常的游戏方式所取得的,不能说也应成立盗窃罪。原判决对于被告人通过正常的游戏方法取得的弹子与X通过作弊行为取得的弹子混在一起的上述‘弹子篮’内的所有486枚弹子判定成立盗窃罪,在盗窃罪中有关占有侵害的法令的解释适用上存在错误,并且是事实认定错误,应该说,在本案中,盗窃罪的成立范围是除了上述(接弹子的)容器内的72枚弹子之外,止于上述‘弹子篮’内的414枚弹子。”——译者注,一并作为对不利于被告人的结果一体化持否定态度的判例而广受瞩目③参见松尾誠紀:《事後的な関与と傷害結果の帰責》,《法と政治》第64卷1号(2013年),第1页以下;高橋則夫:《“承継的共同正犯”について》,《川端博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成文堂2014年版,第557页以下。。
所谓因果共犯论,意味着(广义的)共犯也应该对基于自己行为的外界形成(对外界的改变)被追究责任④参见平野龍一:《刑法総論Ⅱ》,有斐閣1975年版,第380页。,这正是行为主义与个人责任原则在共犯中的体现。为此可以说,本决定意味着,最高裁判所承认行为主义与个人责任原则在共同犯罪中也是妥当的。本文想从以个人责任原则为背景的因果共犯论的视角,重新探讨能否成立承继的共犯的问题。
二、问题所在
(一) 一般而言,所谓承继的共犯,是指先行为人部分实施特定犯罪的实行行为之后,在犯罪结束之前,后行为人认识到先行事实,在与先行为人之间的意思联络之下参与了该犯罪的情形,具体包括承继的共同正犯即先行为人与后行为人共同实施此后的犯罪行为的情形、承继的帮助犯即后行为人帮助先行为人完成犯罪的情形。
不过,从肯定过失的共同正犯的判例、通说的立场来看,尽管后行为人对于先行事实没有认识,但如果对先行事实存在认识可能性,也许会出现“过失的承继的共同正犯”的问题,例如,中途参与一系列的过失行为的,问题在于,能否成立包括由参与前的行为引起的(存在可能性的)死伤结果在内的(业务)过失致死伤罪的共同正犯呢?而且,与对先行事实的认识相关联,问题还在于,在行为人参与之前发生了加重结果的案件中,如果立足于肯定结果加重犯的承继的共同正犯的立场,(尽管单独犯中不需要对加重结果存在认识)这里是否需要对加重结果存在认识呢?⑤有判例判定,即便对参与前的暴力所引起的伤害结果不存在认识,仍成立抢劫致伤罪的承继的共犯(参见札幌高判昭和二十八年6月30日高刑集第6卷7号,第859页);但也有判例以对由参与前的暴力引起的伤害结果不存在认识为理由,否定成立强奸致伤罪的承继的共同正犯(参见岡山地津山支判昭和四十五年6月9日判時611号,第103页)。
与意思的联络相关联,立足于肯定片面的帮助犯(从犯)的判例、通说的立场,在缺少与先行为人之间的意思联络的场合,“片面的承继的帮助犯(从犯)”也成为问题,而且,如果采取肯定片面的共同正犯的立场,是否承认“片面的承继的共同正犯”也理应会成为问题。(在一定范围内)肯定承继的共犯的观点将对先行事实的认识、意思的联络包括在承继的共犯的定义之中,其旨趣究竟是否定“过失的承继的共同正犯”与“片面的承继的帮助犯(从犯)”,还是只是将这些排除在当下的研究对象之外,这一点并不明确。
如果在承继的共同正犯的定义中包括“先行为人与后行为人共同实施此后的犯罪行为”,看上去似乎完全如字面那样仅仅是指共同实施实行行为的“协动型”。但只要以肯定共谋共同正犯的立场为前提,在先行为人与后行为人的意思联络之下仅仅由后行为人承担剩余行为的“替换型”自不必说,想必也没有理由将在先行为人与后行为人的意思联络之下仅仅由先行为人承担剩余行为的“承继的共谋共同正犯”①承认“承继的共谋共同正犯”的判例,参见札幌地判昭和五十五年12月24日刑月第12卷12号,第1279页。排除在承继的共同正犯之外。
(二) 承继的共犯成为问题的犯罪类型、案件类型是:①抢劫罪那样的手段—目的型结合犯;②诈骗罪、敲诈勒索罪(恐吓罪)那样的手段—目的型多行为犯②不过,在诈骗罪中,虽然以对方的交付为必要,但正如让对方向银行账户汇款那样,有时候也不需要行为人一方的接受行为,因而将其称为“多行为犯”是存在质疑的余地的。;③抢劫致伤罪那样的结果加重犯;④由一系列的行为引起的伤害罪那样的包括的一罪;⑤监禁罪那样的继续犯③分别针对各种事例对承继的共犯进行分析的学术成果,参见十河太朗:《承継的共犯の一考察》,《同志社法学》第64卷3号(2012年),第345页以下。。学界主要研究的是①、②、③类型,有关④的判例也不少。
(三) 在刑法学界,全面肯定说也曾得到一定的支持。该说主张,既然在对先行事实存在认识、放任的基础上参与进来,包括已经发生的结果在内,应就整个犯罪成立共犯④参见植松正:《再訂刑法概論Ⅰ総論》,勁草書房1974年版,第354页以下;木村亀二:《全訂刑法読本》,法文社1967年版,第270页;西原春夫:《犯罪総論》(下卷·改订准备版),成文堂1993年版,第386页;等等。。近年来,全面肯定说已经销声匿迹,现在主要是限定肯定说——在利用先行为人的行为效果的限度之内承认承继的共犯⑤参见大谷實:《刑法講義総論》,成文堂2012年新版第4版,第418页;大塚仁:《刑法概説——総論》,有斐閣2008年第4版,第294页以下;川端博:《刑法総論講義》,成文堂2013年第3版,第570页;藤木英雄:《刑法講義総論》,弘文堂1975年版,第290页以下;西田典之:《刑法総論》,弘文堂2010年第2版,第366页以下;平野龍一:《刑法総論Ⅱ》,有斐閣1975年版,第282页以下;等等。,与否定承继说——从因果共犯论的角度仅就参与后的事实承认共犯⑥参见野村稔:《判批》,平野龍一、松尾浩也编:《刑法判例百選Ⅰ総論》,有斐閣1984年第2版,第169页;相内信:《“承継的共犯”について》,《金沢法学》第25卷2号(1982年),第42页;町野朔:《惹起説の整備·点検》,《内藤謙先生古稀祝賀·刑事法学の現代的状況》,有斐閣1994年版,第132页以下;金尚均:《承継的共同正犯における因果性》,《立命館法学》310号(2006年),第150页以下;山口厚:《刑法総論》,有斐閣2007年第2版,第350页以下;浅田和茂:《刑法総論》,成文堂2007年补订版,第422页;曽根威彦:《刑法総論》,弘文堂2008年第4版,第258页;林幹人:《刑法総論》,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第2版,第380页以下;等等。,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对立。而且,对共同正犯持否定承继说、对帮助犯(从犯)持限定肯定说的二元说①参见齊藤誠二:《承継的共犯をめぐって》,《筑波法政》8号(1985年),第36页以下;照沼亮介:《体系的共犯論と刑事不法論》,弘文堂2005 年版,第244页以下;高橋則夫:《刑法総論》,成文堂2013年第2版,第447页以下;井田良:《講義刑法学·総論》,有斐閣2008年版,第473页、490页以下;等等。的支持者也在增加。
(四) 也曾有判例②有关判例情况的介绍,参见大越義久:《共犯論再考》,成文堂1989年版,第90页以下;大塚仁等:《大コンメンタール刑法(5)》,三省堂1999年第2版,第224页以下〔村上光鵄〕;高橋直哉:《承継的共犯に関する一考察》,《法学新報》第113卷3、4号(2007年),第120页以下;西田典之、山口厚、佐伯仁志编:《注釈刑法 第1卷——総論》,有斐閣2010年版,第853页以下〔島田聡一郎〕;西田典之:《共犯論の展開》,成文堂2010年版,第216页以下;照沼亮介:《体系的共犯論と刑事不法論》,弘文堂2005 年版,第214页以下;十河太朗:《承継的共犯の一考察》,《同志社法学》第64卷3号(2012年),第355页以下;等等。持肯定说。例如,先行为人杀害被害人之后,后行为人帮忙夺取财物的,大审院昭和十三年(1938 年)11 月18 日判决判定后行为人成立抢劫杀人罪的从犯③参见大判昭和十三年11月18日刑集第17卷,第839页。;又如,看到先行为人用菜刀砍向被害人之后,经过与先行为人之间的意思联络,后行为人又殴打了被害人,被害人最终因后行为人参与之前的行为死亡的,大阪高等裁判所昭和四十五年(1970 年)10 月27 日判决判定后行为人成立杀人罪既遂的共同正犯④参见大阪高判昭和四十五年10月27日刑月第2卷10号,第1025页。。相反,近年的判例则是限定主观说占主流。例如,对于在一系列暴力行为的中途参与进来的后行为人,大阪高等裁判所昭和六十二年(1987 年)7 月10 日判决认为,由于不能认定积极地利用了参与之前的暴力,因此对参与之前的暴力所引起的伤害不承担责任⑤参见大阪高判昭和六十二年7月10日高刑集第40卷3号,第720页。;也有判例以积极地利用了由先行为人的暴力引起的压制反抗状态而参与了夺取财物为由肯定成立抢劫罪的共同正犯,同时又以不能认定积极地利用了先行为人的暴力引起的伤害结果为由判定不对致伤结果承担责任⑥参见東京地判平成七年10月9日判タ922号,第292页。。另外,也可以零星地见到采取否定承继说的判例。例如,先行为人强奸被害人致其受伤之后,后行为人参与进来,奸淫了处于压制反抗状态的被害人,对此,广岛高等裁判所昭和三十四年(1959 年)2 月27 日判决判定成立准强奸罪的共同正犯,而不是成立强奸致伤罪或者强奸罪⑦参见広島高判昭和三十四年2月27日高刑集第12卷1号,第36页。。
下面想对全面肯定说、限定肯定说,以及理论上虽立足于否定说但又支持限定肯定说的结论的观点进行探讨,并从因果共犯论的视角明确是否有承认承继的共犯的余地。
三、肯定承继的各种论据
(一) 一罪的整体不可分性
经常被全面肯定说作为论据的是“一罪的整体不可分性”①参见植松正:《再訂刑法概論Ⅰ総論》,勁草書房1974年版,第345页;札幌高判昭和二十八年6月30日高刑集第6卷7号,第859页;等等。。例如,Y 出于抢劫目的杀害A 之后,被告知情况的X 参与从尸体身上拿走财物的〔案例1〕,由于抢劫杀人罪属于不可分的一罪,因而X 应成立抢劫杀人罪的共犯。
然而,结合犯、多行为犯、包括的一罪等虽然是由数个事实组成,但这些事实本身是可以分割的,这一点已经成为研究是否成立共犯的前提。对于该说所称“整体不可分性”,即便认为不是指事实的属性而是指规范的要求,其根据也不明确,而且也难以认同这种要求可以优越于个人责任原则②即尽管存在违反个人责任原则之嫌,却仍然以这种所谓规范的要求来肯定承继。——译者注。
尽管认为这种“整体不可分性”不是犯罪本身的不可分性,而是作为基于犯罪共同说或者共同意思主体说的共犯成立上的一体性要求,但在共犯的错误、共犯与身份的问题中,现在已经广泛承认,共犯之间罪名是有可能不同的③即已经广泛承认不同构成要件之间的共同犯罪,在同一个共同犯罪中,各个共犯的罪名可以不同。——译者注④有观点以共同意思主体说为前提,出于“共犯成立上的整体性、共犯处罚上的个别性”的要求,主张承认成立抢劫杀人罪的共犯,但在抢劫罪的共犯的限度之内科刑[参见岡野光雄:《承継的共犯》,阿部純二等编:《刑法基本講座》(第4卷),法学書院1992年版,第179页以下]。而且,还有观点虽立足于共同意思主体说,但以针对结合犯中的参与前的事实不能认定共同意思主体的形成为理由,否定成立承继的共犯(不过,承认针对整体的帮助犯)[参见山本雅子:《承継的共同正犯》,《立石二六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成文堂2010年版,第467页以下]。。
另外,“一罪”中包括单纯的一罪、包括的一罪以及科刑上的一罪等各种各样的单位、阶段,也难以从同一个意义上确定整体不可分性的要求所涉及的“一罪”的范围。我们能够想到,该说的论者想必也不会认为,科刑上的一罪也属于整体不可分的行为,甚至连参与“使用伪造的文书罪”的后行为人也要成立伪造文书罪的承继的共犯。但是,只要对整体不可分的规范性根据不予明确,对此就无法显示明确的理由。
(二) 对先行情况的认识、放任
全面肯定说的论者经常强调对先行情况的认识、放任⑤参见西原春夫:《犯罪総論》(下卷·改订准备版),成文堂1993年版,第386页;東京高判昭和三十四年12月2日東高刑時報第10卷12号,第435页;等等。,部分肯定说的论者通常也将这种认识、放任包括在承继的共犯的定义之中。
但是,如果将这种认识、放任作为故意的内容来把握,那是属于认识、放任之对象的先行事实被包含在为后行为人的犯罪奠定基础的事实之中的归结,不可能成为其根据。而且,对过去发生的法益侵害的认识、放任,属于“事后的故意”,由此来为行为人的责任奠定基础无非一种心情刑法①参见平野龍一:《刑法の基礎》,《法学セミナー》143号(1968年),第30页。。
另外,正如在结果加重犯中将针对由参与之前的行为所引起的加重结果的认识、放任作为承继的要件的立场那样,如果将对先行事实的认识、放任作为不同于故意的其他要素来要求,那么,就需要明确其法律性质及其在犯罪论上的定位。
(三) 对先行情况的利用
限定肯定说以利用了先行为人引起的状态或者先行为人行为的效果作为承继的主要根据。那么,在〔案例1〕中,由于X 在拿走财物之际利用了Y 引起的压制反抗状态,势必也应成立抢劫罪的共犯。
但是,从对“效果”或者“状态”的利用,直接推导出针对引起这种“效果”或者“状态”的行为的归责,这是一种“跳跃”②参见山口厚:《刑法総論》,有斐閣2007年第2版,第351页。。准强奸罪(第178 条)处罚的是利用既存的不能抗拒状态实施奸淫,而抢劫罪(第236 条)处罚的是通过暴力、胁迫引起压制反抗状态(中间结果)进而夺取财物(最终结果)。压制反抗状态在准强奸罪中是行为状况,而在抢劫罪中则属于中间结果。这样,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不仅仅是以压制反抗这种状态作为构成要件要素,而是以由暴力、胁迫行为引起的压制反抗状态作为构成要件要素,因此,要将暴力、胁迫结束之后的参与者认定为抢劫罪的共犯,就必须论证,不仅仅是压制反抗这种状态,而是将暴力、胁迫行为以及压制反抗状态的引起归属于后行为人的正当性。单单以对先行情况的利用为根据来肯定承继,这种做法无视准强奸罪这种利用型构成要件与抢劫罪那样的引起型构成要件之间的区别,存在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③参见野村稔:《判批》,平野龍一、松尾浩也编:《刑法判例百選Ⅰ 総論》,有斐閣1984年第2版,第169页;野村稔:《刑法総論》(成文堂1998年补订版),第397页、第398页注(3)。。
原本来说,对效果的“利用”并不能替代“因果性”。这一点通过通说对下面两个案例的态度也能体现。例如,〔案例2〕X 目睹了Y 杀害A 并强取财物的情形,在Y 离开之后,在与Y 之间不存在意思联络的情况下又拿走了A 的财物的;〔案例3〕X 杀害了A 之后才产生取得财物的意思,并且拿走了A 的财物。在这两个案件中,尽管X 也是利用先行行为引起的压制反抗状态夺取了财物,但通说认为X 不成立抢劫罪。
不过,对于〔案例3〕那样暴力、胁迫之后才产生夺取财物的意思的情形④作为有关该问题的先驱性研究成果,参见西原春夫、野村稔:《暴行·脅迫後に財物奪取の意思を生じた場合と強盗罪の成否》,《判例タイムズ》329号(1976年),第22页以下。,作为限定肯定说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的藤木英雄,采取的也是认定X成立抢劫罪的立场⑤现在仍然持这种观点者,参见森永真綱:《強盗罪における反抗抑圧後の領得意思》,《甲南法学》第51卷3号(2011年),第139页以下。。藤木英雄认为:“即便是单独犯的场合,首先,由于是出于暴力的意思对人实施暴力造成对方被压制的状态,因此,乘势另外产生夺取财物的意思,夺取了无抵抗的被害人的持有物的行为,可以将整体综合认定为抢劫。同样的原理也适于承继的共犯中的后行为人的责任。”①藤木英雄:《刑法講義総論》,弘文堂1975年版,第290页以下。另外,引文中“后行为人”在藤木英雄的原文中是“A”。
由此可见,藤木英雄是从有关抢劫罪的单独正犯的解释中推导出承继的共犯的限定肯定说的。因此,最高裁判所平成二十四年(2012 年)11 月6 日决定中所讨论的伤害罪这样的包括的一罪的案件,起始就不在藤木英雄的限定肯定说的射程之内。此后的限定肯定说虽对暴力、胁迫之后产生夺取财物的意思的案件否定成立抢劫罪,但对承继的共犯却采取了限定肯定说,因而,对该说在理论上的一贯性是存在疑问的,同时该说的射程也不明确。
另外,藤木英雄本身的限定肯定说,与包括〔案例3〕在内的暴力、胁迫之后产生夺取意思的情形的解决是共命运的。然而,抢劫罪是由以暴力或者胁迫、强取作为手段、目的而结合起来的犯罪类型,抢劫罪的法定刑已经考虑了出于夺取财物的目的而试图压制反抗这种行为的特别的危险性,将对压制反抗状态的“利用”等视于压制反抗状态的“引起”属于心情刑法的思维,因此,在暴力、胁迫之后才产生夺取财物的意思的情形应成立抢劫罪这种解释不能得到支持②参见松原芳博:《強盗罪·その1》,《法学セミナー》607号(2013年),第110页以下。。
(四) 意思联络
同样是积极地利用先行的他人行为的案件,包括藤木英雄在内的限定肯定说的论者,对〔案例1〕肯定承继却对〔案例2〕否定承继。〔案例1〕与〔案例2〕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先行为人与后行为人之间是否存在意思联络。因此,除了对先行事实的积极利用之外,限定肯定说还将与先行为人之间的意思联络作为承继的根据③藤木英雄指出,在承继的共犯的案件中,“通过对作为一个整体实施此后的行为这种合意,再加上将至此已经实现的事实也用于实施犯罪这种意思,就不单单止于将他人引起的结果用于自己的犯罪行为,而是能够肯定这样的关系:将他人引起的结果,通过与该他人结为一体,就像自己引起的结果一样地利用”。藤木英雄:《新版刑法演習講座》,立花書房1970年版,第408页。。
但是,如果共犯之间的意思联络在给心理的因果性奠定基础这一点上存在刑法上的意义,那么,意思联络之中有关参与之前的事实的意思联络就无法具有刑法上的意义,有关参与后的事实的意思联络只能为有关参与后的事实的刑事责任奠定基础,而不能为有关参与之前的事实的刑事责任奠定基础。“利用”与“意思联络”均不能为对先行事实负责奠定基础,即便将二者并用在一起,也难以将对先行事实的负责予以正当化。
(五) 相互利用、相互补充的关系
大谷实从认为共同正犯之部分行为全部责任以及正犯性的根据在于相互利用、相互补充关系的视角主张,“在将先行为人的行为等作为实施自己犯罪的手段而积极地加以利用的意思之下,后行为人在犯罪中途参与进来,并利用了先行为人的行为的场合,能认定存在相互利用、相互补充的关系”①大谷實:《刑法講義総論》,成文堂2012年新版第4版,第418页。持同样旨趣者参见大塚仁:《共同正犯の本質》,《法学教室》109号(1989年),第31页;川端博:《刑法総論講義》,成文堂2013年第3版,第570页。,“如抢劫罪那样,在作为手段的暴力、胁迫与财物的取得成为一体的犯罪的场合,后行为人利用、补充先行为人的行为这种情况一般是有可能的,因此,对后行为人也应认定成立抢劫罪”②大谷實:《刑法講義総論》,成文堂2012年新版第4版,第420页。。藤木英雄试图通过运用对有关单独犯中的先行行为的利用的理解来为限定肯定说(利用说)奠定基础,而大谷实则是从共同正犯的固有原理中推导出限定承继说(利用说)。
但是,只要是以因果共犯论为前提,所谓共同正犯中的相互利用、相互补充的关系,就属于以各个参与者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性为前提的关系,而不是为了补充(弥补)因果性的不存在。共同正犯中的部分行为全部责任,正是以通过各人的贡献对其他参与者的行为施加影响进而对犯罪事实的实现施加了因果性为根据,而非像同时伤害的特例③日本《刑法》第207条“同时伤害的特例”:二人以上实施暴力伤害他人的,在不能辨别各人暴力所造成的伤害的轻重或者不能辨认何人造成了伤害时,即便不是共同实行者,也依照共犯的规定处断。——译者注(《刑法》第107条)那样,在不存在因果性的地方肯定刑事责任。
另外,大谷实认为,“对于承继的帮助犯(从犯),应该与承继的共同正犯同样处理”④大谷實:《刑法講義総論》,成文堂2012年新版第4版,第445页。,从属于共同正犯之固有原理的相互利用、相互补充的关系中,应该无法推导出承继的帮助犯(从犯)的正当化根据与成立范围。对从相互利用、相互补充的关系中寻求承继的共同正犯的成立根据与标准的立场而言,必须说,承继的帮助犯(从犯)的成立根据与标准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
(六) 对后行行为的评价
西田典之认为,犯罪实行途中参与进来的后行为人虽仅对自己参与之后的情况承担责任,但像〔案例1〕那样的场合,在先行为人看来,夺取财物就是抢劫罪中的强取,参与这种强取行为的后行为人应成立抢劫罪的共犯⑤参见西田典之:《刑法総論》,弘文堂2010年第2版,第366页以下;西田典之:《共犯論の展開》,成文堂2010年版,第223页以下。佐伯仁志也是同样旨趣[参见佐伯仁志:《刑法総論の考え方·楽しみ方》,有斐閣2013年版,第387页]。另外,也有观点作为对后行行为的“评价”,得出了与限定承继说相同的结论[参见高橋直哉:《承継的共犯に関する一考察》,《法学新報》第113卷3、4号(2007年),第152页以下;松宮孝明:《刑法総論講義》,成文堂2009年第4版,第272页以下]。。在西田典之看来,在〔案例1〕中,后行为人参与的是他人的抢劫行为,而在〔案例2〕中,问题在于对被害人被压制反抗之后,后行为人作为单独犯的行为的评价,因此,前者成立抢劫罪,后者成立盗窃罪或者侵占脱离占有物罪,这并不矛盾。
的确,后行行为“在先行为人看来”属于强取行为,但“在后行为人看来”也可谓窃取行为或者侵占脱离占有物的行为①特别是在“替换型”的场合,由于实际上并不存在应该被评价为“强取行为”的先行为人自身的行为,因此,将后行为人的行为评价为“强取行为”的抵触要大于“协动型”。。后行行为在先行为人看来可谓之为强取行为,必须说,这不是所给予的前提而是进行一定评价之后的结论。那么,这种评价是由何种事实来为之奠定基础的呢?西田典之尽管采取的是肯定片面的共同正犯的立场②参见西田典之:《刑法総論》,弘文堂2010年第2版,第355页。,但对于〔案例2〕中的后行为人,则没有将其认定为片面的共同正犯,而是认定为盗窃罪或者侵占脱离占有物罪的单独犯。也就是说,西田典之虽认为通常的共同正犯不以意思联络为必要,但限于承继的共同正犯则以意思联络为必要。这样,就可以说,在〔案例1〕中,西田典之是以先行为人与后行为人之间存在“意思联络”为根据的,即便是在与后行为人之间的关系上,也是将后行行为评价为“强取行为”。但是,如前所述,在因果共犯论中,意思联络的机能在于通过给对方的行为施加心理的因果性,从而贡献于将来的情况形成③正因为如此,西田典之认为,能肯定存在物理的因果性的,这种场合就不要求存在意思联络,并以此为理由,肯定了包括片面的共同正犯在内的片面的共犯的可罚性。,但不包括将下面这一点予以正当化的契机:将包括过去的行为在内的先行为人的行为与后行为人的行为予以一体化,将后行为人的行为评价为“强取行为”。如果可以与因果性毫无关系的、由先行为人与后行为人之间的意思联络本身而为“对先行为人的行为与后行为人的行为进行整体性评价”奠定基础,那么,这种做法就完全属于从赞同他人不法行动的态度、心情中探寻共犯处罚根据的不法共犯论(对他人的不法的连带说④Vgl.,Shumann,Starfrechtliches Handlungsunrecht und das Prinzip der Selbstverantwortung der Anderen,1986,S.49ff.)。也可以说,西田典之的观点是以“共犯的从属性”为根据的,认为对先行为人的评价对后行为人也是妥当的,但从既考虑正犯的不法也考虑共犯固有的不法的混合惹起说来看,则不能承认正犯不法的全面连带性⑤参见山口厚:《問題探求——刑法総論》,有斐閣1998年版,第264页。。只要立足于因果共犯论,“共犯的从属性”原本就是以因果性的存在为前提的,而非补充因果性之缺少的理论⑥参见小林憲太郎:《いわゆる承継的共犯をめぐって》,《研修》791号(2014年),第9页。。
(七) 因果性的缓和
前田雅英认为,“在通过相互协动而扩大正犯范围的共同正犯的场合,只要存在与单独正犯相比更为缓和的因果性即可”,因此,“是有可能在其他共同者引起的压制反抗状态下共同实施抢劫、强奸的”⑦参见前田雅英:《刑法講義総論》,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第5版,第501页。。但是,包括共同正犯在内,共犯所承认的因果性的缓和,通常是指即便没有条件关系,只要存在促进关系即可,而不是指将因果性溯及过去的事实。指向将来的情况形成,这是因果性概念的核心,放弃这一点无疑是对因果性的放弃。而且,如果前田雅英的观点的旨趣是在共同正犯中只要对部分犯罪事实存在因果性即可,那么就存在与下一观点相同的问题。
(八) 因果性对象的限定
十河太朗认为,“在以复数法益作为保护法益的犯罪中,就不能说第二性的(次要的)保护法益是为该罪的不法、责任的程度以及法定刑奠定基础的决定性要素”,因此,“在承继的共犯中,即便后行为人的行为与针对该罪的第二性的(次要的)保护法益的侵害或危险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如果与针对第一性的保护法益的侵害或危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能评价为,后行为人与先行为人一同实现了该构成要件”,在〔案例1〕中,既然X 与属于抢劫罪之第一性的保护法益的占有侵害之间存在因果性,就可以认定为抢劫罪的共犯①参见十河太朗:《承継的共犯の一考察》,《同志社法学》第64卷3号(2012年),第368页。。
但是,既然对第二性的(次要的)保护法益的侵害或者危殆化(危险)也是成立该犯罪的必要条件,那么就属于共同形成该构成要件所预定的不法内容的侵害或者危险,将这种侵害或者危险排除在因果性的对象之外却仍然以该犯罪之刑予以处罚,至少有关对第二性的(次要的)保护法益的侵害或者危险的部分而言,是违反个人责任原则的②山口厚批判限定肯定说不当地缩减了因果关系的对象。参见山口厚:《“共犯の因果性”の一断面》,《神山敏雄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1)》,成文堂2006年版,第354页以下。。
另外,也有观点基于否定承继说倡导,对于所有构成要件该当事实均需要存在因果性③参见山口厚:《刑法総論》,有斐閣2007年第2版,第350页。。但是,诸如妨害灭火罪(《刑法》第114 条)中的“火灾之际”那样的行为状态、受贿罪(《刑法》第97 条)中的“公务员”那样的身份,犯罪构成要件中也包含即便是单独正犯也无须因果性地引起的事实。这些行为状况、身份——除了有关行为人之责任的情况之外,意味着引起法益之侵害或者危险所需要的物的、人的环境,我们能将其称为“不法前提”。相反,实行行为、中间结果以及最终结果的实现,都属于成为法之否定对象的该犯罪的“不法内容”。从主张共犯的处罚根据与正犯一样都在于针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危险的因果共犯论的角度来看,与正犯一样,共犯也不需要针对“不法前提”存在因果性,而是需要针对“不法内容”存在因果性。抢劫罪、敲诈勒索罪(恐吓罪)中的暴力、胁迫,在为针对身体安全、意思活动自由这种第二性的(次要的)保护法益的侵害奠定基础的同时,作为突破取得财物的障碍的行为,而且,尽管对于将“意思决定的自由”视为诈骗罪的第二性的(次要的)法益存在异议,但诈骗罪中的欺诈至少作为解除被害人针对财物的支配、突破取得财物的障碍的行为,均隶属于各罪的不法内容,因此,共犯的因果性也必须及于这些情况。
(九) 被单位化的事实之间的因果性
桥本正博虽坚持“无法肯定蕴含因果溯及之意的‘承继的共同正犯’”,但认为这里的问题在于“作为各个共同正犯之正犯性的贡献的集聚‘由共同正犯所集合性地实施的实行行为’,与由此所实现的构成要件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能够被认定为机能性地支配了(因果性地引起了)应成为构成要件该当评价之‘单位’的事实过程的限度之内,就该‘单位’事实整体成立共同正犯”①参见橋本正博:《“承継的共同正犯”について》,《川端博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成文堂2014年版,第591页。。在桥本正博看来,在由一系列的殴打引起的伤害中,各个殴打行为被淹没在整体的殴打行为之中,整体的殴打行为被一体化,因此,中途参与者就对整体承担责任;在诈骗罪那样的多行为犯中,手段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存在很强的有机关联,由于能认定两者之间的不可分的整体性,因此仅仅参与财物之收受的后行为人也可谓为因果性地引起了诈骗罪之整个构成要件该当事实;但在抢劫罪那样的结合犯中,由于手段行为有可能成为独立的评价对象,因此能否定手段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的整体性,通常是不能认定中途参与者成立抢劫罪之共同正犯的②参见橋本正博:《“承継的共同正犯”について》,《川端博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成文堂2014年版,第594页以下。。
桥本正博的逻辑是,从构成要件评价的视角研究被“单位”化的行为—结果之间的因果性。但是,在单独犯中之所以允许将一系列的行为予以整体化,研究一系列行为的整体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因为那属于贯彻了同一个意思决定的、同一人的行为,当初的意思决定的因果性及于整体;相反,像承继的共犯的情形那样,承认与已经过去的其他人的行为之间的整体性,在允许将不能由自己的行为所左右的事实算入由其负责的对象之内这一点上,违背了个人责任原则,是难以通过构成要件该当“评价”而将其正当化的。
四、是否应肯定承继的共犯
如上所述,全面肯定说、限定肯定说等所依据的各种论据,并不能在因果共犯论的框架之内,将“包括先行事实在内的该犯罪整体的不法内容归责于后行为人”或者“对后行为人的行为与先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同样评价”予以正当化。仅就帮助犯(从犯)而言,上述批判也同样适于“二元说”。并且,因果共犯论是共犯中的行为主义或者个人责任原则的表现形式,只要是有关因果性的必要性这一点,因果共犯论适于包括帮助犯(从犯)在内的整个广义的共犯。仅限于帮助犯(从犯),将因果性贡献的对象限定于针对第一性的保护法益的侵害或危险,在此限度之内是有违个人责任原则的。原本来说,承继的共犯研究的是是否存在因果性这一共通于共同正犯与帮助犯(从犯)的问题,因此,一方面否定承继的共同正犯,另一方面却仅仅肯定承继的帮助犯(从犯),“二元说”的这种逻辑是不能成立的。
这样,只要以因果共犯论为前提,就应该采取否定承继说,〔案例1〕中的后行为人X 应成立侵占脱离占有物罪的共犯。当然,如果承认死者的占有③参见野村稔:《刑法における占有の意義》,阿部純二等编:《刑法基本講座》(第5卷),法学書院1993年版,第80页。,X 就应成立盗窃罪的共犯。但是,所谓占有是针对物的、“人”的支配,并且死者无法成为法益主体,因而难以承认死者的占有。也有观点虽否定死者的占有,但认为在与杀害者(行为人)之间的关系上,在被害人死后也应该持续地保护其生前的占有①参见団藤重光:《刑法綱要総論》,創文社1990年第3版,第572页。。然而,死后保护生前的占有,只能说这种观点本身除了矛盾还是矛盾。而且,即便采取持续保护说,从否定承继的共犯的角度来看,如上所述,将后行为人的行为等视于先行为人的行为这一点也是不能被正当化的,因此就应该视为,在与后行为人的关系上,生前的占有不受保护。
按照否定承继说,对于在敲诈勒索罪(恐吓罪)、诈骗罪中仅仅参与收受财物的后行为人,只要不能认定其参与之后通过态度或者不作为实施了胁迫、欺骗,就与抢劫(抢劫杀人)罪的中途参与者一样,仅成立侵占脱离占有物罪的共犯②参见浅田和茂:《刑法総論》,成文堂2007年补订版,第424页。。也有观点立足于否定承继说主张这种场合的后行为人是不可罚的③参见山口厚:《共犯の処罰根拠》,山口厚编:《クローズアップ刑法総論》,成文堂2003年版,第245页;相内信:《“承継的共犯”について》,《金沢法学》第25卷2号(1982年),第43页。。但是,收受被害人基于由先行为人的欺骗行为所引起的错误而交付的财物,原则上与收受错送的邮件、错找的零钱并无不同,如果后者收受错送的邮件、错找的零钱的行为要成立侵占脱离占有物罪,前者成立该罪就理应不存在障碍。确实,针对被害人基于其意思而交付的客体(财物),通常不存在是否成立侵占脱离占有物罪的问题,那是因为在存在被害人之交付行为的场合,会成立诈骗罪、敲诈勒索罪(恐吓罪)或者侵占委托物罪,在不成立诈骗罪等其他犯罪之时,侵占脱离占有物罪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另外,《刑法》第254 条中“脱离了占有”之物这一表述被理解为为了将成立夺取罪的情形排除在外的“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④松宮孝明:《刑法総論講義》,成文堂2009年第4版,第192页以下。,既然要从该表述中找到积极的含义,在与后行为人之间的关系上,可以通过将接受财物之后的、某种实现所有权能的行为视为侵占脱离占有物罪的实行行为,肯定成立侵占脱离占有物罪。在这种场合,先行为人也应成立侵占脱离占有物罪的共犯,其行为属于敲诈勒索罪(恐吓罪)或者诈骗罪的共罚的事后行为。
就文章开头介绍的最高裁判所平成二十四年(2012 年)11 月6 日决定而言,下面几种观点都是有可能成立的:立足于否定说的理解;在包括的一罪中立足于否定说,而在手段—目的型的结合犯、多行为犯中则立足于限定肯定说的理解;虽立足于限定肯定说,但就伤害罪,认为没有满足该罪之构成要件的理解①千叶胜美裁判官的补充意见指出:“针对在所谓承继的共同正犯中后行为人是否承担共同正犯的责任的问题,在让其承担抢劫、敲诈勒索、诈骗等罪责的场合,通过利用共谋参与之前的先行为人的行为的效果而对犯罪的结果具有因果关系,进而成立犯罪,这种情形是有可能存在的,因此,也是有可能认定成立承继的共同正犯的。但是,至少就伤害罪而言,难以认定存在这种因果关系(正如法庭意见指出的那样,先行者所实施的暴力、伤害,不过是会成为后行者的暴力行为的动机或者契机而已),因而很难想象出能够成立承继的共犯的情形。”②在最高裁判所平成二十四年(2012年)11月6日决定之后的下级裁判所判例中,对于处于包括的一罪的关系的一系列的遗弃尸体与损坏尸体的行为途中参与进来的后行为人,有判例以没有积极地利用先行行为等为理由,否定成立有关先行的遗弃尸体行为的承继的共同正犯,判定仅成立有关参与之后的损坏尸体这一事实的共同正犯。参见東京地立川支判平成二十六年3月20日LLI/DB06930113。。然而,考虑到以下几点,本文认为,采取否定说是最符合本决定之旨趣的,这也是最高裁判所采取的因果共犯论的正确归结:该决定是以“在该场合下,对于共谋、参与之前A 等人已经造成的伤害结果,由于被告人的共谋以及基于该共谋的行为与该伤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为理由;对先行行为的效果的利用无法替代因果性;即便在手段—目的型的结合犯、多行为犯中,后行为人虽然能对最终的结果施加因果性,但无法对为第二性的(次要的)法益的侵害奠定基础的实行行为以及中间结果施加因果性。
五、追论:论事后抢劫罪
针对事后抢劫罪(《刑法》第238 条③日本《刑法》第238条“事后抢劫罪”:盗窃(盗窃犯)窃取财物之后为了防止财物被追回,或者为了逃避逮捕,或者为了隐灭罪迹,而实施暴力或者胁迫的,以抢劫论。——译者注),基于该条的“盗窃(盗窃犯)”这一表述,有力的观点认为,该罪是以盗窃犯为主体的身份犯(身份犯说)。基于这种立场,对于仅参与该罪之暴力、胁迫的后行为人,如果将盗窃犯视为真正身份或者违法身份,就应根据《刑法》第65 条第1 款④日本《刑法》第65条“身份犯的共犯”:(1)加功于因犯罪人的身份才构成的犯罪行为时,即便是没有身份者,也是共犯(第1款);(2)因身份而特别存在刑的轻重时,对没有身份者科以通常之刑(第2款)。——译者注成立事后抢劫罪的共犯⑤参见大阪高判昭和六十二年7月17日判時1253号,第141页;前田雅英:《刑法講義各論》,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第5版,第300页;堀内捷三:《刑法各論》,有斐閣2003年版,第135页;等等。;如果将盗窃犯视为不真正身份或者责任身份,就应根据《刑法》第65 条第2 款成立暴行罪或者胁迫罪的共犯⑥参见大谷實:《刑法講義各論》,成文堂2013年新版第4版,第243页等。另有观点虽将盗窃犯视为不真正身份,根据《刑法》第65条第1款认定成立事后抢劫罪的共犯,但主张再根据第65条第2款在伤害罪的限度之内科刑[参见新潟地判昭和四十二年12月5日下刑集第9卷12号,第1548页;日髙義博:《共犯と身分》,《川端博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上)》,成文堂2014年版,第776页以下]。⑦另外,还有观点认为,在出于阻止财物被追回的目的时属于违法身份,应适用第65条第1款,而出于逃避抓捕与隐匿罪证的目的时则属于责任身份,应适用第65条第2款。参见佐伯仁志:《事後強盗の共犯》,《研修》632号(2001年),第6页以下。。
但是,即便将规定“抢劫”的抢劫伤人罪、抢劫杀人罪(《刑法》第240 条⑧日本《刑法》第240条“抢劫致死伤罪”:抢劫致人负伤的,处无期惩役或者6年以上有期惩役;致人死亡的,处死刑或者无期惩役。——译者注)视为结合犯,第238 条的表述也不会成为将事后抢劫罪理解为身份犯的决定因素。身份,是指“属于有关一定犯罪行为的犯罪人的‘人的关系’的特殊的地位或者状态”①最判昭和二十七年9月19日刑集第6卷8号,第1083页。,是产生法益侵害或者危险(危殆化)的、作为“人的环境”的“不法前提”,或者是为针对行为人的特别的责任非难奠定基础的“责任前提”,而事后抢劫罪中的盗窃,是行为人必须有责地由自己来实现的、属于该罪之“不法内容”的情况,不应将其视为“身份”。尤其是将盗窃犯视为真正的身份或者违法身份,通过适用《刑法》第65 条第1 款,对于仅参与了暴力、胁迫的后行为人追究事后抢劫罪的共犯之责,这无异于将该罪的不法归责于没有实现该罪之不法内容者,与因果共犯论之间不相容②参见林幹人:《刑法総論》,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第2版,第385页;山口厚:《刑法総論》,2007年第2版,第352页以下。。
这样,事后抢劫罪是以窃取行为、暴力或者胁迫行为这两种行为作为实行行为的结合犯(结合犯说)③参见山口厚:《刑法各論》,有斐閣2010年第2版,第232页以下;西田典之:《刑法各論》,弘文堂2012年第6版,第183页以下;等等。。只有立足于这种理解才有可能解释:先行的盗窃罪被事后抢劫罪吸收、事后抢劫罪的既未遂取决于盗窃罪的既未遂④也有观点认为,本罪是结合犯还是身份犯,在理论上都是有可能的,这属于应该从妥当处理共犯问题的视角来决定的问题[島田聡一郎:《事後強盗罪の共犯》,《現代刑事法》44号(2002年),第17页以下]。然而,本罪的定性涉及本罪之不法结构的根基,即盗窃的事实是否包含在应由行为人本人实现的、本罪的“不法内容”之内。。
不过,事后抢劫罪不是抢劫罪那样的手段—目的型的结合犯,而是与抢劫强奸罪一样,属于原因—结果型的结合犯(事后的结合犯)⑤参见松原芳博:《強盗罪·その2》,《法学セミナー》698号(2013年),第112页以下。,因此,在起初的盗窃的时点,不需要存在暴力、胁迫的意思。针对结合犯说,经常看到这样的批判:在着手盗窃的时点存在事后抢劫的(未必的)故意的,(即便事后没有实施暴力、胁迫)也要成立事后抢劫罪的未遂,这种结论是不妥当的。但是,在原因—结果型的结合犯(事后的结合犯)中,只有着手实施第二行为才能认定结合犯整体的未遂,这是原则。而且,即便是抢劫罪那样的手段—目的型的结合犯,仅仅是出于转化抢劫的(未必的)故意着手了盗窃的,仅此还不能成立抢劫罪的未遂,正如这一点所显示的那样,也并非因为着手了第一行为,就总会成立整个结合犯的未遂。
按照这种结合犯说,仅参与事后抢劫罪之暴力、胁迫行为的后行为人的罪责,取决于对承继的共犯采取何种立场,按照本文支持的否定承继说,止于成立暴行罪或者胁迫罪的共犯。相反,按照限定肯定说,仅参与事后抢劫罪之暴力、胁迫行为的后行为人,只要利用了先行为人的窃取财物的效果,就应该成立事后抢劫罪的共犯⑥参见西田典之:《刑法各論》,弘文堂2012年第6版,第183页以下;島田聡一郎:《事後強盗罪の共犯》,《現代刑事法》44号(2002年),第20页。。这里能称为后行为人利用了先行为人的盗窃效果的,想必应该是以盗窃达到既遂为前提的、后行为人出于防止财物被追回的目的参与了暴力、胁迫的情形。的确,在这种场合下,明明是以暴力、胁迫手段阻止财物被追回,后行为人却只成立暴行罪、胁迫罪的共犯,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妥。但是,这种场合下,后行为人能够实现的,不是夺取财物的事实,而是逃避财物之返还请求权的事实,因此,应该认定后行为人成立第2 款抢劫罪①日本《刑法》第236条[抢劫罪]采取暴力或者胁迫手段,强取他人财物的,是抢劫罪,处5年以上有期惩役(第1款)。以前款方法,获取非法的财产性利益,或者使他人获取该利益的,与前款同(第2款)。——译者注。对这种场合的后行为人而言,存在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一直作为事后抢劫罪的问题来处理,认为既然盗窃罪已经达到既遂,即使阻止财物被追回的行为归于失败也要成立事后抢劫罪的既遂;与这种做法相比,第二种处理方式更加符合司法实务的现实,亦即,作为第2 款抢劫罪的问题来对待,根据实际是否逃避了返还财物来决定该罪的既遂或者未遂。另外,在该场合下,出于防止财物被追回的目的与后行为人协作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的先行为人(盗窃犯),成立事后抢劫罪既遂的单独犯与第2 款抢劫罪既遂或者未遂的共同正犯,两罪属于包括的一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