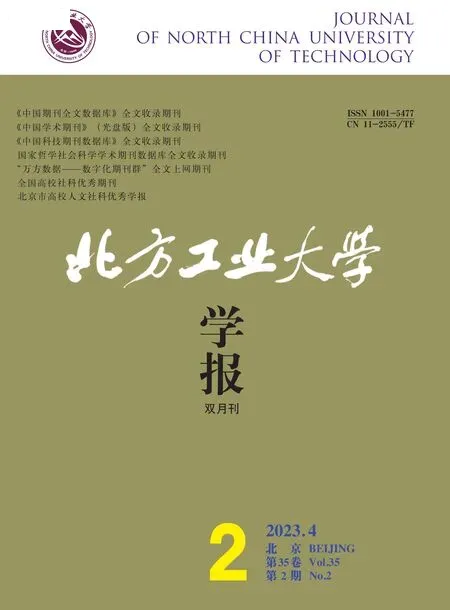殷弘绪与清初景德镇制瓷生态及经验西传*
鲍家树
(1.民革中央团结报社, 100006, 北京; 2.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100048, 北京)
1 殷弘绪其人及相关学术史回顾
殷弘绪(1662—1741),出生于法国利摩日,本名昂特雷克莱(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后取汉名殷弘绪,号继宗,以拉近与中国文化的距离。1682年,殷弘绪在阿维尼翁加入耶稣会,此后在里昂和皮内罗洛的耶稣会学院任教。根据耶稣会罗马档案馆的档案记载,按照当时的惯例,每三年耶稣会会对学院的人员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智力、判断力、审慎度、处事经验和学术潜力等方面,殷弘绪得到的评语基本上都是“好”,未来可以安排治学或布道。[1]通过这些评价,可见殷弘绪在神学造诣、处事能力等方面的素养。康熙二十六年(1687),由白晋(Joachim Bouvet)、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等人组成的法国科学传教团抵达中国,他们或被任命为御前侍讲,或被批准前往各地传教。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命白晋返回欧洲继续招募传教士来华服务,殷弘绪便成为其中一员。康熙三十八年(1699),殷弘绪抵达厦门,后接受传教士利圣学(Jean Charles de Broissia)的托付,赴江西北部传教。康熙四十二年(1703),殷弘绪到达江西,其活动范围主要是九江、南昌、饶州以及景德镇等地。康熙四十六年(1707),殷弘绪被耶稣会任命为中国传教区的新一任会长。康熙五十九年(1720),殷弘绪调任至北京,在“北堂”(今西什库教堂)主持教务,此时正值清廷与教廷关系紧张,禁教令之下,殷弘绪秘密传教,直至乾隆六年(1741)去世,葬于正福寺墓地。殷弘绪在华的40余年,撰写了大量书信寄往法国,书信内容十分广泛,既有科学信息,也有人文信息,从天花接种到养蚕技术,从教育体系到民间文学等,其中有关制瓷的书信尤为著名,被誉为“制造陶瓷之专书”。[2]其内容在此后欧洲汉学家的论述中也得到广泛引用,1735年,法国汉学家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在其主编的《中华帝国及其鞑靼地区地理、历史、编年、政治、自然之描述》(Descriptionge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et,plysiquedeL’EmpiredeLaChineetdelaTartarieChinoise)中收录殷弘绪有关中国瓷器的书信;1856年,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根据《景德镇陶录》翻译出版的《中国瓷器的制作与历史》(Histoireetfabricationdelaporcelainechinoise),以中国陶瓷为书写对象并特别加入欧洲原本对此题材的理解内容,其中就大幅引用殷弘绪介绍景德镇制瓷的书信。
在相关的学术史方面,1970年代,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殷弘绪,但相关研究成果尚未脱离殖民主义的色彩。①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浓厚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述得以扭转,朱培初认为,殷弘绪“在江西景德镇瓷器和世界交流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3]此外,法国学者伊夫斯·德·托玛斯·德·博西耶尔(Yves de Thomaz de Bossièrre)的《殷弘绪和18世纪中国对欧洲的贡献》(FrançoisXavierDentrecolles,YinHong-siuKi-tsong,etl’apportdelaChineàl’EuropeduXVIIIesiècle)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殷弘绪对18世纪欧洲的贡献。总的来看,国内外史学界对殷弘绪的研究专论并不够丰富深入,所见论著较多关注殷弘绪生平及其介绍高岭土等内容,如洪秀明的《中国“高岭”扬名与法国殷弘绪的功勋》、刘芳的《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来华活动述评》、李晨哲的《耶稣会士殷弘绪与18世纪法国的硬瓷生产》等;亦散见于科学技术史、中西关系史等相关论著中,如韩琦的《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刘朝晖的《明清以来景德镇瓷业与社会》、刘芳的《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对中国医学的研究》、罗伯特·芬雷(Robert Finlay)的《青花瓷的故事:中国瓷的时代》(ThePilgrimArt:CulturesofPorcelaininWorldHistory)等。在已有的相关学术成果中,以下专论亦值得关注:牟学苑的《殷弘绪的传教活动与景德镇“窑神”故事的传播》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角度,论述了殷弘绪在景德镇发现的“窑神”故事以及该故事的翻译和传播;孟华的《法国18世纪“景德镇神话”何以形成——一个感觉史意义上的中法文化交流的个案》以殷弘绪的书信在法国广为流传并形成“景德镇神话”这一文化现象入手,以感觉史为视角探讨“景德镇神话”形成的原因;余佩瑾的《殷弘绪书简所见陶瓷样式及相关问题》以陶瓷作品样式为基础,结合与之相关的产造脉络,支撑殷弘绪书简论述的真实性等。就新近研究而言,尤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吴蕙仪博士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深入,例如,《传教士殷弘绪的翻译(1644—1741):地方性与知识流通》(TheTranslationsofFrançois-XavierDentrecolles(1664—1741),MissionaryinChina:LocalityandtheCirculationofKnowledge)、《清初中西科学交流的一个非宫廷视角——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的行迹与学术》等,探究了殷弘绪传教过程中的知识流通及其在宫廷之外的学术研究。
当前,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带动相关领域研究的兴起,中西文化交流史亦复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而对以殷弘绪来华传教和促成制瓷经验向西传播相结合为视角的互动探究则关注较少,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通过爬梳殷弘绪在华期间的书信等史料,探究殷弘绪笔下的景德镇制瓷生态及其传教策略,以及经由殷弘绪而传入欧洲的中国制瓷经验。
2 殷弘绪笔下的景德镇制瓷生态
殷弘绪在书信中详细描述了景德镇的地理环境和城市样貌,景德镇是一座由群山环抱却热闹非凡的城市,“也许正是这种群山环抱的地形适合于瓷器的制作”。[4]景德镇“有一万八千户人家。有些富商巨贾占据着宽敞的宅院,内有大批工人。因此,人们都说全镇有一百多万人口,每天消耗一万多担大米和一千多头猪。景德镇坐落在一条美丽的河边,延伸长度足有一法里……街道如一根根墨线似的笔直延伸,隔一段距离便纵横交错。城中没有空地,房屋显得太挤,街道也太窄;穿行其间犹如置身闹市,四周尽是挑夫们要人让道的吆喝声。”[5]
2.1 因瓷而兴的城市
因为陶瓷业兴盛,景德镇吸引了远近四方的民众,“完全可以和中国最大的、人口最多的城市相提并论。这些被称为‘镇’的地方人口不多,但交通方便,商贸发达。它们习惯上不筑城墙,或许为了可向四周拓展延伸,也可能为便于装卸货物……生活费用比饶州高得多,因为一切消费品均需从外地运来,甚至烧窑所必需的木炭也是这样。尽管如此,景德镇仍是周围城市里生活无着的大批贫困家庭的谋生之地……各处升腾起的火焰和烟云首先可让人看到景德镇的纵深范围和轮廓。入夜,真好像看到了一个到处着火的大城市,或是一个有许多通风口的大火炉。”[6]殷弘绪在书信中说,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体力差的人,都能在景德镇找到工作,甚至残疾人也可以依靠研磨颜料来维持生计,陶瓷业的兴盛极大带动了景德镇及其辐射地区的就业,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非常强。殷弘绪的描述与乾隆年间朱琰在其著作《陶说》中所言“景德镇袤延仅十余里,山环水绕,僻处一隅,以陶来四方商贩,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藉此食者甚众”[7]是相契合的。
此外,尽管景德镇位于内陆山区,但却毫不闭塞。景德镇的一位富商曾经漂洋过海出外经商,返回景德镇后,建造了一座天后庙,“这座新庙宇是靠在印度各地积聚的皮阿斯特兴建的,当地对这种欧洲货币很熟悉,因此不必像其他地方那样将其熔化后再用于流通”,[8]当时景德镇对外商贸之发达,由此也可见一斑。
2.2 对“火神”的偶像崇拜
殷弘绪在书信中提到,景德镇有瓷窑不下三千座,因为在制瓷过程中火灾频发,于是人们便纷纷建造火神庙,对火神不遗余力得顶礼膜拜。“每个行业皆有特定的偶像……(按:陶瓷业的)这个神的名称叫菩萨;它的出现正是起因于瓷工们无法做成的这类式样。后来变成了主宰瓷器制作的神。”[9]
殷弘绪所说的“菩萨”神,即指明代浮梁县的窑工童宾。明代宦官潘相在督理御器厂期间,烧造龙缸,久未成功,于是苛索工匠,派役于民。童宾性情刚直,不忍同役受苦,“跃入窑突中以死,而龙缸成”。[10]景德镇的窑民通过对“火神”的崇拜,他们相信制瓷之事有神灵庇佑,而能避免火灾,从而顺利完成制瓷任务,这也反映了当时景德镇的民间信仰和偶像崇拜。
2.3 井然有序的社会治安
景德镇因陶瓷业的兴盛,聚集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然其社会治安却井然有序。“一个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每天有无数船只穿梭往来、根本没有城墙的地方居然只有一名官员管理,却又丝毫不见混乱……治安制度很令人钦佩:每条街都有一个由地方官指派的地保,长一点的街道则有几个地保;每个地保有十名下属,每名下属各为十户人家担保;他们必须维持秩序,一有骚乱就立即平息并向官员报告,违者将被杖责……每条街道都有栅栏,夜间关闭;大街则有好几道栅栏。每道栅栏皆有一个本地人守夜,只有见到某些信号才敢开启栅门。此外,地方官常出来巡视,浮梁的官员们不时也会来视察。再则,陌生人不得在景德镇住宿,他们要么在船上过夜,要么住在为他们作保的熟人家里。这种治安制度维持了秩序,在整个这片因其财富而引起无数盗贼垂涎的地区确立了完全的安全感。”[11]
令殷弘绪大为惊叹的是景德镇的社会管理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景德镇陶瓷业的繁盛。
3 传教策略与制瓷经验的获取
殷弘绪作为一名来华传教士,有效地与本地的官民、窑工进行沟通是其获取制瓷经验的基础,而传教策略在其中发挥了桥梁纽带的关键作用。殷弘绪在实践中形成的传教策略使其得到了官方的庇护,能够游刃于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得以自由进出陶瓷作坊、熟悉烧造工序、了解制瓷技艺。而且,在景德镇的信众中,“不少人是从事瓷器生产的,另一些人则做瓷器生意”,[12]这些人或为殷弘绪传授制瓷技艺,或为殷弘绪解读制瓷文本,为殷弘绪获取中国的制瓷经验扮演了重要角色。
3.1 争取本地官员的支持
中西之间有着不同的信仰、传统与习俗,彼此差异很大,当西方教义传入中国,不可避免会产生碰撞、抵牾甚至冲突。据殷弘绪的书信记载,因为偶像崇拜的异见,基督教信众往往受到地方迫害,“有些人被上了镣铐,另一些人遭了杖击,还有人因信奉基督教或因帮助有人归信而丧失了财产并遭到其他许多虐待。”[13]在殷弘绪看来,紧要之举在于正其名,使信教活动得到政府的认可和保护。
康熙四十八年(1709)2月26日,殷弘绪应江西巡抚朗廷极的通知,向康熙进献西洋葡萄酒。殷弘绪陆续呈送了西洋葡萄酒66瓶、哈尔各斯默1瓶、朱谷腊8瓶,并同郎廷极亲手装贮加封,按照康熙的要求,“速著妥当家人雇包程骡子星夜送来,不可误了时刻”。[14]三月初二,郎廷极将此事奏报,康熙朱笔批示:“此折奏来的甚是。已后你有西洋人有进之物,折子上写明,不奏闻。”[15]由此可以看出,殷弘绪、郎廷极得到了康熙的赞许。康熙五十四年(1715),殷弘绪在给布鲁瓦西亚神父的信中说,“(结交官府)是令人讨厌的不得已之举,但又是发展宗教所必需的”,[16]“送一些欧洲礼品来赢得其友情和保护”[17]成为殷弘绪与新上任地方官员相处的经验之谈。
此外,殷弘绪还通过基督教徒的虔诚祈祷这一宗教活动获得地方官员的认可和保护,在给中国和印度传教区巡阅使神父的信中,殷弘绪详细记载了一则祈雨事件。康熙五十一年(1712),饶州旱情严重,面临颗粒无收的境地。道台龚嵘②“忧心如焚,夜间数次起来查看天上是否有云”,[18]于是派管家向殷弘绪致意并转告当前的困境。殷弘绪回到饶州后,龚嵘专门派人告知,打算亲自祈求上帝保佑,并请殷弘绪向他说明应该如何行事。面对这种情形,殷弘绪把基督教徒全部集中到教堂祈祷,祈祷结束后不久,大雨即倾盆而下。龚嵘“马上派人给教堂送来大蜡烛、香及插满了他亲手采摘的当地最名贵的花的一只花瓶,通通供于祭坛上。他还要郑重其事地感谢最高主宰……身穿大礼服,还配带着表明其官衔的其他标志……整个仪式表明,他对上帝怀有至深的敬意,人们简直以为道台是我们最虔诚的基督徒中的一员”。[19]经过这一事件,殷弘绪进一步得到了地方官员的尊重和认可。殷弘绪向龚嵘谈及对基督教徒的欺压一事,“信徒们每天都要遭到新的强制” “有人责令他们捐助偶像崇拜”,希望龚嵘能够通过行政权力予以支持,以免信众“被反对者的权势压垮”。[20]龚嵘答应了殷弘绪的请求并发出告示,禁止辖区内再发生强迫捐税等类似事件,“违反本告示者予以惩处,必要时将其押送本衙听审”。[21]此外,出于对殷弘绪的尊重,龚嵘还免除了对基督教徒的某些劳役。
3.2 循序渐进的本土化
康熙年间,基督教作为民间的外来非官方宗教,其信众主要是底层民众。在殷弘绪看来,向底层民众传播教义,与他们进行有效沟通是开展活动的重要环节。殷弘绪在到达饶州之前,这里的传教状况并不乐观,“未至饶州以前,信教者无一人”。[22]当时首先加入教会的是一位参与修建教堂的贫穷泥匠,在泥匠去世后,殷弘绪用基督教的仪式为他举行了丧礼,当地人感觉十分特别,“时为新年,来堂询问者不下万人”,[23]加上殷弘绪“性情和蔼可亲,温厚宽和”,[24]很多庶民和士人都乐意与殷弘绪交往。
同时,殷弘绪主张传教应从平民路线开始,逐步由穷人向富人延伸。“穷人和富人都是我们热忱工作的对象……我还有许多教友却在丛林中与未开化的人生活在一起,为把后者争取到耶稣基督一边,他们使自己也变成了与后者一样的野人。”[25]
随着殷弘绪开展循序渐进的本土化传教策略,入教人数有所增加。康熙五十一年(1712),殷弘绪在给中国和印度传教区巡阅使神父的书信中写道:“今年我为约80名成年人施了洗,其中许多人已开始在不同地方让人们领略基督教了。”[26]
3.3 创新退省方法
在信众反思退省的过程中,殷弘绪创新了一系列更为实用的方法,例如,敬奉十字架、③变换退省期间的每日活动、④对展示罪人和义人在今生和死后不同状况的图画予以解释、改课间休息为餐后个别交谈、对忠实履行退省进行书面诺言等,通过这些方法,使信众笃信基督教教义,进而虔诚恪行。
4 中国制瓷经验传入欧洲
16世纪以来,中国瓷器以其材质独特、品种繁多、器类丰富、纹饰多样等特质得到欧洲人的青睐,欧洲各国王室和贵族竞相追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人的生活美学和艺术风格。16世纪下半叶,欧洲一些瓷器厂已经开始烧造瓷器,但始终停留在低温软质瓷阶段,胎体的质地疏松,釉面的硬度也不高。1708年,在位于今德国境内的萨克森王国,炼金术士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格尔(Johann Friedrich Boettger)和数学家奇恩豪斯(Ehrenfried Walther von Tschirnhaus)共同研制瓷器,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硬质白瓷花盆;1710年,在德国德累斯顿附近建成的迈森皇家瓷器厂,批量烧造出硬质瓷。然而,无论是在釉色上,还是在纹饰上,仍然无法与中国瓷器相媲美。此时,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瓷器依然是双边贸易中最大宗的商品之一,由于商路遥远加上海运具有风险等因素,其价格非常昂贵。而且,殷弘绪还指出了价格高的另一个原因:“一窑瓷器完全成功的情况是罕见的,整窑报废倒是常事……运往欧洲的瓷器几乎总是照新式样——往往是奇怪的式样——制作的,因此很难成功,稍有点缺陷便会被欧洲人拒绝……瓷器就积压在瓷工手里,又无法卖给中国人,因为这种式样不合他们口味。所以,取走的瓷器中应当包括被抛弃的瓷器的费用。”[27]在这种情形下,掌握中国瓷器的制作技艺并在欧洲进行本土规模化生产便成为欧洲人的急切之盼。
通过长期的实地考察、与从事瓷器生产经营的基督教徒交流以及研究《浮梁县志》等典籍,殷弘绪对中国瓷器的制作技艺形成了“全方位的相当准确的了解”,[28]在其《致耶稣会中国和印度传教会巡阅使奥里神父的信(1712年9月1日于饶州)》《致本会德布鲁瓦西亚神父的信(1715年5月10日于饶州)》《致本会某神父的信(1722年1月25日于景德镇)》《致杜赫德神父的信(1734年11月4日于北京)》等多封书信中细致描述了中国制瓷经验,其翔实程度甚至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不多见。对于当时的欧洲人而言,这是第一次系统了解到烧造瓷器的中国经验,极具实操价值,可以说是最为直接且最具有参考价值的第一手研究资料。18世纪前期的法国古董商杰桑(Edmé-François Gersaint)曾批评当时对于中国瓷器的报道只会抄袭殷弘绪的论述,[29]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欧洲人对殷弘绪书信资料的重视程度以及中国制瓷经验对欧洲人的重要价值。
4.1 烧造经验
殷弘绪在书信中介绍了瓷器的原料来源、制作工序、施釉技法、温控措施等烧造经验,其中,尤为关键的是,殷弘绪介绍了制瓷的两种原料,即坯胎子土和高岭土,这也是制瓷技艺的中国秘诀——“二元配方”。
“精细的瓷器正因为高岭土才这般坚实:它犹如瓷器的肋骨。因此,取自最坚硬的岩石的坯胎子土必须与柔软的(高岭)土混合,因为后者可使它具有韧劲。”[30]坯胎子土和高岭土的混合比例在瓷器生产的过程中非常重要,“净化后的胚胎子土和高岭土须按精确比例混合,制作细瓷时两者对半相混,制作普通瓷器则四成高岭土对六成坯胎子土;最起码的比例是一份高岭土对三份坯胎子土。”[31]胚胎子土加高岭土的配方,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欧洲瓷厂烧造高温硬质瓷的关键难题。
此外,在书信中,殷弘绪还提到了制作瓷器的新配料——滑石,用滑石制作的瓷器质地极为细腻,即使在中国也非常罕见,因此它远比其他普通瓷器昂贵,“犹如上等羔皮纸与一般纸张相比”。[32]
4.2 筑窑置瓷经验
殷弘绪在书信中介绍了窑的建造情况。窑建在空旷的地方,“人们把窑建于一片场地的尽头,这片场地既可使窑通风,又可堆放出窑的瓷器”[33]“窑周围整齐地砌着一围砖墙,砖墙底部留有三四个通风口,犹如火炉的风箱。”[34]窑有铁制的,但通常是土窑,“高2寻(按:约3.2米),深约4寻(按:约6.4米)。顶部和窑体都相当厚,这样,人在窑顶行走不致因火焰而感到不适。窑顶内侧不是平的,也不是尖的;它是向窑顶的大通风口渐渐收口变小的,滚滚浓烟和火苗从这个口子里排出。此外,窑顶还有五个如同窑眼的小口子,人们用破罐片将其盖住……通过这些窑眼来判断瓷器是否已经烧好……当看到窑内火光明亮清纯、所有箱子都已烧红,尤其是各种色泽大放异彩时,说明瓷器已烧好了。”[35]
殷弘绪对瓷器在窑中的置放、制作盛装瓷坯的箱子所用的泥土等问题也进行了描述,“最上等的瓷坯放在窑的中部,底部摆放最普通的,窑口边放色彩最深的……(按:盛装瓷坯的箱子所用的泥土)一种是相当常见的黄土,它因大量存在而成为最基本的原料。另一种叫牢土,这是一种胶土。第三种是称为油土的油质土。后两种土是冬天从很深的矿里挖出来的,但夏天无法下矿去挖。把几种土平均掺合起来使用,箱子造价要高一些,但使用时间也长……出于节省,人们主要以黄土制作箱子,所以他们只能在窑里烧两三次,之后便完全破裂了。”[36]
4.3 审美经验
殷弘绪在书信中同样关注瓷器的装饰纹样、造型特征等审美元素,并且介绍了诸多中国的名贵瓷器。例如,臧窑是臧应选于康熙二十年(1679)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以工部虞衡司郎中之职兼任督陶官时在景德镇烧造的瓷器,“其浇黄、浇紫、浇绿、吹红、吹青者亦美”。[37]殷弘绪在书信中对吹红釉的描述佐证了臧窑的施釉方式,“吹红是这样制作的:先备好红色颜料,再取一根管子,一端蒙一块绷紧的纱罗,把管子下端轻轻贴在颜料上,然后从管子里对准瓷器吹,颜料经由纱罗喷到了瓷器上,使之布满小红点。这种瓷器……更贵,也更罕见,因为要想吹得像要求的那样匀称是十分困难的”。[38]除了吹红釉以外,紫金釉、乌金釉以及透雕等类型的瓷器也在殷弘绪的书信中有所描述。
窑变是殷弘绪论及的一种意外收获的瓷器审美经验,“这种变态是在窑内发生的,其原因或是因为火势不够或太过,再或是因为其他某些不易猜测的原因。这件瓷器未能依瓷工预期目标烧成……然而却照样很美,很受重视……这件瓷器出窑时像一件玛瑙制品。如果人们愿意冒险并不惜承担种种试验费用,最终就能发现并掌握这种看似偶然性所形成的窑变的技巧……窑的变幻无常主宰着这一探索,但是人们获得了成功”。[39]
对于瓷器审美元素之一的瓷画图像,殷弘绪也有其独到的见解。殷弘绪承认在瓷器上作画会让瓷器更精美、更名贵,但同时他也指出,“画工通常只有中国画的技巧,无任何准则,只按某些陈规作画,想像力相当有限。他们对绘画艺术的所有规则均一无所知”。[40]
4.4 辨赝经验
殷弘绪在书信中甚至还对赝品瓷器有所论述,“制作此类瓷器无任何特别之处,只是上釉时用的是由黄色石头制成的一种釉,但其中混有普通的釉,而且以后者为主……瓷器烧好后需放入由阉鸡和其他肉类做成的非常油腻的汤里再次烧煮,捞出后在积满污泥的阴沟中放置一月有余。从阴沟里取出后,它就像三四百年前的或至少是明朝的瓷器了”。[41]
4 结语
通过殷弘绪系统而完整的介绍,法国乃至欧洲掀起了借鉴中国制瓷经验尤其是用“二元配方”研制高温硬质瓷的热潮。1740年代,迈森皇家瓷器厂在以往自行研制硬质瓷的基础上,运用“二元配方”的经验,烧造出青花、描金等高温硬质瓷。1760年代,法国塞夫尔瓷厂在利摩日发现优质的高岭土并烧造出硬质瓷,成为继德国之后、第二个生产硬质瓷的欧洲国家,利摩日因此跃升为欧洲瓷都而享有盛誉。在殷弘绪书信的指引下,欧洲的制瓷技艺得到加速成熟并取得本质突破。
注释:
① 认为殷弘绪来华是“为了侵略中国,披着传教士的外衣,刺探和提供中国的经济、政治、风俗和文化等各方面情报。昂特雷克莱的两封信正是这个殖民主义分子刺探和反映景德镇社会状况,进行殖民活动的铁证”。参见:景德镇陶瓷馆文物资料组,编.陶瓷资料[M].南昌:南昌市瓦子角誊印组,1978:1。
② 经笔者考,信中所言的道台应为龚嵘。《江西通志》(雍正十年刻本)卷四十八载,“龚嵘,字澹岩,福建闽县人,监生,康熙四十八年任(按:饶南九道道台)”;《清史稿》载,龚嵘“初仕浙江馀杭知县,治县民杀仆疑狱,为时所称。擢直隶赵州直隶州知州,浚河兴水利。再擢江苏松江知府,渡海赈崇明灾黎,全活甚众。官至江西广饶九南道,单骑定万年县匪乱,殁祀饶州名宦祠。”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926。
③ 殷弘绪在致中、印传教区巡阅使的书信写到,“他们匍伏在带耶稣像的十字架旁,泪如泉涌,教堂各个角落一片叹息呜咽之声……正是这一切使我下了决心:不管何时举行退省, 这一仪式不可省略。”参见: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61。
④ 殷弘绪在致中、印传教区巡阅使的书信写道:“这些活动包括:深思基督教的伟大真理和宗教的主要奥义、劝导其遵守上帝的戒律,进行忏悔和领圣体,在逆境中应有耐心,注意使一切最普通的行为也变得圣洁,还要热心关注教友的永福。”参见: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61。
——省景德镇老年大学校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