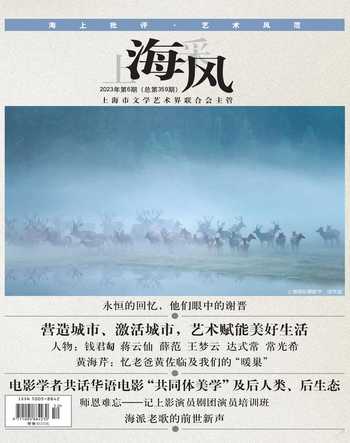搞译制片要多读书,当个“杂家”
孙渝烽



最近在整理书橱时,突然找到了当年上译厂老厂长陈叙一送我的一本《新旧约全书》,至今已有40多年了。老厂长1992年4月因病离开我们,才74岁,似乎早了一些。30多年来一提起上译厂,我们都会深深怀念这位上译厂的奠基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译制事业。
了不起的“杂家”
20世纪70年代,我从上影演员剧团调入上译厂,是老厂长手把着手教我搞译制片,培养我当译制导演。回想当年译制厂的工作,事无巨细,老厂长都认真过问,这是一份“家业”更是一份事业。凡是厂里生产的译制片,绝大多数剧本老厂长都亲自审阅,以保证译制片的质量。20世纪70年代译制厂迎来一批年轻的翻译人员,为译制片事业注入新鲜活力。老厂长十分关注年轻翻译的成长,很多影片他都带着他们一起搞剧本翻译,使他们尽快能独立工作。年轻翻译译制的剧本他都亲自把关,给予细心的指导。我还常常听到老厂长告诫年轻翻译:“这个典故,你可以从《旧约·创世纪》中去查。”因为译制片的台词中常常会碰到引用《圣经》里的典故和词句的情况,有时老厂长会告诫年轻翻译:“有时间,《新约》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这两章你们一定要认真地读一读。”
记得老厂长带我译制《孤星血泪》时,他又提到搞好译制片一定要懂西方的历史文化,要认真读《圣经》读《希腊神话》以及但丁的《神曲》,这如同中国电影里也常常引用《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红楼梦》等名著一样。搞译制片一定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越丰富越好,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杂家”。
我后来跟老厂长一起译制美国影片《猜一猜谁来赴晚宴》时,老厂长带来这本《新旧约全书》查资料。搞完对白剧本后,我向老厂长借了这本“圣经”,我想认真读一读。过了很久,总有一两月之久吧,我看完后归还老厂长。他说:“你留着吧,我家里还有一本大的。”这就成了我的一份珍贵礼物。后来搞片子,我多次从这本书中查到了原文的意思。老厂长说得很对,外国人的对话中常常会引用《圣经》里的典故来说明一些事情。
上译厂第一代配音演员中,如卫禹平、邱岳峰、毕克、尚华、苏秀……都十分敬佩老厂长知识面渊博,称他为“杂家”。他们也常常告诫我:想要搞好译制片,特别是当导演,一定要多读书,多查阅史料。因为译制片中很多人物的经历,我们只有从书本上去找、去借鉴,你无法也不可能去体验。更重要的是,我们搞译制片接触的涉及的人物或历史事件,都是五花八门的:上层人物是帝王将相、总统、达官贵人、教皇、传教士、科学家、学者,下层人物有流氓、妓女、人贩子、杀人犯、同性恋者……总之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会出现在我们搞的译制影片当中。因此只有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使自己成为一个“杂家”,才能适应我们的译制工作。
老厂长陈叙一就是我们上译厂搞好译制影片的一根标杆。几十年过去了,他的水平和知识面,至今似乎依然无出其右者。他翻译剧本时那种执着、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我至今难以忘怀!最近有机会重看他当年翻译并导演的电影《简·爱》,让我又回忆起当年工作的情景。
这部电影是1972年译制的,他让我当他助手。接到译制任务后,他问我看过小说《簡·爱》吗?我说中学时看过。他说你现在看过电影了,再读读小说会有新的体会和感觉。我从上海电影局资料馆借来小说《简·爱》,徐大雯老师(谢晋导演的爱人)还把小说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资料一起推荐我看。
说到这里我必须插一段话,真的要好好感谢大雯老师对我们译制片的大力支持。我只要打电话告诉大雯老师影片的内容、年代,她就会给我准备好有关资料。记得搞卓别林电影,以及拿破仑相关影片时,她为我找了一大堆史料。我抱回厂里,老卫、老邱高兴极了,老厂长偶尔也会挑一两本去翻阅。徐大雯老师对我们译制工作的支持是实实在在的,十分尽心。
实际上搞译制片工作最重要的难点就在于努力搞好译制对白台本,有了这个配音的一剧之本,那大功就完成一半了。配音台本要从头到尾一段段地编词,意思要准确,口型要对,所以译制导演和翻译会无数遍地看影片。记得我当时就有机会一边看小说一边反复看影片。我真的十分敬佩《简·爱》女主角的扮演者苏珊娜·约克(当年她已五十岁),扮演一个18岁的姑娘是那么出彩。小说中有很多简·爱内心活动的描写,影片中的演员从她的眼神、表情和一些不动声色的动作中,充分展示出女主人公内心复杂的活动。小说中描写的大段内心活动,演员都充分展示出来了(我这里不一一举例了),这位英国女演员真是太棒了。
我很感谢老厂长让我重读这部小说,后来我为上海广播电台写了《简·爱》的电影录音剪辑,请李梓老师用第一人称内心独白的形式,把电影有机地串联起来,受到听众极大的欢迎。
老厂长搞《简·爱》十分用心,他告诉我这部名著改编成影片改得非常好,比美国的拍得好。他当时告诫两位配音演员李梓、邱岳峰,这部名著改编很成功,反复提醒李梓老师配音时一定要把握简·爱这个人物“不卑不亢”这四个字,这是简·爱这个人物的主心骨。特别是“花园”那场戏,充分展示简·爱那种不卑不亢的精神,而这段精彩的台词老厂长也是下了大功夫,几经琢磨、推敲才译成的。电影里这段精彩的片段,现在很多电影观众都会背诵:“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她跟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这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地站在上帝面前。”
这段台词,老厂长是经过反复推敲才定下来的。如“我也会的”“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为了想这些词该如何说得更确切、更符合人物内心活动,他甚至在洗脚时忘了脱袜子,双脚就浸在脚盆里了。李梓老师配音也十分出色,充分展示了简·爱对罗彻斯特的爱,那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的爱!
老厂长还特别提醒邱岳峰,罗彻斯特的脾气古怪、冷漠,甚至不近人情之处完全在于他内心的痛苦所致。
当罗彻斯特醒来后发现简·爱不在身边,离开了桑菲尔德庄园,那寻找简·爱喊的十个“简·爱”,声声撕心裂肺。当时在棚里录音的时候,老邱喊好几遍,嗓子都有点哑了。我当时听,已经十分动情了。可老厂长说:“还不够揪心。”只有“揪心”才能把简·爱最后找回来。最后录得非常好。老邱是一位很了不起的配音演员。
老厂长还特别提醒老邱最后那一场戏:一定要恢复这个人物内心的平静,但对简·爱的关怀是出于对简·爱深深的爱。那些对话说得十分平静,但要充满关切、爱护之情感:“还没有结婚?”“这个不好,简,你长得不美,不能太挑剔。”“你几时结婚?”“早晚有个傻瓜会找到你。”这场戏老邱分寸把握得非常好。
上海外语学院有一位教授十分喜欢这部电影,把原版片和我们的配音版同时放,进行比较,最后他非常感慨地说:“邱岳峰的配音太棒了,为原片演员补充了很多细节,把急促的呼吸声、喘气声都配出来了,太棒了!”
《简·爱》应该是老厂长翻译、导演众多精彩影片中的一部,是一部花了心血的杰作!可他的作品多着呢。我仅举几部大家非常熟悉的影片,譬如说《华沙一条街》《偷自行车的人》《王子复仇记》《三剑客》《神童》《红菱艳》《冷酷的心》《音乐之声》《大独裁者》《现代启示录》……
还有一个事例值得一提,那是在搞《加里森敢死队》这部系列电视剧时。这是一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一位上尉带领几个囚犯去执行打击德国法西斯的战斗任务,这些囚犯中有杀人犯、惯偷……文化素质不高,出于对法西斯的痛恨,所以作战很勇敢、机智,剧本中对带领他们执行任务的上尉,称呼是很明确:“上尉”“长官”,字面上也很合理。可老厂长觉得这个称呼对这些囚犯来说太文绉绉了。从剧情发展上来看,他们在上尉带领下出生入死,和上尉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了,成了生死之交。老厂长一直在想这个称呼怎样才更合适,让我国观众能接受理解。对白剧本完成了,马上要正式录音了,那天他向大家宣布剧中“上尉”“长官”的称呼全都改成“头儿”。
这个词太绝了,既符合这些大老粗的身份,又表现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个转译是非常成功的例子。电视剧公映后,这个“头儿”的称呼一下子风靡全国。后来好多文艺作品也常常用这个称呼,从这里不难看出老厂长在译制上的用心良苦。这都是属于搞译制片“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案例。这些努力对我们这些晚辈来说都是非常有教益的!
“别得意,继续努力。”
记得我在译制英国电影《野鹅敢死队》时也遇到很多难处。
我是这部电影的译制导演。在厂长办公室,老厂长把翻译剧本交给我,我翻了一下傻眼了,剧本好多地方都开天窗,有些地方是大段空白。老厂长说:“小孙,这个剧本确实有难度,啃啃硬骨头对你有好处。小刘(我厂年轻翻译)已联系好她外语学院的老师,请张宝珠老师来参加工作,配合你搞好这个戏的对白台本。你什么时候把剧本搞好,我们就马上进棚录对白。我不催你,但必须抓紧时间把对白本搞好。”
这部电影我们看过原片,是描写一批雇佣兵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全是大老粗,人物性格很鲜明,戏挺好看。
过了一天张宝珠老师来厂,我陪她看了原片《野鹅敢死队》。她看完对我说:“孙导,这部电影不好译,人物身份层次很多,有銀行家政客,有非洲革命家,特别是这批雇佣兵说的很多是粗话,我明白对白的原意,但不知如何用中文来表达。”
“张老师,我听小刘说,你在美国长大,回国来搞教学。你英文底子厚实,你把原文意思告诉我们,我们共同来想办法。”
张老师当时在外语学院还有教学任务,凡是不上课就来厂里帮我们译剧本。
当年厂生产办主任陆英华知道我接了这部电影,就来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录音。我告诉他,老厂长没有给我时间限制,什么时候搞好对白剧本,什么时候录对白。
“天哪,那怎么行,中影公司这部电影要得很急,下个月公映时间表都出来了,这是要赶任务的!”
“老陆,你跟我急没用。张宝珠老师来想协助我们译剧本,你们生产办准时去接送,我们一定努力。”
老陆是个很细心的人,了解了张宝珠老师的授课时间表,凡是第二天不上课,他就求张老师在厂里加几个夜班,就这样我们整整在暗房里关了22天,才把对白剧本攻下来。
这部戏的难点在于这些雇佣兵,说的话比较粗,很多用我们的国骂“他妈的”是无法代替的。特别麻烦的是其中一个男卫生兵是同性恋者,很多粗话是针对他说的,要找到合适的词来表达难度很大。比如军事训练那场戏,为了今后执行任务,军士长训练所有人必须加快跑步速度,不然短时间无法穿越开阔地,很多人跑得都爬不起来了。军士长对躺在地上的卫生兵踢了一脚骂道:“……”张老师说这话骂得十分粗鲁、恶心,不知道怎么用中文来表达。类似这样的拦路虎很多。为了进度,我们只好把这些戏先跳过去。那天下班,张老师乘车要回去,我问张老师这句骂人的粗话是针对这个同性恋者骂的吗?“是的,很粗鲁。”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这脏话该如何表达为好,折腾了一晚上也没睡好。没想到第二天骑车上班路上突然想了出来。到厂里,张宝珠老师已被厂车接来了。我对她说:“张老师,昨天那句骂人话你听听可合适:‘你再不起来,我就把你的屁眼缝起来,快起来!’”张老师听完高兴地说:“太好了,这意思准确。”对后面那个趴在地上的也骂了一句:“再不起来,我把你那玩意儿吊起来。”就这样,这场戏过去了,也让我们打开了思路。张宝珠老师毕竟在美国长大,英语功底很扎实。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让她把英文的原意讲清楚,内容大约指的是哪方面,我们就挖空心思去找合适的中文词句来表达,最后再让她定夺。我这部戏的口型员是配音演员施融,他正在努力学英语,我们常常一起用这种方法编台词,后来剧本进展就顺利多了。
我发现打字员小董每天都要来我们放映间好几次,取对好的口型稿。我说:“小董别急,下班前我们会给你送过去的。”她悄悄地对我说:“孙导,我不急,是老厂长急着要看你们每天的口型稿。”我明白了,老厂长实际上比我们还急。中影公司要的电影,我们厂从来没有拖后过,总是提前完成的,这是信誉问题。
老厂长一方面关心着我们的进度,同时也认真地审稿,帮我们把语言关。
拦路虎还是有的,同样发生在同性恋卫生兵身上。他有一段词比较“黄”,张宝珠老师说:“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好,不能太直露。”我把这段话的口型字数记下来,先往下顺剧本。过了两天,我把想好的词告诉张老师,请她斟酌。“小伙子们去城里玩得开心,晚上回来姑妈把床单铺好了给你们打针。哈哈哈。”张宝珠听完:“说得太好了,打针这个词儿绝了!”她非常感慨地说:“我英语可以,但如何用中文来表达这方面的知识太欠缺了,这次和你们一起工作,让我长了不少见识,要补中文这一课。”“不,张老师,老厂长教我们:一定要吃透原文意思,寻找最合适中文,观众能听得明白的词句,这是我们译制工作者每天要下功夫做的事情。”
在张宝珠老师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完成对白剧本的工作。
搞完最后一页,老厂长让我交出配音演员名单,并告诉我明天下午就复对,准备正式录对白。配音工作进行得也很顺利,老厂长亲自把关鉴定补戏。
陆英华把印制拷贝相关的事情也全安排好了,对白、音乐混录完马上印拷贝送北京审查。
有一件事我至今很后悔,愧对张宝珠老师。当时我想一定要把张宝珠老师的名字写在影片翻译一栏里,是她们师生俩共同完成翻译工作的。当我把这事告诉陆英华时,他说晚了,字幕已拍好了,老厂长审定过了,明天就印拷贝了,没时间改了。几十年过去了,这一直是我一块心病。张宝珠老师,我们不会忘记你为这部影片付出的辛劳!
《野鹅敢死队》按时在全国公映了。有天夜里我接到孙道临老师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渝烽,《野鹅敢死队》这个戏搞得不错,人物语言挺有个性。祝贺你又完成一部好电影,搞译制片就要在台词上下功夫。”
第二天早上,我见到老厂长:“道临老师很关心我们译制的影片,昨晚给我打电话,说《野鹅敢死队》译制得不错。”
老厂长看着我,笑着留下一句话:“别得意,继续努力!”
我们这些长期在暗房里工作的“棚虫”,最大的乐趣就在于能想出一些绝词儿,把电影译制好,让观众看了满意。“得意”实际上也是给自己的一份奖励。记得老厂长想出“头儿”这个词,也乐过一阵子,后来配音演员潘我源就直呼他“陈老头儿”他也挺开心。
还要译制片吗?
最近我看到多篇文章谈及译制片的生存问题,记得早几年就有记者问我:“孙导,你认为译制片还会在我国存在吗?”
我说,干嘛不要译制片这个片种呢?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有十亿的观众,不可能人人都懂外语,译制片大有存在的必要。现在大城市年轻人懂外语的不愿意看译制片,说什么破坏了原片的艺术效果。你可能懂两门,就算三门外语,能看懂三个国家的影片,那其他语种呢?说打字幕就行了,那你只能了解个故事情节,对于一些好影片的精彩台词你能欣赏吗?
实际上我了解了一下,很多人对影片中很多精彩的对白并非都很了解,外语学院的教授们也说看原版影片一次能懂七八成那已经很不错了,好电影必须反复看多次才能真正理解其内在的艺术性。对于广大的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来说,还是喜欢看译制片。现在的关键不是讨论译制片的存在、去留问题,我认为译制片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很有必要存在,而且要发展、扩大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活动。让我们的影片走出国门,各国的好影片不断地引进来,丰富我国人民的文化娱乐生活,更多地理解世界。
译制片有必要存在,关键是做到两点:一是保证译制质量,二是不断出新人、出好声音,事实早已证明这一点。为什么很多观众怀念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譯制影片,因为那时译制影片的质量好,而且配音演员声音丰富多彩。老厂长陈叙一在上译厂30周年厂庆时讲了一段肺腑之言,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30年来,有两件事是天天要下功夫去做的,那就是:一、剧本翻译要‘有味’,二、演员配音要‘有神’,关键是下功夫。”
我期望我们国家的译制事业能不断欣欣向荣,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多好译制片,极大地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