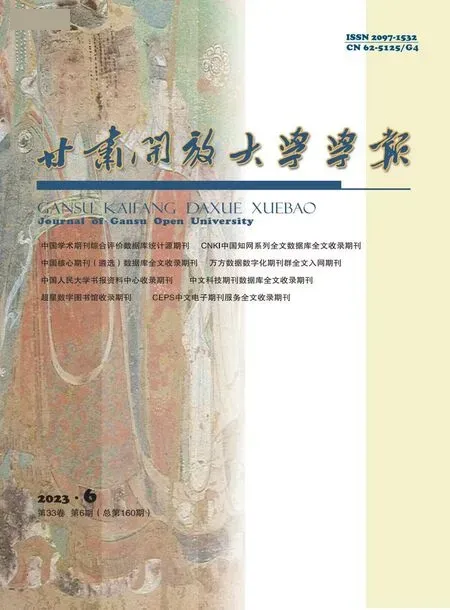浅窥《白鹿原》中的关学文化传统
何文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6)
在《白鹿原》中,“朱先生”这一人物形象贯穿始终,并对小说的情节发展有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小说中朱夫子教化乡民所遇到的种种困境,也是关学在具体传播中遇到的问题。小说中的“朱先生”是以关学大儒牛兆濂为原型创作的。牛兆濂为作为关学史上最后一位大儒,站在传统理学的立场积极思考与回应社会问题,既是清末民初多元化思想的有机组成,又为接续关学学脉、振兴关学做出努力[1]。从中可以看出在传统与现实的碰撞中,关学学人的内在矛盾。
学界关于“朱先生”这一形象的研究多以典型的儒者形象入手,并加以分析,虽较为整体地对朱夫子这一人物形象进行了多角度勾勒,但从人物原型批评视角而言,仍较为单薄。有鉴于此,本文拟从陈忠实创作“朱先生”的初衷出发,结合原型牛兆濂的人生轨迹,来探讨《白鹿原》中透射出的关学传统。
一、创作背景与人物原型
陈忠实于1942年8月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霸陵乡西蒋村,他生于兹长于兹,对关中文化有深切体悟。他在文学创作中,赋予作品更广阔的文化视角,力求展现一个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历史文化风貌[2]。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中国文坛“文化寻根”热潮兴起,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陈忠实也毅然辞去工作全身心投入写作。1986至1987年,陈忠实先后前往西安周边的蓝田县与长安县,查阅了地方志,翻阅了咸宁县志、地方党史等资料,并在白鹿原上与当地乡民一同生活数年,将白鹿原上那些不曾写入正史的内容,以小说的方式呈现出来,对长久以来隐匿在民族集体记忆深处的话题予以探讨。
正如陈忠实所言:“我对《白鹿原》的选择,是因为我对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有了自己的感受,或者说对民族精神中的鲜见部分我有了重新的理解和认识。所以,我规定了《白鹿原》向秘史的方向发展,这自然也说明了我为什么喜欢巴尔扎克对小说的定义。”之所以称为“秘史”,正是“相对于大历史、正史而言的,是正史的孑遗,是正史的背面,是偏重于感性和个人性的小历史”[3]。陈忠实笔下的历史真实是有自己独特的发现和洞见的。《白鹿原》中的许多人物原型正是由此而来。白灵的原型来自党史回忆录,田小娥形象的灵感来源于蓝田县志中的洁妇烈女,被誉为“白鹿精魂”的“朱先生”,正是以“横渠以后关中一人”的牛兆濂为原型创作而成[4]。
牛兆濂号蓝川,陕西蓝田人,生于同治六年(1867),卒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被认为是传统关学的最后一位大儒,他的生平事迹载于张元勋的《牛蓝川先生行状》[5]507。他自幼聪慧,遍读四书五经,二十一岁时,在沛西大儒柏景伟主讲的关中书院,得闻濂洛关闽之学及贺瑞麟之名,开始接受程朱理学。牛兆濂二十八岁赴三原拜贺瑞麟为师,确定了终生坚守程朱理学的信念,后来他亲手打造了关中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芸阁学舍。他曾中举,但因父母殁而未赴公车,例当除名,陕西巡抚惜才爱才,便以孝廉奏请朝廷,他辞官不就,终不赶公车。
牛兆濂虽不喜为官,但当国家危难之际,他又不遗余力为国奔波,对陕西地区赈灾、禁烟贡献颇多。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出面斡旋,使得陕西地区的百姓免受一场战祸。面对日军侵华,年逾花甲的牛兆濂依旧为国事奔波,为抗日募集勇士,但却在奔赴前线之际被劝回。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饮恨而亡,享年七十一岁,牛兆濂用一生践行了“位卑未敢忘忧国”。
牛兆濂经历了戊戌变法、废除科举、新式学堂、清帝退位、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救亡等中国百年史上的重大变革。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传入,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牛兆濂却仍然恪守程朱理学,坚持理学救国,对西学采取排斥的态度。正如刘学智所言:“牛兆濂在传统与现实的冲突中,以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来支撑其对社会种种运动的积极参与,说明他始终没有自觉也没有勇气冲决固有的藩篱,这正是牛兆濂身上所体现出的时代悲剧。”[5]520
正是由于牛兆濂与作品中的“朱先生”的经历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当牛兆濂回顾中国百年理学,以求为民族文化寻求出路时,作家陈忠实也在百年之后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一场文学的“寻根之旅”。
二、《白鹿原》中关学思想的展现
关学指由张载创立并在其后流衍中与张载学脉相承的关中理学。关学自北宋开宗立派,至晚清牛兆濂等人,历时约八百年,其基本特征表现为躬行礼教、笃实践履、崇尚气节[5]59。关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宋明理学又是儒学在宋代的新发展,亦称为“新儒学”。儒学从先秦孔子发轫而来,起初就代表了没落贵族阶级,因而在后来的发展中总是要依附于政治才能使自己学派的思想得以最大程度发挥效用。当一个村落千百年来恪守着一套礼法制度生活,这套体系在面对外来冲击即将崩溃时,传统儒学能否能解决这一问题,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做了深层探讨。
“朱先生”是白鹿原的文化精魂,代表了儒家的理性文化。关学以“笃风尚实,注重践履;崇尚气节,敦善厚行;求真求实,开放会通”[5]59为旨归,“朱先生”的一生就是对这一精神的践行。“朱先生”首次出场时,作者写“朱先生”刚从南方讲学归来”,其南行目的在于“充分阐释自己多年凿研程朱的独到见解,以期弘扬关中学派的正统思想”[6]。可见“朱先生”并非是作者纯粹虚构的人物。
(一)笃风尚实,践行仁义
小说中的“朱先生”与牛兆濂高度相似,自幼聪颖,长大后参加省试拔得头筹,但因为父守孝而不赴公车,陕西巡抚念其重孝道,因而大力举荐,后被破格录取,但“朱先生”屡次辞官不就,后住进白鹿书院,开始了润物无声的树人大业。小说主人公白嘉轩作为白家长子,更是踊跃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学习,即使是白家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白嘉轩也让其进入书院学习。“读书学习不求升官发财,只为读书明理”。
牛兆濂重视礼教,他主张理学救国,排斥西学,面对中西方文化的碰撞,牛兆濂坚定地坚守儒家传统,深信理学能够扶大厦之将倾,而“教”则是不二法门。牛兆濂一生致力于讲学,曾先后执教于多所书院,并捐资办学,经其大力发展,芸阁学舍声名远扬。
关学坚守孔孟之道“不语怪力乱神”。当孔孟重人事、轻鬼神观念与文化基础薄弱的低层民众相遇时,会碰撞出怎样的结果?在修复白鹿书院时,工人们都不敢推到四尊神像,“朱先生”就亲自动手,推到了泥像,并强调“不读圣贤书,只知点蜡烧香,头怕是越磕越昏了”。
“朱先生”虽然代表了“白鹿精魂”,但在几千年的中国宗法社会里,并没有实际的话语权。因此,《白鹿原》中的男主人公白嘉轩便在这一层面与朱夫子交相辉映。白嘉轩是白家长子,后来成了白鹿原的族长,他有事实上的话语权,他对鬼神同样无所畏惧。当田小娥的鬼魂附他人之体,说出瘟疫由来时,人们纷纷跪求白嘉轩为田小娥的鬼魂修庙安魂,但白嘉轩认为“人妖颠倒,鬼神混淆,乱世多怪事”。他坚持修建“镇妖塔”,驱魔降鬼。
(二)开放会通,气节为重
开放汇通是关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张载“学凡数变”,朱熹在《朱子全书》中记载:“夫子蚤从范文正公受《中庸》之书,中岁出入于老、佛诸家之说,左右采获,十有余年。”[7]《白鹿原》以艺术的形式复演着关学的内在精神。
《白鹿原》开篇讲“朱先生”从“南方讲学归来”。南行的动因是“杭州一位先生盛情邀约,言恳意切,仰慕他的独到见解,希望此次南行交流诸家沟通南北学界”,以期弘扬关中学派的正宗思想。但这一行程似乎并不愉快,终日游山玩水地讲学与“朱先生”的设想大相径庭,于是他大发雷霆道:“吾等应著书立论,大声疾呼,以正世风。”随后愤然离去。“朱先生”虽是一位儒者,但他并没有走儒家“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而是选择在白鹿原讲学,一生不仕。他既有儒者关心民间疾苦的精神,又有道家的隐逸情怀。白鹿原仿佛是他身居江湖的理想家园,但并不妨碍“朱先生”心忧魏阙。小说中对于占卜情节的描述,更使“朱先生”带有玄学色彩,特别是在“朱先生”生命的最后,白鹿腾空的意象又带有佛家涅槃重生的意味。
“朱先生”的身上带有士大夫的风骨,宠辱不惊,坚守本心。“朱先生”有晨读的习惯,总督派兵去他家中找他,他正在晨诵,但“朱先生”并未屈服士兵手中的枪,直到晨诵结束后才出门会见。张总督请他出面说服方巡抚停止战争,在去游说的路上“朱先生”依旧在晨光中坚持晨诵,哪怕汽车轰鸣着从他身边驶过,也充耳不闻,充分体现了儒家“君子慎独”的精神。在清兵全服武装集于西安城外即将屠城时,“朱先生”勇闯敌营,劝退二十万清兵,保全了百姓的性命。特别是“朱先生”进入清兵大营后,吟唱《渭城曲》这一段,使人不禁想起《单刀会》的情节。关羽只身赴会,有万夫不挡之勇,而“朱先生”唯有传统文化给予他的心灵力量,极具悲壮的美学意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善是永恒的追求。“朱先生”是善的化身,他放弃了出仕为官的生活,寄身白鹿书院,只求温饱,选择带给白鹿原文化的曙光,特别是“朱先生”在清兵大营中生死未卜却认真教导白嘉轩如何成为一位合格的族长,更使得他带有“哲学王”意味。充满智慧与谋略,却不求荣华富贵,旨在培养合格的领袖人物,“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三)德业相劝,礼俗相交
关学历来主张“以礼为教”。在小说中,“朱先生”除了让孩子们进学堂,还为乡民们制定了《乡约》。当革命尚未来到白鹿原时,白嘉轩就开始思考:“没有皇帝这日子怎么过?”“剪了辫子的男人成什么样子?长着两片大肥脚片子的女人还不恶心人?”于是,“朱先生”牵头,拟定《乡约》,并由族长白嘉轩监督执行。考虑到乡民们的接受程度,朱先生便将那些文绉绉的大道理编成顺口溜。《乡约》定好之后,短短几年,白鹿原上的人们便讲礼仪,赌博等陋习逐渐消失。
《白鹿原》中的《乡约》,是以历史上著名的《吕氏乡约》为原型。《吕氏乡约》是北宋时期,关学学派的蓝田三吕制定并推演的首部成文的乡村民约,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礼化俗”的乡村治理思想。
在《白鹿原》中,陈忠实首先赞扬了《乡约》规范下民风日渐淳朴的良好风貌,但作者对《乡约》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当田小娥由于个人生活的混乱而被白嘉轩在祠堂里当着全族人施以刑法时,《乡约》中所展现的残酷令人瞠目:刺枣枝抽打、开水烫嘴烫手等一系列酷刑使人很难与“仁义”二字联系在一起,无疑作者对此种行为的合理性心存质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农民阶级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一方面他们想维系宗法制带给他们的好处,另一方面又没有真正领悟到宗法礼法的变通性,将其视为僵死的教条,因而在如何处理未来与传统的关系上出现了巨大的、无法调和的矛盾。
三、《白鹿原》中关学书写的当代意义
陈忠实在小说中以白鹿两家三代人的爱恨情仇为主线,展现了从清末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人所经历的巨变。关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无论是作为“白鹿精魂”的“朱先生”,还是曾经享有白鹿原上绝对话语权的白嘉轩,都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因而《白鹿原》不可避免地带有挽歌基调,其中既有对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的赞美,更有作家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度反思。
(一)对关学的反思与批判
《白鹿原》在实践层面推演了理学思想,关学作为理学的分支,虽不似宋明理学一般高呼“存天理,灭人欲”,但依旧带着宗法等级的枷锁。《乡约》虽然很好地规范了乡民的行为,但这种秩序建立在人对于宗法制度的绝对遵从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之上。理学强调压抑人性,维护伦理秩序。族长白嘉轩在得知田小娥与多位男性有染时,将她抓进祠堂,并对田小娥施以成年族人每人一鞭的鞭刑,他为了家族的声誉,全然不顾事实真相,选择牺牲田小娥来维护礼法制度。
陈忠实坦言,田小娥就是他在翻阅地方志等文献时,看到一位位贞洁烈女的悲情一生时脑海中浮现出的反抗人物形象,她既是一个被白鹿原排斥,又是被白鹿原上的男性们玩弄的物化了的女性形象。她被“媒妁之言”挟持,委身于年近半百的郭举人,正当妙龄的它也渴望有一位年龄相仿的爱人,从此过上男耕女织的平凡生活。田小娥遇到黑娃后,春心萌动,二人私定终身。但红杏出墙的女人始终无法被祠堂接纳,她只能与黑娃住在村外的破窑洞里。白鹿原上的男人们明面上唾弃小娥,背地里又私会小娥。在黑娃离家后,田小娥被鹿子霖和狗蛋欺侮,后来被公公鹿三砸死,死后她还要被镇压在镇妖塔下。爱情自古以来都是作家笔下表现人欲的有力武器,陈忠实俨然意识到在繁似鬃毛的乡约族规家法的桎梏之下,男女情爱始终要让位于礼教,人性始终被束缚,特别是从田小娥的死中,不难感受到理学对人欲的压迫。
(二)对文化的寻根与回归
《白鹿原》作为20 世纪80 年代兴起的寻根文学浪潮下的作品,它以小说的形式,对那些正史中秘而不宣的民族秘史作了展示,对那些条理清晰的哲学史中没有展开的关学与民俗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从这样一部人物原型有据可考的小说中,关学在白鹿原上的传播无疑代表了关学在民间传播的某种趋势与风貌。
关学与千百年来形成的民间礼教正面相遇时所存在的困境也能够从《白鹿原》中窥见一斑。当社会面临新旧思潮交织的时候,当传统的价值观即将被打破而人们由此产生价值危机的时候,朱夫子主张订立的《乡约》在生活的具体方面给了人们新的支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用。但朱夫子与牛兆濂作为程朱理学的拥戴者,他们对新学持强烈的排斥态度,因此他们在思想上落后于时代,而这也是他们的悲剧之所在[5]517。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对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正如他所言:“白鹿原上,最坚实的基础不是别的,而是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存留下来的那一套伦理规范,几千年文化积淀形成的那一种文化心理,几千年相沿流传的那一番乡俗风情。”[8]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丰富,但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也在经受冲击。于是,韩少功等一大批作家开始呼吁进行一次文学的“寻根”,正是这些文化与精神,几千年来支撑着我们的民族在黑暗中缓慢前行,但我们同样看到了传统文化发展中的种种糟粕与境遇。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对“正史能不能代表一个时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史’不能只是精英化,反而是那些无名碑刻,倒有可能利于重建或呈现思想的真实历史窘境。”[9]在此维度上文学或许可以予以回复巴尔扎克将小说定义为“一个民族的秘史”。在主流的哲学史或历史中,人们读到的往往是一些具体的、抽象的关学思想,或是里程碑式的大事件,而在小说《白鹿原》中,一些问题能够被充分地展开讨论。《白鹿原》以恢弘的史诗气度,描写了新旧思想与新旧文化交织下的白鹿原上的人们生活,当关学与民间文化碰撞在一起时,会激发新的问题,衍生化解的手段,同样会有遗留的问题。白鹿原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关中文化的精神土壤,宋明理学的气质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