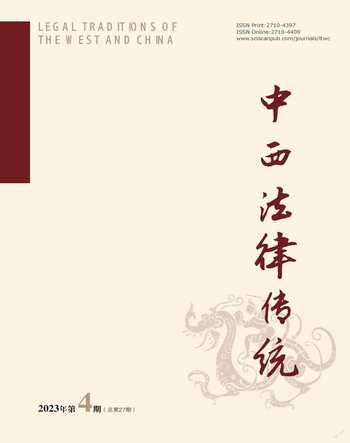“共业分股”与“相共管业”
徐梓俊
摘 要|从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田土契约文书中可以窥见一种特殊的产业形态,即由多个主体共同对某项产业享有权利,已有的研究将其称为“共业”。通过对契文内容的考察,其可进一步分为“共业分股”和“相共管业”两种模式,二者就产业之上各项权能的行使及相应义务的承担等内容各自均形成了一套稳定的规则体系。从形成路径来看,共业的原初形态系家族在分家析产时保留部分产业不进行分析,以“存众”的形式加以维持,后其逐渐溢出家族领域,陌生人之间亦可基于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建构相应的共业关系。最后,在底层逻辑上,共业是明清时期民间社会建构的“业”权秩序的一种特殊形态,系由多个主体共享一份业,共同行使业之上的使用、收益等权能,共同享有“管业”的资格、名分,相当于是围绕业之上的各种权益所结成的一共同体。而共业人依合意而订立的各类契约文书则可被视为系该共同体之“章程”,用以调节此种权益的享有、利用与分配。
关键词|契约文书;业;共业;共业分股;相共管业
一、问题的提出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土地交易市场十分发达,这从卷轶浩繁的契约文书中即可窥见其端倪。这一时期土地交易市场的繁荣与实践中层出不穷的各种产业形态和交易模式是相伴而生的。学界以往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两种情形:一是由单一主体对某一产业享有完全之权利,即所谓的“全业”;第二则是关注土地之上“田皮”与“田骨”权利的分化,即“一田二主”现象。但在明清时期的徽州契约文书中,一种由两个或以上的主体对某一产业共同享有权利的产业形态及相关的经营、交易实践也屡见不鲜,此即本文所要讨论的“共业”现象。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章有义先生最早注意到了此种现象并称之为“合业”,是“由多数业主,同姓的或异姓的,同买一宗田产、共有一纸文契”[1]。刘淼先生将其称为“分数田”,系由承继人占有祖遗产业的数分(或称数股)并可自由出卖[2]。栾成显先生则进一步将此种现象划分为两种形态,即“存众未分”及“共业分股”。前者是“尚未析分清楚而由全体或部分家族成员共同所有”;后者则系未正式析分而采取同族共业的形式,由家族中的各房按诸子均分制的原则享有特定的股分[3]。
稍晚近的一些代表性研究则不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试图从不同的视维探究共业现象之本质。如日本学者中岛乐章在沿袭栾成显先生观点的基础上,着重考察了山场的共业现象。其指出:单一户管业一个字号的山地即为“全业”,若为复数户共同管业则是“共业”。共业又可分为两种形态,其一是各户对山场享有股分,按其股分的多少领受山场之收益并可将股分对外出卖。此外还有一种“存众未分”的情形,即由复数户共同经营、管业,一般系由分家过程中尚未析分的部分财产而形成的[4]。汪庆元在讨论徽州地区宅基地上的共业现象时称此为“土地占有股份制”,即由业户共同占有同一块土地,共同负有权责,且宅地分股买卖的事例所在多有[5]。胡英泽则认为,共业实质上是多个所有权的联合,其表现形式可以是多个个人财产所有权或家族等集体财产所有权之联合,也可以是二者之间的联合[6]。
应当指出,已有的研究基本上均着眼于共业的外在形态或其内部关系结构,将其概括为多个主体共同或按份额占有、经营某一产业,且有简单地套用法学中“共有”“占有”“所有权”等专门术语之嫌,未能准确地揭示出共业现象的底层逻辑。本文欲通过对这一时期的阄书、卖契、共业合同等相关契约文书[7]的考察,就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共业的实际运作规则进行考察,并试图挖掘此种特殊产业形态的底层逻辑。
二、契约文书中所见的共业模式及其实际运行规则
(一)共业分股
先來看一份合同文书:
立议合同人王时良、邵可琅等,今因合买到方泉山佘源维字山地等号壹契……其山地税亩以作伍股均买,合众管业。其山地税亩,各买大小股法花分,各家入户输粮,分税不分产。日后诚恐人心不壹,各愿托中故立合同伍纸。三面立议:之后其山地等号,出拼杉木柴薪,租召开□拨,依五股均分,毋许私自出拼。但有山地字号遗失未清及外侵损杉木柴薪,接获刀斧,理论使费支用,照股均派,不得推委……其有野火,治绝火路,照股出土,不得避躲。(中略)
再批,计开股法:王时良伍股之壹,去价纹银三拾贰两;邵可琅伍股之壹,去价纹银三拾贰两;王时良、王贵祯合伍股之壹,去价纹银三拾贰两;邵可盛、王贵玉合伍股之壹,去价纹银三拾贰两;邵可盛伍股之壹,去价纹银三拾贰两[8]。(后略)
王时良等人共同出资购买一处山场,随后各方共同订立该合同文书以明确各自之权利义务。从文本来看,系按出资比例将该产业划分为五股,由各方根据各自之份额共同对该产业享有权利。具体来看,契文中有“出拼杉木柴薪,依五股均分”之语,反映了共业人可共同对产业实施收益行为并按照自身的份额分享相应的实际利益。但单个共业人不得私自对产业实施收益行为,即所谓的“毋许私自出拼”。而与此对应,相关的义务同样系按照份额进行摊派:其一,山税、地税按股均摊入户,“分税不分产”;其二,若有外人侵损山中林木,告官理论的相关支出“照股均派”;其三,若发生山火,需各共业人“照股出土”。
再来看一则卖契:
六都程云河,今有承祖水田一号,坐落土名方坑源。其田四至、亩步,自有本保经理可照,计租二十秤,与叔程鏊相共,本身该得四分中一分,计租五秤,自情愿出卖与竹岩公四分秩下子孙为业,面议时价文银一两六钱整。(后略)
程云河与其叔程鏊共业一宗土地,程云河对该土地享有四分之一“分”,现其将该份额对外出卖予“竹岩公四分秩下子孙”。可见在共业分股的情况下,共业人享有的权利,除了按份额对产业进行收益外,尚可以出卖自身享有的该份额。
除此之外,共业人享有的此种份额还可为其子孙所承继,如下例:
……计开存众承祖正租并田皮于后:
一、土名杨家坦子钦公租五斤半,身该分数,佃胡元质,佳、佐均业。
一、土名杨家坦田租壹零三斤,该得三股之一,佃元质,佳、佐均业。
一、土名许大坞塘下田租十二斤,该得三股之一,佃胡有缨,佳、佐均业。
黟县胡氏家族“有辉公”一房,在家父有辉公去世后订立阄书,载明三项田皮产业由二子佳、佐均业,即新分出之两房对该部分产业各自享有一半的份额。而从文本来看,上述田皮系有辉公与他人共业,其只享有部分份额。现分书明确载明,上述份额作为有辉公之遗产由其二子承继,可见,在共业分股的情况下,共业人对产业享有的份额不仅可对外出卖,还可作为其专属财产由子孙加以承继。
前述三个例子均指向一种特定的共业形态,即将某项产业划分为确定的份额,由两个或以上的主体按各自的份额共同对该产业享有权利。此种份额在契约文书中一般被称为“股”“分”“该得分”“该分籍(截)”等,因而笔者将此种共业形态称为“共业分股”。其实际运行规则可概括为:第一,共业人可共同对产业实施收益行为并按照自身的份额分享产业之上的可得利益。但单个共业人不得私自对产业实施收益行为。第二,与此相对应,产业之上的相关义务同样系按照各自份额进行摊派。第三,共业人可对外处分其对共业享有的“股分”。易言之,股分是一种可以兑现的财产,设定股分就意味着股分可以单独出卖,这是股分共业关系的一大优势。因而,在股分共业关系中,各共业主体享有的股分,不可避免地要投入到买卖、互易等交易过程当中。第四,此种份额可作为共业人之专属财产,由其子孙加以承继。
(二)相共管业
除上述共业分股的模式外,从契约文书中还可窥见另一种共业形态,如下例:
立议合同人吴、叶二姓,原置七保土名金家坦背后里边山一号,照原置买契界至不□。其山契,系吴姓一人名目,未出叶姓。其价银,吴、叶二人均出均派。今立有合同,二家照先年契据为准,相共管业,蓄养成林。并松杉苗木、柴薪,毋许一人私自入山砍斫,亦不得瞒心私卖、典当、失漏契据。其山在兴养之后,二家商议,桃林开砍。再者,倘有内外人等侵害盗砍,务要同心协力,不得缩脚、推挨、执拗。照派公理示费,身无异言。(后略)
吴、叶二姓合买到一处山场兴养林木,价银由两家“均出均派”。两家在买受产业后订立的共业合同中并未按出资比例划分份额,而是约定“相共管业”。在此情况下,第一,两家对该山场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权利,不存在共业人出卖自身的份额一说,只能长期维持山场现状蓄养林木。第二,各共业人不得私自处分产业本身,即契文中所载“不得瞒心私卖、典当、失漏契据”。第三,林木成材后由两家商议后砍伐、出拼,共同获取收益。第四,若有人盗砍林木,相关的维权费用也应由两家不分份额地共同负担。
综上所述,我们可窥见一种与前文的共业分股模式存在明显差异的共业形态,即不在产业之上划分份额,而是由两个或以上的主体不分份额地共同对产业享有权利。在此情况下,各共业人对产业的权利均系不完整的、需与其他共业人共同分享。其实际的运行规则表现为:第一,各共业人就产业的收益而言并不具备完整的权能,不得私自对共业实施收益,一般须共业人全体共同商议、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进行,由此产生的实际收益也由共业人全体不分份额地共享。第二,各共业人对产业不享有专属之权利或份额,不得私自处分产业本身,亦不存在处分自身权利或份额之说。对产业之处分同样须由共业人全体共同商议、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实现。第三,产业之上的相关义务也由共业人全体不计份额地共同承担。综上所述,笔者欲借用契约文书中的用语将此种共业形态称为“相共管业”。
三、共业形态之来源路径考察
(一)家族场域
众多学者在研究徽州地区的族产问题时均注意到,在宗族势力发达的徽州地区,许多家族在进行分家析产之际往往会保留部分产业不进行实际分析,而是按诸子均分制的原则在阄书中载明各房对该部分产业所享有的份额,此即所谓的存众(或称众存)产业[1]。存众之“众”,系指族众、众人,存众即单独保存以利族众之义。存众财产是相对于各房的家产而言的,原家族的财产经过分家析产后转化为各房的家产,在此之外,保留一些财产不进行分析而由各房共同管业[2]。
此种家族内部存众产业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是出于养老、丧葬和祭祀等特定目的留存部分产业不加以分析,而是采取轮管、召佃等方式进行统一地经营管理,所得的收益则用于抵充养老、祭祀等活动的公共支出,所谓的存众膳产、祀产及禁止分析的坟地、坟山等即属此类[3]。第二是将某些无法或不便直接分析的财产设定为存众,由各房共同管理、使用,如楼屋厅堂、房前余地、围墙过道以及耕牛、水碓等大件劳动工具[2]。第三则是出于某些特殊情况,留存部分产业不加分析而留待日后处理。典型的如某些需要长期蓄养林木的山场,在分家时不进行实际的析分,而是由各房共同经营管理,日后出拼林木的收益则按份额均分。
可见,家族的存众产业与共业现象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钩连关系。而由于分家现象的广泛存在以及诸子均分制原则的普遍效力,此种家族内部各房之间在分家之际形成的共业关系可以说是共业分股模式最重要也是原初的形成路径之一。
来看一份阄书:
……今凭婿余景等,将户下田地山塘肥饶登搭,均分为二,写立孝、弟二字,薄扇一样两本,各阄一本,已分者照依开去土名处所管业;其未分者照依开去土名处所同共对半均业,其一应山场田地及竹园并漏落不及逐一开写,并系对半均业。(中略)
未标田地山二男以洪、以明均共于后:一号土名松树岭下田六坵,与尚伯相共内该一半,租三坪,佃人胡显白[4]。(后略)
汪氏家族在分家过程中保留了部分田地、山场未加分析,而是按诸子均分制的原则由二子以洪、以明“同共对半均业”,即两房对该部分产业各自享有一半的份额。从而,该部分未分析的产业由原家族的全业转化为分家后的两房按份额共同享有权利的共业。
但前已述及,在共业分股的模式下,各共业人对产业之上的份额均有独立的权益,可自由地将其投入到买卖、互易等交易过程中[5]。因此,就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存众产业而言,即使家族在家规族法、阄书或禁约中明确禁止各房对外出卖其分籍以保持产业的完整性,但子孫违反上述规则、私自对外出卖分籍的现象仍然层出不穷。因此,为了维护产业的完整性以及共业关系的稳定性,家族在设定存众产业时往往也会采用相共管业之模式,如下例:
议曰:窦山公承祖未分山场,东西存留以备军装,兹不及论。其摞分并买业山场。充斥本都十保并外都者难以枚举,亲书契文簿尚存可考。但失业颇多,众存无几。除摽分各房各业外,其余各房混业者,嘉靖丁未众立合同文约,其各号内除先葬坟各业外,各房不许侵害,其余山场尽行归众合业兴养。(中略)
栽坌兴养,治山者必要佃与近山能干之人,便于防盗防火。(中略)
凡杉木成材拚卖,治山者告于管理,同家长家众一齐商议,务要至山亲视围径、数目,合众评品应值时价……所得木价若干,尽付管理收贮,以应众用。各房不许分析,治山者不许收价。
祁门县程氏家族原先设定存众产业以备军役,但“失业颇多,众存无几”,于是各房合议将各处山场“尽行归众合业兴养”,即不在产业上划分份额而是采用相共管业的模式,由家族专设的“治山者”统一对山场进行召佃经营,各房不能染指产业的经营管理,更不能私自处分产业,甚至连所得的收益也要“尽付管理收贮,以应众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共业人私自砍伐林木出拼或私自处分山场的情况发生,有利于长期维持山场的现状以蓄养林木。
(二)陌生人场域
如上所述,家族内部的存众产业是共业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徽州地区发达的土地交易市场和繁荣的田土经营实践,加之共业分股模式下份额可自由流转之属性,使得此种特殊的产业形态逐渐溢出了家族领域之外,如下例:
六都张汝清,同侄张昺、张皓共地一备,坐落本都三保,土名鲍家坞口,外至路,东至桂家地,西边至山,约地二亩零。与侄张?、张文昇相共,汝清、昺、皓三分内合得一分,约计九分零,尽数立契出卖与同都程泰名下,面议时价文银一两六钱正。(后略)
张汝清、张昺、张皓叔侄三人与张?、张文昇共业一宗土地,张汝清三人共同对该土地享有三分之一“分”,其后三人共同将该份额对外出卖给程泰。从而该土地由张汝清叔侄等人的家族共业转变为张?、张文昇与程泰之共业,份额的流转使得共业关系溢出到家族以外的场域。
实际上,非家族成员的陌生人之间,出于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需要而在经营、交易实践中形成共业关系,此种实例在契约文书中所见多有。典型的如多个主体合资共买某一产业,随后划分份额、共同经营,所得的收益按股分配、相关的费用则按份均摊,形成标准的“共业分股”之关系。如前引“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王时良、邵可琅等山地共业合同”,王时良等人合买一处山场,按出资份额将产业划分为五股并约定日后“出拼杉木柴薪……依五股均分”,在分散初始投入的资金压力的同时保障各出资人将来的收益权。除此之外,其又约定“各家入户输粮,分税不分产”“使费支用,照股均派”,在一定程度上又分摊了经营的成本与风险。可见在此种情况下,合资置产经营并分散成本与风险是非家族成员的各主体建构共业关系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就某些特殊的产业,如相邻两家共用的围墙和过道、大件的劳动工具和水利工程等,此类产业重在使用价值,当事人关注的是产业本身效用的持续发挥及其对该产业的长期有效使用,不受外人之侵扰且不会被其他共业人私自对外出卖,即使因共同出资购买、修建而形成共业关系,也没有必要或不适宜将产业特地划分为明确的股分。因此,在此种情况下,与家族内部的共业关系一样,非家族成员的各共业人之间也会约定采取相共管业的模式,如下例:
立议合同字人姜显得、姜樟发……显得置得和蕊兄弟等北至砖墙壹面,其樟发亦置得泰万兄南至砖墙壹面,其墙两家合业。日后倘墙有破坏,两家修整。如有各家所做猪栏,两家必装板壁,以保墙固,毋得生端异说。[1](后略)
姜显得、姜樟发共同买得同一面砖墙的北面与南面,随后订立共业合同约定该墙为“两家合业”。显然,双方看重的是围墙的使用价值,只要其保持完整、持续发挥效用即可,无须在其上划分股分并明确两家各自的份额。因此采取相共管业的模式,整段墙壁由“两家合业”,双方共同管理、修缮。
四、共业现象的底层逻辑探析
(一)概念之厘清:“业”与“管业”
根据前文之讨论,我们可将共业初步归结为系多个主体出于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按照不同的模式对某一产业共同享有权利的一种产业形态,这在外观上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现代民法上的共有制度,部分学者在探讨共业现象时也使用了“所有权”“共有”等现代法上的概念。但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大陆法系民法上的共有制度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是指两个或以上的主体基于不同方式共享一所有权的形态[2]。而毫无疑问,自西方近代“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中生发出来的所有权概念,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并无相应的等价物。取而代之的,是民众通过契约文书所建构的“业”的概念以及相应的“管业”秩序。上述字眼在明清时期的田土契约文书中频繁出现,具体到共业领域,多个主体合买产业并划分股分后,会约定“照依合同分法管业”[3];共业人出卖自身对产业享有的股分会在契文中载明“自愿出卖与某某为业”[4];多个主体不分份额地共享同一产业之权利在契文中被称为“相共管业”[5]。综上所述,有必要先行厘清“业”与“管业”此组概念之内涵。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日本学者寺田浩明较早地注意到此组概念在明清时期的田土契约中的频繁出现,其认为“业”与“管业”的着眼点并非是物理性、客觀性的土地,而是业主在土地上进行经营收益的地位。其指出:“根据契据而被交易的对象,与其说是完整的无负担的‘物,还不如说是在不言而喻地负有税粮义务的土地上自由进行经营收益(当时称为‘管业)的一种地位。”[6]李力教授在基本肯定前述观点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补充和修正,认为“收益权是股、地权、田骨、田皮等一系列契约标的的共性所在,被清人表达为‘业的正是作为这种共性的收益权”。其认为:“在清代民间契约所表达的社会观念中,‘业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就是获得收益的权利,而‘管业则是指对这一权利的行使,即实际获得收益的行为。”[7]陈柏峰教授也指出,“业”这一概念“强调气力与心智的投入,意味着经营与经营对象,意味着一种与生存权相关联的生计、营生”,相较于现代民法上的物权概念而言“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既可以用来指代地权,也可以用来指代土地上的其他权利,还可以指代股权等与土地并不直接关联的权利”[8]。而邹亚莎教授通过考察楼屋、水塘和菜园等产业的相关契约文书,进一步指出“业”与“管业”之概念并非仅限于收益权能,而是具有很强的弹性、复杂性和包容性,既有使用权,又包含收益权或处分的权利,因此将其内涵扩展为“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或利益的集合”更为恰当[1]。
综上所述,第一,各学者虽然对于“业”与“管业”的概念中所包含的具体权能存在分歧,但基本上均认为其并非着眼于客观的、物质性的产业本身而是指向产业背后的使用、收益等抽象性的权益。第二,在此意义上说,所谓“土地的买卖”,就是“前管业者”把管业(按照寺田的说法,是在土地上自由进行经营、收益)的地位出让给“现管业者”并且今后永远允许后者对土地进行管业;所谓“土地的所有”,就是向社会公示现管业者与前管业者订立的契据,即现管业者取得管业资格的正当“来历”,以获得社会成员对现管业者享有该土地之上管业资格的尊重与认可的状态。[2]可以说,“业”与“管业”的概念中包含了一种名分、资格的意味,只有拥有“业”的主体才能进行“管业”,方可据此享有实施经营、收益等行为并获取产业之上各种可得利益的正当性地位。诚如学者所言,“‘管业是一种名分,使人与业之间的关系具备正当性,获得管业名分的人就被称为‘业主”。[3]上述思路或对我们考察共业现象的底层逻辑有所裨益。
(二)共业分股模式之底层逻辑
如前所述,我们将共业分股模式初步定位为:在某项产业之上进行份额的划分,由多个主体按各自的份额共同对该产业享有权利。第一,其具体的运作模式,是将产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经营管理(具体的经营管理方式可多种多样),共业人系按照其所享有的份额分享产业之上的收益并分担相关的义务,而非按各自的份额将产业实际划分为各个具体部分后,再由共业人对各个部分各自进行经营管理、获取收益并承担义务,即前引契约文书中所载的“出拼杉木柴薪……依五股均分”“其山地税亩,各买大小股法花分……分税不分产”[4]。可以看到,在共业分股模式下,各共业人享有的份额并非是对产业本身进行实际析分后的产物,而只是一种抽象的分割,其实际上内含了一种名分的意味:只有通过出资合买或分家析产等方式取得产业上的份额之后,方具备共业人的身份与地位,才享有与其他共业人一起、共同对产业实施收益行为并按照自身份额分享产业之上的可得利益的正当资格,同时也要相应地承担相关的义务。相关的契约文书中在划定各共业人享有的份额的同时也会明确此种份额所指向的“管业名分”,如“今将前项三号山地,立定合同……日后两下并照依合同分法管业”[5]“其未分者照依开去土名处所同共对半均业,其一应山场田地及竹园并漏落不及逐一开写,并系对半均业”[6]。
第二,共业人对产业享有的份额可以被出卖或承继,其作为标的物在契约文书中直接被称为“业”:
十六都倪廷贤同侄世济、润共买授得十五都郑永、郑晟、良初、郑本等荒熟田、山一合源……其田三分中买得二分,其山九分中买得八分。今因管业不便,自情愿将四至内荒熟田、山并在山大小木苗力全买得分籍,尽数立契出卖(与)本都郑天芹名下为业[7]。(后略)
倪廷贤同其侄倪世济、倪世润合买郑永等五人共业的田地、山场之一部分,三人享有田地三分之二、山场九分之八的份额,其余份额仍由郑永等五人享有,双方形成共业关系,后三人将其份额出卖给“郑天芹名下为业”。如上所述,份额赋予了共业人共同对产业实施收益行为并按照自身的份额分享产业之上的可得利益的名分、资格,其指向的是产业之上的收益权能及相应的可得利益而非客观性、物理性的产业本身,这与前述“业”的概念是相吻合的。因此,当事人在契约文书中此种份额称为“业”并将其作为交易标的物进行处分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从本质上说,土地、山场等产业之上原本就有一份完整的“业”,但民众出于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需要,会在此基础上建构共业分股关系,即对产业进行抽象的份额划分后,由多个主体共同行使业之上的使用、收益等权能,共同享有“管业”的资格与名分,而非是对产业本身进行按份的实际析分。因此,共业分股模式的实质是多个主体按份额对产业之上的“业”而非物质性的产业本身进行分享。单个共业人分享到的只是一种不完整的“业”,是产业之上的“全业”的一部分,但其中仍保留了“业”所包含的各种权益以及相应的管业资格与名分,只是因其不完整性,需要在集合各共业人的“权利片段”后方具备实施相应管业权能的正当性。此外,在共业分股模式下,由于进行了抽象的份额划分,各主体分享到的此种不完整的“业”可以按照明确的比例关系进行量化,有清晰的范围,从而可以被视为各共业人的专属财产,单独作为买卖和承继的标的物。
综上所述,我们可归纳出共业分股模式的底层逻辑:即在产业之上进行抽象的份额划分,由多个主体按份额共享产业之上的“业”。单个共业人分享到的只是一种不完整的业,但其中包含了共同对产业实施收益、处分权能并按份额分享产业之上的可得利益的名分、资格。并且,其可作为共业人的专属财产被买卖及承继。
(三)相共管业模式之底层逻辑
多个主体不分份额地共同对同一产业享有权利,这在契约文书中被称为“相共管业”。根据前文对其实际运行规则的考察:首先,单个共业人就产业的收益及处分均不具备完整的权能,不得私自实施收益和处分行为,即前引契约文书中所载的“并松杉苗木、柴薪,毋许一人私自入山砍斫,亦不得瞒心私卖、典当、失漏契据”;其次,对产业的收益和处分行为,一般须共业人全体共同商议、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实施,由此产生的实际收益也由共业人全体不分份额地共享,即前引的“凡杉木成材拚卖……同家长家众一齐商议,务要至山亲视围径、数目,合众评品应值时价”以及契约文书中常见的“倘有公众要事看用,公同开匣公看”之语。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方面的结论,在“相共管业”模式下:第一,只有具备共业人的身份、地位,才能参与到“同家长家众一齐商议”“合众评品应值时价”“公同开匣公看”等過程当中,方可在共业人全体就相关事项达成合意时,作为其中之一员,共同对共业实施收益或处分行为并享有产业之上的各种可得利益。各主体虽不像共业分股模式中各自对产业均享有明确的份额,但其作为共业人的身份与地位本身就包含有一种对产业实施收益、处分行为并获取其中的可得利益的潜在权能,意味着一种正当的管业名分与资格。第二,此种名分或资格,指向的是产业之上的收益、处分权能及各种可得利益,系抽象地“悬浮于”产业的整体之上而并不关涉客观性、物理性的产业本身,与前述共业分股模式中的“份额”一样,亦可将此归结为一种“业”,在相关契约文书中也以“业”称呼之:“今立有合同,二家照先年契据为准,相共管业”“其墙两家合业”。第三,相共管业作为一种共业形态,其底层基础亦系田地、山场等产业上的一份“全业”,而由多个主体共同行使业之上的使用、收益等权能,共同享有“管业”的资格、名分。因此,与前述共业分股模式的情况相同,相共管业模式下各共业人所享有的,实际上也是一种不完整的“业”,是对田地、山场等产业上的“全业”进行分享后的产物。所不同的是,此种模式下共业人并不在产业上进行份额划分,因而各主体享有的此种不完整的业,彼此间是混同的,无法被量化、不能界分出清晰的范围,其只能赋予各共业人相应的管业名分、资格而不能被识别为共业人的独立财产从而单独作为交易之标的物。
综上所述,“相共管业”模式的底层逻辑可归纳为:多个主体不分份额地共享对同一产业之上的“业”,各共业人享有的是一种不完整的业,但其中内含了与其他共业人一起,对产业实施收益和处分权能并不分份额地共享相应的实际利益的名分、资格。
五、总结
与近代西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式的观念不同,传统中国对待土地等产业资源,注重的是人与物之间所具有的一种“同生共存”的依赖关系,其本质是“养育”而非“支配”,背后是一種朴素的生存伦理,人与产业之间并非单向度地排他性控制,而是共生性的相互依赖[1]。因此,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并不追求对产业的一种排他性、对世性的“所有权”,更未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种权利类型并在彼此间进行界限明确的划分,而是关注对产业之利用所衍生出的种种实际利益以及在此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衡并由此发展出“业”与“管业”之概念,其重点在于产业之上实际经济效益的利用、分配而不在物权逻辑的自洽。
在此种理念下,“业”本身自然也可以跳脱出单个主体的“管辖”范围,时人可以根据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各种现实需要,将“业”及其所蕴含的实际经济效益分配给多个主体共同享有、利用,由此即形成了共业关系。如家族在分家析产时,对某些特殊的产业如赡田、坟山等,为了保持其完整性、防止各房私自对外出卖,将其设定为存众产业,实质上是将产业背后的“业”及其所蕴含的产业的使用利益分配给各房共同享有,从而在原家族分崩离析后使家族的全体成员仍能长期保有对产业之使用权益、不受外人侵扰。再如水碓等大件生产工具,多个主体在共同出资合买或修建的基础上形成共业关系,其重心实际上亦在于背后的使用权益的合理分配。在此意义上说,共业关系实际上可被视为多个主体围绕“业”中所蕴含的实际经济效益所结成的共同体,共同体内部的各成员有着共同的目的,在前例中是家族的养老、祭祀开支的供给,在后者则是保持其持续有效运作以满足生产使用需求,均需要通过对业之上实际经济效益的共享和合理配置来达成。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不同于单个主体对“业”进行完全掌控的“全业”形态,在“业”被切分为若干不完整的片段的共业关系中,其背后的实际经济效益如何在各共业主体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从前文之考察来看,即便通过分家析产或出资合买、修建等在事实上形成共业关系后,共业人之间尚需通过共业合同、阄书等对份额的划分、产业的具体经营管理方式、实际收益的分配及相关的禁止性事项等进行书面确认。易言之,上述问题的解决系通过共业人全体之合意、外化为各类契约文书来实现的。契约文书虽非共业关系的成立依据,但确系协调同一“业”内各共业人彼此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对“业”背后所蕴含的实际经济效益进行分配的书面凭据。结合前述“共同体”之视维,共业关系可被视作围绕“业”中所蕴含的实际经济效益所结成的共同体。而体现共业人全体之合意的契约文书则相当于系约束共同体内部各成员的“章程”,对此种实际经济效益在多个主体间的共享、利用与分配进行规定,从而在国家未提供充分的制度性资源进行保障的情况下自行构筑了一套原生的规则秩序,以规范此种特殊产业形态的实际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