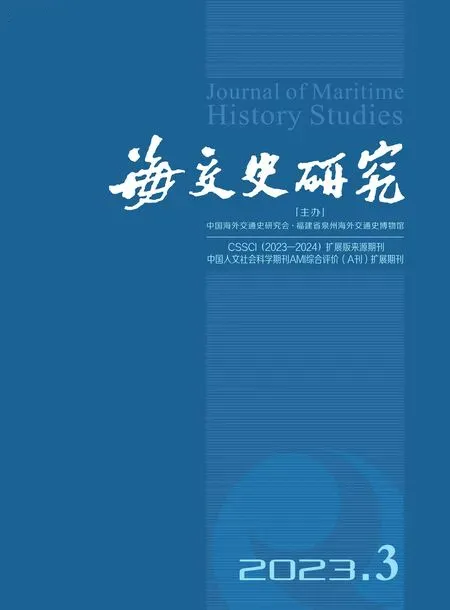明代南京静海寺风物暨创建年代辨析
--以三宝太监郑和的事迹为中心
邵磊 郦英南
引言
2006年8月,有媒体爆料,在南京市“静海寺--《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西边一墙之隔的朝月楼地块,南京图腾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正在兴建名为“大观天地Mall”的工程项目。据当地原住民口口相传,并参考之前的相关研究,可知南京下关西邻热河路、南毗建宁路、东望狮子山的朝月楼地块,即是明代静海寺旧址所在地,而参酌明代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存录的凌大德绘、傅汝贤刊《静海寺全景》木刻版画,尤其是以静海寺左侧矗立的“真假山”与“三宿岩”巨石等完好保存至今的天然景观为参照(1)真假山与“三宿岩”巨石,南宋时犹为江岸,以虞允文破金人于采石后至此系舟并歇宿而得名。详见明代陈文烛撰《三宿岩记略》一文,载[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18,《卢龙山静海寺》,《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年,第363-364页。,可以断定,南京图腾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建的“大观天地Mall”建筑工地,正位于明代静海寺旧址之上。南京市博物馆闻讯后随即会同下关区文化文物主管部门前往现场踏查,并与施工方进行接触。
可惜限于当年的社会环境与客观条件,文物考古部门只能在施工方未完全停工的情况下,便投入到了抢救性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之中,以至考古发掘所触及的部分明代建筑遗存,最终也未能保存下来,这些当然都令人扼腕叹息不已。本文即是笔者在考古调查与发掘的过程中,关于明代静海寺建置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一、水月镜花--明清文人笔下的静海寺风物
明代初年,在南京北城仪凤门外龙江“聚沙浮渚一瓯”的荒凉江滩之上,先后建成规模宏大且彼此毗邻的道观与佛寺各一所,这便是赫赫有名的龙江天妃宫与静海寺。其中,关于龙江天妃宫的营造始末,史载甚为确凿,咸谓为三宝太监郑和等第一次下西洋出使古里、满剌加诸番国平安归来,因“言神多感应”,遂于永乐五年(1407)九月初六日敕建完工(2)《明太宗实录》卷71,永乐五年九月戊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994页。。值永乐十七年(1419)九月十二日,复又“重建(龙江)天妃宫于南京仪凤门外”(3)《明太宗实录》卷216,永乐十七年秋九月甲寅,第2156页。,而从时间上推算,重建之期正值郑和等众第五次下西洋归来未久,庶几可见,永乐十七年对龙江天妃宫的重建,依旧不脱与郑和下西洋之间的联系。
关于龙江天妃宫的肇建年代,还有《金陵玄观志》与《康熙江宁府志》两书所持的永乐十四年(1416)之说,但这显然是将永乐十四年(1416)四月初六日明成祖朱棣《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立石的时间,误作为龙江天妃宫的创建年代。龙江天妃宫初创于永乐初固无可疑(4)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在南京南郊天堡桥发掘出土的明天顺年间守备南京的司礼监太监怀忠墓志有云:“(南)都城之外,旧有神祠,曰‘天妃宫’。永乐初年,奉勅创建,典守不谨,厄于回禄。公念其神显灵洋海,护国庇民,具疏请于朝,捐平昔恩赐之赀,市材鸠工,鼎新盖造。复募两京内外重臣官员士庶,舍财以成其事,可谓乐善好施者矣!”其中,“永乐初年奉勅创建”表述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龙江天妃宫创建于永乐五年的史事。详见南京市博物馆(周裕兴执笔):《江苏南京发现明代太监怀忠墓》,载《考古》1993年第7期。。《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极力铺陈了郑和下西洋船队经海路出使往返之际,得到天妃显灵护佑化险为夷并奏请朝廷敕造龙江天妃宫以表彰天妃之情状。由此可见,明初永乐年间南京龙江天妃宫的肇建与重建,皆与郑和舟师出使西洋的经行往返存有极密切的因果关系。
有意思的是,在南京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书里,与龙江天妃宫相距仅仅一箭之地的静海寺,更是一处几乎周身每一个毛孔皆透射出与郑和下西洋相关气息的所在。至于这些让人耳熟能详以至浮想联翩的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建于明永乐年间的静海寺,规模宏阔,气势不同凡响,直至明末犹位居南都“次大刹”之列,与此相偕应的是,静海寺的建筑用材亦精良无比,据清代甘熙《白下琐言》记载,静海寺殿堂内的“础石大若车轮,润如苍玉。柱皆数围,或云沉香木为之,其实钟山楠木耳”(5)[清]甘熙撰:《白下琐言》卷7,《南京稀见文献丛刊》,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120-121页。。
其二,据明代顾起元所撰《客座赘语》记载,三宝太监郑和永乐年间从西洋携带西府海棠而归,遂“建(静海)寺植于此”,而这些由郑和永乐年间下西洋带回并植于静海寺的西府海棠,至明末“犹繁茂”(6)[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花木》,《元明史料笔记丛刊》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6页。,入清后仍花开如锦,树荫可遮蔽方圆数亩地(7)参见[清]陈作霖撰:《金陵物产风土志本境植物品考》,光绪戊申(1908年)可园刊印本。,堪称旧时南京的一处奇观。
其三,除了西府海棠,《客座赘语》还记载,静海寺内还藏有郑和携归、出自西域画师手笔的水陆罗汉像,值每年夏天张挂之际,南都士女都纷纷前往观览(8)详见[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9,《诸寺奇物》,第298页。,可谓极一时之盛。与之相似的是,《续文献通考》也记载道:“金陵静海寺藏有佛宝,来自西方,每岁时出献佛堂上祝,云亦郑和所取”(9)[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236,《四裔考西南夷》之“锡兰山”条,《续修四库全书》第76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84页。。这里所谓静海寺所藏郑和自“西方”所取得的“佛宝”,虽然并未具体说明是何物件,然以其“每岁时出献佛堂上祝”,也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顾起元所记郑和自西域携归的水陆罗汉画像来。
其四,清道光时举人潘德舆《养一斋集》存录《静海寺》长诗,诗云:
“龙江烟水秋茫茫,静海寺外千帆樯。眼前江水等一勺,寺僧为我谈西洋。荷兰真腊久入贡,雄心未餍明文皇。刑余之臣佐远驭,戈船直指西南荒。从行白骨掷海岸,九死归来头亦霜。大共小球侈王会,明珠犀象盈归装。奇珍钜万不暇数,龙骧万斛堆沈香。请看入门第一殿,以香为柱香为梁。游人传诵五百载,手摩鼻嗅怜芬芳。稽首奉上信香国,此公所到真天堂。我闻僧语色不许,喜功好大无纯王。穆满瑶池不足信,春秋外传讥白狼。史公微文大宛传,张骞广利谋非臧。何况魁柄假阉寺,远人不来专出疆。千寻梁栋足瞻仰,万人汗血谁怜伤。更看铜鼎万钧重,雷纹古篆追周商。洪熙元祀郑和造,益知货宝归貂珰。委鬼逆焰屋明社,永乐作俑堕乾纲。兵部册籍可一炬,良臣卓识邦家光。语僧勿祀马三保,读史吾钦刘职方”(10)转引自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55页。。
上述潘德舆《静海寺》诗可谓基于经世致用立场的咏史诗,通篇充斥着对明初郑和下西洋得失的反思,惟诗中假静海寺僧之口道出寺内所存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两种遗存,即静海寺天王殿的梁、柱与所供置“雷纹古篆追商周”的“万钧重”的铜鼎,甚是引人瞩目。关于静海寺天王殿内的梁、柱等木构件,传为郑和下西洋携归的沉香木斫制,游人至此,莫不“手摩鼻嗅”以感触芬芳(11)据明代《金陵梵刹志》静海寺木刻全景图所示,静海寺山门内的建筑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弥勒殿、方丈、毗卢殿及其上的潮音阁,故可断定潘德舆的《静海寺》诗的“入门第一殿”即天王殿。。但潘德舆却对此殊不以为然,在他眼中,明初劳民伤财的七下西洋,无非是为了满足明成祖朱棣平服诸番的好大喜功乃至对海外奇珍异宝的占有欲,于生民无益,静海寺天王殿以西洋沉香木构架的“千寻梁栋足瞻仰”,但背后却是“万人汗血谁怜伤”,代价未免太过沉重。
至于寺内“雷纹古篆追商周”的“万钧重”的铜鼎,传云亦是洪熙元年(1425)由屡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施奉寺宇。潘德舆对此更是嗤之以鼻,并以“益知货宝归貂珰”的诗句,直指郑和等也在屡下西洋的过程中获利自肥的可能。因此之故,潘德舆盛赞成化朝兵部职方郎中刘大夏将“兵部册籍可一炬”的极端做法,认为是“良臣卓识邦家光”,并“语僧勿祀马三保”,可能也有规劝静海寺僧大可不必动辄将郑和下西洋的事迹及其与静海寺的渊源挂在嘴上喋喋不休的意思。
其五,清代咸同间的上元人张汝南《江南好》词云:“江南好,静海傍江洵,殿础九楹雕碧玉,佛龛百炼抹黄金,三宝证皈心。”并有注曰:“静海寺在仪凤门外,明内监马三宝使西洋回建护法,塑三宝像,殿柱以碧玉石为础,最有名。”郑鹤声、郑一钧编纂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根据《江南好》词注文中的“塑三宝像”,认为南京静海寺中曾经安奉郑和的塑像,并且这一尊塑像直至清代晚期仍存(12)转引自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第51页。。
上述种种关于郑和下西洋与南京静海寺的因缘的具体材料,不可谓不丰富。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叙述无一不是发生于明末以后,并且大多是入清以后的记载,几乎与可信度大打折扣的民间口碑史料无异,充其量只能是聊备一说而已,然而历经当代文化学者不求甚解、添油加醋的重复与演绎,几已成为人所共知的确切不疑之论。
譬如,清代甘熙《白下琐言》所记“大若车轮、润如苍玉”的青石质鼓镜式柱础,在围绕朝月楼地块进行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过程中时有所见,但其规制并没有与南京南郊华严寺等位列“中刹”的寺院础石有什么不同,倒是关于天王殿内柱础石之上的“柱皆数围,或云沉香木为之,其实钟山楠木耳”(13)据潘德舆《静海寺》诗云:“请看入门第一殿,以香为柱香为梁”,可推知《白下琐言》所言应是特指静海寺“入门第一殿”,亦即天王殿。,历来却乏人深究,因为不仅考古发现静海寺柱础石鼓镜的周长(亦即其上所承木柱的周长)不可能达到数人合围的体量,且其所述亦不免令人生疑,莫非南京钟山也会有楠木生长?
再如,潘德舆《静海寺》诗中所谓“洪熙元祀郑和造”的“万钧重”铜鼎,尽管《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指出:郑和既然曾铸造铜钟供奉于福建长乐三清殿,那么铸造铜鼎供奉于静海寺也就不是孤立的现象,故而值得信从,并且进一步推断这铜鼎应是郑和率领下西洋官兵守备南京时,“为了纪念以前六下西洋所铸造的,鼎上也必铸有铭文。……若日后能发现这一铜鼎,那对研究郑和下西洋,将提供一件珍贵的实物资料。”(14)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第55-56页。不过推究文辞,笔者却认为这件“雷纹古篆追周商”的铜鼎仍有于理未安之处。
明初所铸金属礼器或供器,如铜鼎或三足炉之类,在南京南郊明代早期的华严寺僧人墓与朝天宫道士刘渊然墓内多有发现,其中,刘渊然之死还曾得到了具有官方背景的悼亡之礼。(15)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西善桥明代长春真人刘渊然墓》,载《文物》2012年第3期。然而这些方外人士的墓葬里所随葬的金属鼎、炉之类供器,皆墓主生前使用的器具,其器表皆光素无纹,无一例外,可见是明初时代风气使然,并非偶然的现象。这样看来,同为明代早期,郑和即便真的有发心铸造铜鼎施奉于静海寺之举,所施奉的铜鼎亦必不脱此窠臼。更何况潘德舆所记述的铜鼎兼饰“雷纹”与“古篆”的商周风骨,形制既宏大厚重,且有指向性明确的铭文,如此珍贵且夙有掌故可考的物件,居然不见载于明人笔记,反而呈现于晚清时人的诗作,则不免令人疑为清代金石学大兴之后出于好事者牵强附会的“赝鼎”了。
至于《江南好》词也是如此。张汝南生活的年代,静海寺的建筑规制仍保持旧有的格局,但张汝南眼中的“殿础九楹”,亦即九开间的建筑,显然是只有皇宫、帝陵或与之相埓的礼制建筑才可以拥有的规制。对于在明代南京寺院中属于“次大刹”的静海寺而言,则是难以想象的。庶几可见,《江南好》词关于静海寺殿宇开间的记述也不能令人信服。以此而言,词句中提及的静海寺内“塑(马)三宝像”云云,或也有道听途说的可能。有意思的是,或许正是为了“契合”《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一书对《江南好》词注的解读,近年在海外果然“新发现”了一尊传为南京静海寺早年流出的郑和铜像,该铜像是一尊头戴官帽、身着补服的拱手立像,仅存上半身。铜像本身并非新仿,但附会为郑和的塑像,却并无确凿的材料予以证明。
明都南京与郑和有因缘的寺庙不可谓少,除了静海寺之外,至少还有归诸“大刹”的大报恩寺与“中刹”的碧峰寺等。其中,大报恩寺为郑和奉敕监造,碧峰寺则是郑和所中意的终老之所,郑和甚至在生前就已安排其宦官同侪将自家的佛教法器、法物捐赠碧峰寺内供奉(16)邵磊:《郑和与碧峰寺非幻庵--以<非幻庵香火圣像记>与<非幻禅师塔铭>为中心》,载《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5-108页。。此外,还有明初同样为纪念明代太监出洋通蕃而建成位于南京南郊的“小刹”宁海寺等。但问题是,前述三寺都没有像静海寺这样,在时移代易之后却反而衍生出许多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传说见闻,这自然是很令人感到兴味的。而究其原委,或许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大报恩寺与碧峰寺、宁海寺等梵刹入清以后皆法门不振,香火衰微,有的甚至近于废圮。相较而言,由于江岸环境的变化乃至顺江而下的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等因素,由明入清的静海寺仍然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至清乾隆年间,住持浩清更将静海寺重新修整,并于寺内创石戒台,使得静海寺这一前明旧刹竟一度被誉为金陵佛教律门之冠冕(17)[清]甘熙撰:《白下琐言》卷7,第120、121页。,慕名前来剃度皈依者日众,直至“道光壬辰二月二十二日卯时,不戒于火,悉成灰烬,仅留山门、天王殿而已。当是时,赴救水龙铜管多裂,水不能出。殿旁大银杏一株,烈焰腾腾,自树腹吐出,以助其猛,盖数为之也”(18)[清]甘熙撰:《白下琐言》卷7,第121页。。但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静海寺犹被选中作为中英“江宁条约”的议约地而言,可以想见在经历了道光十二年(1832)的回禄之厄后,静海寺很快便得以兴复,并且仍然是下关沿江一带最为气派的建筑群。由此可见,对于入清以后的静海寺住僧而言,附会前朝三宝太监郑和及其下西洋的史迹,不能说没有增添静海寺身价乃至香火的因素在内。
二、永乐乎?洪熙乎?--静海寺的创建年代问题
明代南京静海寺的创建年代缺乏第一手史料的确凿记载,在这一方面远不如毗邻的龙江天妃宫之渊源有自,前文对此已有述及。因此,欲探究静海寺创建的年代,仍然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从相对晚出的材料来寻绎迹得近真相的认识。
关于静海寺建置的文献史料,以前引明代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葛寅亮撰《金陵梵刹志》卷18《卢龙山静海寺》收录最为集中,后世学者对静海寺创建年代与相关问题的探究检讨,也多是围绕于此来进行的。不过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金陵梵刹志》虽有来自南京礼部的官方背景,但毕竟成书并“发南京僧录司刊”之际,已届明末的万历三十五年(1607),而其时由于南京佛寺制度涣散,萧条不振,加之寺产流失严重,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多付之阙如,甚至连南都“三大刹”天界寺、灵谷寺与大报恩寺的“因革鼎新”,也都难于周悉。故而葛寅亮在遍检礼部档案之余,也不得不“礼失而求诸野”般登门,向先世自洪都大树里徙居南京,一向“避世隐居、谭禅缮性、修出世法”的居士刘瑜(别号次山)谘诹,以求得其“劻勷”(19)详见明代万历二十三年(1595)大泌山人李维桢所撰《明隐君次山刘公墓铭》,志石现藏南京市博物馆,拓本见录《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南京》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74页。关于京山名士李维桢,史载“其文章弘肆有才气,海内请求者无虚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碑版之文,照耀四裔。门下士招富人大贾,受取金钱,代为请乞,亦应之无倦,负重名垂四十年,然文多率意应酬,品格不能高也”。详见《明史》卷288,《文苑四李维桢传》,第4938页。李维桢为此诸商贾富民撰写的碑志,无非是收受润金的应酬文字,在编订传世的《大泌山房集》之际不予收录亦情理中事,此《明隐君次山刘公墓铭》即其一例,从这一个侧面不难想见以“隐君”自况的传主刘瑜更为丰富的社会属性。。
据此当不难想象,《金陵梵刹志》所存规制远不及“三大刹”的南京其余诸寺,又何尝不是如此。具体就静海寺的建制史料而言,《金陵梵刹志》存录文献除了南京礼部侍郎杨廉《敕建静海寺重修记略》一文撰于稍早的正德十四年(1519),其余如方克《玩咸亭记略》、陈文烛《三宿岩记略》、俞彦《静海寺重修疏序》、吕柟《游卢龙山记略》等,则无一不是明代晚期以至明末的文字(20)上述诸文,收录于《金陵梵刹志》卷18,《卢龙山静海寺》,第33-36页。,其中不乏舛错到几乎离谱的认识,如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累官至南京大理寺卿的陈文烛,于万历十九年(1591)所撰《三宿岩记略》一文所云:“而高皇帝起淮甸,命使大征西洋,奏凯而归,建静海寺。”陈文烛在上述碑文中,居然将郑和、王景弘诸辈下西洋之举归诸明太祖洪武年间,将静海寺的肇建同样也系于洪武年间,仅以此言便不难想见,明代晚期以后,即便是饱读诗书的硕儒,对于国初郑和下西洋的史事也难免不求甚解,以至隔膜殊深。
除了陈文烛这样的特例之外,总体来看,《金陵梵刹志》汇录的相关文献中有关南京静海寺创建年代大致不外两种,即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建成说与明仁宗朱高炽登基之后建成说,而最为人耳熟能详的便是前者。
关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肇建静海寺之说,以明末吴郡进士俞彦所撰《静海寺重修疏序》一文所述最详:“文皇帝践祚,海夷西洋,尚逆颜行。爰命专征,艨艟千计,战士帅属,以万万计。乃折鲸鲵,飓涛弱浪之外,楼帆无恙,获所贡琛异以归。岁奉朝朔,皇灵震荡,说者奇其绩,谓为神天护呵,合建寺酬报。诏可,赐今额,遂为名刹焉”(21)[明]葛寅亮撰:《金陵梵刹志》卷18,第364、365页。。据《疏序》一文,静海寺乃是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在国家内政外交的鼎盛时期为纪念郑和下西洋的业绩而敕建。《金陵梵刹志·卢龙山静海寺》起首的总说亦云:“卢龙山静海寺……文皇命使海外,平服诸番,风波无警,因建寺,赐额静海。”
前引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花木》谓:“静海寺海棠,云永乐中太监郑和等自西洋携至,建寺植于此。”此外,《客座赘语》卷1《宝船厂》也明确记载:“今城之西北有宝船厂。永乐三年三月,命太监郑和等行赏赐古里、满剌诸国,通计官校、旗军、勇士、士民、买办、书手共二万七千八百七十馀员名。……和等归建二寺,一曰静海,一曰宁海”(22)[明]顾起元撰:《客座赘语》卷1,《宝船厂》,第31页。。凡此,皆认为静海寺是明成祖永乐年间建成。入清以后,此说复为《江南通志》等官修志书所采纳(23)如《江南通志》卷43,《寺观一》:“静海寺……明永乐间内监郑和使西洋归国,建寺赐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至如《白下琐言》所谓“仪凤门外静海寺明永乐间建”云云,以及王友亮、潘德舆分别所作《静海寺》诗、陈文述《静海寺诗并序》(24)[清]王友亮《静海寺》“般棹秋江十里长,招提结伴且寻将。凭谁导路蹲狮子,怪而开门叫凤凰。海外灵搓曾揽胜,岩端健笔自流芳。老僧不观空旨,对客犹然说郑挡。”清人陈文述《秣陵集》亦谓:“(静海寺)在仪凤门外卢龙山西,永乐中以海外平服,因建寺”,载《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第253页。等,亦皆持如是之说,可见其说影响之深远。
而随着郑鹤声先生1936年在静海寺内僧厨墙壁上发现的一块残碑,关于静海寺建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及其与郑和下西洋之间的联系,在今人的不断推绎之下,遂呈现出越来越细化的趋势。
郑鹤声先生在静海寺内僧厨墙壁上发现的残碑,尚可辨识140多字,内容记述了静海寺建置与明初郑和下西洋诸事,残文内容依次为:
“……帝敇建弘仁普济天妃之宫于都城外龙江之上,以……帝复建静海禅寺,用显法门,诚千古之佳胜,岂偶然之……一,永乐三年,将领官军乘驾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清海道。永乐四年,大艐船驻扵旧港海口,即古之三佛齐……首陈祖义、金志名等,扵永乐五年七月内回京。由是……永乐七年,将领官军乘驾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其国王阿烈苦柰儿谋劫钱粮船只,事……阿烈苦柰儿并家……”。
可惜的是,一度镶嵌在静海寺僧厨墙壁上的这一通残碑,早已毁佚无存,直至1977年郑一钧发表《郑和下西洋对我国海洋科学的贡献》一文(25)郑一钧:《郑和下西洋对我国海洋科学的贡献》,载《海洋科学》1977年第2期。和1980年代郑鹤声、郑一钧父子编纂的《郑和下西洋史料汇编》付梓出版,此静海寺残碑的碑文与拓片资料,始得以公诸于世(26)碑文照片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图版4。。
从《郑和下西洋史料汇编》下册图版存录的静海寺残碑照片来看,此碑碑文残存8行,每行残存7字至20多字不等,碑文的主要内容与记载郑和下西洋史事的江苏太仓、福建长乐两地明代天妃宫碑相近。郑鹤声1936年发现的静海寺残碑虽然也记述了郑和下西洋的史事,不过推究文意,即便是残碑未经破坏之际的完整内容,也远不能与太仓、长乐两地的明代天妃宫碑碑文之丰富相提并论,正如陈得芝先生指出的那样,静海寺残碑相较太仓、长乐两地天妃宫碑而言,容纳不下永乐五年第二次下西洋的纪事(27)陈得芝:《关于郑和下西洋年代的一些问题》,载《郑和与海洋》,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06-212页。。在2014年举办的“中国历代涉海碑刻学术研讨会”上,陈得芝先生进一步指出,太仓、长乐两地明代天妃宫碑署名立碑的正使太监不止郑和一人,而静海寺残碑很可能只署郑和一人之名,故而郑和没有身与其事的第二次下西洋事迹,在静海寺残碑之上也便不予记载了。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里曾提及“静海寺有篇重修碑可证”(28)[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100回,《奉圣旨颁赏各官 奉圣旨建立祠庙》,陆树崙、竺少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87页。,这里所谓的静海寺“重修碑”,指的很可能便是郑鹤声1936年发现的静海寺残碑。明代静海寺自落成后曾历经数次重修,其中,见诸史载最早的一次重修工程告竣于正德十四年,是由“(南京)守备太监黄伟、高隆等议重修,以宦官杨宽专其任。杨宽用浮屠故事,费出募缘,经营三载,厥功告僝。”由此可见,如果郑鹤声1936年发现的静海寺残碑确实是《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提及的“重修碑”,则残碑可能也并非明初肇建静海寺之际的遗存,故而碑文所记述明初郑和船队历下西洋的内容,只不过是后世之人追溯前尘,因而出现节略其文的情形,则其篇幅固远不若明初在太仓、长乐两地所置的天妃宫碑,也就不是不能理解之事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郑鹤声1936年发现的静海寺残碑碑文前两行,其中的“……帝复建静海禅寺”云云,明确记载静海寺的肇建尚晚于龙江天妃宫,这段内容对于探究静海寺创建年代诸问题而言非常重要,从中可见,明成祖朱棣敕建静海寺的缘起,固与之前已竣工的龙江天妃宫相类,同样有祈愿郑和舟师出使西洋平安往还、风波无警的象征意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供职于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王能伟先生根据静海寺残碑有述及郑和永乐七年(1409)下西洋俘虏锡兰山国王亚烈苦柰儿之史事,遂撰文认为静海寺应是郑和永乐七年下西洋返程之后的永乐九年(1411)所建(29)王能伟:《静海寺》,载《金陵胜迹大全》之《寺庙道观编》,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年,第658页;《南京文物志》第3章,《历代建筑(上)》,北京:中国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139页。。但问题在于,郑鹤声1936年发现的这一通静海寺残碑,通篇只存8行“斩头截脚”的片段碑文,是一件内容很不完整的材料,至于碑文中是否有述及郑和后来的若干次下西洋事迹,尚且是未知数,因而王能伟先生仅仅根据静海寺残碑内容记载郑和下西洋船队俘虏锡兰山国王亚烈苦柰儿之史事,便推断静海寺系郑和永乐七年下西洋归来之后的永乐九年所建,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在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前夕,郑一钧先生根据《明实录》关于龙江天妃宫始建于永乐五年(1407)九月(30)《明太宗实录》卷71,永乐五年九月戊午,第994页。、重建于永乐十七年(1419)九月(31)《明太宗实录》卷216,永乐十七年秋九月甲寅,第2156页。的记载,并参之以乃父1936年发现的静海寺残碑的部分内容:“……帝敇建弘仁普济天妃之宫于都城外龙江之上,以……帝复建静海禅寺,用显法门,诚千古之佳胜,岂偶然之……”,进而推断静海寺是在永乐十七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归来,值明成祖朱棣重建龙江天妃宫完工之后,才得以建成的一座寺庙(32)郑一钧:《论南京郑和遗迹的历史文化价值》,载《郑和研究》2004年第7期。。如前所述,在笔者看来,郑鹤声1936年发现的静海寺残碑的碑文充其量只是揭示出静海寺的创建晚于龙江天妃宫而已,但静海寺的创建究竟晚至何时,却由于碑文残损不全、内容缺失,仍然无法知晓。换言之,龙江天妃宫始建于永乐五年,复建于永乐十七年,则静海寺究竟建于永乐五年与十七年之间,抑或建于永乐十七年之后,仍然是个未知数。
此外,明代《南京都察院志》记载:“……静海寺,坐落郡字铺,永乐八年剙。天妃宫,坐落郡字铺,永乐七年剙。”(33)[明]施沛撰、徐必达领修:《南京都察院志》卷22,《职掌十五西城职掌古迹》,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原内阁文库藏明天启年刊本,第11册,第80页。这一段记载很明确地将南京静海寺的创建年代系于永乐八年(1410),但前人显然对此均不曾留意,否则那些坚持静海寺为明成祖朱棣敕建的学者们不可能不对这一材料大加引用。不过笔者认为,《南京都察院志》的成书亦值明末,况且书中同一页所记“坐落郡字铺”的龙江天妃宫系出“永乐七年剙”云云,即与史实不符,故书中所载静海寺“永乐八年剙”云云,虽然言之凿凿,但在具体使用之际仍需审慎。
关于南京静海寺为明仁宗朱高炽在位期间建成一说,源出明代景泰年间成书的《寰宇通志》卷8:“静海寺在城西北二十里,洪熙元年赐额。”(34)[明]陈循等纂修:《寰宇通志》卷8,《玄览堂丛书续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本,第41册,第38页。正德十四年(1519)成文的南京礼部侍郎杨廉所撰《静海寺重修记略》,则借正德年间南京守备太监黄伟之口述云:“黄公(伟)且谓……永乐年间,命太监郑和辈尝奉使航海,往来于粘天无壁之间,曾未睹夫连山排空之险。仁宗皇帝敕建此寺,而因以名焉。盖以昭太宗皇帝圣德,广被薄海内外焉耳”(35)[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18,第362-363页。。
值得一提的是,从《寰宇通志》与《静海寺重修记略》等文本的成文时间来看,静海寺为明仁宗朱高炽登基之后建成一说,其实较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建成静海寺之说出现得更早,并且也为《万历应天府志》与《万历上元县志》这样的官修志书蹈袭相沿。凡此种种,皆足以表明,南京静海寺为明仁宗朱高炽登基之后建成一说,较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建成静海寺之说,或许更为接近真相。
三、关于郑和施奉大藏经的线索
如果静海寺系明仁宗朱高炽登基之后方始建成,那么由于明仁宗朱高炽在位的起讫年限为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至洪熙元年(1425)五月,这也就意味着南京静海寺的竣工落成,当不出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至洪熙元年五月这不足一年的时间之内。
不过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明仁宗朱高炽其实对于耗费巨资出洋通蕃的热情并不高,这从朱高炽甫一登基,随即颁发诏书,令郑和、王景弘诸辈停罢下西洋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举措,便可见一斑。明仁宗既然并不热衷下西洋,何以却仍然要在南京继续劳师动众地兴建为祈愿郑和、王景弘诸辈出使西洋平安往返、风波无警而具有象征意义的静海寺呢?这便需要引出另一件重要的材料,即民国时期冀县人李杏南访获的明初刻本《优婆塞戒经》了。
据邓之诚《骨董三记》卷6《郑和印造大藏经》记载,冀县人李杏南于1947年曾访得明初刻本《优婆塞戒经》,在此经的第7卷之后刊有署款为“内官监太监郑和”的题记,题记之中便有涉及南京静海寺创建的相关内容,不过似乎还未及引起学界同仁足够的重视,今转录如下:
“大明国奉佛信官内官监太监郑和,法名速南吒释,即福吉祥。切念生逢盛世,幸遇明时,谢天地覆载,日月照临,感皇上厚德,父母生成,累蒙圣恩,前往西洋等处公干,率领官军宝船经由海洋,托赖佛天护持,往回有庆,经置无虞,常怀报答之心。于是施财陆续印造《大藏尊经》,舍入名山,流通诵读。伏愿皇图永久,帝道遐昌。凡奉命于四方,常叩恩于庇护,次冀身安心乐,福广寿长,忏除曩却之,永享现生之福。出入起居,吉祥如意,四恩等报,三有齐资,法界群生,同成善果。今开陆续成造《大藏尊经》计一十藏:大明宣德四年,岁次己酉,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牛首山佛窟禅寺流通供养;大明宣德五年,岁次庚戌,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鸡鸣禅寺流通供养;大明宣德五年,岁次庚戌,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北京皇后寺流通供养;大明永乐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静海禅寺流通供养;大明永乐十八年,岁次庚子,五月吉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镇江金山禅寺流通供养;大明永乐十三年,岁次乙未,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福建南山三峰塔寺流通供养;大明永乐九年,岁次辛卯仲冬吉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天界禅寺毗卢宝阁流通供养;大明永乐八年,岁次庚寅,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云南五华寺流通供养;大明永乐五年,岁次丁亥,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灵谷禅寺流通供养。”邓之诚并附按语云:“记中遇佛字圣字皇字,俱空一字,年号庙宇抬头。按《明史》郑和凡七往西洋,此所述年月多属其启程之时,盖就地排列,不依年月为次第。和,云南人,故五华寺亦施一藏。五华寺与华国寺同在省城五华山颠,其废已久矣。”(36)邓之诚:《骨董三记》卷6,《郑和印造大藏经》引郑和题记,载《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564-565页。
值得一提的是,《郑和印造大藏经》所述及的由“内官监太监郑和”刊印的《优婆塞戒经》,亦曾见于1964年夏在北京中国书店举办的古籍小型展览。在这次小型展览中所陈列的宋元旧刻、明清精椠、名人抄校、活字本、木刻插图和彩绘图书等共计九十余种,其中就有明初刊印的《优婆塞戒经》。根据长年贩书为业、后进入中国书店工作的肖新祺先生所撰《业余偶抄》书稿的著录:“见诸1964年夏北京中国书店举办古籍小型展览的《优婆塞戒经》,系梵夹装,存七卷,为明宣德五年(1430)郑和刻本”(37)李希泌:《郑和印施<大藏经>题记--郑和皈依佛门的佐证》,载《文献》1985年第3期。。以此而言,肖新祺《业余偶抄》书稿所著录的明宣德五年郑和施刻的七卷本《优婆塞戒经》,与1947年冀县人李杏南所得并经邓之诚寓目、记录的明初刻本《优婆塞戒经》,固应属同一版本,甚至不排除就是李杏南与肖新祺两人先后寓目的同一部书。这样来看的话,明宣德五年郑和刊施的《优婆塞戒经》七卷本仍然可能幸存于天壤间,如果有幸被重新发现,不仅将为“佛弟子”郑和所奉施、刊印的佛经再增添一桩重要实物,也可为当年邓之诚《郑和印造大藏经》过录的宣德五年郑和题记内容,提供可靠的验证(38)《骨董三记》卷6,《郑和印造大藏经》过录的宣德五年内官监太监郑和的题记,谓郑和在永宣之际陆续印造的《大藏尊经》共计十藏,但实际上郑和题记列举受领《大藏尊经》的寺庙只有9座,尚缺一藏未有着落。不知是邓之诚先生过录郑和题记之际漏略,抑或郑和原文即是如此。。
在上述经郑鹤声过录的“内官监太监郑和”宣德五年刊施《优婆塞戒经》卷7之后的题记中,有关于郑和“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静海禅寺流通供养”的内容,而“发心印造”的具体时间是大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岁次甲辰十月十一日。据以可知,南京静海寺至迟在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已然建成,这无疑是迄今所见关于明代南京静海寺创建年代最为确凿的第一手史料了。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二十二年七月辛卯在榆木川病故(39)《明仁宗实录》卷1上,永乐二十二年七月辛卯,第5页。,仁宗朱高炽于同年八月丁巳登基(40)《明仁宗实录》卷1上,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丁巳,第13页。,故郑和于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静海寺之际,其时明仁宗朱高炽已经登基。而结合《静海寺重修记略》一文所述“仁宗皇帝敕建此寺,而因以名焉。盖以昭太宗皇帝圣德,广被薄海内外焉耳”云云,当不难想见,静海寺的肇建应始于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而在仁宗登基之际,静海寺的主体工程可能刚刚完工或接近完工,故明仁宗朱高炽敕赐静海寺额,不过是“顺水人情”,与他并不赞成劳民伤财下西洋的举措,可以说并无违碍之处。
另一方面,如前引述,关于明代人所论及静海寺的创建年代,但凡谓静海寺系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建成者,其成文固已晚至明末以至入清以后;而谓静海寺系明仁宗朱高炽在位期间建成或敕赐寺额者,则不乏明代中叶成文者。由此可见,明仁宗朱高炽敕建静海寺之说渊源有自,不容置疑,而郑和在明仁宗朱高炽登基后的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静海寺以为山门之镇,可能恰恰与仁宗登基之后静海寺竣工落成并敕赐寺额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