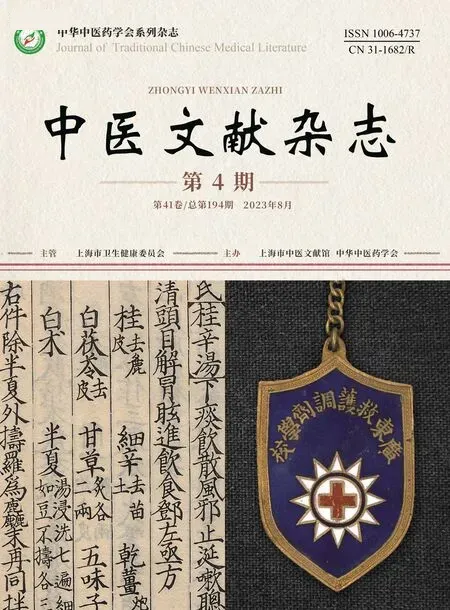中医论治小儿不寐古籍文献撷英*
刘旭华 姜永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200032)
失眠的中医病名为“不寐”,古籍中亦可见“不得眠”“不得卧”“不得睡”等病名。小儿不寐在明代以前多散见于“惊风”“疮疹”“泻痢”“喘”“积滞”等各类疾病中。《保婴撮要》有专门的章节论述不寐,提出了不同的病因病机。我们对历代有关小儿不寐的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古人对小儿不寐分别从五脏进行论治。
从心论治
心藏神,统领五脏,神为人的精神思维活动的统称,是人体最高级别的自我精神活动。《灵枢·本神》言“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神接受外界刺激而整合信息,产生意、志、思、虑等思维活动[1],故心神统领魂魄、意志。因其为人之自觉意识,故人之将寐,始于心神沉敛。又心属火,《素问·解精微论》言“火之精为神”,心神充沛,可驱散邪魅鬼魍,保持安寐[2]。故入睡困难、夜寐不宁、噩梦等多从心论治。
1.养心安神
清代夏禹铸《幼科铁镜·不寐多困》中言:“婴儿不睡有二。一心虚,一胆虚。睡中不闻人声,忽醒而不寐者,此心血不足,宜用人参安神丸;有睡中稍闻人声响动,即惊而不寐者,此胆虚之极,宜用参竹汤。”认为婴儿不寐有心虚和胆虚两种情况。
心虚者重在心血不足,小儿稚阳未充,心脏未臻成熟,心血未充,心神怯弱。治以人参安神丸,方中以生地、麦冬、酸枣仁、当归补血滋阴,茯神宁心安神,人参为“心虚惊悸……诸类用之”。诸药合用,补心之气阴,养营血之亏,心血充则神魂得安,寤寐协调。明代医家薛铠以归脾汤、人参养荣汤、养心汤治疗心血不足之失眠。归脾汤、人参养荣汤补益气血,养心汤养心血益心气,诸方用药多以人参、当归、茯苓、远志、酸枣仁等药,补血养心以助安眠。
胆虚者,正如《太平圣惠方·治胆虚不得睡诸方》所言“是五脏虚邪之气,干淫于心”。夏禹铸参竹汤中以人参、麦冬、小麦养心除烦;用陈皮“味苦清心,味辛能通,所以通神也”,又用生姜性辛温,“久服阳胜,所以通神明也”,二药可通神明而止惊悸,全方补气养阴而安神定悸。薛铠以妙香散治疗胆虚不寐。妙香散其妙在于用木香、麝香,木香味苦入心,《雷公炮制药性解·木部》言“得木香则心气畅而正气亦畅”,则拂逆之气得平,心气通则神魂定;《难经·四十难》云“心主臭”,凡气味芳香者通于心,麝香辛香温通,为诸香之冠,用之则开心窍、通神明,二香合用,心则气通神清,通神不梦;又以山药益阴涩精,人参、黄芪固气,茯苓、茯神、朱砂宁神,远志既开心气又通肾气,交通心肾,则肾精、心神相依而自固。又有桔梗载诸药上行以益心经,甘草调和诸药交于中,助远志交通之力。故此方调补心气为主,而补、行心气以宁神,神宁气固以涩精,精神相依则寐安。
2.清心除烦
若心经实热,扰动心神,亦难以入眠。《保婴撮要·惊悸》治以茯苓散,“治心经实热,口干烦渴,眠卧不得,心神恍惚”。方中茯神宁心安神,用麦冬“去肺中伏火,伏火去,则肺金安而能生水,水盛则能清心而安神矣”,紫菀“苦能入心,而清上炎之火”,赤石脂“色赤,宜入心经……心主血属火,得石脂以疗之”(《雷公炮制药性解》)。三药均可清热泻火,宁心安神。通草、桂心引热下行,知母滋阴降火,大枣调药味,补脾和胃,竹茹清热化痰,升麻清泻阳明之热,取“实则泻其子”之意。《幼幼集成·惊悸》以天竺黄丸治疗该型不寐,用药不悖清热安神之旨。
从肝胆论治
肝藏魂,所谓“随神往来谓之魂”,魂之初生,是伴随神的产生而生成。《四圣心源·精神化生》载:“阳气方升,未能化神,先化其魂,阳气全升,则魂变而为神。魂者,神之初气,故随神而往来。”魂主宰人身非本能的、后天的、较高级的心理活动,在接受外界信息后,魂作为中间媒介,上传于神以整合、决策,下达于魄以反映、表达[3]。作为接收外界信息的魂,若不能在寤寐时敛藏于肝,而病态地激发神、魄等功能,则多见易醒、睡不安稳、梦游、梦呓等[4]。
1.补血养肝
《保婴撮要·不寐》云:“病后余热者,酸枣仁汤。”酸枣仁汤是治疗肝血不足之不寐的代表方。肝为罢极之本,气血充盈,但小儿稚阴稚阳,罢极更易伤肝;肝血亏虚,久则母病及子,见心肝血虚,虚则生热,故养肝血以荣心。极者宜收宜补,以酸枣仁养心补肝,收而补之,辅以川芎之辛散,合肝条达之性,补而不滞;“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故用甘草,兼可防川芎疏泄太过;知母滋阴制虚火、茯苓淡渗兼可甘补育阴,则阴阳和合以助宁神安魂。《证治准绳幼科·不寐》引《太平圣惠方·食治骨蒸劳诸方》中酸枣仁粥治烦心不得眠,亦以酸枣仁、地黄、蛤蜊水煎服,主以滋阴清热而助眠。
薛铠以珍珠母丸治疗不寐。原方见于《普济本事方·中风肝胆筋骨诸风》,曰:“治肝经因虚,内受风邪,卧则魂散而不守,状若惊悸,真珠丸。”此肝经虚,不能濡养肝体,血不舍魂,而致不寐[5]。故用珍珠母丸滋养阴血,潜阳安神。其养血补肝又摄纳浮越之肝阳,一补一降,则神得内藏,夜寐得安。
2.化痰温胆
小儿因脾胃虚寒,阳气失于温运或惊恐所致胆伤气陷而见胆经郁滞,失于疏泄,脾寒本有痰湿,胆经气滞更助生痰,痰生困阳,不得温煦而见胆虚则寒[6];胆为少阳经,为心肾交接之所在,胆经病则影响心肾交接,遂见不寐[7]。《婴童类萃·急慢惊风论》《保婴撮要·惊悸》认为,胆虚不眠皆由“心惊胆摄,气郁生涎,涎与气搏,变生诸症……胆虚不能制脾,则脾之水饮作矣”。胆虚烦不眠之证,以温胆汤、加味温胆汤清胆理气化痰。温胆汤原方见于《外台秘要·病后不得眠方二首》引《集验方》,方中生姜用至四两,徐灵胎《兰台轨范·情志卧梦》言“生姜一味足散胆经之寒”[8];合陈皮、半夏等辛温之药,甘草甘平,所用诸药以温为主,可温补胆腑[9];又因胆气郁滞与脾虚互为因机,酿生痰涎,以半夏、生姜、竹茹化痰和胃,陈皮、枳实理气则气顺痰消。枳实理气助半夏化痰,竹茹化痰助陈皮理气,二药其性微寒又防温燥太过。全方以温为主,如《医方集解·和解之剂》言“如是则不寒不燥而胆常温矣”。全方虽未用安神之药,但俾其气通痰消而阴阳可交,则能助寐[10]。《婴童类萃·伤寒论》载加味温胆汤“治病后虚烦不眠,心惊胆怯”,为温胆汤去竹茹加人参、柴胡、桔梗、浮小麦、灯心,减化痰之力,借调心肾之机以复胆经交接心肾之用。
3.疏肝健脾
《丹溪心法·小儿》言:“小儿易怒,肝病最多,大人亦然。肝只是有余,肾只是不足。”小儿肝常有余,易为情志所动,肝之相火妄动,郁而不得泄,则魂不入肝而不寐,兼见乘脾土及心经之传变[11]。《保婴撮要·不寐》治肝火不宁之不寐,用加味小柴胡汤,即小柴胡汤加山栀、牡丹皮。《绛雪园古方选注·和法》言柴胡汤“不从表里立方……而以升降之法和之”,其中柴胡升少阳之气,黄芩降肺经之热,助其所胜之气,解少阳之邪;再以人参、甘草等补脾土,以防其所不胜之气相乘;又以生姜、大枣和营卫,半夏和阴阳,再加丹皮[12]、栀子清泻肝胆之热。方中所用,既治肝经之热,又兼治其所胜与所不胜脏之传变。
薛铠治肝郁之不寐,不纯治肝,亦兼用治他脏之药。他曾治一女童因饮食怒气,而有“不寐、腹痛”等表现,先用六君子汤合柴胡、升麻,再以加味逍遥散、加味归脾汤助眠。六君子汤健脾益气,加味逍遥散在逍遥散疏、补基础上加用丹皮、栀子,增其泻热之功;加味归脾汤即归脾汤加柴胡、山栀。三方皆以补益脾胃为主兼以泻热疏肝,何以用治肝病?其意在升麻、柴胡。薛氏首言六君子汤加升麻、柴胡以止腹痛,即针对其肝郁气滞兼脾弱之病机。我们认为加用升麻、柴胡之意,不止于此。首先,食积肝郁必有相火之虞,加柴胡可疏肝行气,清热泻火,《本草备要·草部》言其“为升清退热必用之药”,又借柴胡升肝之用以解脾胃之壅[13];升麻可引药入阳明,以补脾胃不足[14],又升发郁火。其次,升麻与柴胡相配,可调节气机。二药皆为风药,升麻升阳明清气,柴胡升少阳清气,阴中升阳,可使浊阴、阴火下降[15];既是疏肝之用,又有运脾之功,如李东垣所言“以诸风药,升发阳气以滋肝胆之用,是令阳气生,上出于阴分”[16],肝胆气机条达,脾胃壅滞自除[17]。
从肾论治
肾藏志,所谓“意之所存谓之志”,志乃意之所专,是在认识事物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认知,并可以支配自身行为活动[18],这种对自身的自知会进一步形成记忆,可以影响心神,甚至作用于思维过程,从而影响自身的行为。因志乃意更进一步的思维过程,二者常相并而言,《灵枢·本脏》有“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又有“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佐证上述论证结论。故肾不藏志,则多见睡眠焦虑,睡眠不规律、紊乱,甚则彻夜难寐、焦虑不安等。
1.滋补肝肾
《保婴撮要·不寐》认为肾虚而兼见肝之不足,其治小儿肝肾虚热之不寐,方用六味地黄丸。因肝肾阴阳互滋互制,肾之真阴不足可累及肝阴,则阴不制阳,虚热内生,而致不寐,六味地黄丸为钱乙减肾气丸之桂枝、附子。以六味地黄丸养阴泄浊以降火,切合病机。
2.调补心肾
海派徐氏儿科认为,小儿以“阴为体,阳为用”,不寐之证因肾阴、心阳不调所致,总以潜阳温肾为法,复阴阳平和之机以助安寐。
温潜法即宗祝味菊所言:“气虚而兴奋特甚者,宜与温潜之药,温以壮其怯,潜以平其逆,引火归元,导龙入海,此皆古之良法。不可因其外形之兴奋而滥予清滋之药也。”[19]以温热之附子,配伍磁石、龙骨、石决明、紫贝齿等潜降之药[20],附子温补心、肾之阳,走而不守,紫贝齿、龙骨、磁石等既滋阴敛阴,又制约附子走而不守之性,使浮越之阳气潜下,诸药用之,既致心肾阴平阳秘,兼可温运一身之气,则夜寐神安。若有禀赋不足或久病而见气阴两虚者,则据“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辛”及“有形之火不可纵,无形之火不可残”之经旨,在温潜法的基础上,加减黄连阿胶汤等养血育阴之药,成潜阳育阴之法,温潜生气则气旺可以生阴,养血补阴则阴充可以生阳,诸药合用,则水火既济,阴阳平和,夜寐可安。
从脾胃论治
脾藏意,意为五神之一,有记忆、思维、注意、推测、心理、怀疑等多种涵义[21],《杂病心法要诀·神之变化》云其“意者,心神之机,动而未形之谓也”,故调节“意”可助神志安定,正如张景岳所言“脾藏意,神志未定,意能通之,故为谏议之官。虑周万事,皆由乎意,故智周出焉[22]”。《灵枢·本神》言“脾藏营,营舍意”,脾藏意功能的正常发挥,需以脾运化水谷、化生营气、以营养意这一过程为物质基础[23]。故调节脾胃功能,可助脾藏意而助安眠。
1.消食和胃
《幼科心法要诀·积滞门》载:“乳滞之儿,其候睡卧不宁,不时啼叫……惟宜调和脾胃为上,以消乳丸消导之。”幼儿因乳、食积滞,导致小儿睡卧不安,烦不安眠,即以消乳丸或木香大安丸调和脾胃,使小儿得以安睡。正如《素问·逆调论》云“胃不和则卧不安”,小儿脾常不足,易饮食积滞,不得运化,停积胃中,而致胃气失和,不得安寐。治以消食助运之法,积滞除而睡眠安。
2.健脾益气
脾胃气虚而致脾胃不和,影响人体正常寤寐。《保婴撮要·不寐》云:“寤则魂魄志意散于腑脏,发于耳目,动于肢体而为人身指使之用;寐则神气各归五官,而为默运之妙矣。若脾胃气盛,则脏腑调和,水谷之精,各各融化,以为平和之气。若胃气一逆,则气血不得其宜,脏腑不得其所,不寐之症,由此生焉。”首先,脾气虚弱影响纳运失因,使胃气上逆,神思不安,夜不能寐;其次,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运不足则五脏无以滋养而变生诸证,影响安寐;再次,脾为水之中州,脾气虚弱,则水液不得四布,积聚成痰湿,更困脾使其难以运化。薛铠父子以四君子汤加远志、酸枣仁等治疗小儿不寐,一则使脾气健则胃气和,纳运相得,气血充盛,津液四布,五脏安和;二则脾胃安则魂得由目藏于肝,遂得安眠。
从肺论治
肺藏魄,《左传注疏·昭公七年》言“附形之灵为魄,附气之神为魂也。附形之灵者,谓初生之时,耳目心识、手足运动、啼呼为声,此则魄之灵也;附所气之神者,谓精神性识渐有所知,此则附气之神也”。魄指人身与生俱来的感觉运动,是一种非条件反射性的运动[24];魄亦以精为基础,与人之形体关系密切。故魄受神魂等思维意识激发,从而可形成特定的行为反应,为人身外在表现的物质基础。肺不藏魄,易为神魂而激发,则多见睡眠轻浅、易醒,多梦等表现[25]。
1.清解肺热
《太平圣惠方·治小儿伤寒余热不退诸方》载:“治小儿伤寒,得汗利后,余热不除,心神烦躁,夜卧不安,黄连散方。”小儿肺脏最易受邪,若为热邪所扰,魄不能藏,则见不眠、哭闹易醒等症,其以黄连散清泄肺经余热,热清则肺魄得藏。《素问悬解·至真要大论》云:“肺主气而藏魄……火炎肺热,收敛不行,精魄郁蒸,化为汗液。四面升腾,泄而不藏也。”
2.理肺安魄
《证治准绳幼科·喘》载:“碧玉丸,治痰嗽气喘胸满,饮食减少,睡不得宁,烦躁有热。”《圣济总录·小儿咳逆上气》亦见“治小儿上气咳嗽,不得安卧,桔梗饮方”。肺主气,司呼吸,为魄之处,若肺脏受邪,其气壅滞,则魄不得安其位,则见不寐,正如《灵枢·淫邪发梦》所言“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桔梗饮以桔梗、桑皮、贝母、南星等理肺化痰之药,清肺经之邪,以安肺魄,则魄安得寐。
历代医家论治小儿不寐皆蕴含调补五神脏以助安眠之意。所谓调心和其神,补肝而悦其魂,清肺而安其魄,健脾以存其意,滋肾而通其志。正如《续名医类案·不眠》所言“人之安睡,神归心,魄归肺,魂归肝,意归脾,志藏肾,五脏各安其位而寝”。古人所用方药固然对今人临床辨证施治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各医家思辨之理法更应为末学后辈所重,临证用之,才能融会贯通,收获良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