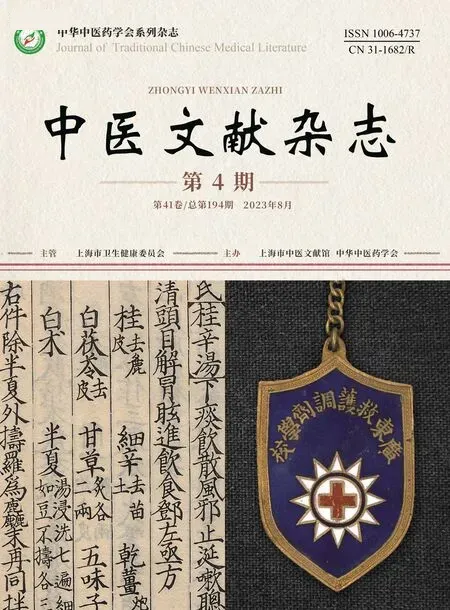《素问·气府论》“足太阳脉气所发”考*
瞿筱逸 张 潮 王 静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201203)
《素问·气府论》(以下简称《气府论》)是论述针刺部位的名篇。此篇对正确认识腧穴内涵、归经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但文中关于“足太阳脉气所发”的穴名及穴数历来认识不一。本文以唐代王冰次注、宋代林亿等校正,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顾从德翻刻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1]为底本,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文本考释
《气府论》[1]500-517足太阳脉气所发部分,历代多有不同见解,其中争议较多者如下。
1.“足太阳脉气所发者七十八穴”
此句概述全身足太阳脉气所发数,“七十八穴”计入了足太阳双侧穴数,而非现代通常采用的穴名计数。
对“七十八”这一数字,诸家记载或注解不一。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以下简称《太素》)载作“七十三”[2]。王冰则认为这一数字当作“九十三”,包括本经脉气所发的78穴,以及“气浮薄相通”的15穴,即下文提及的“凡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穴中,除足太阳膀胱经10穴之外的15穴。张介宾的观点与王冰同[3]232-237,吴崐考得91穴[4],张志聪考得77穴[5],高世栻则称原文有误,将“七十八”直接改为“七十六”[6]。
2.“入发至项三寸半,傍五,相去三寸。其浮气在皮中者,凡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
“入发至项三寸半”,《太素》作“入发项二寸,间半寸”,杨上善认为,此指“额上入发一寸,后从项入发一寸,但间亦有一寸半处,故曰半寸也”,此处杨上善未注明穴位。王冰则认为有大杼、风门各2穴。林亿等人校书(下称“新校正”)时认为此注有误,“项”当作“顶”字,此句主要说明“五五二十五”的部位,即百会向前后左右各3寸,共五行五列的25穴。马莳则认为,“入发至项三寸半”,发指后发际,项则指后颈,“自入发至项而下”,有3.5寸许,“相去三寸”,则指左右大杼或风门之间的距离为三寸,王冰所注无误[7]。张志聪从马莳之说。
“傍五,相去三寸”《太素》作“傍五相去二寸”,同时杨上善注“《明堂》傍相去一寸半”。“凡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杨上善释为中行督脉的的囟(误作亚)会、前顶、百会、后顶、强间,两侧旁开足太阳脉的五处、承光、通天、络却、玉枕,以及再外部足少阳的临泣、目窗、正营、承灵、脑空,共25穴。杨上善认为,太阳为二阳之总,故这些穴位“皆为太阳所营”,一并计入太阳脉气所发数。王冰、马莳、张介宾、张志聪(强间误作长强)所注穴位皆同此。高世栻与“新校正”观点相仿,认为“入发至项”的“项”为“顶”之误,故将原文改为“入发至顶”,并在从发际至前顶之前的3.5寸内,注有神庭、上星、囟会3个督脉穴。其后的25穴,中行是前顶、百会、后顶、强间、脑户5穴,余足太阳和足少阳脉气所发则与其他人相同。这一解释,当代有学者部分认同[8-9]。
3.“风府两傍,各一”
杨上善注为天牖2穴,而王冰认为指风池2穴,后世学者多采王冰之说。“新校正”则指出,《甲乙经》中,风池为足少阳和阳维之会,非太阳脉气所发,且“经言风府两傍乃天柱穴之分位”,此句只是再次说明前文“项中大筋两傍”的天柱穴而已。故新校正认为,此处的风池、前文的大杼和风门均在王冰所说的93穴之外。
4.“侠背以下至尻尾二十一节,十五间各一”
“侠背以下至尻尾”,《太素》作“侠脊以下至尻”;杨上善认为此指大椎以下至尻尾二十一间,“十五间两傍各有一输”,共30穴,但未注明具体穴位。王冰用《中诰孔穴图经》所存的13穴,即附分、魄户、神堂、、膈关、魂门、阳纲、意舍、胃仓、肓门、志室、胞肓和秩边来说明这一部分的脉气所发;但对“十三”与原文“十五”的差异,王冰并未分析。“新校正”认为,王冰说足太阳93穴,是计入了2个缺失的穴名,按“十五间各一”计算的。吴崐据《甲乙经》所注的穴位与王注相同,同时怀疑“十五”当为“十三”,因为即便加入了后世出现的膏肓,两侧也不得30之数。张介宾考察《甲乙经》后,认为可以补充大杼及膏肓,成15之数。
5.“五脏之俞各五,六府之俞各六”
此句不见于《太素》。王冰注为肺俞、心俞、肝俞、脾俞、胆俞、胃俞、三焦俞、大肠俞、小肠俞、膀胱俞,即五脏六腑的背俞穴,两侧共22穴。
随着卷筒纸印刷机速度的上升,折页机构动态响应表现出丰富的非线性特征.以前对折页机构的研究,都是认为运动副是刚性且无间隙的理想状态,将折页机构做为单自由度系统进行分析[8,9],无法解释折页机构的非线性动态响应现象.实际状态下,运动副间隙和轴承滚子的变形会引起与运动副相连两构件相对微小的运动.随着折页机构速度的提高,两构件的微小相对运动使折页机构表现出非线性动态响应.下面考虑运动副间隙和轴承滚子变形因素,对折页机构进行动力学研究[10~13].
马莳将此句与句6合并解释,认为句6中的左右30穴,包括了五脏六腑之背俞穴,以及厥阴俞、膈俞、中膂内俞(即中膂俞)和白环俞。张志聪、高世栻持相同观点。
讨 论
1.足太阳脉气所发数
足太阳的脉气所发数,原文作78;但若据原文对足太阳脉气所发的描述,则总计不止78。在上文提及的代表性注释中,各注家给出的计数各不相同,除王冰外,其他注家的计数均能自洽。
王冰注解本篇,查得“兼亡者,九十三穴”,认为是传写有误导致。按王冰注,78是93减去头部“气浮薄相通”但不属于足太阳的15穴的结果。实际考察结果表明,王冰注实得穴数95,“新校正”所说的99穴计入了王冰注“十五间各一”时,除《中诰孔穴图经》13穴之外,未作说明的2个腧穴。同时,新校正认为,王冰说93,而实得99,是后人妄增了“入发至项三寸半”处的大杼、风门,和“风府两傍”的风池所致。
吴崐、张介宾所注腧穴基本与王冰同,惟吴崐不认可大杼、风门,而张介宾则去风门,加膏肓。张志聪和高世栻注解时,依马莳而未采纳王冰等人所注的“十五间各一”的腧穴,故最终穴数与《气府论》原文相近。
2.气府、脉气所发与腧穴归经
《气府论》以“XX脉气所发”为主要形式,介绍了手足三阳、任脉、督脉、冲脉的脉气所发总数及分布,并提及足少阴、足厥阴、手少阴和阴阳跷的个别腧穴。“XX脉气所发”这一提法说明了腧穴源于经脉之气,也表明了腧穴的经脉联系和归属,故“脉气所发”所指大致与现代的“经穴”相同。
在这三种解释中,高世栻之说显然不合理,因《气府论》除六腑阳经外,还论及了阴经及任、督、冲等脉。马莳“脉气交会之府”之说也不合理,因为本篇的重点不在于交会之处,而在于分经论述各经脉气所发。张介宾的注解是这三者中较为合理的,因为按各家注解,《气府论》各经脉气所发既有本经穴,也有他经穴,如足太阳脉气所发除足太阳本经腧穴外,还有督脉和足少阳经穴。但是,这一定义与所注腧穴有矛盾。如临泣、目窗、正营、承灵、脑空5穴,王冰注足少阳脉气所发时,指出临泣是足太阳、足少阳、阳维三脉之会,而其余4穴均是足少阳和阳维二脉之会,据此则后4穴不应列入足太阳脉气所发;天冲、曲鬓,王冰注于足少阳脉气所发之中,并说明它们是“足太阳少阳二脉之会”,但并未列入足太阳脉气所发。所以尽管这三种解释可以帮助理解气府的内涵,但它们的定义并不确切。
有现代学者认为,“气府”是指脉气所发之一类穴位的总称,而《素问·气穴论》中的“气穴”只能用于某一个具体穴位的称呼[10]。这一观点区分了气穴与气府的不同,但考察《气穴论》[1]485-500与《气府论》的内容可知,两篇的区别主要在于腧穴是否归经。《气穴论》中的腧穴主要以分部、分类的方式呈现,如张介宾所说,“言穴不言经”[3]227。而《气府论》是以经统穴,先言经再列其穴。腧穴归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黄帝内经》之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也称《黄帝明堂经》,以下简称《明堂》)将肘膝以下的腧穴归经。头面躯干的腧穴则分部分行排列,并在部分腧穴下注明“XX脉气所发”或“X脉之会”[11]。这些都是后世腧穴归经理论的基础。王冰所注腧穴,理论上与《甲乙经》基本一致,只是将部分“X脉之会”,分别归入X条脉,如前文的临泣,分别被归入于足太阳和足少阳。但是他的做法并不是主流,更多的医家,如杨上善、王惟一等人,倾向于将交会穴归入一条经脉。自汉至宋,腧穴归经标准最终由宋代《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确定,影响直至当代。而该书中的归经和脉气所发都发生了较大变化[12]。这也是吴崐、张介宾等人在注解《气府论》时,都称该篇所载各脉腧穴名称和数目与当时理论不同的重要原因。
考察“脉气所发”含义和腧穴归经理论演变后可以推断,“气府”是脉气之府,是“脉气所发”的源头,所指即经脉。“X脉之会”,是X条脉的脉气所发交会处。正如道路交叉处属于任一条相交的道路,“X脉之会”可归属于X条脉。只是因腧穴归经常受主观因素影响,形成了某穴只能归某经的共识。而各家又因穴数有矛盾时,会从交会穴的角度来解释穴数并阐发“气府”,造成了“气府”和交会穴有关的误解。此外,理论形成过程中的缺失、文献传抄过程的错讹,使腧穴脉气所发、脉气交会等内容的记录不全,给后人辨识增加了难度。
3.“侠背(脊)以下……十五间各一”与“五脏之俞各五,六腑之俞各六”
《太素》所引用的《气府论》原文中,穴位数为73,杨上善所注腧穴的计数与此数吻合。但是有两个问题:杨上善的注未给出“十五间各一”的具体穴位;《太素》引用的原文中,没有“五脏之俞各五,六腑之俞各六”之句。这是杨上善区别于后世注家的主要不同。
马莳等人认为,“十五间各一”所指的腧穴包含了“五脏之俞各五、六腑之俞各六”,以五脏六腑的背俞穴及厥阴俞、膈俞、白环俞和中膂俞等双侧共30穴数释这两句话,故其穴数总计与《气穴论》原文非常接近。这一理解,也是他们与王冰、吴崐、张介宾等注解的主要不同。
《明堂》失传,可由《甲乙经》转载的内容窥知《明堂》原貌。《甲乙经》“背自第一椎两傍侠脊各一寸五分下至节”和“背自第二椎两傍侠脊各三寸下行至二十一椎下两旁侠脊”分别有42和26穴(双侧),当代一般将这两条线称为足太阳经的第一侧线和第二侧线。张志聪和高世栻所注腧穴均在第一侧线,这样的注解带来了两个问题:《甲乙经》无厥阴俞,厥阴俞见于《千金要方》[13]363;其余14穴中,除胆俞、三焦俞和白环俞在正文中说明是足太阳脉气所发外,剩余各穴均未说明由何经脉气所发。在《明堂》之前的《黄帝内经》仅见五脏背俞穴,并在《灵枢·卫气》说明了五脏背俞穴与阴经的联系。现存文献中,六腑背俞穴见于《脉经》及《甲乙经》,两者均无六腑背俞穴与足太阳经相关的记载。《医心方》转载有六朝时期的《产经》,此书将俞、募穴分别归入于各经,而非足太阳经下。就目前文献所见,唐中期752年的《外台秘要》以后,脏腑背俞穴才记入足太阳经下[14-17],而王冰在762年注《素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王冰将“五脏之俞各五,六腑之俞各六”理解为脏腑背俞穴,理论依据并不充分。
《气府论》“五脏之俞各五,六腑之俞各六”中的“各五”“各六”,王冰等人均按“各一”解,显然与语义不合。时人疑“各”字错讹,故新校正补充说明经文没错,“所以言‘各’者,谓左右各五各六,非谓每脏腑而各五各六也”,这一理解比较牵强,或可参考《太素》的相关内容重新解释。《太素》在“足太阳脉气所发”一节无“五脏之俞各五,六腑之俞各六”句,但接近文末处有“五脏之输各五,凡五十穴”,并注有“五脏之输,有二十五,两箱(相)合论,故有五十”。《灵枢·九针十二原》有“五脏五腧,五五二十五”之句,又有“六腑六腧,六六三十六”,即分别指阴经和阳经的五输穴和原穴。杨上善的注解无疑更合《黄帝内经》之旨。有学者认为此句是后人所增[18];但据以上分析,也有理由认为,《气府论》原文有“五脏之俞各五”“六腑之俞各六”,但并不在足太阳一节下。在文字流传过程中,出现错讹,杨上善所见的版本丢失了“六腑之俞各六”等字;而王冰或他人所见的版本未失,只是因误将这两句所指理解为背俞穴,而将其移至足太阳一节下,王冰以背俞之意为此句作注。唐中期至宋代成型的背俞归经理论、宋代“新校正”对王冰误注的确认则进一步造成了后世注家的误解。
王冰所注的《中诰经》的13穴,位于足太阳经第二侧线,《甲乙经》均在正文中说明是足太阳脉气所发,或某经与足太阳之会。王冰所注的大杼、风门2穴,“新校正”认为是后人妄增,两穴位于足太阳经第一侧线,《甲乙经》载明为足太阳与某经之会。这两个穴位,同在“十五间”,惟附分与风门在同一水平,不符合“十五间各一”之说。
至于膏肓一穴,存世文献中最早见于《千金要方》[13]540。吴崐指出,晋汉之上,此穴尚未有。有现代学者提出承扶在15穴之列[9,19],但承扶的定位与尻尾无关,在《甲乙经》中被归于“足太阳与股”一部;且秩边的定位已是21节中,最下的“第二十一椎下两傍”[20],故承扶不应属于“十五间各一”之穴。
《气府论》是《黄帝内经》腧穴归经理论的代表篇章之一,本篇提出的“脉气所发”“气府”等概念可以从腧穴归经的角度来分析其内涵。受不同时期腧穴理论影响,历代医家所注的腧穴与《内经》原意不尽相符。故研究《气府论》时,不应囿于原文及其注解,而是更应注重观察腧穴理论的发展演化,从而深入探讨腧穴和经脉理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