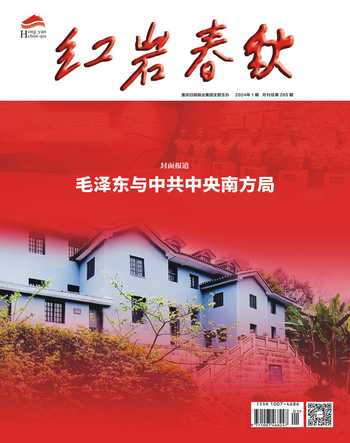皖南事变前夕一对新四军父女深情话别
蔡长雁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部长朱镜我在突围中牺牲。
在长女朱伊伟看来,父亲不仅是一位卓越的革命文化战士,也是一位疼爱子女的好爸爸。皖南事变前夕,父女俩深情话别的情景,永远铭刻在朱伊伟心中。
文化战士
朱镜我(1901-1941),浙江省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10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他被寄养在外祖母家。1920年7月,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浙江公费留日学生。求学期间,他勤勉好学,广泛涉猎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类书刊。他在日记中记录:“2月10日,买《欧洲近世思想史》,殊合己意。”“2月11日,近代思想十六讲看完。”“3月12日,读《近代文艺思潮论》。”“3月15日,所购《胡适文存》邮到。”“12月7日,托朋友购买《创造》杂志第2号。”
1922年11月2日,朱镜我就读的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老师坂本公然在汉文课上叫嚣:“中国国民顽冥而不知恩义,极难强盛。”朱镜我愤慨不已,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最后的感想:就是我们中国,非同日本一战不可!预备着死于沙场上,当然是我们的权利!”1924年初,朱镜我得知列宁去世后深感痛心,在3月1日的日记里写道:“列宁死了,但他的精神不死,要想改造社会,非有他的精神不可。”
1927年10月,应创造社元老成仿吾的邀请,朱镜我毅然中止在日本的学业,回到上海,加入创造社。他主编《文化批判》月刊,响亮地提出了“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列主义,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迷茫彷徨的进步青年的欢迎。他还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恩格斯这本著作的中文单行本。《文化批判》被查封后,朱镜我又主编《思想》月刊等,坚持革命文化工作,促进了左翼文化队伍的形成,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后来“左联”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1928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朱镜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立,朱镜我为文委成员,参与筹建“左联”。
1930年3月起,他先后任文委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宣傳部部长。同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他任党团书记。随后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他兼任党团书记。1935年2月19日,朱镜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6月,经党组织营救获释。
父女情深
朱镜我拥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但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他多年孤身一人在上海做党的工作,很少有机会同家人在一起。历经被捕、坐牢带来的身体折磨,以及长期伏案工作的呕心沥血,仍是青壮之年的朱镜我瘦成了皮包骨,经常大口大口吐血。1937年9月,朱镜我返乡养病,与妻儿团聚。在家乡,他发展党组织,将变卖家产和10多亩土地得来的钱,用作党费和革命事业的活动经费。
1938年春,朱镜我调到江西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宣传部工作,主编《剑报》副刊。同年秋,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任军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首任部长,兼军部刊物《抗敌》杂志主编。
朱镜我到新四军军部后,便鼓励妻子赵独步(又名赵霞君)和长子朱庭光、长女朱伊伟参加新四军。赵独步先任军部译电员,后任新四军抗日军人子弟学校教务训导主任。夫妻俩携手并进,与袁国平夫妇、薛暮桥夫妇一起,被军部评为三对“模范夫妻”。
1939年9月的一天,朱镜我得知朱伊伟从浙江丽水新四军办事处随汪海粟夫妇一路来到皖南,正在新四军军部招待所,便披上雨衣,提着风雨灯,迫不及待地赶来接她。一见到父亲,朱伊伟马上高兴地跟着他往回走。朱镜我是个瘦高个儿,步伐矫健,精神抖擞,每往前跨一步,瘦小的朱伊伟最少得走两步,后来她不得不跟着一溜小跑。朱镜我一面提着灯照路,一面问朱伊伟,丽水办事处的张贵卿伯伯怎么样了?她又是怎么来的?朱伊伟一一作答。在她眼里,随风飞起的雨衣,使父亲的身影在黑夜里显得更加高大。
最后离别
1940年11月底的一天下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服务团二队工作的朱伊伟,接到队长何士德传达的指示:“作好准备,明天和军部部分非战斗人员一起,随渡江先遣部队北上。”何士德还告诉她,在军部已同朱镜我交换过意见,是随队先走还是暂时留下来,由她自己决定。
当晚,朱伊伟便在同队音乐组长陈国等的陪同下,翻越二三里山间小路到军部去向父亲辞行。来到政治部宣教部,朱伊伟走进父亲的房间,看见他正在仅有的那张小板桌前埋头工作。他一边继续整理手头的文件,一边问:“你身体好了吗?”朱伊伟不由得一惊:这两天她身体不适,只能卧床休息,当天下午才起来。她想,大概是何士德告诉了父亲,便嗫嚅道:“还好。”
“你能跟着部队行军吗?”
“能!”朱伊伟满怀信心地说。
朱镜我仔细看看她,说:“也好,你随服务团—起走吧,何士德同志会照料你的。如果身体不太好,就留下来在我身边休息几天。”
“不,我身体已经好了,我要和服务团的同志一起走!”见女儿着急又坚定的样子,朱镜我考虑了一会儿便同意了,说:“行军途中你要多加小心,服从领导,听何士德同志的话,不要自由散漫。”
那时朱伊伟只有15岁,还有些懵懂,但也感到了与往日迥然不同的气氛。平时,朱镜我总爱和她说笑,关心她的学习与生活情况,不厌其烦地为她解答学习上碰到的难题。那天,朱镜我却什么都没有问起,甚至连朱伊伟摸黑跑了许多路都没顾得上问。这时,等在房门外的警卫员走进来,送给朱伊伟一双结实的布草鞋。这双鞋用布条编结而成,鞋头上还有一颗大毛线球。朱伊伟非常喜欢这双小巧精致的鞋。
12月1日一早,铅灰色的天空沉重地压在人们头上。军部大操场上排着整齐的队列,四周还围着不少乡亲,军部的首长们也来送行。但与往日部队集会时各兄弟连队互相拉歌的热烈场面不同,四周静静的,让人感到异常压抑和莫名酸楚。
朱镜我缓步向队列走来,他站到朱伊伟旁边,又一次问:“身体好吗?能跟得上部队行军吗?留在爸爸身边同爸爸一起走好吗?”朱伊伟确实想过留下来,但一想起父亲以往的教育,便克制住了念头,说:“我身体好了,我要和服务团的同志一起行军,我走得动的。”说着又下意识地摸摸打在背包后面的小草鞋。朱镜我虽然不舍,但他尊重女儿的选择。
在首长、老乡们的殷殷目光中,部队出发了,步子由缓而疾。朱伊伟禁不住回过头来,只见朱镜我还站在那里,目送着部队,她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妈妈几个月前离开了皖南,现在自己又告别了父亲、哥哥,跟随部队东进。不过,一想到他们不久后也要离开皖南东进,心里顿时宽慰了许多。
1941年皖南事变前夕,新四军军部决定后方机关及朱镜我、组织部部长李子芳等老弱病残人员,先期分批撤离皖南,经上海去苏北根据地。李子芳向朱镜我传达军首长的决定,要他准备出发,但他不肯先走。统战部长夏征农又来劝说,他依然坚持跟大部队一起行动。他说:“我是宣教部长,怎么可以离开部队先走呢?”
皖南事变爆发后,朱镜我抱病随军部撤离安徽泾县云岭,遭遇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为了不拖累同志,朱镜我纵身跳崖,壮烈牺牲。
当朱镜我牺牲的消息传来,朱伊伟悲痛欲绝。她没想到,那次见面竟然是永别,她后悔当时没有留下来,在父亲最后的时刻陪着他。后来,朱伊伟在《诀别——忆父亲朱镜我同志》中写道:“记得抗战爆发后,他刚从监狱里出来在杭州家中小住,常爱吟诵杜甫的《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想不到,这竟成了我们对他的悼念!”
作者单位:中共宣城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编辑/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