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茨海默病先生的妻子:我不想成为一个受害者
韩茹雪
“亲爱的,我要回家。”第五十几次听到这个请求时,蓝江刚吃完晚饭。所有家务活都做完了,她正准备松一口气,这个熟悉的声音立即令她浑身紧张。
蓝江一遍一遍地告诉声音的主人——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丈夫克拉德,“我们已经在自己的家里了。”
“我不知道你想去哪里,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吧!”妻子的绝望换来丈夫的沉默,随之是妻子的内疚。
2002年,克拉德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这预示着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走向死亡的过程,通常持续数年甚至十余年。不仅病人自己,还有病人的家人和朋友,都将沦为“受害者”,他们将被迫目睹病人的情形日趋恶化,被迫目睹自己的爱人在痛苦中挣扎却无能为力,同时为了补偿病人失去的能力,还要承担起越来越沉重的照护责任。
从拿到诊断书到克拉德离世,在9年的时间里,蓝江慢慢学会了如何打这样一场仗,并把这一过程写成《阿尔茨海默病先生的妻子》一书,该书中文版于2023年11月出版。她在书中强调,“高尚从来不是我的目的,选择怎样的照护是个人自由,这只是我个人的选择。”
2023年11月,回忆这段漫长时光时,她喜欢谈论那些留给自己的“一小时”,在那样的时间里,她把克拉德放到其他的照护者或机构手中,自己得以短暂喘息、充电,这是支撑她完成漫长照顾的“蜜糖”,也是她对照护的独特认识,“依恋是没有尽头的,我有一个自我,这样才能持续。”
蓝江出生在上海,80年代赴美工作、定居,现在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她的丈夫克拉德生前是美国某大学董事会顾问,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9年后离世。
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以为这关乎感动与高尚,而蓝江从一开始就打破这一印象,“高尚从来不是我的目的。成为一名照护者也不曾是我的初衷,但当所爱之人患上不治之症,我责无旁贷地挑起了这副重担——我是阿尔茨海默病先生的妻子。”
没有生计的被迫,也非道德的规训,蓝江是自己选择成为这样一名照护者的,“我有得选。”她几次补充。
第一次听到丈夫患病的消息时,蓝江形容,“‘阿尔茨海默病’从千里之外朝着我袭来,像一个重量级拳击手,一拳击中我的脑袋,打得我头晕目眩。”在这之前,她身边没有患阿尔茨海默病的人,所听说的也是照护家中长辈、老人。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因高患病率、高死亡率和高疾病负担等,成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该病具有不可逆性,目前所有治疗手段都只能延缓疾病的进展。就像一条下坡路,人们穷尽各种努力,也只是让下滑的速度慢一点。据央视网消息,截至2019年,我国约有1000万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数量居全球之首,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主的老年痴呆疾病发病人数持续增加。
这是一种在活着的时候不能够100%被诊断的疾病,只有死亡以后通过对大脑的解剖,在显微镜下面才能准确判断,彼时患者的神经已经被不能排除出去的“废物”堵塞,新的神经链无法连接,因之大脑不“生产”新的记忆,这也是克拉德一遍遍发出“我要回家”的原因——他对“家”的记忆消失了。
在一次次的绝望中,蓝江坦言,是记忆中丈夫曾经的好,帮助自己在两人共同度过的余下岁月里,在丈夫的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混乱和落寞中,得以始终保持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发生的一切。
东西乱放、重复提问,甚至大小便无法自理,她形容那些绝望的时刻为“理性与非理性的战争”。蓝江找不到任何理由告诉克拉德,“告诉他有一个可怕的不可治愈的退化性疾病,是这个疾病让他感觉到种种不存在的危机”,对丈夫说出这些真相可能会使自己感觉痛快,但他需要的是安慰和安全感,而不是真相。
蓝江慢慢调整好自己,融入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奇异的思维世界,在那里,幻觉和扭曲取代了现实。时间带来的转变是缓慢的,后来蓝江能够平静地面对混乱,甚至坦然地笑对克拉德那个荒谬的世界,她称之为“那个已被我们共有的世界”。
“给我一件活儿干。”克拉德又开始了他的重复,像一根缠在狗毛里的蒺藜子般黏着,令蓝江无法摆脱。蓝江找不到使丈夫安静下来的办法,直到护工查理的出现。
查理会故意找一些琐碎、安全、耗时的小事,请克拉德帮忙,之后热切地称赞和感谢克拉德的“帮助”。蓝江确信克拉德是无功受禄。不过他的认真努力确实值得称道,她在书中写道:这位前大学校长全神贯注地做着鸡毛蒜皮的家务活,卖力地完成任务,好像正在全身心地投入一个数百万美元的重大科研项目。
阅读是克拉德一生中最大的爱好,但此刻他已经丧失了阅读能力,也无法理解大多数电视新闻或脱口秀节目。而他的身体却仍然强健,精力充沛的他像笼子里的困兽一样在房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试图弄清楚自己在哪里,该做些什么。好几次,一不留神他就走出家门,迷路了。
种种举动让蓝江觉得自己不被理解,她知道丈夫病了,但在一些时刻无法接受爱人這般对待自己,“理性上的理解并不能够抹杀感情上的需求。”
蓝江曾把丈夫交给一家养老照护机构,在那里,克拉德和另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女性发展出依恋关系,他们会牵手、作伴,从表面看似乎是对方的“爱人”。

在定期看望之余,蓝江空闲时读了《达芬奇密码》,悬疑小说是她最好的庇护所,她补充,还看了些催眠的园艺目录。她喜欢园艺,喜欢看着生命生机勃勃的样子。
当患病的克拉德进入公共谈话的领域,经常是他加入聊天后,所有的人都感到茫然无以应对,因为他在“奇异的思维世界”里说的话常常无法被理解。这时候,蓝江往往感觉自己的心绷紧了,“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残疾儿童的母亲。孩子天真无邪,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母亲太清楚了。”她要保护她的孩子免受赤裸裸的、残酷现实的伤害。
蓝江不愿意让丈夫克拉德的疾病限制她的想象力,阻止两人做仍有可能一起做的事。后来,她带着患病的克拉德,走访他早年生活过的地方,拜访他的朋友,这可以强化他的记忆,“也为我创造新的记忆。”蓝江穿过马路,看着面前的人来人往。她带着“战胜”的心态,带着丈夫走入人群。
她提到马克·吐温的一句话:“在搏斗中,狗的大小并不重要,狗的内在战斗精神的大小才是最重要的。”蓝江称,自己的内在战斗精神有着令人生畏的规模。“我奋力前行,在旅途中面对克拉德的各种功能的减退,他使用厕所时的艰难,他饮食时引发的混乱……我顽强地决心创造我们所能创造的记忆,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寻找最好的方式,尽可能充分地感受生活,不留遗憾。”
蓝江说,在家中照顾克拉德的日子“占据了我的日日夜夜”。她像一个溺水者挣扎着获取空气,渴望在一个更繁忙的秋季学期开始之前,有机会从无休无止的烦琐看护中逃脱几天。工作给了她几乎唯一的正常生活的空间,是一帖调剂情绪的良方。
照顾克拉德的生活经历像极了蓝江记忆中童年时上海的冬季:多云、寒冷、陰暗和潮湿,连绵不断地刮风下雨,偶然出现蓝天和阳光。她有时也会陷入虚无的思考:想知道是否真的是上天在惩罚我,在克拉德生病前给了我们超乎寻常的幸福,现在又把幸福从我身边夺走,从而平衡了我该得到的幸福的份额。
如何让照护可持续,蓝江的方法是“永远记得留给自己一小时”。蓝江认为,前提是不要把自己放到受害者的位置,这样才能看到照护中的可爱。
随着照护日久,蓝江渐渐明白美国诗人玛雅·安杰卢的意思了,安杰卢曾说,“我们可能会遭遇很多失败,但我们绝不能被打败。”她不能阻止克拉德的阿尔茨海默病的恶化——没有人能够——“但我可以选择希望,希望我能在经历磨难后,不是成为一个令人怜悯的受害者和失败者,而是淬火成钢,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人道主义愈加坚定不移的人。”

在蓝江看来,停留在感动层面是廉价的,应该关注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具体生存状况,关注到他们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不一致的情况。
比如,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餐馆会把食物和饮料洒得到处都是。克拉德曾从坐在他旁边的陌生人的盘子中拿食物,这发生在飞往中国的航班上;克拉德还会在电影放映中大声说话,在集体活动时让别人等待,甚至会出现更糟糕的情况。
因为这些原因,许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健康配偶选择完全避开公共场所,随之而来的是患者和照护者被社会孤立的状态和精神抑郁。蓝江不同,她一直在努力防止陷入这样的状况,“因为它们破坏我的幸福,让我质疑生命的价值。”
同样作为照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健康配偶,哈佛医师、医学人类学奠基人凯博文照护患病妻子10年后,用亲身经历书写了《照护》一书。面对一场终将“失败”的战斗,我们该如何抗争与坚持?
凯博文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相当危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高质量照护已经受到了威胁,无论是家人之间的照护、医疗行业的照护、医院或养老院里的照护,还是存在于整个社会中的照护。一种反照护的社会风尚,已经弥漫开来。而我们的经费又经常捉襟见肘,很难满足照护的各种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照护无疑受到了影响,甚至被误认为是软弱与矫情的代名词。
但在凯博文看来,照护可以是某种人性的胶水,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社会紧紧地黏合在一起。照护能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讲故事,关于我们是谁、我们该如何生活的故事。可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我们却在减少照护、贬低照护,甚至把它作为某种牺牲品,送上了追求经济与效率的祭坛。这个祭坛正在不断削减着照护的资源,却反过来要求家人和医务工作者倾其所有,甚至要将照护的意义从医疗服务中驱逐出去。照护——这个讲述着人类经验、讲述着人性苦难与疗愈的道德语言,曾经奠定了我们共同存在的基础,如今却被死死地扼住了咽喉,甚至将迎来消亡。
让患阿尔茨海默病的丈夫进入人群,蓝江甘之如饴。她觉得这正如欧美经典歌曲《甜蜜的梦》里所唱的,“我环游世界和七大洋,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东西。”归根到底,我们不都在寻找同样的东西——以最好的方式与亲人共度时光。
《阿尔茨海默病先生的妻子》一书的编辑木木说,书中最打动木木的,是“家,甜美的家”这个章节,里面写着,患病后的克拉德,某些时候从精神上重返了自己的儿童时期,反复对蓝江提出回家的要求,哪怕他们此刻就处在他们曾经最温馨的家里。蓝江从刚开始的幽默应对、耐心解答,到逐渐崩溃、发泄,到沮丧,内疚……她笔下的这种感受太让人感同身受了。照护者并不是机器人,也不需要是“完美”的照护者,也应该允许自己有情绪,并给自己机会找到情绪的出口。而同时,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这种对“家”深切渴望又求之不得的心情,让人非常真切地感受到疾病带给人的痛苦,思考我们在生活中终将面对的“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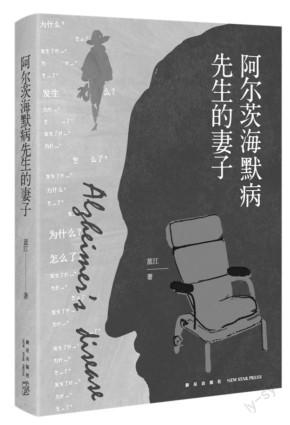
克拉德离世后,蓝江继续她的旅途。她喜欢探险家的故事,打开手机给我看不久前去南极看企鹅的照片。此时我们走到上海市图书馆,那是她小时候经常来的地方。青少年时期,蓝江爱看的书是《战争与和平》,她相信如书中所写,哪怕再艰难的境遇中,也能找到一朵花去欣赏一番。
午后的图书馆外,阵阵桂花香袭来。蓝江想起在上海生活时,美国电视剧《草原上的小木屋》(1980年代曾在中央电视台播放)风行一时,但她当时没看过。看这部剧的时候,蓝江已是中年,在美国的家中和克拉德一起。
她一直记得电视剧中的女主角劳拉·英加尔斯说的话:“我知道会有河要穿越,有山要攀爬。我很高兴,因为这是一片美丽的土地,我为能看到它而感到欣慰。”
蓝江补充,“我们都知道那就是生活”。

